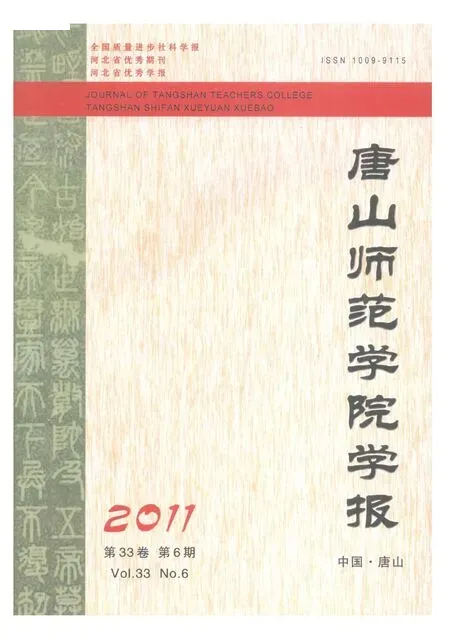江永的古音学开创性辨析
王树江
(北京师范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5)
江永的古音学开创性辨析
王树江
(北京师范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5)
江永是清代有名的古音学家之一,但是前人的研究大都认为他是继承顾炎武而来的,通过分析江永的声、韵、调研究来探究他的古音学思想,考察江永在古音学上的开创性,认为江永对古音的研究是古音学研究上的关键。
古音学;江永;开创性;地位
朱晓农在其《古音学始末》[1]中明确提出:“我们把顾氏以前的古音学叫做‘古韵学’,顾氏到高本汉之间的古音学叫做‘古音学’,高本汉以后的研究称为‘音韵学’。”但朱先生并没有具体展开。通过考察吴棫以来的古音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古韵学”的研究对象是以《诗经》、《楚辞》等群经韵文为主;所谓的“古音学”,是除了韵文研究之外,还包括声纽研究和声调研究在内;所谓“音韵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与现代语音学的结合,使用了内部构拟法来研究古音。朱先生的观点在传统古音学史研究中具有创新意义的。
古音学研究始于宋代吴棫,明代陈第为一变,后经昆山顾炎武,清代学者研究都宗顾炎武。顾炎武固然是开了清代古音学研究的先例,但是从他的考证内容来看,还是注重于韵文的押韵情况,并没有注意古声的情况。虽然李葆嘉说顾炎武有古无轻唇的观念,但是我们不认为顾炎武是有这个观念的。首先,顾炎武的例子都是零散的,没有系统地来论述。这正如我们说虽然许慎已经注意到了声兼义的情况,但是真正要提出右文现象的只能是像杨泉的《物理论》中的类聚以明才能算作明白了声兼义的规律,所以我们不认为零散的例子能够支持顾炎武的“古无轻唇”观点。其次,虽然罗常培说“黄先生谓:古声数之定乃今日事,前者顾亭林知古无轻唇……(?)”但是这个问号说明了是有问题的。要么就是罗认为黄侃有误,要么就是罗对此记不太清,故疑之。最后,顾炎武的说法都是以随文作注的形式出现的,对他的处理只能说如同郑众的六书理论不为后世所采用一样,是不能归于理论层次上的。总之我们可以赞同黄侃在《尔雅略说》里所言的“古声类之说,萌芽于顾氏”,但是顾氏没有进行古声纽的考究是十分明了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顾炎武还属于古韵学研究阶段。真正对古音学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始于顾炎武之后的江永。江永是清代古音学研究局面的真正肇始者,他的著作宏丰,最著名的有《古韵标准》、《四声切韵表》和《音学辨微》等,在这三部著作里,江永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古今音观念以及声纽、韵部、等第与古音的关系。
一、江永在古韵学基础上的开创性
前人的古音学研究只是重视韵文的采集和一部分谐声方法的运用,这样的研究方法是每一个考古派都利用的,但是到了顾炎武时代,他已经基本上做到了古韵学的极点,如果再有研究者寻这条路,那么势必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江永率先确定了对古韵进行审音的研究方法。
江永《古韵标准》里系统论述了顾炎武的得失,认为顾炎武“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顾炎武是考古派的代表,他在《音学五书》里已经把《诗经》、《周易》的古音进行了系联,并且以此来考证《唐韵》里的韵字归类问题,最后形成了自己的古韵十部,这是他的考古结果,而没有从音理上离析他们。但是顾炎武的考古结果中对《唐韵》的离析都是正确的,例如:他把平声支韵析为二,一属歌部,一属脂部;尤韵析为二,一属脂部,一属萧部;麻韵析为二,一属鱼部,一属歌部;庚离析为二,一属阳部,一属耕部。这些离析结果都为后来学者所承认。顾氏又将入声韵离析:
屋分三支,一归脂部入声(职部),一归鱼部入声(屋部),一归萧部入声(药部);
沃分二支,一归鱼部入声(屋部),一归萧部入声(觉部);
觉分二支,一归鱼部入声(觉部),一归萧部入声(药部);
麦分二支,一归脂部入声(职部),一归鱼部入声(铎部);
昔分二支,一归脂部入声(锡部),一归鱼部入声(铎部);
锡分二支,一归脂部入声(锡部),一归萧部入声(药部);
药分二支,一归鱼部入声(觉部),一归萧部入声(药部);
铎分二支,一归鱼部入声(铎部),一归萧部入声(药部)。
江永没有满足于前此研究,而是通过审定音读的侈弇,将顾炎武的真部,分为“口敛而声细”的真部和“口侈而声大”的元部,将顾炎武的宵部分为“口开而声大”的宵部和“口弇而声细”的幽部,同样和真元问题一样的侵、谈二部也一样依这个原则分成了两部,同时在他的《四声切韵表》里明确地标明了古音的等次在今音中的演变规律,这是顾炎武之前所有的古韵学家所没有考虑到的问题。在江永之后的戴震就利用这个原则,他在《答段若膺论韵》中曾经提到江永的分韵方法,又据此方法而批评段玉裁①,从而又进一步提出了“同呼而具四等者二”的理论,并且还在《四声切韵表》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审音,从而单独列出了更加系统化的古音等次,后人在研究古音学时,无不考虑中古音与上古音的等次对应关系,这不得不说是江永的一大开创。
二、江永在古声学上的开创性
江永的开创性不仅表现在他的古韵学原则上,更重要的是他的著述中所反映的古声学思想。江永在《古韵标准》和《音学辨微》中都阐明了很多古声钮的相互关系。这对后人的古声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1. 关于轻重唇关系
江永《音学辨微》对轻重唇的关系有一段很精彩的描述:
轻唇重唇,音每相转。“不”之为“弗”,邦、非转也;“勃”之为“艴”,滂、敷转也;“冯依”之“冯”为姓氏之“冯”,“风帆”之“帆”今读如“蓬”,並、奉转也;“无”之为“没”,《春秋》“筑郿”亦作“筑微”,释氏有“南无”之“无”音“模”,即《穆天子传》之“膜拜”,皆明、微转也。[2,p70]
传统认为钱大昕是最早提出“古无轻唇音”学说的,但是在他之前,已有人认识到了轻重唇之间的关系,江永就是其中之一。李葆嘉《清代上古声钮研究史论》指出江永之前的顾炎武就有“古无轻唇”的观点,但是我们不认为他已经有了这个观念,上面已经说明。另外,江永在以《切韵》系统为基础的基础之上来论证他们的关系,这点在系统性上要比钱大昕高明。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所举的例子,江永所指出的都在其中,可见钱大昕是继承了江永的这个观点,只不过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古无轻唇音”的说法而已,却也没有证明为什么。其实对照这个观点,我们宁可说是轻重唇有密切关系,而且我们现在用的也是这个关系,不是他的结论。
2. 关于舌头舌上关系
刘熙《释名》云:“天,豫司兖冀以舌腹言之,‘天,显也,在上高显也’;青徐以舌头言之‘天,坦也,坦然而高远也’。”舌腹,今人所谓舌上也。“天”字分明是舌头,乃有以舌上呼之,方音之不正者也。朱子《楚辞辨证》“论九歌灵何为兮水中”之“中”,云:“此处人以‘中’为‘当’”,是呼“东”韵为“阳”,“知”母为“端”,舌上如舌头也。安溪李文贞公光地谓闽广人知彻澄犹作舌音,意其如此类耳。《仪礼·觐礼》“匹马卓上”,注:“卓”读如“卓王孙”之“卓”。盖马之“卓”者其颡白,即《易》所谓“的颡”。古音“的,都药切”,而姓氏之“卓”,汉人亦读为“都药切”,不如今音“竹角切”也。明朝李贽字“卓吾”,其乡人呼之为“笃吾”(见《李氏文集》),此亦以“知”母为“端”母,而“笃”字方音亦有“都药切”之音也。又《诗》“伐木丁丁”之“丁”,转“都经切”为“知经切”。田齐本陈氏,后改姓为田,此音舌头舌上音相互。而唐人反切有“类隔借母”之法,以“长幼”之“长”为“丁丈反”,亦此类也[2,p70]。
江永认识到了舌头舌上是有关系的,又认为二者是可以转化的,具体转化的方向,现在学者一般认为江永的转化没有代表他的观点是上古没有舌上音,是一种不科学的“音转”观。但是仔细阅读他的这段论述以及全书的体例,我们就可以明白,江永确实是认为古今音舌头是转舌上的。首先,他的这个论述是在正音,具体说就是在纠正当时方音的读法,遵从韵书系统来读,是想统一学人的研究辨音方法,并不是在讨论古今转变的问题的,学者认为他泥于“三十六字母”而不知声之流转,这是没有明白他这段论述的目的的缘故。其次,我们从他所说的“古音‘的,都药切’”,“转‘都经切’为‘知经切’”中不难看出,他是承认古音是端之类的舌头音的,而现在读音是知类的舌上音,并没有明确指出古音也有舌上音。另外,在他的《音学辨微》的“十一辨婴童之声”条下说:“能呼妈,唇音明母出矣;能呼爹,舌音端母出矣;能呼哥,牙音见母出矣,能呼姐,齿音精母出矣”,再加上“影”“喻”二母是人之元声,可以推想,江永为什么不言“非”组、“知”组、“照”组呢?比较合理的推论是,江永知道人初之元声应该是有上面几组音,而不是有下面几组音,这也可以印证他不是不知道“舌头舌上”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的。江永的这个思想对后代的戴震、黄侃影响很大,黄侃在对古声纽的研究过程中,始终没有把喻四拿出来归入定,而是附着于影,就是笃信江永之论述的结果②。
从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中也都能看到江永举的例子。在此之后,研究古音大都是审音考古并重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江永对于“舌头舌上”的论述是具有开创性的。
3. 关于照系二、三等的问题
关于照系二、三等的问题,一般而言,都认为是陈澧的《切韵考》才始分开,但是在江永的音学观念里,照系二、三等已经有了分别,这和他分析《广韵》的《四声切韵表》是分不开的。江永《音学辨微》反复强调照系二、三等应该分开的问题。他说“照穿床审禅之二等三等不相假也,喻母之三等四等亦必有别也”[2,p73]又在所列常用反切上字表照组下注曰:“右正齿音唯禅母专三等,照穿床审四母二三等不通用。”[2,p75]这说明江永在照系二三等问题上是十分清晰的,后来陈澧的《切韵考》从实践上证明了他的观点。陈澧影响了黄侃,在江永明确区分照系二三等问题的同时,也看到了照二与精组的关系以及照组与知组的纠葛,他说:“方音呼二等之照穿床审似精清从心者非正音”,“知与照,彻与穿,澄与床,易混者也”。这两条加之上面力主照系二、三等分开,另外,前文已经说到的他于人之元声根本没有提及照系,对于后人研究照系有很大的启发性。黄侃虽然师从章太炎,但是治学风格完全不同于其师。所以说,江永在解决照系问题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启发性功建。
三、江永在古调类上和韵尾分类及其关系上的开创性
江永在对待古代声调的问题上,认为“四声虽起江左,案之实有其声,不容增减,此后人补前人未备之一端”,而且他认为四声是可以通押的,出现通押现象的原因是因为“随其声讽诵咏歌”。在江永之前陈第已经指出前人在押韵的韵脚字上随叶改定音读的做法是错误的,但是江永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古人四声通押的现象和原因的。
另一方面,江永在对待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的关系上比顾炎武之前发生了质变。顾炎武之前的古韵学者认为,阴声韵和入声韵是一样的,因此他们往往是把入声韵附属于阴声韵,因此造成之前和之后的考古派学者大都是只明白阴声、阳声的对转,而不知道入声应该对立和阴声也是对转关系,当然这和他们的考古作风是分不开的。江永在《音学辨微·凡例》里指出“数韵同一入,犹之江汉共一流也,何嫌于二本兮”。他的这个思想,使他在考察古今音的时候,十分注重阴阳入三声的相配。于是江永就把《广韵》中无入声的韵配以阴阳声,如在他的《四声切韵表》里把“祭”配“薛”“仙”;“泰”配“曷末”和“寒桓”;“夬”配“辖”“山”;“佳”配“麦”“耕”;“皆”配“黠”“删”等等,这样江永利用这个原则就把《广韵》里的阴声韵全部配有了入声和阳声,这是前代研究者所没有认识到的。但是,十分遗憾的是,江永没有来得及思考或者没有人和他讨论,使他没有能够彻底贯彻这种想法到他的《古韵标准》里,从而使他的入声分部里的“锡”部、“质”部、“职”部、“月”部找到相应的阴声韵和阳声韵。
在处理韵尾的问题上,江永起到示范性作用的是他把入声独立出来,放到阴声、阳声的后面,形成入声八部,段玉裁为《音学十书》作序曰“婺源江氏又析为十三部,其入声八”,王力、李葆瑞都认为江永其实已经把入声独立出来了[3],尤其王力直接讲明,江永的古韵分部其实是二十一部。虽然现代学者研究认为江永的入声是不独立的,理由可能是江永把入声放在后面,没有像顾炎武那样直接给出明晰的表来表示,实在是在讨论韵字的问题,有点像顾炎武的《唐韵正》。可是,我们可以看出,江永确实又把某韵该分,某几韵当合标得很清楚,而且顾炎武的《古音表》讨论时也有列字情况,江永只不过是把这两个工作合在一起做而已。因此我们认为,江永的入声确实已经独立出来了。退一步讲,就算是没有独立出来,也不能否定江永在入声处理上的开创性,因为顾炎武之前是没有任何学者将入声独立作为一部分进行考察的。江永的入声独立,给后人以很大的启发,戴震就是在江永的启发下,又进一步使阴阳入三声形成对转的局面。段玉裁的“支”、“脂”、“之“三分,除了他具有的考古之功以外,我们认为,未必不是在江永的基础上看到三部入声韵的区别才将三部相分离的。从以上几个角度来看,江永在古音学上确实具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认为,前人对江永的地位认识得还很不够。
综上所述,江永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利用了自己的审音原则,为古音学的研究打开了全面研究的局面,从前人的韵文韵脚归纳泥淖里仗着审音的拐杖走出来的江永,实在一个伟大的古音学家。他开启了古音学研究的新天地,为后世古音研究者提供了治古音学的途径,使得“后学转精”,使乾嘉一派音韵学者不断得以完善,从而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学术高峰。我们可以说,江永是古音学研究史上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著名古音学者,他对后人研究的启发性还很多,但是对于江永的研究还很不够,我们真心希望学者再来重新认识这个古音学史上的巨人。
[注释]
○1 戴震的《答段若膺论韵》说:“仆谓:‘审音本一类,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有不相涉,不得舍其相涉者而以不相涉为断。审音非一类,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始可以五方之音不同,断为合韵。’”在这里戴震明确提出了审音应当是前提,不同意段氏的考古观,是为江永审音方法之影响。
○2 见《黄侃声韵学未刊稿》。按其所说,黄侃在同曾运乾进行讨论之后,同意了喻三与匣纽的关系,但是直到最后,黄侃也没有把喻四分出来放入定,我认为原因大概是一是因为喻四和定之间还有未定的疑案,二是受江永人之元声之影响,喻确实和影是人的原初声纽。
[1] 朱晓农.古音学始末[EB/OL].http://www.pkucn.com/ viewthread.php?tid=5122.
[2 ] 江永.音学辨微[M].续修四库全书本.
[3] 王力.王力文集[C].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304.
(责任编辑、校对:郭万青)
The Pioneering Study of JIANG Yong's Ancient Phonology
WANG Shu-ji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Jiang Yong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phonologists in the study of ancient phonology in Qing Dynasty. But most previous researchers say that his study inherites from GU Yan-wu. Jiang Yong’s pioneering thought in ancient phonology is studied by analyzing his theory about the consonant, rhyme and stress. It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Jiang Yong’s research is a key factor in the research of ancient phonology.
ancient phonology; JIANG Yong; pioneering; status
2009-11-06
王树江(1984-),男,河北涉县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训诂学。
H109.2
A
1009-9115(2011)06-002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