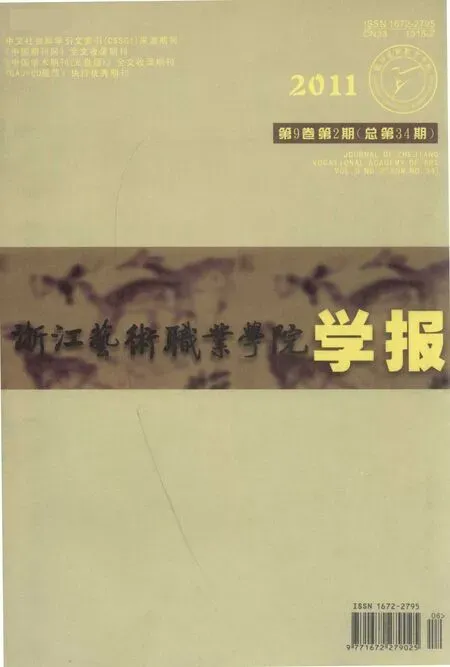当代小剧场戏剧漫谈
孟京辉
小剧场戏剧漫谈,为什么是漫谈呢?我就先从小剧场开始。说到小剧场,大家想到的就是在一个小空间里演出的话剧。这个话剧一般来讲谁也看不太懂,你也不用看懂,因为这个事情在80年代的时候差不多就发生在北京和上海,开始有了。为什么变成小剧场呢?因为你如果在大剧场里演,没有那么多观众,没有人理解在那么小一个空间里会有戏剧,它的表演是什么样的。然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到90年代再到现在,这么20年左右的时间里,小剧场发生了很多变化。从它的发生、发展,从它的壮大,各种各样,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出现了。但是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归结为小剧场。1995年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去日本参加一个导演的会议。大家都知道日本的英文本来就不怎么样,不怎么好,他们翻译小剧场叫little theatre,就是小的剧场。这个就太偏颇了。实际上从整体来讲,小剧场在英文中准确的翻译叫experimental theatre,就是实验性的剧场。这个应该追溯到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
大家知道,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整个世界风起云涌,“冷战”也开始了,各种思维、潮流、思想也就在全世界各个范围内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交错、交织。那个时候在美国最著名的就是反战运动、嬉皮士运动。与当时的整个美国生活相关联的戏剧就出现了一种小剧场运动,以生活剧团、开放剧团、理查·谢克纳、辣妈妈剧团开始的,和当时的政治社会生活一样,来反抗当时主流已经拥有的成果和拥有的社会资源方式。然后,在那个时候,年轻的新一代的艺术工作者突然出现了非常多的艺术创作。在百老汇之外、外百老汇之外,占据了外外百老汇,或者说非常实验的空间和剧场,有点像北京的798。那个时候出现了特别多不同的戏剧,产生了不同流派的戏剧。整体最突出的就是导演,各种各样的戏剧团体都以导演为先锋冲击力量的核心。这是一大股力量。它的成果从七八十年代一直到现在,甚至影响了百老汇的主流戏剧,以至全世界最富生命力、最有活力的戏剧,影响了整个世界戏剧的发展。还有,整个欧洲戏剧在七八十年代之后,在八九十年代,在欧洲形成了强烈的实验戏剧的模式,在德国、英国、比利时、荷兰,都出现了非常强有力、特别有创造力的戏剧大师。德国有非常著名的皮特·斯丹,专门做戏剧的。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开创了舞蹈剧场的皮那·鲍什,他是个舞蹈家,在德国的一个小镇乌珀塔尔,有个舞蹈团,形成了他自己的一整套戏剧风格、流派方式,引领风骚30年,在近30年的舞蹈剧场里,完全影响了众多的人。尽管之前有格林·艾尔,还有很多大师出现,但是他一直影响着当代的世界剧团。
再说到日本。日本在70年代的时候反对美国的安保运动。随着政治运动,以寺山修司、唐十郎、黑战壕、红战壕这几个剧场为主的年轻剧团,七八十年代开始在日本的小剧场运动中,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创造力。
还有台湾。台湾8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新浪潮的小剧场运动,有很多小剧场出现。那么,整个世界范围,在20世纪初以现实主义文学为基础的状态下,突然出现了一批年轻的富有活力的导演艺术家和表演艺术家,致力于发展一种全新的舞台表演方式和观演方式,在近60年的过程中,创造了一种新的时代属于他们的新的文学。说到中国戏剧的时候,就必然说到全世界范围内受到上述戏剧影响的戏剧。真正权威的说法是,100年前,真正的话剧。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厉害极了。布莱希特、伏尔泰,中国的戏曲对他们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中国影响了他们。但是,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戏剧就是在八九十年代受到了西方美学思潮的影响,在短时间内发生了非常剧烈的流变,风格、样式、导演主体、创作的美学特征、个性化的发展,等等。如果说到中国戏剧整体的纵向发展,我觉得有几个特别美丽的时代。一个时代是100年前,话剧刚传到中国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是爱美戏剧,爱美是英文“业余”的翻译。国外有一些先进的年轻的知识分子,觉得戏曲是一种方式,还有,与新文化运动齐名的连接西方的一种新的方式就是爱美戏剧,在北平、上海、重庆、成都几个重要的城市,发生了自发的学生演剧运动。第一次把国外的表演方式带过来了。第二个最美丽的时刻,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放下你的鞭子》。有良知的艺术工作者认为,戏曲是可以拯救我们的生活,介入社会的。那时候有街头戏剧,各种各样完全不同的样式出现了。另外就应该首推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像《茶馆》就出现了。《雷雨》是二三十年代在爱美戏剧之后的专业戏剧。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是样板戏,它结合了西方的形式和中国传统的根。八个样板戏,我认为是戏剧美学发展的非常辉煌的时代。到了后来,就是最重要的一段时间,是我们可以辨认的,也是可以探讨的,每个人都触摸到的戏剧时代就是改革开放后,1978年之后。从文学上讲,是伤痕文学。之后就出现了一批戏剧,《于无声处》,就是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初的戏剧作品,非常好的作品。
应该说1978年之后,中国突然向世界敞开了大门,世界上的各种流派、各种美学思潮一股脑地进入了中国。当时我正好是80年代的大学生,那时候我们像海绵一样吸收西方各种戏剧、文学、美学、美术各种艺术思潮。那时候像新小说派、荒诞派戏剧、未来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小说,所有东西一股脑地进入了中国,80年代中国的戏剧就开始了小剧场的成长期,到了现在将近30年了。小剧场艺术的发展正好是随着整个戏剧艺术的发展而壮大成长的。到现在,中国已经有好几个非常好的小剧场的孕育的温床,一个是北京,一个是上海。这也跟两个地方的文化生活以及在整个中国社会和改革开放中的位置有关。北京的小剧场运动、上海的小剧场浪潮在最近的十年发展得越来越快了。我说的小剧场,为什么加上“当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指最近十年的小剧场。说到小剧场,更多的是我个人和中国当代小剧场的关联。我也正好是在当代小剧场这个环境中成长、吸收的,从没有发言权,到发言多,到胡言乱语,到走了一道弯路,又勇敢地往前冲,头破血流,最后到现在这个状况。我现在就简单说一下我自己是怎么和当代小剧场发生联系的。
我是学文学的,80年代初,1982年上的北京师范学院的中文系。我们上学的时候接触的最多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美术,一个是文学。文学就不用说了,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有梦想,每个人都想成为文学家,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文字会印在报纸杂志上,会成为历史的永久的丰碑被人们记住。我当时在上大学的时候,就两个愿望:一个愿望是获诺贝尔文学奖,一个愿望是建一个巨大的足球场。后来我发现这两个都离我太遥远了。我在差不多12年前就再也不看中国足球队,因为我知道在最关键的时候……我估计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我觉得没有必要把自己的生命浪费在一个很悲哀的事情上。只要是中国足球队,在一个很关键的场次,说只要打平就可以出线,它准输。这个就太奇怪了。我记得在1996年的时候,我和演员郭涛还有好几个朋友一块儿看足球转播。刚开始就说我们还有希望的,一个90分钟的比赛,刚开始转播都气宇轩昂的;到中场休息的时候就输了两个球,就说我们要总结经验,不过我们还有机会;等到最后5分钟的时候,输局已定的时候,解说员就说我们的路还很长很长。后来我们就乐了,就在这么短的90分钟,人的变化就这么快,而且他的语言、语境变化得这么强烈,也就中国足球队能产生这种戏剧性的效果。我们就想中国足球队有一点点问题,我们就别再关注了。但是,我又从事了一项和足球特别相似的职业,就是戏剧。因为戏剧一般来讲也是90分钟,也是需要人配合的,进门的一瞬间就是戏剧的高潮;英国足球队的表演和巴西足球队的表演不一样,一个更加漂亮点,一个更加实用点,这就是两个足球队的风格。戏剧也需要风格。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事,我和何院长还聊过。1997年的时候,我见过高行健先生,当时在香港,聊了很多戏剧方面的东西。他当时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实验的东西还是不够的,还应该有更高的角度。给我印象很深。中国在未来的日子里还可以得更多的诺贝尔文学奖。现在心情也平淡了,并不觉得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一个奥林匹克,完全不是一回事。
漫谈当代小剧场,我就说说当时我在中央戏剧学院学导演。我是学文学的,在学校里也写些剧本,也跟着老师导演了几个作品。当时娄乃鸣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有一天,我对他说我想继续学导演。他说,那你就考中央戏剧学院吧。我说,怎么才能考上中央戏剧学院呢?他说,你就去导演系报名就行了。我就去了。导演系当时有个张真先生,我的恩师,现在已经过世了。他当时问我是干嘛的,我说是学中文的。他说学中文的文学就别管了,直接上导演系就行了。我以非常高的写作的高分,但非常低的面试成绩进入了中央戏剧学院。记得当时9个老师坐一排,就我一个学生。那个时候考研究生不那么普遍,就我1个。人家说矮子里边拔将军,都没法拔,就我一个人,就凑合让我上了。因为说到《雷雨》、《茶馆》的时候,我的分析和他们不一样,而且我把时间搞错了。他们问:你觉得《茶馆》经历了多长时间?我说,有100多年吧。全是瞎编。他们觉得这小子有一点点胡闹。但是,由于我的写作成绩、文学全是90分以上,他们觉得这小子可以调教一下,就让我上了戏剧学院。上了戏剧学院以后,我当时最想排的是荒诞派戏剧。现在说起荒诞派戏剧,已经成为中国戏剧吸收国外作品的古典主义的一部分。那个时候,觉得最来劲的东西就是让人看不懂。看不懂就说明比其他人高那么一点,你的知识结构、美学的渗透力,和这些人不在一个系统里面。我记得当时我们在戏剧学院做的最有名的一个戏是《秃头歌女》,是在一个地下室里。《秃头歌女》是法国一个非常有名的剧作家尤金·尤涅斯库,中国有高行健译的一个版本。说的是特别荒诞的一个事实。一位男士和一位女士在对话。男的说:“我叫马丁。”女的说:“我也叫马丁。”“我住在伦敦。”“我也住在伦敦。”“我住在唐宁街25号。”(我瞎说的)“我也住在唐宁街25号。”“我家楼下有个捡破烂的老太太。”“对,我认识她。”“你住在几楼?”“我住在6楼。”“6楼?你住在甲号还是乙号啊?”“甲号。”“我也住在甲号。”“我们俩原来是一家子呀。”说到后来,他们俩就互相拥抱,原来这两个人是夫妻。他用一种奇怪的方式,说一个简单的荒诞的道理。中间有一段叫“感冒”。有个人说了一个戏叫“感冒”,从一个人说到另一个人,说一长串。那是一个冬天。我就让我的演员说:“我给大家说一个故事,叫感冒。”然后就把电扇给打开了。里面一共有四个电扇,我们就想让观众感冒。观众很冷,我们很开心,这有一点点突破。到快结束的时候,剧中有个消防队长说:“哎?那秃头歌女呢?”所有6个演员就把椅子翻倒,翻倒以后每人就保持一个姿势,不动,我的演出就停止了。没有表演了,就定格。定了3分钟的格。观众就不知道怎么了:好好地演着戏呢,怎么就不演了?然后观众就等着,10秒钟、20秒钟、30秒钟、1分钟,有的观众就站起来了,以为结束了。但是又不对,刚刚发生到最重要的时候。有的观众就自己鼓掌,逗演员,演员也不动。我觉得在1991年1月份,特别冷的那个冬天,这3分钟的停顿对中国的小剧场戏剧是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实。那3分钟,什么都没有发生。《等待戈多》里,贝克特有一句话:没人来,没人去,什么也没有发生,太可怕了。我觉得在那个瞬间,中国当代戏剧对观众完成了一次幼稚的洗礼。3分钟以后,瓦格纳的交响乐《众神的黄昏》开始奏响。然后,所有的演员就在撕他的书,互相撞,一些用纸壳做的东西开始坍塌,有人在打着雨伞、念着台词,有人在胡言乱语,15分钟之后,《秃头歌女》的戏就结束了。整个呈现了非常零散的、碎片的、荒诞的状态。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们似乎完成了什么东西。完成了什么呢?不知道,什么也没有。中央戏剧学院1991年的时候,我们的学生做了一个实验戏剧演出季,上演了4个作品,一个是这个,一个是哈罗德·品特的作品,200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剧作家的作品,一个是未来主义的作品,就是《洗澡》的导演张扬导的《黄与黑》,还有一个《风景》,也是哈罗德·品特的戏,都是很小的剧场。
我想暂时停顿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做这种小型的剧场?因为在十几年前的那个时候,整个中国的戏剧状态全部都是现实主义,都是起承转合、故事性的,北京人民剧院的《茶馆》、《雷雨》、《原野》这样的作品,当然也出现了一些其他很好的作品,但基本上戏剧是一种厅堂似的、典雅的、四平八稳的形式展现在观众面前。我们当时作为年轻人,觉得这样的东西和我们自己的生活,和我们感受的世界和整个社会风潮,全面接收各种各样新思潮的整体社会姿态不一样,所以我们开始了自己的创造。之后我们又做了《等待戈多》。《等待戈多》值得说一下,因为我最早出的《孟京辉先锋戏剧》DVD的四个作品里有一个场景展示。是我的中央戏剧学院研究生的一个毕业剧目,主演是现在比较有名的一个演员郭涛,就是演《疯狂的石头》的那个家伙。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叫胡军。他们俩一个演弗拉基米尔,一个演爱斯特拉冈。他们俩当时一个是88班、一个是87班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学生,我把他们俩凑在一起,排演一个跟他们的教学、和以往的表演经验完全不同的戏剧《等待戈多》。《等待戈多》说的是一个叫弗拉基米尔,一个叫爱斯特拉冈的两个流浪汉在树底下等待一个叫戈多的人。第一天来了一个小孩说,戈多今天不来了,明天来。第二天又来了个小孩说,戈多今天不来了,明天来。故事结束了。有时候你看着剧本,施咸荣老先生1965年就翻译了,翻译得非常好。但也有些问题,一些细节看不太明白。但是,一演就能演出来了。我们当时在中央戏剧学院,最早演出的时候是1989年12月的某一天,大家从一个消息里听说塞缪尔·贝克特死了。然后我们就在我们学校的大煤堆上准备演《等待戈多》。当时学院因为氛围的问题没让我们演。第二年,1990年我们又想演,又没演成。1991年,特别热,我们还是演出了《等待戈多》。这个戏是特别典型的小剧场的戏。我们在四楼的一个礼堂演出。把所有的观众请到舞台上,把所有的观众席座位全部抬出去。我带着6个戏剧文学系和舞台美术系的学生一块儿,把整个观众席用刷墙的大白,包括窗户、地面、灯、电扇,全都给刷成白颜色,像个精神病院,然后让演员穿着黑衣服在观众席里演出。演出两个多小时,很热,很沉闷,但在沉闷的进展中,有种被抑制、被憋住的力量慢慢在剧场里生成。结束时,是两个人很无奈地等待未来对他的宣判。我们最后最高潮的阶段,就是爱斯特拉冈拿着他最善用的那把雨伞,把剧场的玻璃全都打碎了,然后他自己趴在玻璃的碎片里说“老虎也有自己的孩子……”大段台词。就演了两场。之后我毕业了,到中央实验话剧院做导演,做了《思凡》。《思凡》就是小尼姑和小和尚成双对,有情人对有情人的一个戏。我们把意大利薄伽丘的《十日谈》合在一起,成了一个新戏。两个戏合在一起的戏剧形式,在之后的《放下你的鞭子/沃伊采克》也是把德国毕希纳的《沃伊采克》和中国的《放下你的鞭子》两个戏合在一起做了一个演出。1993年《思凡》在北京演出了很多场,后来又到日本、香港,演出了很多场。我们准备过一段时间重新搬演这个剧目。
后来的小剧场运动做了各种各样的实践。我认为小剧场戏剧的发展最有生命力、最不计后果、最有冒险精神,而且最能发挥年轻人的创造力想象力,各种各样的美学能力、组织能力、社会渗透能力,比较重要的是,它的实验性的当代戏剧美学的传递这样一个功能。我们现在一直说的小剧场戏剧,最应该说到的是80年代的探索戏剧和90年代的实验戏剧的发展。我始终认为,80年代的戏剧是探索性的,90年代的戏剧是实验性的。因为探索戏剧更多的还是从西方各个风格流派的发展变革中找到方法。到了实验戏剧阶段就不只是方法,更多的发挥了导演个性的东西,与这种发展的联络和联系。个性的东西在实验戏剧里更重要了。换句话说,实验戏剧更注重创作者的创作个性,彰显作者热衷的戏剧美学的运动和潮流性的发展。说到小剧场戏剧,不得不提到90年代初。从90年代初到现在这20多年间,我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导演,我基本上是用几种方式在做我的戏。一种就是大家可能看到的,以《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这样的戏剧发展过来的具有批判性的,具有强烈的社会讽刺、社会批判色彩,战斗性当之无愧,那种直面惨淡的人生、直面社会生活的戏剧。之后还做了相关的戏。另外一个戏不是我做的,是《切格瓦拉》。后来我们做的《两只狗的生活意见》也是沿着这个发展的。另外一种是比较实验的、比较探索性的,比如《我爱XXX》这种宣言性的,当代的视觉艺术、美术潮流结合在一起的。后来做的《镜花水月》,在上海演出过,也在北京和墨西哥演出过的一个戏,根据中国著名诗人西川的诗改编成的一个多媒体戏剧。这是第二条线索。第三条线索是假借中国主流戏剧,在它的发展框架下发扬实验戏剧的成果做出来的,《恋爱的犀牛》、《琥珀》、《艳遇》三个戏。说到小剧场戏剧,我们更多的是往实验性的先锋的发展,但我们在小剧场探讨出来的所有创作痕迹、所有成果最后都服务于、奉献于对当代主流戏剧和当代艺术性严肃戏剧的发展,这个系统里发挥了实验戏剧的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说了这么多,其实大家有的看过,有的没看过。我更想让大家简单地看一眼,我们当时从小剧场戏剧概念出发,在20年前演出了很多场,对我自己也很振奋,也是我戏剧作品里很重要的一个作品《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我们看开头一段和中间一小段。我在旁边做一些简单的解说。
这个戏剧是我们根据意大利诺贝尔文学奖的作者达里奥·福的戏改编的。这个戏很简单,说的是米兰的一个爆炸案,跟当时的无政府主义有关。当时意大利政府伪造了很多证据,推给无政府主义者。主演是陈建斌。我也在里面演了个宣讲人。演出就像一个运动会。每次在演出现场,我们都先画像黑板报一样的东西。这个戏当时我们演出的时候非常奇怪,就是没有一部作品是这样直接说社会生活的。这个戏讲述了警察局长带着的警察甲警察乙两个帮凶,他们在一次审问犯人的过程中把犯人打死了,不知道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我们得把谎言编下去啊。我们怎么编啊,吃保胎丸,打催产素,我们不是这个料啊。”后来从监狱里找了个导演,编这个犯人是怎么死的。演这个导演疯子的就是陈建斌。他第一次编,不对;第二次编,不对;第三次编,不对;第四次编,不对。每次编,警察局长都说不对。在编撰的过程中,体会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所有权力象征的人充满了愚蠢的胡言乱语。最后结束的时候,以鞭笞的态度把最黑暗的东西揭露出来了。这个戏当时在北京演了30多场,场场爆满,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时候还没有炒作,我们也不懂。《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充满了力量,充满了对社会批判的强烈责任感。另外,它的表演和以往的戏剧完全不一样,结合了中国的戏剧表演和意大利即兴喜剧表演,还有学院派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式的表演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表演风格。在这之前是什么让我们想到这种形式呢?当时,陈建斌和我看了一个达里奥·福自己演出的宗教滑稽剧的录像。达里奥·福当时在上千人的大剧场演出,他自己拿了个麦克风,拿不干胶粘在自己胸前,演得漂亮极了,完全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当时,我和陈建斌就震住了,我们觉得完全可以有更自由的方式演出,就像戏剧可以给人的东西一样。然后这个戏剧样式就产生出来了。结果,我们第一次感受到了观众在笑声中得到的强烈的满足。它不是一般的闹剧,也不是一般的小情小调,或者是误会啊,进错门啊,上错床啊这种小型喜剧,不是。是非常大的,非常有力量的,充斥在舞台中。当时我们甩出笑料的时候,就感觉观众的笑像波浪一样从第一排传到后面。在这里面我唱了两首歌曲,一个是根据聂鲁达的诗改编的《我是人民,无数的人民》,另外一个是《你们的思想》,也是抨击小资产阶级无聊的美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