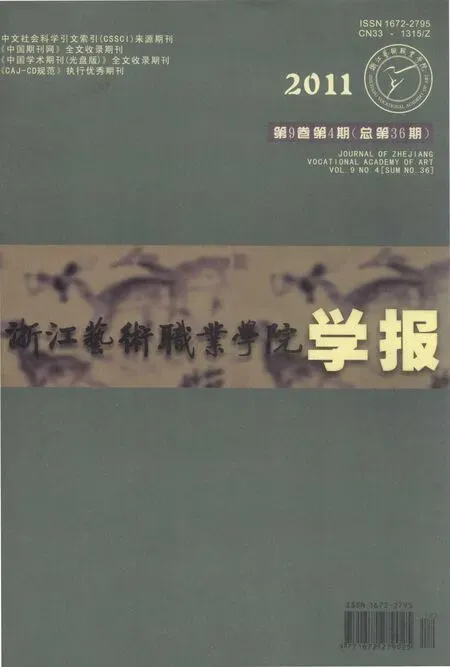自我人格的追寻和完善——论悲剧艺术的特征
陈建娜
悲剧,是戏剧重要的艺术形式。从古希腊戏剧到现代戏剧,悲剧始终占据了戏剧舞台至高无上的地位。虽然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悲剧,从希腊的三大悲剧家的悲剧到现代奥尼尔的悲剧,这之间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我们还是能找到一以贯之的东西,这些就是悲剧艺术的特征。
首先,悲剧是关于苦难和痛苦的戏剧。
没有苦难不成悲剧,正是因为遭遇了苦难,悲剧人物才有了行动,才有了冲突,才造成了流血和死亡。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这个定义中的“行动”,就是悲剧人物面对苦难时采取的行动,因为面对困难,所以严肃。这些苦难,有时候以命运和神的名义出现,如在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命运出现在舞台上方,像是第四个演员,扮演着一个主要角色,它欺骗人、蒙哄人、出卖人,带着冷漠的微笑注视着那位可怜的国王因无知而犯的错误”[1]。有时候,苦难又被归结于人生、社会,如在《人民公敌》、《群鬼》中,社会、人生以冷漠的面孔对悲剧主人公造成巨大的压力和苦难。其实,这两者的性质是相同的,都是外在于人的世界。没有意识、没有情感,外在于人的世界造成了悲剧人物的苦难和痛苦。
哲学家马克斯·舍勒曾区分过人类痛苦的类型,一类是生成的痛苦,即人要成长,要成为自己,要实现自由人格,但是世界阻碍了他,从而产生痛苦。这是一种先知先觉式的痛苦。另一类是匮乏的痛苦,即人的力量太弱小,而强硬的世界气焰嚣张,人成了世界的牺牲品。相对应的,悲剧中的痛苦也有两类,一类是人凭借着自由人格的力量与之做殊死斗争的痛苦,这是关于生命激情的悲剧。另一类是人无法与之斗争或者根本就未曾与之斗争的痛苦,这是关于纯粹悲伤的戏剧,已经偏离了悲剧,走向悲情戏或哀情戏。西方的传统悲剧一般属于前者,通过反抗痛苦产生积极的力量,如《俄狄浦斯王》中的俄狄浦斯、《哈姆莱特》中的哈姆莱特。而中国传统的悲剧则偏向后者,主人公在消极的忍受中使痛苦成为一种毁灭性的力量,如《琵琶记》中的赵五娘、《窦娥冤》中的窦娥。
两类不同痛苦的悲剧,同时也对应了悲剧中两种不同类型的冲突,内在的冲突和外部的冲突。内在的冲突,是悲剧人物内心各种心理力量之间的冲突。如《哈姆莱特》就是一部充满了内在冲突的悲剧。哈姆莱特的复仇延宕了四个月的时间,就是因为他强烈的内心冲突,在每次行动之前,哈姆莱特都要对行动的前因后果进行理性的衡量,都要思考“to be or not to be ”这个问题。《美狄亚》也是一部充满了强烈内心冲突的悲剧,美狄亚在杀子之前的那一段独白,充满了撕心裂肺的痛苦,是同时身为母亲和复仇女神的痛苦的斗争:
哎呀!我的心啊,不要这样做!可怜的人啊,你放了孩子,饶恕他们吧!即使这些孩子不能同你一块儿生活,但他们毕竟还活在世上,这对你也是一个宽慰嘛!——不,凭那些住在下界的复仇神起誓,这样做一定不行,我绝不能让我的仇人侮辱我的孩子,不管怎样,他们非死不可!既然要死,我把他们带到人间,我就可以把他们送回冥界。[2]
所以,内心的冲突就是一个自我与另一个自我之间的斗争,就是关于自我“生成”的悲剧。而外部冲突则是人的精神作为整体同外部世界的冲突,包括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社会的冲突以及人与人的冲突。如《安提戈涅》中,安提戈涅不顾禁令,坚持将哥哥的遗体收埋,被国王克瑞翁处以死刑,她与国王/国家之间的这种强烈冲突导致了她的被毁灭。在中国古典悲剧中,出现的多是邪恶力量与正义力量之间的外部冲突。如《赵氏孤儿》中屠岸贾与程婴等人之间的冲突,就是典型的奸臣与忠臣之间的冲突,恶人与好人之间的斗争。在外部冲突中,往往悲剧人物个人的力量无法抗衡与之冲突的对方,从而遭到毁灭,这就是关于“匮乏”的悲剧。
悲剧中的苦难,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普罗米修斯对上帝表示了忏悔,如果俄狄浦斯的追查适可而止,如果窦娥顺从了张驴儿父子,那么他们所要面对的苦难就自动化解了。但是,这样悲剧也就不成立了。与普通人主动躲避苦难相反,悲剧人物通常都是有意识地主动地承受苦难,从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到哈姆莱特,从麦克白、卡尔到斯多克芒,莫不如此。这种对苦难具有观察能力和深刻体验能力的人的苦难,是所有苦难中最深重的苦难,因为没有被意识到的苦难,对受难人来说也许只是一些皮肉之苦,并不会真正影响到他的内心。并且,正是在对苦难的反抗中,悲剧主人公落入了无罪之罪,陷入了更深一层的苦难之中。在这一点上,俄狄浦斯是最为经典的悲剧,他逃避罪恶的行为恰恰是他犯下重罪的行为。为此,他自残双目,自我流放。
其次,高贵的悲剧主人公,是悲剧艺术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戈德曼说:“悲剧的伟大在于把忍受的痛苦由没有灵魂和意识的世界强加给人的痛苦,变为自愿的和创造性的痛苦,变为由人的有意义的行动对人的苦难的超越。”[3]正是悲剧主人公有意义的行为使苦难成为一种载体,一种展示人类高贵人格的载体。
我们所说的悲剧主人公的“高贵”,并不是指这个悲剧人物的地位和身份。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的悲剧理论都认定悲剧主人公必须是帝王将相、王公贵族,那些经典的悲剧似乎也证明了这个观点,《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主角是天神,《波斯人》是国王,《俄狄浦斯王》是国王,《安提戈涅》是公主和王子,《美狄亚》是公主,《特洛亚妇女》的主角是皇后。但是,这并不是正确的观点。这种观点的出现,是因为人们是被表面现象迷惑了,没有发现这些悲剧主人公背后隐含的真正的共同点——高贵的人格。鲁迅先生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人生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人的生命,不仅仅是肉体的生命,更是具有独立意识和独立人格的生命。一个人的人格是否高贵,并不在于他是一个好人或是一个坏人,而在于他是否具有选择好或坏的自由意志,是否能够把这个自由意志贯彻到底。因为,清醒地意识到自由意志的存在,并且运用自由意志对人生的每一步做出自己的选择,对自己的选择承担最终的责任,这是只有人类才可能有的高贵的人格。在这一点上,一个普通人和一个国王并没有区别。
从这里出发,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像麦克白这样弑君篡位、杀害忠良的坏蛋会成为悲剧史上闪烁着独特人格魅力的英雄。其中的原因就在于麦克白始终坚持了他的自由意志,坚持了自己的选择。这是一场无比艰难的选择,因为在麦克白的心中始终存在着善与恶的斗争,所以他始终存在着一种犹豫、矛盾甚至深感罪恶的心理。如在第一幕第三场中,他刚想到要通过谋杀的手段来篡夺王位,马上就被自己的这个想法吓坏了:
为什么那句话会在我脑中引起可怖的印象,使我毛发悚然,使我的心全然失去常态,卜卜地跳个不住呢?想象中的恐怖远过于实际上的恐怖;我的思想中不过偶然浮起了杀人的妄念,就已经使我全身震撼,心灵在胡思乱想中丧失了作用,把虚无的幻影认为真实了。[4]60
但是,麦克白最终听从了自己内心的意志,并且在自己的意志做出了选择之后,就从来没有把责任推给过给他预言的女巫或者强烈怂恿自己采取行动的妻子,而是勇敢、坚定地对自己的自由意志负起全部的责任,一步一步地在这条血泊之路走下去。这种坚强和独立的人格,使他在最后的孤家寡人式的抗争中也表现出英雄般的悲剧形象:
虽然驳南的森林已经到了邓西嫩,虽然今天和你狭路相逢,你偏偏不是妇人所生的,可是我还要擎起我的雄壮的盾牌,尽我最后的力量。来,麦克德夫,谁先喊“住手,够了”的,让他永远在地狱里沉沦。[4]113
从这一点来说,麦克白具有比哈姆莱特毫不逊色的高贵的品质,他的异乎寻常的坚强意志,使他能够一步一步地成为他自己,而不是另一个虚假的他所不愿意的忠臣的形象。所以,如朱光潜先生所说的那样:“悲剧主角还往往是一个非凡的人物,无论善恶都超出一般水平,他的激情和意志都具有一种可怕的力量,甚至伊阿古和克莉奥佩特拉也能在我们心中激起一定程度的崇敬和赞美,因为他们在邪恶当中表现出一种超乎我们之上的强烈的生命力。”[5]
最后,悲剧尤其是古典悲剧隐含了一个内在的基本模式。
这个基本模式是一个悖论:悲剧人物肯定自我、创造自我的过程同时是毁灭自我的过程;反过来,正是在这毁灭自我的过程中达到了对自我的确认。那些经典的悲剧莫不如此,奥赛罗为了自己的荣誉,误杀了自己的妻子,于是他用自杀真正地维护了自己的荣誉;麦克白听从内心野心的驱使,一步步走向毁灭,但正是在流血和死亡中他完成了自己的人格塑造。尤其是《俄狄浦斯王》这部悲剧,整个戏剧过程就是肯定自我的同时毁灭自我。俄狄浦斯悲剧的根源就在于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一再追问。在怪物斯芬克司那里,俄狄浦斯以足够的智慧回答了“人”这个答案,但这并不够,他还需要完成对自我人格的追寻。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对自我人格追寻的过程。有的人遇到挫折,妥协了,回避了,放弃对这个问题的追问;而悲剧中的主人公则坚持了这个独特的自我人格,他们以不妥协的勇气和无与伦比的力量打败了所有敌对的力量。虽然他们死了,但是他们胜利了,他们用自己的死亡来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证明了独一无二的自我人格。
这种“肯定—毁灭—肯定”内在戏剧结构,就是舍勒所说的,“倘若同一种力量一方面促使某一事物实现它本身或另一事物相当高的积极价值,另一方面同时又是这个作为价值载体的事物惨遭灭顶之灾的原因,这就达到了悲剧性的极致”[6]。就是戏剧家阿瑟·米勒所说的“悲剧是一个人全力以赴地要求公正地评价自己所带来的后果”[7]。所以,所谓的悲剧性,就是以自身遭受毁灭的方式来获取对自身价值的肯定。
值得说明的是,在中国古代悲剧中,这个内在的基本模式有些变化,需要把自我人格替换成伦理人格。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悲剧的基本模式是:一个好人,一个作为某种抽象伦理象征的好人为了坚持这种伦理准则而落难,并且他或她又为了捍卫这种准则进行反抗直至自我牺牲。比如《窦娥冤》中的窦娥就是“节”和“孝”的象征,为了坚持这“节”和“孝”的伦理准则,窦娥被迫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死亡,但正是通过死亡她维护了这些伦理准则。同样,《赵氏孤儿》中程婴、韩阙、公孙臼三人是“忠”和“义”的伦理象征,他们用自我牺牲的方式维护了“忠义”的伦理观念。
从悲剧的内在结构中,我们可以发现观众需要悲剧的真正原因。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六章中说,观看悲剧是为了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得这些情感得到疏泄,这仅仅是答案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悲剧满足了我们对崇高感——作为一个人的崇高感的需要。的确,观看悲剧会让人产生怜悯和恐惧。怜悯是我们居高临下对他人的一种同情感,当我们对悲剧人物产生怜悯时,我们往往把自己提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就像佛祖、上帝那样具有悲天悯人的胸怀。恐惧是由于我们对悲剧情境感同身受而引发的一种情感,这种情感的产生是把自己与悲剧人物放在同一高度。而崇高感则是一种向上的情感,是“一种更强烈的生命力的洋溢迸发”(黑格尔语),一种非凡、伟大和庄严的情感体验。这种情感体验,使我们重新认清了人的价值所在,认识到自我的价值所在。
所以说,悲剧不仅仅激起我们的悲伤、同情、怜悯和恐惧,更重要的是,它还带给人们启迪,关于如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启迪。在一点上,悲剧超越了怜悯,它带给人们希望和光明。“我认为,当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人物在必要的情况下,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而准备献出自己生命的时候,一种悲剧的感情就在我们心中油然而生。”[8]2这种悲剧的情感就是一种崇高感,一种对人的尊严感到骄傲和振奋的情感,正是从这种情感中,观众得到了巨大的安慰和确证,因为他们自身就是属于其中这个类群的。所以,悲剧让人产生幸福的感觉,因为悲剧总是让人不由自主地反观自身,从崇高的状态中体验人格自我的完善。
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清楚地知道自己必定死亡的动物。这种生命的自觉意识,是人类的悲剧意识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如何才能超越死亡、战胜对死亡的恐惧?悲剧以戏剧的方式告诉人们,死亡并不可怕,重要的是人在死亡之前做了什么。从奥列斯特到哈姆莱特,从美狄亚到麦克白,每一个悲剧人物都以其悲剧性的方式提醒人们,生命的价值并不在于肉体本身,而是每个人独特的人格。当我们甚至能够把死亡变为成全自我人格的手段时,死亡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即使牺牲肉体,也要真正地做一回“我”,这个“我”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戏剧家阿瑟·密勒坚定地说:“悲剧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完善的表达手段,表明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必须是什么样的人——或者说应当争取成为什么样的人。”[8]10
[1]阿·尼柯尔.西欧戏剧理论[M].徐士瑚,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132.
[2]欧里庇得斯.美狄亚[M]//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一).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94.
[3]戈德曼.隐蔽的上帝[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109.
[4]莎士比亚.麦克白[M]//外国戏剧经典10 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20.
[6]舍勒.爱的秩序[M].刘小枫,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298.
[7]罗伯特·阿·马丁.阿瑟·米勒论剧散文[M].陈瑞兰,杨淮生,译.上海:三联书店,1987:40.
[8]阿瑟·密勒.阿瑟·密勒论戏剧[M].郭继德,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他者形象的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