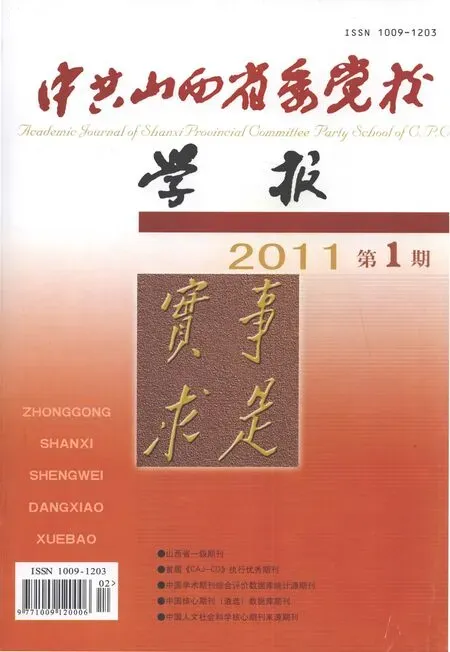反“文化贫困”战略思考
——基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实践
杨丽萍,赵晓霞
(四川农业大学,四川雅安625014)
反“文化贫困”战略思考
——基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实践
杨丽萍,赵晓霞
(四川农业大学,四川雅安625014)
甘孜州文化贫困主要表现在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差、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落后等方面。文化贫困有着强大的辐射力,不仅影响了甘孜州贫困农牧民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生活方式等,还直接造成教育科技的落后和人力资本存量的不足,从而制约了甘孜州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此,应当以政府为主导、以当地民众为主体,采取一些反文化贫困战略,具体包括:注重农牧民自身能力建设,发展教育和科技;重建社会组织体系,推进参与式扶贫;关心文化转型,保护文化遗产。
甘孜州;文化贫困;反文化贫困
甘孜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甘孜州)是集“老、少、高、穷、山”为一体的全国典型集中连片和特殊类型贫困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扶贫开发以来,经过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及启动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新村扶贫、移民扶贫、产业扶贫、劳务扶贫等一系列扶贫工程,甘孜州的基础设施得到较大改善,贫困状况有所缓解,扶贫开发工作取得重大成绩。然而,目前甘孜州的贫困发生率、恩格尔系数等贫困量化指标依然居四川省甚至全国之首,据甘孜州扶贫办统计,截至2009年底,按照过去1 067元的贫困标准,甘孜州尚有贫困人口30.82万人,占全州人口的35.85%,甘孜州的扶贫开发任务仍然艰巨。
长期的反贫困探索和实践证明:贫困绝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或经济问题,更主要的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也就是说,“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价值观念及其生活方式,以及一个社会的文明开化程度,从更深层次上决定着人们是否贫困的命运。”〔1〕回顾甘孜州几十年来的反贫困历程,不难看出,尽管投入了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但是其始终无法走出贫困怪圈。究其根本,更多的原因还“在于自身机体僵化凝固,失去了再生功能,在于不少贫困者本身根本没有构成反贫困的主体,而只是政府和社会反贫困或救助的对象”。〔2〕正是从这个角度,笔者认为,甘孜州的反贫困问题不单纯在于经济扶贫,更在于根治文化贫困。只有走文化扶贫之路,致力于贫困主体的意识提升和能力建设,才能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等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变革。
一、甘孜州文化贫困的现状分析
“文化贫困是指相对于在社会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文化而言,某一社会群体在生活方式、思维与信仰方式,以及知识、观念、习俗和技能上的滞后与缺乏现象。”〔3〕甘孜州的文化贫困主要表现在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差、生活方式落后和价值观念落后等方面。
(一)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差
文化素质是人口素质中的最核心部分,直接反映出一个地区国民的整体受教育程度。甘孜州人口的文化素质差,主要表现在基础教育水平低、拥有的大学生和中学生数量少、专职任课教师人数少以及就业培训落后等方面。
来自甘孜州统计局的资料显示:2009年该州小学阶段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8.3%,“普九”人口覆盖率92.73%(尚有石渠县未完成“普九”),初中净入学率为86.4%,但我们在实际调研中发现学生辍学率和厌学率都处于较高水平。2009年该州每千人拥有的专职任课教师人数仅为8.78人,每万人拥有大学生71.45人,每万人拥有中学生470.13人(数据来源于甘孜州统计局),都与四川省和全国的平均水平差距很大。
在就业培训方面,甘孜州明显落后于四川其他市州。即使与阿坝、凉山两个少数民族自治州相比,甘孜州在创业培训和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方面也处于较低水平。具体数据参见表1(数据来源于甘孜州统计局)
(二)生活方式落后
生活方式落后是最能体现文化贫困程度的参数。生活方式落后主要体现在消费结构不合理、生活条件差和精神文化生活匮乏等方面。
第一,消费结构不合理。由于长期贫困和环境因素等的制约,甘孜州农牧民的消费结构不合理,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比重小,食品消费比重大,主要食品消费种类单一且消费量不足。2009年底,甘孜州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仅有2 229元,而食品支出为1 385元,恩格尔系数高达62.2%(分别高出全国和四川省水平的19%和10%)。粮油类食品、肉禽蛋水产品、蔬菜类食品、干鲜瓜果类食品等主要食品消费量,以及其他生活消费支出如耐用消费品、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医疗保健支出都远低于四川省和全国平均水平。
第二,生活条件差。甘孜州的自然环境恶劣,基础设施落后。据甘孜州政府统计,截至2009年底,全州尚有1 354个村不通公路,1 562个村不通电话,1 679个村不通电,1 153个村没有解决安全饮水,1 435个村未建卫生室。人畜共居也是一种常见现象。每年因包虫病、大骨节病、碘缺乏病、鼠疫、克山病等地方病、流行病和传染病致贫和返贫人口高达25%。
第三,精神文化生活匮乏。甘孜州的文化服务落后,文化产品奇缺。很多地区缺乏供农民农闲时期休息消遣的娱乐场所及娱乐设施,缺乏文化管理和服务人才。据统计,2009年末,全州有文化馆19个,公共图书馆3个,文化站202个。而实际上,很多文化机构实行“一套人马、几块牌子”,正常运作的乡镇综合文化站和文化活动室并不多。此外,尚有1 462个村不通广播电视,农村的广播电视入户率不足10%,许多农牧民多年来听不到广播,看不到电视、电影,读不到报纸书籍,处于完全封闭的境地。
(三)价值观念落后
价值观念落后是文化贫困的最深层表现,同时也是导致文化贫困的重要原因。这些落后观念包括:依赖政府救助和神灵保佑的心理,多子多福的生育观,故步自封、拒绝革新的观念等。
第一,依赖心理。由于贫困农牧民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生存压力大,相当多的贫困人口抱着无能为力、听天由命的思想,不努力奋斗,却寄希望于政府救济,形成“等、靠、要”的心理。同时,还有很多农牧民笃信宗教,不仅浪费了生产创造财富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将自己的很多资产花费在宗教信仰上,希望宗教能改变自身贫困的命运。
第二,“多子多福”的生育观。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于少数民族较为宽松,然而,即使这样,当地农牧民依然沿袭传统的“多子多福”观念,导致当地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高速增长。据统计,2000年甘孜州人口数为88.9万人,有19.4万户;到2007年甘孜州人口数为95.5万人,有23.5万户。而截至2009年底,甘孜州人口数达致102.32万人,当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56‰。9年来增加了13.42万人。(图1)可以说9年来的扶贫成效基本上被增长的人口抵消了。
第三,故步自封、拒绝革新的观念。甘孜州农牧业产业结构单一,总体处于原始和传统农耕游牧生产水平,以家庭为生产和消费单位,自给自足。“因为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影响着人们。这种习惯势力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4〕长期的封闭、贫困和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使甘孜州地区农牧民习惯于固守落后的生产方式,害怕变化,拒绝革新,排斥新产品和新技术在农牧业生产中的应用和推广。
二、文化贫困对甘孜州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文化贫困有强大的辐射和遗传力,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体现在贫困农牧民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生活方式等方面,而且直接造成教育科技的落后和人力资本存量的不足,从而制约着甘孜州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一)人口过快增长、文化素质差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甘孜州高人口出生率和高人口自然增长率使人口规模超速扩大,直接造成人均资源占有量变少。同时,由于当地经济不发达,缺乏稳定的致富产业,很难吸纳这些新增劳动力,造成劳动力过剩。而过多的人口,又进一步造成了教育、社保的投入不足,反过来造成人口素质的低下。因此,人口的过快增长不仅不能创造财富、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且还消耗物质资料,造成社会压力。
只有拥有高素质的人口资源,才能为现代制度和经济提供赖以长期发展且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甘孜州劳动人口文化程度低,参加农牧科技知识培训少,了解信息渠道窄,在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等方面都缺乏先进实用的科学技术,科技的推广率和应用率较低,这些从更深层次上决定了当地的劳动生产率低、产业结构以第一产业为主且生产方式落后、生活消费多生产积累少等现状。可见,人口过快增长、文化素质差是制约甘孜州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
(二)生活方式落后不利于社会的协调稳定发展
甘孜州贫困农牧民消费需求压抑、生活条件落后、精神文化生活匮乏、社会组织水平较低、社会交往范围狭窄等状况,从不同层面给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带来很多负面影响。更为严重的是,先进文化不能渗透进去,外来糟粕就会乘虚而入,黄赌恶习、犯罪行为等就会生根发芽,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价值观念落后使得贫困主体能动性降低
甘孜州农牧民长期生活在十分恶劣的自然环境下,教育水平较低,且农牧民语言隔阂、信息闭塞,许多信教群众置生产、生活于不顾专门从事宗教活动。此外,当地许多人还抱有“你认为我穷,但我不认为我穷”的主观不贫困观念,这种观念使人消极无为、不求上进,扼杀了人的欲望和潜能,长此以往他们就会失去上进心和竞争力。
因此,在贫困者价值观念不改变的条件下,单纯提供物质帮助的办法是难以完全消灭贫困的。甘孜州经济贫困是表象,文化贫困是深层次因素,所以反文化贫困才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出路。
三、甘孜州反文化贫困的战略选择
为了有效缓解、消除甘孜州的文化贫困,笔者认为应当以政府为主导,以当地民众为主体,注重能力建设,发展教育和科技,重建社会组织体系,通过参与式扶贫来实现贫困主体的意识提升和能力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等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变革。
(一)注重农牧民自身能力建设,发展教育和科技
解决甘孜州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政府作为扶贫的组织者起主导作用,在扶贫政策安排上应当注重激发贫困主体的内在活力和潜力,注重其能力建设,打破政府与贫困主体之间救济与被救济的格局。
提高农牧民的文化素质,增强他们的自身能力建设,要从发展教育和科技入手。政府应当牢牢抓住“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提高人口素质、发展人力资本为中心,以发展教育和科技为两个基本点。教育是基础,科技是动力。具体来说,政府尤其要高度重视当地教育和科技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切实抓好甘孜州的基础教育,提高学龄儿童入学率,控制辍学率,逐渐减少文盲与半文盲率;加强中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强化农村劳动力在职培训,扩大劳动力转移规模;加强文化设施建设;大力推广普及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等。因此,政府在经济扶贫的同时,应加强资金、人才、政策等支持,不断发展人力资源、积累社会资本。
(二)重建社会组织体系,推进参与式扶贫
由于自身生活方式和环境的因素,本来最需要社会组织的甘孜州农牧民却没有组织的意愿和能力。如果扶贫战略以贫困农牧民为主体,就需要建立这一行动的载体即社会组织,以凝聚地区发展的内在合力。事实证明,按照传统的自组织模式,按自愿的原则,重建以反贫困为目标的经济合作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是较为有效的。〔5〕例如,农牧民可以在政府的引导下组成挖掘销售中藏药的经济合作组织,克服农牧民自身信息不灵通、不能及时了解市场需求的弱点,从而使农牧民更好地增加个人收入。
要培育和发展贫困主体的自身能力,还应当改变在具体的扶贫项目上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传统模式,大力推进参与式扶贫。因为反贫困是事关农牧民切身利益的事情,因此必须培养起农牧民自身的主体意识,让农牧民真正参与其中,参与扶贫项目的管理,参与决策。扶贫项目要考虑当地的发展需要,把救助式发展转变为扶植其自我发展的能力,建立反贫困的内在机制,形成反贫困的不竭动力。具体到文化扶贫的过程中,要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和传统习俗,对各地的地方性文化作深入而全面的调查与重估,通过科学求证的价值评估作出能否开发、怎样开发、如何实施等决策,让群众成为地区发展的生产者和参与者,提供地区社会自我成长的发展计划。
(三)关心文化转型,保护文化遗产
在注重能力建设和重建社会组织体系的过程中,应当非常关心文化转型的问题。要避免发展与文化重建脱钩,而“窒息”当地知识的自我进化。要避免单纯地输入一种制度或者自上而下地贯彻一种制度,在理解、变革、挖掘的过程中实现文化的重构。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抓好贫困农牧民的思想文化建设,更新其观念,培育其文化自觉意识,帮助其树立通过自身力量摆脱贫困的信心和决心,又要建立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等人文环境,使他们在健康文明的氛围中转变生活价值形态,从而积极进取地担当和参与社会的变革与发展。甘孜州独特神秘、品种丰富的康巴文化融合了原汁原味的乡土生活,承载着原生态、环境及文化的历史印记。应当以扶贫开发为契机,既实现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同时又实现民族文化的良性变迁,更好地弘扬民族文化,保护民族文化遗产。
〔1〕辛秋水.走文化扶贫之路——论文化贫困与贫困文化〔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3).
〔2〕龚志伟.反贫困文化: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战略〔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8(1).
〔3〕赵秋成.对贫困地区人口文化贫困的研究〔J〕.西北人口,1997(3).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2.
〔5〕戴庆中.文化视野中的贫困与发展——贫困地区发展的非经济因素研究〔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195.
Strategy Against“Cultural Poverty”——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Ganzi Tibetan Autonomous Perfecture
YANG Li-ping,ZHAO Xiao-xia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Ya’an 625014,China)
The cultural poverty of Gaze prefecture is primarily manifested in the backwardness in education,life-style and values,and the backwardness restrict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Therefore,in developing Gaze,it is necessary to adopt some measures against cultural poverty,such as paying attention to developing education,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 improvement of cap ability as stress,reestablishing the system of social organizations,carrying out participant help-the-poor activities,showing great concern about cultural tansformation,and protecting cultural heritage.
Gaze prefecture;cultural poverty;antipoverty in culture
G127
A
1009-1203(2011)01-0074-04
2010-11-22
杨丽萍(1982-),女,山西阳泉人,四川农业大学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硕士研究生。赵晓霞(1964-),女,重庆人,四川农业大学语言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梁华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