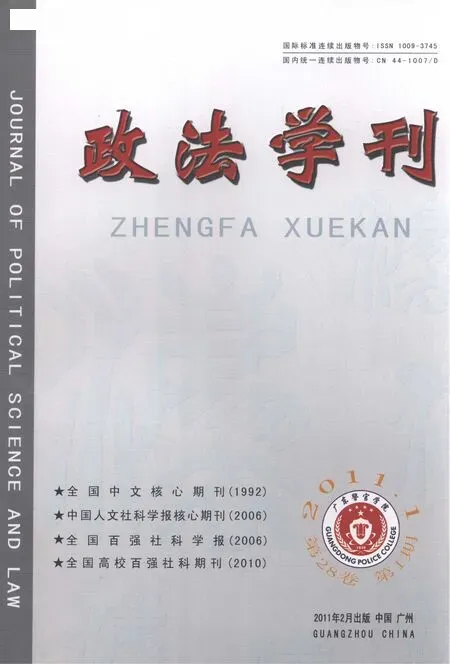无知之幕与正义的蒙眼布——对程序正义的反思
姚志伟
(广东金融学院 法学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521)
在法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中,正义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而罗尔斯因为其对正义理论的独特阐释而成为现代法学和政治学理论的巨匠。本文并不打算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作系统的研究,而是对其中有关程序正义内容作一个初步的梳理,在此基础上,针对当下中国有关程序正义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争论发表一点自己的思考。
一、程序正义的概念
首先,需要对罗尔斯正义体系里的程序正义概念以及在相关的形式正义、实质正义概念作一个简单阐释。形式正义是指“平等地对待平等之物”,其核心是正义普遍实现过程中的平等性,并且这种平等着眼于形式。实质正义则与形式正义的概念正好相对,其要求事实意义上而非形式意义上的平等。实际正义的背后是各种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在支撑,他要求人们作出实质性的判断。
罗尔斯的正义体系中还有“程序正义”的概念,这一概念融合了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罗尔斯根据两者融合的程度 (或者说关系的不同),将程序正义分为三种类型:纯粹的程序正义、完善的程序正义和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罗尔斯所言之纯粹的程序正义是指,“不存在对正当结果的独立标准,而是存在一种正确的或公平的程序,这种程序若被人们恰当的遵守,其结果也会是正确的或公平的,无论它们可能会是一些什么样的结果”,[2]61-62这种程序的典型代表就是赌博。其实纯粹的程序正义也就是形式正义,而排除了实质正义。
与此相反,完善和不完善的程序正义中既包含了形式正义,也包含了实质正义。完善的程序正义是指,“有一个决定什么结果是正义的独立标准,和一种保证达到这一结果的程序”。[2]86标准就是实质正义,也就是由价值观决定的标准,而程序则是形式正义。完善的程序正义的典型是切蛋糕的思维试验。如何保证切蛋糕最为公正,在给定二个假设的基础上:第一是技术假设,假定蛋糕可以被均分;第二是人性假设,假定人性趋向于利益最大化。在这两个假定的基础上,要保证公正,首先提出公正的标准,即均分;其次,提出保证实现这一结果的程序,即先切者后拿。
不完善的程序正义指存在独立的结果正义标准,但是不存在达到这一正义结构的完美程序,但是存在一些程序,可以偶合性的达到正义结果,当然这也意味着偶合性的达不到正义结构。这种程序的典型代表就是刑事审判,刑事审判存在正义标准,即以罪刑相应为原则惩处犯罪者,但是人类无法发展出完善的刑事程序保证达到这一结果。刑事审判的结果有时达到了,有时没达到,而更可悲的是,很多案件我们永远无法弄清楚是否刑事审判程序达到了正义的结果目标。①即使在美国这种刑事程序和刑事侦查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刑事错案仍不可避免。详细论述参见甄贞等编译:《法律能还清白?美国刑事司法实证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二、无知之幕、正义的蒙眼布与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在罗尔斯的思想体系中十分重要。罗尔斯正义观的核心是建构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而要建构这种正义则需要指导原则,罗尔斯认为这二个原则是建立社会基本结构正义的指导原则:
“第一个正义原则: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
第二个正义原则: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
(1)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
(2)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2]86
很明显,这两条原则带有浓厚的实质正义色彩,如对自由、平等的推崇,和对弱者的关照。这些原则符合很多人的价值观,也必然与另一些人的价值观相冲突,所以罗尔斯要使这两个原则成为不同的价值观的人都共享和共同遵守的基本正义原则,需要对这两个原则进行合法性论证。
罗尔斯的合法性论证是通过程序正当化也就是程序正义的方式完成的。他设定一个称之为“无知之幕”的程序。在无知之幕下,人们除了有关社会理论的一般知识,对自身和自身所处社会的特殊情况都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当然,这里存在对人性的自利性假设)会选择出两个基本的正义原则。
无知之幕的关键在于用以保证选择出来的规则 (原则)的平等性,而这是用过滤参与者对特殊信息的掌握之方式来实现的。无知之幕的设置类似于西方的另一种正义观念——蒙眼的正义女神。西方正义的形象为女神、白袍、金冠。左手持秤 (代表公平),右手握剑 (代表惩罚)。最为特殊之处在于蒙眼,为何要蒙眼呢?西方人的传说是这样解释的:
“天庭上的众神失和了,世界处于灾难的边缘。谁来调解仲裁?血气方刚的容易受水仙女的勾引,老于世故的却不敢对权势直言。天上地下找遍了,也没有合适的人选。最后,天帝身旁站起一位白袍金冠的女神,拿出一条毛巾,绑在自己眼睛上,说:“我来,众神一看,不得不点头同意:她既然绑上双眼,看不见争纷者的面貌身份,也就不会怕她的权势。”②转引自冯象:《政法笔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页。
美国学者柯维尔对这个传说作了这样的解读:“蒙眼不是失明,是自我约束,是刻意选择的一种姿态……真的,看的诱惑,君子最难抵挡;尤其是克服屏障而直视对象,最诱惑人。”②从这个传说和学者的解读中可见,蒙眼是一种遮蔽信息,保持公正的设置,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程序,通过蒙眼的程序一方面保证公正结果的获得,另一方面也为审判者的公正性提供合法性论证。正如柯维尔所言:“程序是正义的蒙眼布。”②
所以无论是无知之幕也好,还是女神的蒙眼布,都是为了实现公正,而设置的程序。这种程序的核心在于删除特殊的信息,以保证决定平等性,而这种程序本身也是结果的合法性证明。换种正式一点的说法,可以这样表达,通过程序的正义来实现结果的正义。
这一思路无疑是极具有诱惑力的,在一个价值观、正义观日趋分裂的社会里,作出一个同时满足所有人 (或者说绝大部分人)都满意的公共决策是非常困难的,不论是立法还是司法的决策都是如此,因为每个人的环境、观念、信仰等等都不同。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也通过直接追求实质正义的方式来作出公共决策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那么在这种情况,程序正义就成为很好的代替工具,人们可以不用再进行痛苦而无效的价值观直接撞击,而只有通过程序的方式,就可以产生至少让大家接受的正义结果。
三、从罗尔斯的程序正义观看刘涌案
程序的合法性论证价值,使得程序正义的观念在学界很受热捧,在法学界尤为如此。①这方面研究成果极多。代表性的有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载《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1期。法律学者们力图纠正以往中国法律实务界重实体而轻程序的作法,力图将程序正义的概念注入中国的司法实务中,以推进中国的法治进程。学者们的努力在司法实务界受到诸多抵制,取得的成果有限,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学者们热吵的沉默权至今仍然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付之阙如,②有关沉默权的介绍及学者的呼吁可参见刘根菊:《在我国确立沉默权原则及几个问题之研讨》(上、下),分别载《中国法学》第2000年第2期、第3期。更使学者们有挫败感的是,他们的努力不仅不被司法实务界所接受,也不被普罗大众所认可,专家的思维和民众的观点产生了激烈的碰撞,这一碰撞在2003年的刘涌案中激烈的爆发出来。③有关刘涌案的案情介绍可参见杨晓雷:《规则建立过程的知识考察——以“刘涌案”事件为空间》,载《北大法律评论》2007年第8卷,第2辑。
在刘涌案的审判过程中,以大多数学者 (主要是法学学者为一方)和普通大众为另一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而在辩论中,正义特别是程序正义问题是核心争论点。在学者看来,虽然刘涌罪大恶极,但由于证据有颇多漏洞,并且在侦查过程中他可能受到刑讯逼供,所以应该不判死刑,而判死缓,以实现程序正义,保障人权。而在民众看来,像刘涌这样罪大恶极的人都可以不判死刑,还能判谁的死刑。并且如果要维护程序正义,保障人权,为何是从刘涌这样一个黑社会老大。④限于篇幅和论述重点,本文不再将争论人和论点一一介绍,因为实在太多,只列出主要争议点,论战方也简化为学者和大众两方,但事实上学者中也有不同声音。对这次论战的详细介绍和研究可参见杨晓雷:《规则建立过程的知识考察——以“刘涌案”事件为空间》,载《北大法律评论》2007年第8卷,第2辑。学者和民众的争论彰显了专家思维与大众逻辑的巨大差异,而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理念在其中进行激烈的交战,双方在争战中表现出来的决心正如那句罗马法谚所言:“为实现正义,哪怕天崩地裂 (Fiatjustitia ruatcaelum)。”
为何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异,民众为何不认可专家所称的程序正义呢,况且这种程序正义按照专家所言是保护每一个人的。此种分析已极多,本文并不想赘述,⑤相关介绍参见杨晓雷:《规则建立过程的知识考察——以“刘涌案”事件为空间》,载《北大法律评论》2007年第8卷,第2辑。而是从罗尔斯对程序正义的论述来探讨这一问题,以期发现新的视角。
在罗尔斯的思想体系中,程序正义本身这个概念融合了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两个方面的内容,当然,与结果正义相比,程序正义更偏重于形式正义。但问题是,程序正义能脱离实质正义而存在吗?程序正义是否需要一个预设的实质正义前提呢?罗尔斯对此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他谈到:
“采用纯粹的程序正义的概念,有必要实际地建立和公平地管理一个正义的制度体系。只有在一种正义的社会基本结构的背景下,在一种正义的政治结构和经济与社会制度安排的背景下,我们才能说存在必要的正义程序。”[2]87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何普通民众并不相信专家所言的程序正义。并不是民众无知或者愚昧,或者说是“乌合之众”,而是他们以简单的直觉就能感到,在我们这样一个转型期的社会里,基本社会结构的公平尚有问题,在这种环境中,谈程序公正无异于缘木求鱼。具体到刘涌的案例中,民众所感到的社会基本结构的不公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的普通大众有一种强烈的被剥夺感,以财富为标准划分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大,民间仇富的心态日盛,而政府却不能取得足够的信任去缓解这种矛盾。在刘涌案中,刘涌是富人的代表,所以民众质问的是,为何号称保护每一个人的程序正义首先是保护富人而不是穷人。更值得思考的是,如果刘涌不是因为有钱,他就不可能聘用起有名的律师,并且请全国最知名的法学家为其出具专家意见书。民众在思考,如果刘涌是一个穷人,他能享受这些待遇吗?程序正义能保护他吗?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号称保护每一个人的程序正义真的能保护每一个人吗?人们真的能无分贵贱地站立在号称最为平等的程序正义面前吗?在现实世界中,真有遮住一切的蒙眼布吗?遮住以后真的能实现平等吗?当然,这些问题还牵涉到程序正义的实现可能性。在程序正义口号高昂的年代,人们往往轻视了程序正义的成本,这一点在司法上表现得极为突出。以美国为例,它的司法程序极为重视程序正义,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尤为如此,抗辩制、陪审制等程序都是用以保证程序正义的实现。通过这些制度保证当事人在审判中得到平等而公正的对待。但同时,这些程序有时耗资巨大的,可以这样说,大多数人无法支付享受这些程序的费用 (主要是律师费),即使对于政府而言,也是巨大的负担,所以在美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刑事被告未经庭审,而是以“辨诉交易”的方式定罪。被中国学者视为程序正义绝好范例的“辛普森案”,其耗费的律师费多达七百多万美元,这岂是普罗大众能够享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原本追求平等的程序,因为现实生活中本身的不平等,完全有可能导致不正义的结果——即有钱人享受了程序正义的保护,而穷人只能寄希望运气的照顾,希望程序正义也能落到自己头上。当然,法治发达国家会通过律师援助等制度来缓解这种局面,中国也开始建立这些制度,但其路仍漫漫。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百姓将程序正义认知为保护富人的工具,也无可非议。
第二,正如孙立平所指出的,九十年代以来,“信任结构解体之后,中国的社会处于一种完全没有信任结构的状态,这时候出现的不是规则的建立,而是以强凌弱格局的形成,这样的趋势现在正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①孙立平: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断裂社会”之演变前景,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3089,2010年5月14日访问。这种局面的出现导致整个社会趋向于“西西里化”,弱肉强食成为社会的主导准则,其中最为恶劣的是黑恶势力的泛起。他们以暴力为凭借,以金钱开路,以官员为保护伞,盘踞一方,欺行罢市,草菅人命,使得普通民众敢怒不敢言。在黑恶势力没有得到有效打击,普通民众的生命财产仍然受到黑社会势利严重威胁之时,民众们如何会信服以程序正义为名为黑社会头目宽罪呢。
第三,在当下的环境中,专家也不被信任。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民间颇有号召力,但是九十年代以后,知识界开始转型。一方面是,思想淡出,学术占为主导;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和资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从而受到民众的普遍质疑和不信任。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经济学家遭受了普遍的信任危机,被视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在刘涌案中,法学专家们也遭受了这种质疑。当法学专家们在向民间传授程序正义之道时,民众所关心的却是他们在出具专家意见书的时候有没拿钱,当专家最后羞羞答答的承认拿了酬劳费后,他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在民众眼中就完全丧失了,民众把他的话当成是为金钱而找的幌子而已。①这方面情况的介绍参见杨晓雷: 《规则建立过程的知识考察——以“刘涌案”事件为空间》,载《北大法律评论》2007年第8卷,第2辑。法学家也被视成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非代表民众利益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专业分析也就无法再取信于民众。
总的而言,民众对刘涌案中表现出来的程序正义不认可,乃是由于他们对社会结构的公正度的认知,在一个公正存在问题的社会基本结构中,正如罗尔斯所言,追求程序正义是意义有限的。
当然,笔者在此,无意否定程序正义的价值,只是我们应该牢记罗尔斯的提醒,在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性尚存在问题时,拘泥于程序正义是无意义的。程序正义必须有实质性的正义前提,当然,这些实质性正义前提的建立又反过来通过程序正义来建立。比如通过无知之幕来得出基本的正义原则。而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主张融合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一方面,要以正当的程序取得重叠共识,使之作为成为基本的实质正义。另一方面,又要以重叠共识来评判各种程序,使程序的结果不能过于脱离实质正义。[2]449
上文颇为繁琐的论证可以说明,程序正义问题在当下中国的复杂性,不过简而言之,如果说从罗尔斯的提醒中我们可以学到些东西的话,那就是当我们高扬程序正义的大旗时,不要忘了程序正义的实现条件,不要忘了我们当下所处社会结构的基本特质。
[1]季卫东.法律程序的形式性与实质性——以对程序理论的批判和批判理论的程序化为线索[J].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
[2]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3]冯象.政法笔记 [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