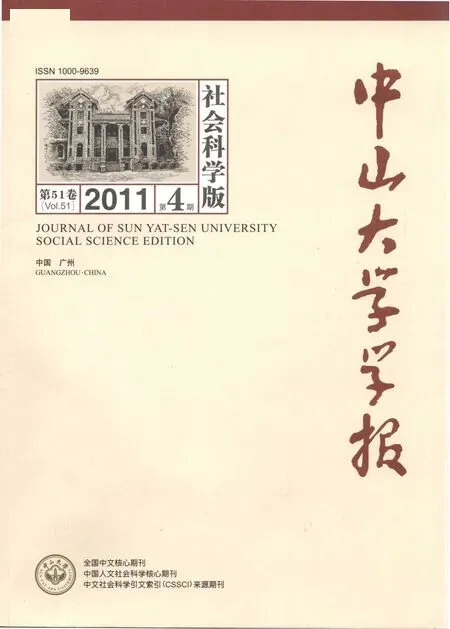中国小说史的构建*
——鲁迅与盐谷温论著之比较
谢崇宁
在中国小说史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日本学者盐谷温①盐谷温(1878—1962),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汉学家,著有《支那文学概论讲话》、《新字鉴》等。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1919)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1923—1924)②本文引证《中国小说史略》的版本有:北京:北大一院新潮社,1925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都可谓先驱之作,获得了中日学界的广泛好评。另一方面,鲁迅的论著成书不久,也曾引起轩然大波:1926年,北京大学教授陈源在《致志摩》中指称,鲁迅的著作抄袭了盐谷温著作的相关内容。长期以来,学术界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面对陈源的攻击,鲁迅在《不是信》一文中回应道:“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③此文最初发表于1926年2月8日《语丝》周刊第65期。本文引自《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29页。笔者认为,上述问题之所以会长期引起争议而形成学术界公案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正反双方都没有真正对两本原著作过较为全面深入的分析。当今,在讨论两著的学术关系之时,有关两者的学术思想及研究方法之异同还有待我们重新甄别和认识。其后两位学者的学术交流和相互促进,也成为中日近代学术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深入探讨。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小说史形成的学术背景以及中日近代学术交流的内涵,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上述鲁迅与盐谷温的论著(以下简称“鲁著”和“盐谷著”)进行具体的比较研究。
一、两著的体例、引证材料及其分类
首先,两著的体例结构是不同的。盐谷著属于中国文学概论,其内容分为上篇(音韵、文体、诗式、乐府及填词)和下篇(戏曲、小说),可见小说史及其研究只是其中的一个门类。鲁著是专门的中国小说史,由二十八篇构成。故两著的中国小说研究各有侧重,其视角及方法也自然会产生各种差异。专门史和通史的内容篇幅两相比较,其深广度不言自明。
两著论古小说引用的原文分析材料,鲁著显然要比盐谷著丰富。如据盐谷著“两汉六朝小说”一节统计,其从《汉魏丛书》引用辨析的古籍主要有14种:《神异经》、《汉武故事》、《搜神记》、《述异记》、《还冤志》等。在论述中国小说的起源及其发展的章节中,鲁著除了从《太平广记》中引用与盐谷著相同的古籍外,还外加多种:《三五历记》、《史记》、《穆天子传》等。鲁迅更注意从类书等古文献中辑佚,其中有:《太平御览》卷378引《琐语》、晋立《太公吕望表》石刻、《太平御览》卷29、918引《玄中记》等。鲁著第三篇“《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取材也不限于《四库全书》分类,如《师旷》八篇。他指出:“《汉志》兵阴阳家有《师旷》八篇,是杂占之书;在小说家者不可考,惟据本志注,知其多本《春秋》而已。《逸周书·太子晋》篇记师旷见太子,聆声而知其不寿,太子亦自知‘后三年当宾于帝所’,其说颇似小说家。”鲁迅读书考证之勤,尤其善用类书,由此可见一斑。
鲁著与盐谷著的取材还有一个显著的不同点:盐谷氏注意新发现的材料;鲁迅则取常见可靠的材料,能说明问题即可,所以他推崇《太平广记》(见第十一篇),但因此也被某些学者讥刺为不知“版本秘籍”。鲁迅对台静农谈治学方法就曾说:“郑君(振铎)治学,盖用胡适之法,往往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此实足以炫耀人目,其为学子所珍赏,宜也。我法稍不同,凡所泛览,皆通行之本,易得之书,故遂孑然于学林之外,《中国小说史略》而非断代,即尝见贬于人。”①鲁迅:《致台静农》(1932年8月15日),《鲁迅全集》第12卷,第102页。鲁迅对有史料而无史识者也不屑与之为伍,这也本是章太炎学派的特点②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29页。。
然而,在实际的学术研究中,鲁迅并不真正排斥史料学和新国学,也深知当时国际汉学主流之所在,尤其是法、日汉学研究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因此一直注意购藏罗振玉和王国维的《流沙坠简》等著作。只是他受个人条件的局限,未能将更多有价值的小说史料用于其论著,所以后来盐谷温在日本得见中国失传的古小说等重要资料,并见示于鲁迅,鲁迅即在修订本中加以引用。如第十四篇“元明传来之讲史(上)”,就采用在中国已失传,新发现于日本内阁文库藏元代至治(1321—1323)年间新安虞氏刊本全相平话五种,以阐明“宋之说话人,于小说及讲史皆多高手”,并称此为盐谷氏对中国小说史研究的重要发现。
盐谷氏的学术研究属于日本新“东洋学”的一部分,自然其论述十分注意采用中国久已失传而在近代新发现的“版本秘籍”。他提到在中国失传而今存日本的张文成撰《游仙窟》,指出此书在日本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就有其底本的痕迹,并援引《拙堂文话》③此著为日本江户末期儒学者斋藤拙堂(1797—1865)所撰。云,日本的“物语、草纸”之作,在汉文大行之后,多有从唐《本事诗》、《霍小玉传》等文本演变而来④[日]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东京:大日本雄辩会,1919年,第443页。。
从充分占有原始资料和了解相关发现与研究的现状入手,注意吸收新成果,应当说是盐谷著胜于鲁著的一个特点,颇有王国维倡言的“二重证据法”的色彩。如当时学界有新见景宋残本《五代平话》与《京本通俗小说》二书(影印本)出现,盐谷氏根据狩野直喜⑤[日]狩野直喜(1868—1947),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京都中国学的创始人,著有《中国哲学史》等。之说,认为从版式考证来说,前者可能是元版书,但从文体来说,又似南宋之《宣和遗事》,为后来演义小说的雏型。又辨析属珍本的《京本通俗小说》,指出其用当时通行的略字和俗体字,对汉字研究是重要的资料。他还从游学英、法的狩野直喜的研究了解到,敦煌石室文书的发现中有雅俗折中体的小说,于是意识到,在唐末五代之际,于传奇小说之外还有平民的小说,称此为中国俗文学史研究极重要之发现。
在论述小说的材料选择上,鲁著与盐谷著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如论《儒林外史》,盐谷著是一笔带过,不给予应有的重视,虽然他也强调这是考察中国的人情风俗、研究其国民性的重要材料。鲁著则不然,其以《儒林外史》为论述中心,专辟第二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称其为“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
在使用传世文献材料上,鲁著的辨伪功力强于盐谷著。如鲁迅考现行之《述异记》二卷为唐宋间人伪作,《异苑》十卷亦然,已非原书。他指出,刘宋时期的临川王刘义庆“为性简素,爱好文义,撰述甚多……其书今虽不存,而他书征引甚多,大抵如《搜神》《列异》之类;然似皆集录前人撰作,非自造也”(第五篇)。如果不亲自作这许多深入的校勘,鲁迅绝提不出这样的见解。又如考唐代的《枕中记》之故事原型是取材于干宝《搜神记》,而明人汤显祖的《邯郸记》又是本之《枕中记》。诸如此类的考证,鲁著远比盐谷著要多。对于讹传为唐人传奇的《绿珠传》、《杨太真外传》,鲁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是宋乐史所撰(第十一篇)。但盐谷温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将《太真外传》当作唐代小说中的别传来论述。鲁著在评述宋人秦醇的传奇小说时还具体地指出:“其文颇欲规抚唐人,然辞意皆芜劣,惟偶见一二好语,点缀其间;又大抵托之古事,不敢及近,则仍由士习拘谨之所致矣,故乐史亦如此。”《赵飞燕别传》“文中有‘兰汤滟滟,昭仪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语,明人遂或击节诧为真古籍,与今人为杨慎伪造之汉《杂事秘辛》所惑正同”(第十一篇)。以此来阐述宋代传奇的性质及其特点。
当然,鲁迅的某些考证结论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如关于《梅妃传》、《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等的作者、版本考,后来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①关于《梅妃传》考,参见鲁迅著,周锡山释评:《中国小说史略:释评本》,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92页。关于《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考,参见欧阳健:《中国小说史略批判》,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8—40页。。客观地说,由于小说史料和时代的局限性,鲁著的考据出现失误也是在所难免的。
另一方面,对小说的作者、真伪及版本源流作考辨,盐谷著也不是没有独自的见解。如论《海山记》的成书时代,《四库全书提要》断为宋人依托之作,盐谷著据其中的《望江南》词体的缘起和李商隐《隋宫》诗的典故,断其为与晚唐时代相近之人所作,也可视为一说。
对此,鲁著则祖述宋人作品说,但同时又指明《海山记》等有明代人妄增唐人作者名,具有一定的说服力。鲁迅编有《唐宋传奇集》,其资料的收集和辨析远比盐谷著更为广泛、细致,如考证《大业拾遗记》等皆如是。
盐谷著的小说分类与鲁著也有所区别。按《四库全书提要》,古小说分为三类: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辑琐语。然而,盐谷云此分类不够明了,因而森槐南②[日]森槐南(1863—1911),日本东京大学讲师,汉诗人,著有《唐诗选评释》、《古诗平仄论》等。将之改为:(一)别传(即传奇小说);(二)异闻琐语;(三)杂事。他又认为“杂事”不能算小说,“异闻琐语”虽有小说的元素,但唐代小说之精华才称得上“别传”,故据《唐人说荟》的材料又将唐人传奇小说细分为四种:别传、剑侠、艳情、神怪。
鲁著论述的取材、分类则与之不同,鲁迅在《不是信》中曾说:“唐人小说的分类他(盐谷温)据森槐南,我却用我法。”鲁迅所言是符合事实的。例如,第八、九篇“唐之传奇文(上、下)”的取材、分类及论述可谓具有鲜明的独创性。另外,鲁迅还指出:“唐人小说他(盐谷温)据谬误最多的《唐人说荟》,我是用《太平广记》的,此外还一本一本搜起来……其余分量,取舍,考证的不同,尤难枚举。”此言也许给予盐谷氏一定的启示,他在修订版《支那文学概论》中改用了一些《太平广记》中的小说史料。
的确,盐谷著最初取材的《唐人说荟》之类的文献,其中存在未加考订,或擅改篇名,或妄题作者,甚至或以宋人小说误作唐代传奇,且所收传奇专集和笔记,大都只摘录一部分,并非全本等诸多问题。当年鲁迅所作的这些考证①鲁迅:《破〈唐人说荟〉》,《鲁迅全集》第8卷,第106—108页。,今天已成为学界的定论。与盐谷著相比,鲁迅不仅取材严谨,而且还花费大量的时间,有针对性地搜集繁杂的资料而编辑成《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其理由是,今存之《太平广记》中者,“实唐代特绝之作也。然而后来流派,乃亦不昌”(第八篇)。
二、研究方法与论述形式的异同
从目录学入手,考史载之小说篇目及作品的流传及真伪,都是两著的出发点。若说考证的深度,尤其用辑佚比勘的方法考辨古小说,应说是鲁著分量更重。虽然同是从目录学入手,但鲁著更注重通过自己的考证来阐明《汉志》、《隋志》等文献所著录的篇目作品的真伪源流。如考已散佚的魏文帝撰《列异传》三卷,鲁著是从宋裴松之《三国志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检索出所征引的部分,以确证《列异传》为魏晋人所作。
盐谷氏则直接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订的《拾遗记》、《搜神记》等七种可信的主要材料入手分析论述。可见鲁著引用古籍材料远比盐谷著要多,其原因就在于鲁迅一直长期在做古小说的辑佚辨伪及校勘工作。
当然,盐谷著也常用文献互证的方法,如指出陶渊明的《读山海经》诗等内容有与《汉武内传》相似处,以证后者的成书年代可能是在魏晋之间;从文辞的风格断定《飞燕外传》非西汉作品而出自六朝间。此法都互见于两著。
文史互证,也可说是鲁著与盐谷著的共同特点。盐谷著指出《唐人说荟》所收《虬髯客传》,即是明代戏曲《红拂记》的故事来源;论《东城父老传》,注意揭示小说反映的玄宗时期盛行斗鸡的颓靡之风,这也是盐谷著吸收洪容斋等前人点评观点的一个方面。又如盐谷著论剑侠小说产生的背景,认为是唐中叶后藩镇坐大,盛行培养死士从事暗杀活动,因而产生以剑侠为题材的小说,并言“以唐代小说的特色,亦足以窥察时世”。这与鲁迅《古小说钩沉》序所言相似。
与鲁著相比,笔者感觉盐谷著更具现代倾向。由于盐谷温受过西方学院派训练,故盐谷著常用的比较文学方法也为鲁著所罕见。盐谷著开篇即讲中国小说起源于神话传说,其论从史出,实也是对中国古人见解的引申(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他又从神话材料比较中得出东西方天体神话同一轨等观念,这也是他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听康拉第教授讲《楚辞》学到的方法。应当说是盐谷著开了用西方比较神话学观点研究中国文学的先河,其说应当要早于茅盾、郑振铎等人的研究。当他在德国访问席勒纪念馆时,发现这位大文豪居然读过中国明末清初小说《好逑传》德译本,又在哥尔彻的《汉籍解题》中看到许多中国戏曲小说类欧洲文字译本,这都可能是他大受刺激而日后勤奋攻治中国文学史的又一原因吧。
治中国文学史,不仅是鲁迅,盐谷温在接受日本、欧洲汉学影响的同时,也注重从中国古代文论家中吸取有益的营养。他推重中国古戏曲小说,认为其文学价值不亚于汉史唐诗宋文,其观点源自中国俗文学大批评家金圣叹、李笠翁等人之说。
另一方面,以史为主线,具体论述各时代的主要作品时直接深入到小说故事情节中去点评,这也是鲁著与盐谷著的又一个共同特点,但两著各有侧重。盐谷著中对古小说的片断赏析,是择其时代要著,以点带面,深入故事加以论述。其论《红楼梦》,阅读细致入微,云史湘云、妙玉没有来历,不知何时进贾府;在称誉其为古今东西第一言情小说的同时,也指出了白璧之微瑕。尤其是他所使用的《红楼梦》解读方法,有助于读者对全书结构、人物及故事情节的把握,故此它也被鲁著所吸收,那就是盐谷著检索排比出的《贾家谱系》。从盐谷氏论《红楼梦》,可知他不仅从叶德辉习词曲,也问考小说等问题。考《红楼梦》的作者,他引述了许多中国红学家的观点,其中就包括1910年至1911年间在长沙向叶德辉问学的笔谈。
鲁著则是先述篇目版本真伪源流,才于所引原文前后加以点评。鲁著的详论小说者,也见于论《莺莺传》(第九篇)等篇,深入情节中夹叙夹议。但其考此书为唐元稹之自叙,则不及盐谷著周详,观点也大致相似。唐代李公佐及其小说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除了对其代表作《南柯太守传》作深入解读之外,鲁迅还将《古岳渎经》与《西游记》结合起来分析,认为宋元流传的猿猴神“无支祁”来自唐李公佐假设之作,从而为孙悟空原型的论考提供了材料依据。这种对作品之间题材关系的梳理在盐谷著中并不多见。在考证与论述方法上出现的这些异同,既与两者的史料解读及小说史观有关,同时也反映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古籍的流传及掌握程度影响到彼此的研究视角这一特点。
三、学术借鉴与理论观点
在对中国小说史发展脉络的把握上,两著确实有不少相同观点。鲁著第四篇“今所见汉人小说”云:“现存之所谓汉人小说,盖无一真出于汉人,晋以来,文人方士,皆有伪作,至宋明尚不绝。”与此相关联,盐谷在“汉代小说”的论述中曾指出,《神异经》是假托汉东方朔撰,《四库全书提要》已从其词华缛丽之处推断为成于六朝文士之手,其内容完全是仿《山海经》的。鲁迅论《神异经》、《十洲记》的成书,也持此论。虽然鲁著的论证更为深入,但鲁迅得阅盐谷著在先,这当是鲁著受盐谷著影响的又一实例。
在此,笔者想要强调的是,正因为盐谷著是鲁著的参考书之一,即使是研究同一问题,鲁迅都努力作出自己的评判,也竭力避免与盐谷著观点雷同。如论《汉武内传》,盐谷称:“其文章极佳,排偶华丽,颇有六朝的色彩。”鲁迅却道:“其文虽繁丽而浮浅,且窃取释家言,又多用《十洲记》及《汉武故事》中语,可知较二书为后出矣。宋时尚不题撰人,至明乃并《汉武故事》皆称班固作,盖以固名重,因连类依托之。”谁之深浅一目了然。又如同论《别国洞冥记》(又称《汉武洞冥记》),盐谷著指出该书内容完全是仿《十洲记》的,也非后汉郭宪所撰,其“文章艳缛,大概也是出自六朝人之手吧”。鲁著与之相比,研究也更为深入,其云:“然《洞冥记》称宪作,实始于刘昫《唐书》,《隋志》但云郭氏,无名。六朝人虚造神仙家言,每好称郭氏,殆以影射郭璞,故有《郭氏玄中记》,《郭氏洞冥记》。”
论汉代及六朝小说,不能不提《西京杂记》,但却为盐谷著所略。鲁著云《西京杂记》在《隋志》中不著撰人,《唐志》则云葛洪撰,可知当时皆不信此书真出自汉人刘歆。其说虽然源自《四库全书提要》,然鲁迅又云:“梁武帝敕殷芸撰《小说》,皆钞撮故书,已引《西京杂记》甚多,则梁初已流行世间,固以葛洪所造为近是。或又以文中称刘向为家君,因疑非葛洪作,然既托名于歆,则摹拟歆语,固亦理势所必至矣……若论文学,则此在古小说中,固亦意绪秀异,文笔可观者也。”可见鲁说是对前人研究的发展,这些观点的提出也要归结于鲁迅作《古小说钩沉》辑本的前期研究工作。因此鲁迅在《不是信》中说:“六朝小说他(盐谷温)据《汉魏丛书》,我据别本及自己的辑本。”这也是符合事实的。
鲁著第五、六篇为“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下)”,这在盐谷著中也不作专论,集中反映了两著在内容、篇幅、体例上有很大的不同。鲁著对《列异传》、《搜神记》、《异苑》、《幽明录》、《神异记》、《拾遗记》等,都有考辨源流真伪规律的论述,如云“晋以后人之造伪书,于记注殊方异物者每云张华,亦如言仙人神境者之好称东方朔”。如今存之托名张华撰《博物志》,“乃类记异境奇物及古代琐闻杂事,皆刺取故书,殊乏新异,不能副其名,或由后人缀辑复成,非其原本欤?今所存汉至隋小说,大抵此类”。言今存之《搜神记》“亦非原书,其书于神祗灵异人物变化之外,颇言神仙五行,又偶有释氏说”。并指出六朝“作志怪者尚多……今俱佚,间存遗文”。
两著注重从原文本分析该作品的时代风格与流变。两人都指出,六朝小说受到佛教文学的很大影响,但鲁著的论述更为深入而广泛。如论梁吴均作《续齐谐记》中的“阳羡鹅笼之记”,鲁迅分析道:“然此类思想,盖非中国所故有,段成式已谓出于天竺……”因为“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如晋人荀氏作《灵鬼志》,亦记道人入笼子中事,尚云来自外国,至吴均记,乃为中国之书生”。又云:“释氏辅教之书,《隋志》著录九家,在子部及史部,今惟颜之推《冤魂志》存,引经史以证报应,已开混合儒释之端矣,而余则俱佚。”(第六篇)这都应当说是中国小说史研究的一些重要观点。
鲁著还指出,为了与佛教横流对抗,六朝方士也造伪经异记,以网罗受众,“今所存汉小说,除一二文人著述外,其余盖皆是矣”(第二篇)。总之,鲁迅都是通过《古小说钩沉》的辑佚,较深入地阐明了自己对古小说源流的许多看法。这是在盐谷著初版中不多见的论证。
鲁著第七篇专论“《世说新语》与其前后”。鲁迅曾专攻魏晋文典和佛学,此为他治学所长,在盐谷著中则无所论及。其重要观点是,《世说新语》之类的丛残小语,“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寥寥数语,即指出了古小说的风格转变。鲁迅考《世说新语》,结论是“乃纂缉旧文,非由自造……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隋志》中之《笑林》三卷今佚,“遗文存二十余事,举非违,显纰缪,实《世说》之一体,亦后来诽谐文字之权舆也”。鲁迅一直注重分析小说史的流变,故又指出:“《笑林》之后,不乏继作……至于《世说》一流,仿者尤众。”此后,直至宋初徐铉《稽神录》,“其文平实简率,既失六朝志怪之古质,复无唐人传奇之缠绵,当宋之初,志怪又欲以‘可信’见长,而此道(志怪小说)于是不复振也”。“宋代虽云崇儒,并容释道,而信仰本根,夙在巫鬼,故徐铉吴淑而后,仍多变怪谶应之谈……毕仲询之《幕府燕闲录》(元丰初作),皆其类也。”(第十一篇)由此可知,鲁著有关《世说新语》诸文的论考慎密而视野开阔,为如何探究中国小说史发展的特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其学术意义及影响非常之深远。
论唐及以后中国小说史,两著的篇幅内容差别更大,盐谷著将这部分内容分为两节(共七小节)论述,而鲁著的论述长达二十一篇。相比之下,鲁著的唐以后小说的论述内容更为丰富。在论述的重点及观点方面,两著也有共同点,但更多的是差异。以下择其要加以比较分析。
盐谷氏认为,小说到唐代已达成熟繁荣阶段,不仅题材广泛,即是短篇,也成辞彩情节有条理之格局。此也为接受洪容斋之说。又云,后世的戏曲小说多取材于唐代传奇,如《西厢》、《琵琶》的蓝本。
鲁迅也同样注重考察此小说之流变,其云:“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今颇有留存于《太平广记》中者,实唐代特绝之作也……惟元明人多本其事作杂剧或传奇,而影响遂及于曲。”(第八篇)并指出唐代传奇是出于六朝志怪,只是文采和构想大异其趣。这些观点与盐谷著相似。
下面比较两著的不同点。
盐谷著考文学作品的源流,指出《吴越春秋》、《越绝书》的小说纪事原型,就是后世演义小说之祖,又在元曲等作品中引为典故。以此为解读主线,盐谷氏高度评价唐人段成式撰《剑侠传》集,详引了其中“聂隐娘胜妙手空空儿”的故事,称其“文章简古”,人物情节描写栩栩如生,从中恰如见到《西游记》的孙悟空,其文学价值在《红线传》之上,认为《剑侠传》反映了唐代小说的特色。
鲁迅则认为段成式《剑侠传》为明人伪作,并根据《太平广记》推断其中“聂隐娘”的故事即源出自唐末人裴鉶《传奇》集。
由此可见,两著因取材不同而产生推论及观点的差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考证结论并非是一种绝对对立的关系,它也可以成为相互引证、借鉴及深入探讨的参考。
盐谷将四大奇书作为专论,认为《三国志演义》是历史积淀及博采众长而成书,如从唐诗知《三国志》掌故早为文人学士所乐道。在唐宋之间,《三国志》的战争故事说书和戏剧已经流行,在金元曲目中有《赤壁鏖兵》等,元曲选中又见有《连环计》等曲目;在考《金瓶梅》的来源中,也指出它是取《水浒传》的骨子,加以复杂的描写而成。在观点上,盐谷更推重唐人的“艳情”类小说,即以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为主的故事,认为是唐代传奇的菁华(如《霍小玉传》等)。他又同意明代谢肇淛(《五杂俎》作者)等人的观点,认为《三国志演义》因事太实而俚而无味,但作为宣教化的普及读物,中国人没有不读三国者。论《金瓶梅》虽指出这是淫书,但与《西游记》的空想相反,其写实性对认识社会倒是真实而重要的史料。类似辩证地看问题的视角,以及从文学与国家政治历史的关系中诠释文学自立性的文学观,在盐谷著文中多有体现。
与盐谷著相对,鲁著则是将四大奇书分别穿插在第十四至十九篇中与其他小说分论,这就是鲁迅所言之“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例如,《三国志演义》是在第十四篇“元明传来之讲史(上)”中加以考述,篇幅不小,称得上是旁征博引。鲁迅尤善于剖析小说中的人物描写,认为该著“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就其艺术性,鲁著也评价不高。由于鲁著的体裁内容与盐谷著不同,故其论述自然要详于盐谷著,也更显治学功力。
如鲁迅考《水浒传》尤详,他认为故事主人公宋江确有其人,以《宋史》、洪迈《夷坚乙志》、宋遗民龚圣与《宋江三十六人赞》、《宣和遗事》诸载籍互证之(第十五篇)。又指出“元人杂剧亦屡取水浒故事为资材”,其后才演变成大部《水浒传》。鲁著考辨《水浒传》的各种版本,得出其实为繁、简两种传本这一结论。又考《水浒传》的编撰作者的几种说法,虽然不是最终结论,但也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鲁迅考论《西游记》,也是从整体上把握“明代神魔小说”的源流,最后得出“似取经故事,自唐末以至宋元,乃渐渐演成神异,且能有条贯,小说家因亦得取为记传也”(第十六篇)的正确结论。他同时还考证了《西游记》的版本内容次第,综合前人的不同说法,确定其作者应当是明人吴承恩(第十七篇)。
所谓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鲁著是将之夹列第十九篇“明之人情小说(上)”中论述。考《金瓶梅》成书的来龙去脉也较翔实,如指出其全书是“假《水浒传》之西门庆为线索”,并认为:“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其观点与盐谷著虽有相似之处,但认为作者著书意在笔伐时弊颓风,其人事皆有原型,称其写作水平为当时之最上乘,这又要比盐谷著进了一步。
四、文学史研究的殊途同归
既然是论从史出,难免英雄所见略同。与盐谷著相比,鲁迅在强调其著之独创性的同时,也坦言:“(两著)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说汉后有唐,唐后有宋,我也这样说,因为都以中国史实为‘蓝本’。我无法‘捏造得新奇’。”当以文学作为文本来解读历史的发展时,他所秉承的是一种主客观融为一体的文史观,即“历史则是纪事,固然不当偷成书,但也不必全两样”(《不是信》)。“诗歌小说”应有其独创性,而对这种独创性的诠释自然就会显现出文学研究方法的异同。
论唐人李朝威《柳毅传》的流传影响(第九篇),鲁著以杜甫《少年行》诗证《霍小玉传》之故事情节,也同于盐谷著文史互证之法;鲁著第十二篇“宋之话本”,称宋代文人的志怪小说无独创可言,“然在市井间,则别有艺文兴起。即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者是也”。他没有将此称为真正国民文学的开始,但把握小说演变的时代特点实与盐谷著略同。
事实上,鲁迅也承认对敦煌文书的俗文体小说是不熟悉的,不知其与后来小说之关系。相反,盐谷氏比较了解日本京都学派狩野直喜的相关研究,称20世纪初敦煌古文献的发现在中国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尽管篇幅不多,研究成果也属于初步性的,但盐谷著的修订版增补了第七章第四节“敦煌发现的俗文学”,并作了具体的论述。这一研究视角可谓具有开创性的学术意义。
此外,鲁著论述宋人通俗小说的起源及当时的现状,也与盐谷著大体相似,认为宋之“平话”源自杂剧中的“说话”。其云:“说话者,谓口说古今惊听之事,盖唐时亦已有之。”并援引段成式《酉阳杂俎》说“有市人小说”;从李商隐《骄儿诗》(集一)也可见“当时已有说三国故事者”;又举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说宋代的说话人已有专家。说话人也有“话本”,其体式相当于今存之《五代史平话》及《京本通俗小说》残本。尽管观点与盐谷著相似,然而鲁著的论述更为深入,引述原文也更多。相比之下,鲁著更为注重分析古小说刊本的版式、风格与流变,如考《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认为:“今所见小说之分章回者始此;每章必有诗,故曰诗话。”(第十三篇)
鲁著考《大宋宣和遗事》也有独到的见解,明确指出该书“世多以为宋人作,而文中有吕省元《宣和讲篇》及南儒《咏史诗》,省元南儒皆元代语,则其书或出于元人,抑宋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皆不可知……其剽取之书当有十种”(第十三篇)。可见其论据之充分、推论之合理。
我们称鲁迅与盐谷温为同一研究的雁行者,是因为两者也确有独自的真知灼见。如盐谷著的点睛之笔,论唐代元稹《会真记》,除采众家之说,更注意从元稹《姨母郑氏墓志》及白居易所作元稹母《郑夫人墓志》,以及日本文求堂所藏《唐故荥阳郑府君(恒)夫人崔氏合祔墓志铭》拓本,寻找旁证材料,以考索其真伪。并指出后世的相关文艺,例如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关(汉卿)的《西厢》杂剧、明人的《西厢》传奇等,皆为《会真记》的末流,表明宋金元明间戏曲的发达,应当溯源至《会真记》,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盐谷著凡论中国古小说的兴盛缘起,必述其原因背景,并视小说为了解中国的历史与人情风俗的捷径,其在论中国古小说的四大奇书中反映得最为充分。他服膺金圣叹的点评,对《水浒传》的评价很高,称其文学的艺术成就足可称雄于世界文坛之林,如鲁智深之传已被译成德文,收入“勒克拉姆文库”。论《西游记》亦然,认为其虽贯通儒道佛三教一家之理,但其艺术成就充分体现在寓意的比喻等方面;其结构的宏大,世界多不见其比,比《天方夜谭》更有趣。堪与之相当的还有《红楼梦》。
盐谷温又指出,唐代的神怪小说与“神仙”、“道释”、“怪谈”有关,是由古代的《神异经》、《搜神记》一类的作品发展而来,只是技巧更为成熟。故元曲中,才有《柳毅传》的翻版或情节,如《张生煮海》、《蜃中楼》等皆是。对这类小说的探讨,盐谷氏深入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与文学之关系,其论承森槐南师说,认为李泌《枕中记》有回教的痕迹,也可反映唐代各种宗教盛行的背景,表明当时宗教题材小说肯定很多,可惜失传,因此《枕中记》的存在更显其价值。他认为唐代小说的故事情节,多成为后世词曲的典故,如《唐人说荟》所收的陈元祐撰《离魂记》的故事为元代郑德辉的著名杂剧《倩女离魂》所采用。
从上述中国小说源流及传承关系的分析中,盐谷认识到文学的发展及其影响既超越时空,也超越国界。其云至宋以后,汉唐骈俪体旧小说渐衰,但明清文人仍大有继其余绪者,如宋景濂的《秦士录》、侯朝宗的《马伶传》等都属于传奇体;类似作品传到日本后,极大地影响了江户时代作家浅井了意、上田秋成、泷泽马琴等人的小说写作。如浅井了意的《伽婢子》是明代瞿佑撰《剪灯新话》的翻版;仿清代蒲松龄撰《聊斋志异》者尤多,其故事成了日本小说家取材的宝库。继而他在其著第六章第四节中强调,中国的小说起源于汉代,自六朝经唐代逐渐发展起来,而真正具有国民文学意味的小说则创始于宋代,即所谓“诨词小说”(俗话体小说)的产生①盐谷氏曾提到在敦煌发现之口语体散文、韵体小说,推测民间文学出现于唐末五代时期,但尚未形成其著之定论。另外,他在其著修订版中将初版的“诨词小说”改称为“通俗小说”。,因为它是用俗语体很有趣地写成的小说。在当时,这无疑是极重要的观点,实际上也是点明了中国近代“白话文运动”的渊源。
虽说前人早有“宋有戏曲唱、诨词说”(陶宗仪《辍畊录》),及“小说起宋仁宗”(郎瑛《七修类稿》)等说法,但只有受西学洗礼之学者才会提出“真正有国民文学意味的小说”这样的观点。这也是治中国小说史的新学与旧学的分水岭。盐谷著云宋代小说的发达,从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中的艺人分类,有“讲史、小说、说平话、说三分(讲《三国志》)、五代史”等分科,已知当时定有许多可供说话的书本。而且从宋人耐得翁的《古杭梦游录》中的说话人分类中,还可见当时有各种专门的社团,如雄辩社即为当时讲小说的团体。
盐谷著考证中国小说史的源流深入浅出,与其青少年时期以来的汉学熏陶、修养与学科训练密切相关。其论宋代“诨词小说”的兴起与发达,从《宣和遗事》切入,解析了《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及其艺术特色。同时,盐谷还非常注重古小说原著的辞彩、文体和时代特点。如指出《拾遗记》中有七言诗,这是六朝诗式的特征;论《搜神记》,鲁著着墨不多,盐谷著则论述较多,认为它“叙事古雅,文字简洁,实为六朝小说中之精品。其中掺入不少佛说……有趣的情节颇多,为后世《剪灯新话》、《聊斋志异》的源流”。
上述可见,在小说史观的形成过程中,两著充分体现了作者独自的治学方法以及学术上的互动关系,成为后世治中国小说史之典范。
五、结 语
通读两著之后,笔者认为盐谷著发表虽然略早于鲁著,但有前期研究的鲁著才可称为第一部较为完备的中国小说史。两相比较,在体例、篇幅、材料的取舍上都有各自的侧重和选择;就研究的深广度而言,在占有材料和论述内容上,鲁著更胜一筹。两著与传统汉学的本质区别,均在于作者都是借助新学的理论来阐明自己对中国小说史基本问题的看法。如研究中国小说史所用之目录文献学、考据校勘诸法,本为乾嘉学派及太炎师生、日本汉学家所传习,但能以“二重证据法”、比较神话学、社会进化论、政治学与历史学诸新学眼光去透析中国古小说的内涵,这又非没有受过西学洗礼的旧学者所能为。尤其是古小说,在封建科举时代的士人眼中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而被忽略。因此,鲁迅和盐谷温都是在融会了东西方科学新知的基础上,才决心去努力开辟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学科新领域。两人的研究结果都是第一次梳理了中国古代小说起源发展演变的脉络,并同时展现了许多学术研究的创见。
如鲁迅所言,鲁著参考盐谷著的部分主要是第二篇“神话与传说”和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说”。关于这一点,虽然鲁迅在著作初版中没有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加以必要的注释,但他对引证盐谷氏的观点还是作了一定的表述,如文中有“说者谓”等词语;在序言中也特别声明中国小说有史是“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就鲁迅当时所能接触到的外文参考书,这主要是盐谷著。然而,围绕这一问题,不懂日文的陈源等人当初并没有对两著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比较,道听途说,即视鲁著为剽窃之作,妄加非议,造成了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相关人士的势不两立,这已完全超出了学术之争的范畴。不言而喻,在论著的立意和结构上,盐谷著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在观点和论述方面,鲁著的独创性是不容置疑的。
自从两著出版之后,鲁迅与盐谷温的学术交流和相互借鉴得以实现,如两著的修订版都吸收了对方的研究成果,并采用了所发现的新材料;1949年10月,盐谷温还将修订版《支那文学概论》下篇改名为《中国小说的研究》单独出版,意在深化中国小说史的探究。
回顾近代中外学术交流史,西学东渐的风潮无疑对中国小说史的构建产生过重要影响,而鲁迅和盐谷温可以说是东西方学术互动的实践者,其研究成果都为中日近代学术交流增添了值得称颂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