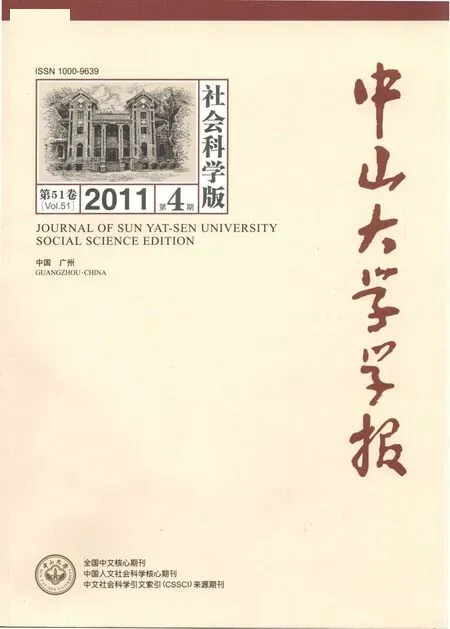吕本中“活法”诗论针对性探微*
祝尚书
吕本中在所作《夏均父(倪)集序》中,极力主张作诗用“活法”,因而在中国文学史,特别是诗歌发展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引起了后代研究者的兴趣,尤其对该序的现实背景与针对性问题,当下学者颇多议论和猜测。由于现存《集序》为节文,宋代文献又没有相关的记载,故这些问题只能靠学者们自己解读。一般说来,提出某种理论,未必一定有特定的指向(比如沈约的“四声论”);即便有所指,也不必事事针对“现实”。吕氏的“活法”论,是对江西宗派诗法的总结,而他在《江西诗社宗派图序》中说,诗歌至“元和之末无足论者,衰至唐末极矣”;“至于豫章(黄庭坚)始大出而力振之,后学者同作并和,尽发千古之秘,亡馀蕴矣。”①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序》,《云麓漫抄》卷14,涉闻梓旧本。则就宏观论,吕本中针对的显然是自元和末到黄庭坚之前的诗歌之“衰”,认为黄庭坚始“力振”之,而江西诗社诸人“同作并和”,然后方“尽发千古之秘”——这就是“活法”论的大背景。
当然,若说吕氏在南北宋之际一再强调“活法”,必有更现实的环境或背景,也不能说没有道理。目前学界论其现实意义,盖主要有针对黄庭坚字法、句法体系和江西诗派末流之说。然若深考之,这类说法很值得怀疑。吕本中作为江西诗社中人,又是后期江西诗派的领袖,他绝无从内部“造反”的可能。据笔者初步探究,吕本中很可能是针对当时受官方词科四六“典雅派”影响的诗坛,因试论之。
一、吕本中“活法”论针对性质疑
在《夏均父集序》中,吕本中所述诗歌“活法”,为治中国文学史,特别是治宋代文学的学者所熟知,为了说明问题,仍先节录于下:
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以与语活法矣。谢玄晖有言,“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此真活法也。近世惟豫章黄公,首变前作之弊,而后学者知所趋向,毕精尽知,左规右矩,庶几至于变化不测。②刘克庄:《江西诗派》引,《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5。按此序当即王正德《馀师录》卷3所引吕本中《远游堂诗集序》,文字与此略有异同。
还在早年,吕本中作《外弟赵才仲(柟)数以书来论诗因作此答之》诗,在评其外弟诗歌艺术时,就已表述了“活法”论的梗概:“前时少年累,如烛今见跋。胸中尘埃去,渐喜诗语活。孰知一杯水,已见千里豁。初如弹丸转,忽如秋兔脱。旁观不知妙,可爱不可夺。”①吕本中:《东莱先生诗集》卷3,四部丛刊续编本。在序文及此诗中,吕本中乃正面提出自己的诗学主张;当下研究者要追问其现实针对性,企图通过解读获得隐藏在“活法”论背后的真相,归纳起来大致有两说(一般是合两说而为一)。由于这些说法较普遍(前此笔者亦持是见),若引出某一具体论者来有失公平,于是我们简述其主要论点和论据,而略其出处。
一是针对黄庭坚字法、句法体系说。据释惠洪《冷斋夜话》、《天厨禁脔》,黄庭坚曾提出“夺胎换骨法”、“用事法”、“造语法”、“句中有眼”、“象外句”、“错综句法”、“对句法”等等,研究者认为这些“法”都可能成为死法。当时学界对字法即有批评,如叶梦得曰:
诗人以一字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变化开阖,出奇无穷,殆不可以形迹捕……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仿用之,偃蹇狭陋,尽成死法。不知意与境会,言中其节,凡字可用也。②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20页。
学者们认为,此批评应当就是针对黄庭坚字法、句法论的,故吕本中提出“活法”,应与叶梦得相类,乃矫黄氏句法、字法之弊。
二是针对江西派末流说。南宋初,诗学界对江西诗派有所批评。如与吕本中同时的王庭珪,曾点名批评“江西社”道:“近时学诗者悉弃去唐、五代以来诗人绳尺,谓之江西社,往往失故步者有之。”③王庭珪:《跋刘伯山诗》,《卢溪集》卷48,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吕本中曰:
潘邠老(大临)言:“七言诗第五字要响,如‘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翻’字、‘失’字是响字也。五言诗第三字要响,如‘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浮’字、‘落’字是响字也。所谓响字,致力处也。”予窃以为字字当活,活则字字自响。④吕本中:《童蒙诗训》,《宋诗话辑佚》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87,594,604页。
吕氏所涉有些“鸡毛蒜皮”,若说针对江西诗派未免夸大,故提出所谓“江西派末流”说。表面看来,似乎也成理。
但由上述,我们生出两点疑问。
其一,吕本中高倡“活法”,果真是针对黄庭坚的句法、字法体系么?前引《夏均父集序》特别指出“世惟豫章黄公,首变前作之弊,而后学者知所趋向,毕精尽知,左规右矩,庶几至于变化不测”,则在吕氏眼里,黄庭坚的句法、字法体系非但不是“弊”,而正是活法;除非有证据说明吕本中这里是言不由衷的谀词,那么两者之间的矛盾就难以消解。从现存文献看,吕本中十分崇敬黄庭坚。比如“活法”讲“悟”,在吕氏看来,黄庭坚是能“悟入”的典范:“作文必要悟入处,悟入必自工夫中来,非侥幸可得也。如老苏之于文,鲁直之于诗,盖尽此理也。”⑥吕本中:《童蒙诗训》,《宋诗话辑佚》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87,594,604页。他又说,黄庭坚诗“极风雅之变,尽比兴之体,包括众作,本以新意者,唯豫章一人”,因而“当永以为法”⑦吕本中:《童蒙诗训》,《宋诗话辑佚》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87,594604页。。这不仅是吕本中的个人之见,也为南宋许多诗人所认同,如杨万里《送分宁主簿罗宏材秩满入京》诗曰:“要知诗客参江西,政如禅客参曹溪。不到南华与修水(按:修水为黄庭坚故乡,此以指代),于何传法更传衣?”⑧杨万里:《诚斋先生集》卷38,四部丛刊初编本。
至于叶梦得批评“今人多取其(杜甫)已用字模仿用之,偃蹇狭陋,尽成死法”,谓其批评江西派中个别诗人是可能的⑨如潘大临即有此病。《王直方诗话》曰:“邠老作诗,多犯老杜,为之不已,老杜亦难为存活。使老杜复生,则须共潘十厮炒。”《宋诗话辑佚》上册,第22页。,若曰是在矫黄,则没有根据。
其二,吕本中“活法”论是不是矫江西诗派“末流”呢?王庭珪《跋刘伯山诗》点名批评“江西社”作诗“往往失故步者有之”,从“有之”的口气看,显然针对的只是“江西社”中的个别人,王氏对他们“失故步”有所不满。“失故步”何所指?该跋下文道:“鲁直之诗,虽间出险绝句,而法度森严,卒造平淡,学者罕能到。传法者必于心地法门有见,乃可参焉。”则他所谓“失故步”,乃指一味求“险绝句”而不能平淡。这是来自外部个人的批评,未必是当时诗界的共识,故与吕本中提出“活法”论关系不大。至于本中评潘大临(字邠老)“响字”说,他并非不赞成字要“响”,只是说用活法则可“字字自响”。这纯属“学术讨论”,无关褒贬。考潘大临生于仁宗嘉祐五年(1060),约卒于大观二年(1108)①伍晓蔓:《江西宗派研究》第8章第1节,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尝“得句法于东坡”,黄庭坚称其为“天下奇才”②见潘淳:《潘子真诗话·潘邠老诗》,《宋诗话辑佚》上册,第309、310页。。则潘氏在江西诗社中辈分甚高,虽作诗有“多犯老杜”的毛病(见上文注),但吕本中将他谱入《宗派图》,显然对他的诗歌仍持肯定态度。无论就年辈还是创作成绩论,谓之为“江西末流”皆不妥。况吕本中作《夏均父集序》时③按《夏均父集序》作于绍兴三年(1133)。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0《江西宗派》曰:“蕲州人夏均父,名倪,能诗,与吕居仁友善。既没六年,当绍兴癸丑(三年,1133)二月一日,其子见居仁岭南,出均父所为诗,属居仁序之。”,潘氏已过世二十多年,更没有以矛头相向的必要。
在现存文献中,吕本中的确有批评江西后学的言论。其《与曾吉甫论诗第二帖》曰:“诗卷熟读……其间大概皆好,然以本中观之,治择工夫已胜,而波澜尚未阔;欲波澜之阔去,须于规摹令大,涵养吾气而后可。规摹既大,波澜自阔,少加治择,功已倍于古矣……退之云:‘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则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皆宜。’如此,则知所以为文矣……近世江西之学者,虽左规右矩,不遗馀力,而往往不知出此,故百尺竿头,不能更进一步,亦失山谷之旨也。”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49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33页。然细揣此帖,他批评的是江西后学作品的规模不大,波澜不阔,“虽左规右矩”,然不知以“气”运之,有些“小家子相”。这与“活法”关系不大。
总之,在笔者看来,吕本中提出诗歌“活法”论,没有针对江西“宗派之祖”黄庭坚的任何可能⑤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序》称“(江西)宗派之祖曰山谷”,见《云麓漫抄》卷14。,也主要不是批判“江西末流”之弊——他作为江西诗法的传人,虽对后学有所针砭,但若仅此而已,那未免将“活法”论理解得过于狭隘。吕本中是“江西宗派”的骨干,又是后期江西诗派的领军人物,而绝不是欲从内部反戈一击的“造反”者——这个角色定位是难以轻易改变的。
二、“活法”论针对词科四六死法说
那么吕本中“活法”论到底针对谁呢?上节所述学界已有的论点,都将目光投向江西诗派自身,而没有顾及吕本中所处的时代,不能不说视野较窄。看来需要转换角度。于是,我们从宋末元初作家方回几句与吕本中并不相干的话中,似乎可以找到新的思路。方回《读张功父(镃)南湖集并序》有诗赞张镃道:“端能活法参诚叟,更觉豪才类放翁。”然后颇有感触地说:
南渡以来,精于四六而显者,诗辄凝滞不足观。骈语横于胸中,无活法故也。然则绍圣词科,误天下士多矣。⑥《南湖集》卷首,《知不足斋丛书》本。
则在方回看来,南宋诗的“死法”源于绍圣初所立词科。因为词科“骈语”(四六)的作法是死法,而诗人用四六法作诗,所以诗歌也就“无活法”。为了印证方回之说,我们还可引叶适对四六、韵语并进而对词科制度的尖锐批评。他写道:
朝廷诏诰典册之文,当使简直宏大,敷扬义理,以风晓天下……若乃四六对偶,铭檄赞颂,循沿汉末以及宋、齐,此真两汉刀笔吏能之而不作者,而今世谓之奇文绝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于朝廷,何哉?自词科之兴,其最贵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为陋而无用。士大夫以对偶亲切、用事精的相夸,至有以一联之工而遂擅终身之官爵者。此风炽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后居卿相显人、祖父子孙相望于要地者,率词科之人也。①《宏词》,《水心别集》卷13。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宏词》曰:“先生(叶适)《外藁》(即收在《水心别集》之文),盖草于淳熙自姑苏入都之时,是书流传则盛于嘉定间。”则所谓“七八十年来”,亦自北宋末算起。
以“对偶亲切、用事精的”为能事,畸型的审美价值观决定了词科四六的变态追求,而这种“绝技”,与“变化不测”的“活法”正好南辕北辙。今按:《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二载,哲宗绍圣元年(1094)五月四日中书省上言:“有唐随事设科,其名不一,故有词藻宏丽、文章秀异之属,皆以众之所难劝率学者。今来既复旧法,纯用经术取士,其应用文词如诏诰、表章、箴铭、赋颂、赦敕、檄书、露布、诫谕之类,凡诸文体施之于时不可阙者,在先朝亦尝留意,未及设科。”哲宗于是下诏“别立宏词一科”②叶适:《宏词》,其曰:“绍圣初,既尽罢词赋,而患天下应用之文由此遂绝,始立博学宏词科。”(《水心别集》卷13)按绍圣初所立为“宏词科”,叶适乃就其终极而言。。则宏词科的创立,完全是为了弥补王安石罢诗赋而用经义取士造成的四六应用文写作人才的匮乏。徽宗大观四年(1110),改为“词学兼茂科”。南宋绍兴三年(1133)七月,高宗又下诏改“词学兼茂科”为“博学宏词科”。这就是南宋和后代通称的“词科”。绍兴法规定,博学宏词科考试以制、诰、诏、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十二件为题③参见《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之一一、《容斋三笔》卷10。。这十二种文体,可分为四大类:一是四六文,包括制、表、露布、檄四种;二是四六或散体皆可,包括诏、诰二种;三是只能用散文(古文)的二种:序、记;四是韵语:箴、铭、赞、颂。王应麟《词科指南》卷1引平斋洪公(咨夔)曰:“制、表,如科举之本经,所关尤重。”并举例道:“隆兴元年(1163)陈自修试颂及露布,冠绝一场,偶表、制中有疵,因不取。”④《词学指南》卷1,附《玉海》卷201,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则制、表为词科中最重要的考试文体,而它们都必须用四六;说明自绍圣设科起,四六文在词科考试中就占有主导地位。
据上引方回的说法,词科四六之所以破坏了诗歌创作,是因为擅长此道的人“骈语横于胸中”,所以作诗也就拘谨“凝滞”,而不懂飞动驰掷的“活法”,故所作诗“不足观”。我们要想明白骈语何以“无活法”,就必须首先了解词科四六的作法;而要弄清四六作法,又必须从“宋体四六”的流派说起。
四六文肇端于齐梁,兴起于晚唐,鼎盛于两宋。宋代四六文的发展方向,杨囦道在其所著《云庄四六馀话》中描述得颇为精确。他写道:
本朝四六,以刘筠、杨大年(亿)为体,必谨四字、六字律令,故曰四六,然其弊类俳。欧阳公深嫉之,曰:“今世人所谓四六者,非修所好,少为进士不免作,自及第,遂弃不作。在西京佐三相幕,于职当作,亦不为作也。”如公之四六有云:“造谤于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阴以中人;宣言于庭者,遂肆鸣枭之恶音,孰不闻而掩耳。”俳语为之一变。至东坡为四六,曰:“禹治兖州之野,十有三载乃同;汉筑宣防之宫,三十馀年而定。方其决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复也,盖天助有德,而非人功。”其力挽天河而涤之,偶俪甚恶之气一除,而四六之法亡矣。
皇朝四六,荆公谨守法度,东坡雄深浩博,出于准绳之外,由是分为两派。近时汪浮溪(藻)、周益公(必大)诸人类荆公,孙仲益(觌)、杨诚斋(万里)诸人类东坡。大抵制诰牋表贵乎谨严,启疏杂著不妨宏肆,自各有体,非名世大手笔未易兼之。⑤《云庄四六馀话》,《历代文话》第1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8页。
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卷2也有类似的论述:
本朝四六,以欧公为第一,苏、王(安石)次之。然欧公本工时文,早年所为四六,见别集,皆排比而绮靡,自为古文后,方一洗去,遂与初作迥然不同。他日见二苏四六,亦谓其不减古文。盖四六与古文同一关键也。然二苏四六尚议论,有气焰,而荆公则以辞趣典雅为主,能兼之者欧公耳。水心于欧公四六暗诵如流,而所作亦甚似之。顾其简淡朴素,无一毫妩媚之态,行于自然,无用事用句之癖,尤世俗所难识也。⑥《荆溪林下偶谈》卷2,《历代文话》第1册,第554页。
由上述可知,欧阳修用古文改造“昆体四六”,产生了一种新的骈文体裁,使传统的四六文为之一变,文学史称之为“宋体四六”。其后,“宋体四六”内部又分成了以苏轼和王安石为代表的两派。元代学者袁桷说:“大要寡学而才气差敏捷者,直师东坡,南渡以后皆宗之,金源诸贤只此一法。惟荆公一派以经为主,独赵南塘(引者按:汝谈,今有《南塘先生四六》一卷传世)单传,莫有继者。”①袁桷:《答高舜元十问·问四六格式及速成之方检阅之书》,《清容居士集》卷4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袁氏认为“寡学而才气差敏捷者”方学东坡,有些绝对(学东坡的不一定都“寡学”),但对两派特征的表述尚清晰。要之,由“昆体四六”到欧阳修“宋体四六”,苏轼继承欧氏,发扬其以才气取胜的一面,而王安石则于欧外自辟蹊径,“以经为主”,追求“典雅”。何谓“典雅”呢?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48作了明确的解释:
余尝考次自秦、汉至唐及本朝景祐以前词人,虽工拙特殊,而质实近情之意终犹未失。惟欧阳修欲驱诏令复古,始变旧体。王安石思出修上,未尝直指正言,但取经史见语错重组缀,有如自然,谓之典雅,而欲以此求合于三代之文,何其谬也!②《习学记言序目》卷48,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则所谓“典雅”,就是谨守法度,乃至组缀经史全句。可以想见,在绍圣初至北宋末“绍述”的政治环境下,主导词科考试的只能是王安石“新学”,词科四六必然都是荆公派的“典雅”体,而东坡派这时被完全边缘化。但“典雅”的结果,四六文也弊病丛生。元代学者盛如梓对南北宋之交的四六文作过很不客气的批评,他写道:“四六文字变于后宋(指南宋)。南渡前,只是以文叙事,不用故事堆垛。(北宋)末年尚(经史)全句,前辈谓赋体也。或无裁制,塞滞不通,且冗长,使人厌观,作者用之,方谓得体。”③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卷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安石的四六主张,直接影响到他的诗学观。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曰:
荆公诗用法甚严,尤精于对偶。尝云:用汉人语,止可以汉人语对,若参以异代语,便不相类。如“一水护田将绿去,两山排闼送青来”之类,皆汉人语也。此惟公用之,不觉拘窘卑凡。如“周颙宅在阿兰若,娄约身随窣堵波”,皆以梵语对梵语,亦此意。尝有人面称公“自喜田园安五柳,但嫌尸祝扰庚桑”之句,以为的对。公笑曰:“伊但知柳对桑为的,然庚亦自是数。”盖以十干数之也。④《石林诗话》卷中,《历代诗话》,第422、423页。
我们再回顾方回的话:“南渡以来,精于四六而显者,诗辄凝滞不足观。骈语横于胸中,无活法故也。”对照上引盛如梓“使人厌观”语,则诗受其影响而“不足观”(方回语),也就自然而然了。因绍圣后禁诗(虽政和后弛禁,但并未解禁),所以方回只论“南渡以来”;又因绍圣后至北宋末进士科不考诗赋,所以科举直接影响诗歌歌创作的,便只有“赋体”化了的词科四六。由讲究对偶到组缀经史全句,甚而必须汉人语对汉人语,梵语对梵语,如此拘泥,岂有活法可言?则吕本中提出“活法”论,如果说是针对官学词科四六“典雅派”影响下的诗坛,较之针对江西派自身来,可能性要大得多,于情于理也更能令人信服。
三、从“活法”内涵看其针对性
宋室南渡后,王氏“新学”衰落,诗学得到恢复。由词科出身或学习词科的人欲赶“时麾”,也开始作诗。然而他们素不娴此道,此前深受骈语影响,只好将组缀经史的惯技移入诗法,那当然只有“死法”了,所以吕本中高倡“活法”与之对抗。吕本中的所谓“活法”,在《夏均父集序》中表述得已很明白,简言之,即作诗既要遵循规矩,又不能拘于规矩。要能“变化不测”,有法而无定法,法在有无之间。据研究,吕本中的“活法”论源于禅宗,云门宗缘密禅师就讨论过“死句”、“活句”的问题⑤见普济:《五灯会元》卷15(下册),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84年,第935页。,大意是意在言内为死句,意在言外方是活句。北宋后期不少诗人以禅喻诗,将禅宗“悟入”的思维方式引入诗法,而“吕氏家学,大率在于儒禅之间”①黎德清:《朱子语类》卷132,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171页。,故他的“活法”论有着深厚的佛学渊源。范温《潜溪诗眼》说:“识文章者,当如禅家有悟门。夫法门百千差别,要须自一转语悟入。如古人文章,直须先悟得一处,乃可通其他妙处。”②《宋诗话辑佚》上册,第328页。所以“活法”也就是讲“悟”和“悟入”之法,故吕本中的“活法”还有个简捷的表述,说要能“将死蛇弄得活”③此是吕本中引禅家语,见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83年,第463页。。诗人曾几曾向吕本中请教“诗律”,后来在《读吕居仁旧诗有怀其人作诗寄之》诗中写道:“学诗如参禅,慎勿参死句。纵横无不可,乃在欢喜处。又如学仙子,辛苦终不遇。忽然毛骨换,正用口诀故。居仁说活法,大意欲人悟。常言古作者,一一从此路。岂惟如是说,实亦造佳处。其圆如金弹,所向如脱兔。风吹春空云,顷刻多态度。锵然奏琴筑,间以八珍具。”④陈思、陈世隆:《两宋名贤小集》卷19,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则“悟”在纵横驰骋间,在忽然变化间,而终能圆转奔突,姿态横生。
但是,吕本中在《夏均父集序》中所述“活法”只是一种理论,一种理想的“状态”。到底如何操作呢?张孝祥在《题杨梦锡(冠卿)〈客亭类稿〉后》中评杨氏之文道:“为文有活法,拘泥者窒之,则能今而不能古。梦锡之文,从昔不胶於俗,纵横运转如盘中丸,未始以一律拘,要其终亦不出于盘。”⑤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卷2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81页。在宋人的语境中,“今”、“俗”都是指科举时文,则为文从古,圆转如盘中丸,不拘于律,即可臻于“活法”。庆元时学者俞成《萤雪丛话》卷上有一段议论,将“活法”说得更具体:
文章一技,要自有活法。若胶古人之陈迹而不能点化其句语,此乃谓之死法。死法专祖蹈袭,则不能生于吾言之外;活法夺胎换骨,则不能毙于吾言之内。毙吾言者生吾言也,故为活法。伊川先生尝说《中庸》“‘鸢飞戾天’,须知天上者更有天;‘鱼跃于渊’,须知渊中更有地。会得这个道理,便活泼泼地。”吴处厚尝作《剪刀赋》,第五隔对:“去爪为牺,救汤王之早岁;断须烧药,活唐帝之功臣。”当时屡窜易,“唐帝”上一字不妥贴,因看游鳞,顿悟“活”字,不觉手舞足蹈。吕居仁尝序江西宗派诗,若言“灵均自得之,忽然有入,然后唯意所出,万变不穷,是名活法”。杨万里又从而序之,若曰“学者属文,尝悟活法。所谓活法者,要当优游厌饫”。是皆有得于活法也如此。吁,有胸中之活法,蒙于伊川之说得之;有纸上之活法,蒙于处厚、居仁、万里之说得之。⑥《萤雪丛话》卷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则所谓“活法”,就是不胶着“古人陈迹”,而能对古人句语进行“点化”。死法是蹈袭,是硬生生嵌入古人“陈迹”,故不能言外生意;活法是“夺胎换骨”,使文意在言外活了起来。“毙吾言者生吾言”,谓虽融化了古人死句,但却诞生了活泼泼的文外之境。这就是“点化”之功,就是“将死蛇弄得活”。俞氏自言他所论“纸上之活法”得之于吴处厚、吕本中和杨万里,从而将“死法”、“活法”的内涵表述得更为简明易懂,且具可操作性。
与俞成大致同时的学者王正德,在谈“文章态度”时说:“文章态度如风云变灭,水波成文,直因势而然。必欲执一时之迹以为定体,乃欲系风捕影也。”⑦王正德:《馀师录》卷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他虽未用“活法”一词,所论实即不执“一时之迹”的“活法”。杨万里《诚斋诗话》又举活法诗例道:
庾信《月诗》云:“渡河光不湿。”杜云:“入河蟾不没。”唐人云:“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尽日闲。”坡云:“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尽日凉。”杜《梦李白》云:“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山谷《簟诗》云:“落日映江波,依稀比颜色。”退之云:“如何连晓语,祇是说家乡。”吕居仁云:“如何今夜雨,祇是滴芭蕉。”此皆用古人句律,而不用其句意,以故为新,夺胎换骨。⑧《诚斋诗话》,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第148页。将古人句律加以改造,用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就是“以故为新”,也就是所谓“夺胎换骨”。清代学者王夫之在论诗格、诗法和经义(指八股文)程式时也说:
(岑参《送张子尉南海》诗)“海暗三山雨”接“此乡多宝玉”不得,迤逦说到“花明五岭春”,然后彼句可来,又岂尝无法哉?非皎然、高棅之法耳。若果足为法,乌容破之?非法之法,则破之不尽,终不得法。诗之有皎然、虞伯生(集),经义之有茅鹿门(坤)、汤宾尹、袁了凡(黄),皆画地成牢以陷人者,有死法也。死法之立,总缘识量狭小,如演杂剧,在方丈台上,故有花样步位,稍移一步则错乱;若驰骋康庄,取途千里,而用此步法,虽至愚者不为也。①戴鸿森:《薑斋诗话笺注》卷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68页。“海暗三山雨”数句,出岑参《送张子尉南海》诗。戴氏谓船山之意,是说“孤立的讲究对偶之类,便是所谓死法;如此诗有其本身之内在脉络,便是真正的法——活法”。
王夫之由诗法论到八股文,其意亦在反对死法。唐僧皎然著有《诗议》、《诗式》,其《诗式》专论四声、对偶、势、体等等诗歌法则,王夫之认为这都是“死法”。对所有“文章”来说,道理都是相同的,没有活法就不可能写出精彩的作品。曾季貍《艇斋诗话》曰:“后山论诗说换骨,东湖(徐俯)论诗说中的,东莱(吕本中)论诗说活法,子苍(韩驹)论诗说饱参。入处虽不同,然其实皆一关捩,要知非悟入不可。”②《艇斋诗话》,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第296页。“悟入”虽来自禅宗,其道理则是世俗的,也并不艰深,用宋人的话说,就是用“点化”(或称“融化”)、“脱胎换骨”的方法,以摆脱古人陈迹的羁绊,让思想自由飞翔,使语言灵动清新,去书写那些富有诗意的东西。
明白了“活法”诗论的内涵,我们似乎更有把握地说,如果吕本中《集序》果有所指的话,不可能是针对立身于“脱胎换骨”理论根基之上、以“悟入”为法门的黄庭坚及江西诗派;即以诗受四六骈语影响论,前引《云庄四六馀话》谓东坡派“雄深浩博,出于准绳之外”,显然也是活法,不应该是他要攻击的对象。于是结论与上节相同,吕本中“活法”论的矛头,很可能就是指向绍圣后受词科四六影响的诗人,因为他们正以组缀经史“陈迹”为能事,而这恰是产生“死法”的根源。
四、吕本中抨击官学诗坛的客观可能性
我们说吕本中“活法”论的矛头所向是官学词科四六影响下的诗坛,还存在客观可能性。吕本中(1084—1145),字居仁,元祐宰相吕公著曾孙,寿州(今安徽凤台)人。绍圣间党祸起,他作为元祐党人的亲属受到牵连,没有机会参加科举考试,徽宗时代只能做一些幕职小官,且屡遭排挤,于是专工于诗。直到绍兴六年(1136)方召赴行在,特赐进士出身,擢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绍兴八年迁中书舍人,兼侍讲,兼权直学士院。然而又忤秦桧,遂提举太平观以卒。
吕本中的经历和遭遇,决定了他对绍圣后王安石“新学”主导下的科举(包括词科)有着天然的心理逆反。周必大《跋韩子苍与曾公衮钱逊叔诸人倡和诗》道:
崇宁、大观而后,有司取士专用王氏学,甚至欲禁读史作诗,然执牛耳者未尝无人。凡绍兴初以诗名家,皆当日人才也。今读韩子苍(驹)与钱逊叔(伯言)、曾公衮(纡)等临川唱酬,略可睹矣。或疑所以然,予曰:举子在场屋,为学不专,为文不力,既仕则弃其旧习,难乎新功。有志之士其操心也专,其学古也力,譬之追风籋云之骥,要非绳墨所能驭。故子苍诸贤往往不由科举而进,一时如程致道(俱)、吕居仁(本中)、曾吉甫(几)、朱希真(敦儒)皆是也。③周必大:《周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8,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又跋曰:
国家数路取人,科举之外多英才。自徽庙迄于中兴,如程致道、吕居仁、曾吉甫、朱希真,诗名籍籍,朝廷赐第显用之。今观曾公衮、钱逊叔、韩子苍诸贤,又皆翰墨雄师,非有司尺度所能得也。①周必大:《周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8,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作为“不由科举而进”的诗人,吕本中有如“非绳墨所能驭”的骏马,其诗歌理论自然也与“有司尺度”圆凿方枘之不入。不过,诗人盖秉承“派祖”黄庭坚处逆境而能心平气和的遗范,在现存诗歌、诗话及文章中极少表达对政治乃至诗坛是非的意见,然而虽讳莫如深,也难免偶露峥嵘。如在《客居书怀奉寄介然若谷才仲兼简信民》诗中,就嘲讽了那些得志的新进:“儿曹乳臭在,瞑目纷黑白。虽无未见书,颇多雌黄笔。出言则周孔,而不辨菽麦。啾啾要酬和,内顾颇牵率。”②吕本中:《东莱先生诗集》卷1,四部丛刊续编本。可以想见,言必周孔、牵率酬和的诗歌,恐怕多是“死句”。这类“乳臭儿”,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前引方回所谓出身词科、“精于四六而显”的官场文人,他虽说的是“南渡后”,其实北宋末何尝不如此。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载:“是岁(何执中修敕令禁诗的政和元年)冬初雪,太上皇(徽宗)意喜,吴门下居厚首作诗三篇以献,谓之‘口号’。上和赐之。自是圣作时出,讫不能禁,诗遂盛行于宣和之末。”这不就是上引《客居书怀》所谓“啾啾要酬和,内顾颇牵率”的台阁酬和么?前引吕本中《外弟赵才仲(柟)数以书来论诗因作此答之》诗,即已提出“活法”,该诗作年虽无法确考,但作于北宋末是可以肯定的。如此说来,主张“活法”诗论的背景,看似隐约难知,却又依稀可睹。
吕本中虽出身贵族,但由于“元祐党祸”的冲击,使他拉近了与平民的距离。从其诗集可知,他平生所与,多为平民小吏,极少达官显宦。因此,较之“出言必周孔”的官学来,其思想也颇有些“草根”:他并非江西人,作诗却以江西为宗,又奉元祐党人黄庭坚为宗派领袖,这本身就是对官方诗坛的蔑视。经过“靖康之难”和朝廷再造,旧的诗风也必然要发生变化,而政治气候的逆转,决定了吕本中也随之“翻身”。在新的时代里,他义不容辞地担负起改造诗坛的重任。袁桷《书黄彦章诗编后》说:“元祐之学鸣绍兴,豫章太史(黄庭坚)诗行于天下。方是时,纷立角进,漫不知统绪,谨懦者循音节,宕跌者择险固,独东莱吕舍人(本中)悯而忧之,定其派系(按指《江西诗社宗派图》),限截数百辈无以议,而宗豫章为江西焉。”③袁桷:《答高舜元十问·问四六格式及速成之方检阅之书》,《清容居士集》卷48,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则所作《夏均父集序》,与《宗派图》盖同一用心,既与“循音节”、“择险固”的官学风气作斗争,又要示天下以法,带领江西诗派更健康地发展。
综上所论,吕本中“活法”诗论原本是他的诗学理论建设,若一定要探究现实针对性,那么笔者以为学界的解读或失之准确:在吕本中心里,黄庭坚是他崇拜的偶像,提倡诗歌“活法”的元勋,而后期江西诗派则是他自己的“队伍”,他不可能将矛头对内而自乱阵脚。倒是循方回《读张功父南湖集并序》所提示的思路,以“活法”论针对的是两宋之际词科四六“典雅派”影响下的诗坛,也许更接近真相。当然,这仍如“瞎子摸象”,未必就探骊得珠,聊献瞽说以质诸方家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