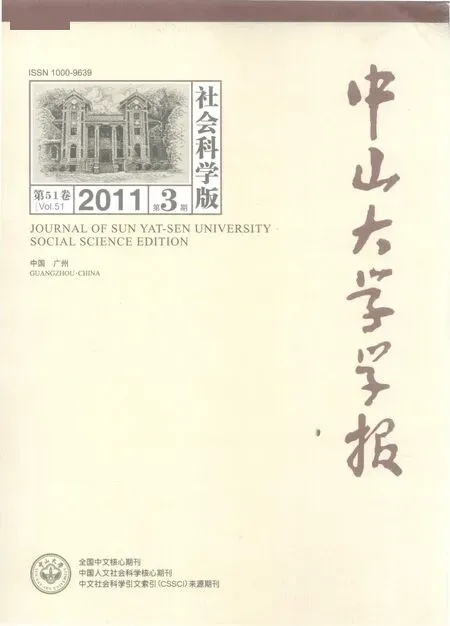欧洲的理性理念:省思胡塞尔的文化论述*
游淙祺
前 言
近二十年来胡塞尔的文化论述,特别是其欧洲中心主义的论调引来不同立场的解读方式。捍卫胡塞尔的学者指出,依据胡塞尔的观点,不能从地理区域来解释欧洲,而该从超越论(transcendental)的角度来看欧洲,欧洲意味着所有人类都该达到的一个超越论境地(transcendental status)(Sepp 2004:297)。如此一来,认同欧洲文化便不再意味着认同于某个异文化,而是让自己的理性及人性获得提升。具体而言,只要人们得以认识带有开放精神的所谓“一个世界的理念”(“the idea of one world”),他便算是欧洲人(Held 1989:22)。质疑其观点的学者则认为我们不该过度强调当前全球欧洲化或西化(Europeanization or Westernization)的含义,换个角度想,全球各地的文化不正是在受到欧洲文化的冲击之下,藉由吸取欧洲文化而重新调整自身的文化吗?所谓欧洲化的含义换成当地的观点来说不就是外来文化的内在化吗(Holenstein 1998:238)?再者,所谓“欧洲”的含义本身就具有各种解读的可能性,在历史发展中,文化的多样性不也是欧洲的核心特征吗?为什么非得高举欧洲中心主义式的普遍主义论调?凭什么要我们非得接收欧洲文化至高无上的想法,文化与文化之间不是从来就处在互相渗透、相互学习的过程中吗(Waldenfels 1997:80;2004:285)?
身为非欧洲人的东亚学者该如何面对胡塞尔的文化观点?假如东亚学者反对胡塞尔欧洲中心主义的论调,是否会连带影响他们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接纳?反过来看,是不是基于对胡塞尔思想的接受因而也一并接纳胡塞尔的该项文化观点?从事现象学研究的东亚学者可以说无从回避这个问题。为了思考这个问题,本文首先将说明胡塞尔的欧洲论述以及密切相关的文化差异论述,其次阐释西方学者对这些论述的响应或批判,最后则在结论部分提出个人的一些想法。
一、胡塞尔的欧洲论述
胡塞尔的欧洲论述主要出现在《欧洲科学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关于互为主体性的现象学》(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Husserliana XIII—XV)及《生活世界》(Die Lebenswelt.Auslegungen der vorgegebenen Welt und ihrer Konstitution.Texte aus dem Nachlass(1916—1937),Husserliana XXXIX)等著作中,其中以他1935年演讲于维也纳的“欧洲人的危机与哲学”(Die Krisis des europäischen Menschentums und die Philoso phie)(收录于Krisis,Hua VI,314—348)最具代表性,本文的论述便是以该篇讲稿为主要参考依据。
胡塞尔论述欧洲的脉络在于:反省欧洲近代以来为何出现科学危机,当代欧洲人所面临的危机,其真正含义为何,进而思索如何对治这项危机。为了理解胡塞尔如何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先知道他对“欧洲”的界定。
胡塞尔指出,欧洲不是用地理疆界来界定的。不是住在地理意义上的欧洲区域的人就可以被称为欧洲人(europäisches Menschentum)的,例如在欧洲各地流浪的吉普赛人。反而一些不居住在欧洲疆界之内的人,例如美国人则在精神意义上属于欧洲(但不包含爱斯基摩人或是印地安人)。胡塞尔所强调的是:所谓欧洲是就其精神生活、精神活动与精神创造的整体来说的。任何个人,无论他是属于哪一个社会阶层、家庭、氏族或民族,跟其他欧洲人在精神上都是内在地结合在一起。个人也好,社会组织、文化成就也好,莫不分享此一共同特质(Krisis,319)。
那么,什么是“欧洲的精神型态”(die geistige Gestalt Europas)呢?胡塞尔指出,有一种历史使命或目的性(Teleologie)内在于欧洲的精神历史发展中;从普遍的观点来看,这意味着一种新的人类发展阶段,一种只愿基于理性的理念而活的生命型态(Krisis,319)。受此理念引导而发展出来的科学文化意味着原本的文化被彻底改变(Krisis,325)。就整个人类文明发展来看,这种改变首度发生在公元前7世纪的古希腊地区。这个作为欧洲精神根源的古希腊哲学之诞生是所有人类历史发展中独一无二的事件。胡塞尔如此强调其独特性,为的是反对一般的认识,以为古印度及古代中国也都曾经出现过哲学,只是型态有所不同。胡塞尔不认为诞生于古希腊的哲学也曾经在其他古文明出现过,因为无论是古印度或古代中国都不曾出现具关键因素的理论执态(theoretische Einstellung)(Krisis,325)。
执态的含义乃是“一种预先表明的意志方向或兴趣的意志生活的习惯性稳定型态。特定的生活往往在这种被当作正常的持续的型态中进行”(Krisis,326)。只有在古希腊才发展出纯粹的理论执态。只有在那里,才出现一群人,群策群力,历经世代,致力于哲学与科学的研究。简言之,“理论的执态在这些希腊人身上有其历史渊源”(Krisis,326)。
理论的执态产生于执态的转变(Umstellung)。每一个族群或时代都有其形塑文化正常型态的主要力量,即胡塞尔所谓“自然的”(natürlich)、“朴实的”(urwüchsig)执态。其他的执态都可被视为这个执态的转换形式(Krisis,326—327)。这个原初的执态表现于人世世代代活在群体里——无论是家庭、氏族或民族。自然的生命在这样的执态里素朴地一头栽入世界中,在他们的生活里,世界作为普遍的视域多多少少被意识到,但却从来没有被当作主题来加以思考(Krisis,327)。
为了让活在世界中的人能够转变执态,往往需要某些特殊的动机,使得自身所在的视域能够成为主题,而且持续成为兴趣之所在(Krisis,327)。执态的转变只发生于一时,要让它具有持续性则需要意志力的坚持,而且让它落实在特定的文化形式中(Krisis,327—328)。执态的转变有三种类型:一种是为生活的现实目的(Lebensinteresse)服务,所以是实践性的,除了一般政治性的执态之外,它还包括宗教—神话的执态(religiös-mythische Einstellung)。第二种是理论执态,它完全是非实践性的(Krisis,328)。除此之外,胡塞尔指出,还有第三种执态,这时理论变成实践,这种新类型的执态将促成新的人性(Menschheit)。作为新型态的实践,它对生活的各个部分,例如生活目标、价值观念、文化体系等等无不进行批判(Krisis,329)。
在胡塞尔看来,相较之下,出现于其他文明的“哲学”实际上只能被当作宗教—神话的实践(religiös-mythische Praxis)表现来看,这种实践脱离不了自然的生活执态。宗教—神话之执态具体表现在“用神话的方式去知觉整个世界”(Krisis,330),认为世界总是被神话的力量所支配。所以根据宗教—神话的执态所建立的知识,都只是关于这些神话力量的知识而已。
胡塞尔并强调,宗教—神话的执态之终极目的在于追求现实的好处,从欧洲的角度来看,中国、印度本质上只能算是宗教—神话型态的思想,所以如前所述根本不该有“中国哲学”、“印度哲学”之类的称号。这些“哲学”完全不能跟希腊哲学相提并论(Krisis,331)。
就整个欧洲文化来看,哲学虽然只是其中一部分的表现,但胡塞尔认为这是该文化的核心部分,也是维系欧洲精神之所在(Krisis,337)。在此,胡塞尔为了厘清哲学的含义,区分了“作为各个时代思想的哲学”以及“作为理念的哲学”,前者在他看来只不过是后者的部分努力与实现的成果而已。哲学的真谛在于最高层次的“自我省思”(Selbstbesinnung),在这个意义之下,哲学乃是普遍的认识(universale Erkenntnis)(Krisis,339)。惟近代以来,哲学虽然自喻为普遍理性的化身,却以客观主义(Objektivismus)与自然主义(Naturalismus)的面貌现身(Krisis,339)。客观主义或自然主义总是将精神性的存在化约成自然的存在,它们采取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精神现象,总认为精神奠定在身体的经验上。总而言之,人仅仅是客观事实的一部分而已(Krisis,341)。胡塞尔对此有所怀疑:用同质性的自然来解释非同质性的精神是否恰当(Krisis,340—341)?他坚信,人的主体是不该用基于客观主义的实证科学来加以研究的(Krisis,342)。只有意向性的现象学(intentionale Phänomenologie)特别是超越论的现象学(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才能恰当地处理精神(Geist)的现象,才能为有关人类心灵的研究找到出路。相较之下,人们才能明白,受到客观主义与自然主义影响的心理学是如何因略过了精神生活(geistes Leben),而无法说明精神的真正含义(Krisis,347)。
总之,欧洲的精神世界是从理性的理念,也就是哲学的诞生发展起来的(Krisis,347)。但近代以来由于受到客观主义与自然主义发展的影响,欧洲就科学或人性来说无不陷入危机状态(Krisis,347)。胡塞尔深刻感受到当时的欧洲对理性文化的倦怠(Krisis,348),于是如何引领欧洲重新体认欧洲理性文化天生的内在目的性,乃成为其现象学的重大使命之一。
二、胡塞尔的文化差异论述
胡塞尔充分认识到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的事实。每一个人都隶属于一个特定的文化,在此之中他与其他人分享共同的文化模式,这个模式具体地表现在胡塞尔称之为“周遭世界统觉”(Umwelt-Apperzeption)(Hua XXXIX:159)的认知模式上。
生活在熟悉的文化环境里,我们往往能够轻易地理解他人行为所代表的意义。例如当我们看到某个人一手拿起一张纸,另一只手拿起剪刀将这张纸剪成一张张的纸条时,可以毫不费力地理解这个人的行为,知道这是使用剪刀的典型行为,而且知道这项行为显然是为了某些其他目的而做;一旦我们知道这个人是学术工作者或制作书籍的人,也知道他所在的工作地点(例如书房或是工作间),则他的目的以及整个行为的意义将更加明朗化(Hua XXXIX:159)。
换句话说,“周遭世界统觉”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人的行为。但有时候这个统觉模式并不存在,使得我对某些人的行为之理解仅止于表面层次而已。当我来到陌生的环境时,不仅他人行为的意义不是自明的,就连分辨个别事物的种类都有困难,例如农地上栽植的是何种植物,如何栽植等等。又假如我看到一栋房屋,我分不清楚它究竟是一座庙宇或是政府衙门。胡塞尔举例说,假设他到了中国,看到市场上熙攘往来的热闹人群,整个环境的典型特征(das Typische)对他而言都是陌生的。他固然知道他们的行为以及行为的目的有其典型特征,但由于对这些特征一无所知,所以难免只能从表面的层次理解他们的行为。
活在我所熟悉的周遭生活世界当中,我总是有我的周遭世界统觉,清楚知道“某样东西实际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事物的意义自明地提供给我。在这样的周遭世界里,就算有些人从事的职业工作与我不同,例如从事耕作的农民,我还是和他们分享共同的周遭世界。我们对周遭世界的统觉是可以彼此互通的。我和我的同胞之间具有经验的共同体(Erfahrungsgemeinschaft)以及思想的共同体(Denkgemeinschaft),我们在这个共同体当中一同前进(Hua XXXIX:171)。他们的行为在我看来拥有我能够理解的类型,我们具有相同的周遭世界统觉,活在相同的“世界界域”(Welthorizont)当中(Hua XXXIX:160)。我和自己文化中的他人之间再怎么说总是都还具有传统的统合性(Einheit der Traditionalität),这是具有熟悉类型的周遭世界的统合性(Einheit der Umwelt mit vertrauten Typik),所以我多少还是可以融入这些人的想法中去,无论他们的职业是军人或是农民(Hua XXXIX:162)。
每个文化或多或少都有其封闭性,具有如同黑尔德(Klauo Held)所指出的自足的内在视域(Innenhorizont)(Held 1989:21)。基于对历史、传统与文化的重视,人们总是缅怀过去,向过去看齐,如此一来更增添了文化的封闭性。周遭世界是当下的世界,人们的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不断往前推进着,但每一个人的当下经验多少依赖于过去的经验(Hua XXXIX:162),所以群体生命也不例外,当下的周遭世界与过往经由世代(generativ)累积的生命共同体(Lebensgemeinschaft)有不可切割的关系。所以为了理解当下的周遭世界,过往的历史经验便不得不被召唤回来。这一点对于理解异文化有着绝对的重要性,我们必须知道他们的过去,才能知道他们当下的周遭世界,换言之,我们必须拥有他们经验世界的统觉模式。
周遭世界统觉有深远的世代传统作为背景,经年累月造就出来的文化特色使得外人难以轻易地进入这个知觉模式之中。一个外人算不算对该文化有所掌握,往往取决于他对这个文化传统掌握到什么地步。
换句话说,在每个人熟悉的周遭世界之外还有自己所不熟悉的陌生人,而这些人都生活在他们自身熟悉的周遭世界中。胡塞尔十分强调,他自己与中国人之间不存在一个共享的世界。远在中国的人,他们的世界都不是胡塞尔所能认识的。那边的人、那边的事物不仅个别看来是陌生的,就算从类型(das Typus)来看,也是不熟悉的。陌生环境里的周遭事物及人的行为都是不容易理解的,外人无法轻易获得当地人所熟知的知觉模式去掌握这些事物或人的行为的意义,他必须学习转换知觉模式才能理解他们的文化。胡塞尔说:
如同作为小孩我是融入我的世代人类世界去,同样地,如果我想要理解中国人和中国的世界,融入其中,则我必须投入地获取他群世界(fremde Welt)的统觉,不论是否可能或可以做到什么样的地步,这几乎等于说,总是变成在中国人当中完全的中国人——而我仍然是德国人而且没有失去德国人的周遭世界。(Hua XXXIX:162)
总而言之,对于一般人来说,世界总是以世代的我群世界(generative Heimwelt)的型态出现,所以其他文化的世界是另一个我群世界(Hua XXXIX:163)。活在该世界中的人总是活在产生目的以及实现目的的交替情况里。周遭世界可说就是他们整个行动的普遍范围(Universalfeld),也可说是熟悉的可用资源的领域,而他们本身作为“人”(Person)也是构成这个世界的一个部分。胡塞尔问:作为这样的人能够突破限制吗?胡塞尔不是文化相对论者,在知识问题上尤其如此,他不认可文化本身在知识问题上拥有最终发言权。胡塞尔问我们如何突破我群世界的封闭性时,无非是问是否有一种科学的文化让我们能够活在其中。
胡塞尔并不否认,透过宗教,人们也具有突破限制的可能性,特别是“绝对宗教”(absolute Religion)也具有“普遍世界的意向”(universale weltliche Intentionen),但作为哲学家的胡塞尔毕竟不能将宗教的启示当作最后的归宿,特别是不能接受将科学奠定在宗教的基础上。这只会造就出神学来,这不是胡塞尔所能接受的①这不表示胡塞尔不谈上帝或信仰的问题。他指出:哲学家就算走向上帝,也必定是一条无神论者的道路,也就是说,不是基于启示经验的道路(Hua XXXIX:167)。。
如何从我群世界的统觉过渡到他群世界的统觉,以便能够理解他群世界?人们可以说是从自己所熟知的统觉模式转移到他人身上。所有的确定性(Gewissheit)都是从我群的统觉而来的(Hua XXXIX:167)。我们所认为的他群世界,究其实仅仅是我群世界的改造(Umbildung)而已(Hua XXXIX:168)。问题在于:我对他人如何经验世界的理解与他人自身对其经验世界的理解之间的落差有多大?
对于胡塞尔来说,理解异文化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理解其神话性(das Mythische)的部分。世俗化之后的欧洲人如何才能理解这些神话的统觉(mythische Apperzeption)?胡塞尔问:是不是在所有的统觉之中都有个核心,甚至于神话性的知觉模式也不能不预设这个核心?也就是说,在所有的世界统觉(Welt-Apperzeption)当中是不是有个核心,使得所有的相互理解都成为可能,使得共同的世界成为可能,更使得理解神话性的知觉模式成为可能?
胡塞尔认为,这个问题与下列的问题是息息相关的:究竟是谁在提供科学的理论去讨论我群世界与他群世界之类的问题?答案无非是继承希腊科学精神的欧洲人,而不是未经希腊化的罗马人或是未经欧化的中国人(Hua XXXIX:169)。胡塞尔进一步指出,只有欧洲人拥有关于野蛮人的知识,人们的知识反省分析等等都是欧洲人的反省分析。在此胡塞尔对于自己的文化背景进行剖析,指出他自己虽然不能脱离自身的成长背景,例如他出生于现今位于捷克境内的莫拉维亚。当他思考人的问题时也不能离开作为众人一分子的身份去进行,也就是说只要身为凡人,他便免不了必须从自身熟悉的周遭世界的类型来思考世界,这些都是他在生命过程中学习获得的,甚至科学的习惯(wissenschaftliche Habitualität)以及普遍的思义(universale Besinnung)也不例外。然而是否就意味着,真理有欧洲与非欧洲的区分?胡塞尔自问,难道说他所作的一切说明都只能算是对他个人而言的自明真理而已吗?胡塞尔的质疑是,假如说我所获得的真理之普遍性与他人的普遍性相冲突,这不是极为背谬吗(Hua XXXIX:170)?
只要我的信念确实为真,就算到原始部落那里也会被承认为真,这就是胡塞尔所坚持的理念。现在的问题是,他所可肯定的最终道理是什么?无非是,同一的世界对任何周遭世界中的人都展现,这个惟一的世界将使得所有的周遭世界都成为仅只是这个世界的一个侧面而已(Hua XXXIX:171)。这个世界也正是被原始部落的神话—宗教执态所预设的世界。换句话说,胡塞尔的真正方案是,把欧洲文化与其他文化严格区分开来。如前所言,其他文化都只能看到内视域,未能看到外视域(Aussenhorizont),未能如欧洲文化树立起共同普遍的世界理念(所谓“一个世界”的理念),而囚禁在封闭的周遭世界里。
另一个方式是把其他文化都看成带有宗教—神话执态的文化,而欧洲则是惟一能够克服这种执态的文化,它为真正的科学精神树立典范。古代罗马人之所以向古希腊人看齐,近代的中国人之所以向西方的欧洲文化看齐,无非都是因为古希腊文化或近代的欧洲文化皆为具备理论态度和科学精神特质的文化之缘故。
胡塞尔指出,在前科学世界,他与其他世界之中的人(例如中国人)之间的距离很大。一旦人们以科学家的角色现身,情况便大不相同,他能够确认这些不同世界中的人所经验的事物之类型为何。胡塞尔着手进行的是“对于周遭世界的描述科学”(deskriptive Wissenschaft von der Umwelt),他除了涉及无生命之物、有生命之物,也涉及作为周遭世界的被给予者(umweltlich Vorgegeben)的人。这是一门有关于个别对象的性质的科学,也就是关于经验世界的科学(Wissenschaft der Erfahrungswelt)。藉由这门科学,人们就能够在遭遇异文化时看到共同于所有文化的那个普遍的经验世界。作为统觉活动的核心,它也是神话性思维或知觉模式所不得不预设的。
三、当代现象学家的评述
关于胡塞尔的欧洲及文化差异论述,当代的现象学界评价不一。黑尔德(Klaus Held)以及瑟普(Hans Reiner Sepp)采取认同的看法,为胡塞尔作深入的阐述;相对而言,霍伦斯坦(Elmar Holenstein)及瓦登斐尔斯(Bernhard Waldenfels)则对该项论述不以为然。
(一)黑尔德① 见 Klaus Held.Husserls These von der Europäisrung der Menschheit.in Phänomenologie im Widerstreit,Christoph Jammer und Otto Pöggeler Hrsg.Frankfurt am Main,1989.SS.13—39;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the Role of Europe.in Phenomenology:Critical Concepts in Philosophy Vol.IV,Expanding Horizons of Phenomenology.ed.Dermot Moran/Lester Embree,2004.pp.267—279.与瑟普② 见 H.Reiner Sepp.Homogenization without Violence?.A Phenomenology of Interculturality following Husserl.in Phenomenology:Critical Concepts in Philosophy Vol.IV,Expanding Horizons of Phenomenology.ed.Dermot Moran/Lester Embree,2004.的阐述
黑尔德以对胡塞尔的文化观点几乎不作任何批评的方式阐述胡塞尔的欧洲论述。在他看来,胡塞尔的欧洲论述是无罪的,我们不该将胡塞尔看作欧洲中心主义的支持者。他认为,欧洲化(Europäisierung)与文化帝国主义无关,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前者是各个我群世界(Heimwelt)之间联盟合作的结果,而不是欧洲同化其他文化的结果。为了支持这项论点,黑尔德为胡塞尔做了一项区分:变质后的欧洲精神与原初的欧洲精神。
变质后的欧洲精神乃是基于科技发展而形成的同质化文化扩张主义,这是近代欧洲实际上的表现,但也是违反原初欧洲精神的结果。黑尔德对变质后的欧洲精神进行批判,他指出,变质后的欧洲精神自认为是全球人性(planetarische Menschheit)的化身。对这种精神而言,只有一种我群世界可以存留,结果导致这种我群世界目中无人,不把其他我群世界看在眼里,换言之,形成所谓没有任何外视域(Aussenhorizont)的情况(Held 1989:28)。黑尔德不以为然地指出:这么一来,这个我群世界跟以往封闭的我群世界有什么两样,差别仅仅在于旧的神话被新的“进步”神话给取代而已(Held 1989:29)。
这种科学所重视的乃是具有同一性的“在己”对象(der Gegenstand in seiner Identität“an sich”)。这时理论变成专业,其他的视域性(Horizonthaftigkeit)通通被排除在外,对象经验(Gegendstandserfahrung)也跟着被窄化了。人们满足于某一面向,而无视对象经验的丰富性(Held 1989:31—32)。
相对于此,根源于古希腊哲学的原初欧洲精神则是一种让人性获得普遍提升,而不是让所有人性被同质化的精神型态。首先,黑尔德指出:每个特殊的个别世界(Sonderwelt),都必然关涉到其他的视域(Verweisungen auf andere Horizonte),而一个世界(eine Welt)则把所有的视域都统合起来(Held 1989:15)。让“一个世界”得以出现的条件乃是在于采取开放(Offenheit)的执态,而让开放性得以出现的基础条件则是理论上的好奇(theoretische Neugier)。并且,只有在此情况下,真理才得以出现(Held 1989:16)。
黑尔德对特殊的个别世界做了区别:一种是“文化上稳定的范域”(kulturelle,feste Umkreise),另一则是普遍而共同的文化(universale,gemeinsame Kultur)。前者就是前文曾经提到的世代与传统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我群世界(Heimwelt)(Held 1989:18),其根本特质乃是神话执态(mythische Einstellung),这个执态既非“不带兴趣的”(interessefrei),也不对整体的世界采取开放性的执态(weltoffen für das Ganze)(Held 1989:19)。神话(Mythos)所具有的特定兴趣在于“趋吉避凶”(Held 1989:19)。在胡塞尔的认知里,这是所有非欧洲地区思想的共同特色,也是为什么它们都不够资格被称为哲学的原因(Held 1989:19)。
能够把各个我群世界内部整合起来的力量往往就是起源神话。这类神话虽然对于各个我群世界具有普遍视域(Universalhorizont)的效力,但往往也只对这个我群世界有效而已,其效力在其他的我群世界就不见得被接受了。我群世界毕竟只是特殊的个别世界而已(Held 1989:20)。
我群世界具有内视域(Innenhorizont)的特性,它所拥有的正常风格(Normalstil)往往排除了外视域(Aussenhorizont),也就是被黑尔德界定为“一个世界”的存在(Held 1989:21)。根据胡塞尔的理论,只有透过理论(Theorie)才能够发现超越各个我群世界的“一个世界”(die eine Welt)(Held 1989:20)。这个透过理论所开展出来的外视域或“一个世界”乃是欧洲文化对人类文化的贡献。与神话传统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前瞻性的,而不是回顾性的(Held 1989:21)。“一个世界”不仅是各个部分的总和而已,它乃是带有视域特性的指涉关连网(ein horizonthafter Verweisungszusammenhang)(Held 1989:22)。
理论执态是经由前理论执态转变而来的,藉由这项转变,原本活在前理论世界中的人也可以经验到透过理论所开展出来的普遍性(Universalität)(Held 1989:22)。换言之,如前所述,理论上的好奇使得开放性得以出现(Held 1989:15)。黑尔德强调:“一个世界”虽然不只是众多个别的特殊世界的总和而已,但“一个世界”这个理念却又不能不在一个特定的特殊世界之内视域中出现。对胡塞尔来说,这个能够显现“一个世界”的特殊世界正是古希腊(Held 1989:23)。
古希腊的文化创建并不是要让所有的文化都变成同构型的一体,“好奇的惊异”(das neugierige Staunen)反而是蕴含了对显现同一世界之多样方式的尊重。而且它带来另外一种效果,亦即让每个原本只知向内看的特殊个别世界都能够开展视野,彼此相互开放,但又不影响各自建立在神话之上的生活正常风格(Lebensnormalstil)。
黑尔德指出:尽管当代讨伐欧洲中心论的声浪四起,但回头看胡塞尔1935年的演讲“欧洲人的危机与哲学”仍是饶富意义的(Held 1989:13)。假若人类的科学能够依照古希腊所创建的模式去发展,则将不至于产生欧洲化有何不良后果的疑虑。黑尔德深信,所有人类都将不排斥地乐于接受这个源自古希腊理想的文化。如此一来,欧洲中心论的疑虑自然化于无形。总的来看,黑尔德主张,欧洲精神是无罪的,全人类的欧洲化乃是可欲的①莫伦(Dermot Moran)在一篇即将刊登于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的论文“Husserl on Universalism and the Relativity of Cultures”之中提到:相对于20世纪30年代德国哲学界与人类学界(例如Ernst Krieck及Alfred Kremmt等人)普遍反对普遍主义,胡塞尔对普遍主义理想的坚持相当难能可贵。虽然如此,莫伦却未进一步省思胡塞尔文化论述中的某些观点,例如欧洲与非欧洲之间的差异并未遭到他的任何质疑。。
另一位当代的现象学学者瑟普也针对胡塞尔的观点做了阐释。瑟普所提出的问题是:在文化间际(interculturality)问题上,超越论的现象学可以被应用到什么程度?假定超越论的元素(transcendental components)非得用某种特定的世俗语言表现出来的话,那么该有哪一个语言或哪一个文化最有资格去表现它?
为了回答该项问题,瑟普做了一项区分:“超越论的原我群世界”(transcendental primal homeworld)不同于“事实上存在的欧洲我群世界”(the homeworld Europe)(Sepp 2004:296)。
根据这项区分,胡塞尔虽然指出“一个世界”理念的开展是位于某种事实上存在的位置——欧洲,特别是古希腊,但我们应该以超越论的意义而非以世俗意义来理解胡塞尔的说法,也就是古希腊在这里意味着“超越论的原我群世界”,而非事实上存在着的某个我群世界(297)。据此我们可以说,它根本就是不在任何空间位置上。如此一来,均质化(homogenization)的危险自然而然也得以避免(Sepp 2004:297—298)。
瑟普强调:对文化间际所做的现象学分析,目标应该在于用这种方式揭示:实际出现在各个不同文化历史中的不同“意向—实现系统”(intention-fulfillment system)型态,均表现出相对应的“超越论的原我群世界”之超越论的结构。换句话说,“原我群世界”在各个特定的质料性当中被明显化(Sepp 2004:297)。
现象学借助“原我群世界”所做的分析,特点在于,虽然它是一项特定的观点,但却不会只和某个特定的我群世界有所关连而已(Sepp 2004:297)。此一情况就好比现象学虽不能脱离世俗语言,但也不该被世俗语言所限定一般(Sepp 2004:298)。
就上述黑尔德的看法来说,笔者认为他深入阐述胡塞尔的观点,十分有助于吾人清楚认识胡塞尔的欧洲论述与文化论述。然而,其不带批判性地进行的阐述之中是否也意味着他对胡塞尔的文化观点,特别是欧洲文化与非欧洲文化(例如胡塞尔本人常举的印度及中国)之间的关系也完全表示赞同?黑尔德的时代背景与胡塞尔迥异,对其他文化的接触与认识也大为不同,难道说他会接受古代印度或中国的思想只是神话—宗教的执态表现吗?
瑟普的观点是值得注意的,他呼应胡塞尔的哲学理念,认同哲学所追求的真理是跨越文化差异的,文化对他来说只是走向哲学真理的阶段过程而已。如此一来,根源于古代希腊的无限理性理念不仅对欧洲人有效,更值得其他文化学习效法。问题是,文化的问题在他的诠释里变得完全不重要了。欧洲不是事实上的欧洲,而是哲学真理在地球上自我显现的化身,其他文化认同的既然不是历史上实际存在的欧洲,则也就不存在欧洲化与否的问题。这种让欧洲化等同于普遍化的想法难道不正是不折不扣的欧洲中心主义吗?
(二)霍伦斯坦① Elmar Holenstein,Europa und die Menschheit.Zu Husserls kulturphilosophischen Meditationen.in Kulturphilosophische Perspektiven.Frankfurt/M:Suhrkamp,1998.及瓦登斐尔斯②Besnhard waldenfeps,Verschränkung von Heimwelt und Fremdweld.in R.A.Mall/D.Lohmar(Hrsg.).Philosophische Grundlage der Interkulturalität(Studien zur interkulturellen Philosophie,Bd.I),1993.的批判观点
首先,霍伦斯坦指出,胡塞尔对欧洲文化的沉思有其特殊历史背景:1930年代欧洲知识分子普遍关心军事、政治上互相敌对各国之间的共同文化根源,以及欧洲面对美国崛起的忧心。霍伦斯坦肯定胡塞尔的基本态度,毕竟在各国竞相声张本国特色而陷入冲突矛盾之时,胡塞尔对于欧洲共同特色的思考显得特别有价值。但是就内容而言,他对于胡塞尔的欧洲论述几乎无一赞同之处。
胡塞尔主张,哲学只在古希腊出现,这是独一无二的,古代中国与印度不能相提并论。霍伦斯坦对此有所质疑(Holenstein 1998:235)。他认为专属于希腊人的成就实际上在古代中国也找得到,例如庄子“道通为一”的想法(Holenstein 1998:232)。换言之,霍伦斯坦想要相对化古希腊人的成就。
其次,对胡塞尔而言,欧洲表现在古希腊时代的精神特质是:对周遭世界采取一种新的执态。跟这种新的执态比较起来,其他都只能算是跟价值有关的实践执态而已(Holenstein 1998:231)。只要能够接受这种新的执态就是欧洲化,也可以称作普遍化。之所以是欧洲化,原因在于它首先出现在欧洲,之所以是普遍化,则是因为它发展出超越国族(übernationalität)的特性。每一个文化都可以去追求这个在己的真理(an sich Wahre)。或者,后者可以表现在各个不同的文化里。
霍伦斯坦说:不容否认,近代科学是由欧洲人率先发展出来的,因此科学家所使用的语言自然是欧洲的语言,但人们不能因此就得出“世界被欧洲化”的结论来(Holenstein 1998:235)。霍伦斯坦进一步指出,有些科学的早期成就来自非欧洲地区,只不过经由欧洲人的改造才让它们变得更有效率而得以普遍化。因此若要论述科学成就,欧洲人的贡献毋宁在于改良,而非原创(Holenstein 1998:236)。换言之,一味强调欧洲科学或哲学的原创性其实是有待商榷的。
此外,霍伦斯坦也对胡塞尔的文化观点特别提出批评。胡塞尔所接受的是赫德(Johann G.Herder,1744—1803)式的文化概念。这种文化观点强调文化的各个部分之间彼此相互紧密连结,宛如有机体或球体一般。霍伦斯坦对此做了批判,指出这种文化概念在经验上站不住脚(empirisch unhaltbar),作为理念型则又是一种误导(idealtypische Vorstellung allzu irrführend)(Holenstein 1998:241)。
当代的文化人类学及生物学都倾向于采用拼凑体(Bastelwerk)来取代球体型(Kugelgestalt)的想法。在拼凑体之中的各个部分只具有松散的衔接关系,彼此之间的联系总是不尽完美的。它的各个部分也不会藉由朝向一体的中心(einheitliches Zentrum)而凝聚起来,反而往往需要外在的支撑力才能将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维系起来。
霍伦斯坦反对赫德所说,一个文化体只能吸收与它相同的元素,而对异质元素则缺乏感觉,甚至反感。事实正好相反,当一个文化体的特殊兴趣无法在自己圈内得到满足时,便会向外寻求补充资源。文化跟人一样,都不会是不具有内在异质性的同质型态(homogene Gestalten)。正如人透过学习可以使用多种语言,每个文化也都拥有向其他文化学习的天性(Holenstein 1998:242)。
针对胡塞尔的“我群世界”、“他群世界”与“一个世界”等概念,瓦登斐尔斯(Waldenfels)指出胡塞尔一方面提出“我群世界”和“他群世界”之间的差异,但另一方面却又藉由“一个世界”来泯除两者间的差异。此“一个世界”既是首要的基础(erster Grund),又是最终的视域(letzter Horizont),而确立它的手段则是理性。欧洲对于胡塞尔来说无非就是这个理性的化身,也是具有普遍性的共同世界之护卫者(Vorhut einer Gemeinwelt),因为欧洲已经为所有文化创立了规范与理念。以此规范为准,其他文化的成就可说都只是达到前理性、前逻辑或直接可说未成熟或原始的阶段而已。在理性发展的历史上,非欧洲人都应该向欧洲人看齐才是。瓦登斐尔斯直接将这种观点称作“欧洲中心主义”(Eurozentrismus),它乃是以牺牲“他者性”(Fremdheit)为手段所达到的全体性(Totalität)(Waldenfels,1993:61)。对此瓦登斐尔斯深深不以为然,追根究底,对“他者”问题的忽视是欧洲思想发展历史上的一大盲点,这个盲点也导致了胡塞尔文化论述上的偏失。
霍伦斯坦的说法特别值得一提之处在于,文化不是封闭的球体,也不是有机体,更非独立发展而紧密的个体,而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取其他文化的元素而将它转换成自身的资源。根据这点来看,胡塞尔虽指出欧洲创造出具有开放特质的“一个世界”理念,但相对来说,欧洲却被胡塞尔看作不假外求的文化个体。赫德式的文化概念是否无形中为胡塞尔所预设,这点可能是需要作进一步检讨的。与此相关,如同瓦登斐尔斯所言,胡塞尔对欧洲的理解本身早已将“他者”排除在外,这显然有失偏颇。
结 论
胡塞尔曾指出,只有基于欧洲古希腊所发展出来的哲学理性才是真正值得所有人类共同追求的普遍理性,这种理性在其他文化例如印度或中国都未曾出现过。所以胡塞尔曾说,所谓“印度哲学”或是“中国哲学”等都是不恰当的称谓。胡塞尔甚至认为,欧洲以外的文化只产生过追求现实利益的神话—巫术思想而已。这项观点已经在当代现象学学者之间引起极大的争辩,捍卫者有之(Held,Sepp,Moran),强力批评者也不少见(Holenstein,Waldenfels)。对照之下,东亚学者对此提出反思批判者并不多见①刘国英2010年发表的一文指出:胡塞尔有关于欧洲与非欧洲之间的强烈对比论调,不免令人想起黑格尔批评印度与中国哲学停留在低下水平的论调。见Kwok-Ying Lau.Husserl,Buddhism and the Problematic of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in Identity and Alterity:Phenomenology and Cultural Traditions.ed.by Kwok-Ying Lau/Chan-Fai Cheung/Tze-Wan Kwan,Würzburg:Königshausen& Neumann,2010.p.224.张汝伦则在1998年的一文中强烈质疑胡塞尔寻找生活世界结构作为所有文化共同基础的可行性。见Zhang Rulun.Lifeworld and the Possibility of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in Phenomenology of Interculturality and Life-world.ed.by Ernst Wolfgang Orth and Chan-fai Cheung.Freiburg/Muenchen:Verlag Karl Alber,1998.。为此缘故,笔者以为,东亚学者没有理由不审慎回应胡塞尔的该项论述,无论赞成胡塞尔也好、反对胡塞尔也好,都应该提出理由申论自身所持的立场。
身为非欧洲人的东亚学者如何从事现象学研究?对于有些人来说,他们的工作应该跟欧洲或欧洲以外的广义西方(包括北美、澳洲、南美等)的学者没什么差别。大家都是专注于胡塞尔思想或进一步发展的讨论,惟一的差别在于他们使用的是东亚的语言,如中文、韩文或日文等等。假如他们采用西方语言例如英文、德文或法文发表论文,则这项差别就微乎其微了。
站在全球化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这项观点无可厚非,毕竟这能够提供现象学更多的人力资源,促进现象学的发展。但笔者深信,东亚学者除了从事与一般西方学者无所差别的现象学研究以外,似乎有必要进一步反思,他们从事现象学研究的立足点何在。一旦触及该问题,文化的课题便不免浮上台面,而从现象学本身出发思索文化以及文化之间关系的问题便特别值得重视了。为此,胡塞尔的文化论述无形中成为吾等反思现象学研究的立足点之重要凭借。
前文提到,黑尔德曾经指出:殖民主义绝非欧洲人与其他文化接触的惟一模式,犹如近代科学的发展绝非科学精神的惟一表现那样,近代殖民主义乃是古希腊“一个世界”理念的扭曲变形。如果该理念得到真正的发扬,则人类世界大同的理想当得以落实。如前所言,这项论点不免带有浓厚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身为东亚文化圈一分子的现象学研究者该如何回应这一类主张?
笔者以为,关键在于吾人究竟该如何看待欧洲中心主义?是否除了完全赞同之外,就只剩下全然拒斥这项选择?文化人类学指出:任何文化,无论大小,免不了都有族群中心论(ethnocentrism)的倾向,这种倾向让每个文化认为自己处在世界的中心,外围环绕着陌生的族群以及其他陌异的存在界。这种情况好比胡塞尔所言,每个人都是空间上的绝对中心点,上下左右前后的方向以及远近的距离莫不是依此中心点而展开。据此而言,假如我们不该问究竟是谁站在世界的中心点,则在文化问题上同样没有必要或不该去问哪一个文化才是中心文化。假如所有的空间中心点都可以被别的空间点相对化为边缘,则同样任何一个自视为中心的文化也会被边缘化。当我们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同时,其他的中心论便也不该获得豁免,反之,要是支持欧洲中心论,我们为何不也为其他的中心论给予肯定?一个能够自视为中心的文化体系必定对自己充满高度的自信,就此而言,欧洲中心论确实是所有文化中心主义的表率,毕竟近代以来欧洲文化在与全球各地文化相互接触时无往而不利。但话说回来,任何曾经有过强烈中心论倾向的例如东亚的中华(或大汉)文化中心论(或者将来有可能出现的取代欧洲中心论的另一个文化中心主义)无非都只不过显示它们为自己感到自豪而已。在向别的文化族群推荐自己的文化时,有的采取硬性的帝国主义策略,有的则是施行软性的怀柔感召策略。文化中心论本身不应该是罪过,帝国主义策略及作为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近代以来,非欧洲文化与欧洲文化的接触经验所导致的丧失文化自信现象多少与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难堪经验有关。如今,假如还要不断计较这段不愉快的历史过程,则再多的恐怖攻击与反恐怖主义战争也平息不了这份怒气。在此情况之下,反思文化的问题不仅只是吾人思索研究现象学的立足点问题而已,而是探索整个文化导向的重大课题了。于是,面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与主张,吾人能否以轻松一点的态度来面对它?假若传统的中国向来以文化的优越性自豪,则欧洲的文化中心论也未尝不可被看作另一种文化自豪的表示。
再说,胡塞尔倡言的欧洲科学与哲学的理性理念,期许所有人能够抱持理论的执态,从自然的状态转变成理论思考的状态,采取理性的态度去面对各种事物。胡塞尔会认为,任何人只要这样做,就会成为“欧洲人”。让我们延续霍伦斯坦的思考来回应这个说法。笔者认为,欧洲以外的文化不是不能向欧洲学习而拥有哲学与科学,如同人可以学习很多种语言一般。其他文化由于未曾独立产生过科学与哲学而不得不向欧洲学习,这是事实,胡塞尔并没说错,问题出于“向欧洲学习就是欧洲化”这个说法。我们为何不说,这是每个文化在发挥向其他文化学习的天生潜力?就像某种语言原本可能欠缺某些特定的词汇,而必须向外学习以便拥有相关的词汇,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去强调这个语言失去了它本身固有的特性,乃至于变质成了另一种语言。毋宁说,这个语言将一些表达方式内化成该语言的一部分而丰富了该语言。据此观点,其他文化向欧洲学习,不是造成欧化的结果,反而是将欧洲文化的元素注入原来的文化而使得该文化变得更加丰富而多元。
所以,站在非欧洲人的角度来看,让自己的文化加入了欧洲的文化元素,进而充实本身的文化内涵,实无不妥之处。况且这是文化间相互学习的一种典型表现。再说我们可以问,假如非欧洲人执意拒绝这种人生执态,则所剩的替代方案是什么?这种替代方案是否难免也带有理性/理论执态的色彩?例如:萨依德 (Edward Said,1935—2003)批判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不正是藉助欧洲式的理论理性作为工具,才能为长久以来饱受西方偏见之苦的阿拉伯世界发出抗议的声音?
Anderson,Benedict.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London:Verso,1983(2006).
Brague,Rémi.Europa:Eine exzentrische Identität,Frankfurt a.M.:Campus Verlag,1993.
Buckley,R.Philip.A Critique of Husserl's Notion of Crisis,in Crisis in Continental Philosophy.edited by Arleen B.Dallery,Charles E.Scott and P.Holley Roberts.(Selected Studies in Phenomenology and Existential Philosophy 16)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0.
Husserl,Heidegger and the Notion of Philosophical Responsibility.(Phaenomenologica 125)Dordrecht/Boston(MA)/Lond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2,XXIII.
Husserl's Notion of Authentic Community.American Cathol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66,1992,pp.213—227.
Husserl and the Continuing Crisi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Review of Edmund 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Ergänzungsband.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24,1994,pp.236—251.
Husserl's Rational“Liebesgemeinschaft”,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26,1996,pp.116—129.
Edmund Husserl.in Ensyclopedia of Phenomenology.Edited by Lester E.Embree,Elisabeth A.Behnke,David Carr,J.Claude Evans,José Huertas-Jourda,Joseph J.Kockelmans,William R.Mckenna.Algis Mickunasm J.N.Mohanty,Thomas M.Seebohm and Richard M.Zaner.(Contributions to phenomenology 18)Dordrecht/Boston(MA)/Lond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7,XIV.
Erdmenger,Katharina.Neue Ansatze zur Organisation Europas nach dem Ersten Weltkrieg(1917—1933):Ein neues Verstandnis von Europa?Sinzheim:Pro Universitate Verlag,1995
Gellner,Ernest.Nations and Nationalism,Oxford:Blackwell,1983(2006).
Held,Klaus.Husserl und die Griechen,in Profile der Phänomenologie:Zum 50.Todestag von Edmund Husserl.Herausgegeben von Ernst Wolfgang Orth(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22),Freiburg/München:K.Alber,1989.
Husserls These von der Europäisierung der Menschheit,in Phänomenologie im Widerstreit.Zum 50.Todestag Edmund Husserls.Herausgegeben von Christoph Jamme und Otto Pöggeler(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haft 843)Suhrkamp,Frankfurt a.M.,1989.
Husserls phänomenologische Gegenwartsdiagnose im Vergleich mit Heidegger.in Husserl-Symposion Mainz,25.6/4.71988.Herausgegeben von Gehard Funke(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und der Literatur.Abhandlungen der geistes-und sozialwissenschaftlichen Klasse 1989/3),Wiesbaden:Steiner,1989.
Heimwelt,Fremdwelt,die eine Welt.Perspektiven und Probleme der Husserlschen Phänomenologie.Herausgegeben von Ernst Wolfgang Orth(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24/25),Freiburg/München:K.Alber,1991.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the Role of Europe,in Phenomenology:Critical Concepts in Philosophy Vol.IV,Expanding Horizons of Phenomenology ed.Dermot Moran/Lester Embree,2004.pp.267—279.
Holenstein,Elmar.Menschliches Selbstverständis.Ichbewuätsein,intersubjektive Verantwortung,interkulturelle Verständigung(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 543),Frankfurt a.M.:Suhrkamp,1985.
Europa und die Menschheit.Zu Husserls kulturphilosophischen Meditationen,in Phänomenologie im Widerstreit.Zum 50.Todestag Edmund Husserls.Herausgegeben von Christoph Jamme und Otto Pöggeler(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haft 843),Frankfurt a.M.:Suhrkamp,1989.
Kulturphilosophische Perspektiven,Frankfurt/M:Suhrkamp.1998.
Husserl,Edmund.Breifwechsel.ed.Karl Schuhmann in collaboration with Elizabeth Schuhmann.Husserliana Dokumente,10 Volumes.Dordrecht:Kluwer,1994.
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en und pariser Vorträge,Husserliana I.
Ideen II,Husserliana IV.
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ah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Phänomenologie,Husserliana VI.
Intersubjektivität,Bd.III,Husserliana XV.
Die Lebenswelt.Auslegungen der vorgegebenen Welt und ihrer Konstitution.Texte aus dem Nachlass(1916—1937),Husserliana XXXIX,Dordrecht:Springer,2008.
Leske,Monika.Philosophen im“Dritten Reich”:Studie zu Hochschul-und Philosophiebetrib im faschistischen Deutschland,Berlin:Dietz Verlag,1990.
Lohmar,Dieter:Zur überwingung des heimweltlichen Ethos.in Philosophische Grundlagen der Interkulturalität.Herausgegeben von Ram Adhar Mall und Dieter Lohmar.(Studien Zur interkulturellen Philosophie 1),Amsterdam/Atlanta(GA):Rodopi,1993.
Home-World and Foreign Ethos:a Phenomenological Attempt to Ethical Problems of Intercultural Exchange.Journal of the Indian Council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9(3),1992,pp.27—54.
Luft,Sebastian.Europa am Kongo.Zu Husserls Kulturphilosophischen Meditationen,In Journal Phänomenologie 10,2(1998),pp.15—22.
Mohanty,J.N.The Other Culture.in Phenomenology of the Cultural Disciplines.
edited by Mano Daniel and Lester E.Embree(Contributions to phenomenology 16),Dordrecht/Boston(MA)/London:Kluwer academmic publishers,1994,VII.
Moran,Dermot.Husserl on Universalism and the Relativity of Cultures,OPO III Conference,Hong Kong,2008.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forthcoming)
Most,Glenn W.'From Logos to Mythos',in From Myth to Reason?: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Greek Thought,ed.Richard Buxt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25—50.
Orth,Ernst Wolfgang:Einheit und Vielheit der Kulturen in der Sicht Edmund Husserls une Ernst Cassirers,in Phänomenologie im Widerstreit.Zum50.Todestag Edmund Husserls.Herausgegeben von Christoph Jamme und Otto Pöggeler(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haft 843),
Frankfurt a.M.:Suhrkamp,1989.
Interkulturalität und Inter-Intentionalität.Zu Husserls Ethos der Erneuerung in seinen japanischen Kaizo-Artikeln,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47,1993,pp.333—351.
Unity and Plurality of Cultures in the Perspectives of Edmund Husserl and Ernst Cassirer.(Translation).in Phenomenology and Indian philosophy,edited by D.P.Chattopadhyaya,Lester E.Embree and J.N.Mohanty,New Delhi:Indian Council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1992,VIII.
Schuhmann,Karl.Husserl-Chronik.Denk-und Lebensweg Edmund Husserls(The Hague:Nijhoff,1977)
Seebohm,Thomas M.:Wertfreies Urteilen über fremde Kulturen im Rahmen einer
transzendental-Phänomenologischen Axiologie.in Mensch,Welt,Verständigung.Herausgegeben von Ernst Wolfgang Orth.(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4)Freiburg/München:K.Alber,1977.
Sepp,H.Reiner.Homogenization without Violence?A Phenomenology of Interculturality following Husserl,in Phenomenology:Critical Concepts in Philosophy Vol.IV,Expanding Horizons of Phenomenology ed.Dermot Moran/Lester Embree,2004.pp.292—299.
Stegmaier,Werner.Europa-Philosophie,Berlin/New York:de Gruyter,2000.
Sträker,Elisabeth:Edmund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Philosophia perennis in der Krise der europäischen Kultur.Husserl-Studies,5,1988,pp.197—217.(Reprinted in)Profile der Phänomenologie.Zum 50.Todestag von Edmund Husserl.Herausgegeben von Ernst Wolfgang Orth.(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22)Freiburg/München:K.Alber,1989.
Tani,Toru.Heimat und das Fremde,Husserl-Studies,9,1992,pp.199—216.
Tengelyi,László:Das Eigene,dans Fremde und das Wilde.Zur Phänomenologie derIntersubjektivität und der Interkulturalität.Mesotes,4,1994,pp,423—432.
Waldenfels,Bernhard:Erfahrung des Fremden in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in Profile der Phänomenologie.Zum 50.Todestag von Edmund Husserl.Herausgegeben von Ernst Wolfgang Orth.(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22)Freiburg/München:K.Alber,1989.(Reprinted in)Waldenfels,Bernhard:Deutsch-Franzäsische Gedankengänge.Frankfurt a.M.:Suhrkamp,1995.Verschränkung von Heimwelt und Fremdwelt.in Philosophische Grundlagen der Interkulturalität.Herausgegeben von Ram Adhar Mall und Dieter Lohmar(Studien zur interkulturellen Philosophie 1),Amsterdam/Atlanta(GA):Rodoi,1993.
Eigenkultur und Fremdkultur:das Paradox einer Wissenschaft vom Fremden,in Studia Culturologica,3.1994,pp.7—26.
Topographie des Fremden(Studien zur Phänomenologie des Fremden 1),Frankfurt a.M.:Suhrkamp,1997.
Experience of the alien in Husserl's phenomenology.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20,1990,pp.19—33.(Translation)
Zhang,Rulun.Lifeworld and the Possibility of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in Phenomenology of Interculturality and Life-world,ed.by Ernst Wolfgang Orth and Chan-fai Cheung.Freiburg/Muenchen:Verlag Karl Alber,1998.
——专栏导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