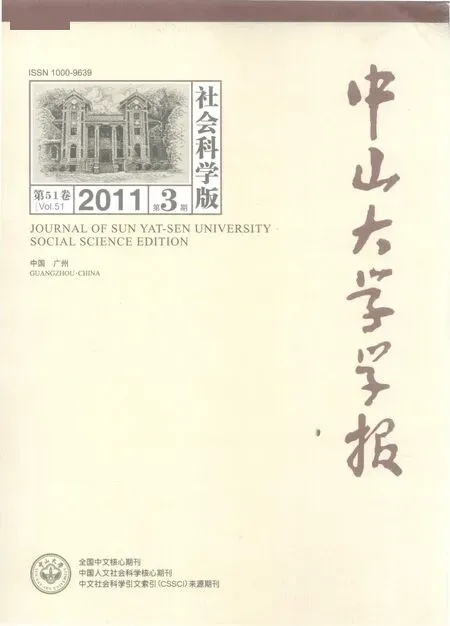悲喜交织的“变老”*
——论叶芝以“变老”为主题的诗歌中的“悲剧中的喜悦”
区 鉷,周 芳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悲剧“通过(激起观众的)怜悯和恐惧来发泄这些情感”①William k.Wimsatt,JR.& Cleanth Brooks,Literary Criticism:a Short History,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57,p.36.另:本文所有引文均由本文作者翻译。此处译文括号中的文字为本文作者所加。。但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认为恰恰相反——悲剧“不是为了发泄恐惧和怜悯之情,不是为了通过发泄危险的情绪来净化人(这是亚里士多德的理解);而是超越恐惧和怜悯,实现永恒的来自生命的快乐——这种快乐甚至包括毁灭的快乐”②Qtd.in Frances Nesbitt Oppel,Mask and Tragedy:Yeats and Nietzsche,1902—10.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87,p.121.。
受尼采的影响,叶芝(W.B.Yeats)认为悲剧的精神是喜悦:“对死去的主人公来说,悲剧应该是喜悦的。”③W.B.Yeats,Essays and Introductions.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61,p.523.尼采的悲剧中的喜悦来自悲剧作家、悲剧主人公对生命实质的领悟,即生命是可以再生的、永恒的。尼采认为酒神荻俄倪索斯(Dionysus)最能代表这种悲剧精神——酒神被众兄弟撕成碎片,又通过大地女神得墨忒耳(Demeter)的孕育复活。酒神的肢解象征着个体生命的终止,而他的重生象征着个体生命与宇宙的汇合。因此个体生命的毁灭是喜悦的,它宣告了与宇宙生命的融合,一个永恒生命的开始。悲剧舞台通过种种形式对酒神命运的再现,“不是展现通过幻象来实现日神的救赎精神,恰恰相反,展现的是个体的破碎及其与大化的融合。”④尼采认为日神阿波罗代表了艺术的修复和救赎精神。艺术通过幻想、通过制造表象来掩盖和修饰生活的丑陋和不足,从而给人们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引自Friedrich Nietzsche,Basic Writings of Nietzsche,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Walter Kaufmann.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2000,p.65.
叶芝的悲剧精神承继了尼采的对宇宙与个体生命实质的领悟——“悲剧应该是隔离人与人的堤坝的决裂与淹没,这些堤坝只是喜剧的基础。”①W.B.Yeats,Essays and Introductions.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61,p.241,254,252.叶芝用堤坝比喻形成个体的基础,用堤坝的决裂和淹没形容个体生命的毁灭和融合,并借此说明悲剧展现的是个体生命与大化的融合。
虽然尼采和叶芝认为悲剧充满来自对生命融入宇宙的憧憬和喜悦,但他们承认,这种喜悦是建立在痛苦和毁灭之上的。不承认这一点,悲剧就不成其为悲剧,而只是如拉马扎尼(Jahan Ramazani)所说,亚洲式的归隐②Jahan Ramazani,Yeats& the Poetry of Death:Elegy,Self-elegy,and the Sublime,New Haven&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p.97.。叶芝曾引用别人的话说:“如果我不承认自己的痛苦,我的极乐就是不真实的。”③W.B.Yeats,Mythologies,London:Macmillan Press,1984,p.332.在叶芝看来,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悲剧中的主人公也是痛苦和欢乐参半的,他们“语气中的极乐一半包含着对痛苦的屈服,而另一半是胜利之剑对战败的世界的挪揄和嘲讽。”④W.B.Yeats,Essays and Introductions.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61,p.241,254,252.正因为悲剧是建立在痛苦和毁灭之上的,对尼采和叶芝来说,悲剧的喜悦不仅来自对个体生命消逝的参透和对与大化融合的憧憬,也包含着征服痛苦和死亡的喜悦。崇尚意志的力量的尼采盛赞悲剧是“强生剂”,是“迎悲剧中的残忍而上的英雄气概:他们坚强,所以将痛苦化为乐趣”⑤Qtd.in Otto Bohlmann,Yeats and Nietzsche:An Exploration of Major Nietzschean Echoes in the Writings of William Butler Yeats,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2,p.54.。而叶芝因为天性中的怯弱和对这怯弱的痛恨,更强调悲剧的喜悦是勇气和力量的象征,是征服困难和死亡的武器,也是对超越自我的肯定。他说:“只有当我们在喜悦之时,才能游刃有余,才能主宰事物,才能清楚自己的力量所在。”⑥W.B.Yeats,Essays and Introductions.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61,p.241,254,252.因此喜悦是勇士的武器。而勇士在困境和死亡面前展示的力量和坚毅,同他对生命的领悟一道,成为喜悦的源泉。如果说来自对个体生命融入大化的喜悦有一些弃世的色彩,是一种被动的情绪,因征服和勇气产生的喜悦则充满了挑战和斗争精神,是对个体生命在最后时刻迸发的绚丽的肯定和赞美。
叶芝以“变老”为主题的诗歌充分体现了叶芝崇尚的以喜悦面对悲剧从而征服悲剧的悲剧精神。“变老”和死亡一样,不可选择、不可逆转。虽然它不像死亡以其突然的毁灭引起人的恐惧和对悲剧英雄的同情,“变老”这种缓慢的毁灭最易引发自我的哀怨和他人的怜悯之情,如《圣经》中人在变老面前的哀怨:“我的年日,如日影偏斜,我也如草枯干。”⑦The Holy Bible,authorized King James Version.(Psalms 102:11—12)但正如尼采拒绝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中的恐惧和怜悯之情,叶芝拒绝哀怨和怜悯。他曾多次说过:“被动受苦不是诗歌的素材。”⑧Qtd.in Jahan Ramazani,Yeats& the Poetry of Death:Elegy,Self-elegy,and the Sublime,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p.202.在他的“变老”诗歌中,叶芝秉承了尼采的“悲剧中的喜悦”的英雄气概,化被动受苦为积极的面对和抗衡。
虽然叶芝最典型的“悲剧中的喜悦”多表现为在死亡面前的欢笑和欣喜,如《旋梯》(“The Gyres”)中悲剧的目击者“在悲剧的喜悦中欢笑”,《在本·布尔山下》(“Under Ben Bulben”)中祈祷战争的战士最后放声大笑等,叶芝以“变老”为主题的诗歌中的“悲剧中的喜悦”以更曲折、多样的方式表现出来。它既表现为恬淡的喜悦,如来自智慧的喜悦、灵魂的歌唱,也表现为不合时宜的舞蹈、老年人的自嘲和疯狂等。虽然不直接表现为欢笑或欢喜,这些行为和情感都是诗歌中的老年主人公或老年诗人用以化解“变老”的失落和痛苦的武器,象征着征服悲剧的勇气和力量。因为这些情感和行为,“变老”不再是单纯的哀怨和默默承受,而是勇气和力量的展现。正是这勇气和力量的展现给“变老”主人公和旁观者带来了喜悦之情。
在叶芝早期的“变老”诗歌中,“悲剧中的喜悦”表现为来自智慧或灵魂的喜悦。如“智慧随岁月而长”(“Men Improve with the Years”)一诗中:
一整天/我盯着这位美貌的女士/犹如盯着/书页中的画像/满足于眼睛或/耳朵的享受/自知让我快乐①本文引用诗歌均出自W.B.Yeats,The Poems,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Daniel Albright.London:Everyman's Library,1992,由本文作者翻译。
对诗歌中的老年主人公来说,美貌的女人只能如同画像一样去欣赏。这看似轻松的笔调隐藏着说话者的巨大失落和痛苦。美人如画的比拟暗示他老了,失去了激情和爱的实际能力,所以只能自我安慰,“满足于眼睛或耳朵的享受”。说话者不但将失落和痛苦以眼睛和耳朵的满足掩盖起来,并且宣称“自知让我快乐”。这种快乐感人至深,因它建立在失落和痛苦之上,并试图战胜失落和痛苦。在尴尬无奈的“变老”事实面前,说话者通过他的“快乐”展示的是他的不屈和骄傲。因此这首“变老”之歌体现了象征勇气和力量的“悲剧中的喜悦”。
在叶芝著名的诗歌《驶向拜占庭》(“Sailing to Byzantium”)中,说话者用灵魂的歌唱来战胜“变老”的失落和痛苦:
上了年纪的人是无用之物/是搭在架子上的破衣裳/只有当灵魂击掌而歌,/为每个破败之躯更响亮地歌唱
诗人毫不留情的比喻——“上了年纪的人是无用之物,是搭在架子上的破衣裳”,暗示了“变老”的残酷和说话者深切的痛苦。但说话者努力不让自己陷入身体破败的尴尬,他通过寻求灵魂的歌唱表达了他的超脱,也表达了他摆脱现实的决心,向世人展示了一个主宰者和胜利者的姿态。“灵魂的歌唱”因此体现了“悲剧中的喜悦”。
虽然这两首诗歌中说话者赖以战胜“变老”带来的失落和痛苦的智慧和灵魂被叶芝以后视为软弱和对生命力的否定②叶芝曾说过:“固守教条的评论家们很难明白,诗人活力四射,无暇理会智慧。如尼采所言,智慧是蹩脚诗人的疗养院……智慧的尽头是勇气的开始……”见Frances Nesbitt Oppel,Mask and Tragedy:Yeats and Nietzsche,1902—10.University Pressof Virginia,1987,p.82.,但在残酷的“变老”现实面前,说话者和诗人将智慧和灵魂变成为战胜失落和痛苦的武器。因来自智慧和灵魂的喜悦,说话者在“变老”面前不再显得软弱无力、徒然伤感,而具有了主宰现实的力量。因此此时的“智慧”和“灵魂”具有了叶芝最喜欢借用的手段——“欢笑”的力量。
在《老疯子简看着舞者》(“Crazy Jane Grown Old Looks at the Dancers”)这首诗歌中,“悲剧中的喜悦”体现为疯子简想跳舞的冲动。这首诗歌基于叶芝的一个梦境:年轻的恋人相拥而舞继而杀死对方。叶芝借这个奇特的梦境象征爱与恨的不可分离。而年老的疯子简作为这爱恨交织的一幕的目击者,不为恋人的死亡所动,而希望回到也能如他们一般的舞蹈的年龄:
上帝与那段时光同在/那时我不惧怕会发生什么/而身段灵活/可以如他们一般舞蹈
疯子简的神往暗示了她的衰老和无能为力。但她用“舞蹈”这一举动化解了应有的悲伤。舞蹈象征着年轻、活力、激情和自由,具有魔力。叶芝在多首诗歌中表现了这一思想。如在《在学童中》(“Among School Children”)一诗中,舞蹈具有融合身体与灵魂的神奇力量:
哦,随音乐而舞的身体,哦,愈发明亮的目光,/我们如何分得开舞者和舞蹈?
在《献给在风中跳舞的孩子》(“To a Child Dancing in the Wind”)一诗中,女孩的舞蹈象征她的年轻和无忧无虑,与年老的说话者的智慧和忧虑形成对比:
在那海滩舞蹈/你何惧风的侵扰/和海的咆哮?
舞蹈象征着年轻和激情,象征着摆脱桎梏。因此,疯子简对跳舞的向往,是对“变老”的现实的不屑,是对约束自己的年龄的挑战,具有“悲剧中的喜悦”的力量。
在叶芝以“变老”为主题的诗歌中,“悲剧中的喜悦”更多表现为强烈的情感如自嘲、愤怒和疯狂。其中自嘲表现为对自我形象夸张、变形的描述。年老的说话者常将自己描述成“破裂的树”(《领养老金老人的哀叹》)、“象荆棘一样粗糙”(《观察水中的自己的老人们》)、“老赶鸟人”(《在孩童间》)、“搭在架子上的破衣裳”(《驶向拜占庭》)、“大理石般的半鱼半人”(《智慧随岁月而长》)等。说话者的自嘲让说话者变成冷眼旁观者,具有了嘲笑的能力,从而走出了被同情和被嘲笑的角色。尼采曾借主人公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之口问过:“英雄,什么是最沉重的东西?去问问负重的灵魂,让我好接过来为自己的力量喝彩。最沉重的难道不是羞辱自己从而让骄傲低头?展示自己的愚蠢从而嘲笑自己的智慧?”①Friedrich Nietzsche,Thus Spake Zarathustra,translated by Thomas Common,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21—22页。叶芝“变老”诗歌中的主人公正是背负了羞辱自己的重担,才让人感受到了他们的力量和勇气,“变老”的悲剧从而演化成为对老年主人公力量和勇气的喝彩。
在诗歌《他年轻时的朋友》(“The Friends of His Youth”)中,自嘲体现为不可遏制的狂笑:
是狂笑而不是年龄/让我的嗓子嘶哑
说话者的狂笑因他的老朋友的荒诞而起:老玛姬给石头喂奶而老彼得声称是孔雀之王。说话者的狂笑化解了因年老的荒诞而产生的怜悯之情。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曾说过:“如果曾经作为发泄某一特殊心理情感的渠道的能量闲置不用,它便自由释放出来,从而产生大笑。”②Qtd.in Jahan Ramazani,Yeats& the Poetry of Death:Elegy,Self-elegy,and the Sublime,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p.102.说话者的狂笑便是对荒诞无奈的老年而可能产生的怜悯之情的释放和化解。更重要的是,狂笑给了说话者以旁观者的姿态,从而使他有别于他的老年朋友,也与同样年老的自我拉开了距离。
随着叶芝自己年龄的增大,他的“变老”诗歌中“悲剧中的喜悦”演变为更激烈的情感如愤怒、疯狂等。如《塔》(“The Tower”)中的说话者宣称要“嘲笑普罗提诺的思想,/在柏拉图的牙缝中大喊”,以对抗社会认为老年人只应满足于“辩论和抽象的东西”而不应纵情于想像的陈见;在诗歌《一亩草地》(“An Acre of Grass”)中,说话者要求:“给我老年人的疯狂。/我要重塑自己,/直到我变成泰门和李尔王,/或是布莱克,/捶打着墙壁,/直到真理回答他的叫喊。”说话者赖以重塑自我的榜样都是激情或疯狂的典型:李尔王(King Lear)是文学作品中著名的疯子形象,布莱克(william Blake)在很多人眼里是疯子。叶芝在著作《灵视》(A Vision)中,将布莱克归为第16月相③叶芝在著作《灵视》中,将月亮的运转划为28个时段,并根据人的外在性情和内在性情等因素将人与月亮的28个时段相对应。此处本文作者将人所对应的时段翻译成人的月相。,位居16月相的人都“带些癫狂”④W.B.Yeats,A Vision,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37,p.138.。说话者以这些癫狂的形象为榜样重塑自我,也宣告了自己的癫狂。
在叶芝的“变老”诗歌中,说话者的激烈情感甚至以“邪恶”的形式表现出来。最坦率的“邪恶”形象当属《一个疯狂邪恶的老头》(“The Wild Old Wicked Man”)中的“我”。“我”宣称“为女人疯狂”。虽然他承认希腊故事中塞勒纳斯(Silenus)关于人生的智慧——人生是充满痛苦的,但他将塞勒纳斯的谏言“最好不要出生,出生了最好马上死去”修改成了“我选择次好,/在女人的胸脯/暂时忘掉一切烦恼”。这种公然对肉体的依恋在传统的眼光看来是邪恶的,但“我”丝毫不讳言其“邪恶”。
叶芝晚期“变老”诗歌中表现的激烈的情感是“悲剧中的喜悦”的极端表现形式。相对于死亡,“变老”作为悲剧是迟缓而漫长的。“变老”通过让人渐渐地变形、变弱、变迟钝而感到无奈和屈辱。这种慢性的折磨惠特曼曾喻为“不知是生还是死”⑤诗句出自惠特曼的诗歌《对七十岁的质问》(“Queries to My Seventieth Year”),qtd.in Wayne Booth,The Art of Growing Older:Writers on Living and Aging,New York:Poseidon Press,1992,p.66.。它需要强烈的情感来撕扯冲破。叶芝“变老”诗歌中老年人的自嘲、疯狂、愤怒甚至“邪恶”恰恰是摧毁这慢性折磨的力量。剧烈的情感犹如兴奋剂,让老年人充满了激情和活力,并且无所畏惧。当老年说话者自嘲、愤怒,宣称自己疯狂、邪恶的时候,他自己便具有了摧毁“变老”带来的悲伤、失落的力量。如史蒂芬斯(Wallace Stevens)所言“内心的狂暴让我们免受外界狂暴的伤害”①Qtd.in Jahan Ramazani,Yeats& the Poetry of Death:Elegy,Self-elegy,and the Sublime,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p.79.。对悲伤和失落的克服既是对自我的战胜,也是对衰老的挑战。老年说话者没有因“变老”而变得孱弱,反而变得更加无畏和强大。“悲剧中的喜悦”由此而生。丹尼尔·阿尔布莱特(Daniel Albright)曾说过:“叶芝认为所有极致的经历是可相互转换的,如性高潮、暴死、憎恨、宗教体验。由此形成了他的‘悲剧中的喜悦’之说。”②W.B.Yeats,The Poems,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Daniel Albright.London:Everyman's Library,1992,p.735.叶芝“变老”诗歌中表现出的极致的情感正是“悲剧中的喜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但叶芝晚期“变老”诗歌中体现出的狂暴的情感也让人不安和质疑。拉马扎尼认为诗人的狂暴让他自己成为摧毁力量的一部分从而自取灭亡③Jahan Ramazani,Yeats& the Poetry of Death:Elegy,Self-elegy,and the Sublime,New Haven&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p.125.。而布鲁姆(Harold Bloom)认为叶芝晚期诗歌中体现的愤怒是徒劳、没有意义的。他说:“在《最后的诗歌集》中,叶芝确实展示了癫狂,但我们不喜欢这种愤怒,原因如西奥朗④西奥朗(Emil Cioran)为20世纪罗马尼亚哲学家和散文家。所言:‘只有摧毁自我从而使生命获得某种意义的人才能够吸引我们。’”⑤Harold Bloom,Yeats,London,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p.406.布鲁姆认为叶芝一贯是避免极端的,因此晚期诗歌中表现的疯狂有些不可理喻。
其实叶芝晚期诗歌中表现的疯狂体现了“变老”现实的愈发残酷和诗歌主人公,也是叶芝本人对“变老”更加激烈的反抗。在初尝“变老”的苦涩时,叶芝试图通过求助于智慧、灵魂等温和的手段来蔑视、战胜肉体的“变老”;当“变老”让人进一步变形、变弱、变迟钝时,对智慧、灵魂的求助就意味着对肉体的放弃,也即对“变老”的屈服,而只有通过狂暴的情感,通过对智慧、灵魂等传统观念认为属于老年人的美德的反叛,诗人才能达到与“变老”抗争的目的。叶芝曾在诗歌中坦率地承认老年诗人对狂暴的情感如“欲望”和“愤怒”的依赖:
你说多可怕呀/欲望和愤怒肆虐着你的老年/你在年轻时它们没有这么猖狂/没有它们我何以歌唱?(《刺激》)(“The Spur”)
此处的“歌唱”可以理解为诗歌创作,也可以理解为战胜“变老”的力量——“悲剧中的喜悦”。这种力量由狂暴的情感而生。因此叶芝晚期诗歌中诸多疯狂的情感的意义在于其体现的力量和反抗。这种反抗也许显得荒诞可笑或如飞蛾扑火,但这反抗显示了老年主人公和叶芝的勇气与力量。老年主人公的肉体随着这绝望的反抗一步步走向死亡,但他们的精神却在死亡中得到了重生,如酒神荻俄倪索斯的肢解和重生。这不正是尼采和叶芝赞赏的悲剧精神吗?
叶芝“变老”诗歌中体现的“悲剧中的喜悦”让“变老”脱去了悲伤和失落的基调,成为勇气和力量的象征。虽然“变老”是无法克服的,叶芝却为我们如何有尊严地变老指出了一条可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