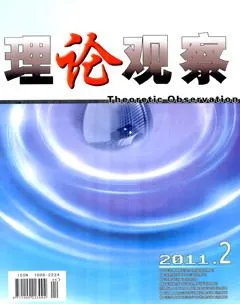对俄汉字教学理念问题探讨
[摘要]教学理念是指导对外汉语教学的指导性纲领,决定了我们采用何种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分析汉字教学理念存在的问题,适时转变教学理念对对俄汉字教学具有一定的帮助和促进作用。
[关键词]教学理念;汉字;俄罗斯
[中图分类号]G643.2[文献标识码] A [文章 编号] 1009 — 2234(2011)02 — 0129 — 02
教学理念指的是“人们在理论层面对汉字及汉字教学总的、一般的看法”〔1〕。教学理念是指导对外汉语教学的指导性纲领,决定了我们采用何种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汉字教学理念可以反映出教师对汉字教学的认识,直接作用于教师的汉字教学过程中。现在的对外汉语教学界深受西方语言学的影响,认为汉字是一种“自源文字”,认为“凡自源文字都是表意的,凡他源文字都是表音的”〔2〕。这种理念引发的“连锁”反应就是将汉字与汉语相分离,只看重口语当中的应用,而忽视汉字的教学。
一、简单挪用西方语言教学相关理论
目前,我国对外汉语研究界对汉字的研究多集中在字形研究上,而且相关的理论基础都是建立在西方语言学基础之上,并没有体现出我国语言学的特色,特别是在整体语言结构上和语法结构上一直缺少系统的理论探讨。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国际交流的加强,缺少语法系统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特别是无法满足对外交流的需要,不利于汉字的推广。所以,有的学者就开始引入印欧语系中的语言研究来为汉语寻找理论支撑,这样,印欧语系的理论就成为了汉语语言理论的研究基础。这种状况从《马氏文通》开始一直延续至今。
受西方语言学影响,我国的研究界也把“词”作为研究语言的基本单位,但是,汉语本身是以“字”为基本单位的,这造成了一种研究上的错位。受到这种研究思路的限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一直比较忽视汉字教学,也出现了“在词语中学汉字”和“随文识字”这类的教学观点。这样造成的连锁反应就是没有独立的汉字课,将汉字教学依附于语言教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重口语、轻汉字、重阅读、轻书写,学生也对汉字学习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只是在汉语学习的过程中,顺便学习汉字。这样学到的汉字基本上是一盘散沙,毫无规律可言。其直接结果就是学生认为汉字“难学”,老师认为汉字“难教”,很多学生逐渐丧失汉字学习的兴趣,也没有找到汉字学习的规律,甚至放弃汉字学习,只练口语。结果,缺乏汉字认知来支撑的口语水平很难再有突破性的进步。
因此,应该加强“字本位”观念。这种“字本位”的理论概念首先是于1989年由张朋朋在法国与白乐桑合著的《汉语语言文字启蒙》教材中提出的。他们认为:“汉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汉字是表意文字,个体突出,以单个汉字为基础可以层层构词,故本教材可称为‘字本位教学法’”。〔3〕对外汉语教学界在不断实践中发现了汉字在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性,因此提出这一理论,这一理论至今都能带给我们重要的启迪。
随后,国内语言学界也逐渐接受了这个原本属于对外汉语教学界的概念。20世纪九十年代,一些学者试图摆脱照搬西方语言学理论的误区,创立属于汉字独有的语言学。原本,中国的语言学紧跟西方语言学的发展,用语法体系研究替代文字研究,用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的话来说就是:“所有理论都是外来的。外国的理论在哪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4〕。但是,后来,语言学者们逐渐发现西方的语言学理论无法解决国内的语言学问题。于是,“汉字”又重新成为研究的焦点。“字本位”语言学认为汉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并以“字”为纲,试图建立以“字”为核心的汉语研究体系。
虽然,“字本位”的理论主张引起过一定争议。但是,语言学界与对外汉语教学界同时意识到“字本位”的重要性,这无疑不是偶然的。这说明,汉字的某种规律与特征正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认识到。而这种理论也可以为我们开展对外汉字教学提供一些理论的支撑。首先,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汉字的地位。
西方语言学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文字”记录“语言”的什么?刘庆俄认为:“语言的本质是语音和语义”〔5〕,但是,很显然,我们无法用语言来记录语音,那么,就只能认为文字记录的是语义。当我们再深入考察汉字的历史会发现,汉字的起源是出于表意的目的,而不像西方语言学家认为的那样,由于语言的需要,才发明了汉字,文字一开始诞生并不是为了记录语言。因此,“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这一论点也自然无法成立。这一观点在对外汉语教学界的直接影响就是使汉字教学成为了汉语教学的附属品,这体现在我们平时教学中采用的“语文一体”、“文从语”等教学方法中。“不正确处理中国文字和语言特有的关系,正是汉语教学危机的根源。”〔6〕汉字教学在汉语教学中丧失自身复杂的系统性,课文中出现的汉字毫无系统性可言,完全是为了整体语言教学的需要,而不顾及汉字教学的循序渐进性。例如,口语教学中教“再见”,汉字教学就教写“再见”;口语教“对不起”,汉字教学就教写“对不起”。不考虑“再”是如何构成的,“起”是怎样分解、组合的,也不考虑最开始是否应该先学习这些汉字。因此,学生大部分都认为学习汉字“很难”,并在障碍面前逐渐丧失了学习汉字的兴趣。对于初学者来说,用汉语拼音来辅助学习汉字是必须的,而且也是应该被鼓励的,但是,从长远来看,不学汉字是不利于学生们汉语水平的进一步提升的。这些学生在初期的提高会比较快,但是,当其他学生学习汉字之后逐渐摆脱了对拼音的依赖,汉字和汉语学习的难度逐渐加大时,那些不学汉字,总拿拼音当拐棍的学生汉语水平就很难提升了。这是因为文字能力和语言能力是不同的,而文字能力又可以转化为语言能力。在教学中也应该促进二者之间的相互转化。
二、脱离汉字文化根基
想要掌握一种文字,就要了解这种文字形成、演变背后所体现的历史、文化特征,特别是使用这种文字的人的历史与特点。汉字经过了漫长时间的演化,背后就浓缩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因此,想要学习汉字,就要先了解中国文化。
汉字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其不断演变发展的漫长历史中承载了中国的文化。但是,在对外汉字教学中,教师往往只是单纯地去就单个字来讲解字义、字形,对于汉字背后所蕴含的文化背景则重视不够。这种教学上的偏差在客观上割裂了中国文化与汉字的关联。俄罗斯留学生在学习汉字时就变成了机械记忆。无法掌握汉字与汉字之间、汉字与词之间所具有的文化上的联系,更谈不上从这种联系之中去摸索汉字构词的规律。这就扩大了汉字与学生之间的鸿沟,更加深了留学生的畏难情绪和厌学心理。
其实,汉字与文化是一种相伴相生的关系。汉字演化的历史就是中国文化不断孕育、重组的过程,中国文化在汉字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心理也深深地烙印在汉字上面。所以,掌握了汉字就基本等同于掌握了中国文化,而汉字也反过来作用于中国文化。因此,在教学中不能忽视汉字背后的文化内蕴。这也是提升学生汉字学习兴趣的重要方法。
三、没有充分认识到汉字与拼音文字的差异
俄语是一种典型的拼音文字,而汉字与拼音文字之间有很大的差别,这也是俄罗斯留学生认为汉字难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实际上,汉字有属于自己的特点。汉字的构成是建立在形、音、义三者统一的基础之上的。教师在进行汉字教学的时候,必须把这三者结合起来,而不能将他们割裂,只加强形和义的灌输,而忽视字音的传授。从本次调查中可以发现,留学生在学习汉字的时候,面对的主要难题就是发音问题,由于俄语与汉语差别较大,所以,他们一时无法掌握汉字的读音规律。为了掌握汉字的读音,他们普遍会使用母语记音的方法。这主要也是因为他们的母语俄语是拼音文字,他们非常习惯看见文字就能发音。在初学汉字阶段,这也可以当做一种学习汉字读音的方式,但是,毕竟这不是一种正规的学习方法,也不利于他们的进一步发展。要改变他们这种学习方法,就需要教师从理念上彻底转变,将读音教学也放在与形、义教学同等地位上。
在语音教学当中,应该重视汉字的声调教学。因为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留学生普遍认为汉字的声调很难掌握,不仅是初学者,连高级班的留学生也面临这个问题。在平时与留学生的交流中也可以发现,他们的声调很奇怪,一听就能听出来是外国人。所以,声调方面的教学也要更加引起教师们的关注,在刚刚开始教授留学生汉语时,就要让他们掌握汉语拼音与声调,并强调他们发音声调的准确性。
从视觉角度来看,拼音文字的基本构成形态是字母,采取线性的组合方式,而方块汉字由笔画构成的间架结构,这让汉字看起来就像一个个的小方块。对于基本没有汉字基础的俄罗斯留学生来说,汉字就像是一幅幅“图画”,这些“图画”还有着特殊的“画法”——笔画。笔画之间可以相连、相接、相交,也可以分离,整体结构也各有差异。对于俄罗斯学生来说,由于他们写惯了拼音文字,写汉字甚至都不知道要如何下笔,很多留学生初学写汉字的时候就像是画画一样。他们并不了解汉字的构型,只是将汉字作为毫无规律的图画来死记硬背,这样不仅会耗费学习者大量额外的精力,还会打消他们学习汉字的兴趣。
汉字教学理念是教师在汉字教学过程中需要遵循的指导性纲领,虽然不直接显现于外,但却贯彻于教师的教学行为中。正确的教学理念应该建立在充分遵循汉字自身性质、特点的基础之上来展开,还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国家留学生母语与汉语的语言学习差异,对留学生在汉字学习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要区别对待,根据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来加以解决。
然而,当前的对俄汉字教学主要还是遵循西方语言学和语言教学理论的整体脉络,没有充分认识到汉字自身的规律,将汉字与拼音文字相区分。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语言先于文字而存在。但是,不能因此就彻底抹杀文字的独立性,特别是汉字的独立性如此明显。如果在教学中对这一点不进行强调,就很容易出现整体教学上的偏差。
所以,对俄罗斯留学生汉字教学要树立符合汉字自身特质的教学理念,明确汉字的基本性质:汉字是表义性的文字。汉字的出现不仅是为了记录语音,还对文字的含义有一定的指示作用。这种汉字所独有的表义特性使汉字能够被汉民族所传承。不仅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而且,还能够跨越地域的局限,不受任何方言的束缚。
〔参考文献〕
〔1〕张楚廷.课程与教学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113.
〔2〕潘文国.字本位与汉语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90.
〔3〕白乐桑,张朋朋.汉语语言文字启蒙〔M〕.法国:La Gompagnie,1989:3.
〔4〕潘文国.字本位与汉语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6.
〔5〕刘庆俄.《汉字文化》语言文字大论坛〔J〕.2007,(01).
〔6〕白乐桑.汉语教材中的文、语领土之争:是合并,还是自主,抑或分离?〔J〕. 世界汉语教学,1996,(04).
〔责任编辑:孙文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