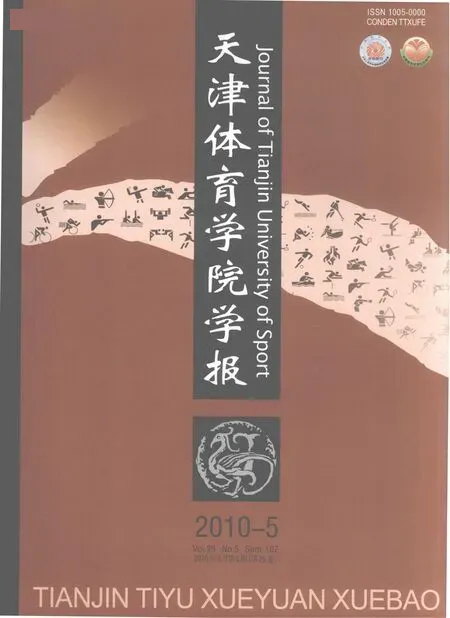竞技体育规则:规制伤害行为的优位选择
——兼论刑法的适度干预
刘延军
竞技体育规则:规制伤害行为的优位选择
——兼论刑法的适度干预
刘延军
在竞技体育中,重大伤害时有发生,如何规制竞技伤害行为引起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且争议颇多。但是理论界多将视角放在刑法对于竞技伤害行为的抑制方面,而忽略了竞技伤害行为的特殊性。对于触犯刑法的竞技伤害行为,应当依据刑法进行规制,但是由于竞技运动存在规则允许的前设性条件,这就使得竞技伤害行为的主观故意异于普通伤害行为之主观恶性。因此,对于竞技体育伤害行为,应当完善竞技体育规则的处罚体系,优先适用竞技体育规则,必要时才辅以刑法的适度干预。
竞技伤害行为;刑法;竞技规则
竞技体育之所以得以续存、发展,是因为竞技行为具有正当性且它的竞技规则被法律所认可。严重犯规造成的竞技伤害行为似乎失去了这种正当性,越来越多的理论界呼声要将这类竞技伤害与其他的体育暴力一起置纳入刑法规制的视野。
但是,笔者认为,竞技体育中的这一类伤害,具有其特殊性,刑法不规制和过度规制都会引起人们对竞技体育良性发展的担忧。当发生较重的竞技伤害时,由于现有的竞技规则对是否产生伤害后果的行为处罚未作区分,使得对这种伤害行为的处罚过轻,不足以给违规者足够的惩戒,以至于一些竞技者有意无意地利用规则来规避处罚。于是,理论界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将这种严重的竞技伤害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可是,笔者通过对竞技体育严重犯规、恶意伤害的刑事立法本身及其在法律实践中的实际效果进行分析与研究,发现将竞技伤害行为犯罪化的做法,无法在法益判断上寻求到立法的根据,即使能找到法益的依据,但在司法实践中也会遭遇无法适用的困难。纵观竞技体育,我们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在造成伤害的竞技行为中,超过竞技正当性的行为未必就达到了犯罪的程度,刑法的介入并不是我们在规制恶意竞技伤害行为方面所能达致的唯一期待。
1 竞技体育伤害行为概述
竞技体育是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体育竞赛为主要特征,为了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发挥人在体力、心理、智力等方面潜力的基础上,以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和创造优异运动成绩为主要目标的一类体育活动。竞技体育作为一种体育运动,最大的特征是竞争性。“竞”是指比赛和竞争,实现所有选手的目标和个人优势的最大化,而“技”是使它还具有公平性、规范性、协同性和观赏性等特征。竞技体育得以存续发展与其具有的显著特征即对抗性密不可分。然而与激烈对抗使命相伴的便是在对抗中给选手带来的身体伤害,特别是身体直接对抗的项目伤害可能更大,如拳击、跆拳道、中国散手、冰球、橄榄球、足球、篮球等。
首先,我们需要对两个概念进行区分,即体育暴力与竞技伤害行为。罗嘉司从刑法学角度在其博士论文中对体育暴力进行了这样的界定:体育暴力指在竞技体育活动的过程中,基于行为人的故意,实施冲撞或其他行为导致超出社会所容许的危险范围的伤害行为。主要指运动员在场上的各种攻击和暴力行为,包括互相殴打(运动员对运动员,运动员对观众、观众对运动员)等,这是一种对体育暴力的狭义界定。韩勇[1]在其《体育法的理论与实践》中对体育暴力给出了广义定义,即:“体育暴力是体育中发生的一种有目的的伤害或破坏行为,有外显的语言或身体动作。包括竞技场内或外,竞技人员或非竞技人员之间。”这种界定是为了适应研究当前体育暴力向场外扩展趋势的需要。而本文中的竞技伤害行为,仅指运动员之间在比赛中发生的,并且与其他竞技行为看似相连贯的伤害行为,是更为侠义的界定,称之为竞技伤害行为,无论这种伤害行为是有意的、无意的,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也即奥伦·弗雷利认为的犯规的三种类型:无意犯规;故意犯规以从中获取一定的优势,但其犯规行为包含了很高的技能和技巧,以试图免于受罚;故意犯规而甘愿受罚。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体育部,重庆401120。
其次,从是否可避免的角度把竞技伤害可分为两类:竞技运动意外伤害和犯规造成的伤害,其中后者包括无伤人故意的严重犯规和有伤人故意的严重犯规。竞技意外伤害指在竞技体育中产生的,由于运动员的竞技行为造成的,但运动员没有重大违规时产生的轻重伤害。它的特征是无法预测和不可避免性,是竞技比赛规则允许的。比赛中的恶意伤害,首先是严重违反竞技规则,而且有伤人的故意。它具有两个故意性:(1)违反竞技体育规则的故意;(2)伤人的故意。而在比赛暂停或终止后以及与正当竞技行为明显不连贯,由运动员的恶意行为产生的各类轻重伤害,都不属于竞技伤害行为,是与比赛无关的,不能以竞技行为论。这种行为的伤害后果只要到达了一定程度,就可以直接适用刑法,而不能以行业内部行为论,不能以行业内部处罚代替刑事处罚。
正常竞技行为产生一定的伤害是不可避免性。从运动伦理学的角度讲,是一种有限伤害,是合理的[2]。而那些表面上是比赛行为,实则使用危险方法所造成的重大伤害是不合理的,是竞技体育规则所不允许的,它违反了竞技体育有限伤害的原则,严重侵害了体育的公平竞争原则,不属于竞技体育的正当行为。博克斯尔认为,体育一般有维持公正公平的规则和构成性规则两种不同类型的重要规则。有些运动项目可能比其他运动有更多的规则,也可能仅有一种类型的规则。例如保证礼仪、安全和公平竞争的规则:在拳击比赛中,不能击打腰部以下的部位;在棒球比赛中,不能掷击球手的头部。当运动员违背这些规则时,就要受到惩罚。公平竞争的规则对在比赛中擅自改变平等竞争态势的作法做出惩罚。体育比赛中人们理应接受这些基本规则,但有时为了获得战略上的优势,可能要控制利用这些规则,这种对于规则的僭越,必须立即进行惩罚,否则竞技体育这座大厦将因失衡而坍塌。
在2008年奥运会足球比赛中,中国对比利时,中国运动员谭望嵩为争球而使用粗暴的动作将比利时球员波科尼奥利踢成重伤,以致这名球员失去生育能力,比利时足协随后向比利时法院以故意伤害罪起诉谭望嵩[3]。按照我们给竞技伤害行为下的定义,在此案中,谭望嵩的蹬踏动作已严重犯规,被裁判当即判罚下场,显然这一行为已超出了竞技体育意外伤害的范畴,属于严重犯规造成的伤害,失去了竞技正当性。如果有证据证明谭望嵩在主观上有伤人的故意,对谭进行刑事起诉是可行的。但要证明谭当时的动作是要伤人而不是正常的踢球却非常困难,因为在高速奔跑中,在亢奋精神的支配下,运动员的动作瞬息万变,轻重缓急不易控制,依据竞技规则去判断是否违规容易,但要从刑法的角度认定谭在主观上具有伤人的故意则太难。
2 竞技体育伤害行为法律规制之域外考察
由于现代体育源自西方,对于在竞技体育中发生的暴力伤害理论界早有关注。司法实践中,对于法律与竞技体育的关系也有相当数量的研究。由于司法传统和立法体制的原因,这些研究主要散见于司法判例中。
早在19世纪末,英国的一系列司法裁定都认为拳击不合法。其中最典型的是1882年做出的一项裁决。法官认为在这样的比赛中,参赛者的直接目的就是要用暴力的手段击倒对方,这是最明显不过的事情。不论参赛者是基于愤怒或是为了金钱,还是为了其他利益,这种行为都是对社会安宁的违背。但后来,由于竞赛规则进行了重大改革,职业拳击这项运动最终被法律认可。虽然拳击比赛经常会造成运动员的严重伤害,甚至是永久性的伤害,但还是认为拳击运动并不是非法或犯罪行为,前提是不论是否为了获取奖金,参与者的目的是仅把它作为一项拳击运动或竞赛,比赛自始至终没有敌视愤意的存在,仅仅是把比赛作为在竞赛规则限定下拳击技巧和身体的较量,而且“有条件保证身体伤害能够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能够保证降低或减少人身伤害的危险性,是在遵守竞赛规则的情况下通过展示最佳的拳击技术而取得的胜利”。
1878年发生在爱尔兰Leicestershire郡的Bradshaw案。在两支当地球队进行的足球比赛中,Bradshaw造成了对方球员Dockery的死亡。官方的司法报告对事件的叙述如下:“比赛开始一刻钟后,死者带球向对方球门突破,而被告人冲过来进行抢断。双方都在正常的速度下奔跑,在身体接触前,Dockery将球踢出,而被告人在‘冲’向原告的过程中跳向空中,其膝部撞在死者胃部,双方侧向相撞,同时跌倒,被告人平安无事的站了起来,而死者在艰难的爬起后又摔倒在地。在经历了可以想见的痛苦后,死者于次日死亡,死亡原因是肠断裂。”本案的主审法官Bramwell在对案件进行总结时提出,如果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运动员没有做出超越足球比赛规则以外的行为,那么就应该认定其行为合法,“如果一名运动员完全遵守比赛规则进行比赛,没有任何逾越,那么就很有理由认为他没有任何恶意,没有做出任何他认为能够造成他人死亡或受伤的行为”。法官最后向陪审团表明自己倾向判处被告人无罪,因为所发生的一切只是一个事故。此判例被作为即使在激烈比赛中发生重大危害结果,司法也不宜介入的经典案例。
1992年,英国发生了这样一起橄榄球案例:诺丁汉队与伦敦队进行的比赛中,诺丁汉队球员马蒂与伦敦队球员瑞斯发生了纠缠,致使马蒂受到了较重的伤害:颌骨骨折,并被打掉两颗牙。在向法庭提供证据时,马蒂详细地描述了整个事件,试图证明起诉瑞斯的合理性,并讲道:“我无法忍受在一项如此钟爱的运动中看到出现这种程度的暴力行为”。瑞斯则辩解说是马蒂一直在对自己犯规,打马蒂只是为了引起裁判的注意,以阻止这种非法的干扰,而没有伤害马蒂的意图。最后皇室陪审团裁决瑞斯无罪。在其后来的辩护词中,说道“如果运动道德的重要元素之一竞赛精神和裁判的权威都要诉诸于类似的诉讼程序来决定,而且这种决定成为体育活动的控制性因素的话,那将是十分不幸的”。此判例被作为体育竞技伤害豁免于司法裁决的经典案例。
从以上发生在英国的两个典型司法判例来看,即使比赛中发生了重大伤害,只要运动员证明是出于比赛的良好动机,当伤害案件诉诸司法,也都能得到豁免。美国法学会1962年通过的“模范刑法典”第二章“责任之一般原理”第十一条“被害人之承诺”中的规定:对于伤害身体之场合对其行为或引起危害之承诺,在下列情形可作为抗辩,其行为与伤害由共同参加合法的运动与竞赛一事,通常即能预见其危险时。
而大陆法系国家多把竞技体育以正当业务行为规定在刑法条文中,如“日本刑法”第35条、“西班牙刑法典”第8条、“瑞士刑法典”第32条、“意大利刑法典”第51条、“保加利亚刑法典”第10条等。
对于竞技伤害的责任承担上,从外国法律的规定可以看出,竞技体育恶意伤害属于轻罪,对之大多处以罚金。“对于竞技伤害在司法适用方面,由于该罪在调查取证及认定上确存在很多困难,所以真正以恶意伤害罪处理竞技伤害的还是少数”。
3 我国对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规制现状
3.1 我国对竞技体育伤害行为规制的困境
由于竞技体育自身的特殊性,加之社会发展及各种因素的影响,对竞技伤害行为的规制也给我们带来困境,面对越来越多的竞技伤害,我们不完善的竞技规则处罚体系已经不能最大程度地有效抑制竞技伤害的发生,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呼吁将这种文明背后的不文明伤害纳入刑法规制[4],可是对于此行为的入罪出罪标准,现行的刑法却很难认定,这不仅给理论带来挑战,更给司法实践带来困难。
3.1.1 我国法律对竞技体育行为排除犯罪性的规定 我国刑法规定正当行为只有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两种,而对于竞技行为的正当性没有作出任何规定。理论界虽然对正当行为外延的范围未达成一致意见,但竞技行为是属于正当行为的一种类型还是被大家普遍认可的。正当业务行为包括医疗行为、体育竞技中的误伤行为。所谓体育竞技中的误伤行为,是指在剧烈的体育竞赛中,运动员之间因过失而致人伤亡的行为[5]。在体育竞技中,如赛车,拳击、足球、武术等项目,危险性很高,自古以来有不计其数的运动员在其中致伤致残,有的甚至丧失了生命。马克昌[6]在“犯罪通论”中写到:“由于体育竞技属于正当业务行为,运动员只要遵守了有关竞赛规则,非故意致人伤残,就排除犯罪性,不负刑事责任。但如果不是在比赛的过程中,而是在比赛场外,故意打伤、打死对方,则不是体育竞技中的正当行为,应追究刑事责任。”李晓明在“中国刑法基本原理”论述中认为,“竞技体育是一类正当业务行为,但并非因为是业务就不成立犯罪,而是因为”正当“才排除犯罪。要排除犯罪,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必须是法定业务内的业务;(二)必须是业务范围内的正当行为;(三)行为不得超出业务上要求的必要限度”[7]。竞技行为不能超出必要的限度,正当业务行为的法学理论依据是社会相当性。“所谓社会相当性,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历史所形成的社会伦理程序所允许的行为。例如医生的外科手术行为、拳击、摔跤等竞技行为,就是具有社会相当性的行为适例”[8]。社会相当性理论从动态的观点出发,将违法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加以考虑。根据社会相对性理论,“违法的标准不是单纯地看法益是否受到侵害,如果凡侵害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法益都作为违法而加以禁止,那么,社会生活就停滞不前了。为了使社会生活发挥生气勃勃的机能,对于那些从静止、绝对的观点来看似乎是侵害法益,但从动态、相对的观点来看则是社会的相当行为,并不认为违法。只有那些超越了社会相当性的行为,才能视为违法”[9]。在竞技体育中,意外可能造成伤害,但严重伤害通常是严重犯规造成的。而严重犯规并没有都造成严重伤害,从以上正当业务行为的理论依据,即社会相当性来看,没有造成伤害后果的严重犯规和造成伤害的单纯的严重犯规行为,是与竞技体育危险性相当的。只有一小部分恶意的严重犯规才超出了这种相当性,应该受到刑法的处罚。但是,在实践中如何找出这一小部分具有伤人故意的严重犯规却是非常困难的。人在特定场合下,对周围事物的注意和反应取决于多种因素。而且,个人行为的认定还需要考虑特定的前提条件,即除纯身体的行为可能性外,还要求把行为人对行为目的的认识以及动机可能性作为认识基础。刑法上的罪过是一种主观因素,是认定犯罪所必需具备的犯意要素,人们只能根据外在行为来判断主观的内容[10]。刑法实践中,为了证明行为人是否具有主观恶意,经常采用一种叫“理性人”的判定模式,即一个正常的普通的人处于此位置上,是否会做出这样的行为。但笔者认为这种判定模式是不能在竞技场上适用的,因为在瞬息万变的“准战场”上不存在一个标准的“理性人”[11]。
3.1.2 现行竞技体育规则处罚力度不足 竞技规则不完善的处罚体系,让那些严重违规可能导致伤害的行为得不到与其危害性相当的处罚,导致有无伤害后果的严重犯规受到一样的处罚,对危险动作约束力不足,于是当有这种竞技伤害时,我们的竞技规则显得无能为力。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现行规则下运动员严重犯规产生的处罚后果:要么按照既有的规则判罚下场,要么按照伤害罪定罪处罚。这两种处罚结果实在反差甚远,失掉一两场比赛和被判刑入狱,之间没有缓冲地带或中间地带,这种处罚体制,即体育行为社会控制太不科学,太过粗糙和简陋。只有设置了哪怕是不尽合理的中间地带,那么作为法治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刑法就大大减少了与竞技伤害行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有鉴于现有的规则对严重犯规行为的处罚过轻,易造成刑法处罚面的扩张[12]。如果规则加大了对严重犯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刑法就只需发挥谦抑辅助的作用,因而可以做到最低程度地规制竞技伤害行为。
3.2 我国竞技体育伤害行为规制的出路
3.2.1 竞技体育规则的完善及优先适用 没有规则,就没有竞技运动。游戏可以自订规则,非正规比赛可以让参与者协商酌定,半正规比赛可以对正规比赛规则进行修改,到了正规比赛以上层次,其规则就不再由参与者确定,而是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制定,并成为一种惯例,久而久之这种规则对于竞技者就成为一种“法律”。这也正是竞技体育规则的权威性所在,它是竞技运动这一行业里运动员必须遵守的“法律”。
对于违规行为的处罚规则是竞技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是身体接触多、对抗性强的比赛项目,罚则规定的就越详尽。西方体育哲学长期存在“游戏的连续统一体”理论,认为现代体育都是由play-game-sport不断演变的过程。所以,竞技体育是人们拟制的在规则下的自由竞争的虚拟世界,就自然成为人们的共识。竞技体育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今天的职业体育已不能与当初的竞技体育同日而语。但一百多年前诞生的竞技体育违规处罚的规则几乎没有改动过,对严重犯规的处罚基本上是被罚下场,失掉本场比赛资格,有些项目还会追加停赛一场。这样的处罚对集体项目而言尤其的不公平,即一方的损失与所得相比严重失衡,如一方非核心球员对另一方核心球员的恶意伤害,犯规方球员用被罚下场的代价换来球队整体的战略利益。再有规则对于伤害后果没有区别对待,伤害后果的有无和程度不会做为处罚的标准。
正是由于竞技规则处罚体系没有重视对严重违规者的处罚,更没有从预防的角度去制定违规处罚规则,才造成了今天这种竞技局面:当赛场上出现粗暴行为导致严重伤害的后果时,竞技规则没有相应的罚则对其进行严厉的处罚,人们就开始转而寻求最后的救济——法律[13]。行规不能排斥法律的呼声日益增高,在这种呼声下,刑法在竞技体育领域的适用有扩张的嫌疑,这是人们不愿看到的,更是竞技者不愿看到的。因此,竞技规则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竞技规则曾经有过几次小的改变。1994年,国际足联对《规则》的第八项进行了修改,即背后铲球判红牌。以前的规则没有禁止从身后铲球,从后方铲球如果没有铲到人,则不算犯规,但这种毫无准备的进攻,无论从身体上还是从心理上都给运动员造成很大的危害。规则的这一小小的改动就大大减少了曾经泛滥不绝的铲球给运动员造成的伤害。
对2008发生在北京奥运会上的摔牌事件的严厉处罚,足以说明国际奥委会IOC和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各国政府有能力对严重违规以及严重违反体育道德的行为进行有效的制裁。在2008年8月14日举行的北京奥运会男子84公斤级比赛中,阿布阿拉米安在半决赛中输给了后来夺冠的意大利选手安·明古齐。他认为裁判不公,抗议无效后大发雷霆。虽然他最终夺得铜牌,但在颁奖仪式上却走下领奖台,将奖牌扔在地上后拂袖而去。随后,国际摔跤联合会作出给予他禁赛两年的处罚。此前,国际奥委会纪律委员会已取消了阿布拉哈米安获得的奖牌。国际摔跤联合会称,阿布拉哈米安的行为是“不光彩的”“严重缺乏奥林匹克精神”。处罚的对象还包括他的教练员莱奥·米莱里以及瑞典摔跤协会。瑞典摔跤协会在未来两年内也被禁止组织任何国际赛事。此外,阿布拉哈米安、米莱里和瑞典摔跤协会还将分别被处以3 000、1万和5万瑞士法郎的罚款。
近年来国际奥委会IOC、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各国政府在抑制违规服用兴奋剂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强调各国政府干预和重罚的“世界反兴奋剂条例”,我国颁布的《反兴奋剂条例》及国家体育总局制定的《国家队运动员违规处罚办法》,都对违规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及相关人员做出了非常严厉的处罚规定,特别是国家队运动员,一经查出服用,将处以终身禁赛,这样的力度就足以告诫胆敢以身试法规则的运动员,将面临本行业最严厉的惩罚。笔者认为,正因为竞技体育行业有自身的特殊性,所以首先完善和使用本行业的规范来约束本行业的行为是最科学最有效的,理由如下:
(1)竞技规则是竞技运动员最直接的行为准则,规范、约束、制裁是应有内容;(2)竞技规则对竞技行为的规定是明确和具体的,哪些不可为、哪些可为,一目了然;(3)竞技规则能对大绝大多数违规行为进行处罚,通过处罚,能把容易转化成犯罪的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中;(4)竞技规则可以做出一段时间禁赛甚至终生禁赛的处罚,这样的处罚足以预防和警诫严重粗暴行为的发生;(5)竞技规则的效力在法律之下,规则处罚权的合法性在我国被认为是法律的授权,符合了规则的行为就符合了法律的要求,这是竞技运动员行为的潜在意识。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竞技伤害行为的抑制,应当通过完善竞技规则本身,加大处罚力度。为了有效的规制竞技伤害行为,国际奥委会IOC、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各国政府,应当相互配合,制定出严谨、严厉的重大违规处罚规则。(1)增加更详尽的禁赛处罚,要区别对待有无伤害后果的严重犯规;(2)增加违规处以罚款的处罚明细,根据不同程度和性质的违规,制定不同等级的罚款和禁赛。
有了这些严厉的处罚体制,运动员在竞技中自然会平衡违规行为所带来的利益与受到的处罚交换是否值得。因为竞技者参与竞技的目的无非有二,一是因为热爱,二是因为效益。对于热爱竞技的人来说,禁赛就是终止他的“生命”,这就是对他最重的惩处,这种惩罚的威慑力强于把他投进监狱。对于追求效益者来说,金钱是最直接的体现,因此巨额罚款可以让这类竞技者杜绝严重违规。
总之,由于竞技运动的特殊性,竞技规则非常重要,我们必须重视其合理性。为了使竞技运动更好地展现它的魅力,也为了使参与者的技能得到更好的展现,相关组织应该不断地完善竞技规则,从而最大限度地抑制竞技伤害行为。
3.2.2 刑法对竞技伤害行为的适度干预 使用刑法对竞技伤害行为进行规制应当谨慎。首先,我国目前的立法技术还没有发达到能准确识别竞技体育伤害行为中的犯罪行为,理论界对严重违规行为的正当性程度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超出竞技规则限度多少才构成犯罪更是个难题。其次,多数竞技伤害造成的是轻伤和中等程度的伤害,重伤害很少,竞技者主观上带有伤害故意的伤害更少,并且竞技者对于竞技规范的认识因素是主观的东西,很难用客观的标准来刻画、认定。竞技体育恶意伤害在刑法上的损害性因果关系与行为效果范畴均不明确。
对竞技伤害行为保留必要的刑法介入、规制是因为:(1)在竞技场上发生的伤害行为有些是在哨音终止后或比赛时间以外,对其适用刑法是可行的,在学界已形成共识;(2)对在比赛中发生的伤害行为即本文的“竞技伤害行为”,有些虽是处在比赛进行中,但行为的发生具有极其明显的伤人故意,如2006年的世界杯齐达内在比赛进行中用头故意撞击马特拉齐;泰森在一次职业比赛中用嘴咬霍利菲尔德的耳朵等。这类行为与一般的竞技行为就不具有模糊性;(3)随着今后比赛中多裁判执法和录像能作为辅助执法的依据,将会为准确识别运动员竞技行为的性质创造条件。
4 结 语
笔者所论述的完善竞技规则,加重规则对竞技伤害的处罚力度,以优先适用竞技规则来抑制竞技伤害行为的发生,不是试图以规则代替法律来规制犯罪行为,而是在目前实践中针对这一竞技伤害没有刑事立法规范,理论界也没有清晰界定出“意外竞技伤害”、“正当竞技伤害”和“恶意竞技伤害”的范围以及“恶意犯规”与“竞技伤害罪”的概念时,暂且成为对竞技伤害行为进行抑制的一种出路。
在如何有效规制竞技场上的这一小块圆圈内暴力的问题上,如果强调用刑法去抑制,可能会影响到单纯严重犯规造成伤害行为的定性错误,造成主观上没有故意伤害的运动员受到刑事制裁。所以在对待这一类竞技伤害行为时,一定要持非常谨慎的态度。正如本文前面所提到的,即使在那些已经规定了竞技体育恶意伤害罪的国家,其适用效果如何、人们对其信任与认可度有多高仍是有待研究的问题。刑法因为有其独立的法律目的,而且在各种社会规范中,刑罚属于最后的制裁方法,也许,我们都应该树立这样一种共识:一方面,竞技体育恶意伤害事件违背了一种精神利益和伦理道德价值,对其进行制裁当然具有社会利益属性。但是,刑法的存在并不是使竞技者不敢在竞技体育中进行恶意伤害的唯一原因。竞技体育的健康发展还将基于自身良好的规则引导,而不是坐等刑法来规制。另一方面,我们不应为了打击少数恶意竞技伤害行为而采取误伤大多数正常的竞技体育行为的方法,应当通过抑制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总量来降低恶意伤害事件的发生率。这样一来,既解决了竞技者现实的困惑,又实现了更为人性的法治理念。
[1]韩勇.体育法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9.435.
[2]于涛.体育哲学研究[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9.176-180.
[3]徐江.谭望嵩后悔自己主动申请红牌我把一切都弄砸 [EB/OL].http://2008.sohu.com/20080811/n258741214.shtml,2008-08-11.
[4]石泉.竞技体育刑法制约论[D].吉林:吉林大学,2004.144-154.
[5]杨武,易小坚,刘哲,等.竞技体育伤害行为之刑法分析[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5,(4):32-34.
[6]马克昌.犯罪通论[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821.
[7]李晓明.中国刑法学基本原理(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328-329.
[8]陈兴良.刑法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96.
[9]中国刑法词典编委会.中国刑法词典 [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233-234.
[10]罗嘉司.竞技体育犯罪研究——以犯罪学为视角[D].吉林:吉林大学,2006.81-82.
[11]楚晋.体育竞技伤害行为正当化的依据及限界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2007.35-36.
[12]娄看风.论对抗性体育运动伤害行为的法律责任 [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7,(4):428-430.
[13]贾文彤,杨银田,盖立忠.我国体育法学中的法治浪漫主义评析[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6,(3):32-35.
Regulations of Competitive Sports:The First Option to Regulate Competitive Injury and the Appropriate Intervention of Criminal Law
LIU Yanjun
(Dept.of PE,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401120,China)
In competitive sports,the major injuries occurred and how to regulate acts of athletic injuries caused by theoretical circle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and a lot of controversy.But the theory of multi-sector perspective on the inhibition of the Criminal Code for the competitive aspects of injury,while ignoring the special nature of sports injuries.Athletic convicted of criminal victimization,criminal law,laws and regulations that should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ystem,but because of the harmful actions of the legitimate existence of competitive athletics rules allow the former set of conditions,which makes athletic injury is different from ordinary acts of intentional harm to the subjective act of subjective malignant.Therefore,for the behavior of sports injuries,we should improve the rules of competitive sports punishment system,and give priority to the rules applicable to competitive sports,if necessary,to intervene only when accompanied by appropriate criminal law.
harm in competition sports;criminal law;rule of competition
G 80-05
A
1005-0000(2010)05-0434-04
2009-04-02;
2010-08-30;录用日期:2010-09-01
刘延军(1973-),男,山东淄博人,讲师,研究方向为体育法学、体育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