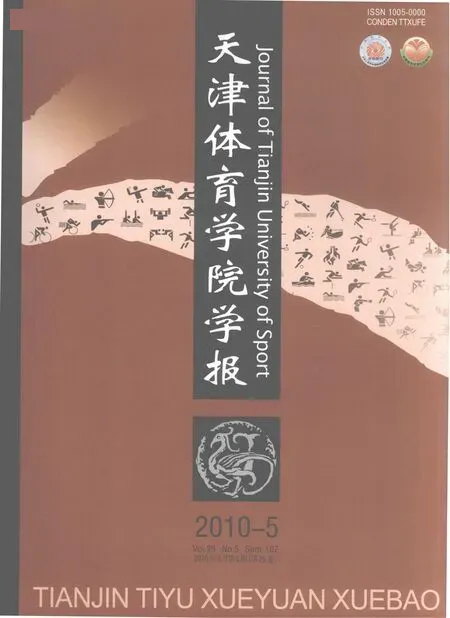博斯曼法案的国际政治经济本质
黄 璐
博斯曼法案的国际政治经济本质
黄 璐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博斯曼法案的社会影响,认识跨国资本主义全球文化殖民和政治经济秩序本质,加深对资本主义全球化与职业体育间关系与本质的理解。冷战时期,西方发达国家致力打造全球职业体育赛事运营平台,凭借先发工业化、城市化优势吸引世界精英运动员资源。冷战后,跨国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与文化殖民的欲望无限膨胀,亟待创造适宜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国际法律环境,夯实跨国资本主义利益最大化的合法化基础。博斯曼法案迅即出台,民族国家的体育法效力边界受到极大消解,为跨国资本主义争取实现全球体育人力资源最大化扫清了制度障碍。中国职业体育发展的轴心是如何争取自己的话语权,为世界职业体育经济发展的区域平衡与和谐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国际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全球化;博斯曼法案;职业体育;转会制度
博斯曼法案是国际体育法律纠纷的著名案例[1],历经十余载后,其社会影响方可辨认。在贵族们看来,它体现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意志与追求,为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提供了基础;在博斯曼们看来,它解开了逾百年的人力资源跨国流动枷锁,为人生事业发展送来了福音;在发展中国家看来,它背负骂名,为赤裸裸的掠夺行径实现合法化;在商业巨头看来,它建立了新的自由贸易市场,为“大鱼吃小鱼”市场法则提供了保障;在技术全球主义者看来,它再现了全球市场分工合作精神,为维护后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秩序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无论置于何种身份立场的考量,均颇为在理。事情有本末,矛盾有主次,必然存在影响全局的轴心。对博斯曼法案的进一步研究,将有利于加深对资本主义全球化与职业体育间关系与本质的理解。
1 前博斯曼时代的职业体育全球市场秩序
职业体育(Professional Sport)和精英体育(Elite Sport)是竞技体育的两个核心概念,源于不同的历史传统。职业体育源自现代游戏(Game)与休闲(Leisure)文化形态,是资本主义商业化进程的组成部分,而精英体育源自古希腊奥林匹克竞技文化形态,是现代身体文化的衍生物。二战结束,西方发达国家加快经济重建步伐,出台系列外交政策吸引跨国人力资源,职业体育的全球市场秩序传承自由放任(Laissez-faire)资本主义发展形态,即“弱肉强食”或“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市场规则,这使得打造全球职业体育赛事运营平台成为迫切的国家事件。赛事平台或者说世界金融文化中心的作用与魔力是巨大的,“20世纪前半叶,欧洲依然是西方的无可争议的中心。美国还依然只是一个在探求其自身认同性的华丽的外围。甚至极大多数的美裔作家如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和亨利·米勒都感到需要冲去巴黎以充分理解他们自己。[2]”卢梭亦狂放的指出,“如果你有一点天才的话,请到巴黎去住一年,你马上就能充分地发挥你的天才,否则你就会一事无成的。[3]”
西方发达国家选择足球、篮球、橄榄球、棒球、网球等广受民众青睐和商业前景广阔的运动项目,提升至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致力建构全球职业体育联赛品牌。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先发工业化、城市化优势吸引到更多的优秀运动员资源,致使后发工业化国家优秀运动员人才流失成为全球普遍现象。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培育出全球顶级职业体育赛事的文化氛围,竞技的卓越与荣耀化为全球共享记忆与神话想象,致使后发工业化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精英运动员心驰神往、心凝形释,深深向往这样一种乌托邦化的契约与承诺,一个实现人生价值、成就与梦想的地方[4]。
作者单位:河北理工大学体育部,河北唐山063009。
冷战时期,世界职业体育发展两极分化态势成为全球普遍发生的状况。以足球运动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乌拉圭逾400名球员在国外效力,分布在知名的南美洲联盟球队和较好的欧洲俱乐部球队,这些球员足以组建成世界前两名的顶尖球队,然而持续多年的精英球员流失,使乌拉圭民族不得不为取得世界杯晋级资格而挣扎[5]。阿根廷足球俱乐部面临相似的问题,不仅精英球员及有天赋的年轻球员大量移居欧洲,而且新秀球员亦将中等规模的欧洲足球俱乐部作为人生事业发展的跳板[6]。更有研究者认为,自19世纪末至今,苏格兰精英球员几乎是每个世界级足球俱乐部的核心队员,而在苏格兰本土俱乐部,即便是最强大的凯尔特人队,都缺乏足够酬金让天赋球员留下[7]。
应当认识到,后发工业化国家优秀运动员人才流失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现象,而是根植国际劳工移民的历史大背景。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重建进程对移民劳工的需求增加。以西德为例,二战后接纳了来自东德的1 200万难民,来自其他欧洲国家、亚非国家的“访客”工人也从50年代中期的1万人增加到70年代中期的230万人,他们对联邦共和国的“经济奇迹”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8]。
2 博斯曼法案与后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秩序
冷战结束,柏林墙倒塌,共产阵营全面解体,跨国资本主义全球化与后殖民进程稳步推进,西方发达国家致力推行新自由贸易主义(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变种形式及后现代发展)主导下的职业体育全球市场秩序,受到后发工业化国家或民族国家的联合抵制,面临建立后资本主义职业体育全球市场秩序的制度障碍,最典型的莫过于传统的运动员转会制度,这使得调整与修改“国际体育法”规则成为一件亟待攻克的战略性事件。援引“国际体育法”这一概念体系是为了更清晰的阐述观点,借此表示传统意义上的国际体育贸易契约,以及西方发达国家为颠覆传统契约体系发起的一系列法律公关行为。
19世纪中下叶,世界风行不加掩饰的掠夺、战争与殖民地文化,有观点认为一战是几个主要西方军事强国在殖民地利益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所致,二战后人类从梦魇中惊醒,了悟到悍然发动侵略战争意味着什么,尤其在冷战后世界多极化格局与全球核力量扩散的背景下,赤裸裸的跨国掠夺成为永远的历史。往昔那些双手沾满鲜血的野蛮人,改头换面、西装革履,变身为古灵精怪的生意人,他们强调公平与正义、和平与发展,满嘴喷出的是“人权”和“自由”。在这样一种价值紊乱、对错模糊的氛围里,矗立一批具有行业典范与强大震慑力的法案迫在眉睫。从博斯曼事件发生的时间来看,正值苏联分崩离析,资本阵营最强大的敌人垮塌了。跨国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与文化殖民的欲望无限膨胀且无人能挡,唯一缺乏的是创造适宜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国际法律环境,以夯实跨国资本主义利益最大化的合法化基础。博斯曼法案迅即出台,民族国家的体育法效力边界受到极大消解,为跨国资本主义争取实现全球体育人力资源最大化(运动员、教练员、科研人员等)扫清了制度障碍,后资本主义职业体育全球市场秩序基本形成。
后博斯曼时代,全球体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足球运动为例,全球精英球员聚集在14大商业巨头控股的18个世界顶级足球俱乐部中[5],包括意大利的国际米兰、尤文图斯、AC米兰足球俱乐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皇家马德里、巴伦西亚足球俱乐部,德国的拜仁慕尼黑、勒沃库森、多特蒙德足球俱乐部,荷兰的阿贾克斯、埃因霍恩足球俱乐部,英格兰的阿森纳、利物浦、曼联足球俱乐部,法国的里昂、马赛、巴黎圣日耳曼足球俱乐部,葡萄牙的波尔图足球俱乐部。形成了以意甲、德甲、英超、法甲、西甲等五大国家联赛品牌为中心的世界足球经济核心区域。在核心区外,一些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葡萄牙、荷兰、比利时、苏格兰等)利用核心区人才溢出资源建立了本土联赛,这些处于外核心区的联赛吸引了全球次精英球员及被核心区淘汰的精英球员,无奈面对收益欠佳的小型电视市场[5],虽然外核心区国家相继制定实施了一系列限制性政策,如“博斯曼事件”中利益受损方比利时足协,随后采取了放宽劳工移民政策、深化联赛体制改革等应对性措施,但却收效甚微。这种应对性的政策调整成为全球普遍现象,诸多国家紧随其后放宽了居民认证条件(尤其在职业体育方面),甚至越来越多的国家足球联赛不再限制球员国籍[9]。即便如此,仍无法扭转乾坤,两极分化现象日趋严重。最新有关博斯曼法案对职业足球运动员移民影响的研究显示[10],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精英球员从东欧、南美洲、非洲和亚洲迁移到西欧(世界足球五大联赛),强化这一现象的幕后推手来自欧洲法院于1995年12月审判生效的“博斯曼裁定”,令人吃惊的是,虽然制定出台了“本地球员”上场时间限制等相关政策,却并未有效遏制球员进口国与出口国间的竞争失衡。
在世界体育经济核心区与外核心区之外,更为糟糕的情形正在发生,仍以足球运动为例,东欧国家(俄罗斯、兰斯拉夫等)、拉丁美洲国家(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国家(巴拉圭、乌拉圭等)、非洲(南非、尼日利亚等)的精英球员大量流失,边缘区国家遂转向培养本土具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和征募下一层级国家的优秀球员,例如澳大利亚足球俱乐部广泛吸纳太平洋岛屿的优秀球员,南非足球俱乐部则启用本土新秀球员[5],以维持边缘区国家的联赛实力,由此形成国际体育劳工体系的科层化结构。在非洲国家,一些剥削年轻球员不正当利益的欧洲经纪人和俱乐部教练已被形象描述为当代奴隶贩卖贸易[5]。而像中国、印度、埃及、巴基斯坦等处于再边缘区国家的情形,甚至连表达自身苦难的基本话语权都没有。以此相比较,外核心区国家为争取权利的行动显得多么不合时宜。
在国际足球运动职业化之外,尚有世界四大网球公开赛等多国控制单项体育发展的赛事,亦有一国主导单项体育发展的赛事,如 NFL、MLB、NBA、NHL、北美四大拳击组织(WBC、WBA、IBF、WBO)的系列赛事等。这些主流项目赛事的全球中心地位由西方发达国家包揽,联赛体制健全,经济实力雄厚,是诸国精英运动员证明自己与梦寐以求的归属地,世界体育经济外核心区与边缘区国家很难与之竞争,其竞争结果是投入大量资金,费时费力,最终被边缘化,如日本的J联赛和NPB联盟等。诸多后发工业化国家看透其中端倪,纷纷在职业体育非主流项目上建构全球赛事品牌,学习西方发达国家职业体育发展模式,打造非主流项目运动员国际纵队,如韩国的电子竞技、日本的相扑、中国的乒乓球、中国香港的赛马等。这些非主流运动项目的全球受众影响力一般,即便成为该项目的“世界中心”(如中国乒超联赛),其赛事品牌也不会具有太大的国际影响。
毋庸讳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建立的主要制度)、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是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持建立的,即便当下这些组织在政策制定、处理国家事务、人员构成等方面越来越像国际舰队(倾向多国参与),但其主要权力仍控制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这些控制国际经济体系与国际法资源的西方发达国家精英,权衡利弊,审思再三,虽然考虑到博斯曼法案的预期结果将导致欧洲职业体育历时百年的转会制度的崩盘,以及由此引发的欧洲职业体育经济市场的动荡与不安,但却可以适时建立符合权力体意志的新的全球职业体育自由贸易市场,以零成本、零风险获取全球体育人力资源。为了切实保护、落实与最大化西方发达国家的根本利益,唯有二者选其一,留住西瓜扔掉芝麻,亦即保障美、英、德、法等大资本家的利益,放弃为葡萄牙、荷兰、比利时、瑞典等小资本家利益诉求的辩护。实质上,从欧盟竞争法适用性的角度判断,博斯曼事件原本可以有另一种裁定结果[11],如果裁定结果改变,所有依附在博斯曼法案上的一切秩序都将改变。很显然,造成当下世界职业体育马太效应状态的不是备受指责为草率裁定的博斯曼事件,而最终是由跨国资本主义全球殖民的本质决定的。
在一个满怀虔诚的人心中,法律代表尊严、正义与和平,但更多的时候,它只是强权、后殖民与紊乱的象征,无怪乎霍布豪斯畅言,“历史,甚至连古代史,都是根据编写者个人的某些假定,按照某些精神和倾向写成的。[12]”寻觅至此,不禁诘问,美国争当国际警察也便作罢,难道欧盟也要殖民世界?
3 博斯曼法案与中国面临的状况
在此补充中国案例分析,希冀从国际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重新理解博斯曼法案的中国意味。中国足球竞技水平亚洲三流,一般不会引起核心区、外核心区甚至边缘区国家足球俱乐部的兴趣,鲜见培养出的精英球员流失海外,譬如2009年初的周海滨转会埃因霍温事件,因中国足协常年坚守农耕时代陈旧生产模式,无视国际足球产业发展规律,联赛运作问题频出,恰巧遭遇博斯曼法案威慑,顿时惊慌失措,结果自然是奉承国际规则,无奈放人。不仅中国足球运动发展面临窘态,中国在所有主流职业化运动项目上,惟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在今后一段长时间内,难有较大改观。
早年的王治郅事件同样是博斯曼效应下的产物。在博斯曼法案推行的丛林法则中,“人权高于主权”,世界公民享有基本人权,跨国流动属个人意愿范畴,运动员进口国与出口国间不具有直接利益联系,博斯曼法案的出台有效规避了国家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而将冲突风险转嫁到运动员身上,使得运动员与运动员出口国间的利益矛盾逐渐升级,形成个人与国家权力间的博弈。像美国这类崇奉消费主义和文化时尚的后现代国家,个人挑战国家权力仅仅是利益权利问题,而像中国这类崇奉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的民族国家,个人挑战国家权力则偏向于道德权利问题,利益瓜葛被道德冲突深深掩埋,个人背负民族道义的谴责,如小山智丽(何智丽)、王治郅、郎平等人,他们被国家大批未开化的人民扣上了“吃里爬外”、“卖国贼”或“叛军者”的帽子。无论哪一方在这场利益博弈战中胜出,都将给运动员出口国带来经济损失与感情伤害,最终的幕后赢家是西方发达国家。
在一些深谙市场经济规则的明智人看来,凭借个人公关活动的开展,在个人与运动员出口国间可以寻求一种关系调解与和谐,在本土社会制造更有利于人生发展的舆论氛围,按照某种非正式的说法达成利益契约,这里的出口国并不一定代表国家立场,更多的是单项运动协会主导的部门利益使然。同样是运动员跨国流动,巴特尔、姚明、易建联等人的命运截然不同。这种跨国流动带来的影响与责任,原本应当由运动员进口国以经济支付的形式承担,而现在则全然倚靠运动员的公关技艺来获得实现。西方发达国家成功规避了发展的代价与风险,实现了矛盾与争议的乾坤大挪移。这种发展代价的转移并非新鲜事物,而是历史积弊的延续与重演(来自非洲的案例[13])。
从博斯曼事件的涵义及所产生的国际影响来看,中国职业体育的发展道路并非越来越顺畅,反而是越来越艰险,面临更大的危机与挑战。中国没有建立起具有国际影响的本土联赛,近年来引进轮流坐庄式的职业赛事,发展状况令人堪忧,譬如F1上海站、网球大师杯等。北京奥运会取得金牌霸主地位,号称世界竞技体育强国,是通过乒乓球、跳水、举重、体操等非主流项目的软金牌争夺实现的,这在严格意义上来说属于精英体育的范畴,并非西方发达国家竞争白炽化的职业体育形态。中国精英体育日益强大,职业体育始终低迷,似如病态的中超联赛。
美国职业体育的蓬勃发展,很大程度上来自美国强大的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以及二战后逐步建立的国际话语霸权,尤其在政府间国际组织(IGOs)和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s)的参与度和影响力方面。美国在国际组织的议程设置、政策制定和多方契约上施加影响,使局面向有利于美国的方面发展。欧盟也不甘示弱、分庭抗礼,积极参与利益分割行动,主动建立权力制衡机制,冀望建构自己的区域集团与国际影响。由此形成了体育纠纷解决的国家立场、区域集团立场和国际立场,如欧洲法院和国际体育仲裁院(CAS)分别服务于不同的权力体,在涉及利益分歧问题上,自然会出现不同的裁决结果。这些官方或非官方机构的法律效力,或者说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14-15],再次取决于不同的结盟国家权力体。中国职业体育发展的轴心是如何争取自己的话语权,消解既有政治经济秩序的垄断格局,为世界职业体育经济发展的区域平衡与和谐化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一争取过程是艰难漫长的,仅凭借国家或协会的努力不足以实现,建立区域共同体至关重要,譬如相对于CAS提出的亚洲体育仲裁院(隶属亚洲国家奥委会或亚洲国家体育委员会)、泛亚洲体育仲裁院、东亚体育仲裁院等可能的概念。
一些学者认为博斯曼法案引起了世界职业体育的秩序紊乱,很快将走到历史的尽头。这种植根弱者立场的主观意愿,只能成为空中楼阁。不深入认识跨国资本主义全球文化殖民和政治经济秩序本质,平衡与消解世界职业体育经济秩序,博斯曼法案将永远屹立。
[1]郭树理,肖伟志.体育纠纷的法律解决——国际体育界若干著名案例探讨[J].体育文化导刊,2003,(7):52-55.
[2]阿方索·贝拉尔迪奈利.从后现代主义到变异时代:20世纪如何临近结束[J].姚介厚,译.第欧根尼,2002,(2):33-50.
[3]卢梭.爱弥尔——论教育[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504.
[4]郑志强.职业体育市场交易制度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0,(1):40-42.
[5]Richard Giulianotti.Playingan Aerial Game:The NewPolitical Economyof Soccer[A].John Nauright,Schimmel Kimberly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port[C].New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26-27,35,28-29,28-29,32-33.
[6]Andersson T,Radmann A.Post-modern Times:Identities and Violence in Argentine Football[A].Gary Armstrong,Richard Giulianotti.Football,Cultures and Identities[C].NewYork:Palgrave Macmillan,1999.77-85.
[7]Ronald Kowalski.‘Cryfor Us,Argentina’:Sport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late twentieth-century Scotland [A].Adrian Smith,Dilwyn Porter.Sport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Post-War World[C].London&NewYork:Routledge,2004.74.
[8]弗雷德里克·皮尔逊,西蒙·巴亚斯里安.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体系中的冲突与合作[M].杨毅,钟飞腾,苗苗,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68.
[9]Michael Holmes,David Storey.Who are the boys in green?Irish identity and soccer in the Republic of Ireland [A].Adrian Smith,Dilwyn Porter.Sport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Post-War World[C].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4.91.
[10]Bernd Frick.Globalization and factor mobility:The impact of the"Bosman-Ruling"on player migration in professional soccer[J].Journal of Sports Economics,2009,10(1):88-106.
[11]刘进.关于欧盟足球运动员转会费规则的竞争法思考[J].体育学刊,2008,15(2):24-27.
[12]L T霍布豪斯.行而上学的国家论[M].汪淑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7.
[13]Robert Simmons.Implications of the Bosman ruling for football transfer markets[J].Economic Affairs,1997,17(3):13-18.
[14]黄世席.奥运会争议仲裁[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82-86.
[15]张宾.对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问题的思考 [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7,30(4):458-460.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 Nature of Bosman Bill
HUANG Lu
(Dept.of PE,Hebei Polytechnic University,Tangshan 063009,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the social impact of Bosman Bill was examined.We can know the natures of the global cultural colonization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and political economy orders and strength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and the essence between capitalism globalization and professional sports.During the Cold War,developed countries in Western devot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operational platform for global professional sports,and to absorb the elite athlete resources by the advantages of initiative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After the Cold War,the unlimited growths of global expansion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and the desire of cultural colonialism were yearning to create an international law environment,which was proper for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of capitalism,to pave legitimate grounds to maximize the benefits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The Bosman Bill came out at once.The law validity boundary of the national sports law dissolved extremely,cleaning up the systematic obstacles to realize the maximizing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esources for sports.The development core for China’s professional sports is how to struggle for its own voice and how to contribute itself to the regional balance and harmonization for the world professional sports economy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conomy;Capitalism Globalization;Bosman Bill;professional sports;transfer system
G 80-05
A
1005-0000(2010)05-0392-04
2010-04-16;
2010-08-10;录用日期:2010-08-2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9BTY039)
黄 璐(1981-),男,江西宜春人,讲师,研究方向为体育人类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