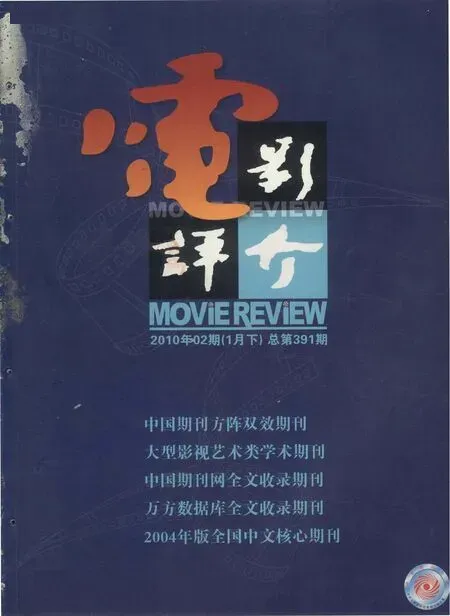牢房中的性别困境——《 蜘蛛女之吻》 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研究
1976年出版的西班牙文小说《蜘蛛女之吻》[1](原名El beso de la mujer arana,英译Kiss of the Spider Woman)是阿根廷作家曼努埃尔•普伊格(Manuel Puig)的第四部作品。这部对话体小说手法新颖,它标志着普伊格“新叙事”技巧的成熟。《蜘蛛女之吻》于1979年被翻译成英文,陆续在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版,但是此小说真正引起关注还是在其电影版上映后。电影《蜘蛛女之吻》(Kiss of the spider woman,1985)是阿根廷裔巴西籍的导演赫克托•巴本科(Hector Babenco)进军美国影坛的第一部英语电影,这部作品在法国戛纳电影节上放映后好评不断,并且在同年的金球奖和奥斯卡上获得多项提名,饰演莫利纳一角的威廉•赫特(William Hurt)更是获得当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1946年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赫克托•巴本科是后“巴西新电影”(post-Cinema Novo)[2]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在其30多年的导演生涯里一直着力于探讨社会文化当中的各种冲突和矛盾,从1981年的成名作《街童》(原名Pixote-A lei do mais fraco,英译Pixote-The Survival of the Weakest)开始,政治、性和权力一直是其作品的核心主题。其中《街童》、《蜘蛛女之吻》和2003年的《卡兰迪鲁》(另有译名《监狱淌血》,原名Carandiru)被视为最有“巴本科风格”的监狱三步曲。《蜘蛛女之吻》在国际上的成功是巴本科导演生涯的一大转折,此后他大部分作品都主要面向英语系观众,着力去挖掘跨文化影像表达的多种可能性。
《蜘蛛女之吻》的电影版改编一直被认为是成功的,因为这部号称为美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独立制作的电影将一切敏感话题处理得合情合理,具有一种微妙的情感张力。《蜘蛛女之吻》小说的叙事主题有性与权力、女性意识、政治运动等,而1985年的电影版试图再现小说内蕴,并做了一定程度的改编。目前的研究聚焦于小说和电影的文化研究和批判。而笔者则是回到电影本身,以电影为主要研究对象,认为电影版在改编之后,实际上加重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力度。本文拟对影片中戏中戏和戏外戏两条叙事主线进行分析,结合具体的场景说明导演是如何运用各种影像符码,强调和深化了原作对主流浪漫爱情剧的批判态度,从而证明电影版比小说更深入地突出了传统性别机制以及异性恋霸权的吃人现象。
一、戏中戏的女性
小说是从3个层面上进行叙事的,一是角色所处的现实世界,二是莫利纳所讲述的电影世界,三是角色的精神世界(心理活动)。三条线索互相交叉作用,打破了有限的时间和空间,营造出一个封闭却又开放的微观世界。莫利纳这个生理上的男性为了打发在牢房里的时间,主动要求向同样为男性的瓦伦丁讲述他钟情的情节剧。尽管身为激进革命分子的瓦伦丁很不屑于那种“低俗无聊”的电影,但是他并没有阻止莫利纳。小说中莫利纳一共讲述了6部电影,电影版只保留了纳粹宣传片《命运》,却把原著中蜘蛛女意象扩充为另一部戏中戏的女主角。通过对戏中戏的改编,女性变得更为可悲无助,她们的立场也更加微妙尴尬。
首先我们看到了这部影片对情节剧女主角的改造。小说通过莫利纳之口,将《命运》的女主角雷妮描绘成一个柔弱高贵的女神。“每当我回忆起她唱的那首歌,心里就感到恐惧,因为她唱歌时,目光空虚缥缈,没有露出幸福的眼神。你别以为她很幸福,不,她露出惊恐的神情;同时,又显得无力自卫,屈从于命运的样子。”[3]“她既像一位女神,同时,又是一个感情脆弱的女人……”[4]。雷妮个性中的敏感、脆弱和不安因素注定其在与男性的关系中只能处于被动、压制的位置,俨然一个理想的男性情欲对象。可是电影版却把这个被莫利纳称赞被“世界上最迷人的女人”,塑造成一个具有双性气质的中性化女星。
普伊格在接受采访时曾表明,雷妮的原型是三四十年代风魔全欧洲和好莱坞的瑞典女歌手札瑞•朗德尔(Zarah Leander),《命运》的构思主要来自札瑞1942年参演的第三帝国宣传片《伟大的爱》(Die grosse Liebe,英译the Great Love)[5]。但是由于文字的间接性和不可看性,读者无法从文字片段中组合出札瑞的形象,结果小说中的雷妮只是简单复制了传统浪漫爱情节剧女主角的形象。可是电影版就充分利用视觉音效地再现了雷妮与札瑞的神似。札瑞的银幕形象一向冷艳高傲、独立自信[6],她那沙哑低沉的歌声使得她散发出一种中性美。长久以来她都是众多同性恋者与跨性别者的模仿对象,尤其受到非异性恋男性的欢迎。美国学者Alice A Kuzniar说这位女歌手之所以能成为广大非异性恋者的偶像,是因为她整个形象就是一道跨性别的奇观:“这道跨越社会性别的奇观带来了某种脱离异性恋秩序的解放:一个拒绝与这女性外表和感受产生共鸣的男人,一个拒绝发出男性声音的女人,这使得她的表演就像一个男人在向另一个男人唱情歌。假如你对呆板的异性恋霸权感到不满,你就会对她男性化的音色以及她在情节剧里矛盾过度的表演这两者的对比产生认同感。”[7]电影版中饰演雷妮一角为巴西著名女演员索尼娅•布拉加(Sonia Braga),她在里面的表演经过了普伊格本人的指导,刻意模仿了那位中性歌女:同样低沉沙哑的音色、僵硬呆板的脸部表情、夸张变形的肢体动作。这样变相的易装和非写实表演似乎可看作是一种对主流电影叙事机制的嘲弄和颠覆。因为索尼娅的表演留下了十分明显的做作痕迹,观众与戏中戏的距离顿时被拉开了,以致观众难以产生认同感和代入感。一旦保持了距离,观众有可能理性清醒地观察戏外戏的莫利纳,这为后来对他愈发主观化浪漫化的复述定下了批判的基调。
另一部点题的戏中戏——《蜘蛛女之吻》中蜘蛛女的形象则是完全属于电影原创。在小说里,蜘蛛女意象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在莫利纳与瓦伦丁的对话中,另一次则是在瓦伦丁的梦境里。两人面临分离时,莫利纳希望瓦伦丁能跟他接一次吻。莫利纳问瓦伦丁是不是对与他接吻感到恶心,瓦伦丁回答道:“嗯……也许是怕你也变成一只金钱豹,就像你给我讲的第一部电影中的那个女人那样。”[8]莫利纳说自己并不是金钱豹女人,然后瓦伦丁就说莫利纳是蜘蛛女人,“用自己的网擒获男人”[9]。而在小说结尾处,瓦伦丁梦见自己与一个女人做爱后看了一部小电影,电影的主角正是一个身上长出蜘蛛网的女人。蜘蛛女作为坐以待毙、悲惨孤单的金钱豹女人的对立面,象征着一种女性捕猎者主动,男性猎物被动的两性关系,而且,谜一样的蜘蛛女意含了不可捉摸的女性奥秘。她的一切行为缺乏前因后果,迷离的表象阻碍了他者对其内心的深入。而电影版里,蜘蛛女故事的讲述者却成了莫利纳,戏中戏糅合了小说中瓦伦丁的梦境。蜘蛛女身上的主动性被抹去,作网自困的她只能如深闺怨妇般,在无人的热带小岛上等待猎物的到来。
二、戏外戏的跨性别者
一般评论[10]都把莫利纳与瓦伦丁看作是多组二元对立的身份集合:同性恋与异性恋、反革命与革命分子、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情感与理性、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两人在一个封闭的空间(牢房)通过电影相互交流理解,打破现存的界限,最后完成了一次身份转换:一开始对政治运动毫不关心的莫利纳成了革命烈士,原先排斥主流电影的瓦伦丁则对它们入了迷。普伊格的小说打乱了传统的叙事期待,解构了被普遍接受的文化二分法,模糊并融合了这些极端的划分,目的是要引发读者对既定的身份类别的再思考,使得他们重新审视看似顺理成章的社会性别划分。
而且,假如简单地把莫利纳定义为一同性恋者,实属不妥。他只是一个被刚硬的男性外表伪装起来的柔弱女性,是一个典型的跨性别者而非同性恋。所谓跨性别,最通俗的解释是在出生时根据其性器官而被定义为某个性别,但是却感觉那个性别对他们是一种错误或者不完整的描述的人。显而易见,莫利纳对自己的性别很不满意。他向往柔弱的女性气质,他自我认同为该受男人控制和保护的弱女子,他幻想能以女人的身份嫁给一个异性恋男人。一个“渴望找到一个真男人来当我的上司”的男性,恰好是女性电影最理想的观众。普伊格本人曾经说过《蜘蛛女之吻》并不是一个同性恋爱故事,之所以要安排一个女子气的男性为主角,是因为生理性别为男性的莫利纳永远都无法体验真实的女性生活,因此情节剧所带来的幻想永远都不会被摧毁[11]。由于生理与心理的悖离,以及主流社会的驱逐,莫利纳在这种女性电影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源源不断的快感支撑了其空虚的人生,因此他就可以把成为柔弱女性的幻想一直延续下去。在建构莫利纳这角色时,电影版表现出了与小说最明显的不同。影片利用戏外戏加重了莫利纳对浪漫情节剧的痴迷与再创造,从而突出了莫利纳与异性恋霸权的矛盾关系。
电影版里莫利纳的“入戏”程度是小说所不能比及的。小说依靠言语的破绽以及逻辑上的自相矛盾,暴露了莫利纳自动将电影浪漫化的毛病。两人讨论《金钱豹女人》时,瓦伦丁认为这个故事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处处表现了男人的处女情结,女主角伊雷娜的神经和癫狂正是女性欲望被压抑的结果。瓦伦丁一针见血地指出隐藏于凄美爱情故事背后的男性霸权,随后嘲笑了愚昧无知的莫利纳。莫利纳却反驳道:“这一切全都是你想像出来的。”他亡羊补牢般的辩解顿时被瓦伦丁识破,他最终承认他确实重新剪辑和修饰了这些电影。“有些事情,为了让你了解

电影版一开始就把莫利纳的形象定型为一个极端狂热的情节剧爱好者,他总是一边讲述一边配予相关动作,整个人都陷入了表演的状态中。影片通过画面动作和声音的对称,利用镜头间的连续性强调和突出了莫利纳内心对成为凝视焦点的渴望。莫利纳不只是从语言上再现他所看过的电影,并且配上解说动作,身心投入至这样的幻想中。玛丽•安•多恩说道,在当代电影理论里,观众的欲望通常被描述为窥淫癖或恋物癖,它就是男人在观看那些被禁看的女性身体时所获得的快感。但是获得这样快感的前提是,窥淫者必须要与自己的欲望对象保持距离,否则就会失去欲望的形象。因此女性观众是无法在电影中找到一种主体位置,因为她本身就是欲望的客体,“在观看与理解之间缺少距离,是‘迅速而直接’判断的模式,它促成了与形象的所谓‘过分认同’”[13]。很明显,莫利纳的入戏不是因为他对女性身体的窥淫欲,而是因为他强烈的代入感。他不是要去窥视,他是渴望被窥视。因此,复述电影对他来说不只是娱乐消遣,而是自我催眠和自我建构的最重要手段。
电影版的纳粹戏中戏是从莫利纳的视角展开的,可是最终呈现出来的影像,却又与现实存在的经典情节剧有所不同。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雷妮的形象具有了跨性别的特征,打破了传统的二元建构论。莫利纳对雷妮的强烈认同感和对其形象的改造,都向观众传达了一种明确的暗示:雷妮实际上是莫利纳内心欲望具象化的结果,“她”是莫利纳这个“男人”的一部分。原本服务于异性恋霸权的情节剧被跨性别者改造为表达欲望的工具,莫利纳对主流文化的戏仿和颠覆力度通过此方式得以加重。
三、高潮过后的死亡
在完成了对戏中戏与戏外戏的改写后,电影版要完成的最后一步就是在宏观上完成两者内在对应关系的再创造,从而突出主线,揭露以男权为中心的异性恋霸权吃人的现象。电影版的戏外戏实质上是戏中戏的再现,是现实生活与虚幻世界的高度重合。两者的重叠关系在结局处达到颠峰。
上文已经论述了莫利纳对于雷妮有着过剩的认同感和代入感,因此他后来从反对革命到为革命献身,是出于对瓦伦丁的爱还是出于自身的政治觉悟,值得一再探讨。普伊格自己的解答是,一方面他是受到感情的驱使,一方面他是受到意识形态的控制。而电影版却倾向于呈现后者,莫利纳最大的动机是通过冒险成就自己浪漫爱女主角的地位。
最后在1小时48分11秒到36秒,莫利纳站在房间的镜子前,摄影机对着镜子,莫利纳的镜像反射到镜头前。这个中景镜头将莫利纳和他身后墙上女星的海报清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就在女星的凝视下,莫利纳戴上了殷红的颈巾,特殊的透视角度使得莫利纳的目光既像投向自己,又像看着身后的海报。通过这个双重的凝视,莫利纳与浪漫爱女主角完全重合了。电影版多处展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如何利用各种具有暗示性的道具(电影、镜子、照片)撒开自己的权力网,让观众心甘情愿地响应它的召唤。在这个异性恋霸权的管控下,被认为“不正常”、“不合理”的莫利纳无法在真实世界中找到表达欲望的途径,他只能借助电影的幻想自我麻醉和催眠。到最后,当现实与幻想开始重叠时,电影暗示了莫利纳表达欲望的唯一途径就是把生活变成大众化的幻想。
莫利纳从被跟踪到被枪杀,电影里所有街景都是不清晰的,那些街道的名称和方位均不可辨别。有观点认为,导演这样做是在误导观众,容易让他们以为拉美所有国家城市都一样(这场戏是在巴西街头进行拍摄的,而原著的地点应该是在阿根廷首都),这样的话不就跟莫利纳所做的一样把电影主观化浪漫化了吗[14]?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样的艺术呈现却又恰恰与主题相一致,现实与幻想的界线已经模糊,在莫利纳眼中两者已无从区分。电影版一直刻意划分戏中戏与戏外戏,使用不同的色彩来再现现实与虚幻。但是到了结局处,原先采用单一色调的戏中戏变成了彩色,现实与幻想的界限不再清晰。
小结
综上所述,电影版并不是对原著的简单重复,而是通过对角色、场景和情节的改编加重了原著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有效地利用各种场景调度完成了从小说到电影的转换。电影版的成功在于,导演利用各种视觉符码再现了跨性别者对于传统性性别机制的戏仿和颠覆,也突出描写了他们的困境——在内心欲望在无法得到合理表达的情况下,他们把情节剧当成了唯一的精神避难地。在莫利纳的幻想中女性被赋予了一种雌雄同体的形象,但是始终未能摆脱被欲望客体化的命运。莫利纳将浪漫爱情节剧进行再创作,试图以此来逃离主流文化对自己的压迫。但是本质为男权社会和异性恋霸权所服务的主流情节剧却又无法为其指明出路,最终莫利纳只能以极端的方式来满足自身的欲望。女性和跨性别者的困境在电影版被表露无遗,社会制度给予她们的只有虚伪的快感和无意义的死亡。
[1]国内现存最早的中文版本是由屠孟超译,林一安主编,中国工人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本文所采用的版本是中国加入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公约后重译的版本,译者同样为屠孟超,译林出版社,2004年。参考的英文版本为1991年由London:Vintage出版的译本,译者为Thomas Colchie。
[2]Cinema Novo在国内亦被翻译为巴西新浪潮电影,指的是1962年兴起的巴西新电影运动。标志性事件是1962年导演安塞尔莫•杜阿特(Anselmo Duarte)凭着影片《承诺》(原名Pagador de Promessas,英译The Promise)在法国嘎纳电影节上获奖,这使得巴西电影第一次受到国际影坛的普遍关注。更多相关内容可参见George Csicsery and Hector Babenco, Individual Solution: A Interview with Hector Babenco, Film Quarterly,Vol.36, No.1(Autumn,1982),pp.2-15
[3][阿根廷]普伊格著,屠孟超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52页。
[4][阿根廷]普伊格著,屠孟超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55页。
[5]Ronald Christ, A Last Interview with Manuel Puig, World Literature Today, Vol. 65,1991.
[6]关于她的生平和评论,详见h t t p://en.wikipedia.org/wiki/Zarah_Leander
[7]Alice A Kuzniar, Zarah Leander and Transgender Specularity, Film Criticism, Wntr-Spring, 1999
[8][阿根廷]普伊格著,屠孟超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250页
[9]同上
[10]关于此类观点和评论,可参阅Steffany Drozdo:The Deconstruction of Binary Ideological Structures in Manuel Puig’s Kiss of the Spider Woman,International Fiction Review,vol.26,1999
[11]Ronald Christ, A Last Interview with Manuel Puig, World Literature Today, Vol. 65,1991
[12][阿根廷]普伊格著,屠孟超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9页
[13][美]佩吉•麦克拉肯主编,艾晓明、柯倩婷副主编,《女权主义理论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329页
[14]Bruce Williams, I Lost It at the Movies:Parodic Spectatorship in Hector Babenco’s Kiss of the Spider Woman, Cinémas, vol.10 n1,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