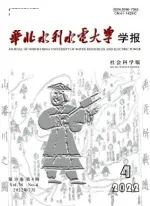论河南籍作家对中原特色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周引莉
(商丘师范学院,河南商丘476000)
论河南籍作家对中原特色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周引莉
(商丘师范学院,河南商丘476000)
河南籍作家在创作时或借鉴中原曲艺文化,或表现中原神秘文化,或体现中原民间道德,或展现中原农民顽强的生命力,或反映官本位等权力政治思想对人的影响和戕害,以及对中原民俗文化、中原诙谐文化等的借鉴与表现,不仅丰富了小说内容,而且提高了文学的品味、认知价值和文化审美价值,也体现了他们对中原特色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河南籍作家;中原特色传统文化;继承;发展
中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历史上,地处中原的河南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有“逐鹿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当代河南籍作家和最具中国原型意味的“中原传统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从他们的创作实例中得到验证。笔者主要以周大新、阎连科、李佩甫、刘庆邦、刘震云、张宇、李洱等人的小说创作为例,来谈谈河南籍作家对中原特色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河南籍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对中原特色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中原曲艺文化的借鉴
河南籍作家在创作时不时借鉴中原曲艺文化丰富小说内容,起到或营造氛围、环境,或塑造人物,或点缀情节的作用。
刘庆邦的小说基本上分两类:柔美小说(如《鞋》、《梅妞放羊》等)与酷烈小说(如《走窑汉》等)。但短篇《曲胡》可以说两类兼具,让人不忍细读。因为一开篇除去两自然段对曲胡的常识性介绍外,就马上进入一种凄惨的基调。瞎祥天生瞎子,练得一手曲胡,后父母早逝,哥哥抛妻弃子,在城里又婚。于是,瞎祥与嫂子、侄子相依为命。作者把瞎祥辛酸的身世与凄凉的琴声融为一体,让人读了立马产生一种冷嗖嗖的宿命感,还有一种不忍面对和细究的心痛感。等待看完,才明白这又是一个乱伦的悲剧,而且是一个凄美的悲剧。其实这个悲剧在某些情况下完全可以避免而以喜剧结束,但男女主人公都太闭塞执拗了。究竟这一切是谁之罪?民间这样的悲剧还有多少?还会持续下去吗?这样的疑问暂且放下,先看一下作者的技巧。《曲胡》非常精工细致,在几千字的短篇中,塑造了五个鲜明的人物,讲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故事,营造了或凄美哀伤或柔美舒畅或惊涛骇浪的氛围。小说把人的情绪与曲胡的音调结合起来主要有三次:写到瞎祥及嫂子的身世时,曲胡的调子是“悠悠扬扬”、“如泣如诉”;写到瞎祥沉醉于和嫂子的爱情时,曲胡奏出的音乐是“舒舒徐徐,送柔抽丝”;写到叔嫂约会前的音乐基调是“先疏后密,由缓到急,急到一个高峰,又跌下来,趋于平缓,而后归于寂静”。三次写曲胡的调子都与人物的心理情绪融为一体,写乐即是写人,人物形象因乐曲而更加丰满生动。
李佩甫的《羊的门》中有两段民族乐曲与按摩手法相结合的描述,非常精彩。县长呼国庆带着满脑子烦恼被“大师”按摩时的感觉,从半睡半醒,欲醉欲仙,到彻底放松,都是与音乐同步进行,水乳交融。《二泉映月》的如泣如诉,《百鸟朝凤》的欢快明媚,都随着“大师”轻重快慢的按摩手法揉进呼国庆的大脑和感觉。
张宇的《乡村情感》中三次引用了爹和麦生伯爱唱的民间小调:“和成的面像石头蛋,放在面板上按几按,擀杖擀成一大片,用刀一切切成线,下到锅里团团转,舀到碗里是莲花瓣,生葱,烂蒜,姜末,胡椒面,再放几撮芝麻盐儿,这就是咱山里人的面条饭。”这首民间小调从表面上看是体现了农民对家乡面食的喜爱,但从作者三次引用的目的看,则大有深意。第一次引用是爹拉弦麦生伯唱,体现俩老朋友不慕官位富贵,回乡种田的深情与默契。第二次引用是在麦生伯病危的窗前,爹自拉自唱,目的是让麦生伯听着舒心,死也落个快乐死。体现了俩老友的心心相印和深情厚谊,有点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意思。第三次引用是“我”在城里新春联欢晚会上,本来是出于恶作剧般的目的,通过吼叫父辈喜爱的“面条饭”,向城里人示威,但“我”博来的不是嘲笑,而是疯狂的掌声。于是,“这掌声让我极不平静。”“我”领悟到这里面有一种沟通,不是城乡差距与界限,而是“乡村情感是城市感情的源头”。
二、对中原神秘文化的表现
阎连科的乡村小说大多以豫西河洛地区耙耧山脉的山村生活为背景。河洛地域文化是中原文化和地方山区的混合杂糅,所以,这里的民间生活既有中原文化的传统伦理,又保持着比较原始的带有神秘色彩的生存风貌。在《耙耧天歌》中,尤四婆独立支撑一家人的生活,为先天痴呆的四个儿女四处奔波。为了治好儿女们的痴呆,她用死去丈夫的尸骨甚至最后用自己的尸骨去医治儿女们的病。而尤四婆临死前,给她的四个儿女留了一句话:“这疯病遗传。你们都知道将来咋治你们孩娃的疯病吧?”这句话含义丰富:子女的疾病甚至过错其实都是父母给的,父母对治愈自己孩子的疾病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搭上性命也不为过。这其实也是一种弱小本位思想,与鲁迅先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提倡的现代思想其实是一致的。这让人联想到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不健全儿童被遗弃的事。孩子的不健全都是父母给的,而有些父母却把自己身上的责任一推了之。这样的父母和尤四婆相比是不是缺少起码的家庭道德伦理意识?尽管尤四婆的故事不无夸张、神秘的色彩,但中原传统道德伦理文化在民间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李佩甫的《黑蜻蜓》中写在姥姥的丧礼上,二姐被老祖爷的魂灵扑到身上,像“先人”一样用老人庄严、肃穆的口气,“缓缓诉说久远的过去,诉说岁月的艰辛……那话语仿佛来自沉沉的大地,幽远而凝重,神秘而古老,一下子摄住了所有人的魂魄,没有人敢去惊动二姐”。这种神灵附体的现象在很多文艺作品中出现,尤其在影视作品中,基本上都冠以封建迷信的色彩,但在《黑蜻蜓》中,作者进行了两面分析。李佩甫的分析没有简单化地归结为封建迷信,而是站在科学的角度上,表达了对未知世界的想象性猜测。这样的猜测其实比武断的结论更有说服力,也更能启发读者的思考。
三、作为双刃剑的民间道德
进入新时期,在经济改革大潮的影响下,民间道德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如果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民间道德是精华与糟粕同在。民间道德在周大新小说中是一把双刃剑,周大新对民间道德的评价常采取不置可否的矛盾态度。周大新的《武家祠堂》中描写了商品意识与民间道德的冲突。尚智因为技术革新而使服装成本降低,他决定薄利多销,但这样一来影响了同样在镇上做服装的烈士遗孀常二嫂的生意。同情弱小的民间道德发挥了作用,镇上人们的义愤逼迫尚智只好远走他乡。这种“同情弱小”的善良之举和民间道德观念固然是一种传统美德,但它与公平竞争的现代意识产生了矛盾,因此也限制了正常的经济行为,压制了新生事物的生长。另一方面,村民们同情弱小的背面,是否有“红眼病”在作怪呢?可见,平均主义、宗族意识常常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这种落后意识在改革初期骚动的村镇较为明显。
周大新的《第二十幕》是一部史诗性的长篇小说,是作者用近10年时间构思写出的一部长篇小说,被誉为“中国的《百年孤独》”。《第二十幕》中尚达志为继承祖辈遗志,保存家族的实业,不得不牺牲爱情,后来甚至于卖掉自己的亲生女儿。如果从理想的角度看,尚达志是一个坚强地执着于家族理想的、精神力量十分强大的人,家族利益大于一切的民间道德似乎高于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但民间道德对个性、情感的否定和践踏,甚至对生命的轻视,也是其显见的局限。
四、对中原农民顽强生命力的表现
阎连科的绝大部分作品都以农村为背景。无论是《坚硬如水》、《受活》,还是《耙耧天歌》、《年月日》,阎连科都呈现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把生活中的事件放大到极致甚至怪异的程度,好像放在显微镜下观察。于是,一些有声有色的语言,甚至惊心动魄的场面都被鲜明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李洱说过:“阎连科是在酷烈的耙褛山区成长为庞然大物的。”“‘耙楼山区’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地形图上最奇异最复杂的景点。”[1]这条山脉借助阎连科对苦难的讲述而获得了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如《年月日》写大旱那年,耙楼山脉方圆百里的村民都逃离了家园,只有七十二岁的先爷和他的一条盲狗留下。老人不走固然有年老力衰、不愿离开家园的原因,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株冒了芽的玉蜀黍给老人带来了希望。于是,他的生存便有了意义,他要为村人留下来年秋种的种子。经历了种种磨难,先爷终于盼到了秋熟,但关键时期,玉蜀黍缺少肥料。先爷穷尽一切办法,最后不惜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那棵玉蜀黍作肥料。在这看似不可思议的举动中,蕴含了先爷顽强的生命意识和坚忍不拔的生命意志力。正是这种坚忍不拔的意志力才使人类一步步发展壮大,这也是人类本质中最原始、最可贵的精神。
五、对中原官本位等权力政治思想的揭示
官本位等权力政治思想是长期封建统治所积淀的民族文化心理。在封建社会,人们敬祖、畏官、媚权,同时又希望做官。如果说“学而优则仕”还是一种积极向上的追求,那么官本位则成为一种不健康的权力政治思想。而这种思想在中原文化中极为突出和普遍。从刘震云的《塔铺》,到周大新的《向上的台阶》、李佩甫的《羊的门》,再到阎连科的《受活》,无不显示了官本位思想对人的戕害。
李佩甫的《羊的门》从乡村到县城,都对权力系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呼家堡堡主呼天成对“人场”的经营,要利用的是权力;呼国庆挖空心思登上县长、县委书记的职位,谋求的也是权力;王华欣、范骡子等人争夺的也是权力……他们都想建立一个属于自己势力范围的“权力圈”,而一般的民众也乐意往这个圈子里钻,以谋求个人的利益。谢丽娟曾指责呼国庆:“在这块土地上,到处生长着这样(玩弄权术)的男人,为了权力你们什么都可以牺牲。”呼国庆的辩解是:“至于权力,那是每一个地方的男人都向往的。权力是一种成功的体现。不错,在这里,生命辐射力的大小是靠权力来界定的。这对于男人来说,尤其如此。这里人不活钱,或者说不仅仅活钱,这里生长着一种念想,或者说是精神。”而这种“念想”或“精神”恰恰是追求权力、名誉的官本位思想。官本位思想不仅成为具有权力野心的人的信仰,也对普通民众产生了蒙蔽、腐蚀和戕害的作用。徐三妮在呼天成临终时,跪在地上,泪流满面地说:“呼伯想听到狗叫,我就给他老人家学狗叫。”而此时的呼家堡人也忧心忡忡:“如果呼天成有个三长两短,我们怎么活呢?”这些人都变成了被权威奴役和驯化而失去了独立人格的“羊”。
除以上几个方面外,还有对中原民俗文化的表现,对中原诙谐文化的借鉴与表现,对古代文学、考古文化的借鉴等。如李佩甫的《黑蜻蜓》中写二姐在她奶奶的丧礼上,为了表达对奶奶抚养自己长大的感恩与孝心,在生活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借钱为奶奶请了一班响器。葬礼上的响器寄托了活者对死者的纪念,也增强了葬礼的隆重程度。又如河南作家张宇的《乡村情感》中有一部分详细写到小龙和秀春的婚礼,从礼炮、鼓镲的地动山摇,到五杆唢呐的热闹喜庆,再到婚礼的繁琐程序,用书中话就是“动了老礼”。这古老的礼节既繁琐又隆重,充分展示了民俗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在民间诙谐文化方面,如刘震云的《手机》,从总体风格上,充满诙谐色彩。周大新特别善于借鉴中原考古文化丰富小说内容,如《左朱雀右白虎》、《湖光山色》等。这些中原特色的传统文化,不仅丰富了小说的内容,而且提高了文学的品味、认知价值和文化审美价值。
[1]李洱.阎连科的力量[N].北京日报,2004-4-2.
Abstract:Henan writers Central China’s folk culture,show the mystery of the Central China’s culture of the Central China’s mysterious culture,or reflect the Central China’s morality,express the vitality of the Central China’s farmers,and present the negative effect of th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thought upon peogile.They not only enrich the content of the novel,but also improve the taste for literature,cognition,and cultural aesthetic value.All this embodie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Henan writer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entral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Henan writers;Central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al;inheritance;development
(责任编辑:刘 明)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Henan Writer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entral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ZHOU Yin-li
(Shangqiu Normal University,Shangqiu 476000,China)
I206.6
A
1008—4444(2010)02—0071—03
2010-03-01
2009年度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中原特色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研究》(课题编号:B393)。
周引莉(1974—),女,河南夏邑人,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07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