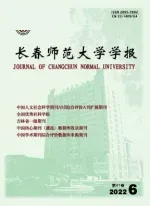钱大昕的目录学思想及成就
郑春颖,杨 萍
(长春师范学院,吉林长春 130032)
清乾嘉时期,学风大变,由明朝的空疏泛言转为重质尚实。目录学作为“学问之眉目”与考据的重要方法,被士人所推崇,当时学者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开始自觉地对前代目录书进行品评考证,整理研究。钱大昕曾对《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等史志目录做过考订工作,对《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渊阁书目》、《竹堂书目》等官方、私家目录亦颇有研究。
一
在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中收录《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五家史志目录,考辨内容多达二百三十三条。其中,文字校勘方面,纠正错字、剔除衍字、增补脱字、指明异体字、辨析通假字,几近百条,甚为精细。如卷五十八《旧唐书·经籍志》第二条,梁简文撰《长春秋义记》,钱大昕指明“春”为衍字[1]。卷七十三《宋史·艺文志》第二十一条,编年类《三十国春秋》原题作者萧方,钱大昕加注“本名方等,脱‘等’字”。[1]资料搜集方面,钱大昕利用本校、他校、理校等校勘法,细检各书,往往能查漏补缺,如卷三十四《隋书·经籍志》第十八条,他利用孔颖达《诗正义序》、贾公彦《仪礼疏》引文等资料,增补六艺经纬类未录之书二十八种。[1]第三十六条依据《隋书》列传补充于仲文《汉书刊繁》、张冲《前汉书义》等史部书籍十六种。[1]考证辨析方面,钱大昕不但对目录的作者、书名、卷次逐一考究,对书中的内容,如官制、避讳、籍贯、地名等亦往往有精彩的论断。如卷四十五《新唐书·艺文志》第二十五条,刑法类《开元后格》,原注云“礼部侍郎兼侍中宋”,钱大昕批注“侍郎当作尚书”[1];《宋史·艺文志》第二十三条,程正柔《大唐补记》三卷,钱大昕注云“本名匡柔,避讳改”。[1]
中国古代的目录书肩负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任,作为指导治学的工具书,若书写体例混乱,分类标准庞杂,势必影响它的功用价值,因此目录书在体例分类方面,往往都有严格的要求。体例分类合理与否不但是学者考究目录书的重点内容之一,同时也是衡量编修目录者学术思想、综合治学能力的重要参考因素之一。在《宋史·艺文志》第七条载钱大昕在朱熹《书说》下,加注提示“黄士毅集”四字应该分注。[1]“分注”的目的是使条理更为清晰,方便检索。凡各家目录归类有异议的书籍,他或是两者并举存疑,或是根据各方资料重新判定,纠正讹误。如《宋史·艺文志》第五条杨简《已易》,《宋史·艺文志》归于易类,钱大昕注“《文献通考》在儒家类”[1];《隋书·经籍志》第十四条《江都集礼》一百二十六卷,《隋书·经籍志》将其附于《论语》之末,钱大昕分析“此书本为议礼而作”,应当归于“礼家”,或“仪注”目下,批评《隋书·经籍志》的分类“失其伦”[1];《新唐书·艺文志》第四十七条,总集类司马相如《上林赋》下,钱大昕注云“《上林赋》以下八部,不当入总集。”[1]
钱大昕格外关注一书重出现象,对目录书中互著的分类方法颇有微词。在《隋书·经籍志》第十条,京相《春秋土地名》题目下,钱大昕按云:“志中一书而重出者,如京相《春秋土地名》三卷,一见春秋类,一见地理类;李概《战国春秋》二十卷,一见古史类,一见霸史类……庾季才《地形志》,两收于五行类,而前云八十七卷,后云八十卷,皆史臣粗疏之失。唐、宋而后,志艺文者,重复益甚矣。”[1]在《宋史·艺文志》第一条,钱大昕加按语“此志合《三朝》、《两朝》、《四朝》、《中兴国史》汇而为一。当时史臣无学,不能博涉群书,考其同异,故部分乖剌,前后颠倒,较之前史,舛驳尤甚,有一书而两三见者。如陆德明《经典释文》三十卷,见经解类,又见小学类。李涪《刊误》二卷,见经解类,又见传记类。……后有钟辂《感定录》一卷,疑为一书也。”[1]此条摘录《宋史·艺文志》中一百余部存在重出现象的书籍。此外,在《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文献通考》一文中,钱大昕又进一步论及重出问题,其云:
予读唐宋史艺文志,往往一书而重见,以为史局不出一手之弊。若马贵舆《经籍考》,系一人所编辑,所采者不过晁、陈两家之说,乃亦有重出者。如陆德明《经典释文》三十卷,见卷百八十五“经解类”,又见卷百九十“小学类”;宋敏求《春明退朝录》五卷,见卷二百一“故事类”,又见卷二百十六“小说类”;郭茂倩《乐府诗集》一百卷,见卷百八十六“乐类”,又见卷二百四十八“总集类”……[2]
以上这些评断表明钱大昕基本对一书重见现象持否定态度。其实,在钱大昕罗列的诸条重出书目中,根据产生原因不同,可以将其分成三小类:
第二类,错误。如《宋史·艺文志》第三十三条,传记类刘谏《国朝传记》三卷,钱大昕按:“《唐志》小说家有刘讠柬《传记》三卷,注云:‘一作《国史异纂》。’则《异纂》与《传记》本是一书。此志小说家既有刘《传记》三卷,而传记类又有刘《国史异纂》三卷,已为重出,又不知‘谏’、‘纟柬’皆‘’字之讹,而更出之,益可笑矣。”[1]此例是由编修目录者学识浅薄所造成的错误。
钱大昕分析产生一书重出现象的原因,要么是“史臣粗疏”,要么是“史臣无学”,要么是“史局不出一手之弊”,这几点原因作为第一、二类重出状况产生的内因较为准确,但是,第三类与前两者不同。第三类分类方法在目录学中被称为“互著”,此名词由章学诚提出,后演变成为目录学家常用的一种编排书籍的方法,此法便于读者即类求书,因书究学。钱大昕笼统地将“失误”、“错误”与“无误”混为一谈,未免不妥。但是,钱大昕作为杰出的文献学家,他对于此现象的否定也并非毫无意义。此种否定一方面表面钱大昕认为凡是书籍,无论内容多么庞杂,横跨多少学科,总会有一定的倾向性,而此倾向性恰恰是可归之类;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对目录书价值的定位与普通目录学家不同,他可能更看重的是目录书是否能给学者提供最有学术价值的参考书籍,而不是简单地将各类书籍烦冗堆砌。这二点体现了一个学术大家的独特视角。
钱大昕对前代目录书的研究工作,除了校勘考证文字内容、辨析分类体例外,对各种目录书的版本源流亦颇为重视。如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是宋代著名的私家目录。钱大昕曾于《十驾斋养心录》卷十四,对其各种版本的优劣及源流详加考证。首先他指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宋时有两个版本,然后对此两本基本情况加以介绍,其云:“袁州本仅四卷,淳佑庚戌番阳黎安朝知袁州刊之郡斋,又取赵希弁家藏书续之,谓之《附志》。衢州本二十卷,则晁之门人姚应绩所编,醇佑已酉南充游钧知衢州所刊。”进而从两本内容入手比较此二书优劣,云:“两书卷数不同,所收书则衢本几倍之。”之后又以赵希弁、马端临对此两版本的取舍作为旁证,得出衢本好于袁本的结论,并为“今世是通行本皆依袁本翻刻。予婿瞿生中溶购得钞白衢本,惜无好事者刊行之”[2]的现状感慨不尽。
目录书是治学的启蒙读物,如果目录书在文字、分类、内容上存在讹误,无疑会将初学者引入歧途。钱大昕将各类前代目录书作为研究对象,或校勘,或考证,辨析版本,探究真相,此项工作有益于后学之士,并能真正展示目录书的价值,有利于目录学的发展。
二
钱大昕作为乾嘉时期最著名的考据学家之一,利用目录书考订文字,考辨史实真伪,是其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在钱大昕众多的考证实例中,目录学研究方法总是处于比较重要的地位。同时,目录学与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等相关学科研究方法的相互结合又是钱大昕历史考证方法的另一特色。
钱大昕的考证,有繁有简,简单者仅使用一种方法,寥寥数语,却论断明确。如《廿二史考异》卷七十三《宋史·艺文志》第三条,载有《易口诀义》,《宋史·艺文志》题作者为史文徽。钱大昕按云:“《崇文总目》云:‘河南史证撰。’晁氏云:‘唐史证撰抄注疏,以便讲习,田氏以为魏郑公撰,误也。’陈振孙亦云:‘避讳做“证”字。’则此志‘徽’字当作‘徵’之讹。”[1]第五十二条,马融《忠经》,《宋史·艺文志》题一卷。钱大昕云:“隋、唐《志》俱无此书,盖宋人伪托。”[1]第五十八条,法林《辨正论》,《宋史·艺文志》题陈子良作。钱大昕按:“法林《辨正论》八卷,又见于《破邪论》之下,此讹‘琳’为‘林’,实一书也。晁氏云:‘颖水陈良序。’《唐志》云:‘陈子良注。’此以为子良作,亦误。”[1]以上三例,钱大昕通过不同目录之间的比较,或是发现讹字,或是揭露伪书的真实面目,或是指明作者真身。大体上《廿二史考异》中诸书的考证多简短,《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中的考证相比则丰沛许多,这些考证更能体现钱大昕的目录学思想。
如《星经》一书,流传已久。虽前人已怀疑它的真实性,但尚无系统考辨之说。明清以来,受西学的影响,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天文历法方面的专门知识,钱大昕亦是其中一人。他在天文、历算方面的造诣,为他考证此书提供了可能。在《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四《星经》[2]、《潜研堂文集》卷三十《跋星经》[3]中他详细地论证了《星经》的伪书性质。首先,钱大昕考辨《星经》著录之源,其云“不知何人伪撰,大约采晋、隋二志成之”,又云“《续汉志·天文志》注引《星经》五六百言,今本皆无之,是刘昭所见之《星经》久失其传矣”。其次,他进一步指出“甘石书不见于班史。阮孝绪《七录》云,甘公有《天文星占》八卷,石申有《天文》八卷,今皆不可见矣”。再次,他又从《星经》的文辞特点分析“今《星经》词意浅近”,判定此书“非先秦书也”,在此基础上又引明人《汉魏丛书》中的评价“汉甘公。石申,皆在战国时,非汉人也”作为补充。钱大昕考证此书所用的主要方法是以各代目录书的著录为纲,文辞特点及前人相关评价为目,纲举目张,以目补纲,使书籍真伪不言自破。
再如《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吴越备史》[2]、卷十四《严州重修图经》[2]二书。《吴越备史》原书卷首题武胜军节度掌书记范、武胜军节度巡官林禹撰。钱大昕首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观点“钱俨所作,托名林、范”。又引《宋史·艺文志》的记载“霸史类载此书,十五卷,亦云钱俨作,托名范、林禹撰”。初步判定该书作者是钱俨,而非托名的林、范二人。此外,又别考钱俨《备史遗事》一书,先指明此书“今世所传乃明钱德洪刻本”,在介绍该书体例及记载内容时间起讫之后,指出此书“与史志卷数不合”。又引书末题跋引出撰者“中孚”之名,此后依据程俱《北山小集》考证“中孚”是“中吴军节度使元之曾孙,於武肃为四代孙也”。又引钱岱序谓“范、林二记室撰《备史》五卷,至十九世孙绪山公命门人马荩臣补忠懿遗事,合六卷,刻之姑苏。”进而考证云:“今考荩臣所撰,唯《吴越世家疑辨》一卷,德洪序中初不言补遗出其手,岱盖考之未审矣。”又引钱遵王家藏本补证,云此本“止四卷,又称忠懿为今元帅,吴越国王,自乾戊申至端拱戊子,终始历然,何缘更有补遗?”最后判定此书“显系明人妄改”。
对于《严州重修图经》,钱大昕先指明其所见版本为淳熙重刻本,仅存首三卷。次提及卷首有“绍兴己未正月知军州事董序,及淳熙丙午正月州学教授刘文富序”,进而初步推断“文富盖承郡守陈公亮之命订正是书者也”。又云“卷首载建隆元年,太宗皇帝初领防御使诏;宣和三年,太上皇帝初授节度使制,及敕书、榜文二道”,进而解释“太上”称谓,缘由“淳熙丙午之岁,高宗尚在德寿宫”。之后,考辨此书云:“董初创此志,本题《严州图经》,陈公亮重修,亦仍其名;而王氏《舆地记胜》、陈氏《直斋书录》、马氏《文献通考》皆作为《新定志》。盖宋人州志多用郡名标题,续志载书籍,亦但有《新定志》,初无《图经》之目,名目虽异,实非有两本也”。
此两例反映,钱大昕在考证书籍时思维方式具有发散性的特点,他考辨的内容不仅包括此书的作者、卷数、题跋、时间,还包括本书作者撰写的其他著作,或是与此书相关联的各类书籍。钱大昕考证的方法是以目录书著录的内容为中枢,用目录中的内容来组织安排整个考证过程,目录著录的内容无论置于何处,开端、中段或是结尾,因其在整个考辨进程中的核心地位,往往令人瞩目。同时,钱大昕又不被目录的记载所囿,将版本学、辨伪学与目录学知识相结合,努力探究致误之因。
判定一书之真伪并非易事,钱大昕对于那些可以判定的书籍,往往详细地考证,并给出清晰的结论,以免后学误入歧途,对于那些尚难判定者,他也会将种种疑问罗列于一处,以待后生定夺。如《周成杂字》[2]一书,钱大昕首先提及此书元应《一切经音义》、李善《文选注》屡有引用。进而考论《隋书·经籍志》小学类,发现有《杂字解诂》四卷,提名为魏掖庭右丞周氏撰。又有《解文字》七卷,提名周成撰,此书已经亡佚。他认为周氏与周成不是同一个人。钱大昕又查《唐书·艺文志》有周成《解文字》七卷,而无周氏书。因此推论“两志所载周成书,俱无杂字之名,未知即此书否。”其后,又对官职考辨云:“掖庭左右丞,汉制皆宦者为之。魏承汉制,则周氏亦必宦者。如注《尔雅》之李巡,亦中黄门也。”(见《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此推论虽无定论,但其考证对人们了解这部书的基本情况有一定的帮助,此例体现了钱大昕求实的治学态度,同时也体现了他一贯的治学方法。
史学考证是集提问、求证、推理于一体的学术研究工作。考证过程往往是多个学科、多门知识的协同作战。钱大昕的考证多是以诸家目录校勘比对为始,通过目录的对校,发现问题,再进一步追查根源,补充相关信息,最后辨证疑误,正本清源。在其考证过程中,目录学研究方法,往往处于核心地位,同时钱大昕又注意将目录与版本、校勘、辑佚、辨伪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相结合,多角度、全方位地对某部古籍及其相关领域的内容加以考辨。目录书被应用于考证工作是由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性质所决定的,同时,它也说明了钱大昕对于目录书的性质有着清晰的认识:目录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良好途径。钱大昕的考证实践活动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宝贵的治学经验。
三
如在《元史·艺文志》经部著录的十二种图书分类中,易类、春秋类,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类著作非常多,它反映了元代学界春秋学、理学兴盛的情况。又如史部编年类著录数量颇多,代表的有:杨云翼等《续资治通鉴》,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释文辨误》,尹起莘《通鉴纲目发明》,王幼学《通鉴纲目集览》,刘友益《通鉴纲目书法》,徐昭文《通鉴纲目考证》,张特立《历代系事纪》,胡一桂《历代编年》,察罕《帝王纪年纂要》,苏天爵《金纪年》等。这些图书资料说明元代通鉴之学、编年类体裁备受学者关注。
钱大昕在网罗旧籍的基础上,根据元代特定的学术背景及当时书籍的保存现状,对目录子目的设定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这使《补元史艺文志》在同类补作中显得颇为别致。
首先,钱大昕取消了在《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等目录书中常见的子目。这些子目取消的原因,有的是因为流传下来的典籍数目较少,如史部中的纪事本末、时令、别史、载记等目;有的是因为原有子目名与其收录书籍有出入,名实不符。如经部中的五经总义、四书二目,往往收书超越五经、四书总论,甚为庞杂。此两目的撤消体现了钱大昕学术思想的严谨;有的则是钱大昕对于某类书籍性质重新评定的结果,它反映的是钱大昕学术思想的独特性。如史部制诰一类,各家目录多将其置于诏令奏议子目中,钱大昕则不设此目,将其处于实录之下。实录是中国封建时代记载皇帝在位期间重要史实的资料性编年体史册。制诰是皇帝发布的一系列公文,每一份公文无不与某一件历史事件存在某种必然联系。钱大昕此目的处理方式,表明他对于制诰性质的认识较其他目录家更为深邃。
其次,钱大昕增加了一些前代目录书中未见的新目。如经部中译语目,此目收录的是翻译成辽国语、金国语、蒙古语的儒家经典。其中,辽语的有《五代史》、《贞观政要》、《通历》等;金国语的有《易经》、《书经》、《孝经》、《论语》、《孟子》、《国语》、《新唐书》等;蒙古文的有《孝经》、《大学衍义》、《贞观政要》、《帝范》等。此目的出现与当时统治阶级的少数民族身份有关,它反映了辽、金、元三代儒家经典在社会主流思想中的流行情况,也反映了钱大昕对于儒家思想在元代社会地位的关注。清末学者文廷式曾称赞此举“体例最善,深得“隋志之意”。再如子部中的经济目,此目下收录辽、金、元三朝各类经国济民之书,共42种。此类书籍不是对前代统治经验的总结,就是针对现实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提供的解决方法。此目反映了钱大昕经世致用的思想。钱大昕提倡“文以贯道,言以匡时”,认为“儒林经济非两事,根柢深厚枝叶荣,……文章须有裨名教,经史自可致治平”。钱大昕不是钻进故纸堆里,为了考据而考据的学者,在他考据的背后,隐含的是从古学中总结为政之道,以为当世所用的动机与热情。所以,当其他目录家将这些经世济民的良策泛泛地归于儒家一类时,钱大昕却将此目独立出来,以示明鉴。再如,集部中的科举目,此目收录了大量的有关科举考试指导方面的典籍,如各类试卷汇编等。此目的设立突出了目录在现实生活中的工具书职能。
再次,钱大昕并不遵循目录编修中的一些惯例。从最初的《七略》,至《四库全书总目》,类目的划分渐趋精细,由二级类目到三级类目的出现,代表的是当时目录学发展的总趋势。钱大昕却化繁为简,虽分经、史、子、集四部,但子目数量比其他同类目录少,并且在子目下,不再设细目。此种分类方法最大的好处是方便学者查找资料,它体现了钱大昕对于目录书功用价值的重视。无论《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等史志目录,还是《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私家目录,或是《四库全书总目》等官方目录,往往史部刑法 (或法令、政书)目与子部法家目并举,因对二者的区别不甚明晰,经常张冠李戴。钱大昕则根据元代无法家著作的现实情况,取消了子部中的法家类,将《唐律疏义释文》、《刑统》、《无冤录》等刑律、办案汇编类的典籍收入刑法目,此分类科学地反映这类书籍的性质。钱大昕关注刑法类书籍与他“德主刑辅”的政治理想有关,他曾经对《宋史·刑法志》有一定的研究,他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主张“法当杀而故出之,是之谓纵;法当宥而故入之,是之谓滥。天子之不可以纵奸,而士师之不可以滥杀也。”钱大昕在法律方面的修为,有助于他对刑法类书籍范围的界定,也使目录的分类更为客观。
钱大昕除编修了《补元史艺文志》外,还编修了《范氏天一阁碑目》、《道藏阙经目录》等目录书。钱大昕在金石学方面颇有造诣,其考史补史工作经常以金石学方面的资料作为重要依据。乾隆五十二年六月,他来到宁波范氏的天一阁,将范氏子弟未尝重视的碑刻资料清理出来,编为《范氏天一阁碑目》,收拓片580余通。这部关于碑刻的专题目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它体现了钱大昕对于金石资料的重视,同时,也说明他将目录编修作为整理资料的一种方法。钱大昕早年听惠松提及道藏中多儒书古本,归田后广为收集,先后求得朝天宫本、玄妙观本等版本,又得袁又恺协力,成书八百余卷,多为儒生必读之书。在《道藏阙经目录》的跋文中,他说“宋《藏经目录》失传,此册乃元人所记,和之今传者,可以得宋藏之梗概”。恢复宋藏之原貌,可谓功不可没。
综上所述,钱大昕注重目录学在文献整理工作中的实际运用价值。他对前代诸家目录或有评价,或有考证,时推善本,以企流惠后学。目录学研究方法是其历史考证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他将目录与版本、校勘、辑佚、辨伪等工作相结合,形成了具有其个人特色的考辨系统。钱大昕学识渊博,横跨经史,兼修各家,具有良好的学术修养,这使他比普通的目录家更能认清书籍的本质。钱大昕不是钻进象牙塔不问世事的学者,他一直强调学术的现实意义,强调经世致用,因此他所编修的目录书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独特的学术气息。
[1]钱大昕.廿二史考异[M]//陈文和.嘉定钱大昕全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1139,1378,738,740,945,1378,1376,1376,737,948,736,1369,1373,1380,1375,1382,1383.
[2]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M]//陈文和.嘉定钱大昕全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360,397,383,349,369,343.
[3]钱大昕.潜研堂文集[M]//陈文和.嘉定钱大昕全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506.
——以谭瑟勒的《目录学概论》课程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