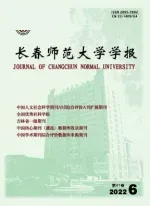民初鸳鸯蝴蝶派历史定位新探
郭建鹏,郭建辉
(1.长春师范学院,吉林长春 130032;2.河北省昌黎县安山镇实验中学,河北昌黎 066601)
诞生于清末民初的鸳鸯蝴蝶派,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遇、撞击、融合的特定时代和文化生态环境中,形成了以南社小说家为主流的传统士子与新派知识分子杂糅的蔚为壮观的文学创作群体。同时,以上海为中心的“现代性”市民构成了它的消费群体,在文学商业化市场的操作下,鸳鸯蝴蝶派文人为迎合读者的“期待视野”,将中国正统雅文化拉向了轻松消遣的趋俗脱雅之路。这一群体的主流意识在民初的创作环境中难以与传统意识彻底地决裂,文人的主体地位使他们试图有所超越,又无法摆脱传统的伦理规劝意识,只好利用文学的娱乐功能来记录小市民阶层生活的变迁,为市民枯寂的世俗人生增添一份快感。鸳鸯蝴蝶派大部分成员与五四新文学的发起者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胡适等基本属于同一代人,但他们走的道路迥异,新文学的发起者吸纳西方文化的同时将其转化为救国拯民的良方,继之成为新民革命的号角;虽然鸳鸯蝴蝶派成员在科举废除后大都进过新学堂,但他们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至深,一时难以舍弃,最终选择了本土文化的经营与创作。
晚清民初,在西学东渐过程中,翻译文学兴起。此间,鸳鸯蝴蝶派成员如包天笑、周瘦鹃、恽铁樵的翻译小说深得大众喜爱。辛亥革命胜利后,翻译高潮逐渐褪去,受时代和社会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他们所持有的文化资本迅速贬值,地位不断下降,已无力为变动的社会提供一种核心价值。与科举时代相比,鸳鸯蝴蝶派成员好像被废黜的贵胄,所学已不能为世所重,为时代所迫,转为自娱、娱人、卖文为生,并逐渐下沉为市民通俗文学的创造者。其创作倾向于民间立场的回归,最终导致鸳鸯蝴蝶派与历史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在五四新文学兴起之际,这种距离成为新文学家批判的靶子。
如果从今天的阅读立场来审视鸳鸯蝴蝶派及其文学作品,则完全失去了五四新文学家戴着充满政治色彩的有色眼镜去批判鸳鸯蝴蝶派的激情。实际上,正是鸳鸯蝴蝶派作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跋涉与努力,才推动了五四新文学家的创作内涵。在民初,南社社员由诗文转向小说创作,并成为鸳鸯蝴蝶派的主流,是文学话语疏离政治在场的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要想正确地解读鸳鸯蝴蝶派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与贡献,就必须还原其历史本源,通过它的主流群体与创作立场及倾向来建构时代的意义与历史定位。
一
从鸳鸯蝴蝶派这个创作群体的主流来看,他们大多是清末民初最具影响力的社团——南社的社员,如王钝根、许指严、朱鸳雏、包天笑、徐枕亚、周瘦鹃、范烟桥、姚民哀、姚宛鸟雏、徐天啸、赵苕狂、陈蝶仙、叶楚伧、闻野鹤、刘铁冷、王西神、贡少芹、苏曼殊、胡寄尘、程善之、戚饭牛、蒋箸超、谈善吾、宋痴萍、张冥飞、叶中冷、姜可生、陆澹安等,他们活动的空间多在上海,从事的是新兴的行业——报刊业,他们的思想意识和创作成就不仅在南社占有一席之地,在鸳鸯蝴蝶派中也是中坚力量。据郑逸梅先生的统计,以《小说时报》为起点的鸳鸯蝴蝶派杂志有113种,大报副刊4种,小报45种 (杂志从辛亥革命前夕到解放前,大报副刊和小报止于抗战前)。[1]在这160余种报刊中,有46种杂志 (五四前21种)、2种大报副刊(《申报》副刊,《民权报》副刊)和4种小报主编或编辑是南社社员。剩余的杂志、副刊、小报中的撰稿人大部分是南社社友。以南社出版的唯一一部小说集——《南社小说集》(1915年,王均卿编)为例,它收了周瘦鹃《自由》、成舍我《黑医生》、程善之《儿时》、叶小凤《贼之小说家》、王钝根《予之鬼友》、赵苕狂《奇症》、胡寄尘《黄金》、闻野鹤《媒毒》、姜杏痴《蛇齿》、叶中冷《云》、王大觉《红爪郎》、孙阿瑛《伤心人语》、贡少芹《哀川民》13篇小说,除王大觉、孙阿瑛外,其余的作者都属于鸳鸯蝴蝶派成员,这些作品在选材上可归属于当时流行的鸳鸯蝴蝶派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除此之外,在民初至五四之际,数以百计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中蕴含了大部分南社社员的作品。
辛亥革命前,南社社员紧紧围绕着陈去病、高旭、柳亚子高举的民族主义革命大旗进行反清革命与创作,武昌起义胜利后,他们又以诗文方式吹响反袁运动的号角。民初到五四前夜,因统治者的专制与高压政策,一部分人从热衷入世转向潜心遁世,在消沉苦闷中远离政治现场。他们的创作转向了哀感顽艳的言情小说,通过写情文本来宣泄对礼教专制的愤懑。鸳鸯蝴蝶派中南社人的言情小说,大多以婚姻与爱情自由之间的交叉矛盾所引起的痛苦与悲哀为创作基点,诉说着这代人在道德价值与情感价值上难以抉择的困惑。受西方“男女平权”、“恋爱自由”思潮的影响,他们对传统礼教中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提出质疑与抗争,并将婚姻自主的觉醒化作一种文化心态,通过小说创作表现出一种集体探寻意识。徐枕亚、苏曼殊、周瘦鹃、陈栩等人的写情小说,以自身的情感悲剧为参照,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策划了民初婚姻革命的风暴。“寡妇再嫁、和尚恋爱”首当其冲地向封建婚姻道德发出了挑战。虽然他们没有五四作家的果敢,态度还有些暧昧,最终结局都是悲歌式的痛吟,但是,对他们来说,是用一种癫狂的叛逆来拯救心灵深处的创伤。
籍属鸳鸯蝴蝶派的南社小说家,不仅掀起了写情小说创作高潮,而且在翻译小说、社会小说、黑幕小说上,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中国第二次翻译高潮中,周桂笙、包天笑、周瘦鹃的翻译小说给中国文学思潮带来了很大影响。周桂笙的翻译活动主要在清末民国以前,包天笑和周瘦鹃的翻译作品则主要集中在民初五四前,从他们的译本选择、翻译中所存在的“归化”与“异化”现象来看,其作品都没有脱离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与受众的阅读心态,而是在读者的猎奇心理中达到启蒙与宣化的目的,在情节“衍生”中蕴藏了革命力量的整合。虽然袁氏政权的高压政策使南社社员的创作与社会活动受到钳制,但他们的反抗与革命的信念并没有动摇,并将笔触直指最高统治者。如叶楚怆的《如此京华》披露了袁世凯政府的黑暗统治;周瘦鹃的《亡国奴之日记》和《卖国奴之日记》于嘻笑怒骂之间痛斥了侵略者和卖国贼,表达了强烈的爱国心;姚宛鸟雏《龙人套语》(后更名《江左十年目睹记》),记述了民初至北伐前北洋军阀在江南的残暴统治,集谴责与批判为一体。他们的作品更多的是通过底层人间百态的描绘来反映他们对社会的愤懑,如《弄堂小史》通过一个皮匠的眼光折射出上海的社会现状;《茶寮小史》再现了民初作为过渡时期知识分子的生存现状。
在鸳鸯蝴蝶派兴盛与繁荣时期,以南社社员为主流的小说家并没有完全退出政治舞台,而是在规避与隐逸中书写他们的政治情怀。为了生存下去,他们只好借助“消闲、娱乐”的外衣来内隐。也正是这种内隐因素,导致他们转向“民间文化”立场,并在此进行深耕细作,最终使鸳鸯蝴蝶派执意于都市市民意识的创作流向。
二
任何事物的滋生,都离不开它赖以存在的环境。考察鸳鸯蝴蝶派的活动场所就会发现,它的兴盛与上海这个新都市的崛起紧密相关,最显著标识是上海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引起的文化生态环境的变迁。近代上海,它的基层组织成员的身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上海的群众大多是江浙地区的移民,这些移民自身结构与中国其他大城市的移民又有着内在的差别。明清以来江南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促使大部分自由民脱离封建制度的束缚,寻求独立人格的存在方式。商品经济的发达,使他们潜意识里透着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追求,体现在文学上则是文学作品开始作为一种商品,按自由交换的方式朝着文化产业方向发展。蜕变中的城市生活与都市人的价值观改变了传统的文学阅读理念与期待视野,在都市文明的形成、发展过程中,经过漫长农业社会历史的居民突然转化成现代都市的市民,其根深蒂固的集体潜意识内容和某种深层心理原型发生了质变,这种变化并没有因为都市化的生活而褪色,而是随着都市化的步伐和种种文化形态继续滋长着民间因旧体制的崩溃而散失的传统文化的萌芽。多种意识形态的扭结最终囿定了鸳鸯蝴蝶派的“民间”立场。
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鸳鸯蝴蝶派小说确实起了一个过渡作用。它骨子里渗透的是旧文学的艺术张力,在思想和外表上却罩上了现代性的光环。高度集权的政治环境,使鸳鸯蝴蝶派成员失去了封建社会文人入世的职业选择权,而现代小报的兴盛、印刷业的发达、稿酬制度的建立都为末世文人营造了宽松的生存环境与职业场所,并极尽所能地传承着它作为一个特殊文学流派具有的通俗性和大众化的特色,在其固有的趣味性中宣泄着消遣娱乐的作用,并始终以“民间文化”为主旨。早期鸳鸯蝴蝶派期刊杂志的办刊宗旨,有意地将他们的创作引向“民间”立场。于1912年3月在上海创刊,由蒋箸超、吴双热、徐枕亚、李定夷等任编辑的《民权报》,虽然没有发刊词之类文字来标榜办刊倾向,却因刊载徐枕亚的《玉梨魂》和吴双热的《孽冤镜》两部小说而引发了中国民初文坛的言情小说热潮,促进了鸳鸯蝴蝶派写情小说的发展。《民权报》被袁氏政府的封杀,并没有阻止编辑的办刊热情,而是将副刊上未载完的稿件移入《小说丛报》,“假使把《民权报》作为鸳鸯蝴蝶派的发祥地,那么《小说丛报》是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了。”[1]《小说丛报》确实延续了《民权报》的写情风格,并且进一步明了化:“原夫小说者,俳优下技,难言经世文章;茶酒余闲,只供清谈资料。……有口不谈家国,任他鹦鹉前头;寄情只在风花,寻我蠹鱼生活。……[2]这一举措最终结果是将鸳鸯蝴蝶派的“民间立场”明细化了,无形中为以后鸳鸯蝴蝶派期刊的旨归做了铺垫。
时代精神、政治环境、价值准则影响了这一时期文学期刊的办刊方针,体现在社会政治批判性的削弱,取而代之的是追求消闲、娱乐和趣味。鸳鸯蝴蝶派的核心刊物《礼拜六》杂志,在《出版赘言》中阐明了其办刊宗旨:“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人皆从事于职业,惟礼拜六与礼拜日,乃得休暇而读小说也。……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游倦归斋,挑灯展卷,或与良友抵掌评论,或伴爱妻并肩互读,意兴稍阑,则以其余留于明日读之。晴曦照窗,花香入坐,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3]休暇、省俭、安乐的旨趣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读者群体的扩大,使前百期《礼拜六》在民初市民文学杂志中迅速脱颖而出,销数最高达到两万余册。受其影响,而后刊行的鸳鸯蝴蝶派杂志《眉语》、《小说新报》等都将办刊宗旨定位在游戏、消闲和趣味之间。鸳鸯蝴蝶派在改变文学期刊传播方向的同时,引领了中国小说文学观念和审美追求朝着世俗化、大众化、社会化方向发展,确定了中国近代通俗小说的基本特征。这也是鸳鸯蝴蝶派以“民间文化”在场的身份于五四新文学鞭挞声中表现出顽强生命力的内在意蕴。
民初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家以半新半旧的文人团体意识活跃在民初报坛文界,通过其作品中的素材来传达“民间”信息,以言情、社会、历史、战争、侦探等纷繁杂陈的门类反映社会现实。他们接受新文化中萌动的现代性,又割舍不掉传统文化的熏染之情,当民间立场与国家政治呈相互交错、既对峙又融合的变态时,他们便呈现出对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价值理论体系的反观、批判能力的缺失,在对统治者的容忍与依附过程中出现“提倡新政体,保持旧道德”的被动,这种被动因他们依赖的受者群体的庞大而存在。鸳鸯蝴蝶派的“民间”性,扩大了它的读者群体,(从士大夫阶层转变而来的遗老遗少、新兴市民、接受新思想教育的知识分子、传统的农村读者)这些读者更多观照的是“民间”信息中的传奇色彩、轰动效应和感官刺激。为迎合这部分读者的需求,鸳鸯蝴蝶派丧失了对文学“高雅”的艺术追求。在西方新思潮的引介、民族意识再次高涨、新派读者群体的张扩、都市现代化演进的过程中,传统的民间信息出现难以弥补的裂痕,随着新文化的发展呈现出雅俗合流的动态特征。鸳鸯蝴蝶派作家依靠“民间文化”,经过主体性的择取积累起了与雅文学相抗衡的力量,于国家空间意识形态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外营造了一个文学话语选择的立场,在作品中呈现出芜杂的多元文化。而商业价值的刺激更坚定了他们在都市中选择“民间文化”的权力。
三
民初,鸳鸯蝴蝶派能够迅速地成长为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无组织的文学流派,与以上海为中心、报刊文学为主流的现代都市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报刊一方面对应着城市世俗化、物质化的生活内容,另一方面则表现着城市商业性、功利性的精神实质与原则。”[4]建立在商业运营机制和新兴价值观念基础上的报刊文学,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迎合广大消费者的阅读品味成为发展趋势。同时,都市市民的阅读心理和价值观念的转变、现代印刷技术的推广和在稿酬制度催生下小说生产节奏的加速,刺激了创作队伍和消费群体的壮大,正是在这种商业化的文化公共空间下,民初知识分子成为依赖报刊杂志、传媒体制和稿费谋生的专业化、职业化作家。
小说家职业化和小说生产商业化是文学存在方式多元化的必然结果。近代稿酬制度的完善是其主要原因,除个别刊物不付稿酬外,晚清民初的报刊都向作品的创作者 (译者)支付比较昂贵的稿酬。“在1917年‘文学革命’之前至少20年,都市文学刊物——‘民众文学’的一种半现代的形式——已经为日后从事新文学运动的人们建立市场和读者群。这些杂志的编辑和作者如痴如狂地撰写文章,大笔大笔地赚取稿酬。”[5]丰瞻的稿费诱惑造就了清末从事小说创作的群体,科举制度的废除使他们丧失了依靠仕途谋生的资本,最终转向了卖文为生的新职业,成为中国第一代职业作家。鸳鸯蝴蝶派本质上就是一批以南社社员为主流的报刊作家,(如严独鹤、周瘦鹃、徐枕亚、包天笑、陈蝶仙等)他们大多数直接参与过报刊的编辑出版工作,报纸杂志的销路与他们的经济状况紧密相关,与清末第一批职业作家相比,他们的文学商品意识表现得更为明显,更能真切地体会市场的冲击。市场、经济利益的介入,促使小说家拼命地多写,以出奇制新的故事情节来吸引读者的眼球,相对长篇小说而言,短篇小说的优势日益凸显,这也是民初短篇小说在数量上远远超越长篇小说的原因。为了适应了大众的“消闲”、“娱乐”要求,进而扩大市场和读者群,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他们忽略了小说界革命提倡的“救国”精神,导致小说创作主题远离政治性进而落入通俗甚至庸俗化的窠臼。
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大部分是以办报 (创作)作为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为生计而写作的现实需求并没有误导他们成为粗制滥造的低级文学生产者。他们虽然在创作上趋向于商业化,却依然固守着传统文人赖以栖身的精神家园,淡漠的只是政教伦理的群体意识。他们将维新派推小说至政治宣化之功的巅峰重新拉回面向大众生存的通俗领域,在商业化关照的过程中还原小说的文体本色。鸳鸯蝴蝶派在商业市场价值定律指挥下,并没有完全抛弃中国古代小说“文以载道”的传统,只是在赤裸的商业气息包围下尽力地去拼除旧小说中的道学气;受翻译小说文本的影响,它将西方文艺复兴思潮和近代都市趣味带进了弥荡着腐朽气息的传统文坛,形成一股无法抗拒与归避的冲击力。
四
民初封建伦理观念失去了国家权力的庇护,人性原始自由欲望在西方思潮的鼓动下开始了朦胧的觉醒。率先擎起反对礼教、争取个性解放大旗的是封建观念相对淡薄的都市新市民阶层。鸳鸯蝴蝶派回归传统,是其“民间立场”和“文学作品商业化”的本性决定的,其以满足市民的“趣味”为创作标准,更多地发挥了文学的消费功能。他们也曾进行过深层次的文本审美艺术的探索,在传统中隐性地传承着现代性气息,而这种隐性往往是新文学家所忽略的,“当‘五四’知识分子开始以启蒙、理性、革命等角度来回顾他们的文学传承时,这些作品很快被贬为琐屑、颓废,或是反动。”[6]新文学家的评判将传统与现代性隔阂成“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并视为文学研究的圭臬,将其植入20世纪文学的历史价值、工具理性的单向度诉求,忽略了文学文本多元形态的实际存在,导致文学中多重价值范畴的失衡。
新文学的现代性是在思想启蒙下赋予的具有政治的、历史的双重使命要求,而鸳鸯蝴蝶派文学是在文学市场的驱动下进行尝试性地现代性变革,这种现代化观照了对传统的接应和回归,是渐变的,其现代性叙事技巧运用突破了传统叙述模式并呈现出外向性。它的现代性表现在封建礼教与婚姻、爱情自由之间的矛盾,表现在社会基层与统治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还有来自关系民族存亡的国际历史问题。鸳鸯蝴蝶派在反对封建政体和礼教意识前提下继承了晚明“以情抗理”的思想观念,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了相通的一面,只不过被它的通俗性所遮蔽,鸳鸯蝴蝶派所依存的都市“民间”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屏蔽了文学的“载道”模式与鉴赏品味的崇高感,与五四精英的启蒙思想和重塑国民精神相悖离,最终在五四作家急于摆脱传统文学接纳来自西方现代性文本之际,被冠以“思想的反动”、“拥护旧道德的封建余孽”之罪名,进而掀起了声讨笔伐的文学论战。
文学话语权的张力受囿于文学文体所处的历史情境,有时不得不屈服于历史期待视野,不管何种文体,它们体现出的历史同构性是平等的,只是价值维度不同而已。在五四文学高涨时期,鸳鸯蝴蝶派的“民间性”与启蒙或革命文学之间滋生了对抗因素。鸳鸯蝴蝶派游离于社会、历史及中国主流文学“现代性”边缘,实际上是在疏远文学政治角色的过程中真正地迎向时代与现实。每一个流派、文学思潮及作家都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新旧更迭的端口,但是并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成为文学史流变中真正意义上吐故纳新、具有代表性的“过渡的一代”。而现代性的实现是多维度、多层面的,它主导了文学从“异化”向“同化”发展的结构形态。南社早期高涨的政治情操相对于启蒙和救亡的五四作家主体而言有些幼稚和偏激,当它被解构到鸳鸯蝴蝶派群体中时,其被压抑的现代性在民族文化内部籍借民族传统文化基础得以舒展与释放。
总之,以南社小说家为主流的鸳鸯蝴蝶派文学继承了传统的文化精神和艺术表现方式,同时,贴近现代都市生活,通过“民间文化”在场和商业化价值追求来满足现代市民对文化的需求欲望。在小说界政治革命思潮澎湃激荡之际,逃避了启蒙文学家那种“救民族于水火”的高昂姿态,转为对市民生存的抚慰,为文学多极化发展作出“现代性”反映,架起一座传统与现代之间非对抗性转换的桥梁。不足的是,鸳鸯蝴蝶派文学中杂糅了一些过分追求低级趣味的作品,消解了文学作品中的现代性,带来了负面影响。
[1]魏绍昌.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M].香港:三联书店,1980:277,293.
[2]徐枕亚.小说丛报(第一期)[M]//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461.
[3]王钝根.礼拜六(第一期)[M].影印本.江苏:江苏广陵古籍出版社,1987.
[4]陈国恩,左敏.小说稿费制与清末民初文学变革[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5).
[5]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484.
[6]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