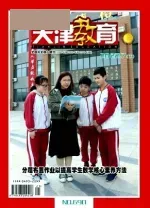“流水线作文”之诊治
■李玉山
李玉山 北京师范大学天津附属中学
“流水线作文”之诊治
■李玉山
编者按:写作是学生需要掌握的一种基本能力,但是当前学生的写作水平和写作能力状况不容乐观,主要表现为模式化现象严重和思维僵化。这固然有学生自身的原因,但与教师的教学行为也是直接相关的。作为语文教师,应该真正承担起教会学生写作的责任,采取有效的教学方式,切实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我刊邀请了几位一线的语文教师阐述他们对当前中学写作教学中存在问题的认识,希望能够对读者有所启示。
“阅尽千篇无他样,似曾相识一般文。”这样的感觉,凡参加过高考作文阅卷的人大都会有过。说“千篇一律”绝对是夸张,但有一半左右考生的习作就像经过“流水线”加工一样,且大有愈演愈烈、渐入歧途、向其他年级蔓延的趋势。这样的“惨状”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如何矫治学生习作中的机械操作与形式主义倾向,给学生营造一个“绿色写作”的良性的“场”。所以,对“流水线作文”做具体而微观的解剖,还写作一个健康的肌体,是本文的终极所指。
“流水线作文”的基本结构一般为“总—分—总”,开头总起点题,结尾总括全文,中间的“分”一般为三个部分,有的用分论点,有的用小标题;这相当于盖房子的“框架”,而“砌墙”则主要用事例,事例的多少视“篇幅”而定,但大多数用三个例子即每部分一个例子;华丽、生动、有气势的语言,浮华式表述和口号式句子较为多见。
写作不是不可以化用“套路”,不是不可以使用例子,而“有文采”更是优秀习作的标志之一。“流水作业”能提高工作效率,也可以生产出精品,有些高分作文就存有“流水线”痕迹;但由于习作者的思维真正活跃起来了,对问题的认识真正透彻了,对生活的感悟真正深刻了,文章的内容与形式有机地统一了,得高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笔者所反对的是将写作异化为“流水线”式的机械操作,使其成为单纯功利思想下“拿分”工具的做法。
需要特别声明的是,本文“解剖”的“活体”均为见于纸质媒体的考场“优秀作文”。因为既然能得高分,最起码在阅卷教师眼中是很不错的或基本上还算漂亮的习作;既然能通过编辑的法眼发表、收入集子,则说明编辑对这些作文是认可、赞同或基本肯定的,是“达到了发表的要求”的。所以,这些作文在某种意义上就有了标本的价值,对其作聚焦扫描庶几能直抵时下作文教学尤其是应考作文训练所存在问题的核心。
一、“唯模式化”僵化了思维、凝固了情感
应该承认,对于初学写作者来说,了解一些基本的文章模式是尽快“入门”的捷径,但若让其出神入化,必须有思维的深度、广度做支撑,切不可陷入“唯模式化”的泥淖。任何一种文章模式一旦成了固化、唯一的套路,那么写作也就成了彻头彻尾的机械操作,这种功利主义写作观是对写作本质的亵渎与背叛。遗憾的是,为数不少的教师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亵渎者和背叛者。
笔者曾接触过各类学校的学生,有些学生有很好的写作基础,但他们的习作大都是“总—分—总”式的,有的学生甚至从高一到高三三年间所有的作文都是“总—分—总”模式。这颇有点像瓦岗寨的程咬金,就会那三斧子半,遇到外行还能对付一下,遇到真正的高手就只能是脚底抹油。问题的关键是,程咬金是由于天资迟钝、悟性较差,无可奈何才练那三斧子半,而有些教师则不管三七二十一,不论学生写作基础的差异,统统的“总—分—总”,是不是太简单化、太功利化、太不负责任了?
有些负责任的教师则把这种模式研究到了“极致”。如开头的总起有多种方法;中间的“分”可横向分解,也可纵向展开,甚至每一“分”的段落结构是多少句都有明确的规定;最后的“总”如何出彩有几招,等等。很详细,很具体,就像是模子,学生只管往里面添些颜料,大同小异的画作就诞生了。这让我想起了前些年曾风行一时的“作文魔盘”与“作文克星”软件,以及现在仍甚嚣尘上的各类“快速作文”培训班。人一旦陷入对某种工具的依赖,就会失去独立行走的能力;写作一旦坠入了形式主义的泥潭,形成了条件反射,还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流露出真挚的情感、张扬些许的个性吗?
“总—分—总”模式存在以下几种“异化”现象:
1.“总”不能统领“分”。一题为《腾飞的“90后”》的习作,开头是概括性的两句话:“‘90 后’,拥有年轻的风采;‘90后’,拥有自信的胸怀。”这两句有明显的逻辑错误:“自信的胸怀”属于“年轻的风采”的特征之一,属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并提,令人费解。作者到底是要表现“90后”“年轻的风采”呢?还是要表现“90后”“自信的胸怀”呢?从下文所写来看,作者举了三个事例:汶川大地震中的救人小英雄林浩、与病魔作战的“90后”作家子尤、2008年奥运会举重冠军龙清泉。林浩的事例主要表现“90后”的沉着镇定、临危不惧;子尤的例子主要表现“90后”的坚强、敢于直面人生的不幸,以及张扬着生命激情的自信;龙清泉的例子主要表现“90后”的自信。“总”难以覆盖“分”、“分”与“分”之间(后两例)又重复着同一点。这是一篇蹩脚的“总—分—总”结构的文章。根源就在于写作时的唯形式化造成了思维的游离,或者说作者写作时精力聚焦于“形式”而忽略了对“内容”的加工整合。
2.“拼盘”现象。主要指几个“分”之间缺少内在的必然联系,貌合神离,数典型的“拉郎配”。一篇题为《相信“90后”》的高分作文,主体部分有三个分论点:①“‘90 后’独立、有主见”;②“‘90 后’有很强的理财观”;③“‘90后’开朗、自信”。第二点与另两点就不应该出现在一篇作文里。因为“独立、有主见”与“开朗、自信”属于性格、品格等精神方面的元素,而“有很强的理财观”则属于生活方面的认识,将这些不同种、属的内容“拼”在一起,让人感觉不够协调,就如让穿着军装、礼服、休闲服的几个人一起练习队列一样。
有的教师时刻不忘提醒学生要学会从几个方面去具体阐释文题,但这几个方面如何设定,则只教给简单的物理标准,有的甚至付诸缺如。缺少有效的事理逻辑方面的思维训练,在“分”的设定上出现不合逻辑、违反事理的现象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更有甚者,有的教师居然教给学生“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的绝招,即让同一句或表明观点、或抒情议论、或点睛升华的话在每个例子后反复出现以刺激阅卷者的眼球儿,提醒阅卷者“我没跑题”。这样的指导太过于“形而下”,对大多数有一定写作基础、肯于动脑的学生而言是毫无意义的。
3.思维的“平面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作文题的阐释只停留在表层,不能抓住问题的关键,也不能层层深入地揭示问题的本质。以“人之常情”为题作文,有个考生写的是“哭,是人之常情”,接着便列举了古往今来名种不同的“哭”:李煜是低吟,杜甫是哭诉,李清照是悲戚的叙念,林黛玉哭得一塌糊涂,陈子昂则对天地哭出内心的不满。且不论这样写是否偏题、是不是“掉书袋”、是否情感矫揉,凭其肤浅的内容,就不应该得“满分”。一般情况下,从阐释解说的角度写“人之常情”,应从分类、特征、例示等方面入手,然后进一步做心理的、文化的、社会的深层解读。这对考生的阅读积累、思维深度及考场应变能力要求较高。二是习作的整体思路缺少层递性。要知道“总—分—总”中的两个“总”的含义是不一样的,第一个“总”是总说、总起的意思,一般的写法是以恰当的方式引领全篇,或是开篇点题,明确文章的基本观点;第二个“总”是在前文具体展开的基础上,或总括全文,或点睛升华,或进一步指出做法;但绝不应只是简单地重复前一个“总”的内容。这种“总—分—总”模式,全文是一种层进关系,与以前我们常言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有相通的地方。可惜的是,这样的“常识”如今却被一些教师忘得一干二净了。
那么如何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思维训练呢?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尤其是要收到实效很难。我认为,干巴巴地给学生一些思维分析的方法不会产生多大的效果,教师要先掌握并能具体运用相关的思维分析方法,然后再将自己思维分析的过程展示给学生,日积月累,这样的示范才会渐渐转化为学生的写作能力。
以“相信自己”为例,若写成议论文,确定“相信自己才能成就人生辉煌”的中心论点后,还要考虑哪些问题呢?①要在哪些方面“相信自己”,即相信自己什么;②“相信自己”与“成就人生辉煌”二者之间的连接点何在,即“相信自己”会产生怎样的积极作用进而“成就人生辉煌”;③写这篇文章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即文章最后的落脚点在哪里。
在实际写作当中,有的考生可能在确定中心之后,就只能想到具体的事例。怎么办?教师要教给他们加工处理事实材料,从中提取关键信息加以概括、凝练的方法并做有效练习,使之成为自觉的习惯。可惜的是,这种“由具体到抽象”的分析方法同样也被很多人抛弃了。
有个考生写“相信自己”举了李斯、贝多芬、泰格·伍兹三个事例。应该说这三个例子的选择较为恰当、新颖,如果加工得法,可以写出材料充实、分析具体、层次感强的佳作;但习作者对这三个材料的处理只停留在“他们都是相信自己而成功”这一点上,给人以堆砌材料的感觉。那么,应该如何处理这三个材料呢?李斯原来只是上蔡一个小小的狱卒,后来做了秦国的宰相。他的人生轨迹陡转的原因很多,如个人的才能、不懈的努力、天赐的机遇等等,也与其“相信自己”的心态有很大关系;贝多芬在耳聋后写出大量不朽的音乐作品原因也很多,如高超的音乐造诣、扼住命运咽喉的坚韧等等,同样与“相信自己”的精神关系也很大;泰格·伍兹成为当今的“高尔夫之王”,原因有自己的天赋、科学的训练、过硬的计算能力以及“相信自己”的心理素质等。写作时要考虑的是,“相信自己”这句话在三个人的成功中所起作用的“着力点”有何不同?“相信自己”让李斯确定了高远的人生目标,让贝多芬能经受命运的考验,让泰格·伍兹全身心投入到科学的训练中。这样,三个材料就是从不同角度来阐释“相信自己才能成就人生的辉煌”这一中心,文章就是立体的。
教师不是不可以给学生“写作模式”,而是要在科学思维训练的前提下,让学生养成根据具体写作内容选择恰当的文章形式的习惯。但无论如何,“单打一”的套路训练、“唯模式化”训练都是不可取的。
二、“例子”能证明什么
前文所言之《腾飞的“90后”》,选取三个事例来证明“90后”是“腾飞的一代”,其思维的出发点应是“事实胜于雄辩”。实际教学中,“多用例子”也的确是某些教师指导写作时强调频率最高的一点,高考阅卷时发现这类例子组合拼接式的习作实在是大有拥趸的。
写作文当然可以用例子,例子选得好、用得巧无疑会令习作内容充实、分析具体,从而得个理想的分数。而选得好、用得巧应该是建立在对作文题全面、深入分析的基础之上。审题立意靠的是高质量的思维分析,只凭“感觉”或“感性”写出来的作文就可能变成简单的例子叠加,甚至有可能写成表面冠冕堂皇但却经不住推敲的“伪作”。
以“我说‘90后’”为例,写作前要尽可能丰富地解读、还原出试题(尤其是引导语)的明示及隐含的信息。对“90后”,材料提供了社会上的三种态度,但社会赞扬嘉许什么,担忧什么,“90后”“自己的方式”有哪些,材料语焉不详。而对这些问题的清晰化、明朗化决定着写作指向的清晰度、内容的充实具体感。还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要清楚,就是作文题所言之“90后”应该指的是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青少年中的绝大部分 (特别出色、少年得志的不算,特别不成器甚至违法犯罪的也不算),赞扬、鼓励、批评、否定、辩解等等,都应是对这些人而言。所以,切不可用“90后”中的那“一小撮”人(“最优秀”与“最不优秀”)的表现来“以偏概全”地评说“90 后”。《腾飞的“90 后”》恰恰就在这一点上犯了错,林浩、子尤、龙清泉是“90后”中的佼佼者,但不能据此说“90后”全都如何如何;就像不能因为“90后”中有自杀、吸毒、犯罪者就因此说“90后”全都如何一样。一个年龄段人群的两个端点其实是这一群人中的“特殊分子”,一般情况下是不能作为解剖这一人群基本特征的“样本”的。
总之,要证明某一集合有哪些特征,应该以这一集合的大多数元素为参照,这是毋庸置疑的。要证明“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就要以从古而今几千年中的大多数中国人为例,用他们追求真理、不惧艰难等方面的表现来印证,若只是用文天祥、不食嗟来之食者、闻一多的例子,就只能证明“部分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因为我也可以举出秦桧、吴三桂、汪精卫的例子来证明“中国人没有骨气”,当然我证明的对象同样也只能是“部分中国人”。其实,吴晗《谈骨气》中举这三个例子的作用是对“骨气”的内涵做具体的“解释”或形象的“示范”。对作文题(或题目中的关键词)做具体解释或示范,是“例子”在文章中的另一种作用。
也许有的教师会替习作者辩解,说人家写的是散文,是对“90后”的礼赞,没必要照搬议论文的那一套。不同文体(包括散文与议论文)写作的具体操作的确有大不同,但笔者所言的是写作的一些共性问题,比如审题立意过程中的思维要求。即便是散文,还有个“形散神聚”的常识在。以茅盾的《风景谈》为例,这是一篇典型的“画面组合”式散文,文中的几个画面尤其是延安军民生产、生活的画面是作者从无数个类似的细节中精心剪取出来的,是具有“普遍性”“一般性”的画面,能够“以点带面”地反映延安军民的日常生产生活的状态。话说得再明白一点,茅盾先生所选取的“例子”都是延安最普通的“普罗”的事例(生产归来的士兵、石洞里学习的青年、晨光中的号兵等),这样才能尽可能真实地反映延安的面貌。当时延安有没有搞特权的、有没有心怀不满的、有没有好吃懒做的,肯定有,但那属于“特殊分子”,不是主体,当然不能作为延安的“代表”了。
退一步讲,写“我说‘90后’”用《腾飞的“90后”》中的三个例子也并非绝对不可以,但若达到“用得巧”的标准,还需在提高思维质量上下工夫。考题中的“说”应是论说、评说义,所以在“叙”例的基础上,必须“说”出林浩、子尤、龙清泉三人能有“上佳表现”的根由,即家庭教育、社会环境、个人毅力与意志等因素对他们成为“腾飞的一代”起何作用,有了这些分析,才会给读者尤其是其他“90后”以人生的启迪,进而走好今后的路。但由于写作者对作文题的认识只是停留在肤浅的层面,文章就只能变成简单的事例“叙说”而不是“评说”。
其实,问题还出在习作者对事例的选取上所犯的一个“隐性错误”——颇有些中学生患了此“疾”而不觉。由于对所选事例(及人物)局限于媒体的报道,没有更详尽的了解,所以也就只能人云亦云地重复着媒体上的言辞;如果能够选取自己熟悉的“90后”的相关事例即第一手资料,就“能”或更“容易”做出具体的或较深刻的分析。动辄大谈天边的云彩、畅游历史的天空,就是对身边的小树视而不见,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倾向是应该引起师生们的重视与反思的。
由此我想到现在一种颇为“流行”的文体,有人将其称为“散文化议论文”。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文体在很多时候“蜕变”为堆砌材料、华而不实、无病呻吟的形式主义的“畸形儿”。在某次全国级别的作文课堂教学大赛上,一位教师推荐给学生的题为《拒绝诱惑》的“范文”居然就是这样的一篇“不范之文”。文中列举了吴王夫差、邹忌、赵威后、陶渊明、庄子、司马迁、朱自清、史铁生等事例,本意是从正反对比中强调拒绝诱惑的重要意义。但却写成了典型的“掉书袋”文章,而且其中有些材料是乱“堆”一气。比如文中所举赵威后送儿子去做人质的例子,其实质是为大爱而舍小爱,可作者却说成是拒绝“母爱私情诱惑”;而司马迁,又何曾受到什么“诱惑”,他是因与李陵关系甚好且认为朝廷对李陵不公说了几句辩解的话而已,算不得抗拒“皇权意志”,他的遭遇与“诱惑”根本不搭界。徐江先生指出,这篇谈拒绝诱惑的文章本身就表现出作者受“诱”而“惑”,他受“高分”的“诱惑”置历史事实于不顾恣意修改!这种为了自己的需要说大话、编历史的学风、文风是极不可取的。而教师却对这种风气“推波助澜”,既有“眼力”不够的原因,更有失去“理性”的因素在内。先人云:术,不可不慎!为人师者应深思之。
离开了“思维”的调控,“例子”就成了干巴巴的沙子。所以,写作训练首先是思维的训练,为人师者须切记。
三、“精言妙语”的背后是思维的缺席
“流水线作文”的语言表达有两种不良倾向值得注意:
1.多生硬的口号式语言。貌似气贯长虹,实则空洞无物,禁不起思维的检验和逻辑的推敲。如《腾飞的”90后“》在叙述林浩的事迹后,作者用一句“他表现出的沉着镇定、坚强勇敢,是如此让人动容”概括了林浩超人的精神品质,按一般的思路,接下来应指出这种品质在大多数“90后”身上有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表现,这样习作也就多多少少有了些“好作文”的味道。可是紧接着作者却用一个独立的段落写道:
“他用可贵的心,非凡的勇气,顽强的意志,感动着全国人民,感动着世界。”
口号式的语言重复着前面的内容,从中可见那种极端功利而拙劣的“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的“反复点题”式技法的影子。
再如“青春的豪迈,人生的痛苦,毫不畏惧的神情,造就了‘90后’的子尤,也造就了一批的‘90后’。”多有气势,多么豪迈,“造就”了子尤尚可理解,“造就了一批的‘90后’”则是典型的“贴标签”,属于无可稽考的判断。且“毫不畏惧的神情”又怎么能“造就”子尤与“90后”呢?类似的还有“他们,举出世界,举出未来”“用新时代的情怀创造又一个崭新的时代”等等。写作不是演讲,不是集会,不是誓师,还是具体述说、娓娓道来更“得体”些。至于何谓“举出世界,举出未来”,我真的不明白,是不是“90后”都要去练举重?
文中还有一些“正确”的废话,实有凑字数之嫌。当写作者不能对所谈话题有自己的独到认识,却必须要写出800字来交差的时候,就只能说些“放之四海而皆准”、人云亦云的空话、套话。“‘90后’正在迈向新的时代”,说得对极了,不止“90 后”,“80 后”、“70 后”、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在迈向新的时代,哪个有本事开历史的倒车?“他是年轻的‘90后’,成长中的‘90 后’”,林浩 1999 年出生,今年才10岁,绝对“年轻”(准确地说应是“年少”),绝对在“成长中”,且成长的时间、空间不可限量。
2.多华丽浮泛的语言。最常见的是生拉硬拽贴标签,将作文题“泛化”,以自己所掌握的事例牵强附会之。题目是《传递》则古往今来人事景物无不在“传递”着或被“传递”,题目是《熟悉》,则理解、了解、深知、精通等等就都成了“熟悉”的同义词;然后以透视上下五千年的姿态发思古之幽情、论天下之兴替。且看“高分作文”里的几个语段:
①传递,就是诗仙李白夜深人静时低吟“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乡情;传递,就是婉约派代表李清照在深秋时节留下的“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哀愁;传递,就是爱国诗人闲居山阴时发出的“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的愤慨。
②一曲幽径,蜿蜒曲折中不忘把空白传递下去,让人遐想空白之余应该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旖旎风光;一波微澜,剥脱汹涌后不忘把空白传递下去,让人神游空白的意境背后“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雄浑壮阔;一方净土,沉思默想中不忘把空白传递下去,让人渲染空白的色彩应该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奇异。
③因为苏轼熟悉“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熟悉政治上的失意、挫折,熟悉表达内心喜悲的方法,所以他留给中国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因为鲁班熟悉技艺的精雕细刻,熟悉各种机械的奥秘,熟悉自然科学的知识,所以他留下了技术上的一个个神奇创举。因为邓小平熟悉中国应该走的道路,熟悉老百姓心中的希望,熟悉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所以他留下了南海边一个造福后世的圈。
④于是,孔子毅然放弃从政的初衷,开始整理和收集古时名作佳篇,自己从中吸取知识。皇天不负苦心人,因为孔子依然放弃自己熟悉的从政之路,挑选了适合自己的文学大道,终于成为一代宗师,成为古今闻名的教育家、思想家,给中国乃至世界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语言不能说不华丽,文辞不能说不丰富,句式不能说不整齐,语势不能说不贯通。但细细品味,教了这么多年的语文,还真是自愧才疏学浅,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传递”居然就是乡情、哀愁、愤慨,“空白”的被传递居然能令人如饮醇浆般回味不已,孔子居然成了“文学宗师”,其成为教育家、思想家居然是在“放弃从政”之后!读罢,愚钝的我真想找个地缝儿钻进去。
管然荣、任海霞在《经世致用文 为时为事著》一文中将不良文风的主要症状概括为:绮丽浮华,朴素稀缺;笼统空泛,脱离生活;虚情假意,矫揉造作;故作沧桑,迷失本色;随意散漫,文体淡漠;强词夺理,逻辑混乱;典故堆砌,诗文乱配;一知半解,刚愎武断。责任不在学生,因为有些教师一直在鼓励学生写类似的文字。他们“常常被满纸眼花缭乱的‘精言妙语’扰乱了方寸,见几句漂亮词句已然陶醉,再见一堆古诗文,便拍案叫绝起来!而那些朴实本色的文章,却轻易被打入‘冷宫’,以致名落孙山之后”。教师作文观上的迷失,客观上对这种文风的泛滥起到了助推的作用。
言为心声。古人在两千多年前就主张“修辞立其诚”,注重语言表达是为了准确、恰当地抒发情感、传达思想。《文心雕龙·情采》篇说得更明白:“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思想感情是文采的经线,言辞是思想内容的纬线。只有经线正了,用纬线才能织成布帛;只有思想内容确立了,语言才能通达流畅。而“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为了抒发感情而写的作品,语言简练而真实;为作文而造作感情的作品,文辞繁杂且空泛失真。抒真情实感,写独到感受,历来是为文之要旨;以最恰当的语言形式传达自己的思想、情感,是从古到今一以贯之的“好文章”的基本标志。教师切不可在“现实功利面前”遗忘了常识、淡薄了自己的责任。引导学生多读、善思,观察、感悟,培养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提升分析问题的实力,强化感悟现实的敏锐,让学生“有话好好说”,是矫治“流水线作文症”的唯一良药。
李玉山 北京师范大学天津附属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