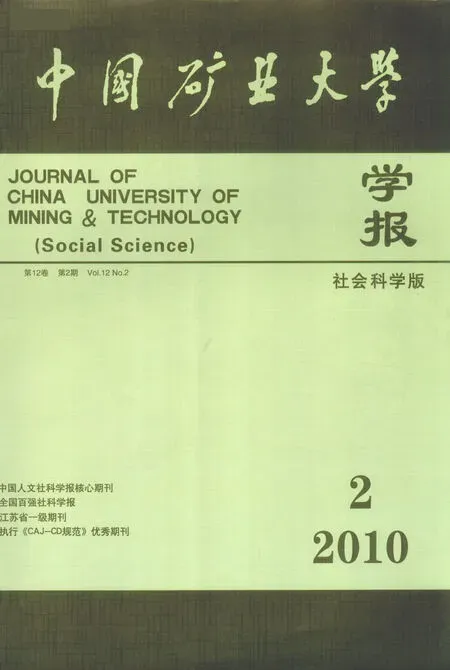行政判决既判力之基准时
田勇军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行政判决既判力之基准时
田勇军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行政诉讼判决既判力仅就诉讼过程中某一时间点(基准点)之前的被诉行为或状态具有遮断效,对该时间点之后的事项不具有拘束力。与民事诉讼以事实审口头辩论终结时之基准时不同,行政诉讼中应以被诉行政行为性质为标准,结合判决类型对既判力的基准时进行划分。对积极行政行为、显失公正行政行为判决的既判力基准时应该是行政行为成立时。对消极不作为行政行为的履行(或给付)判决的既判力基准时为事实审口头辩论终结时,而对其做出确认判决的既判力基准时是行政行为成立时。对行政法律关系和行政事实行为诉讼之判决既判力基准时均为事实审口头辩论终结时。
既判力;既判力基准时;积极行政行为;消极行政行为
一、引言
确定的终局的司法判决具有法律效力,在学理上被称之为既判力。目前国内通行的观点认为,既判力是确定判决在实体法上对于当事人和法院所具有的强制性通用力,表现为判决确定后,当事人不得就判决规定的法律关系另行起诉,也不得就同一法律关系提出与本案诉讼相矛盾的主张;同时,法院亦不得做出与该判决所确定的内容相矛盾的判断①关于既判力概念的观点可以参阅:江伟《民事诉讼法专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邓辉辉《既判力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日)栗田隆《民事诉讼法讲义》,有斐阁2001年版,第258页,等等。。在内容上,既判力包括三个方面,即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客观范围以及时间范围。所谓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就是既判力对哪些人有效、可以约束哪些人。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就是既判力对哪些事项具有效力,而既判力的时间范围则是确定终局的判决对哪一个时间点上之事项产生效力,一旦该时间点经过后所发生的事情不受该判决的拘束。主观范围、客观范围和时间范围三大要素共同支撑着行政诉讼理论。
相对来说,判决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和客观范围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判决的既判力功能主要体现于出现后诉纠纷时,对于其是否和前诉已解决纠纷是否为同一事项(即客观范围)和针对同一当事人(即主观范围)之判断。但是,为什么对于相同的主体之间同一纠纷事项会因为某个时间点的经过而形成此纠纷和彼纠纷?同样一个纠纷会因时间的发展而变化吗?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分析既判力时间范围的作用。
二、判决既判力基准时的一般理论
时间是单维的,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变化的,作为诉讼标的主要内容的当事人之间权利和义务关系也随时可能产生、变更或者消灭,而从法院的审判来说只有审理对象即这种法律关系固定在某一时间点上,审理和判决才有的放矢。在该时间点之前审理对象如何发生变化,或者在此之后是否变更,均不属于既判力确定的内容,这个时间点就是既判力的标准时或基准时[1](为叙述简便以下仅称其为基准时)。在该时间以前的法律关系就固定在此时的状态,也只有在此时间点上的判断具有拘束当事人提起后诉的作用,在该时间点之后所发生的新情况不属于判决既判力拘束范畴,这种作用学说上又称为既判力对后诉的遮断效果[2]。之所以在该时间点之后的事实或法律状态不受判决既判力约束,因为,“在裁判基准时点之后,判决基础之事实及法律状态如有变更,该变更后之事实及法律状态已非原确定判决中经裁判之事项,即为原确定判决实质确定力所不及。”[3]在基准时点后所生之新事由,既非当事人于前诉中所得主张,自不受既判力遮断效所遮断,并不生当事人于后诉中不得加以主张之失权效。另一方面,从当事人所享有的诉权来说,在该基准点之后新发生的事实,由于双方当事人没有享有充分的辩论、质证等权利,法院也没有对此行使司法审查权,更没有对其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认证,当然不能赋予其既判力。
既判力理论在民事诉讼中的研究较为成熟,在民事诉讼中大陆法系基本一致地认可基准时为“事实审口头辩论终结时”,其理由在于:从口头辩论一体性的角度来看,辩论在其终结时可以作出一体性的判断;从当事人的视角来看,至口头辩论终结时点为止的所有事实应当是当事人能主张的事实[4]。基准点之后的新事由,是当事人无法预知的,因此也是无法主张的,而法院的判决是建立在口头辩论终结时所固定的法律关系和事实上的。此时,案件所有关于事实的信息都已获得固定,法官与当事人进行案件事实信息交流的所有途径都已经关闭,而且法官的心证也已获得固定。如果把基准时定得早于事实审口头辩论时,则可能会剥夺当事人的诉权。反之,如果定得晚于口头辩论终结时,会把一些新的事由不当的纳入判决的范围。所以,以该时间点为基准时是合理的。那么,在行政诉讼中既判力的基准时是否也和民事诉讼一样呢?
三、各种行政行为判决既判力基准时
行政诉讼既判力的基准时与民事诉讼是不同的,最主要原因是审判对象的差别。在民事诉讼中,有一个通行的公式,即“诉讼请求=审理对象=判决对象”,意指民事诉讼中两造双方的法律关系始终是整个诉讼的主体,无论是当事人诉请的内容,还是法院审理的对象以及最终判决回应的对象,均是该法律关系。但是,在行政诉讼中,始终贯穿诉讼的则主要是被诉的广义的行政行为①此处之所以称“广义的行政行为”,是因为行政诉讼的审判对象应该不仅包括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条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还包括行政法律关系、行政事实行为等,确切的说是与行政有关的所有可以被纳入行政诉讼的行为或状态。,无论是诉讼请求,还是审理对象以及判决对象均是以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或不违法性)②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条规定,行政诉讼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确切的说是“不违法”的审查,尤其是对各类诉讼请求的驳回诉讼请求的审查中,并没有也很难做到“合法性”审查,只要“不违法”标准就够了。为中心。由于行政行为贯穿行政诉讼始终,也是诉讼中经常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在讨论行政行为既判力基准时的时候,应该以被诉行政行为或状态为切入点。而行政行为的多样性决定了对既判力基准时的合理界定应该是采取针对不同性质的行政行为采用不同的基准时的方式较为科学、合理。
影响判决既判力基准时的决定因素,除被诉行政行为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判决的种类,因为判决的种类决定了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审查视角。例如,针对同一行政不作为行为,如果要做出确认判决,那么该不作为行为状态在一定的法定期间的经过即是一个完整的被诉讼的行政行为,确认判决重在对已发生的行为或状态的判断,所以该时间点之后的任何行为都不会对其具有溯及的影响;而如果对该不作为行为要做出履行判决,那么,既然诉讼追求的是行政主体的作为效果,则行政主体在法庭调查前的任何时间段内的作为行为都是影响判决的。这就如同刑法中的某一个故意伤害行为一样,如果犯罪主体追求的是伤害目的,则就是故意伤害罪,而如果其追求的是被害人的死亡目的,则可能就是“故意杀人未遂罪”。所以,对同一个事项的视角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法律意义。
按说,判决的种类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相对人的诉讼请求限制的,例如,如果相对人提出了撤销的诉讼请求,那么,法院的判决基本上应该是做出撤销判决或者驳回诉讼请求判决。但是,在行政诉讼中诉讼请求和判决的关系并不是如民事诉讼法那样的存在近乎绝对的“诉判一致”,行政诉讼中的诉讼请求类型是决定法院判决类型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总是如此,例如撤销之诉中的情况判决,尽管当事人提出的是撤销请求,而法院的判决则是“确认(违法)+驳回诉讼请求+行政赔偿”之判决。而且,一个案件最终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通常是确定的判决(或者包括有限的判决理由③笔者认为在行政诉论中判决理由也应该具有既判力。),而不是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另外,当前我国行政诉讼中,很多当事人行政诉讼知识欠缺,诉讼技术不高,难免会选择与被诉行政行为客观性质不一致的诉讼请求,例如对不具可撤销性的行政行为提起撤销。还有就是如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被告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的,法院只能做出确认违法判决或者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而不是当事人请求的撤销判决。基于此,笔者以判决的种类,而不是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作为影响判决既判力基准时的一个因素。
法院审查任何一个行政行为,都只有违法或者不违法两种可能结果之一,不存在第三种情况。对于经过审判认定为违法的行政行为,法院可以结合原告的诉讼请求和审查结果,做出支持原告的判决;如果经过审理认定该行政行为不违法,法院一般会做出驳回当事人诉讼请求之判决。该驳回诉讼请求判决既判力基准时应该随本诉讼拟作出原告胜诉之判决既判力的基准时相同。因为,行政诉讼自法院受理诉讼时起,该被诉行政行为就被假定为不合法,行政机关必须举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自己不违法,是依法行政,否则就是不合法的,法院就会做出支持原告的判决,如撤销判决、履行判决。反之,被诉行政行为不违法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这样,无论判决原告胜诉与否,法院的审理对象和审查程序都是一样的,由此所形成的各种证据认定,判决理由等都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结果。所以,每一个驳回诉讼请求判决既判力基准时都和该诉讼类型中的拟判支持原告的判决种类相同。换言之,原告提出的是撤销之诉,就应以撤销之诉的基准时来认定对待;是给付之诉,就应以给付之诉的基准时认定。基于此,在随后对各种被诉行政行为既判力基准时分析时,不再逐一对驳回诉讼请求讨论。
当然,此前也有学者以行政诉讼的类型、行政判决的类型入手对行政判决既判力基准时进行研究。笔者认为,既判力基准时的确定,关键是取决于被诉行政行为的性质和状态,所以,本文尝试以不同的行政行为为切入点,以期能从中找出比较合理的判决既判力基准时划分规律,下面如表1所示几种类型,分别详述之。

表1 既判力基准时分类表
(一)积极行政行为诉讼之判决既判力基准时
此处的积极行政行为主要是指狭义具体行政行为,即只指行政主体积极的做出某种行政行为,不包括行政不作为、行政法律关系和行政事实行为等。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主要是以对积极的行政行为(即具体行政行为)的撤销为主而设计的,这一方面说明了撤销之诉在各诉讼类型中占有巨大的比例,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设计的粗浅。
笔者认为,针对具体行政行为诉讼的判决既判力基准时不同于民事诉讼既判力基准时。首先,民事诉讼强调私权自治原则,民事主体可以自由地、随时地处分自己所享有的权利,即便是在诉讼中具有国家公权力介入情况下。同时,民事诉讼立法采取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5],当事人在诉讼的任何阶段都可以提出证据,都可以反复地认可或否认相关的事实。所以,在民事诉讼中作为审判对象的双方的民事法律关系一直处于变动不居的不确定状态。因此,只有在判决前的最后阶段——事实审口头辩论终结这一时间点上,把这个流动的诉讼靶子冻结、固定较为合适。而行政诉讼中,虽然判决应该是针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但是行政诉讼审理的对象主要是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所以,被诉讼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就成为行政审判关注点。基于依法行政的理念,行政行为的作出必须有法律依据,即有法定的职权、程序、条件等。行政机关在作出某行政行为前,对于做出该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应该已经搜集齐全,即所谓的“先取证,后裁决”。所以,一旦行政行为完成,该行政行为的合法与否的状况就已经固定,这显然不同于民事诉讼审理的对象是在口头辩论前一直处于变化中的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其次,基于行政权的侵略性、扩张性、难以控制性以及当事人距离证据的远近等因素,为了矫正当事人双方诉讼外地位的不对等,诉讼中举证的主要责任由被告行政主体承担。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对此也明确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这是从正面规定了法院在行政审判过程中只应以行政主体所提供的证据和规范性文件作为判断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依据[6]。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项规定,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根据,该解释的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一条对复议机关在复议过程中收集和补充的证据也明确作出排除适用规定。这些则从反面排除了行政行为成立后所获得的所谓的证据,其与英美国家的“案卷外证据排除规则”有着相同的理论。所以,无论从正面规定的“先裁决,后取证”,或是从反面的“后续证据排除”规定,都把主要的行政判决既判力的基准时限制在行政行为生效时。
对于具体行政行为之诉讼,法院作出的判决可能是以下几种情况:行政行为违法→撤销判决、撤销重做判决、确认违法判决;行政行为不违法→驳回诉讼请求(维持判决)、确认合法或者有效判决①笔者认为维持判决,确认合法或者有效判决不符合行政诉讼的理念和合理的制度设计,此处把其列出,只是出于现实中该判决种类的暂时存在,并不代表笔者赞成该判决的合理性,后文论及该两种判决时亦同。。
(二)消极行政行为诉讼之判决既判力基准时
此处的消极行政行为是指从状态上来说,是与前面的积极行政行为相对而言,通常指行政不作为行为,不过这里的行政不作为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行政机关不履行或者怠于履行某种行政行为的纯正不作为,如不理会当事人的行政许可申请,不给付当事人法律上应当享有的财物;另一种是不当的拒绝作出某种行为或者给付,如拒绝行政许可,拒绝给付等。当然,如果从程序方面判断拒绝履行的行为应该属于作为形式的具体行政行为,因为拒绝本身就是一种作为。而此处之所以把拒绝行为和纯正的不作为一并归类为消极的行政行为,是从实体内容方面的考虑,即从内容上说,“拒绝的言行是一种方式上有所‘为’,但其反映的内容则是不为,实质上仍是不作为,[7]”其实也就是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拒绝可能在实体上不是真正的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从这一方面来说,它和行政不作为行为是一样的。当然,本文把拒绝行政行为归属为一种不作为行为,只是为了对判决既判力基准时判断的工具性需要,并不代表主张该种观点。
自始的不作为与拒绝的不作为都是一种持续性的状态,该种状态随时可能会因为被诉行政主体的作为而打断,针对该种状态,只能有两种类型的诉讼,一是要求改变该不作为的状态,即履行之诉和给付之诉,一种是确认该不作为状态违法,即确认之诉。
首先,履行或者给付之诉所针对的是消极不作为行政行为,这种不作为处于一种持续的状态,随时都可能因为行政主体的履行行为而中断,如果我们对某一行政不作为提起履行或者给付之诉,那么,假如行政机关在行政行为生效到一审事实审口头辩论终结前的任何时间作出履行或给付行为,则诉讼的目的其实已经达到,如果此时法院仍以过去的生效行政行为为审判对象,一方面已经失去了诉讼的意义,另一方面,如果强行作出履行或给付判决,则相对人可能会得到二次给付,这显然有违司法公正的初衷。所以,针对不作为状态的可随时变更性,应该把该类行为的诉讼判决的基准时设定于事实审口头答辩终结时,是德国的通说,也为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所赞同[8][9],因为该类诉讼与民法有着类似的原理。
其次,对于同样的不作为行为,如果是提起确认违法之诉,则因为其对不作为行为的关注点不是如前所述对不作为行为的改变,而是追求对该不作为的违法性质的确认,则该不作为状态就应该从其成立并生效时得到确定。我国行政诉讼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复议机关不作为的状态只要延续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即可成为行政确认之诉的司法审查对象。最高人民法院对《行政诉讼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八条也规定了行政不作为行为的状态持续60日即为可诉。如果当事人只是为了追求对该不作为行为的违法性予以确认,则该不作为法定时间段的结束即是一个完整的可诉的对象,随后行政主体是否会主动作出履行则非为相对人所关注,基于审理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受诉讼请求的限制,则行政审判也只是关注不作为行为的违法性,而不是在不作为行为成立至判决前之期间内是否被改变,所以,不作为行为的确认判决既判力之基准时应该是不作为行为法定时间的消耗结束之时——不作为行为成立时。
对于拒绝作为的消极不作为,只要行政主体作出的拒绝行为达至当事人即成立。其实,对该拒绝作为行为的确认违法诉讼具有对积极的行政行为的确认之诉具有相同的道理,所以,其既判力的基准时也是行为发生法律效力时——不作为行为成立时。可以看出,尽管从性质上说,纯正不作为行为是经过一定的法定期间生效,拒绝作为的不作为行为是拒绝通知达至当事人即生效。但是二者的既判力基准时都是行为成立时,即可以获得法律上对外效果状态的固定时。
(三)显失公正行政行为诉讼之判决既判力基准时
从性质上来说,行政行为的显失公正属于滥用职权的一种表现,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中,变更判决是专为解决行政处罚显失公正而设置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目的性。显失公正按说属于合理问题而非合法性问题,是一种行政裁量权的瑕疵,不属于行政诉讼的范畴。但是由于其“显”失公正程度极其严重,显到为司法不能坐视不管,不合理的显失公正达到一定的“量”,使得其发生“质”的变化为不合法。但是,对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判决面临很多困境。一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越过边界的干预,无疑会对司法与行政的关系问题提出了难题;一是显失公正标准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另一个就是结合我国为什么只对行政处罚的显失公正可以变更,其他行政行为的显失公正就不能作出变更判决呢?针对此,不少学者也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和观点[10][11],主要是扩大可诉的显失公正行政行为至所有的行政行为。另一个就是扩大对显失公正行为的判决种类,包括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发回被告重新考虑,法院可以向被告提出司法指导性意见,必要时,可以判决变更等[10]。本文重在讨论作为一类被诉的行政行为之判决既判力基准时,仅关注该类行为的性质和状态,所以对于这些观点只表示赞同,不做过多论述。
既然显失公正被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除了属于“不合理”范畴之外,和其他积极行政行为特征完全相同,其既判力的基准时于作为的行政行为是相同的,即行政行为发生法律效力时,所受限制之处是对该种行政行为只能作出变更判决,如果经审查不存在显失公正的情况就要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当然这只是我国法律当前的规定,不一定合理,不过从对显失公正行为的判决增加撤销判决和撤销重做判决的建议来看,也说明了其与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同样的特征,具有相同的判决既判力基准时。
(四)行政法律关系诉讼之判决既判力基准时
在民事诉讼中,有关当事人法律关系的诉讼比较常见,尤其是确认当事人的身份关系,因为有些时候一旦法律关系确定,与此有关的财产或者其他纠纷都会随之明晰化而迎刃而解。在行政诉讼中,行政法律关系的确认之诉目前不多见,尽管在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确认之诉中均包括对法律关系成立与否的确认[12]。行政法律关系是由行政法所调整的具有法律意义的权利义务关系,它包括法律规范和法律事实两个因素。单纯的确认某种行政法律关系存在与否并不直接改变当事人双方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也没有达到实现行政诉讼解决纠纷和权利救济的目的,所以通常在对行政法律关系的诉讼中会一并提出确认违法与赔偿请求,法院也通常是对该确认之诉和赔偿诉讼一并判决。其实,行政法律关系与前面提到提起履行或给付之诉的不作为行为有着完全相同的特征,即都是某种权利义务关系状态的持续,所以,对于行政法律关系提起确认之诉的既判力基准时也是事实审口头辩论终结时。无论作出确认判决或者是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
(五)行政事实行为之诉讼判决既判力基准时
行政事实行为是指行政主体以不产生法律约束力,而以影响或改变事实状态为目的实施的行为[13]。从分类上来说,尽管在行政法理论上可以对事实行为有不同的理解,但基于我国法律原则和法律规范体系,我们还是能够判断,所谓的事实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法所指的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14]。当前,虽然人们对行政事实行为特征认识不尽一致,但是对于其具有行政性、可致当事人损益性特征从而应该纳入行政诉讼救济范畴来说,人们的看法还是基本一致的。行政事实行为的内容虽不直接设立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但这不等于说其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不会产生实际影响。近年来随着行政法治进步和行政诉讼技术的提高,基于有损害就应该有救济的原则,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在司法实践中都已经对行政事实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了救济。
从行政事实行为的性质来说,有些行政事实行为一旦产生可能马上就会对当事人造成损害。例如错误的公布当事人违法马上就会使当事人的名誉受损;有些事实行政行为的状态持续存在,可能在经过不确定的时间段后才会出现损害当事人利益的情况或者后果,例如行政机关错误的设置路标,可能在某个不确定的时间会有人因该错误路标指引出现损害后果。无论是行为性或者是状态性行政事实行为,只要对当事人造成损害,当事人就可以对此提起诉讼,关键是当事人提起诉讼的种类决定着该诉讼判决既判力基准时的设定。从理论上说,对行政事实行为可以提出停止作为之诉(如英国的阻止令injunction)和赔偿之诉,但是,我国行政诉讼中并无停止作为之诉①在德国,其基本法第19条第4款第1句规定的防御请求权向行政法院提起停止作为之诉,要求判决行政机关停止作出或中止违法的事实行为。该诉是一般给付之诉的亚类型。参见(德)胡芬:《行政诉讼法》,莫光华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95-300页。。有学者认为可以提出确认之诉,笔者认为,由于行政事实行为是行政主体的非意思表示行为,只有对外发生损害的法律效果时才具有可诉性,而且行政事实行为并不以违法为要件,所以,不能对行政事实行为提出确认(违法)之诉。这样,在我国,对于行政事实行为只能提起赔偿诉讼,那么基于行政主体在事实审口头辩论终结前的任何时间都可能主动履行行政赔偿从而使法院的审查对象——行政主体之事实行为造成损害且不予赔偿之事实——发生改变,相对人的诉讼请求也会随之可能完全或者部分失去意义。所以,应该把该种诉讼判决的基准时设定于事实审口头辩论终结时,这其实与对行政不作为状态提起履行之诉有着相同道理。
基于此,对不同的行政行为之判决既判力具有不同的基准时。
[1] (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M].林剑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479.
[2] 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376.
[3] 翁岳生.行政法(下册)[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1412.
[4] (日)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M].林剑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488-489.
[5] 左卫民,陈刚.证据随时提出主义评析[J].法学,1997(11).
[6] 邓辉辉.行政判决与民事判决既判力时间范围之比较[J].广西社会科学,2007(8).
[7] 陈小君,方世荣.具体行政行为几个疑难问题的识别研析[J].中国法学,1996(1).
[8] 陈计男.民事诉讼法释论[M].台湾:三民书局,2000:570.
[9] 吴庚.行政争诉法论[M].台湾:三民书局,2005:213.
[10] 余凌云.行政法上的显失公正与变更判决》[J].法商研究,2005(5).
[11] 关宝英.行政行为显失公正再认识[J].政治与法律,2009(7).
[12] 吴华.行政诉讼类型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303.
[13] 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第三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364.
[14] 龚钰淋.行政事实行为救济制度研究[J].河北法学,2010(1).
Res Judicata Time Point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Judgement
TIAN Yong-jun
(Law School,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The res judicata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judgement just has effect on the things before the time point.The res judicata time point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judgement is different from the civil litigation judgement.The time point of th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judgement was decided by the administrative action and the different types of judgements.The point of the judgement to positive administrative action and injustice administrative action should be at the time“when the administrative action is formed”.The point of the judgement to negative administrative action should be“when the action is formed”to administrative fulfill ment judgment and should be“when the court debates of the litigants are over”to declaratory judgement.The point is“when the court debates of the litigants have been over”to the judgements on administrative relationship and administrative factual action.
res judicata;res judicata time point;positive administratve action;negative administrative action
D912.1
:A
:1009-105X(2010)02-0055-06
2010-04-23
田勇军(1972-),男,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