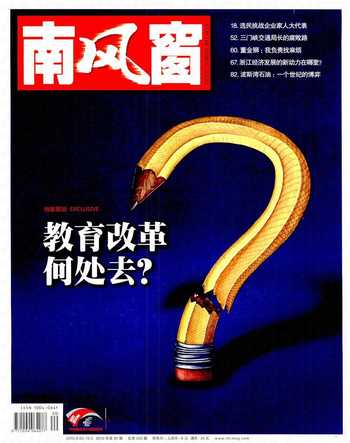关于村委会的立法争论
仝志辉

2009年12月和2010年6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草案还公开向社会征集意见。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审议本来是有关村民委员会设立和内部管理的一部法律,但是,由于草案充实了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拔出萝卜带出泥”,委员们进一步的争论是否要将村民委员会和集体经济组织的不同主体性质和相应的管理职责明確分开。在已经公开的常委会成员意见中,压倒性的意见是要分开。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经研究认为,这个问题涉及的情况比较复杂,各地做法也有差异,拟在进一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意见。有的委员将其理解为“在此次修订草案中对此问题存而不决了”。
委员们提出在法律上明确村民委员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不同性质,甚至要界定两者关系,起因于在现实中要明确集体资产管理的主体是谁。在10月份可能的17次常委会三审中,这仍将是一大焦点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全国近60万个村庄的村级组织制度设计,对于相当比例的村庄中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现实权益将直接带来影响。对于一项事关农村基层治理、村民自治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重要法律,靠两次常委会会议上各半天的审议,也很难讨论出一个周全的意见。此时,对此问题细致、深入的讨论应该成为必须。
对多数村庄而言,维持现有规定并无问题
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村民委员会的成员边界和管理内容是如何出现差别的?搞清楚这一点,也就搞清楚了人大常委会上明确两者区别的辩论日益激烈的原因。
1986年的争议是主要出于对组织性质问题的辨清而起。因为那时的村委会对全国绝大多数村庄而言是一个拟议成立的组织,因此,需要把它和已经存在的“集体经济组织”辨清关系。1998年九届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村组法时,对争议做出维持试行法规定则是因为实践中问题暴露还不很激烈。1998年11月,民政部有关官员在《中国社会报》发文《村委会组织法修订中的四大争论》,将“村委会是否应当有管理集体经济的职能”作为四大争论之一。当时的情况是,“在这个问题上,绝大多数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村委会应当有管理集体经济的职能。”因此,当时通过的法律只对试行法中的个别用词进行了修订,沿用了试行法“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这一规定。
现在的情况则是,村委会在全国绝大多数村庄已经建立,但已经有40%的村庄中单设了集体经济组织,60%的村庄则是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会“合二为一”,“合二为一”的村实际上并无集体经济组织更多的经营管理活动,除了土地发包以外没有其它集体经济组织活动。集体经济组织在60%村庄中已经“名存实亡”。
在60%的村庄中,土地承包、宅基地分配这样的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活动由村委会代为行使,并不会产生多少问题。因为,以往存在的村干部多留机动地、任意调整土地、专权分配宅基地、侵吞承包费和宅基地使用费的问题在村民自治制度下也是不容许的,如果贯彻村委会组织法中有关由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决策和监督的程序规定,就不会出问题。而且,土地承包和宅基地分配作为与全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每家每户都有关的更强调公平和公正的事务,也是适用于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这样的民主规则的。
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委员会的性质区别和职能划分问题,更多是在40%的村庄中才成为问题的。也就是说,只有在本村村民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差异较大,或者在工商业活动发达的集体经济组织中,才有明确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分设村委会和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组织的必要。
这样的村庄在今天中国的村庄中,毕竟还是少数。因此,拿一种并不多见的情况来要求做法律修改,第二次提交审议稿未作回应也在情理之中。
“无风不起浪”
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委员会在管理集体财产上是否需要明确权力性质、归属和产生方式的问题,主要出在以下两个场合:一是集体所有的工商业资产发达,管理活动变得复杂;二是集体土地因为城市化带来升值和新农村建设对于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而使得可分配收益数量巨大,如何分配收益变得复杂。
在以从事工商业为主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由于事实上属于村庄集体组织成员的既得利益巨大,产生了仅仅只是拥有本村户口但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有无分享资格的问题。由于村庄工商业发达,拥有本村户口的村民的数量多数情况下就会大于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数量,多出的村民可能是长年在村里打工或经商的人,或是来村庄中买房置业的人。工商业发达的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进行明确的股份合作制改造或者通过村规民约,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收益的分享资格和比例。拥有分享资格的村民即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有拥有本村户口的村民,在现行法律规定中是村民自治组织的成员,但是,其中有些则不被村集体经济组织接纳为成员。
这个时候,村庄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的成员不相重合,两者的职能自然也就有所区别。自然的,村民选举的村委会就会被“剥夺”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的权力。而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者则可以由党支部书记充任,或由党支部任命,或者聘任本村经济能人担任,甚至可以通过人力资源市场从村外招聘,而并不必然走选举程序。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者的管理方式也就脱离所谓民主管理,而变成更加符合市场经营要求的企业管理方式。应该说,集体经济组织的民主管理不一定就沿用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和监督制度,而是需要符合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活动的民主参与方式。在这个场合下,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者的经营不善、中饱私囊等问题,则要通过建立合理的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制度,而不能追问村民自治制度的失当。
在这种场合中,集体经济组织是否和村委会分别明确职责,多半是一个在实践中已经解决的问题。因为工商业活动的复杂和经营决策的特点,使得村民自治的民主和直接参与原则并不适用,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了更好地参与市场活动,多数都会明确成为工商业法人,为了内部管理,也会建立不依赖于村民直选制度的集体所有者组织(如董事会或理事会)和经营者团队。
当下,随着资本下乡步伐的加快,如何协调外来资本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利益,如何进一步规范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者的权力,如何界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和权利,正在农地流转、开发区占地、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等多个领域对立法提出迫切要求。但是,这是一个不同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另一部法律的立法。
另外,涉及集体经济组织产权改革、村改居等更为根本的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重大事项,现有的村民自治决策和执行程序是否能解决问题呢?这类事项,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之类的组织决策制度,则不一定能保证村民的长远利益。这类事
项影响到村民几代人、同时对全社会利益也会产生重要的外部性影响。因此,并不能完全由村民自治原则来解决。中央和地方政府完全有必要通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条例》之类的法律来进行规范,而改变当前由地方政府单方面制定临时政策,或者利用村民多数人决定的投票程序来决定。
关于农地收益的冲突类型
土地是中国农村中更多出现冲突的场合,也是最需要明确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和村民自治组织中村民身份的场合。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或者国家规划的交通设施和重大产业项目,在城乡结合部的村庄中需要大量征收土地,或者一些农业产业化企业或项目下乡,有关村庄会发生农地的大规模流转,这都会产生巨大的土地增值收益,其中相当部分被以征地补偿、土地流转租金的形式归属集体土地所有者。这时,谁是集体土地所有者也即谁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就不仅需要明确界定而且必须有合理“说法”。
这时的成员资格不仅仅是一个有无农地承包权的问题(农地承包权带来的仅是微薄的农地收入和社会保障,有成员资格就有可能得到征地补偿费和流转租金),而是一笔相比高于若干年农地种植收入好多倍的货币收入,有些地方还附带着社会保障、就业安置等长远福利。在中国的很多村庄中。正是由于谁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法定论而造成了旷日持久的争吵、诉讼和上访,而由于缺乏村庄内部的共识形成和裁决机制,使得这些争吵、诉讼和上访成为矛盾冲突的导火索。
这些涉及农地转非农用的增值收益分配而致的集体成员资格争议和冲突发生在以下几类主体之间:
第一类,承包地被征用的农户与承包地未被征用的农户之间。失地农民要求把有关征收补偿全数归自己所有,但是同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要求分享征收补偿,理由是我也是集体土地的所有者。现有法律和政策并不明确支持失地农民的要求,因为被征用土地的是村集体经济组织,而不是某些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经济组织的全体成员有权通过某种集体决策程序决定征收补偿在成员间的分配范围和数量。
第二类是承包地被流转的农户与承包地未被流转的农户之间的冲突。现有法律支持承包地被流转的农户获得全部流转收益,因为流转的是基于农户承包权的农地使用权。但是,共居一地、同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没有被流转的农户则没有机会享有流转收益。当这种流转是所谓大规模流转,并不与自己地里种什么和土地质量有关,而只与偶然的土地位置有关时,后者的意见将会更大。往往这种大规模流转又要依靠村干部乃至乡干部做很多工作,这就更增加了后者有意见的理由。流转租金低了,土地被流转农户要求重新调整土地;流转租金高了,未被流转农户要求分取租金。
第三类是失地农民、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和村委会(或村集体经济组织)、乡镇政府以及更高级别政府之间的矛盾。由于征地补偿标准不由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决定,土地流转租金很多时候也不能很好体现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而是依据国家有关法律和地方政策,由地方政府或用地企业单方面决定,农民应得大大低于土地的市场价格,农民会产生严重的被剥夺感。这时候,在补偿和租金发放中如果不能做到公开、公平和公正,就很容易产生冲突。
以上这三种基于不同主体之间利益差别的矛盾,都提出了要明确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并由具有相当合法性的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者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分配集体土地收益的问题。
这种情况下,是否需要通过分设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的方式解决可能出现的冲突呢?
如何看待村民自治
从分配土地收益所需要的决策程序和执行程序的性质来讲,作为集体土地共有者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每个人都有参与有关分配方案讨论和决定的权利,决策活动是关于数量明确的存量收益的分配方式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讨论、协商或者投票方式来解决,决定的分配方案应由得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授权的管理机构来执行并受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监督。如果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和村民自治组织成员基本重合,而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的村委会能正常履行职责的话,没有必要单设集体经济组织,来处理集体土地的收益分配事宜。也就是说,目前的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小组会议等的运行程序完全可以解决这类问题。
土地收益分配的问题非常具体而复杂。完全失地的农民想拥有全部征地補偿但是还想从未失地农民那里得到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平均调整来的土地,而没有失地农民则想分取土地收益但是不愿把地调给失地农民;县、乡政府想截留土地收益弥补财政赤字,村级组织想多留集体公益金用于发展事业,而农民基于经济利益和对干部的不信任要求将土地收益完全分到户。而个别村民的很多具体情况使得其提出超出一般村民的特殊要求,另有一些村民(出嫁、户口空挂、土地转包等)到底有无资格分享土地收益,这些问题需要得到细致甄别和个别处理。这些矛盾和问题无疑需要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村民通过民主方式来决定,其决定方式已经蕴含在现有的村民自治制度之中,并不因为新设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组织而得到更为妥善的解决。
在现有村民自治制度框架中,发挥现有村民自治制度的优势,则可解决好多数村庄中农地承包和宅基地分配、社会公益事业兴建之类涉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之类的事务,而不必另起炉灶。
为什么不能处理好这类事务,绝大多数是因为没有发挥这一制度优势的问题。事实上,只要利用好现有的制度渠道,基于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方面的问题的多数就可以得到解决。目前,关于明确村委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同性质,分设两者不同的管理组织的提议更多表现的是对村民自治方式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既源于对村民的自治能力的不信任,也源于对选举出来的村民自治组织的管理者的不信任,或换句话说,对精英为民服务的意愿和能力的普遍不信任。
需要明确的是对于村庄集体经济组织如何管理的问题,的确不是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改中能够彻底解决的问题。笔者只是在于提醒人大常委会委员和社会公众,现有的村民自治的制度资源中仍有巨大空间,村民自治的有关规定完全可以通过充分利用或者稍加调整,用以解决相当部分村庄中的集体资产的处置和管理问题,即使是征地补偿和农地流转这样较为复杂的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