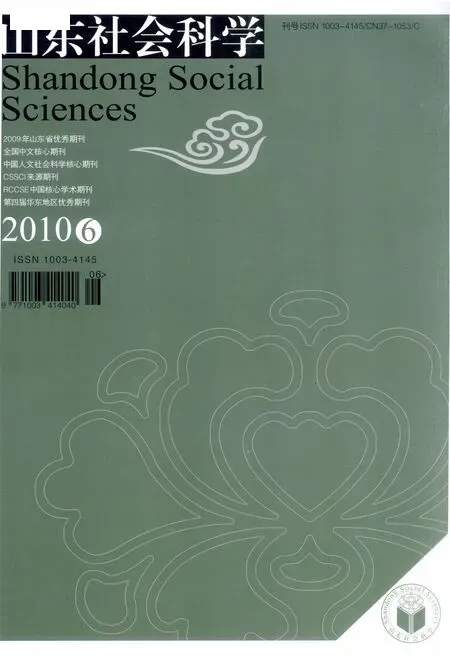排斥或包容:流动人口与社会发展①
[美]狄克·霍德尔 撰 曹南 译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排斥或包容:流动人口与社会发展①
[美]狄克·霍德尔 撰 曹南 译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开篇在对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移民情况与文化适应研究作以简短介绍后,笔者对以下三个部分作了阐述。第一部分首先对以“系统方法”为基础的“文化适应”模式展开叙述。其次,对微观层面、宏观层面及中间层面地区、文化惯例、社会风俗和国家作以区分。第二部分介绍近年出现的作为移民活动理论框架的跨文化生活概念,并说明家庭经济的内部活动加速了社会发展的过程与个人及家庭生活规划的实现。第三部分引用 20世纪 20年代加拿大种族主义政体下的亚裔移民的生活和 20世纪 70年代的多元文化政策这两个案例阐述理论方法。此二案例研究着重说明理论源于实践。
移民;流动人口;社会发展;跨文化生活;文化适应模式
民族国家不仅指的是一种政权组织形式,而且是一种心理状态。在这样的时代,移民者在其离境国被称作向国外移居者,在其终到国被称作外来移民。这一术语指的是永久且单方向的离境和从民族到种族异族文化圈形成的轨迹。人们的精神状态与本民族有着与生俱来的紧密联系。因此,离开其出生国的移民者要么彻底改变其思想,要么生存在两种文化之间的夹缝之中。那些打算重返故土的移民已不再与其出生国有一脉相承的联系,而被看作是过客或暂居者。
20世纪 70年代以来移民的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民族国家的建立存在很多问题,主要原因如下:首先,“国家”强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是启蒙运动时期界定的第一个人权概念),而“民族”的概念却使同一国家中拥有一种文化背景的成员比其他文化背景的成员享有更多的特权。其次,民族国家虽没有永久的固定模式,但却有其历史和地域的特定性。在不同文化的王朝更迭后,民族国家代表了基于单一文化背景的19世纪一种特定的欧洲政权组织形式。然而事实上欧洲大部分的民族国家仅出现于一战末封建帝国瓦解后的 20世纪。强调同一性的民族概念贬低来自文化背景和政权体制与其相异的新移民。特别是在 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冲击下,社会改革思想使公民权概念发生了改变,从对内的单一文化和对外的自我防卫转变为危机时期的对内社会保障 (此后 T.H.Marshall称其为“第二代”人权)。在进入欧洲社会保障国家的移民中,对较小文化群体在此种民族国家历史存在的认可,对移民和居民活动的认可引出第三代人权概念——坚持并发展自身文化的权力。
在历代君王统治下,不同种族文化、不同宗教和不同社会阶层的群体与他们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通常可以通过协商方式保留其文化特征。相反,民族国家的组织架构和统治者强迫移民们实现文化的“同化”,即无条件地放弃原有的生活方式——移民需放弃其原生文化的特征,这有时也被武断地称为随身携带的“文化包袱”,并完全接受移入国的语言和生活方式。由于移民们不能简单地从一种文化跃入另外一种文化,因此像小德国、唐人街这样的可作调整阶段的民族异类文化圈提供了一个“中间文化”的空间以缓冲由彻底根除本国文化带来的冲击或接纳暂居者。
随着对民族国家概念的批评,同化的概念也需要被重新界定。根据 20世纪 80年代的新概念,移民者能“适应”移入国社会 (Bodnar,1980)①Bodnar,John,“ Immigration,Kinship and the Rise ofWorking-Class Realism in IndustrialAmerica,”Journ.of Social Hist.14(1980):45-65.,能在劳动力市场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Isaj iw,1999),②Isajiw,W sevolodW.,Understanding Diversity.Ethnicity and Race in the Canadian Context(Toronto:Thompson,1999).或者说他们能“融入”新社会的经济生活、社会模式和文化语言的交流方式 (Hoerder 1996)。③H oerder,Dirk,“FromMigrants to Ethnics:Acculturation in a Societal Framework,”in Hoerder andLeslie PageMoch,eds.,EuropeanM igrants:Global and Local Perspectives(Boston:Northeastern Univ.Press,1996),211-262.他们建立了一个“第三空间”(Bhabha,1994)④Bhabha,Homi K.,The Location of Culture(London:Routledge,1994).或者说创造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跨文化社会空间。最重要的问题是移民们是否被看作是社会中的一员,是否仍然被忽视或者被社会排斥在外。如果移民被看作是社会中的一员就表明他们可以尽其所能在新的国家中为自己为社会创造最大的价值,如果是被忽视或被社会排斥在外则说明他们既不能最大限度的为社会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新的社会也不能利用这种人才优势。
一种以系统方法为基础的文化适应模式
为了了解全球范围内的移民现象与这些流动人口的文化适应过程,一个全面的研究策略必须使微观的社团层面和宏观的国家层面相结合,就如同在特定的中间区域内两者之间的互动。此策略范围如此之广,包括那些当今为躲避贫穷或逃避战乱的避难移民,也将涉及个人、社会阶层和性别经历。传统意义的宏观层面——国家的范围应被扩展,即应包括世界性的移民区域,也应包括超国家区域。地方或微观层面的个人主义观点 (以个人为单位的移民、组织和斗争)需重新审视,因为单纯的个人活动不能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介于宏微观之间的中间层面包括各种人际关系的个人集合体 (家庭经济情况,邻里关系及工人组织等等)和国家性或世界性的划分 (各部分劳动力市场,民族社团的网络关系,区域性的经济结构和发展)。在上述层面上移民可以在经济管理体制和政权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独立自主的各项活动。
“系统方法”(Jackson and Moch 1989)⑤Jackson,James H.,Jr.,and Leslie PageMoch,“Migration and the Social History ofModern Europe”,HistoricalM ethods22(1989),27-36,repr.in Dirk Hoerder andMoch,eds.,European M igrants:Global and Local Perspectives(Boston:Northeastern Univ.Press,1996),52-69.先分析复杂的社会现象与移民过程,而后研究特定的团体与个人。因此,在移民问题上,需要分析离境国的特征。首先,关于从社会阶层与人口分布特征方面分析的社会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 (或两者都缺失);关于政治体制、政治文化与发展;关于教育制度、信仰和语言习俗,包括宗教、民族构成、境内外移民的传统和流动性。因为这些人不再是通常概念上的印度人、中国人、英国人,而是居住在一个拥有特定地域文化的特定地区——像伦敦、孟加拉、中国的南部省区。对上述政治制度的社会分析需被具体到某一特定的区域和某种当地的现象,并涉及到特定的社会阶层。其次,一旦离境国社会得到详尽分析,移民过程也需要同样的系统关注,其中包括移民前特征和某团体、家庭或个人情况;决定移民的总体情况:家庭经济状况、个人或家庭团体的移民愿望、移民障碍或离境政策的诱导、旅行费用 (包括旅行期间无收入的损失)、旅行的资助 (他人赞助或从亲属处得到的预付票)和移民政策。第三,入境后用研究离境国的分析方法对其特定的目的地在整体移入国社会的框架下进行研究。这一分析将对离境国社会,由移民改变的人生轨迹以及受移民影响的移入国社会进行分析、描述和理解。
对于大多数的移民者(政治流亡者除外)在移入国社会发生的文化适应过程会按顺序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适应在本研究中被定义为移民者在其出生国的文化背景中养成完善的个性后,融入到新文化中的过程。这一定义源于以下观点,即移民决定暗含对出生国现状的不满和在旅行中的转变影响着其看法和行为。这种方法探索了出生国社会化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标准之间关系的弱化现象和对移入国的社会实践及价值观的有意或无意的适应过程。移入国会对移民提供一些综合措施,如由私人或公立机构向入境移民提供的选择机会 (语言学习班,职业培训,怎样得到绿卡,公民教育)。在第二次社会化的文化适应过程中,移民需处理好与“客观”环境的关系即移入国在经济、社会、政治领域的结构特征。“主观”方面包括个人经历以及通过种族社区和重建的人际关系来与新环境中的人交往。这种相互作用也使移入国社会有一定程度上的变化。
政治和法律为文化适应提供了基本原则。经济移民移居到有潜在发展机会的地方,尤其是劳务移民移居到移入国劳动力市场特定的区域。这些移民通常不会有意识地进入某个洲,某个国家或某种政治体系(历史上移民美国中说的“美国”[America]指的是去一个神秘的国家,而不是指一个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体系或者是一个实际意义上的自由国度)。一旦移民者得到一份有酬工作,他们就融入到该社会体系中,从而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最终,他们会转向政界。
除了 20世纪 60年代后的移民在两个北美洲的“打分制”之下得到了承认以外,国际和境内移民入境后通常两手空空。他们不得不在到达之后的短期内进入劳动力市场自谋生路。当前中国的城乡移民与 19世纪末横渡大西洋的城乡移民一样几乎没有资金。到达纽约埃利斯岛 (Eills)移民站的最贫穷的民族文化群体是俄罗斯犹太人,平均每人只有 12美元,“最富裕”的是讲德语的移民,平均也只有 41美元。这不但称不上“启动资金”,甚至达不到“最低生活保障线”。这些钱仅能提供几天的吃住,移民们进入一种“生存经济”状态。他们不得不接受雇主提出的任何条件的任何工作。只有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稳固了家庭,可以选择工作并享受社会生活时,他们才能争取为更好的生活条件去奋斗。
多样性的劳动力市场,其中部分是向国外开放的,而就国内移民而言,那些先前没有城市和工业化经历的移民也可以进入劳动力市场,这才是在国家的基本元素之外最具吸引力的因素。根据经济学和劳动力市场理论,劳动力市场被划分为处于成长中的资本密集型一级集中市场和稳定的二级竞争市场(Doeringer and Piore,1971,Kerr,1977,Piore,1979)①Doeringer,Peter,andMichael J.Piore,Internal LaborM arkets and M anpowerAnalysis(Lexington,Mass.:Heath,1971);Kerr,Clark,M arkets and Other Essays(Berkeley:Univ.of California Press,1977);Piore,MichaelJ.,B irds of Passage:M igrantLabor and Industrial Societ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Press,1979).,还有一个处于边缘贫民区的三级市场对其进行补充。一级市场提供相对较高的工资,良好的工作条件,较强的稳定性,较大的升职空间和工作的安全保障。到 20世纪 70年代这些工作通常只提供给有一定技能,语言交流无障碍的当地人。二级市场的工作特征是:工作不稳定,低薪,工作环境危险恶劣。无一技之长的入境移民通常从事这样的工作,他们往往还要受精通语言文化的中间人或老板的剥削。像已经结束长期学徒生涯的技术人员,有经验的工人或手工艺者,他们作为有经验的技术移民可以进入一级市场工作(尤其是在移入国的培训体系不成熟的情况下)。无一技之长的贫困群体或遭受移入国不平等对待的贫困种族不得不进入三级市场。
移民,作为信息网的一部分,通常选择远离当地的特定劳动力市场,因为他们的朋友或亲属较早移民到此或已经获得了一份工作。只有划分劳动力市场才能满足不同技能、不同沟通能力水平的工人需求,而且允许文化多样性的存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是分层存在的:在提高或改进包括语言和生活方式在内的个人技能之后,才能跨越一定的门槛要求。劳动力市场被隔离区分对待:某些工作取决于性别、民族或肤色 (有时候为宗教)。这种劳动力市场上的纵横划分和隔离对待都表明找工作不存在广义的竞争。只是一些工作提供了与国际接触的机会,一些工作是在国内与“粗野的”乡下人接触。因此进入移入国社会时,新移民不会立即与已在境内的人产生矛盾。进入当地或早期移民的工作圈及这种劳动力的流动性是分阶段的。当两种文化定义下的男女工人在劳动力市场的同一领域竞争时,直接竞争确实存在,但劳动力价值却不尽相同。分隔劳动市场大规模移民涌入会导致劳动力过剩引起的工资增长缓慢或降低。与此相反,当社会需求增长引起产品增加,工作岗位增加之时,工资也会提高 (Bonacich,1972;Christransen,1979)②B onacich,Edna,“A Theory of Ethnic Antagonism:The Split LaborMarket,”Am.Soc.Rev.37(1972),547-59;Christiansen,John B.,“The SplitLaborMarket Theory and Filipino Exclusion:1927-1934,”Phylon40(1979),66-74.。移民的经济性介入会引起劳动力需求增加和经济不断发展——这就是康德拉契耶夫 (Kondratieff)的循环体系,这也是 19世纪70年代到 1914年这段时期欧洲、北美经济与 20世纪 50年代中期到 70年代末期许多亚洲国家的经济状况。
文化适应的第二方面包括风俗习惯、行为标准和价值观之类的社会传统习俗。社会圈包括社会结构和整个“社会循环再生产体系”。将社会圈局限于狭义上的劳动力的自我恢复过分强调了生产的重要性,贬低了工作之外的生活所起的作用。娱乐方面、消遣、家务活、抚养孩子、人际交流网都包括在内,构成社会经济圈。这些圈子界限并不分明固定。通过引入家庭经济、生活目标及全部日常生活这些概念,就更容易理解家庭内部的有酬工作、家庭成员的无偿农作和在小型企业中的家庭工作单位 (Scott and Tilly,1978)。③Scott,JoanW.,and Louise A.Tilly,W omen,W ork and Fam ily(New York:Holt,Rinehart andW inston,1978).此外,马克思主义方法和西方工业化社会方法,在成本消费,费用支出方面更重视工人工资收入。其中暗含了性别划分,因为在许多社会中性别差异把干活赚钱的主要任务分配给了男人,把家务劳动和食住开支的任务分配给了女人。移民和非移民的生活标准既取决于他们的消费结构也取决于他们的收入。系统方法至少将涉及与社会组织架构相关的移民期望值和移民经历的五个关键领域:生活标准、社会障碍/社会流动性、社会民主性、性别差异和前后代间的文化与社会地位的传承。
一旦移民们已经建立了积极的种族社区,更确切地说在特定的劳动力市场的人际关系网,并且在起初的最低生存经济要求实现后,他们会寻找更好的工作。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优先关注点开始于社区及文化即社会架构的互动。后续的移民活动将人们带入已存在的社区中。他们的同乡帮助他们在向他们开放的文化社区的劳动力市场中找到工作。经济稳定性的不断增强和社区规模的不断壮大使得社会活动日益丰富,各种社会风俗得以确立:互助性社团、休闲娱乐厅、民族餐饮、服装特色店、各种宗教场所和在新的社会下新生儿的文化支持体系。一旦组建了种族社区和社会循环体系 (通常这一过程会延续多年),政治制度的问题就会被提上日程。
接收移民的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法律规定范围广泛,始终强制贯彻于社会各层面包括移民入境法规和相应的移入区方面。一旦通过劳务移民,对于那些几乎没有多少存款,不懂当地语言的移民来说,这些法律体系都那么遥不可及。他们无暇理会全洲范围的政治制度,对本地区的政策也兴趣不大。对新移民来说,找到一份工作来维持基本的生活是最重要的。一旦移民者得到社区的保障,重新稳固了家庭经济状况,民族文化圈又为其提供了可充分发展的空间,如下的社区政策才开始受到关注:教育制度的资金如何获得,是否有医疗服务。以这种社区策略为出发点,政治热情扩展到地区 (州或省)最终遍及全国。这种文化适应过程需要历经几代人的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适应渗入生活的各个层面,涉及整个社会经济政治体系。
文化适应的不同程度体现在是否能在经济领域和异类文化圈内找到自己的位置;是否能够在打上特定民族烙印的部分劳动力市场以外被接受;是否能获得各方支持和有限的政治权利;社会架构的整合 (主要体现在入境移民有机会进入不同的社会阶层)和文化适应过程的认同感 (入境移民与新的社会环境相融合,更重要的是,社会也完全接受新移民)。在加拿大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适应性的发展体现在以“多样性就是我们的活力”为宗旨,加拿大通过接受移民和外族从典型的英法双语国家转变成为一个跨文化多民族国家。
移民及其生活方式的跨文化类型
跨越政治上划分的国界和文化边界的移民经历是具有连续性的。即使这种连续性出现中断,也可通过以往的惯常行为准则对此加以说明并得到理解,而这种行为准则又在应对新的急务之时得到逐步调整。自从格利克·席勒 (Glick Schiller)、巴施 (Basch)和布兰克 -赞顿 (Blanc-Szanton)在 1992年出版了一本力作①Glick Schiller,Nina,Linda Basch,Cristina Blanc-Szanton,eds.,Towards a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onM igration:Race,Class,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Reconsidered(New York: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1992),with an introduction by Glick Schiller,Basch,Blanc-Szanton,“Transnationalism:a New Analytic Framework forUnderstandingMigration,”1-24.之后,跨国主义的概念就获得了移民和文化变迁学者的广泛接受。然而此概念并不是首次出现,它是由拥有众多移民的美国社会首次提出的。在美国社会里,每支新到的移民群体都会讨论文化变迁问题。早在1916年美国的反战主义作家兰道夫·伯恩 (Randolph Bourne)就评论说:“美国将不再是一个单民族的国家,而是与他国联系紧密的跨民族国家,就像一台配有各种型号彩线的织布机忙碌运转于各国之间。”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这种广义上的文化互动性观点并没有引起欧洲历史学家或美国移民学者的任何回应。尽管它偶尔被应用于像跨国企业这样的国际经济关系中,应用于涉及多国的法律制度中,应用于非政府组织的跨国政治活动中 (Bourne,1916)。②Bourne,Randolph S.,The Gary Schools(Boston:HoughtonMifflin,1916).
与伯恩 (Bourne)的复杂观点相反,新的狭义跨国主义概念没有在历史上获得一席之地,而是被阿莱扎德罗·波特斯 (Alejandro Portes,1999)③Portes,Alejandro,Luis E.Guarnizo,and Patricia Landolt,“The Study of Transnationalism:Pitfalls and Promise of an Emergent Research Field,”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22(1999),217-37.等社会学者所吸收,他们的著作经常被广征博引。正如彼得·基维斯多 (Peter Kivisto,2001,2003)④Kivisto,Peter,“Social Spaces,Transnational ImmigrantCommunities,and the Politicsof Incorporation,”Ethnicities(Bristol)3.1(2003),5-28;Kivisto,Peter,“Theorizing Transnational Immigration:A Critical Review of Current Efforts,”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24.4(July 2001),549-577.曾批判地指出,着眼于“民族”一方面有悖于国家的整体观念,但是另一方面,尽管这一点从未被这一新概念的支持者详细解释过,着眼于“民族”又是合理的。因为经研究,大部分拉美移民是由难民发起的右翼组织诱导到此的 (这恰巧得到鄙弃西班牙难民的独裁美国政府的支持)。这个概念后来由政治学家托马斯·法伊斯特(Thomas Faist,2000)①Faist,Thomas,The Volume and Dynam ics of InternationalM 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Oxford:Oxford Univ.Press.,2000).从一种截然不同的角度重新定义。像历史学家一样,他批评了以当代标准苛求古人的做法:跨国生活方式已不是一种新现象,而是在 19世纪移民中就存在的。然而,移民史学家和民族史学家们却强烈反对这种理论。即使需要描述这种现象时,他们也从不使用这个术语。跨国主义观点认为,人、文化模式和物质资料不再受限于民族国家的疆界。“人、思想和各种制度都不再有清晰分明的民族定义。更确切地说,人们可以翻译并聚合不同文化的碎片。我们不再说某物是美国、德国、法国或中国等国所特有的,只能说此物的元素来自或中止于何处 (Thelen,1992,p.436)。②Thelen,David,“OfAudiences,Borderlands,and Comparisons:Towar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Journ.of Am.Hist.79(1992),432-62.
强调地区性和社会空间的跨文化主义出现于 19世纪,形成于 20世纪,它通过削弱民族国家的作用从而扩展了系统方法。“跨文化”指的是基于经验主义观察所定义的不同社会层面——即上文中所讨论的宏观层面、微观层面和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层面。因此,不仅小的政治独立体消失了或被降到了次要位置,而且边境和接触带的概念也得到扩展。移民和当地居民运用在家庭、社区和地区的社会经济活动中获取的有限能力,经营着他们的人生或者应付日复一日的生活。人们生存在这样的地区文化中,于是这种地区性文化通过各种具体的日常行为规范塑造了其人群大体的行为模式,在这里即可以规划人生,也可以随遇而安。人们在同一政权统治下的不同文化区域间迁徙。虽然自从 19世纪以来国家就拥有并开始行使控制移民入境的权力了,但如果人们跨越国界,与其说他们移居到另一个国家,还不如说他们进入了另一个社会或一个拥有不同特点的法律地域。从全世界范围看,以超级大国划分的宏观地区决定生存机会,决定着全世界经济圈里工资是否降低,决定着像英国、法国、西班牙这样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文化经济遗产,决定着像 CNN、BBC或RFI这样的大众传媒在发达地区的领导权。在这种多层次的文化中,人们和不同群体进行互动:邻里之间,在思维模式和法律界定上不同的社会群体的同城居民,来自周边带有农村文化的或来自国外语言和生活准则都不同的移民。
文化迁移的发生通常被认为是分层逐级进行的,从国民到移民,从父母到子女,从男人到女人,这种法律释意在基督教世界和儒教世界是相同的,即妻子从属于丈夫,没有独立的身份,不论她出身如何。这种观点认为的迁移是一种无中介的直线分层传递,它发生在按同一标准划分的文化群体内部。然而,文化理论研究发现工人阶级、入境移民、女性、年轻人之类的弱势群体用他们自己的术语解释现象传递信息,例如年轻人面临来自父母、祖父母、亲属以及前辈的朋友以及他们所属的社区的多种复杂而含义丰富的信息。前几代人的文化模式正如供给各类产品的市场供年轻人在其中挑选并进行积极的自我创造的过程。
另外,其他两个可供参考的文化框架的相关提供者也在这样的市场中:地域性或国家性的教育制度可通过当地教职员工和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同辈年轻一代得以调解。此外,年轻人还面临媒体和消费品的市场营销策略的综合影响。同一民族文化群体内年轻与年长人的不同态度通常要大于不同民族群体中同一年龄层的人 (Frideres,1997,Hebert,2001)。③Frideres,James S.,“Edging into theMainstream:A Comparison ofValues and Attitudes of Recent Immigrants,their Children and Canadianborn Adults,”inW sevolodW.Isajiw,ed.,M ulticulturalism in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Interethnic Relations and Social Incorporation(Toronto:Canadian Scholar’s Press,1997),537-61.Hébert,Yvonne,“Identity,Diversity,and Education:A CriticalReview of theLiterature,”Canadian Ethnic Studies33.2(2001),155-85.对于在伦敦、汉堡、卡尔加里、蒙特利尔这样的跨文化社会里,年轻人能独立选择建立生活规划能力的相关评价以及在中国调查所得的实证都表明,绝大多数的年轻人既不会接受像只有单方向高速公路那样单纯的说教,也不会允许文化禁区的存在。多元文化就好比是由许多块不同样式的瓷砖粘合成的一幅静态的马赛克图画。跨文化就好比是动态的存在于现实中的相互关系。年轻男女强调自主,自主探究各地文化背景,自主选择文化道路,但也有人会选择单一文化模式。除非成长于原教旨主义思想体系中,否则多数人在无须探求任何文化本源主义的情况下也知道自身的归属。
强调自主促成发展与个人主义的“行动”两种关系之间的“相互影响”。此外,强调文化的界限性导致对各国实体独特性的重新审视,“相互”的前提就需要文化、经济和社会各层面都有重叠,即一种相互作用。结果是,单一文化中的本源化自身认同融入到社会各种关系和从属地位中,也嵌入到文化传承的复合型自我认知之中。
开放式嵌入模式构成的这种灵活性和供个人可选择的政治经济是在一种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前提之下的,这决不是新自由主义与新达尔文主义的个人主义。因为它使移民者的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运用,不仅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制定自己的生活规划,还能发挥个人的潜力为社会服务。社会的每个成员都不再受肤色、文化习俗、性别或宗教的歧视。当今的大部分社会无论是联邦政府的,社会主义的还是西方民主的都设法建立一种文化政治的一致性。一致性的概念既不是在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并存的 10世纪的伊比利亚社会出现的,也不是在拥有众多人口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时期出现的,更不是在为争取文化统一而东征西讨的拥有众多文化分支、人口稠密的中国帝国时期出现的 (Hoerder,Harzig,Shubert 2003)。①Hoerder,Dirk,with Christiane Harzig,Adrian Shubert,eds.,The Historical Practice of Diversity:Transcultural Interactions from the EarlyM odern M editerranean to the PostcolonialW orld(New York:Berghahn,2003).历史中多样性的存在能帮助我们打破中产阶级社会所建立的单一性的限制:历史上的记录作为政治文化与政治组织形式的研究资料 (Harzig,2004)。②H arzig,Christiane,Einwanderung und Politik.Historische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Kultur als Gestaltungsressourcen in den N iederlanden,Schweden und Kanada( Immigration and Policy-Making.HistoricalMemory and Political Culture as a Creative Strategic Resource in the Netherlands,Sweden,and Canada)(Transkulturelle Perspektiven 1-Göttingen:V&R Unipress,2004).
融入与排斥背景下的移民活动
下文引自加拿大社会 20世纪头十年到 30年代和 20世纪 70年代的两个实例将分别说明在种族隔离和文化多样性的不同社会体制下社会关系的不同选择。跨越大洋彼岸成百上千甚至上万的移民证实了跨洲、跨文化与跨时代生活的家庭是有可能存在的。陈萨姆 (Chan Sam)和他的两个妻子黄波 (Huangbo)、庄美英(May-Ying leong)之间的关系例证了性别差异,而他们孩子的生活反映了两代人之间的复杂变化 (Chong 1994)③Chong,Denise,The Concubine’s Children.Portrait of a FamilyDivided(Toronto:Penguin,1994).。这是个二元家庭或两个家庭?20世纪头十年中国和加拿大都经历着传统与革新的生活目标之间的冲突,中国孔子儒家思想对孩子与父母之间关系的刻板规定和加拿大基督教对人口构成概念一成不变的描述。人们不得不根据政府的法令远离他们每日的生活。加拿大政府的种族隔离手段束缚了选择权,中国政府的不稳定触及了中国几千年的身份门第问题。中国广东农村社会内部的家庭经济及其地位决策都应与远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模式协调一致。
1913年陈萨姆离开了陈村(Chang Gar Bin),他身着西装以表明选择未来之路的决心。他并没有完全告别自己的过去:他的妻子黄波和女儿被留在了家中。在他的移民过程中,他的经济状况得到发展,心理状态也发生了变化。在陈村时,他每天耕地劳作,“乞求老天爷能让他远离饥饿,天天吃饱”。在温哥华他白天在一个木瓦厂工作赚钱,晚上就睡在工棚里。他必须得协调好两种既定的社会身份,一方面是受人尊重的村民,另一方面却是被轻视为“东方的”并被排除在加拿大英语主流社会之外的廉价劳工。十年后他升做店主。1924年他决定依照中国的传统娶庄美英为妾。在中国,嫁娶需要双方商议,需要给新娘彩礼;在加拿大,嫁娶需要克服种族主义者的恶语攻击和相关法令。加拿大的官僚阶级耗巨资制定了复杂烦琐的排外文件;来自不同亚洲国家的男男女女没有理由低人一等,同样也制定了一份与其相对的文件。因此庄美英以华裔加拿大人身份进入加拿大社会。
家庭经济状况与物质情感及个人生活规划紧密相连,这其中还体现着性别与前后辈之间的权利关系。庄美英到加拿大后,在当地一家茶馆里做服务员来偿还她到加拿大过程中所欠的费用。她需要在低微的服务员身份与令她骄傲的店主妻子身份中找到平衡点。陈萨姆需要负担在温哥华与陈村两个家庭的开支。庄美英把工资甚至每一元的小费都交给陈萨姆,他也精心地管理着他们的收入。与其他不同国家的移民在初到时的只有“最低生活保障”的情况一样,两人的生活异常艰苦。他们的两个女儿萍 (Ping)和南 (Nan)分别出生于1926年和 1928年,这两个女儿以祖籍广东的父母和在温哥华的学校中的两种心理状态作为自身标尺。
为了减轻在温哥华的负担,陈萨姆让庄美英在他的店里工作。她良好的社交能力与精明的经营方法提高了营业额也改变了性别间的权利关系:她可以反驳丈夫的观点了。为了弥平和守候在家乡的妻子黄波之间的矛盾,陈萨姆决定衣锦还乡。不同社会层面之间对立的行为标准需要被重新确立,但在温哥华唐人街里的辛苦劳作和勤俭的生活却使他成为中国那个小村庄里最富有的人。陈萨姆采纳了两种社会和不同价值观体系中的新观点,同时对一些传统的做法也加以保留。他资助庄美英在温哥华读书,并在村中炫耀其财富。庄美英也受到了新思想的启发,她拒绝接受作为妾室的从属地位。在 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后,她重新开始工作。1937年日本开始袭击中国,再次使人们确立个人生活规划成为泡影。这个家庭的两部分终于分道扬镳了。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了家庭间的联系。当时具有种族主义观念的加拿大政府拒绝平等地位,而在中国三个成年人劳作所得的家产也未得到承认。
第二个案例的研究是把一个家庭的生活经历与英帝国的衰亡和东非统治者的非洲化政策联系在一起的。在乌干达 (Uganda)曾有一个在亚洲契约劳务移民制度下建立的印度人聚集区,同时这里还有大约 1900人之多的自由移民。其中有一个印度血统的金匠和钟表匠组成的家庭决定改变经济基础的现状:他们的一个女儿去了英国,祖母则留在印度的一个小村庄里。1972年易德·阿明 (Idi Amin)总统把乌干达的亚洲人全部驱逐出境,剥夺社会所赋予他们的知识技能,其目的是弱化非洲人处于社会底层的等级制度。人们都绝望地离开。作为有一技之长的钟表匠宾第(Bhindi)一家与其他 7000多名在乌干达的印度人一样符合加拿大的难民接收标准进入加拿大社会。1972年,多元文化观念初露端倪。因此,宾第一家并没有像陈萨姆和庄美英一样面临种族偏见问题。他的一个叫德利浦(Dilip)的儿子回忆说在一次逃难的旅程中“加拿大政府甚至考虑给我们提供印度食物,因为我们许多人不吃肉”,“我 10岁的时候还一点英语也不懂,当时我别无选择。如果不学,那么在学校的日子就会不好过。”德利浦现在在蒙特利尔能说流利的英语和法语,正如欧洲移民者的孩子们在半个世纪以前一样,他为不会说英语的父亲做“翻译”。在乌干达因受迫害丢失了所有谋生工具的父子二人,在加拿大很快找到了工作。可是已经一贫如洗的二人还得花 550美元购买新的工具。而这家工具店的老板娘与老板不仅为他们落实了工作,还信任他们,让他们赊账购买工具。这是经济包容的一种表现。民族大移居持续发展并不断变化。经德利浦在英国的妹妹介绍,他与一名来自肯尼亚的女子结了婚。当他的父亲在渥太华瞅准时机购买了一家店面时,在英国的一个朋友给他电汇了“启动资金”。在结束他的叙述时,德利浦·宾第承认“多元文化主义在蒙特利尔的真实存在”。
结语
种族排外的作法制造矛盾冲突,减缓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使实现个人生活规划变得更加困难。一成不变的法规,是否实行种族隔离,是否对妇女存在宗教歧视或社会歧视,年轻人是否要绝对服从长辈,是否要强加英国式的政治体制,或者加强某种意识形态或某种政权组织结构。以上这些都会减缓社会和个人的发展。事实确实如此,然而,支持共谋无限制无情搜刮经济利益或在国际社会通行的公平理念之外向弱国强加贸易附加条款的新自由原教旨主义政权依然存在。移民活动,当地居民和社会发展三者紧密而复杂地联系在一起。移民与当地社会成员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一种原动力。①其他参考文献:Bhabha,Homi K.,“DissemiNation:Time,Narrative,And the Margins of the Modern Nation,”in Bhabha,ed.,Nation and Narration(London:Routledge,1990),291-322.Bhindi,Dilip,in Milly Charon,Between Two W orlds.The Canadian Imm igrant Experience(first ed.,1983;rev.ed.,Montreal:Nu-Age,1988),303-313.Bodnar,John,Imm igr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Ethnicity in an American M ill Town,1870-1940(Pittsburgh:Pittsburgh Univ.Press,1977).Hébert,Yvonne,“Identity,Diversity,and Education: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Canadian Ethnic Studies33.2(2001),155-85.Hoerder,Dirk,“LabourMarkets-Community-Family:A Gendered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of Insertion and Acculturation,”inW sevolod Isajiw,ed.,M ulticulturalism in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Interethnic Relations and Social Incorporation(Toronto:Canadian Scholar’s Press Inc.,1997),155-83.Marshall,T.H.,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and Other Essays(Cambridge:Cambridge Univ.Press,1950).Rees,Tim,“Difference and PolicyMaking,”in Christiane Harzig,Danielle Juteau,with Irina Schmitt,eds.,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iversity:Recasting theM asterNarrative of Industrial Nations(New York:Berghahn,2003),308-16.Marshall,T.H.,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and Other Essays(Cambridge:Cambridge Univ.Press,1950).
(责任编辑:蒋海升)
K091
A
1003—4145[2010]06—0005—07
2010-04-06
狄克·霍德尔(Dirk Hoerder),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授。译者曹南,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