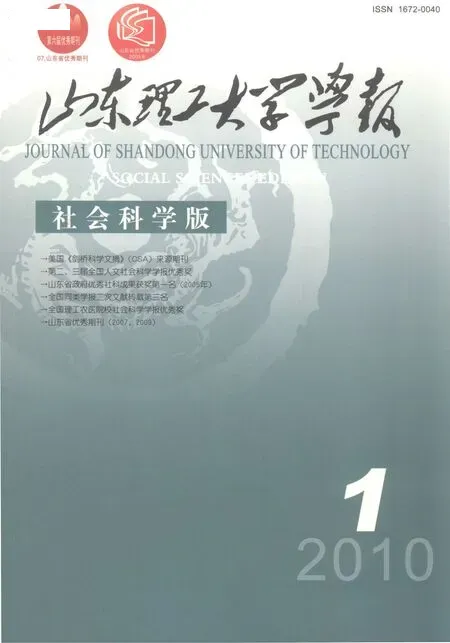新刑事诉讼法存在的控辩失衡探讨
——以“邱兴华案”为例
李晓丽
(厦门大学 法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新刑事诉讼法存在的控辩失衡探讨
——以“邱兴华案”为例
李晓丽
(厦门大学 法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让众多法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乃至全社会看到了中国刑事司法的巨大进步。然而司法实践却一次次地考验着中国的刑事诉讼程序公正,2006年震惊世人的“邱兴华案”就是其中的典型。重温这一引发重大争议的案件审判过程,不难发现,在司法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的背后,中国刑事诉讼控辩依旧严重失衡,对此提出我们的建议。
刑事诉讼;控辩失衡;被告人权利;律师地位
一、案情回顾
2006年 8月 19日,在陕西汉阴县铁瓦殿连杀 10人,潜逃途中又杀死一人的凶手邱兴华落网了。这一震惊世人的特大杀人案从 2006年 10月19日一审到 12月 28日终审执行死刑,经历了长达两个多月的审判期。邱兴华案件的审判实践持续如此之久,主要原因就是是否应给被告人邱兴华做精神鉴定的问题。“从心理学界的争议看,主要以李玫瑾和刘锡伟为代表。李玫瑾依据犯罪心理学的原理,认为邱兴华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是通过远程问卷得出结论的;刘锡伟依据精神病学理论,认为邱兴华具有精神病,他是基于多年的临床实践得出的结论”。[1]“在法律界,则是以贺卫方为代表,从程序正义、司法公正的理念出发,主张应该给邱兴华做精神病鉴定。贺卫方等人从社会责任和个人道义出发,通过网络向社会,包括向法院表达自己对邱兴华案件的看法”。[1]
最终,陕西省高院做出终审裁定,认为上诉人邱兴华提出的上诉理由 (有精神病)无有说服力的相关证据证明,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据此裁定维持原一审判决,并判处被告人邱兴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对邱兴华经验明正身当即押赴刑场执行了枪决。
二、审判终结,争议不断
杀死 10人的邱兴华被执行死刑了,然而,对于其到底是有病与否的争议仍在持续。众多的法学家、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几乎众口一词的认为:邱兴华可能患有精神病!因此呼吁对他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而高院认为他精神正常,直接判决他死刑并执行枪决。现如今事隔三年,关于邱兴华到底有没有精神病这一问题各方论据成山,(在法学界)早已没了讨论的价值,然而,让笔者困惑的是这样几个问题。
对于应否对被告人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这一问题,控辩双方争执不下,此时,由法庭定夺是否合法?是否合理?被告人及其亲属、辩护律师行使司法精神病鉴定申请权这一“合情合理”的基本权利时,为何被法庭轻而易举地驳回,没有丝毫实质的反击之力?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因此,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包括司法精神病鉴定在内的司法鉴定决定权,在不同阶段分别由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行使。邱兴华案在审判阶段,被告人、辩护人申请司法鉴定,非诉讼参与人建议司法鉴定,这是他们的法定权利,法庭应当给与重视和尊重。但法庭最终认为,此案不应启动司法精神病鉴定,这也是法庭的法定权力,被告人、辩护人、非诉讼参与人也应当给与重视和尊重。也就是说,法庭不对邱兴华进行司法鉴定并不违法。
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只有办案的公安人员、检察官、法官有权启动精神病司法鉴定程序。而邱兴华案历经公、检、法几个机构进入庭审阶段,并无任何一方提出要对邱兴华进行司法鉴定。
无论是从专业角度还是司法公正角度,现行法中规定的由法院及控方独霸被告人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启动权都是不合理的。而被告人亲属及其律师所谓的“申请权”也就形同虚设,被无视也就成为必然。
即便如此,学界不应过多地指责陕西省高院的裁定,因为法院的做法是有法律依据的。应该反思的是法院的这一违反程序公正的做法竟然于法有据。我国刑事立法仍然体现着浓重的职权主义色彩。这反映了在新刑事诉讼法颁布后,我国司法界仍十分严重的一个问题——控辩失衡下从法院到整个社会对被告人权利的轻视!
三、控辩平衡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权利之国际考察
刑事诉讼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诉讼,控辩双方力量的失衡是固有的、先天的。因而,为了实现刑事诉讼的公正,通过制度的设置,对控辩双方(实质是审控辩三方)的权利义务的优化配置,以实现控辩平衡便成为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控辩平衡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要求:控辩双方的法律地位平等;控辩双方的权利义务对等;控辩平衡应当贯彻在整个刑事诉讼中。[2]142-143
(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享有的基本权利
11沉默权。为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须有必要的保障措施,包括警检机关询问开始前的告知义务,以及询问时采取的必要措施。侵犯沉默权最为典型的制度就是刑讯逼供。
21辩护权。律师的帮助是被告人实现辩护权的最佳支持,律师对刑事诉讼的全程介入,特别是介入侦查阶段,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实质化的关键。
31调查取证以及证据保全请求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调查取证权是行使实质辩护权的基础。当犯罪嫌疑人无力取证时,有权申请证据保全。
41人身自由权。基于无罪推定原则,公民在被法院的生效判决定罪之前应享有人身自由。但是,根据刑事诉讼的特性,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予以限制与剥夺以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又是必要的。因此,限制与剥夺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必须贯彻必要性原则和比例性原则。
(二)律师辩护的基本权利
律师辩护制度作为控辩式庭审方式的制度基础,其作用的发挥实现了司法的公正。现代国家多把律师帮助权作为被告人的一项重要权利写入法律乃至宪法中。①美国宪法第 6条修正案规定,被告人享有获得律师帮助为其辩护的权利。成熟的辩护制度首先体现为律师的参与率极高。其次,律师充分享有广泛的诉讼权利:会见权,侦查人员询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在场权,调查取证权以及申请保释或释放的权利等。其中,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由会见及秘密交流权,以及律师保守职业秘密的免证权,是真正实现辩护权的重要保障。
四、我国刑事辩护的困境
新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刑事辩护制度的修改是带有历史性的重大改革,特别是大大提前了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但立法修改后多年的刑事辩护实践却证明,刑事案件的律师辩护率非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据统计,在司法实践中,有70%以上的刑事案件无律师帮助,北京律师的“年人均办理数量从 10年前的 2.64件降至 0.78件”。[3]另一方面,律师辩护权利也迟迟得不到有效保障。
具体而言,刑事辩护实践的困境可作如下概括:会见难。虽然刑事诉讼法第 96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律师会见难是侦查阶段普遍存在的问题。具体来讲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律师的会见权异化为追诉机关的会见决定权,会见获得批准难
《刑事诉讼法》第 96条规定,批准会见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两个要件:案件的性质限于国家秘密的案件,诉讼阶段限于侦查阶段,1998年 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六部委《规定》)第 11条规定:“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但对什么才是“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法律并未给予具体明确解释。
实践中,一些侦查人员或是对“国家秘密”作随意性解释,将律师拒之门外;或是令律师写申请、打报告,批了报,报了再批,制造程序上的麻烦;或是不尽告知义务,使许多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不知道聘请律师。这无疑宣告,决定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成为了侦查机关的权力,允许会见甚至成为一种“恩赐”!
(二 )会见安排难
六部委《规定》第 11条规定:“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安排会见,对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或者走私犯罪、毒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复杂的两人以上的共同犯罪案件,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五日内安排会见。”“应当”意味着义务,然而公安司法人员往往将这里的“安排会见”解释为“已经排入了工作日程,而非实际的安排会见”。可见会见权的实现,难上加难!
(三)会见效果不佳,作用发挥难
犯罪嫌疑人得以同自己的辩护律师会见已属不易,《刑事诉讼法》第 96条却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这一本应是非一般情况下的必要例外规定,却造成了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几乎“一律”派员在场的局面。一些地方的公安司法机关甚至在会见场所装设秘密录音、录像设备,对律师会见进行秘密监控。更有甚者,以不成文的方式严格限定律师会见的时间、次数,限制问话内容,禁止记录或允许记录单不让犯罪嫌疑人在笔录上签名等。可想而知,即使得以与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又能如何?
阅卷难。新刑事诉讼法大大缩小了律师阅卷权的范围。律师只能查阅检察院移送到法院的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但法律对于何为“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却未作明确规定。在实践中,只有公诉机关认为是“主要证据”才会提供。致使在开庭前,律师对相当多的证据材料无法查阅,面对公诉人的突然袭击,律师往往措手不及,难以审查辨认。同时,我国立法对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阅卷权并未作任何规定,律师阅卷权流于形式,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难。《刑事诉讼法》第 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然而,这一规定的前半句,却成为办案机关拒绝其申请的“帮凶”——只有在犯罪嫌疑人被捕后,才可申请取保候审;倘若只是被刑拘,则律师无权为其申请。同时,六部委《规定》第 22条规定:“对犯罪嫌疑人采取保证金保证的,由决定机关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定保证金的数额。”“决定机关”也就顺水推舟,往往开出天价保证金。取保候审便成为一纸空文。
调查取证难。“律师调查取证权是其能否充分发挥辩护职责的关键,调查取证权是辩护权的重要体现,是实现辩护权的重要手段,限制、剥夺、不承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这一诉讼就是一个不完善的诉讼、不健康的诉讼”。[2]165
然而,我国《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却对律师调查取证权加以诸多限制。如《律师法》第 31条规定,律师“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刑事诉讼法》第 37条规定:“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就是说,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需要“经过批准”的“权利”,尤其是“须经人民检察院 (辩方的对立方)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依据《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行为于法无据,要么被视为伪证行为,要么被公安司法机关视为无证据能力,而不予采纳。
同时,在实践中,辩护律师的申请取证权也没有兑现。对于辩护律师申请调取证据时,检察院、法院往往以“没有必要”“谁主张谁举证”为由加以拒绝。而且,个别地方公安司法机关常常以“追究伪证罪”等方式变相威胁证人,使其不敢向辩护律师作证。加之辩护律师常常被视为“为坏人开脱”“为富人辩护”,普通公众对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缺少配合的积极性和严肃性。
律师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在我国,辩护律师的人身自由权面临严重威胁。检察机关逮捕的批准与决定权使得其能够以所谓“伪证罪”等诸多罪名陷辩护律师于囹圄之中。公诉人在法庭上不能“战胜”辩护律师——其证据经不起考验,一旦遇到辩护方的挑战,便难以保持冷静的心态,不是以平等的诉讼手段而是以强权对付对手,将刚迈出法院的律师甚至于当庭将律师以“问话”的名义强行带至检察院然后逮捕。据不完全统计,1997~2002年间,至少有 500名律师被“滥抓、滥拘、滥捕、滥诉、滥判”,其中 80%由司法机关“送进班房”,“绝大部分又最终宣判无罪”。[4]这也是律师往往提供“荒诞剧和笑柄”的辩护的原因之一。
律师的人身自由得不到保障,庭审言论豁免权没有确立起来,这使得辩护律师面临严重的执业风险,稍有不慎,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此必然导致辩护律师承担的辩护职能严重萎缩,控辩双方无法实现公平的对抗。
五、向控辩式刑事诉讼体制的转变
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刑事诉讼法》第 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针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无疑是要求犯罪嫌疑人自认有罪,既是不人道、违背人性的,也与犯罪嫌疑人应当享有的辩护权自相矛盾,刑讯逼供就成为必然。“在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问题上,不应存在是否应当的问题,而应是尽快解决的问题,任何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辩解更多的都是观念的问题”。[5]412必须明确的是,沉默权的赋予是无罪推定原则实现的保障。
(一)完善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
强化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与相关权利,切实保障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完善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保护辩护律师参加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的权利,保障辩护律师的人身自由,赋予辩护律师执业权等。
(二)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
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国家法律援助只适用于审判阶段,适用范围显得太窄。法律援助应使用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可以考虑开展值班律师活动,对其提供免费法律援助,并建立起辩护援助基金等。
(三)确立司法审查
强制措施极易侵蚀公民权利,因此应当加强司法制约。结合我国实际,可以考虑在紧急情况以外,参照当今世界各国通行的令状原则,强制措施的采用都必须经过检察院、法院的审查和同意,即取得检察院、法院签发的令状后才能实施。
(四)确定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
当前,我国检察院公诉方与法律监督者的双重身份已遭到众多法学家的质疑与批评。检察机关作为控诉职能的承担者,追溯犯罪是其重要使命,其控诉倾向不言而喻,当然,这丝毫没有降低对其公正性的要求。但不能以对其公正性的要求而否认其追溯的本能,更不能就以此认为检察机关可以保持中立超然的地位从而可能具有监督法庭审判的条件了。控辩平衡不允许控方优越于辩方,甚至凌驾于裁判者——法官之上。控审分离、控辩平衡、审判中立是刑事诉讼永恒的主题。有人认为检察机关的追诉职能与监督职能可以分工行使,后者可以由其他内设部门行使。然而这种设想难以成立:其一,检察机关的一体化关系及其上命下从体制的存在,无法实现其内设部门的独立性;其二,在诉讼三方之外再设立一个监督者,不免不伦不类,“刑事司法的正常运作及公正的实现,还需借助于自身结构的科学架构”。
[1]李富成,董健.莫畏浮云遮望眼:邱兴华案件的鉴定不应泛政治化[EB/OL].东方法眼 (http://www.dffy.com/fay anguancha/sd/200612/20061226115134.htm).
[2]樊崇义,等.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理性思考[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
[3]冯象.中国要律师干嘛[J].中国律师,2003,(8).
[4]邢五一.陈德惠律师无罪陈德惠律师事务所无罪[J].中国律师,2003,(4).
[5]陈卫东.程序正义之路 (第 1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D914
A
1672-0040(2010)01-0058-04
2009-08-11
李晓丽 (1989—),女,山东招远人,厦门大学法学院,主要从事刑法学研究。
(责任编辑 刘迎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