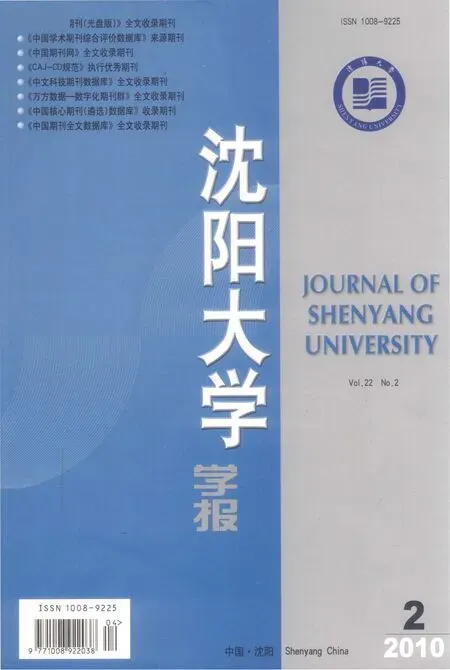“苦难书写”与“超越”——浅析王十月长篇小说《无碑》创作特色
陈礼辉
(湖北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62)
“苦难书写”与“超越”
——浅析王十月长篇小说《无碑》创作特色
陈礼辉
(湖北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62)
从生存的苦难、心灵的苦难、人性的苦难三个维度论述了王十月长篇小说《无碑》的“苦难书写”,认为《无碑》保持了他一贯的“苦难书写”风格,是对底层打工群体生活境遇最真实的观照。从爱和人道主义情怀两方面分析了《无碑》文本和情感的双重超越,指出超越是王十月《无碑》创作的独特之处。
《无碑》;王十月;苦难书写;超越
苦难是文学的永恒母题之一,透过苦难书写,人们可以从中探究出人类精神存在的意义,生命丰富的程度以及人性的繁复与伟大[1]。苦难主题可以说像爱情主题一样是文学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因为苦难是人类成长史的见证,是人的生命史的见证[2]。王十月长篇小说《无碑》是一部自传性的,关涉底层打工群体苦难的书写文本,也可以说是一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另类书写文本。他自己在谈到《无碑》创作时说:“写作这部书,我用了整整二十年。我指的是,我用了整整二十年的时间,和书中的主人公老乌一样,在生活中摸爬滚打,感受着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折中的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希望、幸福、失落、悲伤……”[3]这部小说融汇了作者二十多年的情感历程,作品中作者并不是仅仅停留在对底层打工群体苦难的表层书写,而是将思想的触角延伸至更深层次,以悲悯的眼光审视这一群体,反思其苦难的根源,揭示出灰暗生活中人性的挣扎与坚守,宽容与忍耐,从而带有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
一、“苦难书写”
1.生存的苦难:人的生存困境的展示
王十月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对底层的生存状态是明晰的。《无碑》采用倒叙的笔法,以主人公老乌的视角展示了这种苦难。老乌首次进城打工便遭遇招工骗局,在黄叔的搭救下才获得第一份看鱼塘的工作,虽然月工资只有50块钱却仍心存感激;老乌的第二份工作是在瑶台厂,工人整天在有毒的天那水的厂房里工作,没日没夜地加班,工资又极其低廉,工人在食堂吃饭时“勺子里偶尔舀了两片肉,还要抖掉一片。”
老乌因罢工无果辞掉第二份工作,他的第三份工作是在一家五元店打工。第四份工作是在基德工艺厂,“十二人一间的宿舍,凌空又拉了许多铁丝,挂着衣服、毛巾,风扇一开,如万国旗飘”,军事化的管理将员工变成驯服的、没有思想的机器。保安每隔一段时间就来一次突袭,以防止工人将工艺品偷出车间。
作者刻意安排老乌由一个工作环境跳到另一个工作环境,由此以点带面地描述出底层打工群体的生存困境,他们的要求仅仅限于衣和食,然而如此卑微的物质需求在繁华的城市也得不到片刻保障,真实地展现出底层打工群体的生存困境。
2.心灵的苦难:梦想的迷失与身份的焦虑
打工者的痛苦并不主要来自物质生活的窘困,他们的痛苦更多的是来自心灵的苦难。他们渴望成为生活的强者,渴望过受人尊敬的“体面”生活,这是他们追寻梦想的原动力。但是,现实的冲击和一次次的失败使他们奋斗的激情慢慢减退,迷失在自己的梦想里,无法融入城市或者被城市拒绝使他们开始产生身份的焦虑,灵魂在城市和乡村游荡,既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乡村。
《无碑》中的打工群体是由怀揣着梦想进入城市寻梦的个体组成的。主人公老乌最初的梦想是“水是家乡美,月是故乡明,此处千般好,终非吾故乡。老老实实打几年工,存点钱,回家盖三间房,娶媳妇,搞点种植养殖。这就是老乌的中国梦。”但是,现实的残酷一点点撕碎老乌这并不奢侈的梦想。他因脸上长有一块乌青的胎记处处遭人歧视,工友阿湘给他取了个“老乌”的外号,他的真名李保云从此隐匿。他在工厂受到挤压,始终不被重用,最后自己开了个二手家具店。他的两段爱情均以失败告终,他收养的乔乔最终也归还给阿湘,他想要有个家的梦想也就此破灭。老乌原初的梦想迷失在钢筋混泥土的城市,于是,他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焦虑,由起初“老乌的瑶台”的豪言壮语和满腔抱负到“瑶台的老乌”的落寞与无奈,老乌开始明白自己只不过是千千万万打工者中的一员,城市不属于他。但是,更为可悲的是,乡村的变化也使老乌无所适从,他变成了一个“回不了家”的人,心灵无所归依,灵魂无处安顿。
《无碑》中其他几个人物,同样也承受着心灵的苦难。阿霞为了寻找出路而来到城市,她是瑶台厂最早的员工,本来可以有较好的发展前景。但后来回到农村嫁给一个烂赌的丈夫,她的理想破灭了。为了逃避丈夫的家庭暴力,她又带着孩子回到城市,在将要与老乌结为夫妻时,丈夫的意外车祸使她放弃了和老乌的一起过幸福生活的计划,回到农村照顾终身残疾的丈夫。阿霞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奔波,如果说农村是扼杀她梦想的刽子手,那么城市则是埋葬她梦想的坟墓。
阿湘一开始便被城市的繁华所吸引,对自身的身份产生怀疑,因此她立志做一个城里人,彻底改变自己的身份。她离开烂仔阿昌是因为阿昌实现不了自己的梦想,后来阿湘爱上香港货车司机叶乔治,甘愿当二奶并为叶乔治生下儿子乔乔。阿湘认为自己找到了理想中的伴侣,但叶乔治却抛弃了阿湘,阿湘的理想因此陷落。她将乔乔托付给老乌,并以自己的身体作为报答,从此远走他乡,踏上了艰难的追梦旅程。
小说通过对这些底层人物命运的书写,揭示出打工群落心灵苦难的深重,王十月并没有夸大这种苦难,也没有故意遮蔽,而是将其真实地呈现出来,这种呈现带来了巨大的力量和震撼,使人不禁对这些人物的命运扼腕叹息。
3.人性的苦难:主体自身的困境
王十月在描述打工群体令人触目的生存困境的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他们震撼人心的心灵苦难,但王十月所要表达的还远不止这些,而是进一步向更深层次开掘,展示了丰富的人性及人性的苦难。如果说生存的苦难和心灵的苦难来自于外界施加给主体造成主体处于困境的话,那么,人性的苦难则更多来自于人本性的自私及环境造成的愚昧、偏狭的性格,并且,因为这些因素的存在,人与人之间的苦难不断循环,越来越深地陷入狭隘的境地,可以说这是主体本身造成的困境。
《无碑》中,老乌有两段爱情,一段是与阿湘的,一段是与阿霞的。老乌之所以爱上阿湘,是因为与阿湘产生过一夜情,并且阿湘长相漂亮。阿湘走后,老乌陷入对阿湘深切的思念,并立志将乔乔带大,因为他相信阿湘总有一天会回来。认真考察这段经历,老乌其实并没有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爱情,而是将性和爱分裂开来。他对阿湘的感情,更多的是停留在性欲基础上的,是因欲望而饱受着人性的苦难。与阿霞之间的爱情,老乌更多的想到自己,认为自己长相丑陋,又一个人带着乔乔,便接受了阿霞。而在老乌心里,始终念念不忘的则是阿湘。
在《无碑》中,我们还看到,黎厂长不教老乌配料是因为担心老乌会危及到自己厂长的地位,并且对老乌心存嫉妒;两次工人预谋罢工都以失败而告终是因为老板暗地给罢工领导者好处,使他们尝到甜头,而打消了罢工的念头;李钟免费给工人打劳务纠纷的官司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赚取更多的钱财;子虚暗地举报老乌是为了自己能当上“十佳外来打工者”。而他们做出这些事情之后,或多或少地都感到了良心的不安。
所有这些都表明,人性是复杂的,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王十月没有强调“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的单一层面,而是注重善恶互渗的双向表达,使得他笔下的人物有血有肉,真实可信。
王十月在《无碑》创作谈里这样说道:“写作这本书,我的想法很明确,以一群人和一个村庄这二十多年的历史,努力做到客观书写我所体察到的这个时代主要的真实,不虚饰,不回避,也不偏激。”[3]从以上苦难书写的三个层面可以看出,王十月是一个坚持真实表现生活的作家,他拥有一个作家应该有的现实主义品格。
二、超越苦难
人们常常说文学艺术要超越,可是超越什么呢?文本要超越,文笔要超越,最重要的是情感要超越。如果一个作家对他所写的对象,没有悲悯情怀和敬畏之心,不算超越,也超越不了。作家只有实现了情感上的超越,才会有艺术上的超越[4]。如果说王十月的《无碑》有什么特色的话,这种特色就在于王十月不仅把苦难作为表现真实的一种方式,更在于他没有停留在物质和经验的表层去书写群体的苦难,而是深入苦难发生之时与之后人们所产生的恐惧、绝望、抗争的精神细节,摆脱就事论事的枷锁。不以俯视或仰视的姿态看待他所书写的对象,更多的是以悲悯的情怀去书写,因而体现出一种人道主义情怀。实现了情感和文本的双重超越。
1.爱的超越
对于打工群体来说,生存的困顿,精神的煎熬,人性的挣扎这些负面因子制约了他们的发展,但是,王十月要描述的是他们是如何在无望的现实世界寻找一丝亮色的,这亮色归根结底就是主体自身的爱,在陈金川那里,这种爱“属于灵魂的秩序之德,包括信念、希望、爱、真诚、崇高等人格美。”[5]
在《无碑》中,主人公老乌经受了人生的无数次挫折,心性高傲,秉性纯朴的他因长相丑陋而处处碰壁。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沉沦,他始终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而这生命力的来源便是他自身充满的爱。如他对阿湘和阿霞的爱,虽然在他的世界里他还没有真正弄懂爱情的真谛,但他甘愿为他们付出,这于爱情来说,已经实属不易。又如他对乔乔的爱,乔乔本不是他亲生的儿子,但他视如己出,这种充满大义的父爱化解了生活的苦难,也展现出老乌崇高的人格;还有阿霞,她本可以和老乌过上幸福的日子,但她为了照顾瘫痪的丈夫,放弃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这是一种无私的爱,堪称伟大;李钟策划工人罢工,结果被黄叔提前制止,但他仍大意凛然地孤军奋战,这是一种无畏之情,也是一种对打工群体的大爱。《无碑》中还有很多充满爱的打工者,这是他们人性的闪光点,而这闪光点,足以照亮苦难的生活。
尼采说:“人生可能是悲剧,但绝不是悲观”。所以,在王十月的《无碑》里,他在描述苦难的同时,也对爱情、亲情、友情等发出了赞美之声。肯定了人的“灵魂之德”的巨大作用。这是对自身生存价值的肯定,这些肯定将超越生存的苦难和灵魂的煎熬。
2.人道主义的情怀
北京大学谢冕教授认为:“关怀弱者、关怀弱势群体,这种现象是当前中国文学所匮乏的,我们的文学有太多的高雅,太多的香车宝马、高尔夫球场、五星级大酒店,所缺的是对这种底层的关怀。所以,打工文学的贡献在于弥补了当前文学现象的一种缺失,而且还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尺度。”[6]王十月作为打工文学的代表作家,不是带着怜悯和俯视居高临下地叙述故事,而是带着悲悯的情怀去书写生活和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所以他说:“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希望对打工生活不了解的读者,在读到这本书时,对现在的幸福多一份感恩,把目光与爱能短时间移向身边这些匆匆而过的打工者,对他们也多一些理解,宽容与爱,而不再是指责、专横、歧视与漠不关心。”[3]
《无碑》中,王十月以人道主义的情怀去追踪每个人物的命运,他们虽然被城市的洪流所裹挟,自身产生或多或少的变异,但王十月并不是从批判的眼光来审视这些打工者,而更多的是以悲悯的情怀去观照、追踪这些打工者的命运。让这些打工者通过自身的努力或他人的帮助达到自我的拯救。而这种自我的拯救才真正是拯救人于苦难中,是超越存在的本质力量。
比如老乌,只要他稍微改变一下自己的原则,他都有飞黄腾达的机会。他在瑶台厂做总务主管,完全可以吃送菜工的回扣。小说中有这样的表述:“三年总务头,一幢小洋楼”。但是老乌仍坚守自己做人的原则,那就是无愧于心。既然作者赋予了老乌秉直的性格,而这性格在现实中又不能有施展抱负的可能,作者就给了人物自食其力的本领,老乌开了一个二手家具店,以此为生,他没有被挫折所击败,也没有沉沦,而是坚强、有韧性地活着,这便是作者人道主义情怀的体现。
又如“小不点”周全林,他刚满十八岁便出门打工,眼看着兜里的钱快用完了,而出路却没有找到,此时,他碰到了老乌,老乌把他介绍给瑶台厂的王一兵,周全林这个原本什么都不会的“小不点”最后当了瑶台厂的经理,实现了人生的飞跃。还如李钟,因策划瑶台厂罢工未果离开瑶台厂,又阴差阳错刺伤盘查暂住证的警察,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按理来说,他的人生从此便暗淡无光了,但作者安排他在监狱里学习法律,最后李钟刑满释放,通过自身的努力,考取律师资格证,打赢几场官司,成为瑶台地区赫赫有名的为民工打官司的律师。
这些人物的命运,都有他们人生的低谷期,而这低谷期在某一层面上是极有可能导致人的堕落和人性沉沦的,但是王十月总给这些人的命运戏剧性的转折,将自己的情感渗透到小说的创作中,王十月不愿看到他笔下的人物变异、沉沦、堕落,他更愿意通过自己无形的手,拉这些人物一把,给他们自我拯救的机会,这是人道主义情怀的真实体现。
三、结语
王十月说:“文学,大抵有许多种分法,而我,却想这样来分,有一类文学,是要告诉人们,我们在曾经怎样活的文学;有一类文学,是告诉人们,我们正在怎么活的文学;还有一类文学,是试图告诉人们,我们可以怎么活的文学。”[7]王十月将目光投向少有人关注的底层打工群体,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去观照他笔下的每个人物,书写他们的苦难,这即是王十月所说的正在怎么活的文学,但是,很明显,王十月意不在此,他将爱给予他笔下的人物,让爱化解生活的苦难;他将人道主义的情怀投射到文本的间隙,使笔下的人物通过自我的拯救达到成功的彼岸。“这就好比佛教的度,小乘佛教着重的是自我的修养,度的是自己,而大乘佛教强调的是对苍生的责任,度的是他人。”[7]文学也有小乘和大乘之分,王十月的写作,是由最初的小乘逐渐升华,通往大乘的写作,历史往往观照的是大人物的命运,但王十月将小人物的命运写得如泣如诉,悲怆动人,为这些小人物立下了一座无名的碑石,实现了一个“打工文学”作家的超越。
[1]龙其林.苦难的承担与救赎的温暖——读次仁罗布的短篇新作[J].小说评论,2009(5):121-124.
[2]贺绍俊.从苦难主题看底层文学的深化[J].当代文坛,2008(1):4-7.
[3]王十月.理解、宽容与爱的力量——王十月创作谈[J]长篇小说选刊,2009(6):142.
[4]彭学明.在疼痛中苏醒和超越——深圳打工文学初探[J].理论与创作,2009(1):33-36.
[5]陈金川.地缘中国:区域文化精神与国民地域性格[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124.
[6]石一宁.扶植“打工文学”构建和谐社会[N].文艺报:2005-09-10(1).
[7]王十月.文学的小乘与大乘[J].当代文坛,2009(3):58-56.
Suffering Writing and Transcend——On Cre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Wang Shiyue’s Novel No Monument
CHEN Li-hui
(College of Literature,Hubei University,Wuhan 430062,China)
The suffering writing of Wang Shiyue’s novel No Monument are expounded from the three angles including the sufferings of survival,soul and human nature.It maintains his usual style of suffering writing and it is the most realistic contemplation of the underclass.The double transcendence of text and emotion in No Monument are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s of transcendence of love and humanitarian feelings thus revealing the creative unique of Wang Shiyue.
No Monument;Wang Shiyue;suffering writing;transcend
I207.4
A
1008-3863(2010)02-0001-04
2009-11-20
陈礼辉(1985-),男,湖北鄂州人,湖北大学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王立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