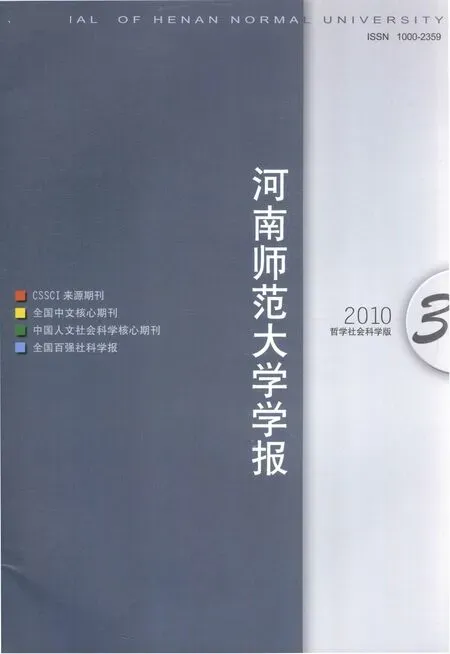反向征收确认中权利冲突的化解
——以公民生存权与环境权为视角
吴 真
(吉林大学法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反向征收确认中权利冲突的化解
——以公民生存权与环境权为视角
吴 真
(吉林大学法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政府基于社会公众的环境权而对私人财产的利用加以限制,财产所有权人是否可以要求政府赔偿,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对一系列相互冲突的范畴进行权衡,其中公民的生存权与环境权的冲突尤为显著。受到限制的财产量占所有者财产总量比例的确认是正确取舍公民生存权与公众环境权的前提。当这一比例难以量化时,应适用“合理的经济用途”标准,即把私人对财产享用的时间及公共利益的迫切程度等都纳入考量范围。同时为防止主体规避法律,在制度设计上应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
反向征收;权利冲突;生存权;环境权
一、反向征收确认中公民生存权与环境权冲突的凸现
通常意义上的征收是指政府为了公共利益需要某人的财产而通过法定程序支付相应的对价将其获得。但有时政府并非取得公民财产的所有权,而是基于公共利益通过限制私人所有者对其财产的享用来保障公众对这一财产的某种使用权,有人将此类情形称为“反向征收(inverse condemnati)”,即如果事前政府并未获得财产所有权,却实际上排除了财产所有者对其财产的使用和享有的权利,财产所有者有权事后向政府要求赔偿。
一般情况下,如果认定政府基于公共利益具有充足的理由对私人财产实行限制,则财产所有权人不得以“反向征收”为据获取赔偿。相反,如果政府的限制行为已完全剥夺了所有权人对其财产的实际权利,则构成事实上的征收,政府必须向财产所有权人赔偿因财产用途受到限制而蒙受的损失。然而,这两种情形并非截然相反、非此即彼。在确定政府是否需要对公民进行赔偿时,需要对一系列相互冲突的范畴进行权衡,其中一对重要的冲突表现为公民的生存权与环境权的冲突。
从字面意义上看,生存权与环境权似乎并无冲突,因为生存即要求有良好的环境,环境毁坏则人亦无法生存。本文认为,反向征收中生存权与环境权的冲突集中体现的是个体性权利与共享性权利的冲突。
生存权作为明确的法权概念,形成于19世纪末,是基于资本主义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产生的。资本主义从自由发展阶段进入到垄断阶段以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贫富分化加剧,在资本家利益得以满足的同时,工人丧失了工作自由与生存的自由。在此情况下,国家伸出了“干预之手”,以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权[1]。从其产生看,生存权更多的是从生产者个体出发而设定的。环境权则是在20世纪后期人类环境不断恶化以及人们寻求环境问题解决的背景之下产生的。环境权是一项共享权,是一种全体人民的环境公益[2]。
生存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生命权,即人的生命非经法律程序不得受到任何伤害和剥夺;另一方面是生命延续权,即人作为人应当具备的基本的生存条件,如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物质保障[1]。对于同一个财产的使用方式,作为个体性权利的生存权与作为共享性权利的环境权有着不同的主张,这就产生了两种权利的冲突。
权利的冲突是两种权利的正当、合法行使而发生的冲突[3],冲突着的权利是否存在位阶,以及如果存在的话位阶的秩序的状况又如何的问题一直是个争议不休的问题。即使是主张存在权利位阶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权利位阶并不具有整体的确定性……许多权利因其价值地位的非确定性而处于相应的不确定的位阶之上”[4]。本文赞同“不同类型的权利受到平等保护”的观点:“权利体系不等于法律体系。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都有一个位阶关系,但权利体系并没有位阶关系,权利体系内的各权利种类之间应是平等的。”[3]不同的权利由于明确体现于法律之中已成为客观存在,因此解决权利冲突问题的根本手段在于依据各自权利的内容、彰显的价值目标、社会的客观需求等,从具体情形出发,充分权衡与协调冲突的利益和价值,使不同的权利在各自的范围内得到最充分的实现。
二、权利冲突化解的前提——分母的计算
以公共利益对私人财产权利限制的程度为标准确定是否构成反向征收不能忽略对受影响的财产量特别是这一财产量占所有者财产总量比例的考虑,即在计算私人财产权利损害程度时应正确确定分母,这是正确取舍公民生存权与公众环境权的前提。而反向征收的确认应以私人的财产总量作为私人财产损害计算的分母。
如果为了公共利益使私人财产事实上损失殆尽,私人丧失了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或其正当的投资期待完全落空,则政府的行为足以构成对私人财产事实上的征收。
State of Maine v.Johnson案[5]中上诉人拥有一块沼泽地并向当地湿地管理机构申请许可对其进行填充。一方面,由于上诉人所拥有的沼泽地处于缅因州珍贵自然资源区域,这一区域对水生生物的生存和繁衍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对它的维持和保护顺应了公共利益的要求。湿地管理机构拒绝发出许可。但是另一方面,对于私人所有者的上诉人来说,他所拥有的这块土地最有价值的利用方式是填充后建造住宅,假如不采取这种利用方式,这块土地就“没有任何商业价值”。缅因州最高法院的法官认为正是由于这块沼泽地对整个州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它的维护所产生的利益由整个州范围的公众享有,所以为此付出的成本也应由公众分担。为了执行政府机构的限制而使上诉人的财产变得毫无商业价值,这样无异于让上诉人承担了超过其应当承担的州水土保持规划实施的成本,上诉人从这一限制中所能获得的生态上的利益与其被剥夺的财产使用收益机会相比实在不成比例。因此政府机构针对上诉人所作出的限制已构成征收。
作为一个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尖锐对峙的案件,缅因州最高法院的判决并无不妥。因为在这一案件中认定政府机构对私人所有者的财产构成事实上的征收,并由政府对私人所有者作出赔偿,应是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最公正合理的调和方案。一方面私人财产所有者在财产的用途方面作出妥协,放弃填充湿地并建造建筑物的方案,这样州的环境得到有效维护,另一方面政府对私人所有者由此而蒙受的损失进行适当的赔偿,保障其基本的生存与发展需求。
从Johnson案看,由政府出资赔偿使私人财产所有者对财产用途作出妥协以保护公众对环境资源的权益似乎是解决公共利益和私人所有权冲突的最佳方案。但是,正如美国最高法院Holme s法官所言:“如果对任何通常意义的财产方面某种程度的变化都必须支付赔偿的话,则政府很难维持下去。”[6]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政府都没有能力对所有作为私人权利客体的资源用途的限制支付赔偿。更为重要的是,私人为公众的环境利益所应支付的成本并不是一个绝对值,而应与他从其财产中获得的利益相对应。因此如果私人所有者由于政府对其财产的用途限制而受到的损失远远小于他从另外他享有所有权的财产中的获益,则政府的行为不构成征收,政府无需为此支付赔偿。
明确提出依照用途受到限制的财产量占所有者财产总量的比例判定政府限制行为是否构成征收的较为典型的案件是K&K Construction,INC,J.F.K.CO.et al.v.Depart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案。该案同样由湿地的填充许可申请引发。
K&K案的原告的土地由界限清晰而又相互毗邻的四个部分组成。原告申请填充第一个部分用来建造一座餐馆和一个综合体育场馆。美国自然资源管理部门拒绝了这一申请,因为这一部分中约有28英亩属于州湿地法所保护的湿地。初审法院把第一部分土地作为唯一与征收争议相关的财产,因而认定禁止在其上建造餐馆和综合体育场馆实质上使原告的财产毫无商业价值。美国自然资源管理部门被要求向原告赔偿其财产的全部价值。
密执安州最高法院Cavanagh法官指出,该案首先需要确定的是究竟哪一部分或哪几部分原告享有所有权的土地涉及征收问题,也就是“分母”的确定非常重要,因为“分母”经常对限制性规定实施后私人财产有效用途的剩余量的认定产生影响。征收案件判定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不可分割”原则,即当衡量对一项财产的管理后果时,这一后果必须从财产的整体视角看待。法院不应把整个财产分割为单独的部分再试图确定某一部分上的权利是否完全被剥夺。因此必须在整块土地的基础上而不是仅仅就受到影响的一小部分审查管理行为的后果。原告向美国自然资源部递交的申请涉及第一、第二和第四个部分的综合开发,虽然第三部分没有被纳入原告的开发规划,因为它早已被开发了,但未被纳入开发规划不应成为不被计入分母的理由,因此初审法院应该决定所有四个部分是否都应在征收的确认中被充分考虑[7]。
从K&K案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对财产基数也就是“分母”的认定不同,同一个案件在不同的法院可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判决。即使在同一个法院,不同的法官也会产生针锋相对的观点。Keystone Bituminous Coal Ass'n v.DeBenedictis案[8]即如此。
美国宾西法尼亚州依《沉陷法》等相关法律要求煤炭公司保留部分矿柱用以支撑地面,这样本案中的煤炭公司必须将两千七百万吨煤置于原地不能开采。美国最高法院Steven s法官认为,确认政府对煤炭公司的煤田开采的限制是否构成征收的标准应以煤炭公司所有的煤田为基础,而不应仅仅考虑它被要求保留的矿柱。宾西法尼亚州要求煤炭公司保留不得开采的煤炭量不足该煤田煤炭总量的2%。
原告试图对其财产分开界定并个别看待,这样宾西法尼亚州的《沉陷法》似乎使得原告无法将其财产投入经济上可行的用途,从而影响了原告的经济收入。这种看法的错误在于,首先,原告关注的仅仅是他们不得不依照《沉陷法》保留在地下的特定的煤炭,而非同一地点原告可以开采的煤炭总量。其次,原告认为宾西法尼亚州政府剥夺了其财产上的一种独立的利益——维持生计的权益,而维持生计的权益既为矿产的所有者所有,也为地面的所有者所有。因此为地面的安全而放弃小部分煤炭也是地面所有者维持生计的权益的内在要求。
与Stevens法官的观点形成尖锐对立的是Rehnquist法官的观点。Rehnquis t法官强调被禁止开采的煤炭无疑是可被确认的独立的财产利益。从这个视角,也就是财产所有权人的视角看,这一利益被彻底摧毁,与政府将这些煤炭开采后为己所用的结果完全相同。《沉陷法》的实施使原告对其维持生计的财产的利益归于消灭,使其购买的依照宾州法律作为一项独立权利存在的财产变得毫无价值。对特定煤炭的开采作出限制是对财产权的全然干涉,使财产权消失,必须对权利人合理赔偿。
Rehnquist法官对Keystone Bituminous案点评的“硬伤”在于,一个案件发生是若干权利冲突的结果,而Rehnquist法官仅仅看到了原告的财产权利,却忽略了与该案也有重要关联的其他权利,首当其冲的是公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侵犯的权利。原告如果全部开采其所有的煤炭而不保留任何矿柱的话,土地沉陷的危险直接威胁的是地面居民甚至行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原告在行使其所有权时无疑不得损害其他人的合法权利。另外地面的沉陷将使环境遭到破坏,使地面动植物的生存繁衍条件受到侵害。每个人都必须为良好环境的维持和发展支付一定的成本,当然这个成本以不威胁其基本生存条件为前提。原告被要求保留不得开采的煤炭量不足其在该地点享有所有权的煤田所蕴藏的煤炭总量的2%,把原告在该地点享有所有权的所有煤炭总量作为分母,而不仅仅着眼于其被限制开采的煤炭,则这部分被保留的煤炭量对原告的开采收入所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因此也不危及其基于财产的维持生计的权益,可以理解为原告为环境的维护所应当支付的成本。
R e h n q u i s t法官对案件的分析还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即政府管理目的的正当性。R e h n q u i s t法官认为从原告的视角看,政府要求其保留部分煤炭不得开采彻底摧毁了所有权人对这部分财产的经济利益,与政府将这些煤炭开采后为己所用的结果完全相同。但问题是,从特定的视角看到两种行为造成似乎相同的结果只是表面现象,不一定意味着两种行为都具有相同的正当性,而从任何视角透过现象都可以看到正当性的差别,这种差别会引发性质完全不同的后果。政府基于公众的安全和维护良好环境的目的对所有权人作出限制性规定,且此规定并未给所有权人的利益造成实质上的损害,则所有权人必须服从。而政府将这些煤炭开采后为己所用的行为却没有正当性为基础,所有权人可以主张权利的救济。
三、分母计算标准的具体化——“合理的经济用途”
无论是K&K案还是Keystone Bituminous案,其对“分母”的计算体现了一种以“利益权衡”化解权利冲突的思想,即政府对私人财产使用的限制是否构成征收应该将该限制所服务的公共利益的重要程度与私人权利受到损害的严重程度相对比后才能确定。而这两个互相对比的要素都并非以金钱数量的绝对值为指数。前者即公共利益更多从长远的环境资源的存续出发考虑,难以量化为具体数值,而且包含着诸多同时期科学技术尚无法完全阐释清楚的因素。后者即私人利益应以受到影响的财产量占私人财产总量的比例,特别是私人财产所有者的基本生存需要是否受到威胁为标准。这一标准在很多市政规划案件中被称为“合理的经济用途(reasonable economic use)”[9],即行政机构的管理行为只有给财产的所有者留有合理的剩余时才是合法有效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适用“合理的经济用途”这一标准时需要考虑一些客观因素。
首先,作为分母的私人财产总量的计算还应权衡时间因素。设想某人在政府管理行为发出前的二十年购买一处矿山并连年获益。二十年后除去被政府禁止挖掘的几个矿柱外所有煤炭几乎被挖空。那么“合理的经济用途”标准的适用是否仅仅考虑防止灾难发生的管理行为施行后所能获取的利润?也就是说是否不论政府管理行为是否发生,财产所有者对每一份财产都有永久获利的权利即投资回报期望的实现可以维持永久?如果只把管理行为施行后所能获取的利润作为分母,无疑所有者的生存无以为继,因为其矿山已无煤可采。但是如果把财产若干年的利润都纳入“合理的经济用途”的计算,则财产所有者有充足的生存条件。显然将时间因素纳入到所有者财产总量的考虑之中意味着只要最初的投资能获取合理的回报,管理行为就是有效的[10]。
其次,“合理的经济用途”较多适用于以长远而概括的思路保护公共利益的情形,也就是此类保护的缺失引发的后果往往将在很多年在不特定的广泛群体中缓慢地发生。当公共利益表现得紧迫而具体时,“合理的经济用途”的标准的适用则需格外慎重。因为此时私人的“合理的经济用途”与公共利益处于更为尖锐的矛盾之中,很难协调共存。
设想当开发商试图在频繁受到飓风与潮水侵扰的海岸低地上建造居民住宅时,可否由于开发商的财产仅仅局限于一块海岸低地而给其保留充分开发这块低地的权利呢?在这种情形中我们的判断似乎遭遇两难:或者剥夺财产所有权人对其财产的“合理的经济用途”,或者置公众的安全于不顾,听任未来此地的居民面临飓风或潮水的危险。由此就产生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
有人主张不得剥夺私人财产的“合理的经济用途”。在In First English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v.Los Angeles案中,美国最高法院的Rehnquist法官甚至将依照《潮水地法》的规定对财产权利人在峡谷低地内建造营地的行为实行的限制视为违背宪法而对财产实行的征收,理由是它使得一块计划用作智障儿童露营地的峡谷内的土地变得毫无经济价值[11]。这也就等于说,依据Rehnquist法官的观点,宪法应该保障财产所有者在洪水反复过往的通道上安置200个儿童的权利,否则他应该由于被禁止对其财产采取这一用途而获得完全的赔偿。
有人则认为不同性质的权利应该以不同的方式衡量,因此应将不同的权利体现的利益在位阶上进行比较,长远而持续性的公共利益应与私人财产权利的合理行使相协调,具体而紧迫的公共利益无疑应优先于私人的财产权利。美国加利弗尼亚州上诉法院在将In First English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v.Los Angeles案发回重审时,就鲜明地体现了对各种利益区别对待的思想,“如果行政权力所服务的利益存在位阶的话——当然无论逻辑还是既往判例都证明存在这样的位阶——则生命的保存必须位于首位”[12]。涉及环境区域规划的行政性限制所服务的公共利益很少达到这样高的等级,更多的情形是“防止过早的都市化”或“保护空地”或致力于有序地开发和减少对环境的影响等。当私人财产用途的管理试图促进的是社区的美学价值等看似不是那么紧急的利益时,这些利益通常与宪法所保护的私人财产权利一起被权衡甚至经常由后者胜出。但是在涉及公共利益的最高层次——预防伤亡事故发生的案件中,管理行为因从以前生命丧失的教训产生,其目的恰恰是防止出现新的丧失生命的事故。如果认为宪法因为政府否认私人财产所有者以生命伤亡为赌注而使用财产的“权利”就要求政府对私人财产所有者作出赔偿,对宪法的如此认识就过于反常了[13]。
In First English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v.Los Angeless案中加利弗尼亚州上诉法院并非从经济角度否认公众的环境权和私人财产权利,而是强调在对二者进行权衡时应依据不同性质和程度区别对待。仅仅为防止给公众环境利益造成微弱的影响就让私人蒙受破坏性的损失是毫无道理的,但这并不表明不得为防止给公众环境利益造成微弱影响而使私人财产的价值轻微减少。而重大的公共利益特别是公众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私人只有承担财产遭到重大损失的后果。
四、分母计算的制度设计必需的保障机制
将所有者财产总量作为“分母”判定政府限制行为是否构成征收无疑对公众的环境权与私人的生存权提供了新的合理而可行的思路。但这也必然需要健全的辅助性制度作为保障,目前主要体现为“分母”计算的时间认定以及当事人明知管理行为的发生而低价购买财产的行为效力认定等。缺乏这些辅助性制度,“分母”判定标准无法顺利实施。
设想某财产所有者的小部分财产用途受到政府的限制,为了达到向政府索取赔偿的目的,他可能将其所有其他利润颇丰的财产暂时出售,以竭力缩减“分母”值,待政府的限制行为被认定为征收,他获得相应赔偿后,再将其他财产购买回来。因此法律必须关注政府的管理行为时间与私人财产所有者出售财产时间之间的关系,并作出明确的规定,这对确认所有者财产总量即“分母”有重要的意义。
再比如某人在得知一项财产受到政府的严格管理后故意以极低的价格购进,而后将其作为唯一财产向法院主张征收赔偿。美国已经有一些法院认定,对于在购买财产时已经获知政府的管理行为的,财产所有者禁止对管理行为提出异议。当然多数州允许以低价购进土地的主体随后主张使价格降低的政府管理行为违反宪法,因为这一管理行为妨碍了土地产生利益。这些州持这一立场的原因在于任何人都不能放弃自己的宪法权利。但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自我强加困苦原则(self-imposed hardship)”强调,此种情形下的财产价值的缩减不构成宪法上的征收。也就是说,虽然不同的州对明知管理行为的发生而低价购买财产以期获取赔偿的私人在诉讼适格主体的规定方面有所区别,但这并不影响最终结果的相同,也就是说,即使征收的主张成立,此类主体也不能因为财产基于政府管理行为导致的价值损失而得到政府的赔偿。
[1]李艳芳.论环境权及其与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关系[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5):98.
[2]周训芳.环境权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52-153.
[3]刘作翔.权利冲突的几个理论问题[J].中国法学,2002(2).
[4]林来梵,张卓明.论权利冲突中的权利位阶——规范法学视角下的透视[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6):9.
[5]State of Maine v.Johnson,Supreme Court of Maine,265A.2d711,(1970).
[6]See Pennsylvania Coal Company v.Mahon,260U.S.393,413(1922).
[7]K&K Construction,INC,J.F.K.CO.et al.v.Depart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Supreme Court of Michigan,No.106712,WL 130936,(1998).
[8]Keystone Bituminous Coal Ass'n v.De Benedictis,,480U.S.470(1987).
[9]See Penn Central Transportation Co.v.New York City,438U.S.104(1978).
[10]See Venezia,Looking Back:a Full-Time Baseline in Regulatory Tak ings Analysis,24B.C.Envtl Aff.L.Rev.199(1996).
[11]In First English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v.Los Angeles,482U.S.304(1987).
[12]First English Lutheran Church v.Los Angeles,210Cal.App.3d1353at 1366,1370(1989).
[13]See First English Lutheran Church v.Los Angeles,210Cal.App.3d1353at 1366,1370(1989).
[责任编辑 张家鹿]
DF521
A
1000-2359(2010)03-0095-05
吴真(1971-),女,安徽黄山人,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民商法研究。
2010-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