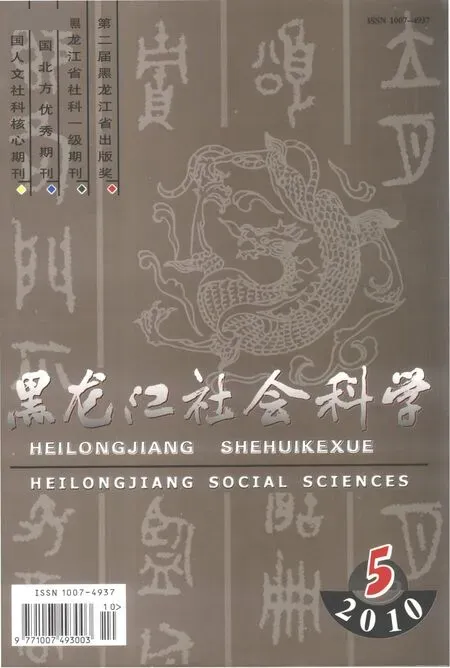从朱熹的格致论出发——论儒家知识论传统的建构
乐爱国,庹 永
(厦门大学 哲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从朱熹的格致论出发
——论儒家知识论传统的建构
乐爱国,庹 永
(厦门大学 哲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学术界通常认为朱熹理学的出发点在于“理”,而事实上,朱熹主要是继承并发挥了二程的格致论,并把格致论当作其理学的出发点。朱熹格致论是知识论的表述,也是一种融合了知识论并以其为基础的伦理学。它发挥了早期儒家“尊德性而道问学”的思想,把伦理学与知识论统一起来,因而是对儒家知识论的建构。
朱熹;格致论;知识论
一、格致论是朱熹理学的出发点
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通常认为,朱熹理学的出发点在于“理”,①其目的在于“存天理、灭人欲”。事实上,这是一个误解。朱熹之前的二程就已经“体贴”出“天理”,并提出了“灭私欲则天理明”的观点,而朱熹则主要是继承并发挥了二程的格致论思想。
朱熹曾于淳熙初年 (公元 1175年前后)的《答江德功》中指出:格物之说,程子论之详矣。而其所谓“格,至也,格物而至于物,则物理尽”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熹之谬说,实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盖自十五、六时,知读是书 (《大学》)而不晓格物之义,往来于心余三十年,近岁就实用功处求之,而参以他经传记、内外本末,反复证验,乃知此说之的当,恐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说破也。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物者,形也;则者,理也。形者,所谓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谓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无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则无以顺性命之正,而处事物之当。故必即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极,则物之理有未穷,而吾之知亦未尽。故必至其极而后已。此所谓格物而至于物,则物理尽者也。物理皆尽,则吾之知识廓然贯通,无有蔽碍,而意无不诚,心无不正矣。此《大学》本经之意,而程子之说然也”[1](卷四十四:答江德功二)。
朱熹的这段重要论述透露出三个方面的信息:其一,至淳熙初年,朱熹已经花费了三十年的心力研究《大学》的“格物致知”,可见,这一时期朱熹学术研究的主题之一在于“格物致知”;其二,朱熹继承二程的思想,主要在于其格物之说;其三,虽然朱熹讲本体论上的“物之理”,但实际上是为了讲“明其物之理”。由此可见,朱熹传二程之道,主要传的是二程的格物致知之论。
朱熹一生致力于《大学》的研究,自十五六岁开始读《大学》,于淳熙初年草定《大学章句》,淳熙十六年 (公元 1189年)完成《大学章句》与《大学或问》,直至临终前还在改《大学》“诚意章”[2],这表明,诠释《大学》是朱熹学术生命的主线,甚至朱熹自己也说:“我平生精力尽在此书 (《大学》)”;“某于《大学》用工甚多”[3]258。朱熹对于《大学》的诠释,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做“格物致知”补传。
从格致论出发,朱熹探讨了理气、心性、理欲等问题,从而建构起他的整个理学体系。朱熹的格致论讲“即物而穷其理”,这就必须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为逻辑前提,因而就要涉及理气问题。朱熹的“理一分殊”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但更多是要求人们“于分殊中事事物物,头头项项,理会得其当然”,因而明显包含了“格物致知”的要求。在朱熹那里,格物的主体是人,并且格物的目的在于复归于人的本心,即所谓“明德”,这就需要讨论“心”、“性”、“情”及其相互关系。而且,朱熹的“格物致知”最终是为了达到诚意、正心、修身,“入于圣贤之域”,并进而在力行中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理欲关系等诸多问题。因此,格致论不只是朱熹理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应当是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和出发点。
二、朱熹格致论是知识论的表述
《大学 》以“格物致知 ”为先 ,进而“诚意 ”、“正心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同时还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因此,以“格物致知”为先、以修身为本乃《大学》的思想。问题在于什么是“格物致知”?如何“格物致知”?
朱熹《大学章句》在解释“格物”时认为:“格,至也。物,犹事也。”[4]17就“物”而言,《大学或问》说:“天道流行,造化发育,凡有声色貌象而盈于天地之间者,皆物也。”[4]526也就是说:“眼前凡所应接底都是物”[3]282。显然,朱熹的格物是要“即凡天下之物”。同时,格物并不仅仅只是接物、多识,而更在于“即物而穷其理”,“知事物之所以然与其所当然者”[1](卷六十四:答或人七)。在如何“格物致知”方面,朱熹提出“持敬是穷理之本”[3]150,还说:“《大学》须自格物入,格物从敬入最好。只敬,便能格物。”[3]269他强调“学、问、思、辨”,指出:“大学之道,必以格物致知为先,而于天下之理、天下之书无不博学、审问、谨思、明辨,以求造其义理之极。”[1](卷六十:答曾无疑五)而且,他还特别强调推类、积累与贯通。由此可见,朱熹的格致论是知识论的表述。
陆九渊说:“格,至也,与穷字、究字同义,皆研磨考索,以求其至耳。学者孰曰‘我将求至理’,顾未知其所知果至与否耳。所当辨、所当察者,此也。”[5]253他认为格物就是要穷究事物之至理。而且,他的格物对象非常广泛,要求“于天地之间,一事一物,无不著察”[5]475。此外,他还明确要求“在人情、事势、物理上做些工夫”[5]400。另据陆九渊《语录》所载:伯敏云:“如何样格物?”先生云:“研究物理。”伯敏云:“天下万物不胜其繁,如何尽研究得?”先生云:“万物皆备于我,只要明理。”[5]440这里明确提出要“研究物理”。关于格物的方法,陆九渊也多有论述。他说:“《中庸》言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是格物之方。”[5]263当然,他讲格物,更为强调“心”的作用,要求“先立乎其大者”[5]400,也就是要“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5]491。他甚至还说:“学者须是打叠田地净洁,然后令他奋发植立。若田地不净洁,则奋发植立不得……然田地不净洁,亦读书不得。若读书,则是假寇兵,资盗粮。”[5]463
应当说,陆九渊与朱熹在格致论方面有许多相同之处;陆九渊的格致论也是一种知识论的表述。但是,陆九渊的格致论更强调“发明人之本心”在格物之先,因而把重点放在了如何“发明人之本心”上。朱熹虽然讲“格物从敬入最好”,但又指出,圣人始教,“为之小学,而使之习于诚敬,则所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者,已无所不用其至矣。及其进乎大学,则又使之即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极,则吾之知识,亦得以周遍精切而无不尽也”[4]527。这似乎表明,朱熹把“敬”的培养主要看作是小学阶段的任务。另据《朱子语类》载,问:“‘格物’章补文处不入敬意,何也?”朱熹曰:“敬已就小学处做了。此处只据本章直说,不必杂在这里,压重了,不浄洁。”[6]326《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虽然没有讲“用敬”,但并不等于大学阶段就不再做要求。朱熹说:“盖吾闻之,‘敬’之一字,圣学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为小学者,不由乎此,固无以涵养本原,而谨夫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与夫六艺之教。为大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4]506他认为持敬贯穿于整个为学成人的过程。所以,在讲“持敬是穷理之本”的前提下,强调格物致知为先,并把重点放在了如何“格物致知 ”上。
王阳明并不是不重视外部知识。他曾说:“天道幽远,岂凡庸所能测识?”[7]800又说:“古之君臣,必谨修其政令,以奉若夫天道;致察乎气运,以警惕夫人为。故至治之世,天无疾风盲雨之愆,而地无昆虫草木之孽。”[7]871可见,王阳明也要求察识天道。此外,他还说:“苟无是心,虽预先讲得世上许多名物度数,与己原不相干,只是装缀,临时自行不去。亦不是将名物度数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后,则近道。”[7]21显然,王阳明并不是绝对排斥认知“名物度数”。但是,王阳明的格致论释“格物”为“格心”,释“致知”为“致吾心之良知”,并指出:“《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诚意之极,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则,致知而已矣。正心,复其体也;修身,著其用也”;“致知者,诚意之本也……乃若致知,则存乎心;悟致知焉,尽矣”[7]242-243。特别是王阳明还有作为为学宗旨的“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7]117王阳明的格致论是对《大学》“格物致知”做出的一种伦理学的表述。
事实上,朱熹的格致论强调“以修身为本”,认为“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一样,都是为了成就修身,所以也是一种伦理学。但是,朱熹的伦理学以“格物致知”为先,以求得知识为先,所以,朱熹的伦理学是一种融合了知识论,并以之为基础的伦理学,而王阳明的伦理学则是一种与知识论相区别的伦理学。
三、朱熹格致论是对儒家知识论的建构
如果仅从伦理学或心性论的角度来界定儒学,可能无法很好地解释《中庸》所言“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事实上,儒家的伦理学是与知识论统一在一起的,尊德性与道问学是统一在一起的。
孔子讲“仁”,但这并不是其全部的思想。孔子还讲“礼”,讲“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即规范,除了有政治上的规范和道德规范,还包括生活规范,比如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之类,为什么“不食”呢?并非是为了养生,而是“非礼勿食”。后来汉儒所确立为经典的《周礼》中,有“冬官考工记”一篇,实为各种器物制作以及建筑工程的技术规范。孔子讲“礼”,因而要求“知礼”,所谓“君而知礼”,“不知礼,无以立也”。这就从讲“礼”,进而讲到“知”。为了要“知”,孔子又讲“学”。孔子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里的“游于艺”,就是要学习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除了要学政治、伦理方面的知识,还要学习生产、生活等方面的知识,当然也包括科技知识。这就是孔子所谓“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儒家讲“学”,首先是要学习儒家经典。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学即经学。儒家经典包含着丰富的知识,涉及各个领域,甚至还包括科技知识,其中《尚书·禹贡》、《礼记·月令》、《大戴礼记·夏小正》、《周礼·冬官考工记》等属于古代科技著作。尤为重要的是,历代儒家学者在学习、诠释儒家经典的过程中,对儒家经典中所涉及的知识不断地予以丰富。由此可见,儒家讲修身是通过道德修养和知识学习来实现的,这就是所谓“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
朱熹接着《中庸》讲“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指出:“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笃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属也。析理则不使有毫厘之差,处事则不使有过不及之谬,理义则日知其所未知,节文则日谨其所未谨,此皆致知之属也。盖非存心无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4]53这就把尊德性与道问学统一起来。当然,朱熹特别强调从道问学入手,并以此诠释《大学》以“格物致知”为先,进而建构了知识论的框架。
问题是,朱熹强调从道问学入手,是否有悖于儒学正宗?事实上,朱熹也讲过“以尊德性为主”,指出:学者“固当以尊德性为主,然于道问学亦不可不尽其力,要当使之有以交相滋益、互相发明。”[1](卷七十四:玉山讲义)又说:“大抵此学以尊德性、求放心为本,而讲于圣贤亲切之训以开明之,此为要切之务。”[1](卷四十七:答吕子约二十四)应当说,朱熹并不反对“以尊德性为宗”,而是要求通过道问学的工夫予以落实。如前所述,朱熹虽然讲以格物致知为先,但仍强调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作为道德修养的基本工夫,仍融合于儒家道德论之中;而且“格物致知”是为了达到诚意、正心、修身,乃至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并不与儒家正统相背离。同时,朱熹的格致论讲“持敬是穷理之本”,要求从持敬入手,把人的道德素质作为格物致知过程中最为根本的要素,而且,强调格物从切己处入手,要求“六七分去里面理会,三四分去外面理会”[6]406,这实际上也包括了道德修养的过程,依然属于儒家的传统。因此,朱熹只是在为学的先后次序上强调道问学为先,并没有从本末轻重上来分辨尊德性与道问学。朱熹在儒学的尊德性与道问学统一的前提下,提出道问学为先,这正是他在儒学范围内的新发明,是对于儒学的继承发展,不应当被理解为有悖于儒学正宗。所以,朱熹的格致论实际上是对于儒家知识论的建构。
四、如何继承和发展朱熹的格致论
王阳明继承了朱熹的格致论,所以,他于亭前格竹。但是,他遇到了问题,这就是他所谓“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即如何从自然知识上升到道德知识的问题。其实,朱熹并没有说自然知识可以直接上升为道德知识,只是认为格物包括了格自然之物,而更多的是要从切己处入手,以道德修养为主,并且要经过一个推类、积累与贯通的过程,才能达到“知至”。同时,朱熹也并没有认为格物致知后就能自然而然地诚意正心。据《朱子语类》载,问:“知至了意便诚,抑是方可做诚意工夫?”朱熹曰:“也不能恁地说得。这个也在人。一般人自便能如此;一般人自当循序做。但知至了,意诚便易。”[3]311可见,朱熹只是从次序关系上或从必要条件上,而不是从因果关系上或从充分条件上确立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的关系;而王阳明的亭前格竹问题,实际上是王阳明继承朱熹的格致论时从因果关系上所引申出来的问题。
那么,朱熹为什么要以知识作为道德的基础呢?而且,作为道德基础的知识为什么还要包括自然知识?《大学或问》在注释“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时,指出:“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诚其意。若夫知,则心之神明,妙众理而宰万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里洞然,无所不尽,则隐微之间,真妄错杂,虽欲勉强以诚之,亦不可得而诚矣。故欲诚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4]511-512因此,在朱熹看来,知识是道德的必要条件。至于格自然之物,朱熹只是对于儒家“博学”的发挥,并以“理一分殊”为依据,强调知识的整体性和融会贯通。
当今社会是知识社会,需要讲知识。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当今社会有道德危机之感,又要讲道德。所以,我们又要讨论朱熹格致论中所存在着的知识与道德的关系。现代人面对知识与道德的关系,有不少是运用二分法,把二者割裂开来,甚至将二者对立起来,事实上这并不能解决问题。朱熹以知识为先、以道德为本的解决方案或许具有参考价值。尤其是,朱熹在以知识为先、以道德为本的基础上所建构的儒家知识论,不仅开出了儒学的新方向,而且有不少内容实际上也是可以为今天所接受的。当然,朱熹的知识论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从伦理学的角度看,朱熹的知识论虽然置知识于道德之先,但只是强调知识的优先地位,并没有真正解决知识,尤其是自然知识如何上升为道德的问题,即王阳明的亭前格竹问题。在不少情况下,知识的增加,即使是道德知识的增加,并不一定能够直接导致道德水平的提升,更何况朱熹的格致论还包括了格自然界事物;把包括格自然界事物在内的格物当做道德修养的基本工夫,这更是难以想象。因此,朱熹的知识论必须解决如何化知识为道德的问题。
从知识论的角度看,朱熹的知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把知识论从伦理学中独立出来,但是强调以道德为本,这是否会影响到知识的独立性。知识本身,尤其是科学知识,以求真为追求的目标,而并非以道德的求善为目的。在知识与道德发生矛盾时,以道德为本的知识是否还具有其独立性?当然,若是过度强调知识的独立性,则可能会违背以道德为目的的儒学之根本。因此,朱熹的知识论必须解决知识与道德在发生矛盾时各自如何定位的问题。
除此之外,从知识论的角度看,朱熹的知识论框架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比如,获取知识的逻辑思维方法、知识的客观性标准等问题,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吸收现代人的智慧而不断加以解决。
[1]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2] 王懋竑.朱熹年谱 [M].北京:中华书局,1998:267.
[3] 黎靖德.朱子语类: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 朱熹.朱子全书:第 6册[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5] 陆九渊.陆九渊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
[6] 黎靖德.朱子语类: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B5
A
1007-4937(2010)05-0001-04
2010-07-25
乐爱国 (1955-),男,浙江宁波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哲学和中国科技史研究;庹永 (1977-),男,河南南阳人,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哲学和中国科技史研究。
王雅莉〕
——访陈嘉明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