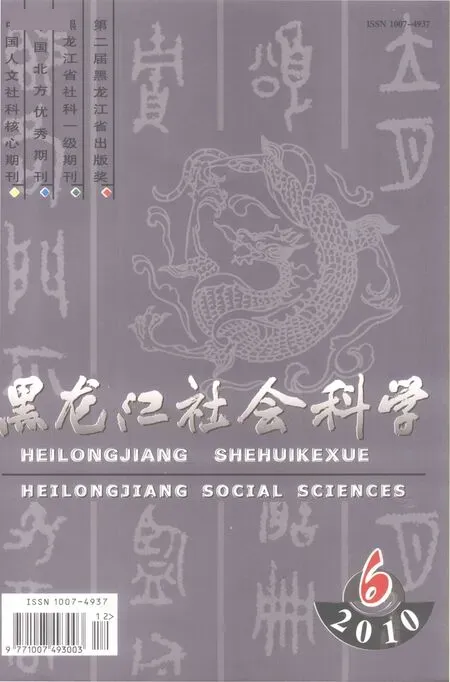草木、花柳与群钗
——神道设教与大观园群钗的神界胎记
吴光正
(武汉大学 a.文学院;b.中国宗教文学与宗教文献研究中心,武汉 430072)
草木、花柳与群钗
——神道设教与大观园群钗的神界胎记
吴光正a,b
(武汉大学 a.文学院;b.中国宗教文学与宗教文献研究中心,武汉 430072)
曹雪芹利用神道设教的方式把太虚幻境、大观园写成草木、花柳世界,赋予降凡的太虚幻境诸风流冤孽以“花柳”、“草木”之特性,群钗咏花实际上就是自咏,大观园的花开花落也就成了群钗命运的象征。这表明曹雪芹成功地将诗性叙事嫁接到宗教叙事中,令《红楼梦》有别于通俗小说而成为抒情体小说经典。《红楼梦》关注的不是思想,不是事功,甚至不是道德,它关注的仅仅是情缘、仅仅是性情、仅仅是生命,其灵魂是生命意识,其精神渊源是《庄子》,其文学渊源是传统的诗词曲赋。
《红楼梦》;神道设教;诗性叙事
曹雪芹利用神道设教的方式[1]赋予降凡的太虚幻境诸风流冤孽以“花柳”、“草木”之特性,让大观园群钗带着这一神界胎记活跃于情感世界中,从而使得整部小说接续了古典诗词曲赋的抒情传统,《红楼梦》因此而拥有了深邃的意境也因此而成为抒情小说的经典之作[2]。
一、大观园的神界胎记
青梗峰的顽石思凡,茫茫大士答应携它到那“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这个花柳繁华地便是大观园,而这个大观园的花柳特质却带有太虚幻境的胎记。太虚幻境是个草木——花柳构成的神界仙境。茫茫大士和渺渺真人指出,太虚幻境有一株绛珠仙草,得神瑛侍者浇灌后已经修成女体,终日“以顽石草木为偶”。第一一六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走入一座宫门,内有奇花异卉,都也认不明白。惟有白石花阑围着一颗青草,叶头上略有红色,但不知是何名草,这样矜贵。只见微风动处,那青草已摇摆不休,虽说是一枝小草,又无花朵,其妩媚之态,不禁心动神怡,魂消魄丧”。这株草就是回归太虚幻境的绛株仙草。这株草和一干“草木”、“奇花异卉”是太虚幻境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贾宝玉的神界导师,警幻仙姑身居离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的放春山遣香洞太虚幻境,其“蹁跹袅娜,端的与人不同”。曹雪芹用一篇赋文来赞叹警幻仙姑,开篇即指出警幻仙姑:“方离柳坞,乍出花房。”这表明警幻仙姑居住、活动的太虚幻境是个香艳的世界,是个草木—花柳构成的世界。贾宝玉在这个神界的“花柳繁华地”,“更见仙花馥郁,异草芬芳,真好个所在”。脂砚斋在旁批云:“已为省亲别墅画下图式矣。”这句话切中了曹雪芹的构思神髓,说明大观园即太虚幻境的人间投影。
大观园是以宁府的会芳园和荣府旧园为基础建盖的,是个花柳构成的世界。会芳园便是一个花柳之地。贾敬生日那天,曹雪芹透过王熙凤的眼睛对会芳园作了描写,并用赋文对之加以讽诵。会芳园这一名称本身就表达了群芳荟萃的意蕴,咏叹会芳园的这篇小赋一如咏叹警幻仙姑的那篇小赋那样,开篇就指出会芳园乃是由“花柳”构成的世界:“黄花满地,白柳横坡。”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贾政和贾宝玉等人从正门、山口、沁芳亭、潇湘馆、稻香村、蓼风轩、蘅芜院、正殿、沁芳闸、怡红院依次游览大观园,眼中所见笔下所题都是围绕着大观园的花柳特性而展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沁芳泉和沁芳亭,走进怡红院前所见到是沁芳闸。泉名沁芳,闸名沁芳,其中有深意焉。沁芳者,渗透着芳香也,而芳香则来自大观园这个花柳世界。贾宝玉将亭子命名为沁芳,乃因极目所见皆花柳,便机上心来,题联曰:“绕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脉香。”这是对大观园特质的总体概括。怡红院总一园之水,这意味着怡红院是群芳的中心所在[3]。潇湘馆有千百竿翠竹遮映,后院有大株梨花兼着芭蕉。贾宝玉认为这是第一处行幸之处,题曰“有凤来仪”,联曰“宝鼎茶闲烟尚绿,幽窗棋罢指犹凉”。蘅芜院一株花木也无,只见许多异草:“或有牵藤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巅,或穿石隙,甚至垂檐绕柱,萦砌盘阶,或如翠带飘飘,或如金绳盘窟,或实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芬气馥,非花香之可比。”贾宝玉题匾曰“蘅芷清芬”,题联曰“吟成荳蔻才犹艳,睡足荼蘼梦也香”。怡红院前碧桃花开,绿柳周垂;“院中点衬几块山石,一边种着数本芭蕉,那一边乃是一棵西府海棠,其势若伞,丝垂翠缕,葩吐丹砂”,后院中满架蔷薇、宝相。贾宝玉将这个院子题为“红香绿玉”,元妃将之改为“怡红快绿”。凡此种种,均在说明大观园是个花柳构成的世界。
大观园的这种花柳特性实际上接续了太虚幻境的花柳特性,因为大观园实际上就是太虚幻境的人间投影。贾宝玉为沁芳亭题联,是“机上心来”,这个所谓的“机上心来”实际上是出于神界经历对他的触动。贾宝玉来到正殿,“心中忽有所动,寻思起来,倒像哪里曾见过的一般,却一时想不起那年月日的事了”。贾宝玉将这个正殿题曰“天仙宝境”。这是在暗示这个地方就是从前梦中所见之太虚幻境。己卯本脂砚斋在此处评曰:“仍归于葫芦一梦之太虚玄境。”元妃省亲,众姐妹的题咏也一直在暗示这个大观园来自仙界:“天上人间诸景备,芳园应锡大观名。”(元妃)“谁信世间有此境,游来宁不畅神思?”(迎春)“珠玉自应传盛世,神仙何幸下瑶台。名园一自邀游赏,未许凡人到此来。”(李纨)“名园筑何处,仙境别红尘。”(林黛玉)这些题咏语带双关,一方面是在应制颂圣,一方面却在暗示大观园非同寻常其渊源乃在仙界。元妃将“天仙宝境”匾额改题“省亲别墅”后,作者还用全知叙事指出“省亲别墅”乃“金门玉户神仙府,桂殿兰宫妃子家”。
二、大观园群钗的神界胎记
曹雪芹透过神话描写指出,太虚幻境的风流冤孽乃是草木之身,这些草木投胎到“花柳繁华地”——大观园后均带有其神界胎记。这些花柳胎记于是成为指称、描述和形容群钗风情、性情和命运的符号,从而将大观园群钗诗化。“司人间之风情月债、掌尘世之女怨男痴”的警幻仙姑是群花之主,其“蹁跹袅娜,端的与人不同”。曹雪芹特意用一篇赋文来形容警幻仙姑。这篇赋是对警幻仙姑的赞叹,体现了警幻仙姑的“兼美”特性[4]。全赋从视觉、嗅觉、听觉等层面对警幻的活动环境、形象、美感和气质进行铺写,并赋予太虚幻境以“花柳繁华地”的特质,赋予警幻仙姑以“花柳”般的品格。脂砚斋指出:“按此书凡例,本无赞赋闲文。前有宝玉二词,今复见此一赋,何也?盖此二人,乃通部大纲,不得不用此套。”这篇赋不仅可以看做是《红楼梦》的总纲,而且还可以看做是关于风流冤孽品格的神谕。
茫茫大士介绍太虚幻境的风流冤孽造劫历世时,特意指出风流冤孽乃是草胎木质之化身。在太虚幻境的神谕中,金陵十二钗都被赋予草木、花柳的特性。十二钗判词和《红楼梦》十二支曲子是关于十二钗性情和命运的神谕,其中的很多神谕都用花柳和草木来指称、形容金陵十二钗。花袭人的册子上画着一簇鲜花,判词指出其“温柔和顺”、“似桂如兰”。香菱的册子上画着一株桂花和枯莲藕败,判词曰:“根并荷花一茎香,平生遭际实堪伤。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这里的桂花即指夏金桂,菱花即指香菱。薛宝钗和林黛玉的册子上画着两株枯木,判词则以咏絮才来赞美薛宝钗的才华。元春的册子上画着香橼,判词用火红的榴花来暗示其封贤德妃,用“三春争及初春景”来说明其比三位妹妹的显赫地位。迎春的判词“金闺花柳质”一则明其地位一则示其风情。惜春的判词“勘破三春景不长,缁衣顿改昔年妆”是用春景的短暂来说明美丽青春的无常。李纨的册子中画着一盆茂兰,判词云:“桃李春风结子完,到头谁似一盆兰。”这是在用花柳暗示李纨的早寡,也用兰花来说明贾兰的爵禄高登。《红楼梦》十二只曲子也有大量花柳意象和香艳意象。《世难容》说妙玉“气质美如兰”,慨叹妙玉枯守青灯古殿,“辜负了红粉朱楼春色阑”。惜春的那只曲子其名称就叫做《虚花悟》,曲子从头到尾都在用花柳意象起兴,述说人生的虚幻:“将那三春看破,桃红柳绿待如何?”“说什么,天上夭桃盛,云中杏蕊多。到头来,谁把秋捱过?”“这的是,昨贫今富人劳碌,春荣秋谢花折磨。”癞头和尚化甄英莲出家时向甄士隐指出:“惯养娇生笑你痴,菱花空对雪澌澌。”这里是用菱花来指称香菱。可见,作为仙界神灵,癞头和尚是深谙神界旨意的。金陵十二钗带着神界胎记来到人间,后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特征便是她们的香艳气息。太虚幻境的日常生活用品群芳髓、千红一窟、万艳同杯均是草木之精华制成,它们让整个太虚幻境充满了香艳色彩。也正因为如此,在《恨无常》、《喜冤家》、《好事终》等曲子中,元春、迎春、秦可卿等人的魂魄和体格都是香艳无比的:“荡悠悠,把芳魂消耗。”“叹芳魂艳魄,一载荡悠悠。”“画梁春尽落香尘。”林黛玉、薛宝钗都是由神界的草木投胎。薛宝钗羞笼红麝串,林黛玉吃醋时向贾宝玉说自己“不过是草木之人”!薛姨妈曾说:“宝丫头古怪着呢,他从来不爱这些花儿粉儿的。”薛宝钗的蘅芜院没有一花一木,全部是各种异香异气的藤草。这是在暗示薛宝钗就是草的化身。她们均有从神界带来的胎记。林黛玉的“怯弱”之症乃是在印证太虚幻境的绛株仙草还泪之说。薛宝钗有“从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癞头和尚“说了一个海上方,又给了一包药末子作引子,异香异气的。不知是那里弄了来的”。这个海上方的成分便是四季盛开的鲜花的花蕊。甄英莲的“眉心中原有米粒大小的一点胭脂痣,从胎里带来的”,这也是在暗示甄英莲的神界胎记。脂砚斋云:“宝钗之热、黛玉之怯,悉从胎中带来。今英莲有痣,其人可知也。”正因为群钗带有神界花柳草木的香艳胎记,所以群钗的魂魄都带有香艳色彩。贾宝玉祭奠金钏,让茗烟代祝曰:“若芳魂有感,香魂多情,虽然阴阳间隔,既是知己之间,时常来望候二爷,未尝不可。”苦绛珠魂归离恨天,“只见黛玉两眼一翻,呜呼,香魂一缕随风散,愁绪三更入梦遥”!这是曹雪芹按照群钗的神界胎记来给群钗的魂魄赋彩。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林黛玉的体香、薛宝钗的“冷香丸”、丫鬟唇上的胭脂何以让贾宝玉如此神魂颠倒了。
这些带有神界草木胎记的群钗往往具有花柳般的风姿,即其长相、体质、神态、性情乃至外号姓名都具有花柳一样的特质。林黛玉“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庸医给晴雯下虎狼药,贾宝玉用花柳打比方:“我和你们一比,我就如那野坟圈子里长的几十年的一棵老杨树,你们就如秋天芸儿进我的那才开的白海棠,连我禁不起的药,你们如何禁得起。”兴儿在尤二姐面前月旦荣府人物,指出迎春的诨名叫“二木头”,戳一针也不知嗳哟一声;探春的诨名是朵玫瑰花,“又红又香,无人不爱的,只是刺戳手”。情小妹耻情归地府,尤三姐“一面泪如雨下,左手将剑并鞘送与湘莲,右手回肘只往项上一横。可怜‘揉碎桃花红满地,玉山倾倒再难扶’,芳灵蕙性,渺渺冥冥,不知那边去了”。这是空前绝后的死亡描写,是对死亡的诗意表达。群衩的言语也被曹雪芹花柳化。群钗建海棠社,各以草木花柳为号,大观园优伶皆以花命名,这都和群钗的神界胎记密切相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曹雪芹用群钗的神界胎记来形塑大观园群钗,有时还别出心裁地利用游戏来展开。如寿怡红群芳开夜宴,群钗抽签为戏,签上的花和诗句都是群钗风情、性情和命运的象征。
由于群钗具有神界的花柳草木特征,因此花开花落就成了群钗命运的象征。这一特征在神界已经确定。贾宝玉一走进太虚幻境,警幻仙姑就对他作歌曰:“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寄言众儿女,何必觅闲愁。”这是在用春花的短暂来警示儿女情感的虚幻。贾宝玉走进“薄命司”,发现两边对联写的是:“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为谁妍。”也是在用鲜花来比喻儿女情感的悲剧性结局。秦可卿临死前托梦给王熙凤,指出:“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也是用春花的命运来比喻群钗的命运。神瑛侍者和绛株仙草降凡后,也喜欢用花开花落来比喻人生聚散:“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他想的也有个道理,他说,‘人有聚就有散,聚时欢喜,到散时岂不冷清?既清冷则伤感,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开时令人爱慕,谢时则增惆怅,所以倒是不开的好’。故此人以为喜之时,他反以为悲。那宝玉的情性只愿常聚,生怕一时散了添悲,那花只愿常开,生怕一时谢了没趣;只到筵散花谢,虽有万种悲伤,也就无可如何了。”海棠花枯而复荣意味着石头将开始回归的历程——贾宝玉身上的那块通灵宝玉随即失去,贾母以之为不祥之兆令贾宝玉搬出大观园。从此,大观园诸艳逐渐搬出大观园,大观园诸艳逐渐回归太虚幻境,大观园成了荒芜的园地,成了妖异时现的所在。尤氏在大观园中邪后,贾府不得不请来法师,用符水驱妖孽。王熙凤大观园月夜感幽魂,受惊后随即到散花寺去求神签。这个散花寺无疑是群钗风流云散的象征。
三、大观园诗社的神界胎记
大观园诗社以海棠社始以桃花社终,大观园群钗的诗歌活动以咏海棠花始以咏柳絮终,其个人创作则以林黛玉的《葬花吟》始以贾宝玉的咏藕香榭终,整个诗社围绕着花柳、草木而忙碌。这一诗社活动的特质渊源于群钗的神界胎记:因为群钗乃神界草木花柳投胎,花柳草木的风姿花柳草木的凋谢实际上就是群衩风情、性情和命运的写照,所以群钗咏花柳、咏草木本质上就是自咏。
大观园总共举行过四次诗社活动,每一次均借咏花来咏群钗自身。第一次诗社活动在秋爽斋举行,题目是《咏白海棠》。湘云未与,后来和作了两首。群钗的海棠诗均为其自身风姿、性格和命运的写照。如探春之诗用玉和雪来比喻海棠花的细腻和洁白,凸显月下海棠的娇弱风姿和销魂魅力,既是咏花也是自比;“芳心一点娇无力”和探春所作风筝谜面“游丝一断浑无力”以及江边远别的判词乃同一意蕴,均在暗示探春远嫁。宝钗之诗首联咏叹海棠洁身自好的品行实即以海棠自比,颔联突出海棠花的洁白同时也在暗示宝钗守寡心境孤寂无意梳妆的悲剧命运,颈联状海棠花的淡雅和怯弱同时也暗示自己的品行受人欣赏并以泪多“讽刺宝黛二人”,尾联再次指出海棠花以清洁品行报答白帝化育之恩。史湘云的两首诗除了状写海棠花的情态外,主要暗示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用海棠花“也宜墙角也宜盆”来比喻史湘云“英豪阔大宽宏量”的性格;一是暗示史湘云婚后生活的不幸。大观园举行的第二次诗社活动是藕香榭咏菊花,题目由史相云、薛宝钗事先拟定。这些诗歌依然展现了群钗各自的性格。如林黛玉《咏菊》、《问菊》、《菊梦》咏叹菊花“孤标傲世”的“千古高风”,同时以“素怨”、“秋心”、“寂寞”、“幽怨”抒写抒情主人公的悲凉意绪。又如,作为群钗护法的绛洞花主,贾宝玉选择《访菊》、《种菊》是符合其身份的,诗中除了描摹菊花的临寒独立、绝尘脱俗外,主要表达了抒情主人公对菊花的怜惜之情。薛宝琴、李氏姐妹入住大观园后,群钗在芦雪庵争联即景诗并咏梅花。这是大观园的第三次诗社活动。薛宝琴、邢岫烟、李纹、李绮来到贾府,大观园群钗艳集,即景联诗凸显了十二位群钗尤其是湘云的才情,咏梅诗则展示了邢岫烟、李纹、薛宝琴的才性、风姿和命运。如薛宝琴《咏红梅花》诗吟咏梅花的奢华气象,活脱脱地凸显了薛宝琴的大家气象、绝色容颜和神界胎记。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后,史湘云因见柳花飘舞,便偶成一小令,群钗于是起社咏柳。这是大观园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诗社活动,群钗借助咏叹柳絮自况未来,悲凉至极。宝钗嫌众人所作“过于丧败”,于是翻众人之意而作《临江仙》词,获得众人齐声赞叹。词中暗寓薛宝钗的处世之道,也暗寓薛宝钗的命运。
林黛玉“自羡压倒桃花”,又被推为大观园桃花社社主,其所作歌行,都是因桃花之飘零触动自己的情思而起,都是对自己命运的哀叹,也是对群钗命运的哀叹。葬花与《葬花吟》均以花喻人,带有谶语的性质。大观园饯花神的行动实际上就是一次伤春的行动。林黛玉作《葬花吟》,是“因昨夜晴雯不开门一事,错疑在宝玉身上。至次日又可巧遇见饯花之期,正是一腔无明正未发泄,又勾起伤春愁思,因把些残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伤己,哭了几声,便随口念了几句”。《葬花吟》一开始就以“花谢花飞花满天”、“落絮轻沾扑绣帘”来点染大观园的神界胎记。在这个花柳世界中,“闺中女儿惜春暮”,感受到的是“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对花的摧残,惜花葬花引发的是红颜不再的悲叹:“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贾宝玉“在山坡上听见,先不过点头感叹,次后听到‘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不觉恸倒山坡之上,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不言炼字炼句词藻工拙,只想景想情,想事想理,反复追求,则实无再有。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使可解释这段悲伤。正是:花影不离身左右,鸟声只在耳东西”。贾宝玉的接受心态表明,“埋香冢葬花乃诸艳归源。《葬花吟》又系诸艳一偈也”(甲戌本脂评)。林黛玉的《桃花行》将帘内之人、帘外之花对举,以花衬人以人衬花,暗示自己命薄如桃花,行将夭亡。因此贾宝玉“看了并不称赞,却滚下泪来,便知是黛玉所作”。在贾宝玉看来,林黛玉曾经离丧,所以“作此哀音”。第七十回回前诗曰:“空将佛事图相报,已触飘风散艳花。一片精神传好句,题成谶语任吁嗟。”在曹雪芹的艺术构思中,《桃花行》无疑是一首谶诗。
贾宝玉一直在感悟绛株仙草以及一干草木的悲剧并形诸吟咏。在他的意识中,群钗即草木,花柳即群钗,草木之衰败即群钗之颓丧,花柳之悲剧即群钗之命运。迎春出嫁,贾府陪了四个丫头过去,贾宝玉感叹世上又少了五个清洁人了,因此特意到紫菱洲徘徊瞻顾,“见其轩窗寂寞,屏帐翛然,不过有几个该班上夜的老妪。再看那岸上的蓼花苇叶,池内的翠荇香菱,也都觉摇摇落落,似有追忆故人之态,迥非素常逞妍斗色之可比。既领略得如此寥落凄惨之景,是以情不自禁,乃信口吟成一歌”。眼中所见、心中所感、笔下所赋,皆衰败凄惨至极!贾宝玉预感到,园中之草木花柳之衰败将会是园中姐妹的命运。所以,脂砚斋在此处评曰:“先为对景悼颦儿作引。”黛玉死后,贾宝玉到潇湘馆吊谒,其景其情有过之而不及。晴雯死后,贾宝玉特作《芙蓉女儿诔》,叙晴雯生前行事,“缠绵而凄怆”(陆机《文赋》)。贾宝玉在诔文中回忆了晴雯来到怡红院后和自己“亲昵狎亵”的种种情景,推许晴雯的风神和德性,声讨谗害晴雯的诐奴和悍妇,对晴雯表示了深切的怀念和哀悼。这篇诔文乃贾宝玉师楚人之《大言》、《招魂》、《离骚》、《九辩》、《枯树》、《问难》、《秋水》、《大人先生传》而作。贾宝玉接续的这个传统是一个伟大的抒情传统,将香草美人的境界发挥到了极致。贾宝玉接续的这个传统和群钗的神界胎记——花柳草木是吻合的,因此诔文自始至终都将晴雯和草木花柳合二为一。贾宝玉认为:“薋葹妒其臭,茝兰竟被芟鉏!花原自怯,岂奈狂飙,柳本多愁,何禁骤雨。偶遭蛊虿之谗,遂抱膏肓之疚。故尔樱唇红褪,韵吐呻吟,杏脸香枯,色陈(咸页)颔。”这是用草木花柳的风姿、性情极其香艳气息来比喻晴雯,用花柳的备遭摧残来比喻晴雯之遭谗害,爱恋之心,痛楚之情,力透纸背!贾宝玉还提到晴雯“艳质将亡,槛外海棠预老”,这是草木群钗共命运的象征。贾宝玉以“群花之蕊、冰鲛之鷇、沁芳之泉、枫露之茗”祭奠晴雯是为了投合神界群钗的生活习性——群钗在太虚幻境中闻的是群芳髓品的是千红一窟,饮的是万艳同悲,而这些香料和饮品都是用草木之菁华尤其是花蕊制成的。贾宝玉确信“上帝垂旌,花宫待诏,生侪兰蕙,死辖芙蓉”,认为晴雯作为芙蓉花神是“相物以配才”,晴雯回归后过的是“发轫乎霞城,返旌乎玄圃”生活。这是对晴雯回归太虚幻境的体认。贾宝玉诔晴雯实际上就是诔林黛玉。这在作品中也有象征性描写。贾宝玉读完祭文后,丫鬟看到“一个人影从芙蓉花中走出来,以为是晴雯前来显魂,最后才发现这个人是满面含笑的林黛玉”。林黛玉认为“红绡帐里,公子多情,黄土垄中,女儿薄命’。这一联意思却好,只是‘红绡帐里’未免熟滥些,建议改成‘茜纱窗下,公子多情’。贾宝玉则将之改成“茜纱窗下,小姐多情,黄土垄中,丫鬟薄命”。遭到林黛玉反对后,又将之改成“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黛玉听了,忡然变色。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描写,表明晴雯的命运就是林黛玉的命运也就是群钗的命运。
四、《红楼梦》的诗性叙事
曹雪芹利用神道设教的方式把太虚幻境——大观园写成草木花柳世界,赋予降凡的太虚幻境诸风流冤孽以“花柳”、“草木”之特性,让大观园群钗带着这一神界胎记活跃于情感世界中,活跃于文学创作中。这一情景——人物特性的界定令《红楼梦》成功地接续了古典诗词曲赋的抒情传统,群钗被当作花柳草木来指称、形容和抒写,作为花主的贾宝玉也被写成了花柳——草木般的人物甚至被形塑为女性化的人物,贾宝玉咏花实际上就是咏群钗,群钗咏花实际上就是自咏,大观园的花开花落也就成了群钗命运的象征。曹雪芹成功地将诗性叙事嫁接到宗教叙事中,用抒情文学的资源、笔法来写小说,为生命意识的传达创造了诗情画意般的境界,诗性叙事令《红楼梦》有别于通俗小说而成为抒情体小说经典。这表明曹雪芹的小说关注的不仅仅是情节和矛盾冲突的设计,他更关注的是情景和境界的营造,这是曹雪芹对小说叙事的最大贡献。这表明《红楼梦》关注的不是思想不是事功甚至不是道德,《红楼梦》关注的仅仅是情缘仅仅是性情仅仅是生命,其灵魂是生命意识,其精神渊源是《庄子》,其文学渊源是传统的诗词曲赋。
小说中的很多场景是化用古典诗词的意境写成的。由于群钗是花柳的象征,所以人花相伴就拥有了浓厚的诗意,最为典型的情境就是史湘云醉卧花下一节。这段诗意般的情境即是化用卢纶《春词》诗句“醉眠花树下,半被落花埋”而来。小说中的爱情描写也大力借助古典戏剧的意境。贾宝玉和群钗在大观园中过的是“惜花与度曲”的生活。宝黛的爱情生活就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展开。贾宝玉在沁芳闸桥边桃花底下一块石上阅读《会真记》,正看到“落红成阵”,“只见一阵风过,把树头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落的满身满书满地皆是。宝玉要抖将下来,恐怕脚步践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来至池边,抖在池内。那花瓣浮在水面,飘飘荡荡,竟流出沁芳闸去了”。林黛玉则“肩上担着花锄,锄上挂着花囊,手内拿着花帚”,将花装在这绢袋里,埋到花冢里。黛玉和宝玉共读《会真记》后,又听到梨香院的戏子唱《牡丹亭》,其中的一系列伤春的曲子深深地打动了林黛玉:“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你在幽闺自怜。”这些诗句引发了林黛玉对古代伤春传统的联想:“水流花谢两无情。”“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脂砚斋指出:“前以《会真记》文,后以《牡丹亭》曲,加以有情有景销魂落魄诗词,总是争于令颦儿种病根也。”而这样一种诗意般的情节描写之所以打动了一代代读者则完全得益于古典诗词曲赋的抒情境界。
小说中的一些叙事手法运用了古典诗词比兴寄托的修辞手法。平儿理妆、香菱解裙均是传达贾宝玉意淫行动的经典例子,而其修辞手法也别具一格。贾宝玉为平儿理妆,“又将盆内的一枝并蒂秋蕙用竹剪刀撷了下来,与他簪在鬓上”。香菱和丫头们斗草,贾宝玉对香菱说:“你有夫妻蕙,我这里倒有一枝并蒂菱。”并将“夫妻蕙与并蒂菱用树枝儿抠了一个坑,先抓些落花来铺垫了,将这菱蕙安放好,又将些落花来掩了,方撮土掩埋平服”。用并蒂蕙和并蒂菱来表示男女成双成对是古典诗词的一种比兴寄托的手法,却被贾宝玉用于实际的传情达意之中。因此,我们可以说贾宝玉的这两个动作应该是一个诗意般的举动。贾宝玉和林黛玉谈论琴道时,王夫人分别送给贾宝玉和林黛玉一盆兰花,林黛玉却因花及人,感伤自身的情缘。黛玉看到盆中“有几枝双朵儿的,心中忽然一动,也不知是喜是悲,便呆呆的呆看”。贾宝玉一心只在琴上,建议林黛玉作《猗兰操》,林黛玉“听了,心里反不舒服。回到房中,看着花,想到‘草木当春,花鲜叶茂,想我年纪尚小,便像三秋蒲柳。若是果能随愿,或者渐渐的好来,不然,只恐似那花柳残春,怎禁得风催雨送’。想到那里,不禁又滴下泪来”。这同样是将古典诗词的伤春悲秋修辞手法直接运用于小说叙事的典型例子:林黛玉由并蒂花联想到自己情缘,由惜花而感伤自己的青春,使得整个场景蒙上了浓郁的悲凉氛围。可以这么说,林黛玉的这些举动是诗人的举动,是生活在诗歌中人才会有的生命感悟。
小说中的很多场景与其说是情节不如说是情境,是用古典诗词的抒情手法制造的意境。林黛玉到怡红院,丫鬟不给她开门,院子里又传来宝玉、宝钗二人的声音,“越想越伤感起来,也不顾苍苔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墙角边花阴之下,悲悲戚戚呜咽起来。原来这林黛玉秉绝代姿容,具希世俊美,不期这一哭,那附近柳枝花朵上的宿鸟栖鸦一闻此声,俱忒楞楞飞起远避,不忍再听。真是:花魂默默无情绪,鸟梦痴痴何处惊。因有一首诗道:颦儿才貌世应希,独抱幽芳出绣闺,呜咽一声犹未了,落花满地鸟惊飞”。这是一个诗情画意般的情节,凄清之景与感伤之情交相融会,境界深远。贾宝玉病后看到“一株大杏树,花已全落,叶稠阴翠,上面已结了豆子大小的许多小杏。宝玉因想道:能病了几天,竟把杏花辜负了!不觉倒‘绿叶成荫子满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舍。又想起邢岫烟已择了夫婿一事,虽说是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个好女儿。不过两年,便也要‘绿叶成荫子满枝’了。再过几日,这杏树子落枝空,再几年,岫烟未免乌发如银,红颜似槁了,因此不免伤心,只管对杏流泪叹息”。这本来是古代伤春文学的经典场景,却被贾宝玉用来传达意淫之情——对青春短暂和美丽无常的体认,对青春和美丽的眷恋,也就是对生命的眷恋!
[1] 吴光正.神道设教:明清章回小说叙事的民族传统[J].文艺研究,2007,(12).
[2] 陈文新.明清章回小说的表达形式与文言叙事传统[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1).
[3] 宋淇.《红楼梦》识要——宋淇红学论集[C].北京:中国书店,2000:105-184.
[4] 吴光正,罗媛.花主、诗人与哲人——神道设教与贾宝玉的形象设计[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3).
〔责任编辑:王晓春〕
J2
A
1007-4937(2010)06-0086-06
2010-09-16
200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神道设教:明清章回小说叙事的民族传统》的前期成果(07CZW 018)
吴光正 (1969-),男,江西永丰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明清文学和宗教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