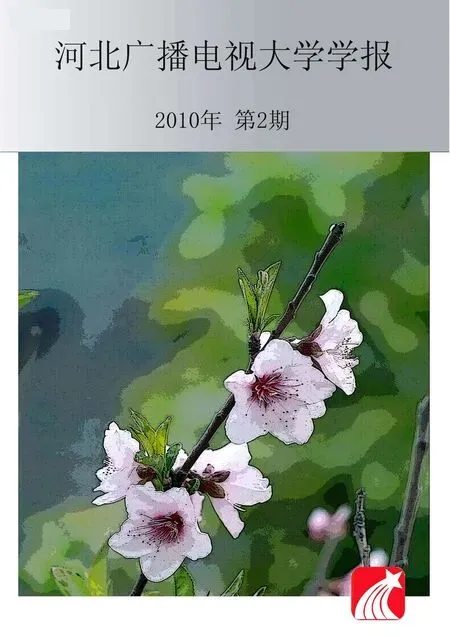探寻内在联系 批驳错简之说*
——《天问》错简调整的辩驳
刘桂荣
(运城学院师范分院中文系,山西运城 044000)
探寻内在联系 批驳错简之说*
——《天问》错简调整的辩驳
刘桂荣
(运城学院师范分院中文系,山西运城 044000)
反思《天问》错简调整的缺憾,依据文本的内在联系,对三处调整进行辩驳:鲧禹治水属于大自然神话,不应后移至夏初;夏朝事中鲧、羿、风、雨、鳌的神话,围绕“天式从横”而写,不应分散;篇末写自我处境,问楚国状况,无须分开。
错简;调整;辩驳
屈原的《天问》问遍天地宇宙,问遍神话传说,问遍夏商周三代兴亡之史实,质问之多独步千古;后人解读《天问》文字有障碍,传说多变迁,史实难确定,疑惑之多难以计数。而最大的疑惑是怀疑其有错简,认为文意难解、层次紊乱的原因是《天问》在传承中竹简断开了,次序颠倒了。东汉王逸说“其文义不次序”,明代汪瑗怀疑其有错简,清代屈复首开其错简整理之风。20世纪初,楚辞学名家染指错简调整者为数不少:游国恩、郭沫若、林庚、孙作云、苏雪林、金开诚、郭世谦等。
研读《天问》一次又一次,比照错简调整了一种又一种,困惑中反思了一回又一回,终于探求到名家正简的些许规律:各种错简调整或从依据上、或从方法上、或从结论上都遵循着按照历史先后的时间顺序重新编排的原则。但是,《天问》是一首咏史性的哲理抒情诗,它借助史实抒发愤懑,阐发哲理。为了抒情的宗旨,为了说理的需求,屈原完全可以突破历史顺序的束缚,产生自我的唯一的灵动的一时的构思,他人无法也无须靠着臆测去演绎“复活屈原”“复制《天问》”的神话。探寻文本的内在联系,便会感悟到王逸的传本有其个性的结构、深层的内涵、别致的匠心;也会发现一处又一处错简调整的缺憾;更会发现原文一段又一段自有其风韵。
一、鲧禹治水属大自然神话
“不任汩鸿,师何以尚之?佥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鸱龟曳衔,鲧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纂就前绪,遂成考功。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洪泉极深,何以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河海应龙?何尽何历?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屈复、郭沫若、郭世谦把以上鲧禹治水的诗句后移至夏朝之前。[1]p86把鲧禹治水从自然史中剔除,作为夏朝历史的开端,此种做法实为不妥。
《山海经·海内经》云“: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在上古时期,洪水泛滥,大地覆没,于是产生天神拯救大地的神话。当鲧禹平治水土后,方划定九州。可见,治水与大地的自然神话前后分明。此段位于问天之后问地之前,有承上启下、自然过渡的妙用。
鲧禹治水与下文“康回冯怒,地何故以东南倾?九州安错?川谷何氵夸”的大地之问紧密连接。治水成功后,九州浮现;地倾东南后,百川归海。这是关于治水的自然史传说,并非关于夏朝的人类史传说。质疑的核心是治水神话历史化后褒鲧贬禹的成说,并非夏朝的历史。放于问地之前,文义贯通;移至夏朝之前,则内容相左。若将鲧禹治水之事后移,承接的是禹与涂山女私通。从形式上考虑,以血缘关系为依据,鲧、禹、启三代一脉相承,应归于一处。从内在联系上辨析,以写作意图作判断,两处皆写禹而叙述角度不同:一处叙述禹治水以定九州,质问关于大地的神话;一处叙述禹的婚姻蕃衍,质疑夏朝先祖的身世,不应合为一处。表层顺序应服从于深层构思。我们不能胶柱鼓瑟,因鲧、禹、启同为夏朝祖先,便以意为之,调整原文;我们应该回归文本,把握内在联系,认定鲧禹治水属于大自然神话的事实,维护天、地、人的原文构思。
顾颉刚说:“鲧禹治水的传说存在神话与历史两个体系。神话在前,古史则是对神话的历史化。”[2]p88此段问天神拯救大地的神话,鲧禹乃天神形象。另外,《天问》对夏、商、周的质疑都从祖先繁衍的神话问起:夏问禹与涂山女私通而生启,商问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周问姜女原履大人迹生后稷而弃之。夏朝历史从禹与涂山女问起,不是从鲧禹治水问起,方有遥相呼应之妙。在夏朝前添加鲧禹治水,有弄巧成拙之嫌。故而,此处没有错简,无须调整。
二、违背“天式从横”的传说
“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咸播禾巨黍 ,莆是营。何由并投,而鲧疾修盈?”郭沫若、郭世谦、孙作云将此两条插入鲧禹治水处,有些顾此失彼。因为此处虽然写鲧并且为鲧鸣不平,但并非鲧治水事,而是与原文相连接,另有其事。“白霓婴,胡为此堂?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臧?天式从横,阳离爰死。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号起雨,何以兴之?撰体协胁,鹿何膺之?鳌戴山扌卞,何以安之?释舟陵行,何以迁之?”屈复、郭沫若、郭世谦、孙作云等认为此处问日月云雨风等自然现象,四人皆将此四条前移至自然传说处,但具体移法各不相同。[1]p86反对前移的理由有两个:其一上下文表面上看似脱节,而深层内涵密切关联;其二此处围绕“天式从横,阳离爰死”的观点组织材料,是以类相归不是依时相问,原文围绕论点,事事相关而问,衔接妙趣横生。
兹体味文本详细论述,共相探讨。先说“阻穷西征”两条,上下皆与后羿之事暗相连接。林庚分析《,天问》在古代原始传说中往往占有第一手材料,鲧事插入后羿事中,表明在原始传说中鲧和后羿曾经打过交道。“帝降夷羿,革孽夏民”,因为后羿要取代夏王朝,所以夏之祖先鲧“阻穷西征”便理固宜然。[3]p208-209鲧阻止后羿率领的有穷部落西征伐夏,但依时空而论鲧早应死去,故而,针对神话发问“,化为黄熊,巫何活焉”,意谓鲧已死去,化为黄熊,巫如何使之复活。
长生不老、死而复活的神话《,山海经》《、淮南子》中多有记载,远古时期普遍流传,古人信而不疑,屈原由上下文联想起相类似的传说,归为一处,用“天式从横,阳离爰死”的论点统率之、批驳之。先问鲧死后如何“化为黄熊”;后问羿如何丢了不死良药“,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臧”;再问羿死后如何化为大鸟“,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天式从横,阳离爰死”,屈原认为自然法则纵横分明,阳气离开身体人就会死亡。诸多神话令人怀疑,岂能相信。“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的具体解释,见仁见智:王逸、洪兴祖说指《列仙传》中王子侨死后化为大鸟,[4]p89林庚说指羿死后化为大鸟,[3]p210熊任望说指钟山之神鼓与另一神钦被处死后化为大鸟,[5]p78虽然看法各异,但传说有相同的实质,即死而复生化为大鸟。“阳离爰死”,怎能复活,正是屈原质疑的关键所在“;天式从横”,不可违反,恰是此处诸多神话的内在联系,可谓形散神不散。
“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由大鸟的叫声,联想到传说中雨师呼风唤雨的奇怪号叫,还有风神的遥相呼应。古人对于自然现象疑惑不解时,往往迷信超人的力量,编撰神灵的故事,于是产生了神话。战国时期是理性觉醒的时代,对于宇宙自然的思考,是先哲们的共性思维,具有时代性和普遍性。《庄子·天运篇》《、逸周书·周祝解》《、荀子·天论》都问及天地的开辟,日月的运行,风雨的产生。参照域外的文献,这种思索也具有世界性和人类性。古印度的宗教典籍《黎俱吠陀·有无歌》、古波斯的《火教经》,也有相似的提问。“号起雨,何以兴之?撰体协胁,鹿何膺之”,屈原怀疑关于雨师风神的神话,于是问到雨师用什么兴雨?风神如何来相应?刮风下雨乃自然现象,并非天神的奇异功能。这是“天式纵横”的无神论,也是朴素的唯物论观点。
“鳌戴山扌卞,何以安之?释舟陵行,何以迁之?”巨鳌背负仙山且拍手嬉戏,山如何能安稳?把船放在陆地上行走,如何能移动?屈原以类相归,继续追问违背自然法规的神话。大山平稳牢固,巨鳌怎么背负?船只能在水中航行,怎能在陆地上行走?同时,一语双关,与下文浇事相连接“,惟浇在户,何求于嫂”。《论语·宪问》“:羿善射,(浇)荡舟。”羿和浇乃有穷部落的两个大英雄。传说后羿首创弓矢,浇能陆地行舟。闻一多曰“:考传说中之浇本即鳌。”[6]p33诸多传说,与前后内容巧妙相连,与“天式从横”的论点密切相关。此处构思独具匠心,不必挪移,无须正简。
三、篇末宗旨乃彰显忠名
楚辞学大家游国恩将《天问》结尾处的顺序调整为:“荆勋作师,夫何长?吴光争国,久余是胜。何环穿自闾社丘陵,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长。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薄暮雷电,归何忧?厥严不奉,帝何求?伏匿穴处,爰何云?悔过改更,我又何言?”[7]p483他将问楚国历史的诗句集中调到前面,问屈原处境的诗句抽出放到后面,颇有新意。但这种局部的打乱重排对个别诗句的理解未必确切 ,如“荆勋作师”处、“吾告堵敖”处、“厥严不奉”处,训释不一而足,未有定论。其二屈原之处境与楚国之状况的发问互相激发,如何能一分为二。其三,《天问》全文四句一条,其两句一组的拆开挪移,既与文本章法自相矛盾,又违反了竹简的书写形式。
《天问》篇末写自我处境,问楚国状况,二者融为一体,旨在唤醒楚王,彰显忠名。末句“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王逸解:“屈原言我何敢尝试君上,自干中直之名,以显彰后世乎?”[4]p103王说影响颇大,但屈原不愿彰显忠名的理解,与其毕生追求忠诚的言行自相矛盾。林庚解释为“子文‘自毁其家以纾国难’,他辅佐成王,振兴楚国,忠名弥彰”。[3]p246吴广平解释为“楚成王弑杀堵敖而得忠直之名”。[8]p126另有推演王逸之说的诸多解释。虽林林总总,却总觉不妥帖,甚或感到如此解释,难以收束全文,《天问》似乎没有写完。
思索《天问》全诗的主题:怀疑天命、强调人事、赞颂明君、突显忠臣、问中暗含明君贤臣的美政观念。如此领悟要旨,使人茅塞初开,查阅《古代汉语大辞典》,比照传统注释,顿觉豁然开朗:“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试,不应解作“尝试”,而应解作“试探”。例句:“主贤明则悉心以事之,不肖则饰奸以试之。”(《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予,不应解作“给予”,而应解作“赞许”。例句:“主盛处贤,而自予雄也。”(《管子·宙合》)句意为如何试探君上赞许自我,使自己的忠名更加显著呢?忠诚、忠信、忠直,以至忠贞、忠烈,屈原为此“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中反复吟诵之,《天问》末勿忘重申之。篇末回归主旨,为其忠而怨,为其忠而疑,为其忠而问。全篇归于楚事,合乎全文的结构层次、写作意图;收于忠名,合乎作者的政治理想、个人志趣。屈原以讽谏君王,表白忠诚,结束全诗,可谓卒章显志,文有豹尾。如此情理兼备的文本,根本无须正简。
毛庆回顾错简整理史得出的结论:“《天问》基本无错简。万一哪一天地下出土文物证明确有错简,也不会超过几处。”[9]p323《天问》其他地方的错简调整也需要反思、澄清、辩驳;《天问》文本的深层内涵、内在联系、宗旨情趣有待更深入地挖掘。
[1]郭世谦.屈原天问今译考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2]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8.
[3]林庚.林庚楚辞研究两种[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4]洪兴祖.楚辞补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5]熊任望.屈原辞译注[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
[6]闻一多.离骚解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7]游国恩.天问纂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2.
[8]吴广平.楚辞(图文本)[M].长沙:岳麓书社,2006.
[9]毛庆.屈骚艺术研究[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赵 君)
I206.2
A
1008-469X(2010)02-0027-03
2010-01-16
刘桂荣(1969-),女,山西运城人,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