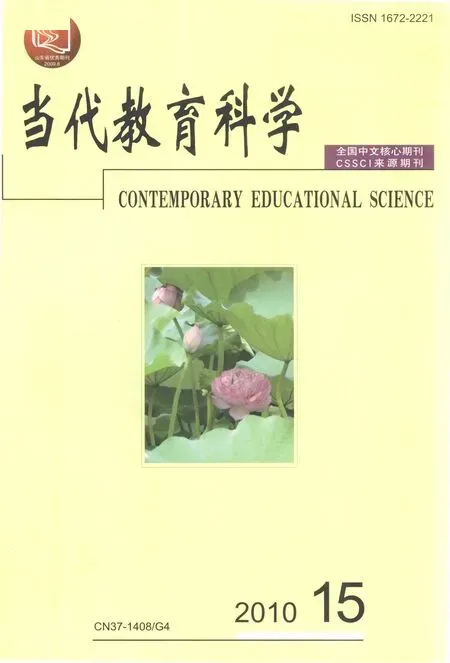繁荣和贫困: 教育学定位的事实之思与价值之辨*
● 于翠翠 朱成科
繁荣和贫困: 教育学定位的事实之思与价值之辨*
● 于翠翠 朱成科
教育学能否捍卫自身的独立性,不仅仅关系到作为一门学科的定位,同时关系到其发展的取向。教育学之所以出现“繁荣”与“贫困”共存的尴尬局面,在于教育学定位中出现的事实困境和价值异化,要实现教育学的创生,关键在于确立无立场的教育学情愫、“作者意识”的教育学角色、双向反观的教育学视野。
教育学;事实;价值
如果说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使独立形态的教育学得以破土而生,那么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则明确诠释了其把教育学建设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设想。 在教育学 “艰苦卓绝的探索和富有想象力的建设”[1]过程中,其内在空间纬度和外在时间经度也得以不断拓展。与此同时,教育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亦愈发暧昧,以至于霍金斯曾发出如下感慨:“‘教育学’不是一门学科。今天,即使是把教育学视为一门学科的想法,也会使人感到不安和难堪。‘教育学’是一种次等学科,把其他‘真正’的学科共冶一炉,所以在其他严谨的学科同侪眼中,根本不屑一顾。在讨论学科问题的真正学术著作当中,你不会找到‘教育学’这一项目。”[2]面对“迷惘”和“躁动”的教育学科,有人认为“教育学成为‘别的学科领地’”[3],有人认为“教育学在与其他学科的砥砺中,陷入‘无根’与‘漂泊’的状态”[4]。“沛然莫能御之”的教育学正逐渐式微,形成了“‘繁荣的低谷’与‘贫乏的丰富’之间的典型矛盾”[5]。
一、教育学的事实之思
(一)边界模糊的教育学范畴
教育学与其他学科的边界不清,不仅使学科彼此之间在重叠交叉之处存有争议,也使得学科团队人员因未达成共识造成研究“失范”而使学术信仰缺失。教育学要么不加限制地无限发展扩大化,要么自身价值日益萎缩狭窄化。沿着分化与整合的理路分析教育学,通过对教育学“症候”的“病理学”阐释,我们发现相较整合而言,分化已然成为教育学的追求。“分化既是教育学进化的标志,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教育学原创力衰弱的标志;枝杈与根基相比,总是营养不良。离核心层或根基越远,教育学科的创造力和分化力越弱。”[6]由教育学衍生出来的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等学科群使得“复数教育科学”正在成为一种幻象。一言以蔽之,我们不断地反躬自问,“它究竟是胜利的号角,还是衰亡的回光返照;它到底是新时代的开始,还是仅仅预示着新时代的终结?”[7]
这正如搬进特洛伊城的木马,教育学愈借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来有效阐释自己的问题域时,却反而因相关学科的浸染而销蚀殆尽。教育学将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上述学科混淆为内在自我“本体”,不断拓宽所形成的多焦点概览,正在成为“乱炖”似的大杂烩。不断地“在铁屋中呐喊”的教育学尚未“出场”便萌生“退场”之念。
(二)表达乏力的教育学话语
包括赫尔巴特在内的教育研究者,一再愧疚而且无奈地提示教育学科被其他学科侵入和占领的事实;但另一个事实却往往被人忽略:在漫长难捱的“被殖民生涯”中,教育学科没有全然放弃抵抗,更没有失去作为一个专业领域的理论所应有的创造力和影响力,只是与“殖民者”们的强大相比,力量显得过于微弱。[8]教育学自身话语权不足使得其假借新词汇、新概念、新术语,不断地对“陈旧”的话语体例加以翻新。教育学只是被动地被大家运用新的语言来表征意义,只不过这是“穿新鞋走老路式”地对原有内容的复述。内生工具化的立场支持使得教育学朴素的话语表达缺席。
与此同时,教育学内在思维范式的文化特质因固着于自身的生态话语权,彼此之间缺乏有效的融合与沟通。孕育教育学话语的原文化与教育学将要运用其中的目标文化之间不是一种平等的“我——你”开放性双边协商对话关系,而是一边倒的“他——我”压迫性对话关系。在面对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话语图谱中,彼此间内在文化认同性的冲突失调导致教育学因难以解开“场域茧”而呈现单向度的“钟摆骑墙”状态。内在茧式化的品质使得教育学系统的话语表达离析。
(三)运用失当的教育学研究方法
教育学由描述研究到质性研究,由坐而论道的夸夸其谈走向“扎根理论”的田野调查。在实证性研究日益关注的今天,教育学中的叙事研究几乎等同于历史学文本化,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教育案例简单化约为讲故事,在不可避免地将研究思维模式、意识形态投入其中的时候,使得研究中自觉不自觉地充斥着想象、创造成分。这正如摄影作品展,在如实表达客观事实的同时,却又因这是摄影者的独具匠心之作,而富于艺术美感。难怪有学者大呼“教育学科从来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艺术存在”。
与此同时,理论与实践作为萦绕教育学适切发展的互生互长的一对关系,出现了裂痕。一方面,以绝对主义的思维方式来“命令”学习者遵守,用“理性的逻辑”来规约现实行为与实践活动,对于复杂的教育事件与人的复杂性缺乏必要的分析和理解,对变化了的教育改革实践缺乏必要的提升、反思和批判。[9]另一方面,摆脱理论“羁绊”的实践尽管得以吸收久违的甘露而缓解干旱,以萌发的驱动力来宣泄内在冲动,却因缺少指向自身的反思性逻辑超越,而成为一种游离生命本体、机械地定格为“向性化”的行动。
二、教育学的价值之辨
关于价值的界说,有学者从经济学、人与物的关系和社会学三个维度加以梳理。从经济学角度,价值是凝结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从人与物的关系,价值是事物所具有的客观属性与人的主观需要之间的关系,即事物对于人的有用性;从社会学的角度,价值是事物对于人的意义、对于社会的意义,以及这两种意义的动态平衡关系。[10]然而,僵化的教育活动因为“无价值”而使教育世界带有丝丝冰冷的寒气,造成教育学平面化、快餐化发展。教育学要立起来、活起来,就需要对其重新考辨。
(一)基础主义到内在生成的逻辑原则
基础主义被视为解决教育问题中的 “回溯论证”的产物。即,教育赋予了充分确证的真信念的意义。因为按照这一定义,确证某种信念的最自然的方式乃是产生一个确证的论证:信念A通过援引另一信念B来确证。在此关系中,信念A是以某种可接受的方式从信念B中推论出来的,信念B也由此能够作为接受信念A的理由。但这样一来,信念B本身又必须以某种方式得以论证,如此反复进行,就使确证陷入一个无限的回溯系列。[11]来自某种个体优越地位的信念原则或过程作为一个培养基,培育教育规律“同质”而非“异质”发展,“内部”而非“外部”控制。尤其是20世纪以降,把数学还原到逻辑与集合论基础的尝试,把有关外部世界的所有物理语言,化约为可观察的感性经验、逻辑与集合论的语言三者结合的努力……昭示了自然科学以肯定的逻辑方式构造于人的直接经验基础之上。遵循确定性品质的教育学在寻找“阿基米德点”的过程中,不断地以感性认识取代理性认识,不言自明地寻求合适且合理的循环论证,却陷入了无限自我回溯的结茧化困境。
教育学没有普遍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律。一味地追求绝对化只会因自身清高而偏离育人宗旨的教育轨道,在“作茧自缚”中丧失自己的品性。这种所谓彻底的阐释与其说是过度,不如说是不足。因为它没能进行足够充分地元素分析,没有进行境遇化的时代考究。正如奥克肖特所说:“一切都是暂时的。”为人的教育学内在赋予其走向宽容、多元与生活本身的生成性品质之中。这种走向被描述得像流淌的河流,而不像固定不变的标尺。教育学之所以为真的教育学,在于其能超越摹写实在本身的存在方式而成功灵活应用于各种情境之中;在于其有效防止回归生活世界的意义剥离中,以网络式的差异原创而非等级式的科层体系加以展现。教育学的生成性在于寻求提示或谈话,而不是结论,在于主动参与学科建设,而不是被动接受。
(二)偏执化到整体化的价值取向
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带给人们普遍的 “面对最佳选择的困惑”,使人类生活在一个 “充满困境的时代”。[12]由于二元论思维从非此即彼的立场思考问题,因而“造成教育诠释与定位问题上呈现出明显的‘排斥性’品质以及片面化特征,使教育系统内部的各个子系统彼此对立,并从中选择某一确定为本质存在的‘内讧式纷争’”。[13]无论是教育理论的研究,还是教育实践的探索,所指向的都是教育领域中存在的某一方面或层次;当我们的视域投射到某一特殊的教育样态时,无形之中使教育领域呈现出分离化趋势。“盲人摸象”的思维形成的“不是……就是……”的原则使得教育发展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视域中进行茧式化的偏执选择。教育因臆测的独断、自以为是的见解、非此即彼的价值观而显得麻烦。坐标点漂移而不是坐标点建构的钟摆取向下,真理在争执之中演变成一笔“糊涂账”,而不是愈辨愈明。
教育学研究所要揭示的是表面粗浅意义下隐藏着的某种深刻的意义。流淌于思维间隙的意识流,在多向道涌动中,正在擦除“辖域化”而带来的单向偏执,以“居间”的方式在淤泥沉积的轨迹中开辟新航线。这正如矗立在眼前的立方体,世上没有人能同时看到六个面。而要想对它进行清楚地观察,需要绕它转动,进行整体式地全焦点概览,通过对立方体暴露其显在一面的感知,来体味其隐藏方面的存在。全景敞视思维意识下的教育学是一种有机整合的教育学体系,它摒弃了固着于某一方面问题以求深入的极端化倾向,在视域的流变与方法的延异中多方面地看问题,以防止教育学单向度信条的垄断,达成彼此之间的“重叠共识”。
(三)“人为的”到“为人的”教育手段
教育活动沿着“输入——加工”模式展开,把个性鲜明的学生加工成适应社会需要的 “产品”。“工具——效用”的教育在推动社会进步中获得的力量和成就,以及无与伦比的威望使教育的目的仅仅限于培养一技之长的精英人才,使自己日益简单化的同时,也使自己最大限度的普遍化成为可能。效用原则在使教育内容变得更加“有用”的同时,也使教育的独立品格、完整形象、丰富内涵乃至自身尊严正在逐渐消失。[14]“意义教育”蜕化为一种“谋生教育”,“分数教育”和“证书教育”的强势扩张导致教育因内在价值萎缩而形成的教育空壳化存在。
“人为”的教育手段物化教育的同时,凸显了教育的功利性倾向,扭曲了教育是“人之自我建构的实践活动”[15]这一基本命题。教育学不仅仅是谋生之学,更是实现人的自我创造、自我发展的育人之学。“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态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16]“为人”的教育学就是要以人的生命、生活、生长、生成为契机,在启蒙人的精神、陶冶人的心灵为旨趣的教育活动中实现人的自我改进,使人在“成人之学”中懂得“为人之道”。
三、教育学的创生之路
教育活动是人的活动,人不仅生活在现实的世界,又不断构筑着其可能的世界,从而赋予教育息人、息事、息心的价值旨趣与思维方式。有学者曾指出,教育学研究成为一个自主的、内在逻辑一致的学术研究领域,需要正确处理好有为与无为、去伪与存真、本土与世界、事功与责任的关系。[17]教育学从追求存在的始基,到以观念为存在的本原,从预设终极的大全,到建构问题域的世界图景,不断寻找一条适合于自身发展的创生路向。
(一)无立场的教育学情愫
教育学作为指南针,要为现实的教育选择提供更好的教育,就需要超越片面抑或简单的立场,在对教育和生活等各方面的公共问题和公正意义进行领悟的同时,达成高于任何一种价值观的教育思想,形成罗尔斯意义上的“重叠共识”。无立场的教育学并不是寻找答案的教育学,而是来刺激教育和生活的教育学,或者说形成教育思想的诱惑和生活的导向的教育学,它以思想展开教育行动的可能性,展示生活的可能性,让教育行动创造更多的形式,让教育中的人能够开展建构自我的生活。[18]超越蜗居时代偏安一方“回报递减”的尴尬窘境,无立场的教育学并不是没有立场,相反,其由局限于特定问题领域的狭窄立场,引向事情本身的多维复杂立场。教育学运用无立场的情怀,不是思想的贫瘠和立场动摇的表现,而是一种研究问题的思想态度标识,是一种谦逊的情怀。在真实面对事情的时候,要悬置自己的先验经验,尽量纯化自己的观察视角,以求得最大程度还事情以本来面目。其中,我们要学会限定自己的“理性僭越”的不自觉倾向,谨慎梳理理论的使用限度和自身内在的局限,而不是“无限理性”的四处张扬,以问题本身的显现方式,推定问题的解决方法。[19]
(二)“作者意识”的教育学角色
教育学和相关学科的密切关系,以及教育学自身“次等学科”的地位,造成相关学科是教育学的资料室,教育学是资料室的忠诚读者。强烈的“读者意识”表明了教育学如饥似渴地追寻其他学科的知识同时,其自身“作者意识”在不断受到压抑和排斥。教育学作为一名“读者”,可以用极少的能量和精力,迅速便捷地在“资料室”里汲取自己所需要尽可能多的养料;而这一优势犹如阿里基斯之踵,正是教育学最为薄弱的劣势所在。教育学置于“他者语境”之下,逐步放弃了思考的权利,失去了思考、体验和冥想的能力,变得孱弱无力,即使如此,也沉浸在对“资料室”的顶礼膜拜之中。教育学要具有独立的勇气,就要有内在消化而非穿衣带饰的创造性转化,就需要唤醒自己的“作者意识”,在“自我的语境”中诠释和演绎自我,在众声喧哗的汪洋中具有“独白”的勇气,能够并且敢于在“照着说”后“接着说”。
(三)双向反观的教育学视野
教育学不仅要从学理层面把握其基于自身思维品性看待其他学科,还应该有一个借此反观教育学自身的视角,以及由自身视角来建立的某种有效交流,以此发现问题、拓展思路。在双向反观的教育学视野中,更需要对教育学自身返本开新培育教育学自身的问题意识,以利于进一步透视学科间际的“思想褶皱”。
任何一门学科的疆界无限扩大,在损害学科自身的同时,也不利于其他学科的良性发展。教育学在指明自身种种可能发展的同时,也要声明其相对的不可能发展,并将其视为教育学的禁区,免于无意义的推论。这不等同于教育学要和其他学科之间建立起等级森严的壁垒,而是立足于教育学自身,坚定地建立起以教育学为起点和终点的独立学科的立场,有条件地因时汇集相关学科,并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点处具有自身的逻辑起点和运行规律。教育学的边限无形之中成为教育学的保护带,任何对相关学科的无限制攫取不仅使教育学成为一个“拼凑的裁缝”,更导致了教育学丧失了自身,使教育学繁荣发展的背后暗藏着宿命般的贫困和虚浮。
[1]蒋建华.中国教育研究需要中国气派—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郭华博士访谈录[N].中国教育学报,2004-5-15.
[2]华勒斯坦.学科·知识·权力[M].北京:三联书店,1999:43.
[3]陈桂生.略论教育学成为“别的学科领地”的现象[J].教育研究,1994,(7):38-41.
[4]程亮.中国教育学:从“漂泊”到“寻根”[J].教育学报,2008,(3):21-25.
[5]李森,张东.教学论研究三十年:实然之境与应然之策[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120.
[6][7][8]李政涛.教育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对话”——从知识、科学、信仰和人的角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60,60,237.
[9]朱成科.分化与整合:论中国教育学的学科范式[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14.
[10]李森,潘光文.教学论研究的事实与价值之思[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117-118.
[11]陈嘉明.知识与确证:当代知识引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83.
[12][13]郝德永.不可“定义”的教育—论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终结[J].教育研究,1994,(9):13.14.
[14]王艹 律.价值观教育的合法性[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7.
[15]鲁洁.教育:人之自我建构的实践活动[J].教育研究,1998,(9):13-17.
[16][德]恩斯特·卡西尔.甘阳译.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8.
[17]靳玉乐.当前教育科学研究的几个问题[J].教育研究,2007,(5):5l-55.
[18]金生鈜.无立场的教育学思维——关怀人间、人事、人心[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9):3.
[19]秦德生,朱成科.朴素地追问“自者”的教育问题——中国比较教育学的“问题域”重构[J].外国教育研究,2007,(5):16.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项目《建国以来基础教育改革的主要理论与时代创新研究》(编号:06JA880012)阶段性成果之一。
于翠翠/渤海大学教育学院课程与教学研究中心2008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朱成科/渤海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刘丙元)
——《教育学原理研究》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