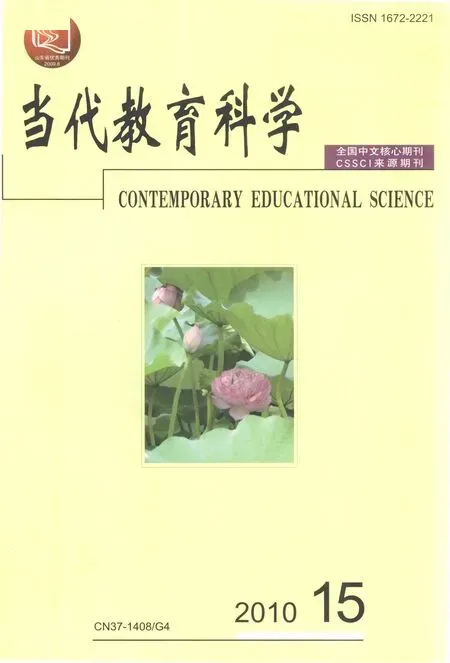想象力的教育危机与哲学思考(上)*
● 潘庆玉
想象力的教育危机与哲学思考(上)*
● 潘庆玉
想象力是人类保持自身活力和发展动力的原始文化基因,是人类把自身从有限的现实世界带向无限的可能世界的不竭动力,是贯穿人类精神生活一切方面的最隐秘最伟大的力量。但是想象力的丰满形象在教育中遭受到了严重的挤压和扭曲,它被减缩为与逻辑思维相对立的形象思维而蜗居在人文艺术教育领域得以暂时栖身;它被视为不切实际、毫无用处的幻想和胡编乱造的虚构而沦为教育所极力回避和抵制的不良因素。教育呼唤想象力,想象力将赋予教育以新的生命和活力。富有想象力的教育不仅是一种系统的理论或理念上的形而上思考,而且是一套行之有效的创造性的教育行动方案。
想象力;教育危机;富有想象力的教育
一、中国教育陷入想象力危机
2009年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世界21个国家的调查显示,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世界第一,而创造力却排名倒数第五,只有4.7%中小学生认为自己有好奇心和想象力,而希望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只有14.9%。早在2000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联合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做过一项名为“我国城市儿童的想象力与幻想”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冒险性和想象力得分大大低于平均值。美国公布的“2001年全球重要科学发现100项”中,中国“三项科学新发现榜上有名”,其中两项是与美国合作完成,独立完成的只有一项。美国的几个专业学会共同评出的影响人类20世纪生活的20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中国学子每年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有2000余人,为非美裔学生之冠,比排第二的印度多出一倍,但美国专家却评论说,虽然中国学子成绩了得,想象力却是大为缺乏。[1]
也许我们可以怀疑上述数字的准确性,怀疑数据选取的公正性,甚至还可以怀疑这类调查本身的倾向性,但是我们却难以回避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教育正面临着愈来愈严重的想象力危机。这个危机不只是表现在上述丧失想象力的教育结果上,而且还表现在学校教肓制度与教育教学实践对想象力的遗弃与压制上。当我们的孩子说“雪融化了是春天”,而语文老师纠正说“错了,雪融化了只能是水”的时候,当孩子们把一首首文辞优美的古诗词翻译成白话文死记硬背以应付考试的时候,当学生通过无数次的机械练习突然顿悟到数学不过就是计算技巧的时候,当小学生不好好读书而热衷于所谓考场作文制胜法宝的时候,我们正在直面想象力在教育中的死亡。在现实的教育中,想象力不再被当作积极的创造性力量,而是被看成威胁学生学习成绩、影响正常教学秩序的捣乱分子。教育中的一切都已经被各种考试标准和评估细则预先决定了,我们只需按图索骥,只需模仿和训练,我们不再需要任何想象力,它对于我们来说太过奢侈了。
但是,没有想象力,就没有人类的任何发明创造和艺术创作。想象力是人类保持自身活力和发展动力的原始文化基因。想象力对人类而言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而是人类把自身从有限的现实世界带向无限的可能世界的不竭动力,是贯穿人类精神生活一切方面的最隐秘最伟大的力量。我们与其说生活在现实中,不如说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对未来的想象中。想象,构成了我们存在的最重要的一个维度,它把过去、现在与未来凝聚融通成一种奔腾不息地向前运动的内在精神结构。丧失了想象力,我们的心灵将会无处栖居。丧失了想象力,我们的生活就会失去存在的价值。
历史上从来不乏对想象力的讴歌和赞美,想象力几乎主宰了一切文学艺术领域。但是,在以人类知识再生产为己任的教育领域,想象力的地位和作用似乎一直处在名不副实的状态。几乎没有人会否认想象力在教育中的价值,也没有人会否认想象力在诸如科学发明、艺术创造与技术设计中的作用,但是,在我们的教育制度的安排中,在我们的课程设置中,在我们的教学过程中,尤其在我们的教育评价中,究竟给想象力留下了多大的发展空间?遗憾的是,作为口号和意念的想象力虽然充斥在我们的教育话语里,但作为严肃的教育理论研究的想象力还处在蛮荒状态,作为教育实践智慧的想象力还被排斥在片面的科学理性主宰的课堂之外,作为学习过程核心动力机制的想象力还被钳制在以理性认知为主导的单一模式中,作为教育评价核心价值尺度的想象力还被标准化意识践踏在虚假的客观性的泥潭中。教育已经丧失了想象力,我们的教育正面临想象力的危机。不正视这一现实,我们就会迷失教育改革的方向,就会陷入各种纷繁复杂、相互纠结的教育乱相和困顿之中。不赋予教育以丰富的想象力,我们就不可能自信地回答困扰温家宝总理的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想象力,应当成为引领当前教育改革的主题词之一,它既需要我们从哲学的高度重新来审理和评估它的教育意蕴与价值,也需要我们从教育实践的角度来探讨拓展教育教学想象空间的创造性途径与方法。
二、想象力在教育中的遭遇
想象力就像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空气,通过呼吸我们能很清晰地感觉到它的真实存在以及它的无所不在,但是,我们却无法凭视觉捕捉它的踪影,用语言来描述它的形象。事实上,由于它的无所不在和无时不在,我们习焉而不察,造成了对它作为我们生存必需条件的重要性的忽视和遗忘。显然,想象力是一个很难定义和描述的概念。如果我们要深入分析教育中的想象力危机,就必须把握想象力在教育中的各种意义和用法,换句话说,也就是要描述想象力在教育中的各种形象,透过这些形象去揭示想象力在教育中的遭遇。
(一)想象力与形象思维
想象力在教育中最广为人知的一个形象是形象思维。把想象力与形象思维联系起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心理学对“想象”的解释大致有:想象是人在头脑里对已储存的表象进行加工改造形成新形象的心理过程;在知觉材料的基础上,经过新的配合而创造出新形象的心理过程,或者对于不在眼前的事物想出它的具体形象;想象是人在脑子中凭借记忆所提供的材料进行加工,从而产生新的形象的心理过程。总的来说,想象就是指通过感觉、知觉或记忆等心理形式形成心理表象并对其进行加工改造的思维操作活动。什么是形象思维?一般来说,形象思维是指主体运用表象、直觉、想象等形式,对研究对象的有关形象信息,以及贮存在大脑里的形象信息进行加工(分析、比较、整合、转化等),从而从形象上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简而言之,形象思维是用直观形象和表象解决问题的思维。
不难看出,想象与形象思维在内涵上存在很大的重叠和共享性,都是以心理表象或形象信息为对象进行思维加工的操作过程,都强调思维的直觉性、形象性和构造性。只不过前者重在心理构造过程,后者重在问题解决过程。二者内涵的共享性使得想象与形象思维的区分变得模糊起来,由于形象思维相对于逻辑思维在认识论中具有重要的对称性意义,因此,它在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教育话语中受到了格外的重视。较之以形象思维,想象力这个概念多少带有浪漫主义的非理性色彩,在常见的教育理论研究中,形象思维逐步成为想象力的代名词。由于人们把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作为一对概念来使用,这样,想象力在形象思维的裹挟下也就逐步成为与理性思维(逻辑思维)相对应的一个概念。
把想象看作形象思维,看作理性思维(逻辑思维)的对立面,在教育上造成了深远的影响,那就是,想象力只专属于文学艺术教育领域,在数学与科学教育中我们需要的只是逻辑思维,想象力不过是一种陪衬和点缀。这一观念几乎成为教育理论中普遍默认的原则。因此,人们普遍地把数学和科学看作枯燥乏味、缺乏想象力的学科,看作只需要智商不需要情感的学科,看作只需要做题训练不需要幻想和创造的学科。想象作为形象思维的这一教育形象,在很大程度上窄化了想象力的理智价值,忽视了它在理性思维(逻辑思维)过程中的超越逻辑局限性的整合联动功能,造成了教育观念与教学方法上的偏颇。
(二)想象力与幻想及虚构
如果说想象作为形象思维在教育中的作用遭到窄化和限制,那么想象作为幻想与虚构的教育价值则不仅是窄化与限制的问题了,而是遭到了严重的否弃和抵制。在日常的使用中,幻想有两个完全相反的理解维度。一方面它是指向个人所希望的未来事物进行想象的过程,意味着无拘无束的自由想象与创造,这是一种积极的教育价值导向;而另一方面则是指人内心的荒谬的想法,意味着无根无据的妄想和白日梦,这是一种消极的教育价值导向。从积极的维度看,幻想是一种高度自由的想象力,具有超强的生成性和构造性,能颠覆性地超越现实时空中的各种关系,体现了人类思想自由绝对性的一面。但从消极的角度看,幻想被贬为一种低级的思维能力,它是建立在虚假的、不真实的、缺乏现实基础的表象之上的胡思乱想,反映了紊乱无序的思维状态,是一种脱离现实、没有实际意义的想象。令人遗憾的是,在教育中,人们普遍接受的是幻想的第二种含义,把幻想看作是不切实际的胡思乱想。把学生从“沉迷于幻想”的消极状态中召唤回到现实的学习生活中来,一直被看作课堂纪律的重要使命。为什么我们在教育中总是想方设法地防范它的消极一面,而对它积极的一面熟视无睹?是因为我们丧失了对教育的想象力。
与幻想一词相类似,虚构也有两个方向不同的理解维度。一是指凭空捏造,或曰瞎编乱造。二是指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依据生活逻辑,通过想象和撮合,创造出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又在情理中的人生图画。虚构是文学创作的本质属性。从唯物主义文艺学的创作论来看,社会现实是第一位的,文学虚构是第二位的,它是作家对社会现实的能动的、曲折的反映。但最终还是社会现实决定文学虚构。尽管在教育中,人们普遍地接受了虚构作为文学创作手段的意义,也把虚构看作是一种想象力的具体表现,但是,在大多数时候,这种接受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虚构永远从属于现实,永远不具有独立的思想价值。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在我们的语文教育中,文学首先不是虚构的艺术,而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工具。在我们整整12年的基础教育阶段的写作教学中,“虚构”作为文学写作的第一手段,第一要义,一直备受冷遇。在潜意识中我们把“真情实感”、“真人真事”与“虚构”对立起来,把提倡虚构写作看成是教唆孩子说谎造假。在我们把文学作品中的想象与虚构看作作家专利的同时,我们的写作教学也就与想象力失之交臂,它无奈地从我们对虚构的忧惧中悄悄地溜走了。但是,当我们从学生的头脑中把虚构观念扫荡一空之后,我们所期待的“真情实感”其实并没有真正地发生,反而,却带了大面积的造假风气和无病呻吟的病症。因为,想象是情感的触发器和放大器。丧失了想象力的情感是不会持久的,它只能在贫乏的思想中慢慢枯萎下去。
一言以蔽之,想象力的丰满形象在教育中遭受到了严重的挤压和扭曲,它被减缩为与逻辑思维相对立的形象思维而蜗居在人文艺术教育领域得以暂时栖身;它被视为不切实际、毫无用处的幻想和胡编乱造的虚构而沦为教育所极力回避和抵制的不良因素。如果说想象力在教育中的价值还没有消失殆尽,那只能归因于人类的想象天性还没有完全泯灭,归因于人的潜意识对想象力怀有难以遏制的渴求。当人们在教育中逐步把想象力与理性对立起来,质疑它的创造价值,担心它的破坏作用,疑惧它那难以驯服的自由本性的时候,想象力也就滑落到了教育的边缘。显然,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考。
三、想象力在哲学史上的命运
美国教育家杜威说过,“教育是哲学的实验室”[2]。想象力在教育中的不幸遭遇与想象力在哲学史上的坎坷命运是分不开的。想象力从来都是哲学思考所面对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很多时候,哲学家宁愿让它保持一份诱人的神秘,也不愿使自身陷入无休止的循环论证的泥潭中。因为,没有什么概念可以在最后一个环节打开“先验的直观”这个物自体套箱。因此,在哲学史上,关于想象的探讨,我们远远做不到像讲科学故事那样清晰明白。换句话说,在想象力上,我们并不见得比生活在远古时代的祖先们更具优势。
(一)西方神话中想象力的启示
从宗教的意义上说,想象的秘密属于上帝,人类一旦窥视,上帝就会毫不犹豫地惩罚人类。希伯来圣经与古希腊神话是形成西方世界观的两大理性传统,在想象力问题上它们却有着相似的故事。希伯来圣经在讲述建造巴别塔的故事时使用了这个看起来最好翻译成“想象力”的词语。耶和华说:“看那些人,没有什么可以限制住他们,限制他们凭借自己的想象力去做事”。在这里,人类的想象力被看作是诱导人类去侵犯上帝特权的一种手段。上帝给予人类的惩罚就是“变乱”人类的语言,使人彼此不能理解,从而造塔的计划便永远搁浅了。古希腊的普罗米修斯的神话与此近似,他从上帝那儿为人类盗取了天火,人类拥有了火,使自身变得强大起来,这是人类再一次地侵犯本属于上帝的特权。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意思就是“超前——思想者”,即拥有伟大的想象力的思想先驱。从这两则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旦人类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威胁:它会破坏自己与圣神之物、与万物秩序结下的既有的关系。显然,人类拥有通过想象那些并不存在着的可能事物预先进行筹划的能力,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它不仅威胁到上帝的尊严而且也威胁到了人类中的掌权者。独裁者根本不喜欢在自己的地盘里看到想象力的丝毫迹象。在这里,想象力成为人类思想的禁忌——运用想象力会触犯上帝的威严,会破坏先天的秩序。因此,那些挥舞着想象力的思想先驱必定要受到某种惩罚。但是,人注定是要被想象力所诱惑的,作为上帝的子民,想象力是他们唯一的骄傲,因为万物中只有人类才会因为拥有想象力而犯错。上帝的惩罚其实是一个吊诡,人类如果没有想象力,就不能体现出上帝的荣光和智慧,因为人类是上帝照着自己的样子所造就的最高级的存在物。但是,如果人类真的拥有了想象力,就会触动上帝的权威,侵犯先天预定的秩序,人类必然要受到上帝的惩罚,否则将难以显示出上帝至高无上的权威性。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二律悖反,通过它,想象力被安置在了主宰人类命运的核心位置。
(二)想象力在西方哲学中的经历
在西方神话中遭受了上帝惩罚的人类想象力,在随后的哲学初创时代并没有获得翻身和解放,反而演变成为一种低级的思维形式,作为理性的对立面而存在于哲学思考中。其始作俑者就是柏拉图。柏拉图把人的认识能力从低到高分成想象、感性、知性和理性四个阶段。他认为,想象只是感性事物的影像,是认识的最低等级。由于它远离理念世界,变幻无常,根本不值得信任。显然,在西方哲学史一开始,想象力就坠入了感性世界的乱相中。柏拉图对想象力的贬斥具有深远的影响力,想象力被描述为一种与人类理性相冲突的不确定因素。理性与想象是水火不容的两种东西,你拥有其中一种能力越多,你拥有的另一种能力就会越少。亚里士多德赋予了想象力一种重要的理性功能,他认为想象力在感知觉转化为理念,或者世界的质料演变成心灵的质料的过程中起着转换的作用。即便如此,亚里士多德还是认为想象是不可靠的,它只是感觉的副产品。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对想象力普遍抱有怀疑的态度,认为只有把它审慎地控制在理性的范围之内,它才是理性的一种潜在的有用的奴仆。想象力尽管能够服膺于理性,但它却是理智活动中最为虚弱和易错的部分,容易与表象所形成的现实混淆在一起。这个敏感虚弱的地带正是魔鬼进入理念世界的踏板。因此,在中世纪想象力又一次成为不被信任的能力,它必须时时处在理性的警惕性的控制之中。
在启蒙时代的早期,想象力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显著的提升。笛卡尔把它看作导致思想混乱的源泉和“浮躁的建造物”。文艺复兴后期的两个先导哲学家赋予了想象力一个新的内涵。休谟不只是简单地认为想象力能把感觉印象转变成观念,而且认为想象力能把短暂易逝的、局部的,不断变换的感觉印象带到连贯的稳定的世界观中。康德称这种理论是自从有形而上学以来,对形而上学这门科学的命运的“最致命的打击”。康德更进一步认为想象力甚至建构了我们的感知觉。因此,我们所能理解和知晓的事物是由我们想象力提前决定好的。康德将想象力当作一种纯粹的认识功能,在认识过程中想象力是从属于知性,符合知性概念的,是知性通过表象(对象的形式)的必要条件。作为一种具有生产力和创造力的现代意义上的想象力概念,主要是来自于浪漫主义时代。浪漫主义者吸收了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主体性思想,认为人类心理的本质是由我们如何感知世界的方式所决定的,想象力并不是简单地再现由感觉所传递来的现实的图像。在这里,心灵不再被人看做是清晰的现实世界的镜子,而是被看作是照向黑暗而复杂的现实世界的灯火;想象力则被看作是人类理解世界过程中的核心要素。浪漫主义者甚至挑战了把科学看作发现真理的可靠的途径的观念,提出“美是真理,真理美丽”的命题。与浪漫主义者则不同,华兹华斯认为,想象力不是别的什么,只不过是“最崇高的情感中孕育的理性”。他认为想象力在诗歌写作中具赋予、抽出、修改、造型、创造、加重、联合、唤起和合并等诸多功能,理性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它的作用。
海德格尔之前的哲学家大都把想象力放在认识论或者艺术创作领域进行研究,想象力或者被看作一种依赖于感性经验的低级思维形式,或者被看作不可名状的先验的直观形式,抑或被看作有别于理性思维的进行自由创造的神秘力量。但是,在这些观念中,想象力作为揭示人与存在之间源始联系的敞开作用被遮蔽了。海德格尔在对现象学方法进行批判的基础上,超越了康德哲学的想象力——通过先验演绎逻辑积极地建构经验对象的能力,借助于对源始的时间性的分析,赋予了先验的想象力新的价值:想象力的综合不再像知性概念那样是规范的,完全依赖于知性统觉,而是自身收成的,是完成自身超越的本源性力量,它不仅独自构成了一切对象知觉的最源始条件,还是人类理性得以从有限的在场者中超越出来的根本原因。由此想象力作为哲学概念超出了知识论层面,打开了存在论的视域,使缘在借助想象的敞开作用能诗意地栖居在存在的身旁。伽达默尔进一步把想象力拓展为一种内在于哲学解释学方法中基本精神。他认为,在我们这个充满科学技术的时代,我们确实需要一种诗的想象力,或者说一种诗或诗文化。想象力超越了主客认识和单纯艺术想象的工具价值,通过与语言结缘而具有了存在本体意义。想象,成为贯通人类意识所有方面的存在之思。
想象力在西方哲学史中的坎坷经历,向我们昭示了这样一种事实:我们对人类自身及其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了解得越多,就会对想象力所拥有的无可比拟的心理渗透力和意识包容性发现得越多,想象力在哲学中的地位也就会愈加突显。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尽管人类获得的各种科学知识都是人类想象力的产物,但是,知识的增加并不必定带来对想象力的尊重和呵护,很多时候,想象力被贬斥为理性思维的对立面,被看作人类理性思维存在缺陷的证明。不过,我们更应当看到,无论想象力经历了怎样的哲学命运,也不论哲学家们对它怀有怎样的偏见,它都以自己顽强的生命力在森严的哲学概念的裂缝中坚韧地生长出来,以自己的坚韧的沉默对抗理性傲慢的喧嚣,以自己无处不在的渗透力量维持着思想与情感的运功和平衡,想象力成为人类意识最深刻、最阔放的心理背景。它不仅每天都工作在我们感知世界的过程中,而且,当我们思考那些不在场的事物、判断眼前的或未出场的事物在我们理解世界的过程中是否重要的时候,它亦参与其中。尽管这种能力使我们的知觉充满了思想,但是,它并不只是属于理性。在我们的意义生成活动中想象力总是能自由自在地参与其中,与情感紧密相连。因此,它的动力既来自理智,也来自情感。而且,在浪漫主义运动中我们还发现了想象力的另一种内涵,即它是按照事物的可能性来思考事物的一种能力,它是我们的创新、创造和生产能力的源泉。正是想象力延伸了人的思想触角,扩展了可能性的边界。(未完待续)
[1]赵永新,王昊魁.中国儿童想象力太差 谁拧死了想象力阀门[N].人民日报,2009-08-17.
[2][美]约翰·杜威.王承绪译.民主主义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347.
潘庆玉/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
*此文是作者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09年度教育规划课题 《“富有想象力”的语文课堂教学研究》(项目编号为FFB90708)与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基于认知工具理论的课堂教学研究”(项目编号为09YJC880064)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刘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