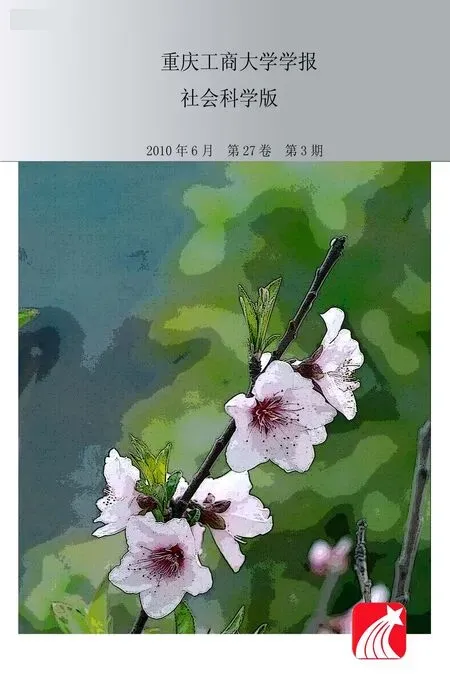寻租对社会影响的定量研究述评
李秉强
(台州学院 经贸管理学院,浙江 台州 318000)
一、引言
所谓寻租活动,是指政府的无意创租、被动创租和主动创租导致社会产生巨额租金,人们通过各种手段为从政府官员获取垄断权而进行的非生产性活动。近年来,我国治理腐败取得了一定绩效[1],然而,只有明确了寻租对社会发展的利弊关系,政府才能够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措施,这就要求定量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国外较早对寻租进行了研究,国内直到1988年才引入寻阻理论,目的是为研究我国转型期出现的腐败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分析方法。国外相关研究源于对垄断成本的社会考察,起初认为哈伯格三角能够反映垄断的社会成本,随后塔洛克(Tulluck)从寻租这个全新视角分析了垄断和关税的社会成本,但在当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直到克鲁格(Kruger)的文章发表后,大量相关研究才开始涌现出来。从现有文献看,学者主要从估算社会成本和社会影响两方面对寻租进行了定量研究,而对寻租成本的度量又通常通过计算福利损失和考察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实现。据此,本文从寻租的福利损失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两方面,将腐败视作寻租的主要表现形式,以此来考察寻租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影响。
二、寻租的福利损失
(一)国外研究
垄断的社会成本是经济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关心的热点,哈伯格(Harberger)[2]采用消费者剩余理论建立了衡量垄断的社会成本的基本模型,认为垄断的社会成本可以通过类似消费者剩余计算得出。鉴于哈伯格首先采取这一方法识别了垄断的福利损失,故在经济学中通常称为哈伯格三角。早期研究主要通过测度哈伯格三角来考察垄断和关税的福利损失,但估计出来的福利损失非常小,引致了Mundell的质疑[3]和Leibenstein的批判[4]。如,多位学者研究后发现,垄断造成的福利损失占GDP的比重为美国1929年的0.07%和1954年的0.01%,而关税造成的福利损失分别为德国1958年的0.18%、意大利1960年的0.1%、英国1929年的1%、所研究的共同市场体1954年的0.05%和蒙特维的亚协约国当年的0.007 5%[注][美]塔洛克. 寻租—对寻租活动的经济学分析[M]. 成都: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 1999: 8.。事实上,哈伯格三角只考察了资源配置扭曲带来的福利损失,但没有考虑由此出现的X-效率。随后出现的寻租理论较好弥补了哈伯格三角测度的不足,逐渐形成了公共选择和国际贸易两大研究视角,同时认为寻租主要体现在垄断和关税两方面。
塔洛克[5]首先从理论上提出了有别于哈伯格三角的度量方法,认为垄断的社会成本不仅包括哈伯格三角,还应该包括为获得垄断利润而花费的资源和成本,即通常所说的“塔洛克方块”,奠定了寻租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石。波斯纳(Posner)[6]也认为垄断租金衡量了寻租的社会成本,首次对修正后的“塔洛克方块”进行了经验检验,得出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5大垄断产业造成的社会成本约占美国当期GDP的17%。然而,Fisher[7]认为,波斯纳选择的5大产业不能完全反映出垄断的福利损失,还应该考虑被管制部门内部企业竞争造成的社会成本,在此基础上推算出垄断造成的社会成本占美国当期GDP的34%左右。考虑到该测度方法是塔洛克提出并由波斯纳进一步完善,故通常称之为塔洛克-波斯纳测度。鉴于塔洛克-波斯纳测度与哈伯格三角有着比较大的关联性,因而有必要将这两种测度进行比较。Lopez和Pagoulatos[8]通过计算1987年美国食品和烟草业由于贸易壁垒而造成的福利损失,发现采取哈伯格三角测度得出的福利损失为国内消费量的2.6%,而采取塔洛克-波斯纳测度得出的福利损失为国内消费量的12.5%。由此可知,这两种测度在度量寻租造成的福利损失时差别较大,足以促使政府为应对寻租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
波斯纳从公共选择领域首次对寻租的福利损失进行了度量,而克鲁格则从国际贸易视角展开了分析[9]。克鲁格认为,人们为获得来自进口权垄断的租金就必然会对进口权进行争夺,并且首次估计了配额造成的福利损失。她将社会劳动力分为从事生产业务和进口业务,认为后者在政府管制的情况下会产生租金,据此估算出印度1964年的租金占当年GNP的7.3%,土耳其1968年仅进口许可证形成的租金就占当年GNP的15%。采取类似方法,Ross估算出肯尼亚与贸易有关的租金占该国当年GNP的38%[10]。但克鲁格只考虑了产品市场,而没有将要素市场纳入分析框架。Mohammad和Whally[11]在充分考虑产品市场的同时,还对价格控制和信贷配给等要素市场形成的寻租进行了估算,得出寻租造成的福利损失占印度当年GNP的30%~45%。可以看出,从寻租的国际贸易视角进行度量,得出的结论与塔洛克-波斯纳测度相似,即使是同一种测度方法,研究层面不同也会致使估算出的福利损失差别较大,但都比哈伯格三角要大得多。
此外,还有学者从其他视角考察了寻租的福利损失。如,Laband和Sophocleus对可能产生寻租的各个层面进行了分析,且采取替代指标度量了寻租的福利损失,甚至把锁、保险箱和警察等都视作是寻租的替代指标,结果表明美国1985年GNP的50%都浪费在寻租上[12]。然而,由于替代指标的选择没有统一标准,得出的福利损失过大的结论也没有被公众接受,但其认为应该全方位考虑寻租造成的福利损失的思路还是可取的。
对寻租福利损失的度量,源于对哈伯格三角测度的质疑,逐步发展成以公共选择和国际贸易为主的两种测度方法,其代表人物分别为塔洛克和克鲁格。塔洛克和克鲁格在研究中有着相同的假定条件,都认为租金等同于寻租造成的社会成本。由于分析方法和数据不同,计算出的福利损失也就有较大差别。每一种方法都有其合理性,但都不能全面反映寻租的社会成本,目前还没有形成一种共识的测度方法。此外,考虑到寻租包含的具体内容没有统一标准,致使不同测度得出的福利损失差别很大,如GDP损失从0.007 5%到50%以上。通常认为,哈伯格三角严重低估了寻租的福利损失,其他方法则因立脚点不同而无法给出定论。
(二)国内研究
学者对我国寻租造成的福利损失进行了相应的探索,但尚未形成一套规范的计算方法,在分析中延续了塔洛克和克鲁格的观点,都把租金等同于寻租的福利损失。如果不能明确福利损失,对寻租现象的研究就只能停留在定性层面上,在复杂的经济系统中就很难辨认寻租是否有利于社会发展,无法判断政府干预是否合理,进而无法确立治理寻租的方案。而如果能够计算出历年租金,则政府就能清楚了解寻租的社会绩效,这对于制定政策有着极大的指导意义。
胡和立在寻租理论引入不久就估算了我国的租金,认为我国租金有价差、利差和汇差等表现形式,据此估算出我国1988年的租金约为4 569亿元,其中,价差约1 500亿,利差约1 138.81亿,汇差约930.43亿,其他租金约1 000亿[13]。对我国租金的后续估计,无论是总体规模还是对行业或部门规模的估计,基本都延续了这一分析思路。如,万安培从价差、利差、汇差、进出口许可证管制、税差、公共福利待遇、股份制改造和房地产开发、财政分成比例不合理、行业和铁路运输状况等方面估算出我国1992年的租金总额为6 343.7亿元,与1988年相比,价差降至766.6亿,利差升至1 983.0亿,汇差升至1 151.1亿[14]。万安培将租金分为基本持平、持续减少、基本消失和较大幅度增加,进一步分析了其构成和规模,得出1993—1996年的规模分别为5 270亿元、5 432亿元、5 665亿元和6 229亿元。其中,基本持平的租金约2 200亿;持续减少的租金主要指价差,如,该项租金历年分别为710.59亿元、680.69亿元、692.66亿元和656.00亿元;基本消失的租金主要指汇差和进出口许可证管制带来的租金;较大幅度增加的租金指利差,如,该项租金历年分别为2 403.83亿元、2 650.60亿元、2 873.40亿元和3 473.14亿[15]。此外,学者研究发现,我国1996—1998年间新股发行的一、二级市场之间分别存在486.6亿、1 266.1亿和410.4亿的租金[16];我国2000年在电力、交通运输邮电、邮电通讯和民航四个行业的租金达到了1 300亿~2 020亿元,在电力煤气及水生产与供应业、邮电通讯业、航空运输业和铁路运输业四行业的职工工资耗散额达到了278.2亿元[17]。
随着我国改革逐渐深入,尤其是1992年后进出口许可证管制和外汇市场相对放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减少了寻租存在的可能,这在总体上表现为租金规模相对下降。如,1988年和1992年的租金规模分别占当年GDP的30.61%和23.80%,而1993—1996年的租金规模分别为当年GDP的15.25%、11.64%、9.85%和9.72%。诚然,如假定胡和立的研究总体上反映了当年的租金规模,那么在经济转型阶段出现的诸多问题就无法纳入分析框架。因此,计算出的租金规模于实际而言就可能相对偏小,这就要求构建新方法来计算福利损失。然而,即使是现有研究也表明,寻租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福利损失,足以引起政府重视和认真对待。
三、寻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政府对寻租的态度不是取决于寻租会造成多大的福利损失,而是取决于寻租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多大的影响,如果寻租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就应该采取鼓励措施,反之就应该实行管制政策。事实上,寻租对经济发展既有正面作用又有负面影响,其综合绩效取决于两者的合力。如果是为了改变无效率的产权而对现有分配进行的改变,那么寻租对于社会而言就是一种有意义或者说是理想的结果[注]张军. 特权与优惠的经济学分析[M]. 上海: 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 36.,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带动了经济发展。诚然,寻租也可能带来社会资源浪费、产出减少和孳生既得利益集团等负面影响。但在定量研究中,考虑到难以有效分解出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因此综合考虑寻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至于寻租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定量研究,学者主要从寻找替代指标、采取内生与外生增长模型和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引入政治经济学等视角进行了探讨。
多位学者选择替代指标考察了寻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Laband 和Sophocleus分别将律师和银行家作为寻租和生产的指标,首先考察了寻租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发现寻租导致美国1985年的GNP减少22.6%[12];Magee等将律师和医生视作寻租和生产的指标,分析了GNP和寻租与生产的关系,结果表明律师相对较少是日本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原因[18];Murphy等分别将主修法律和工程的学生比例看作是寻租和生产的指标,其跨国研究结果表明GNP与寻租负相关、与生产正相关[19]。上述研究都表明,寻租不利于经济增长。通过设定具体指标来衡量寻租和生产,能够较好地与经济增长建立联系。但正如上述各研究所表明的,学者都是将律师(或主修法律的学生)作为寻租的指标,认为律师的活动是非生产性活动,这显然不是一个合乎现代社会标准的假定,由此得出的寻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多大可信度就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经济增长历来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热点,因此将寻租纳入经济增长模型就成了大势所趋,无论是单独从内生增长模型抑或外生增长模型入手,还是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引入政治经济学,都是可取的方向。如果仅从增长模型来考察寻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从内生和外生两方面进行考察。Rama首先采取内生增长模型考察了寻租对乌拉圭经济增长的影响,假定企业引致投资和游说支出分别影响资本存量和法规数量,同时认为资本存量影响当年产出而法规对经济发展有时滞效应,发现寻租在短期会促进而在长期会阻碍经济增长[20]。Brumm采取外生经济增长模型进行了经验检验,在模型中引入了人均生产总值、人口增长率、税收结构、长期平均投资率、人力资本和寻租等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外生变量,并且认为寻租可以用政府雇员人数、律师人数和游说表示,采取美国48个州的面板数据分析后发现寻租阻碍了经济增长,这与Rama得出的长期影响的结论相同[21]。然而,Brumm在研究中采取的模型可能会导致向量自相关,为消除由此可能带来的影响,Cole和Chawdhry采取内生增长模型重新进行了分析,发现寻租不仅对经济增长有直接负面影响,还能通过公共投资和公共服务等渠道产生间接阻碍作用[22]。可知,无论是采取内生增长模型,还是采取外生增长模型,研究结果都表明寻租在长期会阻碍经济增长。
在另外一种研究思路中,学者将政治经济学置于内生增长模型的分析框架中,同时认为人力资本、技术和政府政策等因素是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并重点考察了公共政策外溢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了与前述两种分析视角截然不同的结论。如,Mork将寻租视为游说的函数,实证研究表明寻租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23],这与Mohtadi和Toe[24]的实证研究得出的两个结论保持了一致:其一是为获得公共投资需要更多贿赂的国家有着更高的人均收入;其二是寻租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将获得更快的经济增长。此外,Barreto将公共部门腐败引入新古典内生增长模型考察了腐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腐败在官僚严重的国家有助于经济发展,虽说这可能以国家福利减少17.5%为代价[25]。
一般认为,寻租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经济增长,采取不同的方法和指标会得出不同结论,这就要求客观评价上述各种思路。寻租能力是各要素合力的结果,无论是从经济增长模型出发,还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进行考虑,都是用一个或多个指标对寻租进行替代,得出的结论有着一定代表性,但能否准确反映寻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四、腐败与社会发展互动影响的定量研究
一般认为,腐败会通过各种渠道影响社会发展,社会发展也会为腐败提供存在的土壤,因此有必要就腐败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影响进行定量考察。从现有文献看,关于腐败对社会发展的定量研究集中体现在腐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而社会发展对腐败影响的定量研究集中体现在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对腐败的影响上。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停留在定性研究和经验描述层面[注]杨灿明, 赵福军. 行政腐败的宏观经济学分析[J]. 经济研究, 2004, (9): 101-109.,故本文以外国学者的研究为主进行评述。
(一)腐败对社会发展影响的定量研究
上述研究表明,现有文献就寻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没有达成一致见解。寻租既可能作为润滑剂提高经济增长效率,也可能因为损害创新阻碍经济增长。而作为寻租的重要表现形式,腐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就自然而然成为关注的焦点。如,Mauro将腐败定义为商业活动中的贿赂金额占可疑账款中的比重,将经济增长定义为私人和公共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就58个国家的腐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发现腐败与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26]。Mo在Mauro 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不同传导渠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将腐败的传导渠道分为直接冲击渠道、人力资本渠道、政治渠道和投资渠道,发现上述四种渠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别为11.8%、14.8%、53.0%和21.4%,由此表明政治渠道是腐败影响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渠道[27]。此外,该研究还表明,腐败增加1%将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约0.72%,或者说腐败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将使经济增长下降0.545个百分点。Mo为考察寻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但其不足之处是假定各种冲击渠道外生于腐败而存在。
(二)社会发展对腐败影响的定量研究
1.政治因素对腐败的影响
腐败源于政府官员对自身拥有的垄断特权剩余价值的索取,并且相关研究也表明了政治因素对腐败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考察政治因素对腐败的影响。从现有文献看,学者主要从分权、法律有效性、民主和自由等方面定量探讨了政治因素对腐败的影响。
关于分权对腐败影响的定量研究,学者从财政和制度两方面进行了探讨。Huther 和Shah[28]最早定量研究了财政分权和腐败的关联性,发现分权越显著的国家,其腐败程度也越低,但该研究的不足之处是财政分权指标过于单一。基于上述不足,Treisman[29]引入了一个反映邦联结构的虚拟变量对分权进行测度,并且采用了一系列的控制变量,结果表明邦联制国家的腐败程度高于非联邦制国家。Fisman 和Gatti[30]认为Treisman采取的虚拟变量不能真实反映一个国家的权力和资源的分权程度,而将国家法律制度基础作为衡量指标,其跨国数据研究表明政府支出的财政分权与腐败显著负相关,并且还印证了更透明的政府会产生更大分权这一传统观点,但该研究没有指明哪种分权更加有效以及政府为消除寻租应采取何种措施。上述研究表明,分权对腐败有显著影响,在分权越显著的国家,其腐败程度也越低。
关于法律有效性对腐败的影响,学者已经做了比较多的理论研究,一般认为法律有效性改善将导致腐败水平下降,并且通常认为有效的法律体制是减少腐败的关键要素,但实证研究目前还不为多见。此外,相关研究也表明官僚机构质量和法律制度质量与腐败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31]。Herzfeld 和Wess[32]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尝试,他们采取130个国家1982—1997年的相关数据分析了法律有效性与官僚腐败的关联性,发现法律制度与腐败有着显著的内在关联性,即自我强化的交互作用,这意味着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下,腐败会维持在一个相应的水平,并且在短期内不会消失。如假定腐败增长10%而法律有效性减少10%,在考虑完全反馈的情况下,腐败将增长13%和法律有效性将减少21%。该研究从政治民主视角考察了法律有效性对腐败的影响,认为两者能够内在地产生互动影响。然而,还有很多因素也会制约着法律有效性对腐败的影响,但在研究中并没有得到体现。
经济自由与腐败在理论上不会直接发生关联,但政府官员能通过对经济自由运转施加种种约束,居民和企业为了规避这些约束就会向政府官员行贿,从而在经济自由与腐败之间建立桥梁。至于经济自由对腐败的影响,通常认为在经济越自由的情况下,腐败水平会越低[33]。然而,Graeff 和Mehlkop认为基于标准和传统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差别,不同国家的腐败表现形式也会不同,因此经济自由总以同一种方式影响腐败的传统结论就值得怀疑[34]。为分析经济自由与腐败的关联性,他们采取1998—2002年的相关数据,将77个国家按照不同经济自由度划分为7类,结果发现有些国家的经济自由与腐败正相关,有些国家表现为负相关。此外,该研究还表明,经济自由对腐败的综合影响与国家贫富存在强相关性,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一是增加交易成本会减少腐败,二是政府规模大不一定会产生更高的腐败。该研究考察了经济自由对腐败的影响,表明经济自由的不同层面对腐败的影响不同。因此,为充分了解经济自由对腐败的影响,不仅要考虑政府规模和腐败之间的关系,还要考虑监管非法行为的法律和制度能力。
新闻自由将政府行为置于舆论监督之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政府行为透明化,但这会对腐败产生何种影响?一些学者通过定量研究考察了新闻自由与腐败的关系。如,Brunetti和Weder[35]的研究表明两者有着强相关性,而且测度新闻自由和腐败的方法,对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基本没有影响;并且论证了新闻自由程度与腐败水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据此认为高度的新闻自由和相对独立的媒体机构是应对腐败的一种有效工具,这与Besley 和Burgess的研究结果保持了一致[36]。此外,也有学者发现民主在长期内能够有效减少腐败,而在短期内的绩效则不明显[29]。上述关于新闻自由对腐败影响的定量研究,都是将新闻自由等同于民主,而Chowdhury[37]则认为“新闻自由—选民意识—民主—政党选择—腐败程度”是新闻自由影响腐败的传导机制,从政党竞争和选民参与两方面展开分析,更能有效地考察新闻自由对腐败的影响;其实证研究支持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但发现选民参与对腐败的影响更显著,这可能是由于选民参与的传导渠道相对较短。以上关于新闻自由对腐败影响的定量研究,都是假定腐败外生于新闻自由,这与实际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的偏差。此外,Chalderon和Chong采取乌拉圭的数据实证考察了寻租与民主的关联性,发现民主与寻租之间存在着互动关联性,并且有着较为明显的因果关系[38]。
2.文化对腐败的影响
相对于政治因素而言,考察文化对腐败影响的相关研究不为多见,目前只有Paldam引入“经济—文化”模型定量分析了文化对腐败的影响[39]。其中,经济模型选择了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实际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和经济自由指数等指标,文化模型选择了民主和宗教这两个指标。通过研究得到如下结论:对经济模型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由贫穷向富裕转型会减少腐败,但一定时期内的高通货膨胀会加剧腐败;对文化模型的研究表明,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是腐败的最重要决定因素,相同“传统文化”的国家有着相同的腐败传导路径,通货膨胀在短期内对腐败影响不确定;相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比相同文化背景的国家更趋向于有相同的腐败水平。该模型结合文化因素考虑了腐败的经济效应,指出文化是影响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拓展了腐败研究的传导机制。但其不足之处在于宗教信仰不能真实反映一国的文化状况,即使在宗教信仰相同的国家,受教育内容和程度的差别也会产生不同的文化。
五、小结
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寻租进行了定量研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使用模型和数据上的差别,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从福利损失看,基于寻租的公共选择理论得出的租金规模与基于寻租的国际贸易视角得出的结果相差不大,都比哈伯格三角测度得出的租金要大。从寻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看,采取寻租和生产的替代指标和经济增长模型这两种分析方法,一般会得出寻租阻碍经济增长的结论;而如果将政治经济学置于内生增长模型进行分析,则会得出不同结论。关于社会发展与腐败的互动影响的定量研究,通常认为腐败阻碍了经济发展、相对自由的政治环境的改善能够减少腐败,并且文化因素也会对腐败产生影响。但现有研究主要是以外国作为考察对象,很少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定量测度和分析。因此,我国经济工作者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研究成果,对寻租的社会经济影响进行度量,为政府出台应对寻租的政策提供数据支持。
[参考文献]
[1] 倪星, 王立京. 中国腐败现状的测量与腐败后果的估算[J]. 江汉论坛, 2003(10): 18-21.
[2] Harberger AC. Monopoly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4, 44: 77-87.
[3] Mundell RA. A Review of L.H. Janssen: Free Trade, Protection and Customs Union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2, 52: 622.
[4] Leibenstein H. Allocative Efficiency vs. X-Efficienc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6, 56: 392-415.
[5] Tullock G. The Welfare Costs of Tariff, Monopolies and Theft [J]. Western Economic Journal, 1967, 5: 224-232.
[6] Posner RA. The Social Costs of Monopoly and Regulation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5, 83: 807-827.
[7] Fisher FM. The Social Costs of Monopoly and Regulation: Posner Reconsidered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5, 93: 410-416.
[8] Lopez RA, Pagoulatos E. Rent seeking and the welfarecost of trade barrier [J]. Public Choice, 1994, 79: 149-160.
[9] Krueger A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 seeking societ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4, 64: 291-303.
[10] Ross VB. Rent seeking in LDC import regimes: the case of Kenya [R].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Geneva: Discussion Paper, No.8408, 1984.
[11] Mohammad S, Whally J. Rent seeking in India: Itscost and policy significance [J]. Kyklos, 1984, 37: 387-413.
[12] Laband DW, Sophocleus JP. The Social Cost of Rent-seeking: First Estimates [J]. Public Choice, 1988, 58:269-275.
[13] 胡和立. 1988年我国租金价值的估算[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1989(5): 10-15.
[14] 万安培. 租金规模的动态考察[J]. 经济研究, 1995(2): 75-80.
[15] 万安培. 租金规模变动的再考察[J]. 经济研究, 1998(7): 60-63.
[16] 郭晋刚, 马晓维. 我国股票市场寻租行为初探[J]. 改革, 1999(2): 71-73.
[17] 胡鞍钢, 过勇. 转型期防治腐败的综合战略与制度设计[J]. 管理世界, 2001(6): 44-55.
[18] Magee SP, Brock WA, Young L. Black Hole Tariff and Endogenous Policy Theor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327-352.
[19] Murphy KM, Shleifer A, Vishny RW. Why is rent-seeking socostly to growth?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3, 83: 409-414.
[20] Rama M. Rent Seeking and Economic Growth: A Theoretical Model and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3, 42: 35-50.
[21] Brumm HJ. Rent Seeking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the States [J]. Cato Journal, 1999, 19: 7-16.
[22] Cole IM, Chawdhry MA. Rent Seeking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a Panel of U.S States [J]. Cato Journal, 2002, 22: 221-238.
[23] Mork K. Living with Lobbying: A Growth Policy Co opted by Lobbyists Can Be Better than No Growth Policy At All [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3, 95: 597-605.
[24] Mohtadi H, Toe T. Democracy, rent seeking and growth: is there a U curve? [R]. Center for Political Economy Working Paper, Univ. of Minnesota, Minneapolis, 1997.
[25] Barreto RA. Endogenous corruption in a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0, 44: 35-60.
[26] Mauro P. Corruption and Growth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 1995, 110(3): 681-712.
[27] Mo PH. Corru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0, 29: 66-79.
[28] Huther J, Shah A. Applying a simple measure of good governance to the debate o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1894, 1998.
[29] Treisman D. The causes of corruption: a cross-national study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0, 76(3): 399-457.
[30] Fisman R, Gatti R. Decentralization and corruption: evidence across countries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2, 83: 325-345.
[31] Jain AK. Corruption: A Review [J].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001, 15: 71-121.
[32] Herzfeld T, Wess C. Corruption and legal (in) effectivenes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3, 19: 612-632.
[33] Chafuen AA, Guzman E. Economic freedom and corruption [M]. Washington: Washington Press, 2000: 51-63.
[34] Graeff P, Mehlkop G. The impact of economic freedom on corruption: different patterns for rich and poor countries [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3, 19: 605-620.
[35] Brunetti A, Weder B. A free press is bad news for corruption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3, 87: 1801-1824.
[36] Besley T, Burgess 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India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2, 117: 1415-1451.
[37] Chowdhury SK. The effect of democracy and press freedom on corruption: an empirical test [J]. Economic Letters, 2004, 85: 93-101.
[38] Chalderon C, Chong A. Rent seeking and democracy: empirical evidence for Uruguay[J]. Economic Inquiry, 2007, 45(3): 592-601.
[39] Paldam M. The cross-country pattern of corruption: economics, culture and the seesaw model [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2, 18: 215-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