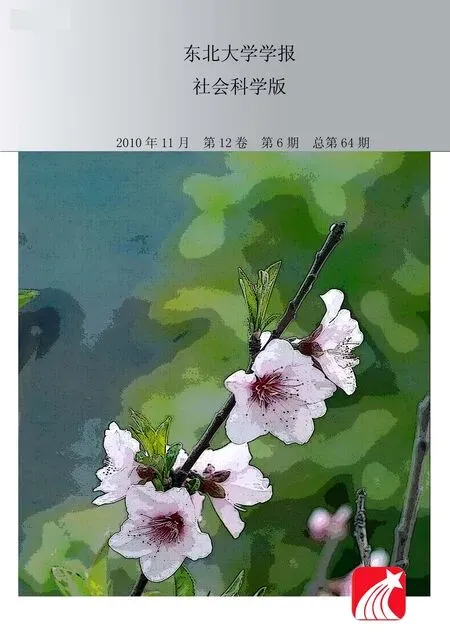从《喧哗与骚动》看福克纳笔下的南方淑女形象
冯 溢,姚 进
(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沈阳 110819)
《喧哗与骚动》[1](TheSoundandTheFury)[2]是美国南方作家福克纳第一部成熟的作品,标志着其创作辉煌时期的开始。福克纳为此书花费了很多心血,他历经了艰难的创作突破,才完成了这部著作。难怪作家本人对这部小说就像“母亲对孩子一样”,有着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小说讲述的是南方贵族家族康普生一家的没落史。老康普生悲观厌世、嗜酒贪杯,康普生夫人郁郁寡欢,有些神经质。长子昆丁性格懦弱,固守传统,因妹妹凯蒂的失贞而溺水自杀;女儿凯蒂放荡不羁,最终堕落为纳粹的情妇;次子杰生唯利是图、冷酷贪婪;三子班吉明天生智障,33岁时只有3岁小孩的智商。书中分四个章节,分别从家族四个人物,三子班吉明、长子昆丁、次子杰生和黑人女佣迪尔西的视角,叙述曾经兴旺繁荣的家族的衰败史和南方社会的变迁。在《喧哗与骚动》中,虽然两位南方淑女人物康普生夫人和凯蒂在叙事中部分或完全缺席,但是她们完全控制着整个故事的发展,是贯穿全书的灵魂人物。Linda Wagner认为,虽然根据语言学定义,叙述人是语言行为主导整个叙事的人,然而康普生夫人和凯蒂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要的叙述人,整部小说充满她们的语言和在场,她们的在场并不存在于书中的某一章而是存在于整本书[3]。这说明了康普生夫人和凯蒂两位南方淑女人物在整个故事中的重要性。然而,评论界对康普生夫人的评论很少,多是批评其由于“固守南方淑女的旧传统”,失去了做母亲的本分。然而通过对南方淑女传统的探究,我们发现,康普生夫人虽然表面上极端地维持着淑女的形象,但在很大程度上,其行为已经背离了南方淑女的传统。她对虚华的家族荣誉的追求导致了这一点。凯蒂是年轻一代南方淑女的代表,童年时代的她纯真、可爱,然而失贞后,在南方淑女文化和家族压抑的环境下,她一步一步堕落下去,最后成为纳粹的情妇。凯蒂的反传统使她不仅失去贞操,而且失去了一切,也导致了康普生家族的悲剧。通过对《喧哗与骚动》中康普生夫人和凯蒂这两位经典南方淑女的分析,我们可以透视南方淑女文化在经历新旧南方更迭时期中的嬗变,窥视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中美国南方淑女形象和南方淑女文化的悖论。
一
旧南方父权制奴隶社会孕育了“南方淑女”(Southern Lady)文化,它强调女性为男性的附属品,反对女性参与社会活动,女性唯一的活动领域是家庭。南方女性接受教育的最终目的也是“帮助她们服侍家庭和履行她们的家庭责任”[4]192。南方女性应是“虔诚的、顺从的、柔美的”[4]191,更重要的是,南方淑女一定要纯洁,南方淑女的贞操受到至高无上的保护,像宗教的信条一样不可侵犯。几百年来,南方淑女文化像一个神话,一个传奇,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和完美主义色彩。
虽然南方淑女被奉为仙女、圣女、贞女,但在现实生活中,她们并非过着无忧无虑的神仙生活。历史学家们考证,南方淑女有着繁重的家务劳动,担负着重要的家庭责任。“南方淑女”的家庭责任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女性要看管家族的产业。Catherine Clinton在关于旧南方妇女的研究中挑战了传统的淑女神话和关于南方淑女的众多浪漫假定,提出南方淑女并没有过着神力庇护般的生活,她们在家庭生产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担任繁重的劳动来确保家族种植园的自给自足,如:管理家中的奴隶以及监督家族产业[4]192。生育、抚养、教育家族的下一代是南方淑女的传统责任之二。因为南方淑女的生活是以孩子为重心的,因此,这是南方女性最重要的家庭责任。“孕育孩子, 生育孩子,以及抚养婴儿是(南方)女性生活的中心话题。”[4]193在研究从1830年到1930年一百年间的南方淑女中,Anne F. Scott提出,大地主家庭中受过良好教育的南方淑女“勤劳肯干”,她们都“全身心投入她们的家庭”[4]192。南方母亲把她们的母性责任看做是“神圣的责任”,她们一生都在为孩子操劳。Scott进一步称,多次怀孕、持续的哺育加上繁重的家务劳动使南方淑女们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苍老得多[4]192。南方淑女的第三个家庭责任是关心家族成员和佣人的身心健康和幸福。“她(南方淑女----笔者注)宁静而富有同情心,关注家族成员、佣人和任何需要关爱的社区成员的健康和幸福。”[5]南方母亲非常重视和关心孩子的身体健康,没有特殊情况,南方母亲都亲自哺育孩子。Sally G. McMillen在研究南方母亲中指出,由于南方恶劣的气候环境、落后的医疗条件和水平以及众多流行疾病,婴儿的患病率和死亡率大大高于北方,而大多数南方母亲都是负责任的慈母,“她们可以几天或几个星期来看护患病的孩子;除非她们患病或没有充足的奶水,否则她们一定要亲自给孩子喂奶,不会依赖乳母的帮助”[4]194。由于持续的哺乳和繁重的家务,南方母亲不得不寻找女性奴隶或乳母的帮忙,但“虽然奴隶在哺育婴儿上担任一些家务劳动,但是南方女性很少会放弃母性责任”[4]194。在精神上,南方淑女依赖对上帝的信仰。在家庭中,她们是上帝的笃信者,是道德规范的坚守者,她们感召丈夫,并把南方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传承给年轻的下一代。Clinton概括了旧南方淑女的特点,她们“象征着美德,遵守着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因为她们的虔诚、母性、多子和纯洁而得到回报”[4]194。可以说南方淑女文化和传统深深地渗透在南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一代一代南方女性。
二
康普生夫人深居简出,不闻世事,不参与任何社会活动,不结交任何朋友。她以南方淑女的神话来约束自己,时刻以淑女身份自居。她说“我是个大家闺秀”[1]316,“我跟一般人不一样”[1]275。小镇上的居民也把她视为南方淑女的典范。凯蒂的未婚夫赫伯特跟昆丁说过:“你有那么好的母亲来教你什么是良好的行为。”[1]121然而,长子昆丁在自杀前却感叹:“她(母亲----笔者注)从来没有做过女王也没有做过仙女……,地牢就是母亲本人”[1]189。昆丁被评论家引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我有母亲我就可以说母亲啊母亲。”[1]188如果说,康普生夫人固守着南方淑女的神话,那么从儿子昆丁的话中,我们可以断言,在现实生活中,康普生夫人不是真正的南方淑女,她没有担负起南方淑女的家庭责任,她的种种行为均与淑女的传统背道而驰。
谈到康普生夫人是一个“缺席的母亲”,就不能不提美国南方的荣誉观。Bertram Wyatt-Brown提出,不同种族的南方人保持着一种共有的、存在于现代化之前的对个人和家庭的荣誉观,南北战争前,在南方人的活动和人际关系中,荣誉观以一种惊人的、错综复杂的方式影响着人的行为、态度和价值观。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避免耻辱比希望获得荣辱更加激励人心,是一种有力的行为动机[4]217。这种固守家族荣誉的文化和南方社会的特点密不可分。南方社会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等级社会,统治阶级靠血统和家族荣誉来稳固等级社会的根基及其统治。此外,多元化的旧南方存在着诸多阶级矛盾和种族矛盾,荣誉感可以“连接社会生活中迥异的方方面面”,“成为连接种植园主和偏远居民的桥梁”,同时“保持地区的共同特征、持续性和差异性”[4]217。康普生夫人正是由于对旧文化中家族荣誉的崇尚,一步步走向抑郁的深渊,放弃了母性,成为一位“缺席的母亲”。
康普生夫人本名卡罗琳·巴斯康,出生在一个南方贵族家族。她受到旧南方血统观念的影响,把家族荣誉看得高于一切。现实和理想却相距万里。卡罗琳小姐嫁给了一个已濒临分崩离析的家族。康普生家族曾经显赫一时,祖上出过好几个州长和将军,然而现在只有为数可怜的几个黑人佣人和一个破败的大宅子。康普生夫人经常抱怨、哀叹,动辄就提起本家巴斯康家族的高贵血统,批评康普生家族的“自命不凡”。 小儿子班吉明最初以舅舅的名字命名,后来因为孩子是智障,康普生夫人怕儿子有辱巴斯康家族的名誉,就立刻改名为班吉明。值得注意的是,卡罗琳潜意识中有一种对本族血统的自卑感和自怜感。巴斯康家族也并不荣耀,孩子们的舅舅毛莱是巴斯康家族唯一的男性,康普生夫人处处维护他,然而这个毛莱并不给姐姐争气,他和有夫之妇帕特太太有染,还被帕特先生发现。在旧南方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丈夫如果发现妻子和他人有染,他可以杀死通奸人而不受法律的制裁。可想而知,这种伤风败俗的行为一定使卡罗琳小姐在整个镇上抬不起头。
但是,正像前面讨论的那样,南方淑女的生活中心是孩子。每个母亲都应该以自己的孩子为傲,然而,康普生夫人却感到极大的耻辱。她的两个最大的耻辱就是小儿子班吉明天生智障和女儿凯蒂放荡不羁。她骨子里憎恨小儿子班吉明,因为儿子的智障给她本家族带来莫大的耻辱,她认为生出白痴儿子是因为她错误地嫁给康普生家族,是上帝对她的惩罚。班吉明“已经是对我所犯的罪孽的够沉重的惩罚了”,“他来讨债是因为我自卑自贱嫁给了一个自以为高我一等的男人”[1]114。她对班吉明冷酷,缺乏母爱。她虚伪地把小儿子改名为班吉明,意为最爱的孩子,但是事实上,不像南方慈母夜以继日地看护生病的孩子,她自己很少身体力行地给班吉明母爱和关怀,依靠黑仆照顾班吉明,班吉明因此经常遭到谩骂和虐待。在很大程度上,班吉明从母亲那里得到的只有她自怜的泪水和压抑的生活环境。
Philip Weinstein提出,康普生夫人把她的婚姻和做母亲的经历看做是对她的一种诅咒,这一诅咒把她曾经受过的淑女教育变成了笑柄[6]69。她受过的教育是,“对于女人来说没有什么中间道路”,“要就是当一个规规矩矩的女人要就是不当”[1]115。对于康普生夫人,女儿凯蒂的失贞是对家族荣誉的最大打击,给家族和她这个母亲蒙上莫大的耻辱。康普生夫人不但没有设法帮助被诱骗的女儿恢复心灵的创伤,还要与耻辱划清界限,甚至怀疑凯蒂是否是自己亲生的。“我到底造了什么孽呀老天爷竟然让我生下这样的孩子。一个班吉明已经够我受的了现在又出了她的事。……有时候我瞧着她(凯蒂----笔者注)心里不由得要纳闷她是不是真是我肚子怀的。”[1]114康普生夫人总是觉得委屈,终日哭泣,耻辱感让她觉得“还不如死了呢”。后来,凯蒂被丈夫抛弃,她感到凯蒂更加有辱门第,于是残酷地把凯蒂逼出家门,自私地不让她见到自己的女儿小昆丁,还不让任何家人提起凯蒂,她决定抚养外孙女也主要是为了保护家族荣誉不再受到侵害。后来,小昆丁跟人私奔对康普生夫人又是一次莫大羞辱和讽刺。
长子昆丁受母亲的影响,他因“爱康普生家的荣誉观念”而死[1]345。昆丁攻读哈佛是康普生夫人的心愿,而昆丁在大学一年级时就因为妹妹的失贞而投河自尽,这又是康普生夫人的人生耻辱。她久久无法理解昆丁的死,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她说这是“……上帝不容的”[1]316行为,是针对她的报复。康普生夫人唯一喜爱的孩子是杰生,她说除了杰生,其他孩子“都不是我的亲骨肉,……与我一点关系也没有”[1]115。杰生却是个自私贪婪、残酷冷漠、唯利是图、背信弃义的小人。“福克纳说,杰生是我所塑造的最丑恶的人物。”[7]他盗取凯蒂给女儿的赡养费,虐待小昆丁,仇恨姐姐凯蒂,对母亲讥讽嘲笑,欺骗怠慢。只要康普生夫人出场,总会传出她的哭声和抱怨声。书中交代康普生夫人经常“犯病”,终日与药为伍,常卧病榻。这其实说明了康普生夫人的精神和身体都处在病态。
当家族荣誉损失殆尽,康普生夫人没有像传统的南方淑女那样诉诸于对上帝的信仰,而是选择了逃避母性责任。她被批评为“缺席的母性”、“不负责任的母亲”并非是因为固守南方淑女的形象,而主要是由于对家族荣誉的虚荣心和自怜。近年有评论家提出康普生夫人是一位“父性的母亲”,这不无道理。她对家族荣誉的极端重视体现出男性特征,她给班吉明改名,把凯蒂逼出家门,把外孙女留在家中抚养,这些都应由传统的父亲决定。难怪昆丁感叹,“……她(母亲----笔者注)总是当国王当巨人或是将军”[1]189。在现实生活中,康普生夫人没有履行其重要的母亲职责,对儿女缺乏母爱,缺乏管教,没有能够把南方传统传承给家族的下一代,连作为女性和母亲最起码的母性也消失殆尽。杰生说“有那么一个母亲,她一点不管束凯蒂也不管束任何人”[1]246。作为老一代南方淑女的代表,从康普生夫人身上,我们既可以看到一个活在南方淑女神话中的循规蹈矩的女人,一个固守荣誉的虚荣的女人,又可以看到她在本质上已经走向了旧文化的反面,这说明了旧文化的颓势已近。
三
如果说康普生夫人的中心话题是家族荣誉,那么谈到凯蒂的中心话题就是失贞。失贞是凯蒂人生的转折点,标志着她童真时代的结束和堕落的开始。在南方淑女的神话中,“贞操乃道德之最”,受到至高无上的保护,是南方淑女的高贵所在。
在班吉明眼里,凯蒂是他心爱的姐姐,她“头发像团火,她的眼睛里闪着小小的火星,……她身上有树的香味”[1]79。在昆丁眼里,凯蒂像个纯洁的仙女,“她的裙裾卷住在手臂上,她像一朵云似地飞出镜子,……在月光底下她像是一朵云彩……”[1]90。童年时代的凯蒂美丽、善良,富有同情心,洋溢着母性的爱和关怀。许多评论把凯蒂看做是母性的代表。在失贞前,凯蒂把爱和关怀给予康普生家族的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替代康普生夫人履行着母亲的责任。“卡罗琳·巴斯康拒绝做妻子和母亲,因而凯蒂必须而且命中注定为兄弟们担任这个角色。”[6]69和康普生夫人对班吉明的态度截然不同,凯蒂对班吉明的爱很感人。她对待小弟耐心、温柔,呵护有加,给他温暖和关爱。当班吉明被母亲说成是“可怜的宝贝儿”时,凯蒂“……跪下来, 用两只胳膊搂着我(班吉明----笔者注),把她那张发亮的冻脸贴在我的脸颊上。……‘你不是可怜的宝贝儿。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你有你的凯蒂呢。你不是有你的凯蒂姐吗’”[1]9-10。凯蒂是美好、纯洁的象征,班吉明能闻到凯蒂身上“有股树的香味”,这种香味一直弥漫在班吉明的叙述中,直到凯蒂失贞。有评论称,因为班吉明只有3岁孩子的智商,他是人类灵魂和道德的一面镜子,从他那里,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自己的面孔。昆丁对班吉明漠不关心,杰生对班吉明冷酷残忍,康普生夫人看到班吉明就顾影自怜,而凯蒂折射出美丽善良的形象。童年时代的凯蒂是南方淑女文化中“真、善、美”的代表。
凯蒂“沾上泥巴”的裤衩的意象,香水污染了凯蒂身上的树香等等都预示着凯蒂的纯真必定会消失。凯蒂的失贞是因为受到了诱骗。那天凯蒂失身了,于是班吉明“边哭边向她(凯蒂----笔者注)走去,她往墙上退缩, 我(班吉明----笔者注)看见她的眼睛,于是我哭得更厉害了,我还拽住了她的衣裙。她伸出双手,可是我拽住了她的衣裙。她的泪水流了下来”[1]75。凯蒂因为自己的失贞而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凯蒂失贞后,嫁给了赫伯特,后来被丈夫抛弃,又被康普生夫人赶出家门。凯蒂一步一步堕落,一个“真、善、美”的化身最终沦为纳粹的情妇。最后一次,凯蒂出现在一张杂志的照片上,我们可以从她的装束中猜出,她一定过着奢华腐败的生活,但“艳丽、冷漠、镇静”,表现出“一副什么都无所谓的样子”暗示着精神的空虚,她最后消失在巴黎街头[1]349。黑人女佣迪尔西一语道破凯蒂堕落的原因,“凯蒂并不需要别人的拯救”,她“已经再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值得拯救的了”,“因为现在她能丢失的都已经是不值得丢失的东西了”[1]352。 换言之,贞操观是导致凯蒂堕落的重要原因。失去了贞操,南方淑女从崇高地位摔到了地狱,她们身上再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珍惜,失去了一切荣耀,真诚、善良、温柔等美好的女性品质也注定随之丧失,连基本的尊严也消失了。社会文化的压力,家族的压力,抚养女儿的压力,加之哥哥昆丁和父亲的死,杰生对她的痛恨也是凯蒂堕落的原因。与母亲康普生夫人不同,凯蒂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她生活在传统大家族,但母亲对她缺乏爱和管束,凯蒂行为与南方淑女文化渐行渐远,她也并非要挑战传统,然而命运的戏弄让她无法走进南方淑女的传统。
凯蒂的失贞体现了南方淑女文化的悖论。首先,她的失贞质疑着贞操观。正像康普生先生所说,贞操是男人发明的。我们不禁要问,失去所谓的贞操就意味着失去了理想,失去了美德,失去一切吗?凯蒂失去了贞操就随波逐流,任凭命运摆布。我们为凯蒂的堕落而感到痛惜,为南方淑女的“真、善、美”的消亡而深深地感怀。另一方面,凯蒂的失贞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康普生家族的分崩离析。昆丁走向自我毁灭,班吉明失去了心爱的姐姐,杰生一生充满憎恨,成为了一个没有子嗣的老单身汉,康普生夫人郁郁寡欢、怨声载道,康普生先生酗酒而死。这又体现了旧文化的残存势力仍然强大,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影响还在控制着人们。
四
南方奴隶制社会豢养了种植园主阶级,他们的一切体力劳动都由黑奴包办,因此在南方社会才有可能出现精心修饰其举止言谈的南方绅士和淑女们。随着南北战争中南方的惨败,旧的种植园经济的宣告结束,种植园主阶级解体了,南方贵族所推崇的南方淑女文化也渐渐走向衰亡。“南方淑女的演变是形形色色的。有的拒不承认现实终将被淘汰,有的面对现实手足无措,只能随波逐流。但是更多的则在变迁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8]
福克纳刻画了形形色色的南方淑女,其中,康普生夫人就属于第一类。她生活在南方淑女的神话中,固守着旧的传统和虚荣,但终将无法阻挡历史的前进,必将被生活所淘汰。在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中,很多南方淑女形象是属于康普生夫人这类。如《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多年来把自己关在家中和死尸共枕的艾米丽;《八月之光》中疯狂而变态的老处女乔·安娜伯顿和《押沙龙,押沙龙!》中的心灵扭曲的老处女罗莎。这些南方淑女像“纪念碑”一样,象征着过去,代表着传统的辉煌,但是又像植物的标本一样,虽然看上去还完好无损,但已经失去了生命,不堪一击。凯蒂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第二种。她在失贞后,完全放弃了一切,随波逐流,丧失了原来美好的一切。书中凯蒂的女儿小昆丁也是母亲的类型。她既叛逆又无礼,完全没有她母亲儿时的“真、善、美”,她最后私奔离家证明了南方淑女文化的真正消亡。《押沙龙,押沙龙!》中反传统的朱迪丝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一类型。
福克纳塑造的南方淑女形象没有侧重于在现实中南方女性如何在新旧文化更迭中积极地面对生活,重新塑造自我。这也许是因为福克纳的作品隶属南方文学,南方文学更加强调哥特式的怪诞情节的描写,因此他的小说更具有神话和传奇色彩。更重要的是,这和福克纳本人对南方文化的情感有关。其实,在很大程度上,福克纳在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中体现了南方文化和传统的悖论,以及对南方淑女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他崇拜南方淑女的“真、善、美”,尊崇她们的母性和纯洁,同时又深刻地体会到南方淑女文化对女性的毒害。在《喧哗与骚动》中,康普生夫人和凯蒂都是南方淑女文化的牺牲品。康普生夫人因固守着南方淑女的神话和家族荣誉,走向了虚荣和自怜,失去了母性,本质上已和南方淑女形象大相径庭,走向了传统的反面,给整个家族带来了压抑和灾难。凯蒂的行为违反了南方淑女文化,她也因此失去了贞操,失去了一切的荣耀,她所代表的南方淑女的“真、善、美”也随之毁灭。两位女性的命运是南方淑女文化嬗变的缩影,从她们身上我们既可以看到旧文化的去势已经势不可当,又可以感受到南方淑女文化的影响犹存。整个康普生家族都因为两位南方淑女而充满了喧哗与骚动。福克纳深刻地展现了南方淑女文化的悖论,把历史更迭时期南方社会生活和文化的诸多方面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用一个贵族家族的衰败史成功地展现了出来。通过两位南方淑女,我们可以窥视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中的淑女形象。文学艺术与历史事实存在本质的区别。我们在体会福克纳笔下南方淑女可悲命运的同时,高兴地看到在历史进程中,广大南方女性没有墨守成规,没有随波逐流,而是积极地走出旧文化的阴霾,重新树立女性形象,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参考文献:
[1]威廉·福克纳. 喧哗与骚动[M]. 李文俊,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2]Faulkner W. The Sound and The Fury[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7.
[3]Clarke D. Erasing and Inventing Motherhood[M]∥Bloom H. Bloom's Modern Critical Views: William Faulkner. New York: An Imprint of Infobase Publishing, 2008:171-200.
[4]McMillen G S. Women in the Old South[M]∥Boles B J. A Companion to the American South.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2.
[5]Wheeler S M. New Women of the New South[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6.
[6]Weinstein P. “If I Could Say Mother”: Construing the Unsayable About Faulknerian Maternity[M]∥Bloom H. Bloom's Modern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William Faulkner's The Sound and the Fury. New York: An Imprint of Infobase Publishing, 2008.
[7]肖明翰. 威廉·福克纳研究[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7:260.
[8]钱满素. 美国南方淑女的消亡[J]. 外国文学评论, 1987(3):6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