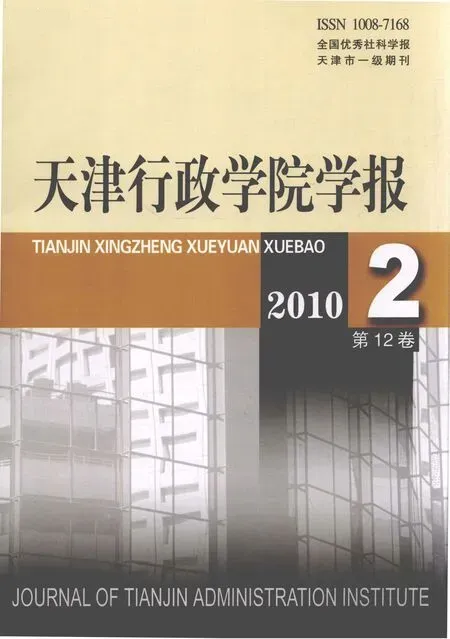环境管制与投资保护的法律冲突与协调
朱工宇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环境管制与投资保护的法律冲突与协调
朱工宇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晚近以来,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投资保护水平,成为了投资者对抗东道国公共管理权的利器,以致环境管制与投资保护之冲突时常见诸报端,并有愈演愈烈之势,东道国往往须就其环境管制行为向外国投资者支付巨额补偿,这引发了普遍忧虑。我们通过以环境管制引起的国际投资争议为焦点,拟从NAFTA条文本身和仲裁实践两个角度探究其处理环境管制与投资保护冲突的经验和教训,考察现有框架并预测未来规范之发展趋势,提出可行建议以资我国借鉴。
环境管制;国际投资;NAFTA
一、环境管制与投资保护之冲突及其实质
晚近以来,环境保护特别是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在各国政府的经济决策过程中占据重要位置,全球或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应以环境、人权利益为代价的观点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所接受,贸易、投资、环境、人权、知识产权等问题密不可分的观念也日益深入人心。过去,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外国投资,竞相降低环境标准,以致“涸泽而渔,焚林而猎”,产生了诸多“污染天堂”。这不仅破坏了全球生态平衡,也造成了国家间投资待遇的不正当竞争。如今,国际社会开始致力于建立合理的环保法制与公平的竞争秩序,以促进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然而,东道国环境标准的提高及环境管制措施的实施,可能破坏投资者的合法期待,影响其对财产的使用、处置和收益,从而引发投资争端。再加上环境标准和环境影响评价往往是复杂的技术问题,受制于科研水平并随其变化而变化,而投资的固定性和长期性决定了它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及时适应新的转变,这就可能导致原先合法的投资在一夜间成为非法,以致投资在事实上归于无效,引发征收争议。同时,贸易投资自由化是全球经济不可逆转之趋势,投资环境的逐步改善促使资本觅利性得以充分实现,同时却也引发了不容小觑的全球环境和公共健康危机。随着经济发展水涨船高并通过新的投资争端仲裁机制获得保障的投资者待遇,成为了投资者对抗东道国公共管理权的利器,以致环境管制与投资保护之冲突时常见诸报端,并有愈演愈烈之势。环境管制引起的投资保护争议只是表象,其背后所体现的利益冲突才是问题的实质。
(一)环境保护与国际投资的冲突。相对早已是国际经济法领域中显学的环境与贸易问题而言,环境与投资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较之前者,后者具有一定特殊性。在环境与贸易相冲突的情形下,环境措施通常针对跨国的货物或服务流动,因此冲突通常发生在国与国之间,其影响波及多国,从而对整个国际贸易产生扭曲作用;在环境与投资相冲突的情形下,环境措施通常针对某个或某些特定领域的投资者,发生在东道国与外国私人投资者之间(虽然投资者之母国亦时常卷入争端),影响范围相对有限。不过,针对东道国禁止或限制外国投资的管制措施,投资者可能面对投资的血本无归,也可能面临繁琐的求偿程序,东道国则常常要承担征收补偿等国际法上的责任,因而解决环境与投资冲突问题比之环境与贸易冲突问题往往更复杂[1](pp.201-202)。
(二)跨国市民社会的基本社会价值与跨国公司代表的私人利益的冲突。晚近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深入,一个由非政府组织代表的跨国市民社会正在形成。非政府组织通过游说、提供信息和专家服务等方式积极推动国际“社会立法”活动[2](p.145)。此类国际社会立法侧重限制跨国公司不当的利益扩张,以保护环境、劳工人权、人类健康与安全等社会价值。环境管制与投资保护冲突的实质就是跨国市民社会基本价值与跨国公司利益之间的冲突。但从目前的实践情况来看,投资领域的立法往往存在强有力的执行机制,而环境保护等社会立法仍然不能摆脱软法的地位。
(三)东道国公共利益与投资者个人利益的冲突。这主要表现为间接征收问题,从目的看,以往的征收是基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现今引起征收争议的措施通常是为了保护环境、人类动植物健康和安全等公共利益;从性质看,以往的征收往往直接剥夺财产所有权而构成直接征收,现今引起争议的东道国管制措施并不直接剥夺投资财产的所有权,却可能产生与剥夺所有权类似的经济效果,从而构成间接征收;从行为主体看,传统的征收基本是发展中国家针对发达国家的投资者采取的,反映了作为资本输入国的发展中国家和作为资本输出国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对抗。而间接征收之实施者却并不分发达与否,故更多体现为东道国的公共利益与投资者私人财产权利的冲突。
近年来,外国投资者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NA FTA)提起的挑战东道国管理主权的案例,引起了东道国政府及国民的极大担忧。若东道国须就环境管制行为向投资者支付巨额补偿,就会对其政府之决策产生影响,使得他们在行使公共管理权时顾虑重重,以致更多在意可能导致的诉累和经济压力而非社会大众的利益[3](p.119)。一些非政府组织也激烈地表达了他们对投资者重复使用投资保护规定来挑战东道国环境管理措施的批评,并认为此举会给环境保护造成不可预估的破坏。笔者拟在下文中从NAFTA条文本身和仲裁实践两个角度探究其处理环境管制与投资保护冲突的经验和教训,以资我国借鉴。
二、NAFTA关于环境管制与投资保护的规定与实践
(一)NAFTA体制背景分析。目前,在区域性国际经济立法层面上,将投资问题与环境问题挂钩的最典型的立法模式出现在NAFTA中。其设计者们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贸易、投资、金融等诸多经济活动之间密不可分,北美统一自由市场的形成,决不能将贸易自由化作为唯一手段和依靠。因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者意图一并解决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知识产权保护、人权保护等诸多复杂的议题。不过,谈判形成的NAFTA,本质上仍主要是一个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条约。
谈判者注意到,虽然 GA TT在推动战后国际贸易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一味追求贸易自由化,GA TT并未成功地倡导以可持续方式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故遭到环保主义者在世界范围内的强烈抨击。为吸取其历史教训,同时也是迫于环保组织和人权组织的强大压力,NAFTA的谈判者在NAFTA的正文以及关于投资规则的第11章,都规定了一些关键性的、有创新性的特别环境条款。此外,在缔约过程中,还缔结了两个附加协议作为NAFTA的组成部分,其中之一(另一为关于劳工保护的协议)就是《关于环境合作的北美协议》(NAAEC)①,以期达到两个目标:其一,实现可持续发展性质的投资自由化,推动环境法规的更新和环境标准的提高,反对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吸引国际投资;其二,防止环境管制措施和立法成为变相的歧视甚至剥夺外资财产权的手段或工具。不过,在投资与环境问题挂钩的立法模式上,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承担严格而全面的环境责任不仅为NA FTA谈判成员方政府反对,也为跨国投资者反对。因此,最终NAFTA没有选择依靠NA FTA该基础条约本身全面解决环境问题,故并未全方位纳入环境规则并使这种规则与投资规则一并生效且具备同等强制执行力,而是将更为详尽的环境义务规定在作为NAFTA附属协议、效力较弱的NAA EC中。这不能不说是其时代局限性所致。
(二)NAFTA体制下的投资规则。NAFTA第11章从实体标准和程序规则两个方面给予了投资者迄今为止的国际投资条约所能提供的最强有力的保护,正因此,对于其对环境保护的影响,学者们普遍表达了忧虑。
1.实体法规则。主要包括:
首先,该章 C部分对“投资”、“投资者”和“缔约国措施”等概念做了宽泛定义。第1101条规定,该章适用范围是缔约方对另一方投资或投资者所采取的措施,可见上述定义的范围大小直接影响该章所有实体规则的适用。“缔约方措施”是投资者提起仲裁的前提,NAFTA所规定的缔约国措施包括“任何法律、法规、程序、要求或实践”,这就为其扩展到政府行为或政策等领域留下了可能,并且该措施不仅指国家政府的措施,州、省等地方政府的“措施”也包括在内。换言之,几乎所有形式的影响外国投资的政府行为都属于NA FTA调整的范畴,其中当然包括各种环境管制的立法和措施。
其次,该章A部分规定了投资保护的实体标准(主要有五大原则)。对上述“缔约方措施”的调整,就主要依据此部分:
就投资待遇,该部分规定了国民待遇(第1102条)、最惠国待遇(第1103条)两大根本原则,并以符合国际法的最低待遇标准(第1105条,包括公平与公正待遇)原则作为补充,从绝对和相对两个层面保证投资者能得到全面的保护。这些待遇标准适用于投资的各个方面,包括投资准入阶段。
就投资经营阶段,规定了禁止履行要求原则(第1106条),成员方不得实施如出口业绩、当地成份、优先购买本地产品或服务、贸易平衡以及技术转让等履行要求。投资者可将其利润、清算或出售所得、借贷支付或其他与投资有关的资金,按市场汇率兑换成可自由使用的货币,自由汇往国外。
就征收问题,规定了高标准的征收补偿原则(第1110条),任何成员国均不得对投资采取直接或间接的国有化或征收,或采取相当于(tantamount to)国有化或征收的措施,除非:(1)出于公共目的;(2)以非歧视的方式;(3)经过适当法律程序;(4)支付公平的补偿。其中“相当于征收”的概念值得关注,这一提法并非NAFTA首创,以往的美式双边投资协定范本中也存在着相似用语,不同之处在于其表述上与直接征收和间接征收并列。这是否意味着“相当于征收”已成为独立于后两者之外的第三种征收形式?如在Pope&Talbot v.Canada案中,投资者就曾主张“相当于征收”突破了间接征收的概念,包含了“会对投资者的投资产生实质性干涉效果的普遍应用的非歧视措施”[4](Para.84)。尽管仲裁庭做了限制解释,认为“相当于”(tantamount)的含义与“等同于”(equivalent)无异,因此“相当于征收”的用语并未“扩大国际法下征收的通常含义”[4](Paras.103-104)。然而,模棱两可的措辞仍然可能导致投资者的宽泛理解,如此一来,东道国之环境管制措施被认定为征收的可能性大为提高。
2.程序法规则。该章B部分为投资者设计了强有力的争端解决程序,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投资者对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M,见第1116条)。NAFTA默认缔约各方对仲裁的同意是“永久性”、“不可变更”的并对任何因该章而起的案件都有效。据此,投资者掌握着启动强制性的、有约束力的仲裁程序的主动权,可以直接将争议提交仲裁,仲裁或依据“ICSID”仲裁规则进行,或依据“UNCITRAL”仲裁规则进行,而不必通过传统的东道国当地救济措施或是外交保护。有学者指出,这可能引发两个严重后果:其一,投资者得以借助一个非透明且没有上诉机会的仲裁程序回避东道国基于当地救济原则或公共利益方面的理由对案件的管辖;其二,由于提起此类国际仲裁成本较低且十分容易,投资者可能会滥用权利随意对国家主权发起挑战[5](p.110)。这就可能导致东道国在环境保护、公共健康等方面的公共管理权行使危机。
(三)制约投资规则的环境规范。NA FTA曾被一些评论家誉为是有史以来“最绿色”的贸易协定[6](pp.817-818)。原因在于其规定了若干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规则,并订立专门的《北美环境合作协定》以促进区域内的环境合作。有关环境与投资的规定突出地体现在第11章第1114条,这也是NAFTA区别于以往国际投资条约的最明显标志,并为成员国处理投资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调。该条规定:本章的任何条款不得解释为,阻止成员方在符合本章规定的条件下采取、维持或执行其认为适当的措施以保证境内投资活动以一种考虑环境因素的方式展开。缔约方认识到通过降低本国健康、安全或环境措施来鼓励投资是不合适的。因而,缔约一方不应放弃或以其他方式减损,或意图放弃或以其他方式减损此类措施,作为设立、收购、扩展或保持本国境内投资者的投资的鼓励。如果缔约一方认为另一缔约方意图提供该等鼓励,它可要求与该缔约方进行协商,双方应就避免该等鼓励而达成意见。
但该条规定仅仅具有软法性质,不具有对抗第11章投资保护条款(包括征收条款)的强制效力。首先,从条文内容来看,什么是“适当性”、什么是“考虑环境因素”(sensitive to environmental concerns),这些重要的概念都没有明确的解释。并且该条文将“在符合本章规定的条件下”作为适用的一个前提,这就意味着如果发生第1114条第1款与第11章其他投资保护条款的冲突,环境规定应当附属于该章其他投资保护条款之下。其次,从该条款订立的背景来看,该条规定是在NAFTA谈判的最后阶段加入第11章的,缔约方没有对该条的适用范围进行过广泛的讨论[7](pp.679-680)。可以推测,缔约方当初制定此条的目的在于防止墨西哥通过降低环境标准来吸引投资,从而避免对区域内环境保护造成损害性后果,并未考虑到第11章的其他条款与该条相冲突的情形。因此,缔约方的订立目的并非确认环境管制作为投资保护例外的地位。再者,从已发生的案例来看,在考虑东道国采取的环境管制措施是否构成征收时,仲裁庭尚未作出“将第1114条作为第11章例外”的判决。因此,对其实际所能发挥的作用不容乐观。
纵观整个NA FTA法制,还可以发现诸多“绿色”内容。例如:首先,序言要求,成员方应“确保为商业和投资提供一个可预见的商业性框架并符合环境保护”。这相当于《W TO协定》中关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宗旨性宣告,虽然抽象,但为界定NAFTA的“绿色”性质以及为日后相关争端解决机构做出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条约解释奠定了基础。其次,依据第1106条第6款规定的关于限制履行要求的环境例外,成员方基于“保护人类、动植物生命之必需”以及“保护生命物和可用竭之自然资源之必需”,可对国际投资采取限制性措施。再次,第2101条规定:“任何缔约方为保证遵守与该协议条款不冲突的健康、安全和消费者保护等相关的法律或规定而采取某些措施,只要该等措施不是任意的歧视性措施,则NAFTA贸易、跨界服务与通讯的技术壁垒和货物贸易的章节不应视为阻止成员方采取或执行该等措施。”这似乎暗示了环境管制措施在贸易领域可作为一般例外而存在。此外,NA FTA附件NAA EC第1条就明确其目标之一是“为我们和下一代的生存,在缔约方领域内培育对环境的保护与促进”而不造成“贸易扭曲或新的贸易壁垒”。第3条还规定“(在)承认每一成员方有权建立本国的环境保护与发展的政策和优先权的标准、有权相应地订立或修订环境法律法规(基础上),成员方应确保其法律法规制定了高标准的环境保护并应力求继续改进这些法律法规”。
尽管有学者认为,这些条款结合在一起可以作为解决第11章征收与环境条款冲突的解释性工具,仲裁庭有可能在上述非投资规则的NAFTA条款中发现类比性,或是支持对第1114条的扩大解释[7](p.682)。但从整个NA FTA法制上说,这些“绿色”条款只反映了立法者们关注环境的倾向,尚不具备抗衡传统投资保护条款的效力。可以明确地说,NAFTA并未赋予环境管制作为征收例外的优先权。不过,如果NA FTA下所涉案件的仲裁员真正能够超脱政治和外交的种种影响而独立行事,并充分认识到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考虑因素,并愿意像W TO某些案件(如“海虾-海龟案”)中的专家小组那样本着兼顾经济利益和环保利益的态度去断案,那么,NA FTA中的环保条款及附属协议中的环保规则甚至NAFTA体制之外的一些环境公约,都可以为仲裁庭善意采用以维护环保和投资之间的利益平衡。
(四)NA FTA的仲裁实践——公益目标依然受挫。遗憾的是,尽管NAFTA做出了上述平衡环境利益和投资保护的立法努力,但正如 W TO虽规定了有利于环保的例外规则却无法有效利用一样,从NAFTA相关具体案例处理结果来看,促进环保的立法初衷很难实现,投资者反而频繁利用ISDM机制挑战NA FTA的环保规则以及成员国的公共管理权。以下是几个代表性案例:
1.“Ethyl案”(Ethyl Corp.v.Canada)。“Ethyl案”是基于NAFTA第11章提起诉讼的第一案。Ethyl公司设在美国佛吉尼亚州,于1997年对加拿大提起诉讼,索赔损失1.25亿美元。Ethyl生产一种被称之为MM T的汽油添加剂,并将其运至加拿大境内加工并销售。1997年,加政府颁布法令禁止MM T的跨省贸易和商业进口,并声称此法令旨在保护人类健康,理由是MM T中含有某神经毒素。Ethyl认为:首先,加拿大对MM T贸易的禁止剥夺了该公司预期的利润,故相当于第1110条所称之“征收”;其次,该禁令属于第1106条所禁止的“履行要求”,因为其实际效果是迫使Ethyl在加拿大每一省份都设立生产MM T的工厂;其三,加拿大没有禁止国内厂商对MM T的生产和销售,导致外国投资者所享受之待遇低于其国内投资者,故而违反第1102条之国民待遇原则。在该案中,加拿大起初试图以管辖权异议为由阻止仲裁,1998年尝试失败后,加拿大通过与 Ethyl主动达成协议结束了诉讼,条件是加拿大废除禁令,支付近2000万美元作为赔偿,并就禁令关于 Ethyl的产品有害健康的暗示公开道歉。
2.“M etalclad 案”(M etalclad Co rp.v.United Mexican States)。M etalclad是一家从事有害物质掩埋业务的美国公司。为拓展业务,该公司收购了位于墨西哥圣路易斯波托西州瓜达卡扎市的一家同业公司。在得到墨西哥联邦政府同意的情况下,Metalclad初步投入资金并准备在该市建立垃圾处理工厂。但瓜市拒绝颁发建筑许可并发布禁令禁止工厂开工,随后,圣路易斯波托西州又宣布该工厂所在地为自然保护区,并声称其目的在于保护稀有仙人掌的生存环境。投资经营活动全盘受挫的M etalclad公司遂依据NA FTA第11章提起仲裁。仲裁庭裁定:瓜市拒绝颁发建筑许可和禁止工厂开工的行为违反了第1105条第1款所规定的“公平公正待遇”规则;墨西哥联邦政府对瓜市政府行为的默许构成了第1110条所称之“相当于征收”的措施;由于未向投资者提供关于有害物质掩埋场地的可预见的法律框架,联邦政府违反了第1105条最低待遇标准义务;故墨西哥应就M etalclad投资所受损失向后者赔偿近1700万美元。该案最终以双方达成赔偿1600万美元的协议而结案。
3.“M yers案”(S.D.M yers,Inc.v.Canada)。M yers是一家处理有害废料的美国公司。为扩充废料来源,该公司游说美国环保局,以求获得允许其从加拿大进口 PCB(一种有害废料)的许可。1995年加拿大环境部长发布一项临时禁令,禁止从加拿大出口 PCB到美国。禁令执行16个月后,出口市场重新开放,然而不久后进出口市场又被封闭。M yers遂依据NAFTA第11章提请仲裁,仲裁庭裁定:加拿大禁止 PCB出口主要是为了保护国内 PCB废料处理产业,因而违反了第1102条关于国民待遇的规定;加拿大以牺牲外国投资者利益为代价禁止PCB的出口,是一种不必要的贸易限制且片面有利于国内产业,因而违反了第1105条关于最低待遇标准的规定。
(五)小结。从NAFTA相关条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NA FTA第11章以高标准的投资保护和全面的投资自由化为目标,虽涉及了环保的内容,但不具有对抗投资者权利的绝对效力。随着各国环境管制措施的增多,引起环境保护目标与投资者权利保护冲突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而NAFTA的规定不能协调这种冲突,反而只能加大政府在投资领域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投资者所代表的私人利益之间的背离。反观W TO机制,GA TT1994第20条(一般例外)的规定起到了一种平衡作用,该条可以作为成员方因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需要而采取贸易限制措施的抗辩依据。
从仲裁庭的实践来看,仲裁庭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环保的内容,无论对国民待遇的判断还是对征收的判断,都肯定了东道国管理公共事务的正当性,但并不承认环境管制具有征收例外的效力。此外,第11章仲裁程序的不透明、仲裁庭的临时性质、缺乏上诉机构等固有缺陷,均可能影响仲裁庭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权衡。因此,NAFTA的争端解决机制并不能保证妥善处理投资与环保的关系,只要仲裁庭对于NAFTA下的一系列投资保护条款做出宽泛的解释,就会危及成员国政府对环境的合法管理权。而从成员国政府的角度来看,考虑到NAFTA下的投资保护条款过于严格,他们有时更愿意积极谋求诉讼外的协商,通过牺牲环保标准或提供赔偿的方式达到息事宁人的目的。
三、NAFTA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的启示及相关对策
NA FTA成员方所遭遇的国家公共管理权危机,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之前由于我国环保力度不够,致使外资将不少污染密集产业转移到境内,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从目前我国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及国内环境立法情况来看,内容上存在诸多缺陷,可能会对我国的投资保护实践带来很大的风险。一方面,随着我国环境保护力度的加强,政府对外国投资采取环境措施的可能性增大,如果处理不当,极易发生投资者对我国提起征收争议的国际仲裁;另一方面,一旦发生投资者因环境措施对其财产的消极影响而对我国提起国际仲裁,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很可能会导致我国在仲裁中败诉从而承担巨额补偿责任。因此,我们应吸取NAFTA的经验教训,首先在立法上对环境管制与投资保护的问题进行协调,防患于未然。
(一)中国应加强环境保护实施标准、程序等方面的国内立法,以求进一步完善环境法制。在环境措施引起的征收之诉中,仲裁庭会对国内的环境政策进行审查。若该环境政策违反国内环境立法,很可能会被认定为歧视性政策,从而构成征收。在这种情况下,歧视性环境措施并不能获得征收例外的效力。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已初步规范了外资准入阶段的环境要求,但对外资运营阶段的环境保护要求规定得很少,且多为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的环境执法程序。国内法中环境评估标准的不完善、执法程序的不透明,很可能会导致我国在有关征收争议的国际仲裁中败诉。因此,中国可借鉴多数国际环境公约的规定,制定具体的风险评估方法和标准及实施环境措施的具体程序,这样才能有法可依,不致因国内环境措施程序不合法或具有歧视性而导致败诉。
(二)在国际投资条约的谈判和执行阶段引入独立的环境评估机制,并强化环境专家参与机制。为确保环境利益能够在投资条约中得到充分体现,并及时有效地影响投资自由化谈判的价值判断,避免出现NA FTA第11章过分偏袒投资者利益的条款设计,从谈判缔约的一开始,就应当引入独立于政府的环境影响评估机制,并由独立的、真正的环境专家组成的专家组进行科学的分析。此外,鉴于贸易投资条约的谈判者和争议裁判者多为贸易投资领域的官员或专家,因此,为缓解贸易、投资和环境利益之间的冲突,合理解决相关纠纷,在条约的执行中引入环境专家参与机制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三)在未来与NAFTA模式相似的综合性自由贸易协定下投资议题的谈判或其他与投资有关的国际协定的谈判过程中,增加环境议题并与其他议题挂钩。可以考虑通过一揽子谈判的方式,将环境规则有效纳入条约中,并赋予其与投资、贸易规则一样的强制执行力,确保其与投资保护规定冲突时,具有相对优先效力。这是因为从历史经验来看,环境问题若留待有关贸易、投资自由化事项谈判结束后再由成员国政府商量处理,其复杂性将导致对环境问题的专门谈判难以单独开启。而且,正如同W TO的谈判方故意选择多种议题的一揽子谈判方式和多个协议的一揽子生效方式一样,如果仅因谈判方对环境议题存在意见分歧而导致整个贸易投资自由化谈判程序的停顿甚至崩溃将得不偿失且成本巨大,故可迫使各方在已就贸易投资规则等其他议题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搁置对环境规则的歧见并接受整个条约。
(四)对投资条约中 ICSID仲裁管辖权的接受范围,应恢复部分接受模式,采取以一揽子部分接受为原则、逐案酌情接受为例外的立场。尽量将环境措施引起的投资保护之诉置于国内法院的管辖下,而不是交给更倾向于保护跨国公司利益的国际仲裁庭。晚近以来,我国缔结的多个B IT(如中荷、中德B IT)全盘接受了 ICSID仲裁管辖权。从原先仅同意就与投资者之间的有关征收补偿款额的争议提交 ICSID仲裁扩展到全盘同意ICSID仲裁管辖与投资者之间有关投资的任何争议。换言之,投资者可以单方面地将有关环境管制引起的征收争议提交ICSID仲裁。这样一来,很可能出现我国国内管制措施在国际上“受审”的情形,而ICSID自身的特点又增大了我国在征收纠纷中败诉的可能[8](pp.128-131)。因此,有必要恢复之前的部分接受模式。
(五)在国际投资条约中应谨慎处理对投资者权利救济问题,尤其不可轻易规定“投资者对国家”争端解决机制。虽然促进投资和确保市场准入具有重要意义,但在投资条约中单方面给予私人投资者救济权以规避东道国国内法律体系的管辖是非常危险的,片面给予权利而不伴随相应义务的做法可能引发严重后果。在贸易投资纠纷中,政府一般会综合考虑多方影响,贸易商和投资者却与之不同,往往只为一己私利而置其他利益诉求于不顾。因此,在投资条约中对投资者权利救济问题的谨慎处理有助于正确处理投资条约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
(六)鉴于与跨国公司有关的外国直接投资在国际投资中所占的绝对比例,在投资条约中应纳入特别针对跨国公司的环境规则。这方面可以适当参考“OECD跨国公司指南”的若干相关内容,依据指南,跨国公司应当:(1)在其决策过程中,说明投资运作生产的主要目的和可以预见的环境后果;(2)向政府当局及时提供关于投资运营时所有的潜在环境影响和危害;(3)采取适当的控制技术和措施,为雇员实施培训方案,并准备意外事故方案,减轻不利的环境影响[8](p.148)。不过,由于该指南制定较早,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没有及时、充分地体现出环境问题在当今社会的一些变化,应对其加以改进。例如,增加民权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和对跨国公司的监管,强调对跨国公司危害环境行为的预防,明确相应的环境责任和补偿标准与程序等。
(七)进一步完善国际投资条约中的环境规则,甚或可采取一步到位的立法模式。首先,在条约措词上应表明东道国具有采取环境管理措施的权利和义务,以及重视环境保护的意图,这样在仲裁时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仲裁庭对协定的解释符合缔约方的本意。同时,借鉴2004年最新的美国B IT范本②以及 GA TT1994第20条,在投资条约中应规定普遍适用的环境例外,以统领各特定领域的环境例外规则(如NA FTA第1106条第6款关于限制履行要求的环境例外)。并明确缔约方旨在保护合法公共利益目标,如健康、安全以及环境而制定并采取的非歧视措施,不构成间接征收,赋予东道国环境管制以征收例外的效力。此外,NAFTA的一大败点在于其采取了将少数抽象的环境条款在条约正文中零星布局,却将促进环境利益的主要内容规定在作为附加协议的、没有强制约束力的NAAEC中的立法方式,以致一旦贸易、投资与环境利益发生冲突时,后者往往只能成为牺牲品。由此可见,以零星、抽象的环境条款来粉饰贸易投资条约的功利性和片面性的立法模式不利于可持续发展这一时代需求的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可能带来的环境影响只能或主要应当由东道国自己解决。因此,有效的解决方法应当是在此类条约中规定详尽的、能有效执行的、能有效消除贸易投资的消极环境影响的规则和原则,而非将环境问题交由环境条约单独处理或麻木不仁地将环保重担推卸给软弱无能的环境条约。
四、结语
目前国际投资立法的一大缺陷就在于不注重环境规则的建构,从而间接导致环境利益和东道国管理主权在环境管制与投资保护发生冲突时遭遇危机。当然,该体系构建本身也并非易事,理念转变也是其中一大难点,我们有必要放弃短视的“经济功利主义”和狭隘的“投资至上主义”。笔者以为,环境规则体系之架构是扭转现有国际体制缺陷、摆脱当前面临的环境困境和公共管理危机的关键一环。
注释:
①NAFTA附加协议的立法方式值得关注,因为这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起的旨在确立贸易投资法与国内、国际环境法之间真实有效的程序和实体联系的第一次多边立法尝试。Howard Mann.NAFA T and the Environment:Lessons fo r the Future,Tulane Environmental Law Journal,2000,113:388.
②2004年美国BIT范本出现了诸多新变化。例如,正文部分第6条规定:任何缔约方不得通过等同于(equivalent to)征收或国有化的措施对条约所保护的投资进行直接或间接征收或国有化。该措辞排除了NAFTA下对“相当于(tantamount to)征收”进行扩大解释的可能。再如,附录B对征收的规定更加详尽地为判断政府管制措施是否构成征收提供明确的标准。其中最具标志性的规定体现在附录B第3条和第4条,指出了直接征收与间接征收的区别,明确了间接征收的判断标准,更为重要的是,第4条第2款规定了国家管理权例外,指出:除极少情形外,缔约方为公共利益实施的非歧视的管制行为不构成间接征收。这是目前BIT实践对东道国管理主权与投资者权利的冲突问题的最终诠释。而我国签订的B IT或M IT中,鲜有涉及环境保护的内容,更没有诸如上述美国BIT范本中关于公共健康、安全及环境保护的征收例外之规定。
[1]Nii Lante Wallace-Bruce.Global Investment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the Battle Lines are yet to E-merge![J].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2002,(49).
[2]徐崇利.经济全球化与国际法中“社会立法”的勃兴[J].中国法学,2004,(1).
[3]Sam rat Ganguly.The Investor-State Dispute Mechanism and a Sovereign’s Power to Protect Public Health[J].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1999,(38).
[4]Pope&Talbot v.Canada[Z].Interim Award,June 26,2000.
[5]Francisco S.Nogales.The NAFTA Environmental Framework,Chap ter 11 Investment Provisions and the Environment[J].Annual Survey of International&Comparative Law,2002,(18).
[6]ThomasWaelde&Abba Kolo.Environmental Regulation,Investment Pro tection and’Regulato ry Taking’in International Law[J].International&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2001,October.
[7]David A.Gantz.Potential Conflicts between Investor Rights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under NAFTA’s Chapter 11[J].The George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2001,(33).
[8]魏卿.从NAFTA和MA I的视角看投资协定中的环境规则[J].经济经纬,2005,(1).
D99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8-7168(2010)02-0087-07
2009-10-16
朱工宇(1985-),男,浙江杭州人,华东政法大学国际航运与海商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博士生。
王 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