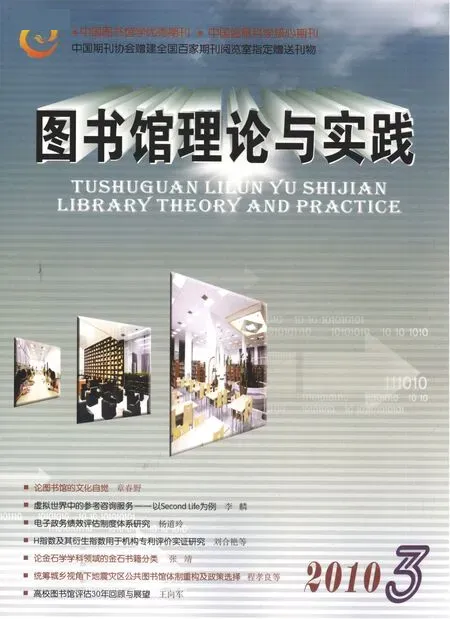研究元代刑狱制度的新史料——《至正条格》“狱官”条格初探
●陈广恩(暨南大学 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广州 510632)
《至正条格》是元朝的第3部法典,也是元朝的最后一部法典,但明以后就失传了,因此学界一直以为这部珍贵的法典已不存于世。2002年,韩国人意外地在庆州发现了元刊《至正条格》残本。残本《至正条格》包括“条格”和“断例”两大部分,其中“条格”部分仅存第23—34卷,“断例”部分仅存第1—13卷和第14—30卷的目录。2007年,在首尔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韩国公布了残本的影印本,中国学者这才开始接触到这部对元代社会历史和中国法制史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的非常珍贵的原始文献。《至正条格》的发现,在国际元史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它势必会为元史研究拓展出不少新的领域。元史专家陈高华先生曾不止一次地指出,《至正条格》将成为今后元史研究的一个热点。
《至正条格·条格》第33、第34两卷是题为“狱官”的条格汇编,共收有39目64条条格,具体名目如下:重刑复奏、恤刑、重囚结案(二条)、斗殴杀人结案详断、刑名备细开申(二条)、处决重刑、决不待时、囚案明白听决、刑名作疑咨禀、断决推理(二条)、罪犯有孕、二罪俱发、二罪俱发遇革、老幼笃废残疾(二条)、废疾赎罚遇革(以上卷33),审理罪囚(二条)、禁审囚科扰、台宪审囚(四条)、推官审囚、推官理狱(二条)、权摄推官、越分审囚、禁私和贼徒、禁转委公吏鞠狱、非理鞠囚(三条)、非法用刑(二条)、禁鞭背、红泥粉壁申禀、狱具(二条)、囚历、男女罪囚异处(二条)、提调刑狱(三条)、司狱掌禁、狱囚博戏饮酒、罪囚衣粮等(八条)、囚病医药(三条)、试验狱巫、病囚分数、囚病亲人入侍(以上卷34)。这两卷的大部分条格不见于元代其他相关法律文献,因而是研究元代刑狱制度的新史料,也是最原始的史料。鉴于此,笔者拟就《至正条格》所载元代“狱官”的珍贵史料进行初步探讨,以期有裨于元代刑狱制度之研究。
《至正条格》成书于至正五年(1345年),颁行于至正六年 (1346 年)。[1]卷四一《顺帝纪》两卷“狱官”条格涉及到整个元王朝的刑狱状况,内容包括刑法、诉讼法、行政法、民法等法学门类。尽管“狱官”条格和元代第2部法典《大元通制》所载条格一样,实际上均是处置具体问题的单行法规,但通过这两卷条格,我们仍然可以对元代的刑狱制度有大体的认识和了解。
这两卷条格主要是刑部的公文,此外也包括皇帝颁发的圣旨,中书省、御史台的呈文等。刑部直属中书省,负责全国的刑狱工作。案件的具体侦破由各级推官负责,审判则主要由当地政府行政官员负责。廉访司负责案件的复审和久拖不决等重大案件的审理,御史台则负责纠察监督,一般的死刑执行要报皇帝审批。这是元代刑狱审判的大致程序。
通过两卷条文,我们发现元朝政府非常重视对死刑的审判。“公事之重,莫重于刑狱;刑狱之重,莫重于人命”。[2]“恤刑”早在中统四年 (1263年),忽必烈就颁发圣旨说:“至如我或怒其间,有罪过的人根底,‘教杀者’,便道了呵。恁每至如迁延一两日再奏呵,亦不妨事。”[2]“重刑复奏”仁宗之前,元朝就出现“五府审囚官”(中书省、刑部、枢密院、大宗正府、御史台)共同审理重刑案件的现象。“先是有旨,定三年五府一出,分行各处虑囚”。[3]卷五《王员外东粤虑囚记》五府审囚官主要是为了加强对死刑案件的审讯,即“所以斩决罪囚者”。[4]卷一二《贞烈墓》至仁宗延祐年间,因为“京师四方辐辏,词讼繁多,有司系囚,时常盈狱”,所以五府官至少每季度就要进行重刑审讯。[2]“审理罪囚”延祐三年(1316年),仁宗颁发的圣旨再次强调了死刑审判的重要性:“罪过好生重,合陵迟处死的,为他罪过比敲的重上,审复无冤了,对众明白读了犯由,那般行来。”[2]“非法用刑”上述史料说明元代开始将死刑的审判权收归中央,这与宋朝截然不同。宋朝一般的死刑案件,地方政府有权裁决。因此与宋朝相比,元朝重视死刑审判无疑是一大进步,明清两朝就继承元朝的这一做法,这在中国法制史上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元朝统治者出于“化外羁縻”的考虑,[5]93“更用轻典,盖亦仁矣”。[1]卷一○二《刑法志》忽必烈统治初期,曾将前代的徒、流等刑折成杖,刺字也由前代的刺于面部改为刺于臂、项等处,这均是元代刑罚较轻的体现。“狱官”中的一些条格,也能反映出元代刑罚较轻的特点。如大德十年(1306年),刑部在审理济宁路张猪狗用棒打死冯五、广平路邢羊儿用头撞死刘大之类案件时,本拟为死罪,但中书省复审时认为“非故杀人,并从杖断一百七下,追征烧埋银两”。受此影响,其后各处官司审断罪囚时,往往将斗殴杀人之罪囚,“轻议比例断遣”。为此刑部还专门呈文提出不同意见,要求对斗殴杀人者处以重刑。[2]“斗殴杀人结案详断”再如天历元年(1328年)刑部文书提到的案例,也可以作为一个例证:“官吏人等,各事取受两主钱物,俱已告发。情犯相同,其赃若等,一主招承,征赃到官,一主未招,追问遇免,拟合照依已招赃数,依例定拟。”[2]“二罪俱发遇革”
两卷“狱官”条格,也能体现出元代司法中存在的蒙古因素和民族歧视现象。元朝处处体现出蒙古人的优越性,司法中保留有蒙古因素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前引“斗殴杀人结案详断”条格中,规定“今斗殴杀人者,杖一百七下”。笞、杖尾数为七,这是蒙古人的传统。蒙古民族乃游牧民族,自然很重视马牛等牲畜,条格中“私宰自己马牛,杖断一百”,无疑是蒙古人保护马牛等牲畜的措施的反映。“盗取他人头匹者,一征其九”,这也是蒙古人偷盗牲畜一赔九的传统,《元典章·刑部》就有“达达偷头口一个陪九个”一条条文。[6]1793
元朝实行四等人制,其中南人地位最为低下,这在“狱官”条格中亦有体现。大德八年(1304年),刑部呈文指出元代刑狱中存在“重刑枉直,推详事头”等腐败现象:“若被殴初不讼官,直待身死,然后方告。或因他疾而死,或事涉暧昧,不愿进词,尸已烧(理) 〔埋〕,其弓手、里正人等,意在挟私,计嘱巡慰、县吏妄投词状。又有妄以惊死老幼为辞,及自伤残害,故行谋赖。胥吏兜搅,受理官亦贪求,从而检验勾拿人众,刻取厌足,改变是非。或以尸首发变青赤颜色,妄作生前打损伤痕,欺诈钱物,倘若不满所求,从而锻炼成狱。及有放火纵迹不明,或被强盗之类,吏卒教令事主,妄指平人,因□□家,致有拷讯而死、捏合文案者,此弊江南尤甚”。[2]“恤刑”上述刑事案件审讯过程中存在的种种不法现象,在江南地区体现得最为明显,其实质则是南人地位最为底下的生动写照。
元朝强调“以忠质治天下,宽厚得民心,简易定国政”。[7]卷七《至正条格序》因此其刑狱制度中也较多地体现出人道主义精神,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禁止酷刑。至元九年(1272年),御史台呈文中提到,陕西等路在鞠问罪囚时,“除拷讯外,更将犯人枷立大披挂,上至头髺,下至两膝,绳索拴缚,四下用砖吊坠,沈苦难任”。不仅陕西一路如此,“其余路分亦有此事”。因这些酷刑属于“法外凌〔虐〕”,因此御史台要求“拟合禁约”。[2]“非理鞠囚”大德八年 (1304年),刑部呈文中显示禁断的酷刑有“鞭背游街、精跪砖石、王侍郎绳索”以及“非法狱具脑箍、夹踝、搅札、麻槌、以棒拗膝之类”。同时要求禁止可以致死囚犯的“摄牢棒”,即“新囚入狱,每过一门,辄用粗棍于囚腰背痛捶三下”。[2]“恤刑”延祐三年 (1316年),仁宗颁发圣旨要求对待犯有死罪的狱囚,不许“将他的肉剐割将去呵”,亦不许将犯人“头发鬓揪提着,脚指头上踏着,软肋里搠打着,精屈膝铁锁上、石头砖上、田地上一两日跪着问”,对于“犯着的官吏根底,要重罪过者”。[2]“非法用刑”
其次,体恤罪囚。元朝往往利用红泥粉壁来惩戒触犯刑律等不法之人,同时也起到警示他人的作用,但这也为司法腐败提供了方便之门。至治二年(947年),象州知州周德贤即“持权弄法,挟私任情,民有小过,辄生罗织,锻炼成狱,擅立红壁,以仇其民”。对于这种挟私报复的做法,刑部认为“甚负朝廷子育元元之意”,要求“今后果有例应红泥粉壁之人,开具本犯罪名,在外路分申禀行省,腹里去处申达省部,可否须侯许准明文,然后置立,仍从监察御史、廉访司纠察”。[2]“红泥粉壁申禀”对老幼残疾等囚犯,元朝政府允许他们通过缴纳罚金抵消刑罚。“残疾病症,非止一端,若妨决科,合准赎罚”,“诸犯罪人若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笃废疾不任杖责,理宜哀矜。每笞杖一下,拟罚赎中统钞一贯”。[2]“老幼笃废残疾”
元朝规定狱囚的衣粮、烧柴等一般由其家属承担,但如果狱囚没有亲属,或亲属在外地,或亲属贫穷不能支付,则由政府承担。元朝政府支付狱囚的费用,中统时期规定于鼠耗钱内支付,至元年间改于年销钱内支付,到文宗至顺时期又改于“有司官仓内依例支给,年终通行照算”。[2]“罪囚衣粮等”对于病囚,令相关医务人员进行诊治,依时支给药饵,以确保其生命安全。如果病囚死亡,则要“开具所犯罪名、收禁月日、感患病证、用过药饵、加减分数、死亡日时,初复检验致死缘由,置簿明白开附,每月牒报廉访司照刷,在都者具申御史台一体施行。中间但有非理死损,严行究治,仍于岁终通类开坐,咨申省部”。[2]“囚病医药”“诸狱囚有病,主司验实,给医药,病重者去枷锁杻,听家人入侍。职事散官五品以上,听二人入侍。犯恶逆以上及强盗至死,奴婢杀主者,给医药而已”。[1]卷一○五《刑法志》根据“囚病亲人入侍”条格的记载,元朝关于允许病囚亲人入侍的规定,至少在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以前就已颁行。
对于女囚,中统四年(1263年),忽必烈颁发圣旨即要求“妇人仍与男子别所”。[6]1485至元十六年(1279年),刑部文书中指出罪囚收入狱中,男女无别,因此明确要求“男女异处”,并要“司狱司官常切照略”。[2]“男女罪囚异处”但男女同牢的现象直到至元末仍然存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宣政院文书中就指出“僧尼混杂同禁”,要求将女尼异处安置,“毋得混杂”。[6]1493
再次,建立囚历,以保证狱囚的相应权利,预防刑狱腐败。大德七年(1303年),刑部上报中书省的呈文中,要求“今后随路司狱司并府、州、司、县委首领官,各置禁历一扇,若有收禁罪囚,随即附写所犯情由、收禁月日,每五日一次结附各起花名,正官署押,佐贰官钦依已奉圣旨事意,轮番提调。……各道廉访司官所至之处,先行提刑体察,仍将囚历照勘。敢有违犯及外监漏报罪囚起数,就便严行惩戒”。[2]“囚历”
两卷“狱官”条格也能反映出元朝刑狱审判过程中相关机构职责不明,出现审判混乱、越职审理案件、差占专职官员等现象。元朝中央政府负责审理刑狱的机构有大宗正府(扎鲁忽赤)和刑部。通常大宗正府负责蒙古人的刑狱审理,刑部负责汉人、南人的刑狱审理,色目人则视情况分归大宗正府或刑部。但二者因民族、地域等因素,一直存在职权范围的矛盾。如皇庆元年(1312年)中书省的奏疏中就指出:“‘奸盗诈伪,休教也可扎鲁忽赤提调,刑部官人每提调者。’圣旨有来。刑部随车架回去了呵,不教留守司官提调呵,不中也者。刑名是大勾当有,教一个色目官人、一个汉儿官人提调呵,怎生?”[2]“提调刑狱”不仅如此,其他机构或官员也存在非法审理刑狱的现象,如至大元年(1308年),徽政院佥院完颜泽借交割嘉兴、隆兴、瑞州、松江等路钱粮之机,审理松江府23起97名在押罪囚。为此,御史台认为完颜泽属于越职行为,刑部认为审理罪囚“已有审断定例”,完颜泽不能“擅自审决”,并且规定“今后诸衙门出使人员,合行禁约”。[2]“越分审囚”
还有京府州县等鞠勘罪囚的官员,将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刑狱案件,转手委托给其他官员负责办理,导致“私下拷问”,造成屈打成招的冤狱。为此,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 忽必烈颁发圣旨,对于这类“转委”案件的官员,“并听提刑按察司(即后来的廉访司——引者) 纠治”。[2]“禁转委公吏鞠狱”而推官、司狱等专管刑狱的官员,也存在被差占的现象。皇庆元年(1312年)刑部呈文中,要求推官“不管余事,专一详谳罪囚。……不许各衙门非理呼唤,余事妨夺。”[2]“推官理狱”至元十五年 (1278年),山东道提刑按察司照得:“随路司狱,专掌囚禁,无致差占。”[2]“ 司狱掌禁”
两卷“狱官”条格,反映出元代司法腐败现象非常严重。仅举如下几例: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一年时间里,江西行省管下路分,“死讫轻重罪囚一千一十一名,其余道分,谅亦如是”。[2]“恤刑”同年,御史台监察御史呈:“审断诸衙门见禁罪囚官吏,每到须有宴会,或以酒食,公厅饮用。上项所费等物,未免科敛,理合禁止。”[2]“禁审囚科扰”刑狱审判的官员,竟然将案件开审当做公款吃喝的良机。大德八年(1304年),刑部指出当时刑狱制度中存在许多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整治措施:重刑枉直,推详事头;推问惨酷,不得真情;追会迟延,久不结案;检验尸伤,亲速详定;狱贵初情,亲任问责;审复依期,囚无冤滞;囚医失治,责任所司;狱事不修,司狱之责;狱卒久役,奸弊多端;枷锁刑禁,毋肆威权。[2]“ 恤刑”
元朝司法腐败如此严重,究其原因,大概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元朝立法本身存在的弊端。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后,蒙古人主要使用的是带有鲜明游牧民族特色的“札撒”。但随着征服地区的不断扩大,尤其是随着中原汉地的陆续占领,“札撒”的局限性日渐显露,因此蒙古统治者不得不沿用金朝的《泰和律》。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为了新王朝的建立,下令禁行《泰和律》。其后到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元朝政府才制定出一部新的法典《至元新格》,但《至元新格》充其量是一部涉及一些刑法、民法和诉讼法原则的行政法规,还不是严格意义的法典。因此,“东平布衣”赵天麟就认为“国家未有律令,有司恣行决罚”。[8]卷六六《太平金镜策》仁宗时期,元朝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编纂新的法律,至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 最终颁布,是为《大元通制》,即所谓《通制条格》。但《大元通制》颁行不到10年,元朝又编纂《经世大典》,其中的《宪典》就是在《大元通制》的基础上修纂而成的。至正六年(1346年),蒙古统治者又颁布了新的法典《至正条格》。《至正条格》颁行不久,至正十一年(1351年),陈思谦等又“修定国律”。[1]卷一八四《陈思谦传》其后五六年,中书右丞乌古孙良桢等又“重定律书”。[1]卷一八七《乌古孙良桢传》由此可见,元朝修定国家法律的工作非常频繁,这反映出元朝法律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其原因是《大元通制》《至正条格》等元朝法典,和其他朝代法律一个明显的不同,是针对具体问题或案例进行编纂,法典往往是具体案件的汇编,因而缺乏应用的普遍性。这正如苏天爵所说:“夫人情有万状,岂一例之能拘?”[9]435因此元朝官员在使用这些法典时弹性很大,自然枉法的空间也就很大,他们往往根据相应的条格或断例各取所需,判决中难免会出现各种不法现象。
第二,元代地方审判机构是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下开展审判工作的,州、县两级的司法官员本身就是由当地的行政官员兼任的,而路、府的审判机构实际上也不是独立的,其审判结果必须经地方政府官员认可后才能生效,因此地方政府官员权力过大,又往往失于监督,司法腐败自然就不可避免。
第三,选任官员,不得其人。大德八年(1304年)刑部呈文中指出:“近年有司官吏不得其人,往往以人命公事视同泛常……因而受贿徇情,改变损伤,出入情节,作弊多端。……自南北混一以来,所在抚字之官,类多杂进之流……以私为念,掊取是图者在在皆是。至如推究狱情,漠然不知,谓如一件人命公事,司县官吏卖弄于检尸之始,迁延于推问之间,所属州府,又不即取发归问,或听信人吏,非理踈驳……及有解到路府,引于公厅之下,众官泛然一问,不待囚人辞说,已即换枷入狱。”[2]“恤刑”这种情况,元代文献多有记载,《元典章》即指出司、县官吏“推问之术,少得其要。况杂进之人,十常八九,不能洞察事情,专尚捶楚,期于狱成而已”。[6]1496就连中央派出的五府官,也是“既不得人,徒增烦扰”。[9]451
第四,元朝重视死刑复核,这本是元朝司法的一大进步,但却矫枉过正,走向了另一极端,造成案件积压、久拖不决、徇情枉法的现象非常普遍。大德八年(1304年),刑部呈文中说:“近年完备结案者,百无一二”。[2]“恤刑”皇庆二年 (1313年),刑部又指出:“近年以来,有司闇于识断,狃于姑息,各处重刑,率多淹滞。廉访司既失究治,复多推延。凡遇牒审,或驳小节不完,或托它故苟避,上下相习,恬不为意……禁系累年,尚不结案……若今之弊,苟不申严,深害政治。”[2]“重囚结案”
五府审囚官主要是为了复审死刑案件而设,但因为要报请皇帝批准,所以他们往往互相推诿,“托故不聚,久淹囚人,明正其罪者百无一二,死于囹圄者十有八九。致使凶顽恶少之徒不知警畏,狱囚淹延”。针对这种现象,中书省曾奏请仁宗,要求“每季委的五府官,将应有的见禁罪囚,不分季分通教审理,合断的都教断了,有冤的辩明,迟了的究问,俺根底合禀的教禀说,发落重囚每,催督着有司追勘完备,疾早结案……五府官似前推称事故,不聚会的每根底,俺斟酌要罪过”。[2]“审理罪囚”但收效甚微。
[1](明) 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至正条格[M].韩国城南:影印元刊本,2007.
[3](元) 刘岳申.申斋集[M].四库全书本.
[4](明)陶宗仪.南村辍耕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5]黄时鉴.元代法律资料辑存[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6]元典章[M].影印元刊本.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
[7](清)欧阳玄.圭斋文集[M].四部丛刊初编本.
[8](明) 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M].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9](元)苏天爵著;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滋溪文稿[M].北京:中华书局,1997.
——以《刑部驳案汇抄》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