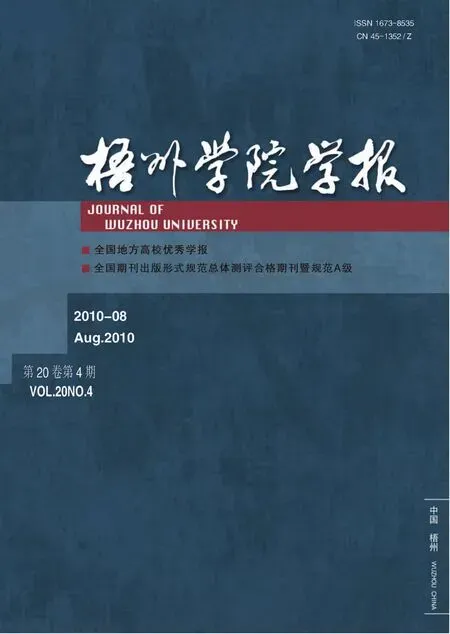身体视阈下文坛新桂军小说“人”的话语构建
秦延良
(梧州学院 中文系,广西 梧州 543002)
身体视阈下文坛新桂军小说“人”的话语构建
秦延良
(梧州学院 中文系,广西 梧州 543002)
在边缘崛起的过程中,“文坛新桂军”将思想触角和现实体验延伸向了喧嚣而复杂的身体,通过身体的异动和精神的嬗变,揭示出在凡俗社会中人的生存本相,并从人的发现与关怀这个视角去阐述社会欲望系统,构建起新的 “人”的话语,体现了这些年轻作家对人生的严肃思考和人文关怀。
身体视阈;文坛新桂军;人的话语
谈起广西当代文学,人们自然会想到那一个充满朝气、边缘崛起的广西青年创作群体——文坛新桂军,经过十年磨一剑的默默积累,一批来自壮乡的作家带着八桂大地的气息,于世纪之交迈着稳健的步伐从偏远地带走到了文坛中心,成为了文学界极为活跃的创作生态群落。“文坛新桂军”的异军突起令人瞩目,文学评论家陈晓明就曾断言:“广西汇集了一批极有才华的作家,迟早要夺下中国文坛的半壁江山”[1]。在小说创作方面,人们看到一批八桂儿女以其敏锐的时代意识、开阔的文学视野和大胆的叙事指向进行着具有先锋性和穿越性的探索。而在他们对现实生活所作出的本质性表达中,身体这一景观被浓墨重彩地凸现了出来,作家们将思想触角和生存体验延伸向了喧嚣而复杂的身体,在笔下刻画了一个个蕴藉丰富的身体意象,建构起新的 “人”的话语,并借此开辟了广阔的文学审美空间。面对着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叙事话语的嬗变,“文坛新桂军”在小说的身体叙事中显示出了与他们在地域上所处的边缘位置所迥异的先锋意识。他们灵敏地抓住身体这个核心符码,将身体与精神、物质、苦难等元素联结在一起,从中探寻多元的身体体验和真实的生活体验,并最终从人的发现与关怀这个视角去阐述社会欲望系统,借助身体的叙事形态,“把灵魂还给肉身,把肉身还给灵魂。灵魂不再冷冰冰,身体也不再赤裸裸”[2],并通过身体的异动和精神的嬗变,揭示出在凡俗社会中人的种种生存本相,体现了这些年轻作家对人生的严肃思考和人文关怀。他们对身体的精心营构和书写既契合了90年代文学中 “人”的话语转型,也为人们考察90年代以来身体的变迁以及“人”的生存状况和精神境遇提供了一个极佳的着眼点。
一、以身体凝眸灵魂的抗争与救赎
面对着纷繁复杂的现实,“文坛新桂军”努力地以身体书写传达出个体对世界的悖离状态,并从中认真地思考了身体与 “人”的主体意识建构的关系,他们重新赋予身体以心灵的皈依、灵性的维度,使笔下的人物经由身体进行艰难的自我救赎,最终完成主体性确认,实现 “人”对自我的发现,从而给作品增添了温暖的色彩。
林白的小说 《一个人的战争》通过身体的叙写实现了 “人”的延伸和转折,文中塑造了一个专注于自己身体、敏感而具有觉醒意识的女体意象——多米,林白围绕着女性身体的在场,把女主人公推到了寻找自我的风口浪尖上,以这个从男性规范权力中挣脱出来的女性呈现出生命个体由逃离——重建的觉醒、对抗姿态,从而确立一个现代人的主体意义。作品写到了一个女性的同性体验和成长故事,描绘了她对自己身体的迷恋以及和男人的性爱纠葛,从身体出发探索 “人”的精神出路。女主人公多米先是由于渴望得到男性而迷失了自我,把富有生命意识的身体降格为物,堕入到男性价值体系之中,使自己的身体成为了爱的祭奠品。后来,随着在这个价值系统中证明自我的尝试的失败,她终于从对男性的幻想中逃离出来,回归到自己的身体,由自己掌握自己的身体,并以这场身体的战争为突破口完成了自我的精神救赎。在这里,林白用她特有的生命体验和身体叙事言说着个体被压抑已久的愿望,大胆地表现被压抑者自我救赎的渴望和勇气,以此来重新构建人物的内心世界。多米的自己嫁给自己的决定明确地表达了一种自我认同的意愿和努力,在这场由性发起的对精神的挑战中,身体成了确认自我的阵地,多米通过这场一个人的战争最终实现了自我主体地位的建构,她的敏感的身体作为显在的意象在文中不断着色,最终变成了女性主体意识的承载体。对自我的发现从身体上得到实现,这标志着作家已经将目光投射在人的自然存在和文化存在上,并以一种敏锐的意识和悲悯的情怀努力挽救在严酷现实中下沉的身体,从而给这个异化的物质时代涂抹上一层理想的色调。
鬼子在其代表作 《被雨淋湿的河》中以形象的身体语言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打工仔晓雷,他以一个社会边缘人的身分,带着自己的理想重复着农民工的平凡生活道路:打工、赚钱、糊口。鬼子对这个人物形象的书写零碎而生活化,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描写,但却加入了身体的元素,以此讲述晓雷对无序而喧嚣的物质世界的种种反抗。在残酷的现实生存中,这个弱小的个体遭遇了许多黑暗势力的压迫,当他发现现实与理想的严重悖离时,晓雷却做出了非常之举,他以一种堂吉诃德挑战风车的姿态和身体语言去表达自己的愤怒和对苦难的抗争,拿起酒瓶杀死了荒淫无耻的老板,随后又以无比的尊严挺直自己的身体,坚决不给 “外国老板”下跪,成为 “又一个不跪的打工仔”。虽然晓雷的这些 “螳臂挡车”式的行为由于其自身力量的单薄最终只能走向悲剧性的失败,甚至使他遭受灭顶之灾,但在鬼子的叙述视角中,“死”并不可怕,“生”才是最艰难的,他正是要以晓雷的身体行为和他的死表现出 “人”对 “生”的积极承担的勇气和无力承担的宿命。在晓雷坎坷的受难历程中,人们能深深感受到一种生命顽强的韧性。
在这些无助的人物身上,新桂军作家投注了一种现世关怀和悲悯情怀,他们从身体表达中表现了渺小个体坚韧的意识和超常的生命力,从而使这些 “人”因为与世俗的斗争而呈现出一种崇高的精神力量,并进而具有了悲剧性的审美力量。借助这些身体叙事,“文坛新桂军”完成了对普通生命的抗争状态的冷静陈述和深度展现,从中表现出对此岸世界的焦虑以及对彼岸世界的关怀。
二、以身体聚焦人生的迷茫和皱褶
在现代社会传统意识形态日益式微的背景下,新桂军作家将目光从抽象的 “人”聚焦到具象的“身体”,在小说中描写了一具具被生活压抑而充满焦虑的身体,由身体传达 “人”的内心体验,标注出身体的隐秘体验对于存在状态的揭示功能,通过建构私人化的存在语境和身体寓意来诠释人在高度异化的现实中自我指认的迷茫和痛苦。
作为 “广西三剑客”之一的东西就是一个书写身体的高手,他的小说往往将笔锋着落在 “身体”上,以身体意象揭示生活的痛苦本质和生命的迷失状态。在 《不要问我》这篇小说中,东西便塑造了一个焦虑而绝望的身份失落者,一具充满荒诞色彩的堕落身体:年轻有为的大学教师卫国成为了身份和身体冲突、分离的暗喻符号。他在辞职南下的路途中意外丢失了装着所有证件的皮箱,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人,而后,身份和身体构成了一个滑稽的悖论:身份证明丢失了,尽管身体行为、自身能力如此真实,却无法获得社会的确认,无法证明自我,只能寄希望于找回皮箱。28年来,卫国一直在压抑着身体的欲望而进行着身份的建构,一旦获得了标志着成功的社会身份,他的身体也随之放纵出轨;而当能证明他身份的皮箱不复存在时,卫国顿时丢失了对于身体的自信,他的身体也变得孤立、焦虑和羸弱,并最终走向自我的迷失。处于迷茫中的卫国反复地背诵这几句话:我叫卫国,男,现年28岁,未婚,副教授。他不断地提醒自己,可别把自己给忘记了。而恰恰正是由于他对身份符号的过度关注,偏偏导致了生命本体的失落。随着身份的建构与解构,卫国的身体也一直在起伏跌宕,始终无法找到停泊的港湾。在这个故事里,“东西是在强调身体的存在。现实主义文学以理性为最高原则,理性关注的是人的社会现实存在,即身份。东西转移了他的关注对象,他将人们从对人的身份关注超拔出来,去掉人的身份遮蔽,呈现人的身体存在。人的身体被理性压抑太久,东西不惜加入梦幻逻辑,夸大人的身体感觉,以加强读者对人的身体存在的意识”[3]。在对卫国焦虑的身体的书写中,东西使人们看到了身体的迷失状态,现实的荒谬处境使身体难以回归到人的正常价值轨道之上,最终,生命个体的精神变成了稀薄的空气,卫国丢失了对于身体的自信,从而也失去了寻找自我的基本依据和心灵的归宿。
凡一平的长篇小说 《变性人手记》刻画了一个变性人的变形人生。在这个故事里,变性成了一个极具身体闹剧性质的人生取景框,人们从中不仅可以清晰地审视外在化的欲望场景,还能看到人的道德观念的离场以及人性的颓败。凡一平给人们展示了一个认同男权社会的漂亮女演员夏妆在主动做了变性手术后的种种命运变化。整篇小说行文虽貌似荒诞,但所构建起来的 “人”的话语却深刻而严肃。变性人夏妆对身体性别的重新选择并不是由于自身生理的驱使,而是源于对男权的极度渴求,她本身是一个命运多舛、饱受屈辱的女性,但她选择的反抗方式——变性恰恰是默认了女性的被动地位,为了实现对生命的所谓自我完成和绝对主宰,她却首先举行了身体的“投降”仪式。 “个人为了获取他已丧失的力量,不惜放弃自我的独立性而使自己与外在的他人或他物凑合在一起的倾向。换句话说,也就是寻求新的第二枷锁来代替业已摆脱掉的原始枷锁的倾向。”[4]实际上,夏妆正是在完成身体的变形中同时走向了人格上的自我解构。她认为变成男性就能获得强势和主导话语权,殊不知正是从变性的那一刻起,她人性中的劣质和弱势就彰显无遗。变性并没有让她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超越和强大,反而使人们看到了她的个性精神的溃退,她变的不光是 “性”,还有自己的人性。因此,在凡一平的身体书写的视阈中,准确地呈现了人性的迷失以及作者颇为鲜明的批判立场。
在90年代写 “人”的文学语境发生嬗变的背景下,新桂军作家以充满焦虑感的身体书写准确呈现出生命个体的孤独意识和迷失状态,他们小说中的这些人物依托着身体痛苦地寻觅着人生的某个出口,但是,身体的迷失却拉扯着精神主体四处飘摇,不知归路,于是,他们自身的实存价值最终指向了虚无。
三、以身体审视人性的异化和扭曲
在 “文坛新桂军”的身体呈现中,人们可以发现作者把物质身体的活动与心灵意志的发掘并举的叙事策略。作家们冷静地解构着其中的种种生命本质,并在还原身体的本真状态过程中演绎出其中的心灵悲剧走向。他们把这些凡夫俗子置于身体异动的现实场景中去表现他们在物质世界的异化和扭曲状态,对此进行着一次次严肃而彻底的审视,从中传达出对现实和人性异化的深刻思考。
在中篇小说 《睡觉》中,东西用一种人们最平常的生理现象,展示了另外一个焦虑的身体意象—— 一个失眠症患者,从中揭示出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小说中的 “我”表面上是一个被睡觉拒绝的人,其实是一个被正常生活所拒绝的人,于是,我的身体与行为也变得焦灼和扭曲,“我”成为了一个变态的窥视者。为了获得另一种生活,“我”在晚上偷偷地溜到别人的窗户下偷窥,并由此获得了身体的暂时快感。在偷窥当中,“我”发现了女朋友的背叛,朋友之间的互相欺骗以及社会上的尔虞我诈等众多秘密,这些秘密随之又成为一种刺激,撩动着我的身体,使 “我”更加难以入眠,担心不能窥视到别人的下一步行动,害怕别人趁机骗 “我”。如此不断反复,失眠— 窥视— 失眠成为了一个恶性循环,“我”想睡觉但又想窥视他人行动,“我”除了窥视再也没有任何能够与正常生活相联系的方式,身体的变态行为导致了 “我”走向了自我的沦丧。东西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时代生活本质蜕变的根本问题,通过身体的异动触碰到了自我与身体关联的命题,从中审视人的精神之维,从而在形而下的身体当中发现和书写了形而上之 “道”。
同样,在 《肚子的记忆》中,东西以极为平常的 “肚子”作为意象指代了异常的精神空虚与恐惧,一个人脑子越来越糊涂,但肚子却时时刻刻惦记着吃,最后查明病因,竟然是来自遗传的“饥饿记忆”基因。故事的焦点由肚子巧妙地落在了饥饿与吃上,因为吃,人性异化到荒诞不经的地步。在成为饥饿的忠实奴仆后,人也因此而变得面目模糊。通过这些身体的异化行为,东西使读者看到了在异化社会中的人的异化状态,从中深刻地揭示出现代人的精神困境。
确实,在新桂军作家的小说的身体叙事中,身体已不再是简单的肉身概念,而是变成了一种复杂的物质和精神的混合物,构建起了作家对于身体/意义、身体/价值、身体/自我等多维度的关于“人”的哲学思考。在身体视阈下,人们看到的其实已不仅仅是身体的显在姿态,而是社会的病态和生活的痛苦本质。拨开身体的表层,其深层结构袒露出来的是作家的悲悯之情,他们共同营构了一个以身体承受与心灵关注为中心的 “人”的话语世界,并希望从中找到一条精神复归和重建之路,从而使小说具有了震撼人心的审美冲击力。
[1]陈晓明.直接现实主义:广西三剑客的崛起[J].南方文坛,1998(2).
[2]张红翠.身体转向与肉身化叙事[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3]黄伟林.身体幻想的后现代书写——论东西的小说[J].山花,2007(10).
[4]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
I207.42
A
1673-8535(2010)04-0065-04
2010-06-02
广西梧州学院科研项目(2009C035)阶段性研究成果
秦延良(1973-),男,广西梧州人,梧州学院中文系教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钟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