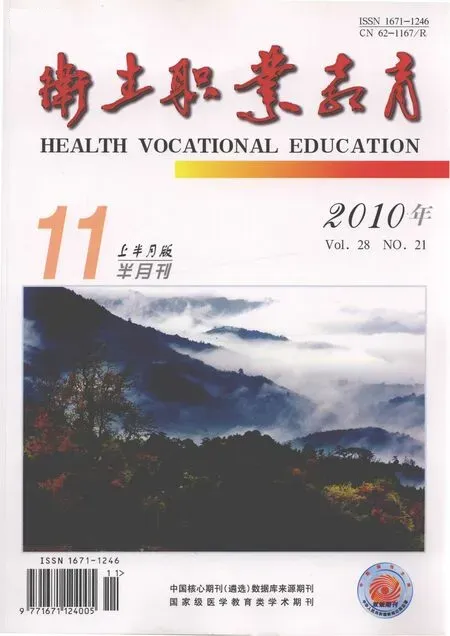现代叙事视角下的施蛰存历史小说《石秀》
安芳宜
(兰州交通大学文学与国际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现代叙事视角下的施蛰存历史小说《石秀》
安芳宜
(兰州交通大学文学与国际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水浒传》中的石秀是众所周知的“拼命三郎”,但现代作家施蛰存运用现代叙述视角与话语,采用心理分析手法,将石秀塑造为迥异于读者心目中的世俗化英雄,还历史一个“真实”的石秀。
现代叙述视角;心理分析手法;石秀
施蛰存与穆时英、刘呐鸥被称为“新感觉派”的3员主将,但施蛰存对自己被归入新感觉派一直耿耿于怀:“因了(楼)适夷先生在《文艺新闻》上发表的夸张的批评,直到今天,使我还顶着一个新感觉主义者的头衔。我想,这是不十分正确的。我虽然不明白西洋或日本的新感觉主义是什么样的东西,但我知道我的小说不过应用了一些Freudism(弗洛伊德学说)的心理小说而已。[1]”施蛰存深受弗洛伊德等人的影响,其小说的突出特点是展示性心理、潜意识、幻觉和变态等心理,可谓是我国现当代文学中第一个将人物深层次的心理分析作为中心进行描写的作家。施蛰存的小说可分为历史心理小说和现实心理小说,其历史心理小说的成就更为显著,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开辟了创作的新蹊径,这条新蹊径不仅对于他个人创作有创新意义,也为我国现代历史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经验。他用现代观念回顾历史,用现代笔法讲述历史。
最能代表施蛰存接受西方学说的历史心理小说就是《石秀》,他运用弗洛伊德学说,采用心理分析手法还原了一个较为“真实”的世俗化英雄。无论是情节设计还是心理描写的魔幻处理都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历史小说,呈现出独特之现代色彩,成为我国现代历史小说中独异之文本。此篇小说初收入1932年版的历史小说集《将军底头》中,也是施蛰存创作转向现代主义的代表作品。
1 采用现代叙事话语重构历史故事
《水浒传》中有关石秀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无论后来的作者如何改变情节,读者都会受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式所左右。因此,施蛰存的创作并非重述历史故事,也并非看重作品情节,而是从现代叙事话语中为读者描绘一个“新”石秀。正因如此,《石秀》这篇改写的历史小说也具有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石秀》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视角,作家将叙述的重点聚焦于人物内心的体验与变化上,故事情节随人物内心冲突的转化而发展。从中可见,作家运用了现代性的文学技巧,表现和挖掘人物的各种心理:幻觉、冲动、情感等,并以此作为小说的中心,建构小说结构。因此,《石秀》无论是在故事层面上还是话语层面上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在话语层面上,小说《石秀》对人物心理的描述分2类,一类是直接式的心理表达,以突出人物的性格并丰富小说故事情节;另一类是间接式的心理表达。在表达梦、幻觉、冲动、情感等“非语言”心理活动时,作家常常采用“间接思想”这一形式。这种被称为“内在分析”或“心理叙述”手法使作家运用自己的语言把人物“非语言”的幻境和感觉表达出来[2]。这种间接式的人物心理表达正是施蛰存作品的独特之处。
在表现手法上,这类间接式的人物内心话语表达有3类:第一类是通过作家之口进行人物心理概述,叙述者通过抽象化的用词、理性的语调、复杂的句式,发出完全不同于人物本身的声音,使人物思想得到形而上的整体化,从而实现人物内心情感的深度挖掘。如“在石秀心里,爱欲的苦闷和烈焰所炽成的魔网,全部毁灭了。这样思索着的石秀,对于潘巧云的隐秘的情热,又急突地在他心中蠢动起来了。”这些话语本不可能从一介武夫石秀的思想中呈现,显然带有作家的主观视角。
第二类是人物内心话语的意象化表述。叙述者为了给读者呈现出主人公的内心冲突,建构了各种具体的意象来表达人物的情感和冲动。如“他所追想得到的潘巧云,只是一个使他眼睛觉得刺痛的活的美体的本身,是这样地充满着热力和欲望的一个可亲的精灵,是明知其含着剧毒而又自甘于被它的色泽和醇郁所魅惑的一盏鸩酒。”作家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潘巧云是“充满着热力和欲望的一个可亲的精灵”和“含着剧毒而又自甘于被它的色泽和醇郁所魅惑的一盏鸩酒”的形象,这种颇具张力的意象的构造,形象地表述了石秀内心对潘巧云极为隐秘、模糊的情感体验。
第三类是作家对人物幻觉画面的呈现。《石秀》通篇可见作家将人物非语言的幻觉以画面的形式展现的叙述。“石秀满心高兴,眼前直是浮荡着潘巧云和迎儿的赤露着的躯体,在荒凉的翠屏山上,横倒在丛草中。黑的头发,白的肌肉,鲜红的血,这样强烈的色彩的对照,看见了之后,精神上和肉体上,将感受到怎样的轻快啊!”作家用充斥着强烈感官刺激的语言描述了石秀对女性身体的变态幻想,这种作家和人物声音并存的形式饱含了超现实主义的气息。
2 从心理分析的层面展示更为“真实”的石秀
《水浒传》中的石秀,是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拼命三郎”,尤其是怒杀淫僧裴如海一节,更令读者拍手称快。而施蛰存的小说《石秀》却别出心裁,将其塑造为一个凡夫俗子,呈现有与常人一样的潜意识、性压抑与报复心理的“真实”石秀。作家在与传统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若即若离的关系中,大量运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手法推动情节发展,并以此刻画人物的内心活动,让读者看到以往未曾见过的英雄人物的另一面。弗洛伊德认为,性爱对于人的一生,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起着巨大的作用。在《石秀》中,作家以观察人物性意识流程的方式展开故事情节,精心安排了5个层次的心理描写推动人物性格的发展。
第一层是石秀夜宿。记叙了石秀初识潘巧云的心理萌动:“躺在床上留心看着这个好像很神秘的晃动着的火焰,石秀心里便不禁给勾起一大片不尽的思潮了。”潜意识的波动,仿佛是虚幻记忆中的一个美妇人在扰乱着他的心绪,加上对义兄杨雄不义的自我谴责心理,使石秀不能入睡。第二层是巧云调情。石秀因觉察到潘巧云对他的好感并对他调情,更掀起了内心波澜,作家在此处深入地刻画了石秀因潘巧云的勾引而产生的矛盾心理:“在第一刹那间,未尝不使石秀神魂震荡,目定口呆,而继续着的对于这个不曾被热情遮蔽了理智的石秀,却反而是一种沉哀的失望。”第三层石秀密恋。这一层中作家更加深入地刻画了石秀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因为怀疑潘巧云出身勾栏而感到不甘心,却又因为潘巧云对自己多次表示好感,产生了一种得到她并没有什么过错的自私的奢望。另一方面,为自己以坚决的态度拒绝潘巧云而后悔,不知不觉走进潘巧云的房中,但又突然瞥见杨雄的头巾而终于使道德与理智占了上风,仓惶逃离。第四层是淫虐意识的觉醒。当石秀察觉潘巧云与报恩寺的和尚裴如海的奸情后,一切因爱欲带来的苦闷与烈焰都不见了。石秀心乱如麻,有对潘巧云的轻蔑,也有对裴如海的痛恨,还有对义兄杨雄的怜悯,最为痛心的是对自己受辱的懊丧。种种矛盾心理的交织构成了人物内心激烈的冲突,使石秀走向了精神崩溃的边缘。而潘巧云手指划破流出的鲜血却成为石秀排除内心恐慌的导火索,一个施虐狂的潜意识被鲜血唤醒了。第五层是残暴后的满足。石秀在种种矛盾心理的煎熬下,最终完成了一个施虐狂的使命。当他亲自剥光潘巧云的衣服,杨雄将她剖腹分尸,眼前呈现出美艳的肉体和淋漓的鲜血时,石秀体验到了一种奇异的快感。石秀在观看杨雄对潘巧云的肢解时,“觉得一阵子满足的愉快了”,看到饥饿的乌鸦啄食潘巧云的心脏时,他不禁想:“这一定是很美味的呢”。这种残暴,对石秀来说“真是个奇观啊!”
这5个层次,逐层深入,以极为细密的观察和流畅生动的笔调,完成对石秀心理发展的描写,展示了主人公不断冲突、旋转向前的感情历程。在这个过程中,作家用联想、独白、幻觉、心理剖析等心理分析手法,着力展示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深入人物潜意识,透过其表面英雄形象,而彰显其内心阴暗面,这不仅是施蛰存小说常用的创作手法,也是其历史心理小说的突出特征:它们不仅充分表现了人的世俗性和世俗人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与那些宏大的神圣的价值意义之间的冲突和分裂,而且把前者看作是“真相”,并且以前者的思维、目的和逻辑组织构成小说中的生活现实和人物形象。这类小说把历史日常化,把神圣世俗化,通过“故事新编”,还历史以另一种“真实”[3]。
施蛰存以其精湛的笔调,将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现代化合流并用,在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上,借用心理分析,透过主观感受和精神活动描写,向读者展现一个不同于常态非概念化的历史人物,从而完成了对英雄人物的世俗化、非英雄化的重构。他的历史心理小说对当代正在进行的历史反思起着举足轻重的重要意义。无可置疑地说,施蛰存的创作是我国30年代文学中的亮点。
[1]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经历[M].上海:上海开明书店,1937.
[2]申丹.小说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雷达,赵学勇,程金城.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
G420
B
1671-1246(2010)21-006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