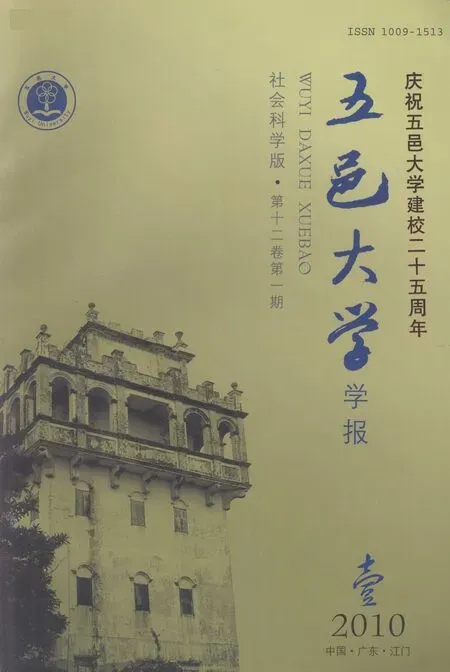涉“性”话语“包装”的文学艺术
——市场化时代文学新的传播手段
陈尚荣
(南京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4)
涉“性”话语“包装”的文学艺术
——市场化时代文学新的传播手段
陈尚荣
(南京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4)
进入20世纪90年代,“包装”被堂而皇之地引入文艺出版领域。无论是“直接包装”还是“间接包装”,各种或明或暗的“性”话语的巧妙缝织成为其主要手段之一。包装本无可指责,但出版商应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在俗与雅、商业化与艺术化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点。
“性”话语;包装;文学艺术;市场化;传播
“包装”最初是用于产品的外表包裹、装潢美化的术语,后来逐渐延伸到人的形象修饰,如影星、歌星的包装。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成熟,文学艺术的商品属性日显突出,文学期刊、图书等文艺作品也开始使用“包装”艺术。文艺作品为什么需要“包装”呢?这显然与文艺作品在上世纪90年代后的生存境遇有关。走向市场的文学期刊、文学图书、影视都面临着市场的残酷竞争,市场决定着文艺出版发行机构的生杀大权,因此,千方百计获取市场的“青睐”就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不管你怎么看,是“虚假”也好,是“泡沫”也罢,总之,90年代后的文艺图书市场用“繁荣”来形容并不为过。①一年六七百部甚至上千部的长篇小说投放到市场上,如果不在“包装”上做点文章,很难引起读者的关注:对那些无名之辈或没有品牌效应的出版社来说,一本不起眼的小说置身于出版浪潮中,无异于石沉大海;而那些知名作家或者有品牌效力的出版社也要通过“包装”来进一步巩固自己对读者的吸引力优势,区别之处只是在于“包装”的具体方法上不同于前者。因此,市场上就出现出版商争先恐后、各出奇招、通过“包装”“夺人眼球”的局面。“在后现代的消费狂潮中,大众陷于对形象的迷恋之中,因而生产成为对象的生产,包装成为生产活动中决定性的环节,而大众对产品的消费转化为对形象的消费。”[1]
文学作品的“包装”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软包装”或“间接包装”,一类被称为“硬包装”或“直接包装”。
一
所谓“软包装”,即着眼于作品的内容,用一些比较吸引人的表现手法来“招徕”读者。通常的做法是用直接或间接的涉“性”话语来刺激读者的阅读兴趣。直接的“性”话语就是有关性爱的内容描写,间接的“性”话语则是与“性”相关的内容,诸如女性身体、隐私生活等的展示。“性”和“暴力”向来是通俗文艺吸引大众读者最常用的两大写作元素。90年代后,严肃文学或曰纯文学作品也越来越多地借用这两个写作元素来包装自己的作品。由于文字对“暴力”的描写缺乏直观的视觉刺激效果,而这些对影视来说却能通过影像语言轻易获得,于是“暴力”元素渐渐淡出文学作品。但“性”话语则不同,影视对“性”的表现尺度很难把握,如过于直露则很难通过审查,也就难以公开发行;如轻描淡写或点到为止,又刺激不了当代观众,因为他们能够从进口的外国大片或碟片上看到更火更暴露的镜头,这样也就失去了包装的目的。相比较而言,文学作品属纸质阅读,在审查方面没有影视严格,通常是出版社或杂志社自己把关。迫于市场的压力,一般的出版社或杂志社也希望有这样一些软包装作为“卖点”来吸引读者,因此,大多对“性”话语采取较宽容的态度。虽然也有少数作品因“性”话语过多、过于露骨,出版后引来有关部门的查禁(如《废都》、《上海宝贝》),但十多年来文学作品因“性”描写问题被查禁的不过几本,因而不足为训。
1993年贾平凹《废都》的出版,就是“性”包装的典型。《废都》尚在写作之中,出版社就以“当代《金瓶梅》”作为广告词,用意再明显不过。果然书一出来,人们发现其中“性”描写之多、之暴露确实可以与《金瓶梅》相类比。而用“□□□”和“此处删去多少字”这样俗套的删节形式,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罢了。尽管评论界一片谴责批评,但该书的销量却直线上升,加上坊间盗版,短短几个月就销出几十万册。“书商们直言不讳:《废都》中诸多的性描写,大大促进了此书的销售,是吸引读者的一个主要原因。”[2]与《废都》同年出版的所谓“陕军东征”的其他几部作品《白鹿原》、《热爱生命》、《最后一个匈奴》、《八里情仇》以及《骚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性”包装的问题,以致于有论者形容其为一股“陕军性狂潮”。[3]
这几部作品都属于纯文学,有较高的艺术水准,也不乏深刻的思想内蕴,其中《白鹿原》更是被誉为90年代以来第一部具有史诗性价值的长篇小说,经对一些涉性描写删节后还荣获“茅盾文学奖”。那么这些纯文学作家为什么要用“性”做卖点来包装自己的作品呢?这与当时的出版境遇有关。90年代初,纯文学陷入一个低谷,即使是名作家要想出版一本小说也很难。策划“布老虎”丛书的安波舜回忆说,他当时正在创作一部书写少年时期成长经历的长篇小说,“每天晚上写得泪流满面。可是想想,写完之后怎么样?谁给出?出了之后谁会看?当时不光我,我周围的许多作家,包括著名的先锋作家马原、洪峰他们都很沮丧。洪峰那时刚刚创作完《东八时区》,在文学圈子内很有影响,但找了几家出版社都不给出。”[4]文学艺术走向市场化后,纯文学作品的发表、出版发行被纳入商业化运作轨道,而商业化运作的铁律是什么好卖就卖什么。既然纯文学不好卖,俗文学好卖,出版商没有理由赔本出版纯文学作品,要出就得经过俗化处理,“性”包装就是手段之一,雅书俗装、雅书“性”装成为一时之风气。评论家白烨认为:“一些出版单位出于营销目的就某些作品所作的舆论宣传,一些职业书商出于赚钱目的就某些作家作品所作的倾力推销,这样不同的环节出于非文学目的的加诸纯文学作品的种种动作,使得一部纯文学作品常常在外形上被包得与俗文学读物无异,从而以更切合大众口味的形式和方式进入市场。这些做法势必给纯文学的作家作品在形象上带来不利的影响,……但有失应有得,这个得就是作品经过商业化的包装与运作,冲出了常在文人圈子里打转的小天地,走向了更多的读者和广阔的社会,这对于作家、对于文学和对社会来说,又都不无益处。”[5]这种认识和评价还是比较客观和辩证的。文学与商业的结合,其中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文学追求艺术审美价值,商业追求经济价值,不同的价值追求自然带来冲突。但冲突不一定意味着完全不能合作,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合作,这往往需要双方做出妥协、让步,纯文学作品的“性”包装也就是文学对商业与市场妥协的无奈之举。然而在这种合作中,由于商业处于有利位置,属于强势话语,因此处于弱势的文学做出的妥协和让步常常就更大一些。很多作家面对商家的包装充满了“妥协”的无奈。王安忆说:“我觉得包装是种不得已的做法。因为文学是纯精神的,但它必须要物质化,当它进入物质化渠道时就需要技术的手段。所以我们就面对现实,要对出版商、出版社互相体谅、互相配合,当然作为我个人来讲,我是不喜欢包装的,可是我从出版商考虑的话,我愿意配合他,但是必须要有分寸。”②由此不难看到市场经济体制下文学艺术走向市场化、商业化所带来的不利因素和负面影响,这也是商业霸权和商品意识形态对文学艺术侵凌的表现。
90年代中后期,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性”话语的软性包装更是走向普遍化,尤其是一些间接的“性”话语包装即女性身体以及个人隐私生活的展示越来越多,越来越迎合商业化、消费主义社会中人们对“性”消费的趣味,像陈染、林白、海男等私人化小说以及卫慧、棉棉等“身体小说”就是属于这一类,现在几乎很难在一本文学杂志或一个书市上找到一篇完全无涉“性”话语的小说。韩少功在一次演讲中说,他在海南作协看一批小说稿子时,发现来稿的题材竟有一大半是写男女偷情故事的。[6]现在就连一些重大而又严肃的题材也不忘渲染一番“性”,诚如陈晓明在评论荆歌、熊正良以及晚生代的一些作家在书写“苦难”这样的主题时所说的:“在当代小说里,性与苦难的相连完全失去了道德非法性的历史本质,与其说它是苦难的根源,不如说它是苦难的道具。而苦难则变成它的布景。对苦难的认真书写,结果是对苦难的颠覆。书写苦难的动机让位于对当代消费社会主导趣味的叙述。”[7]波德里亚曾经说过:“性欲是消费社会的‘头等大事’,它从多个方面不可思议地决定着大众传播的整个意义领域。一切给人看和给人听的东西,都公然地被谱上性的颤音。一切给人消费的东西都染上了性暴露癖。”[8]“性”和“身体”成了“美丽的消费品”,自然也就成为出版商作为“卖点”包装作品的重要手段,作家们则成为无辜的“合谋者”。
二
文学作品的第二类包装是“硬包装”或“直接包装”。与“软包装”的区别是,它不是针对作品内容的构成元素或表现形式,而是针对书名、书刊的封面装帧设计、内容提要等最直观最显眼的部分加以“包装”。这种“包装”的目的和第一类“软包装”一样,无外乎吸引人的“眼球”,只不过它吸引的是读者的“第一眼”,留下的是“第一印象”。而“第一印象”的“首因效应”对消费者的消费决定影响很大,因此,出版商是不会轻易放过这一“促销”手段的。
文学作品的“硬包装”主要体现在“书名包装”上。一本书的书名很重要,它是吸引读者阅读的第一个要素。一个富有诱惑力的书名往往能套牢读者的目光,诱使他们前来翻阅。从销售的角度来说,消费者接近商品、接触商品是整个购买行动中最为关键的一步。正是基于这种出发点,出版商绞尽脑汁在书名上做文章。而作家们对此则往往主动配合,即使有少数作家不大情愿,但迫于出版发行压力也只好无奈妥协。譬如毕淑敏的小说《拯救乳房》,原名叫《癌症小姐》,但出版社认为读者一看“癌”字就会产生抗拒心理,毕淑敏不得不妥协,把书名改为《拯救乳房》。正如波德里亚所说的,“性欲是消费社会的‘头等大事’”,“一切给人消费的东西都染上了性暴露癖”,书名包装自不例外。当下以“性”话语,包括关于女人、身体、欲望、生理器官、隐私等与“性”相关的话语,或让人产生“性”联想的暧昧字眼作包装的书名比比皆是,比如《丰乳肥臀》、《有了快感你就喊》、《大浴女》、《女贞汤》、《私人生活》等等。
对于书名涉“性”话语或“性”暗示,作家们和出版社持何态度呢?《作女》畅销后,张抗抗说,求新求异是商业时代必然的方式,不能老是死气沉沉,墨守成规。图书竞争逼着你去想一个耳目一新的角度。“离奇”书名没什么不好,起码让你精神一振,有想翻翻的欲望。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则直言不讳,书名的好坏关系到一本书的成败。现在图书业竞争那么激烈,整个图书市场都在求新求异,书名也要求新求异。有些书名没取好,销路就不好。中国青年出版社策划部吴方泽说,针对青年读者的书,书名就是要另类和酷,出奇才能制胜。这是从港台书得到的启发,重视书名的轻松、特别、另类。[9]
读者和评论家又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呢?“这几年书名变得越来越俗,也越来越让人费解,……其实,这当中不少书的质量并不错,但是书名让人看了就是不舒服、不痛快。究其原因,可以认为,这是作者和出版社在打读者的主意,用俗气的书名来吸引读者,以扩大发行量。但结果未必如此,因为首先映入读者眼帘的是书名,俗气乃至让人发挥想象的书名,使读者对书的内容质量大打折扣,结果适得其反。”[10]也有少数读者持理解和赞同的观点。如有读者评论道:“作家和出版方都希望在庞大又拥挤的出版市场上让大家能注意到自己的声音,这是人之常情。都说文化快餐时代太浮躁,书太多,书名能否抢眼就关系着作品的市场价值。卖方重视书名和封面,与买方越来越刁的胃口不无关系,谁不愿意看到别具一格的新事物呢?轻松、特别、另类的书名和封面屡屡让读者心甘情愿掏腰包,这是你我都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文学图书作为一种用来愉悦精神胃口的商品,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必然越来越时尚化、生活化和口语化,至少它缩短眼球涣散的时间,大大节约了读者的时间。”[11]
评论家洪治纲对于书名的“暧昧性”批评道:“在商业领域中,以调情的性感方式招揽顾客,几乎是一种无往而不胜的招式,……作家们为自己的作品取一个具有暗示性、暧昧性的名字,以此来吸引读者的眼球,也完全可以视为对这种商业化思维的直接袭用和巧妙嫁接。……我以为,这种用挑逗性话语作为书名来迎合世俗情趣的做法,实质上隐含了创作主体十分浮泛的内心景象,折射了他们精神深处的撒娇姿态。……它充分暴露了作家对自身创作的不自信,对世俗趣味的低级迎合,是一种话语的自我放纵与灵魂的自我放逐。”[12]
由此可见,出版社、作家的态度与读者、评论家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出版社迫于市场竞争要出奇招,作家们只好妥协作出“支持”的姿态,毕竟图书能否出版并畅销事关他们的利益;而读者和批评家则大多对“性包装”难以接受。这表明,读者尽管对晦涩艰深一类“令人难过的雅”不欢迎,但更不能容忍低俗和粗俗。那么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这些挨批的书在书市上却往往能获得好的销量呢?是不是书名起了很大作用呢?个中原因要细加分析。其一,一部分书虽然取了个“惹火”的书名,但其内容却是严肃的,艺术水准也不差,且是名家之作,比如莫言的《丰乳肥臀》、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毕淑敏的《拯救乳房》就属于这一类,这是典型的雅书俗装,读者往往是被书里书外同时吸引。这种情况书名虽有作用但作用不是很大。其二,有些书虽然内容一般,艺术平平,但读者受书名诱惑,以及其他信息如封面广告词、内容提要等误导,等买回去读完始觉上当,但为时已晚,出版商的目的已经达到。这种情况则属于俗书俗装,书名的包装带有一定的欺骗性,对书的销售起的作用就相当大。因此,不管是哪种情况都对出版商有利,出版商何乐而不为呢?
无论是“软包装”还是“硬包装”,各种形形色色的“性”话语巧妙缝织的“包装”术的动机、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试图以“性”来吸引人,但由于手法不同,效果有异。“俗书俗装”、“雅书俗装”比较直接,促销效果不错,但社会评价低;“俗书雅装”和“雅书雅装”的手法相对隐蔽,往往能收到良好的市场效益和社会评价。虽然同用“性”话语之类的“俗”套来包装,但由于其能做到“俗”而不“低”、“俗”而不“粗”,而是“雅俗兼顾”,这要比那种赤裸裸的“性”话语诱惑高明得多,也更容易为大众读者接受。既然包装的目的是出于商业推销考虑,而文学艺术走向市场化后不得不按商业化规律运作,包装也就无可厚非,那么出版商就要考虑如何兼顾传播效果和社会影响,如何统筹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雅与俗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注释:
①据《中国出版年鉴》统计,1990年图书发行80 224种、印数56.4亿册,1993年上升为96 761种、59.3亿册,而到1999年更高达141 831种、73.2亿册。单就长篇小说来说,“在经历了最初一两年的低速徘徊后,自1992年开始回升,1993年初步形成热潮,年出版量为420余部,超过了‘文革’前17年的总和。此后,大约以每年百部的速度递增,1996年达600部(一说700多部,也有的说800部),可谓‘飞速发展’。”参见郑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汤学智《生命的环链——新时期文学流程透视(1978-1999年)》一书第181页。
②参见《海上文坛》1994年第2期与陈村、王安忆等人的访谈《文学需要包装吗?》
[1]陈刚.大众文化与当代乌托邦[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132.
[2]李昭醇.评《废都》的“性包装”[J].图书馆论坛, 1995(5):63-64.
[3]赵遐秋.评“陕军”笔底性狂潮[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5):59-64.
[4]邵燕君.倾斜的文学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34.
[5]白烨.作为文学、文化现象的“陕军东征”[J].小说评论,1994(4):61-65.
[6]韩少功.冷战后文学写作新的处境——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J].当代作家评论,2003 (3):26-40.
[7]陈晓明.表意的焦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416.
[8]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159.
[9]陆梅.小说书名渐入怪圈[N].文学报,2003-02-20.
[10]老李.用俗气的书名才能吸引读者?让书名高雅些吧[N].人民日报,2003-05-07.
[11]书名,此事不关风与月[N].北京青年报,2003-05-12.
[12]洪治纲.撒娇、调情与话语的放纵——从小说篇名的暧昧性说起[J].文学报,2003-08-28.
The Art for Packaging Discourses Involving“Sex”——On a new literary market-o riented means of communication
CHEN Shang-rong
(School of Humanities,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Nanjing 210094,China)
In the 1990s,the term“packaging”was openly introduced into the field of literary publishing.W hether by“direct packaging”o r“indirect packaging”,the ingeniousweaving of all kindsof overt or covert sex-related discourses become the main means of packaging.Packaging itself is irrep roachable,but publishers should take account of both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and balance between the secular and elegant and between commercialization and art.
sex-related discourses;packaging;literary art;marketization;communication
I206.7
A
1009-1513(2010)01-0051-04
[责任编辑文 俊]
2009-08-29
陈尚荣(1965-),男,安徽和县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与影视艺术传播研究。
——以纯文学在近代和八十年代的两次现身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