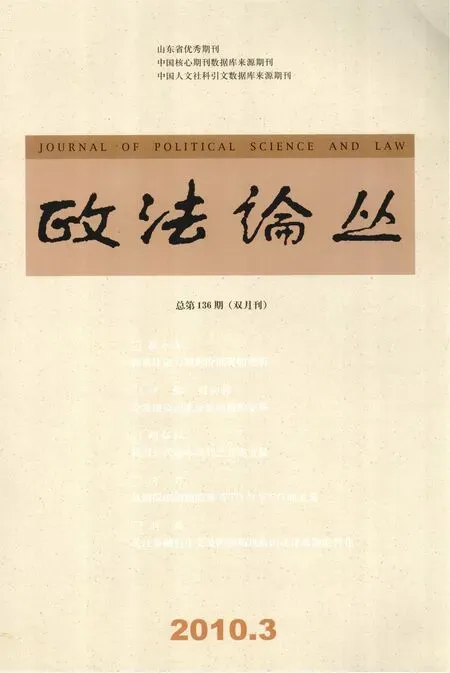《大札撒》中宗教问题探析
王 磊
(山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大札撒》中宗教问题探析
王 磊
(山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法律维护的是当时的社会秩序,宗教坚持的是未世的内心信仰。法律与宗教的关系有时表现为和谐共治,有时表现为消耗对抗。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是每个时期都必须慎重对待的重大问题。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的过程中,很好地利用了本土宗教,结束了蒙古各部的战乱;在对外扩张中,制定了符合当时现状的宗教政策,并将其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定,使法律与宗教的关系在统一和征服的战争中出现了良性互动的奇迹。
大札撒 宗教 宗教政策
“札撒”,系蒙古语汉字标音拼写,也读作“札撒黑”(相当于札撒的复数),有“法规”、“法令”之意。[1]P4《大札撒》,或称《札撒大典》,[2]P28也即我们现在常说的《成吉思汗法典》,从现在已知的内容上看,《大札撒》对大蒙古国的国家、社会、军事、战争、贸易、赋税、社会秩序、诉讼等诸多方面做了规定,对规范当时蒙古社会及后世蒙古各汗国的立法都产生过重要作用和巨大影响,对此本文不做论述。在此,仅就《大札撒》中对宗教问题的规定做一简要探讨。
一、蒙古各部的早期宗教
成吉思汗统一之前的蒙古宗教是与当时的蒙古社会现状紧密联系的。12世纪时期的蒙古,是蒙古各部贵族角逐争雄的时代,当时的蒙古部族众多,其中实力较强的有克烈部、蒙古部、塔塔儿部、乃蛮部、蔑儿乞部。[3]P56这些部落的统治者为了掠夺更多的奴隶和财物,控制更多的属民和土地,进行着不间断的兼并战争,如克烈部后来的统治者王罕,在少年时期就曾在与塔塔儿部的战争中被掠作奴隶。各部落属民的变化与融合,使得具有不同信仰的蒙古各部的宗教,在一开始就具备了开放性和兼容性的特点。
在各部落中盛行的是蒙古地区流传的萨满教,这是当时的主流宗教。萨满教是氏族社会的原始宗教,属多神教。他们认为,世间万物皆有灵性,因此崇拜的对象也很广泛,如天、地、山川、河流、日月星辰、水、火等;也崇拜灵魂,“以为死亡即由此世渡彼世,其生活与此世同”。[4]P30虽然蒙古早期崇拜的对象很多,但是他们承认有一个主宰,这就是天,蒙古人称之为“腾格里”。“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称天,闻雷声则恐惧,不敢行师,曰:天叫也”。[5]P12“其常谈,必曰托着长生天底气力,皇帝底福荫,彼所欲为之事,则曰天教恁地,人所已为之事,则曰天识着,无一事不归之天,自鞑主至其民无不然”。[6]P12-13因此蒙古人有拜天之礼,在他们看来,天不仅主宰着一切自然现象,而且操纵着人类的命运,赋予人类灵魂,是至高无上的。凡事向天祈祷,祈求天的帮助和保佑。更重要的是,天还能赋予人各种权利,这是萨满教为蒙古统治者利用的基础。
当时,大部分的蒙古人深信萨满教,掌教的萨满被认为能够与天对话,有着很高的地位和权威。成吉思汗通过把有影响的萨满争取到自己周围,制造影响,为其统一事业效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萨满豁儿赤宣扬天让成吉思汗做国土的主人,萨满阔阔出(即帖卜腾格里)则传达神的旨意,让成吉思汗做普世的君主。这对成吉思汗稳定部众,瓦解敌军,完成统一大业起到了巨大作用。而属于基督教的景教(聂思脱里派)在蒙古的几个部族中曾有传播。景教自唐朝传入中国,后被唐政府取缔,只在北方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现在我们可以从很多史料中查到景教传播的记载。《鲁不鲁克行记》和《马可波罗行记》中曾记载克烈和蔑儿乞部信奉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这点可在其他史料中得到证实,如“(克烈部)奉基督教,十一世纪初时,聂思脱里派教师曾传教于此部”。[4]P41格鲁塞在《蒙古史略》中也有景教在蔑儿乞部、克烈部和乃蛮部传播的记载。[7]P2-3这些对成吉思汗后来的宗教政策也产生过影响。
二、成吉思汗的宗教政策
通过不断的战争,蒙古各部实现了统一。蒙古各部的统一以 1206年春在斡难河召集的忽里勒台①上推举铁木真为大汗,即成吉思汗,成立大蒙古国为标志。蒙古各部之间的相互掠夺和战争停止了,他们都统一到成吉思汗的大旗下,被分别编入了全国的九十五个千户之中 (千户之下设百户,百户之下设十户),大多数的千户是由不同部族的人民混合组成的。作为统一的基本军事单位和地方行政机关,千户制度取代了以前的部落或氏族结构。通过编组千户,全蒙古的百姓都被纳入严密的组织,由汗任命的那颜 (官员)管领着,在指定的范围内居住,并不得变更统属。至费尼记载道:“自从各国、各族由他们统治以来,他们按照自己习惯的方式,建立户口制度,把每个人都编入十户、百户和千户”。[2]P34“人们只能留在指定的百户、千户或十户内,不得转移到另一个单位去,也不得到别的地方去寻求庇护。违反此令,迁移者要当着军士被处死,收容的人也要受严惩”。[2]P34
统一后的大蒙古国建立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国家组织形式,组建了强大的军事力量。然而,这并不是部族之间的自愿联合,要使这些曾经相互征伐的不同部族的人民共同生活和作战,除了社会的组织形式,精神上的支柱也不能忽视,由此宗教问题也就直接摆在了蒙古统治者面前。
成吉思汗出生在一个笃信萨满教的蒙古部族中,秉承幼年的熏陶,他自己也信仰萨满教。成吉思汗本人对在不儿罕山(今肯特山)向长生天祈祷有一种特殊的执着,这可能和他的经历有关。他在不儿罕山遇难脱险后对天发誓说:“我的小生命,被不儿罕山遮救了,这山久后时常祭祀,我的子子孙孙也一般祭祀”。[8]P51仪式是这样的:“他首先脱帽和解下腰带搭在肩上,以示顺从,然后跪拜九次,并用乳酒做祭奠仪式”。[9]P281此后,成吉思汗在出征之前,往往登上不儿罕山,重复这一朝圣,祈求天的帮助和保佑。成吉思汗也相信占卜,他自己进行占卜,也令其他教徒为他占卜,史料记载耶律楚材就常为之占卜 (《元史·耶律楚材转》)。
根据蒙古当时的情况,成吉思汗成功地利用萨满教把多数的蒙古民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实现了他统一的大业,因为萨满教虽然是一种较为原始的宗教,但在蒙古各部中信徒众多,作为巫师的萨满也地位很高,如萨满阔阔出。成吉思汗必须利用他们为自己服务,这一点毋庸质疑。问题是在蒙古统一的过程中和统一后的扩张战争中,面对与自己信仰不同的敌人,成吉思汗的宗教政策成了关系他事业成败的复杂而敏感的问题。笔者认为,成吉思汗宗教政策的发展主要经历了这样几个个阶段:
(一)接受包容阶段
在统一蒙古的过程中和向外扩张的初期,成吉思汗接触到了与自己信仰完全不同的宗教,如克烈部和乃蛮部的景教,虽然以前他肯定的对此有所了解,但是作为局外人的了解与作为征服者的政策是完全两个概念。不仅仅是景教,在后来对金国的战争中如何对待佛教也是如此。笔者认为,在这一时期,随着成吉思汗阅历的丰富、认识的发展,他并未对其他宗教予以排斥,而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接受包容,并对其中有才能的人予以吸纳和重用。如在打败王罕,征服克烈部后,成吉思汗认为王罕之弟札阿绀孛的女儿唆鲁禾帖尼有智慧,即让他心爱的小儿子托雷娶其为妻。[9]P213众所周知,正是托雷的这位王妃,一位虔诚的景教徒,用自己的智慧扶持儿子蒙哥登上汗位,使帝系由窝阔台系转为托雷系。在对金国的战争中,成吉思汗得到了佛教徒耶律楚材,他对耶律楚材非常器重并委以重任,拜为中书令。耶律楚材对避免蒙古军队对内地人民的大屠杀,制定蒙古的各项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征服乃蛮的战争中,成吉思汗俘虏了乃蛮掌印官畏兀人塔塔统阿,此人“深通本国文字”,成吉思汗命他“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元史·塔塔统阿传》)。有了文字,记录蒙古国家、社会各方面的重要事件成为可能,《大扎撒》就是以畏兀文字记载的。塔塔统阿的宗教信仰虽然不见记载,但是乃蛮部大都信奉景教,畏兀儿则是佛教、道教、景教都有信徒,塔塔统阿也不可能与成吉思汗的宗教信仰相一致。
(二)分化利用阶段
随着乃蛮部政权的灭亡,蒙古实现了统一。统一后的蒙古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开始了大规模的扩张战争,主要是对西辽 (喀拉契丹国)和花剌子模的战争。西辽的宗教政策对成吉思汗启发很大。耶律大石建立西辽后,并未将辽代信奉的佛教强加于当地的人民,仍然允许他们信奉伊斯兰教,西辽的政权也维持了近百年。然而当乃蛮部的王子曲出律夺取西辽政权后,听从其王后的劝告,改信佛教,在征服可失哈耳和忽炭后,强迫当地的伊斯兰教徒改信佛教,遇到反对后即虐杀伊斯兰教士,激化了宗教矛盾。[2]P81-82西辽前后统治者的宗教政策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不同影响,对成吉思汗利用宗教,分化瓦解对方,争取可以利用的力量起到了启示作用。当成吉思汗派哲别率军征服西辽时,即“宣布信教自由”,[4]P81结果“当地的居民把蒙古军队当做摆脱迫害的救星来看待。”[9]P301在随后对花剌子模的战争中,成吉思汗采取了同样的宗教政策。诚然,蒙古军队的扩张战争伴随着残酷的屠杀,然而这种屠杀并不是建立在宗教信仰的不同上,相反,他们利用宗教帮助完成了征服。当时的伊朗学者至费尼曾记载道:“蒙古人的札撒和法令是,向他们纳款投诚者,一律免遭他们凶残的暴虐和凌辱。再说,他们不反对宗教信仰——怎说得上反对呢——宁可说他们奖励宗教信仰”。[2]P14
(三)掌握管理阶段
持续的扩张战争,使蒙古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已经拥有了广阔的国土和众多的臣民。随着战争的深入、领土的扩大和对不同宗教信仰中优秀人物的掠取迁徙,在成吉思汗的面前展现了一幅更加广阔的画卷,他以更加开阔的视野认识到,掌握管理好宗教,消除被征服者心中的恐惧,使臣民顺从,有时比起战争来更加有效。如在他率兵攻打花剌子模的匝儿那黑时,全城就因一名信奉伊斯兰教的使者的劝谕而投降。所以这一阶段的成吉思汗,加强了对各宗教的控制。在征服花剌子模的战争中,成吉思汗召集了伊斯兰教的法官和宣教师各一人,听取了伊斯兰教的教义与教规,他表示赞同,但到麦加朝圣一事除外。他让穆斯林以他的名字进行祈祷,因为他已经取代了苏丹摩诃末。[4]P130成吉思汗赞成伊斯兰教教义,并把自己化身为穆斯林心中的真主,从精神上控制众多伊斯兰教徒的目的是非常明显的。在西征时,成吉思汗派人请到了全真派的道士丘处机,他的本意或许是让丘处机为他传授长生不老之术,然而丘处机对道教教义的讲解,赢得了成吉思汗的尊敬,称其为“神仙”,并以超前的眼光,对尚未在其统治之下的中原内地的道教教众实行管理。他颁给丘处机圣旨,令他“掌管天下的出家人”(《元史》卷 202)。对佛教也是如此,他把佛教僧人中观及其弟子海云称为大、小长老,并令部下“好衣与粮养活着,教做头儿,多收拾那般人,意在告天 ”。[10]P144
从成吉思汗崛起以来,他对宗教的认识随着他征服事业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他的宗教政策也随着他对宗教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变得更有目的性。随着条件的成熟,这一些,很自然的要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
三、《大札撒》中有关宗教的规定
对于《大札撒》在何时制定,一直是学者争论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大札撒》是成吉思汗于 1206年登上汗位,建立大蒙古国时制定和颁布的;②也有的学者认为《大札撒》不是一次制定完成的,而是分别于 1203年、1219年和 1225年等经过几次制定完善的。③这两种说法都有自己的理论基础,也有相应的史料予以证明。就本人而言,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因为蒙古早期的立法是粗线条的,但是随着文字的使用,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成吉思汗数次进行了法律的修订和整理,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终于形成了一部统一的法典——《大札撒》。这也符合古代法从习惯到习惯法再到成文法的一般规律。
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法典的内容进行了诸多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笔者有幸站在前人的臂膀之上对法典中有关宗教规定的内容进行一下探讨。
(一)宗教信仰自由
这一规定贯穿于成吉思汗宗教政策的始终,也是成吉思汗宗教政策的根本问题。允许本民族的人自由信奉宗教,也允许其他民族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是成吉思汗的一贯政策。如本文前述,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和统一蒙古后的对外扩张中,都坚持了这一原则,并取得了巨大成就,用法律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是势所必然的。
(二)尊重任何一种宗教,任何一种宗教都不得享有特权④
这实际上规定了宗教合法和宗教平等。虽然成吉思汗和多数蒙古人信奉萨满教,萨满教也在当时取得了国教的地位,但是成吉思汗通过接触不同的宗教和文化,认识到了大千世界的多样性,对具有更深文化基础的其他宗教表示了认同,认为它们都符合神的旨意。
至费尼记载道:“因为不信宗教,不崇奉教义,所以他没有偏见,不舍一种而取另一种,也不尊此而抑彼;不如说,他尊敬的是各教中有学识的、虔诚的人,认识到这样做是通往真正宫廷的途径。他一面优礼相待穆斯林,一面极为尊重基督教徒和偶像教徒。他的子孙中,好些都按其所好,选择一种宗教:有皈依伊斯兰教的,有归奉基督教的,有崇拜偶像教的,也有苛守父辈、祖辈的旧法,不信仰任何宗教的;但最后一类现在只是少数。他们虽然选择一种宗教,但大多不露任何宗教狂热,不违背成吉思汗的札撒,也就是说,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不分彼此”。[2]P29《多桑蒙古史》记载:“成吉思汗命其后裔切勿偏重任何宗教,应对各教之人待遇平等”。[4]P174成吉思汗的后人也较好的遵守了《大札撒》中的这一规定,“他们不曾强迫过任何人背弃自己固有的信仰或违背自己的法律”。[11]P34
(三)各宗派教师教士免除赋税和差役
这一规定许多史料都有记载,至费尼记载:“他们免除了各教中有学识者的各种临时赋税和差发的科扰;后者供公共使用的宗教基金、捐赠,及他们的农民耕夫,也被蠲除赋役”。[2]P14多桑记载道:“各宗派之教师教士贫民医师,以及其他学者,悉皆豁免赋税”。[4]P174成吉思汗在给丘处机的圣旨中,不仅让他掌管天下的出家人,也蠲免全真门下道士的差役赋税。对佛教也有同样的规定,1219年,成吉思汗在西域传诏,命海云及其师中观统汉地僧人,免其差发。[3]P339成吉思汗不仅接受了其他宗教,而且用法律形式保证其宗教政策的实施,并为实施其宗教政策给予物质保障,这是法典的一大特色。没有赋税和差役的负担,各宗教中的专职人员会对统治者心怀感激,可以更加专心地投入到宗教事业中,利用宗教为统治者服务。
(四)施行妖术者处死刑
多桑记载:“……以其巫蛊之术害他人者……并处死刑”。[4]P173格鲁塞记载:“法典确实严厉:谋杀、盗窃、密谋、通奸、以幻术惑人、受赃物者等死”。[7]P283《元朝秘史》、《史集》和《草原帝国》中都记载了萨满阔阔出事件。萨满阔阔出曾深受成吉思汗信任,他习惯于冬天裸坐在冰上,凝冰为他的体温融化,升起一层水雾 ,蒙古百姓就认为他骑着白马上天去了,他的巫术让人可怕。萨满阔阔出以天的名义散布谣言,对成吉思汗的弟弟哈撒儿和铁木哥进行了离间、中伤,成吉思汗以妖言惑众之罪将其处死。因为科学 (特别是医学)的不发达,古人十分相信巫蛊等邪术,历代统治者也严厉打击和禁止。成吉思汗在法典中的禁止性规范,在后来其继承者严厉打击民间邪教的规定中得到印证。
四、法典化宗教政策的成就
当时的成吉思汗的《大札撒》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其影响不仅在于当时,而且延及其后世。据史料记载,“札撒”在成吉思汗后期已经汇编成册,藏书金匮,被蒙元时代历朝大汗、皇帝尊奉为国宝。[12]P77成吉思汗在逝世前曾立下遗嘱:“……从今以后,你们不可更改我的命令 (Yasaq-札撒)”。[12]P319对此,至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也有详细的记载。成吉思汗将其宗教政策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取得了巨大成就。法典的实施需要国家强制力的保证,而宗教的皈依则是社会个体的自我意识和自我约束。成吉思汗很好地把二者结合在了一起。他的后继者遵从法典,遵守其定立的民族宗教政策,对蒙古持续的扩张统一和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为蒙古的统一和扩张服务,维护政治统治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和对外扩张战争的胜利,除了战略战术和各种政策的运用得当,宗教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前所述,成吉思汗早期利用萨满教为他统一蒙古各部服务,其后在东征西讨中也利用宗教为其扩张战争服务,并把各教派中的优秀人物收归己用,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如畏兀儿臣服后,成吉思汗并未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而歧视,反而对其统治者优礼有加,在后来征讨西辽和花喇子模的战争中,畏兀儿都派兵从征。再如,丘处机自西域回到燕京后,住在白云观。当时山东爆发起义,蒙古军队奉命征讨,受蒙古元帅阿里鲜之请,丘处机亲往招降农民起义。成吉思汗的继任者,遵从法典中确立的宗教政策,利用西藏的宗教领袖,把西藏成功并入元朝版图,更是成吉思汗宗教政策的成功范例。
成吉思汗的宗教政策虽然表现出了宽容的一面,但是这种宽容是建立在利用宗教,维护统治的基础之上的。宗教应为政治和征服服务,不能干涉政权,始终是其坚持不变的宗旨。当教权危及到他的统治时,成吉思汗的处置也是遵循这一原则的。如在处死萨满阔阔出后,成吉思汗任命了顺从自己的兀孙取代了萨满阔阔出,继续为其统治服务。巴托尔德在《突厥斯坦》中记载道:“他‘骑白马,着白衣’,是一位稳重而伟大的萨满”。[9]P280
(二)缓和阶级矛盾,增强了民族文化交流
蒙古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自大汗至奴隶有着严格的阶级划分。蒙古的统治以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为特点,特别是西征后,大批的伊斯兰教徒被掠东归,他们的身份大多是奴隶,承受着阶级的压迫。马克思说过:“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13]P2蒙古统治者利用宗教,使受压迫者有精神上的寄托和心灵上的慰藉,客观上缓和了阶级矛盾。这虽然有萨满教是多神教,有利于接受其他宗教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蒙古统治者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策略。“他们对各教派的首领表现出来的优待为他们的腾格里信仰提供了一种特别的保证。于是,普遍的迷信恐惧产生了普遍的容忍”。[9]P280
经历了窝阔台、贵由后,到蒙哥当政时,蒙古的都城哈拉和林已经有了回回街、契丹 (汉人)街,并有了各种宗教场所,如回教礼拜寺、基督教堂、佛教寺院等,也建有集市和各种工匠的居所。各民族人员的聚集、交往,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提高了科学技术的水平,为元朝建立后逐步接受汉族文化奠定了基础。
(三)补充兵源,维持蒙古军队的战斗力
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骑兵,驰骋欧亚大陆,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冷兵器时代的奇迹,建立了迄今为止版图最大的帝国。确实,蒙古骑兵训练有素,组织严密,战斗力强,但是他们的数量并不多。在成吉思汗逝世时,蒙古军队的数量只有十二万九千人,分为三翼,按蒙古人的习惯向南展开,左翼在东,右翼在西,中军是成吉思汗的护卫军。左翼军有六万两千人,右翼军有三万八千人,其余的则被分配给中军与后备军。[9]P286在西征时,木华黎率领左翼军继续攻打金国,以右翼军为主力,再加上中军和仆从国的军队,要想打败当时十分强大的花喇子模是十分困难的。当时花喇子模有军队四十万,蒙古的军队不超过二十万。[3]P142从军队数量的对比上,蒙古军队就不占优势,况且是异地作战。成吉思汗很好地利用信教的自由,使当地的被征服者相信,他发动的战争是正义的复仇之战,而不是宗教战争。他抽调被征服地区的精壮者组成签军,弥补了蒙古军队数量的不足。实际上,他正是用在不花剌组成的签军攻打撒麻尔干,用在撒麻耳干组成的签军攻打玉龙赤杰。这一措施的成功,除了有军事和行政上的强制外,与成吉思汗认同伊斯兰教,并把自己装扮成伊斯兰教的守护者有直接的关系。
成吉思汗的继任者忠实执行了法典中宗教政策的规定,最终灭亡了金国和南宋。在统一中国的战争中,就有大批归顺和俘虏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各族人,他们组成的“西域亲军”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蒙古统治者成功地利用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民,补充兵源,为他们的征服服务,终于使总人口只有四十万的蒙古民族,成为广阔的中原大地和六千万人民的主宰。
五、利用宗教教义,维护社会秩序
成吉思汗颁布的《大札撒》,规范了蒙古社会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各个方面,得到了普遍的遵守,具有广泛的效力。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典,辅之以宗教教义的德化作用,改变了蒙古社会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社会秩序的稳定令人印象深刻。任何的宗教教义都有一定的伦理性,包含着一定的道德准则,这些伦理道德在某一点上会与法律形成契合,从而达到辅助法律实施的作用。如伊斯兰教教义中的教徒互相友爱、不凶杀、不抢劫、不盗窃、不酗酒等,恰恰符合了统治者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阿布哈奇在《蒙古人与鞑靼人的历史》中记载道:“在成吉思汗统治下,从伊朗到图兰之间的一切地区是如此平静,以至一个头顶金大盘的人从日出走到日落处都不会受到任何人的一小点暴力”。[9]P322柏郎嘉宾在其蒙古行纪中也有类似记载。蒙古统治者巧妙地把宗教教义和法律结合在一起,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与成吉思汗统一之前的蒙古社会秩序形成了鲜明对照。
元朝建立以后,全国的人民被分为了四个等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阶级矛盾和阶级压迫进一步加剧。虽然元朝的法律有了改变,但是元朝统治者遵循成吉思汗法典确立的宗教政策并没有改变。他们通过对各派宗教加强管理,利用宗教领袖和宗教教义,宣扬现实中的一切,都是神祇的安排,人们应当顺从,从而麻痹人们的心灵。如元统治者利用佛教大做法事,宣扬宿命、苦难、轮回等,让人们安于现状,仍然是蒙古统治者“以佛治心”政策的延续。
成吉思汗统一了战乱纷飞的蒙古,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张战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除了他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外,其法典化的宗教政策功不可没,如信教自由,宗教平等,打击邪教等政策。虽然我们现在对法典的相关内容略有了解,但很多的内容仍值得我们去探寻。
注释:
① 原为部落议事会,此时已变为议决国家事务的会议。
② 如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参见《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 283页。
③ 如吴海航、奇格、韩儒林等,至费尼和拉施特也持此说。不过奇格先生认为最后的完成应为 1227年,参见奇格《再论成吉思汗 <大札撒>》,《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第 6期,第25页。
④ 梁赞诺夫斯基表述为:“他命令无差别地尊崇所有的宗教,因为他认为它们全都符合神的旨意”。笔者遵从《<成吉思汗法典 >及原论》中的表述,参见《<成吉思汗法典 >及原论》,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2页。
[1] 张晋藩总主编,韩玉林主编.中国法制通史(元)[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2] [伊朗]至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M].何高济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
[3] 韩儒林.元朝史(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 [瑞典]多桑.多桑蒙古史(上册)[M].冯成均译.北京:中华书局,1962.
[5] 蒙珙.蒙鞑备略.王国维笺证本.
[6] 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王国维笺证本.
[7] [法国]勒内·格鲁塞.蒙古史略[M].商务印书馆,民国 23年版.
[8] 元朝秘史(卷 2)[M].四部丛书刊本.
[9] [法国]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M].蓝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10] 张践,齐经轩.中国历代民族宗教政策[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11] 柏郎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M].耿昇,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1985.
[12] [波斯]拉施特.史集[M].余大均,周建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An Exploring Analysis on the Problem of Religion in the Great Zhasa
W ang Lei
(Criminal Judicial College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Jinan Shandong 250014)
The law is to maintain the prevailing social order and religion adheres to one’s inner conviction in anotherworld.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religion sometimes reflects a harmonious cohabitation,some the times shows a consumed confrontation.It is a major issue to be taken seriously every time that how to dealwith that relationship.Genghis Khan has taken good use of the native religion to end thewar in differentministriesofMongolia in the processof unifying theMongolia,while he has also for mulated the religiouspolicy in keepingwith the situation at that time in the external expansion,which were deter mined in legal form and produced a miracle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law and religion present a state of positive interaction aswell asmade a great achievement in the unifying and conquering process ofwar.
Great Zhasa;religion;religious policy
词】DF08
A
(责任编辑:唐艳秋)
1002—6274(2010)03—108—06
王磊(1963-),男,山东莱阳人,山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诉讼法、法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