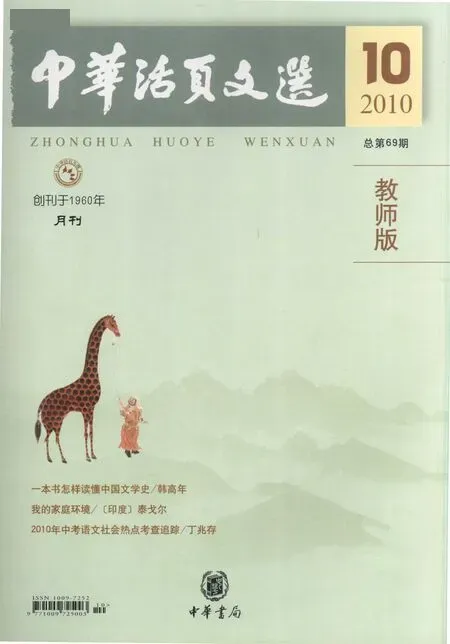我的家庭环境
〔印度〕泰戈尔
我年轻时代所享有的一个很大的便宜,就是弥漫在我家庭中的文艺气氛。我记得在我小时候,我常倚在可以望见那座有客厅房子的独立的建筑的凉台栏杆上。每天晚上这几间客厅的屋子都是灯火辉煌。华丽的马车一直拉进门廊底下,宾客来往不绝。我说不上那里面有什么样的集会,我只从黑暗中凝望着一排排亮着的窗户。隔断的空间虽然不大,而在我的儿童世界和这些亮光之间的空隙,却是很广阔的。
我的堂兄迦南德拉刚拿到塔卡拉特那(孟加拉著名剧作家)先生写的一个剧本,要在我们家里演出。他对于文学和美术的热情是无限量的。他是那一个团体的中心人物。他们永远有意识地努力从各方面引进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文艺复兴。服装上、文学上、音乐上、美术上、戏剧上突出的民族主义,在他心中和周围觉醒了。他在各国历史上,是个精研的学者,他已经开始用孟加拉文写了些历史研究,但是没有完成。他翻译并且发表了梵文戏剧《优哩婆湿》,还有许多有名颂歌都是他的手笔。在创作爱国诗歌上,他可以说是给我们做了领路人。这是在当“印度教徒协会”(印度的一个爱国组织)还是个年会组织的时候,在会里总是唱他那首《唱到印度的光荣我感到羞愧》。
我还很小的时候,迦南德拉堂兄就在盛年逝世了。但是见过他一次的人,也绝忘不了他的英俊、魁梧和庄严的相貌。他有一种不可抵抗的社会影响。他能够把人们吸引到他的周围而且永远和他连结在一起;只要有他的强大的吸引力在那里,就绝不会有分裂的问题。他是我们国家特别类型的人物之一,就是以他个人的吸引力,很容易在他们的家庭和村庄里出名。在任何一个有大的政治、社会或商业团体的国家里,这种人会自然地成为民族领袖。把许多人组织到一个团结的团体的力量,是依靠一种特殊的天才的。这种天才在我们国家里都白废了,白废而又可惜,我认为,就像是从天上摘下星星来当火柴用一样。
我记得更清楚的是他的弟弟,我的堂兄古南德拉(名画家加甘南达拉和阿巴宁达拉的父亲)。他也总使这家庭里充满了他的人格。他的宽大仁慈的心,把亲戚、朋友、客人和家属都一视同仁地拥抱了起来。不论是在他宽阔的南边凉台上,泉边的草地上,或是池边的钓台上,他总在主持着一个不招自来的集会,像一个“殷勤”的化身。他对于艺术和才智的广泛的欣赏,使他永远发出热情的光辉。任何关于节庆、游戏、戏剧或是其他娱乐中的新颖想法,他总是一个踊跃爽快的赞助者,在他的帮助下,就会开花结果。
那时候我们年纪太小,不能参加那些活动,但是他们推动的热闹与活力的波浪,奔涌而来敲打着我们好奇的心门。我记得有一次我大哥写的一出讽刺剧在堂兄的客厅里排演。从我们这边,倚在凉台的栏杆上,我们能听到对面洞开的窗户里的哄堂大笑和滑稽的歌声杂在一起,我们有时也能看到阿克谢◦玛正达的绝妙的滑稽戏。我们不能准确地知道唱的是什么,但总在希望有一天能够知道。
我记得有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使我赢得了古南德拉堂兄对我的特别好感。我除了得过一次品行优良的奖赏以外,从来也没得过奖。我们三个人中间,我侄子萨提亚是功课最好的一个。有一次他考得很好,得了奖金。我们到家的时候,我从马车里跳出来把这重要消息告诉了正在园里的堂兄。我跑到他面前,喊着说:“萨提亚得奖了。”他微笑着把我拉到他膝前去。问:“你得了奖没有?”我说:“没有。不是我,是萨提亚得奖了。”我对萨提亚的优良成绩的由衷喜悦,似乎特别地感动了我的堂兄。他转向他的朋友说着这件事,认为是很好的特色。我记得很清楚,我真是莫名其妙,因为我没有从这一点上来体会我的感情。因为没有得奖而得到了这个奖赏对我并没有好处。给孩子礼物是无害的,但是他们不应当得到报酬。使孩子害羞是不健康的。
午饭以后,古南德拉堂兄就到我们这边房子里来处理房产事务。我们长辈的办公室是一种俱乐部。在那里面谈笑和处理事务自由地杂在一起。堂兄常常在长椅上靠着,我总找个机会挨到他面前去。
他常给我讲印度历史上的故事。我还记得当我听克里夫(征服印度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建立了英国统治之后,回到家去又自杀而死的时候,我是如何地惊讶。一方面,写下了新的历史;另一方面,在人心神秘的黑暗里,却隐藏着悲剧的一章。在表面上那样的成功之内,怎会包含有那痛苦的失败呢?这故事整天很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
有时候,古南德拉堂兄一定要知道我口袋里放着什么东西。在轻微的鼓励下,我的手稿就毫不羞愧地拿出来了。我不必说明我的堂兄不是一个严厉的批评家;事实上,他所表示的意见,倒可以作为极好的宣传。但是当我诗中的稚气到了太冒失的地步的时候,他就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有一天,在一首叫做《印度母亲》的诗里,在一行之末,我所能想到的唯一可押的韵,那个字是“车子”的意思,我必须把这车子拉进来,虽然连一条可让车子通过的道路的影子都没有——押韵的坚决要求,不肯听受纯理性的任何推托。古南德拉堂兄迎接这车子时狂笑的大风,把这辆车子吹回到那条不可能有车子走来的道路上,从此就没有消息了。
我大哥那时已忙着写他的杰作《梦游记》。他的坐垫放在南边凉台上,前面摆一张矮桌。古南德拉堂兄每天早晨都来坐一会儿。他对于欣赏的广大的能力,春风般地催助诗歌的萌芽。大哥写了一会儿就把他写的朗诵出来,他对于自己创造的幻象的洪亮笑声,使凉台都震动了起来。
大哥写出来的比他用到定稿上的要多得多,他的诗的灵感是那样地丰富,像过于繁盛的芒果的小花,在春天的芒果林荫下铺下了一层毯子,《梦游记》的撕弃的稿纸,也散掷得满房子都是。如果有人把这些稿纸都保留起来的话,今天真可以当做一篮花朵,来装饰我们的孟加拉文学。
在门边偷听,在屋角偷看,我们曾充分地分享了这个诗筵,它是那样丰盛,那样富余。那时大哥正在才华英发的高峰;从他笔下奔涌出不停的滔滔波浪,形成一股诗的想象、韵律和词句的洪流,以喜悦横溢的胜利的欢歌,来充满泛滥它的两岸。我们能够充分了解《梦游记》吗?但我们在那时候是否必须完全了解才能欣赏它呢?我们也许得不到海洋深处的珍宝——即使我们拿到了又有什么用呢?——但是我们在海岸边狂欢戏水,在它们的冲击之下,我们生命的血液是如何欢乐地涌过每一根血管啊!
我越想到这一时期,就越体会到我们再也没有了所谓的穆杰利斯(孟加拉语,意为不请自来的非正式集会)的东西了。在我们童年的时候,看到了这一个作为前一代特征的密切社交的临终光辉。那时候乡邻的感情是那样地强烈,因此穆杰利斯成了一个需要,而那些在社交场合有所贡献的人,就受过巨大的欢迎。现在人们只为着事务而互相访问,或把它当做社会义务,而不是以穆杰利斯的方式来集会的。他们没有时间,他们中间也没有同样的亲密关系!我们从前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交往,纷纭的谈话和断续的笑声,使得屋里和凉台上显得多么欢畅啊!我们祖先能成为团体和集会的中心,能创始和保持活泼有趣的闲谈,这种才能现在都消失了。人们还是来来往往,但这些同一的房子和凉台却显得空虚而荒凉了。
在那些日子里,每一件事物从器具到宴会,都是为多数人的享用而设计的。因此无论这些东西是多么豪华精致,也没有一点傲慢的意味。这些附属品,从那时以后在数量上是增加了,但是它们已变得无情,也不了解那能使贵贱一致地感到宾至如归的艺术。那些赤裸的和衣衫褴褛的人,不能只凭着笑脸的魅力,而必须得到许可,才有使用或占据它们的权利。我们今天在盖房子或设计家具时候,所想要亲近的人们,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社会和它的宽泛的款待。我们的毛病是,我们抛弃了我们原有的东西,但是我们没有在欧洲标准上面重建新东西的办法,结果我们的家庭生活就寂寞寡欢了。我们仍为事务和政治的目的而聚会,但从不纯为彼此见面而聚会了。我们不再想出机会,只为着热爱我们的同胞,而把人们聚集起来。我想象不出还有比社交上的鄙吝更丑恶的东西了,当我回忆到这些人从心底发出的朗朗笑声,使我们减轻了俗务的负担,他们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客人了。
(选自《图本泰戈尔回忆录》,冰心译,湖南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