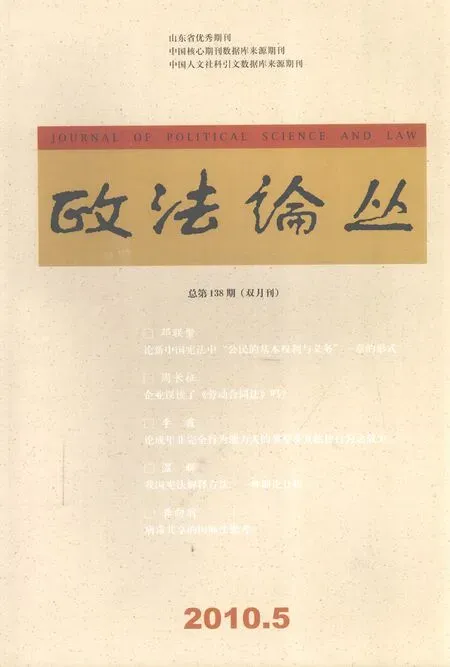使用人责任相关问题探讨*
姚 辉 梁展欣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2)
一、使用人责任的基本界定
使用人责任,是指用人单位(使用人)应对其工作人员(被使用人)因执行工作任务而造成他人损害的行为承担侵权责任。
(一)使用人责任的性质
使用人责任,是法律根据使用关系,使使用人为他人(被使用人)实施的侵权行为承担侵权责任,是一种特殊侵权行为(责任)。使用人虽非侵权行为的实施者,却依法律的特别规定而承担侵权责任,其责任性质应为自己责任。在我国旧法中,《民法通则》第34条第2款后段、第43、121条都曾被视为系涉及使用人责任的基本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中,如《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法(办)发[1988]6号)第58条、《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1992]22号)第42、45条、《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8、9、13条等,也都涉及到使用人责任。作为自己责任的使用人责任,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存在理由:一是使用关系使使用人获益,因而使用人应对被使用人为其利益而实施的侵权行为负责(报偿理论);二是由于使用关系系使他人依使用人之指示,而非依其本人之意志办事,这对全社会而言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使用人应当通过加强对被使用人的监督和管理,以避免侵权行为的发生,而对因该使用而发生的侵权行为自应负责(危险理论);①三是使用人一般比行为人具有更强大的经济实力,将其直接作为责任人,有利于对被侵权人的救济(有效救济理论)。
应当指出的是,使用人责任不同于法人侵权责任(狭义),虽然两者在性质上均为自己责任,但在前者,使用人作为责任人却非行为人,其系根据法律之特别规定而承担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行为人无须为其侵权行为承担责任;而在后者,法人系以其自己意志实施侵权行为,因而应就该自己行为承担责任,于其中虽有被使用人之一定行为,但该行为被视为法人之行为,被使用人对此无须负责。②在《侵权责任法》中,第38~40条规定的学校侵权责任,其性质为法人侵权责任,系采取过错责任原则,学校只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即第40条中规定的“相应的”)责任。这不是关于使用人责任的规定,但在适用上与使用人责任存在一定的竞合关系。许多学者将使用人责任称为替代责任、转承责任或者代负责任,至少在向被侵权人承担责任的方面,是极容易引起误解的。《侵权责任法》对于在使用人承担责任的情况下,行为人是否亦为责任人的问题,未做明确规定。③有学者认为该项责任应为单独责任,即在使用人应依此承担责任的情况下,被使用人无须对其侵权行为承担责任。④但更多的学者则认为,被使用人应当对其侵权行为与使用人承担连带责任,只不过前后两者的请求权基础各不相同。[1]《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9条第1款则以被使用人实施侵权行为系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为条件,与使用人承担连带责任,许多学者对此表示赞同。⑤对此问题,笔者倾向于从自己责任出发,使用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4条第1款规定承担责任,行为人则根据其侵权行为的性质依一般侵权行为或者其他特殊侵权行为的规定承担责任。使用人和行为人系依不同的请求权基础,各自向被侵权人承担责任,因而其责任之间的关系应为不真正连带责任。
(二)使用人责任的构成
成立使用人责任,必须具备如下构成要件:
1.实施侵权行为的行为人须为被使用人。使用,是指依他人之指示从事一定劳务,加入他人之组织并受他人之监督、管理。在传统民法上,一般将使用限于雇用,同时又将雇用人责任类推适用于其他使用的情形。在我国法上,较少使用“雇用”字眼,劳动关系则是最常见的使用关系,是指通过一方为另一方提供非自主性有偿劳动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非自主性的标志是劳动者的人身依附性。[2]但是,使用人责任中的使用关系,不限于劳动关系,是否存在使用关系,原则上应从客观上进行判断,即只要存在事实上的指示与服从、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的,一般可予认定。至于该使用关系有无订立劳动合同等关系之证明、营利抑或非营利、有偿抑或无偿、一时抑或继续等,均非所问。使用人的范围,不限于法人或者企业法人,还包括非法人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以及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⑥如果行为人在实施侵权行为时,使用关系已经消灭的,不发生使用人责任。存在多重使用的,则须视第二被使用人是否系在使用人的指示、监督——不一定是直接的指示、监督,也可能是通过第一被使用人的指示、监督——下执行工作任务,而令使用人对第二被使用人实施的侵权行为承担使用人责任。
2.该侵权行为须系行为人因执行工作任务而实施。“因执行工作任务”是认定使用人责任的关键要件。对此,学说上有三种观点:一是使用人意思说,即执行工作任务系依以使用人的指示办理的事务为范围,超出该范围的,不属于执行工作任务;二是行为人意思说,即行为人系执行使用人所指示办理事务,或者为执行该事务中使用人的利益的,均属于执行工作任务;三是行为外观说,即从行为的外观可以认为行为人系执行工作任务的,不问使用人及行为人的意思如何,就可予认定。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主张采取行为外观说,[3]P190-191王利明教授亦采此说。[4]P144-145但也有学者认为,行为外观说在实务上虽称简便,但该项认定究属法律上之价值判断,含有政策上之考虑,不能纯从外观上加以认定。既然行为人之行为与使用人所委办之事务具有内在关联,则使用人对其中的危险可得预见,事先亦可加防范,并可通过计算其可能的损害而内化于经营成本,予以分散。为此,“因执行工作任务”应解释为因一切与使用人所委办之事务具有通常合理关联的事项。此为内在关联说。[5]P432-433笔者认为,应当区分该侵权行为发生的领域,发生在交易领域的,采取行为外观说较为便宜;发生在非交易领域的,则应采取内在关联说(此点详后)。
3.须具备构成侵权行为之其他要件。使用人承担使用人责任的前提,是行为人所实施的侵权行为须为独立的构成。如果就该侵权行为,行为人自己无须承担侵权责任的,则使用人亦无须承担侵权责任,此为使用人责任附从于行为人责任的一面。详言之,就行为人的方面,不问其是适用过错责任抑或无过错责任,只要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如具有故意或者过失、造成他人的损害、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相当因果关系、行为具有违法性等)的,即应承担侵权责任;就使用人的方面,不问其对行为人所实施的侵权行为有无过错,在行为人应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况下,其即应承担使用人责任。可见,使用人责任的性质为无过错责任。但在有关立法例上,由于各国和地区民法对使用人责任采取不同的归责原则,因而在确定使用人的免责事由、举证责任以及对被侵权人的救济方式等问题上,又呈现出不同的理路。
二、使用人责任的归责原则
对于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4条第1款规定的使用人责任所采取的归责原则,立法例上存在不同的模式,学说上也有很大争议。
(一)使用人责任归责原则的立法模式
在有关立法例上,关于使用人责任的归责原则,计有以下三种模式:
1.过错责任模式。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该法第831条第1款规定:“选任他人执行事务的人,对他人在执行事务时给第三人不法造成的损害,负有赔偿的义务。雇用人在选任受雇人时,或其应购置设备或工具器械或应督导事务执行的,在购置或督导时,尽交易中必要之注意的,或损害即使在尽此种注意时仍会发生的,不发生赔偿的义务。”《瑞士债务法》第55条、《日本民法典》第715条的规定,与此相同。在德国法上,雇用人仅在选任受雇人时,或其应购置设备或工具器械或应督导事务执行的,在购置或督导时,未尽到交易中必要之注意义务,或者如果雇用人尽到此种注意义务损害则不会发生的情形下,才承担本项责任。既然强调雇用人的过错,本项责任的性质为自己责任;唯其过错,系推定而非确定的,雇用人可以通过举证证明其具有上述免责事由而免责。据说该条规定在制定时是为顾及家庭及小型企业的负担能力,而对于法国法的无过错责任模式,则认其乃基于一种功利思想,与德国人的法意识相去甚远。[5]P420但在实务上,雇用人通过举证而免责的案例非常鲜见。
2.无过错责任模式。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该法第1384条第1款规定:“任何人不仅对因自己的行为造成的损害负赔偿责任,而且对应由其负责之人的行为或由其照管之物造成的损害负赔偿责任。”第5款规定:“主人与雇主,对其家庭佣人与受雇人在履行他们受雇的职责中造成的损害,负赔偿责任。”《意大利民法典》第2049条的规定,与此相同。法国学者旧说系采取与上述德国法相同的过错(推定)责任,认为雇用人由于没有挑选好受雇人,没有很好地监督受雇人的活动,因而有过错,但其该项责任可以通过证明其没有过错而推翻。新说则系采取接近于无过错责任的危险责任观点,认为该项责任的根据在于雇用人应对其活动所产生的危险负责。⑦或者认为,此系采一种担保性质的无过失责任,主人与雇主不能证明对其家庭佣人与受雇人的选任及监督,已尽必要注意义务而免责。[5]P418
3.不完全的过错责任模式。以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为代表,该法第188条规定:“受雇人因执行职务,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由雇用人与行为人连带负损害赔偿责任。但选任受雇人及监督其职务之执行,已尽相当之注意或纵加以相当之注意而仍不免发生损害者,雇用人不负赔偿责任。”“如被害人依前项但书之规定,不能受损害赔偿时,法院因其声请,得斟酌雇用人与被害人之经济状况,令雇用人为全部或一部之损害赔偿。”“雇用人赔偿损害时,对于为侵权行为之受雇人,有求偿权。”首先,就责任人的确定,明确雇用人与行为人负连带责任;其次,既然第3项明文规定承担责任的雇用人对受雇人的追偿权,则第1项中的连带责任的性质应为不真正连带责任;⑧再次,对雇用人系采取过错推定责任,即其可以通过举证证明其在选任受雇人及监督其职务之执行已尽相当之注意(否定过错),或纵加以相当之注意而仍不免发生损害(否定因果关系)而免责;最后,对于雇用人经由举证证明其无上述过错而免责,而被侵权人无法获得损害赔偿的,由雇用人承担一定的公平责任。⑨正是基于这最后一个层次,笔者称此为不完全的过错责任。
尽管在立法表述上,上述使用人责任的三种归责模式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同,但从各国和地区的司法实务来看,则存在很大的趋同迹象,学者甚至认为不完全的过错责任模式,只是使用人责任从过错责任(过错推定责任)模式向无过错责任模式转变的中间形态而已。在采取过错责任模式的司法实务中,很少出现使用人可以通过证明其无过错而免责,这在结果上与无过错责任模式是相同的。同时,仔细分析起来,所谓使用人在选任、指示、监督上的过错,与一般侵权行为中的过错并不相同,后者一般是指行为人的过错与加害行为之间具有一种直接的连结;而前者与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行为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连结,因而其强调使用人的过错,目的毋宁只是强调该项责任仍然维持在过错责任的框架之内,但这与一般侵权行为意义上的过错责任已经渐行渐远了。进而言之,即使使用人有选任、指示、监督上的过错,从过责相适应的原理出发,则使用人与被使用人在向被侵权人负责的外部关系上,即应当然发生责任份额的区分问题(《侵权责任法》第12条),但法律上并没有采取这一思路。可见,在使用人责任中,并无特别明显、直接的过错责任依据,必须另辟蹊径找寻其归责基础。
(二)我国法对使用人责任系采取无过错责任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4条第1款关于使用人责任的规定,系采取无过错责任,这与《民法通则》第121条、《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8、9条的规定是相一致的。但在解释上,应注意如下方面:
1.使用人作为责任人,其系根据法律的特别规定而承担无过错责任。对于本项责任的归责基础,传统理论多数是从使用人的经济地位(报偿理论、危险理论)或者经济实力(有效救济理论)的角度进行界定。⑩笔者认为,在违法性要件方面,使用人责任的归责基础应为使用人对其组织义务的违反;在因果关系要件方面,系采取事实推定,即只要损害发生在使用范围之内,与使用人的组织失灵具有相当之因果关系,即可予认定。[6]由此出发,在对“因执行工作任务”的认定中,作为有力说的行为外观说或者内在关联说,均可以觅得一席之地。因此,被侵权人向使用人主张本项责任的,无须对使用人在选任、指示、监督被使用人上有过错负举证责任,使用人亦不得通过举证证明其没有上述过错而免责。有法官称本项归责为所谓“责任推定”,认为在本项责任中,“被告必须证明该损害系出于(原文如此,似属赘言——引者注)与被告毫无关系才可,即是属于与被告无关的外在原因、或偶然事故、或不可抗力,始能免责。如果仅仅是证明不可预见、不可避免、原因不明,还不能免责”。[7]P158笔者认为,该观点以违法性阻却来界定所谓“责任推定”,似非所宜。
2.就该侵权行为,行为人与使用人均为责任人,两种责任之间的关系为不真正连带责任。这与《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9条第1款前段规定的“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观点并不相同。至于使用人或者行为人在向被侵权人承担责任后可否相互追偿的问题,《侵权责任法》未予明确。立法原意认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追偿,情况比较复杂。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工种和不同劳动安全条件,其追偿条件应有所不同。哪些因过错、哪些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可以追偿,本法难以做出一般规定。用人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对追偿问题发生争议的,宜由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根据具体情况处理。”⑪笔者认为,为防止使用人将经营风险转嫁给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作人员,应当允许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一定的自由裁量;法律上对该项追偿权不做一律规定,是合适的。这与《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9条第1款后段规定的“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的观点,并不相同。
在我国目前的规范体系中,《侵权责任法》第34条第1款是使用人责任的概括条款,特别规范主要有:(1)同法第34条第2款关于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为被派遣的工作人员的行为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2)同法第35条前段关于接受劳务一方为提供劳务一方的行为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3)同法第54、57、62、63条关于医疗机构为其医务人员的过错行为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4)《民法通则》第121条关于国家机关对其工作人员的侵权行为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5)《物权法》第21条第2款关于登记机构对其工作人员造成登记错误的侵权行为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6)《律师法》第54条关于律师事务所对其律师的过错行为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7)《公证法》第43条第1款关于公证机构对其公证员的过错行为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等等。其中,第(5)、(6)、(7)项均规定了承担责任的使用人向行为人的追偿权,则系其于其各自的工作人员均系专业人士,因而赋予这些专业人士以更高程度的注意义务。
三、对“因执行工作任务”的认定
前已述及,学说上对于“因执行工作任务”的认定,主要经历了从使用人意思说、行为人意思说、行为外观说到内在关联说的发展。内在关联说对行为外观说的超越在于,强调该项认定并非一项单纯事实的认定,而是一项法律上之价值判断。这在法律技术上,与相当因果关系理论中相当性的认定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但在一定程度上却模糊了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之间的界线。笔者认为,当侵权行为发生在交易领域的,采取行为外观说较为便宜;发生在非交易领域的,则以采取内在关联说较为妥当。
(一)侵权行为发生在交易领域的,采取行为外观说
在交易领域中,被使用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原则上均得构成“因执行工作任务”。从理路上来分析,旧说中的使用人意思说和行为人意思说,实际上都是从交易领域出发的观点,学说上概括称为一体不可分说,即主张被使用人的加害行为必须与执行工作任务密切联系(即“一体而不可分”),使用人才承担责任。但是,由于一体不可分说往往疏于对被侵权人的保护,行为外观说因此而起,在涵括一体不可分说的保护对象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2]
行为外观说可以分以下三个层次:
首先,从使用人的角度来看,行为人执行工作任务系依其指示办理事项而造成他人损害的,使用人应承担侵权责任(使用人意思说)。
其次,从行为人的角度来看,其行为客观上与其职务相关联,且系为使用人的利益,包括但不限于行为人依使用人之指示而执行工作任务,因此而造成他人损害的,使用人应承担侵权责任(行为人意思说)。
再次,从被侵权人的角度来看,被侵权人一般对行为人系执行工作任务具有外观上的信赖,由使用人对该侵权行为承担侵权责任,正是为了保护这种信赖,这是行为外观说的本来意义。这一保护被侵权人外观信赖的观点,与表见代理制度中对相对人外观信赖的保护(“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法》第49条),是同出一源的。《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9条第2款前段界定的“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以及同款后段界定的“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均系从交易领域进行的界定,解释上应从行为外观说。例如,公交车上的乘客因司机超速驾驶肇事而受伤,乘客因而起诉公交公司要求赔偿。该司机驾驶公交车的行为具有“执行工作任务”的外观,因而不管其超速驾驶是否符合公交公司的意愿,也不管其超速驾驶是否在主观意愿上系为公交公司的利益,乘客都有理由相信其系“执行工作任务”,因而公交公司必须此负责。但是,即使发生交易领域,如果被侵权人具有恶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使用人可以免责。于此情形,系认为被侵权人根本不具有外观信赖,因而不值保护。在上例中,如果该乘客明知该司机为醉酒驾驶而仍然搭乘该车的,应认为系属自甘冒险,公交公司可以因此而免责。
(二)侵权行为发生在非交易领域的,采取内在关联说
在非交易领域中,被使用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则须视其行为与使用人事务是否具有内在关联来确定是否构成“因执行工作任务”。于此情形,由于被侵权人对加害行为不存在“因执行工作任务”的外观信赖,因而行为外观说不当然成立。对此,可以参照《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9条第2款后段在规定雇主责任时,界定为“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第8条第1款在规定包含有法人使用人责任的法人侵权责任(广义)时,则系采取反面规定,该款后段规定:“上述人员实施与职务无关的行为致人损害的,应当由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即界定为“与职务无关”;前后两者应属同解。
就该内在关联的类型,主要有如下情形:
1.工作时间和地点的关联。例如,某公交车司机在本公交公司的修理部擅自修理车辆,期间造成他人损害。又如,某工人在工作场所抽烟,因乱丢烟蒂而造成他人损害。对于上述侵权行为,公交公司和工厂均应承担使用人责任。
2.工作机会的关联。例如,公交公司的修理工利用职务之便,将车辆驶出厂区而肇事的,原则上应承担使用人责任。又如,律师事务所的某见习生在社会上诈称可以代向法官行贿而向当事人索要财物的,则须视该律师事务所对其行为是否赋予机会,如使用事务所的公函等。如赋予机会的,则应当承担使用人责任。
上述内在关联的类型,主要是从保护被侵权人的利益的角度,建立起加害行为与使用人事务的客观的内在关联。但从司法实务的角度来看,对于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如何,往往不能不问。主要有如下情形:
1.禁令行为。使用人对被使用人执行工作任务的行为有明确禁令,而被使用人因违反该禁令而发生侵权行为的,该禁令原则上不构成对使用人的免责事由。如在上例中,公交公司和工厂虽有明令,要求司机不得擅自修理车辆,修理工不得擅自驾驶车辆外出,工人在工作场所不得抽烟,仍不得免责。
2.迂道行为。行为人之迂道行为一般与使用人所提供之工作机会具有内在关联。例如,运输公司要求某司机用汽车将货物从北京运送至广州,某司机乃南京人,遂于途中迂道回南京探亲,从南京往广州途中肇事,运输公司仍应对此承担使用人责任。⑫
3.故意行为。如果行为人所执行的工作任务,在客观上增加其实施侵权行为的危险程度或者可能性的,一般可以认为其行为与使用人事务具有内在关联。反之,则不能认为其行为与使用人事务具有内在关联,使用人对其行为无须承担使用人责任。[8]P258例如,商场的某保安员在商场内发现隐藏多年的杀父凶手,愤而拔刀将其捅死,由于该行为与其保安业务无任何内在关联,该商场对此无须承担使用人责任(至于商场可能依《侵权责任法》第37条因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而承担侵权责任,则另当别论)。
对于被使用人发生在非交易领域的侵权行为,学说上又称为事实的侵权行为,其所保护的非如交易领域中被侵权人对交易外观的信赖,毋宁是有鉴于使用人在其支配领域内出现的危险状态,使使用人对此承担使用人责任。但是,如果行为人之加害行为与其职务不具有内在关联性,则系否定了使用人对被使用人危险支配的可能性,由于该加害行为完全脱离了使用人的支配领域,因而不能成立使用人责任。[9]因此,认定被使用人实施的侵权行为与使用人事务是否具有内在关联,原则上应视其行为造成他人损害之危险性,是否由于该使用关系而有所提高。尤其是对于行为人的故意行为甚至犯罪行为的情形,更应赋予使用人以更高程度的注意义务,从而更好地保护被侵权人的利益。
由于认定行为人的侵权行为系“因执行工作任务”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往往必须依靠法官根据具体案情进行认定,而且,在这一定程度上已经越出了一般认为的侵权行为构成要件乃事实判断的认知,已然进至价值判断的阶段,因而在归因与答责的区分上具有一定的模糊。在《美国代理法重述(第2次)》中,对使用人责任中的“因执行工作任务”进行了如下列举式的界定:(1)受雇执行之职务;(2)受雇人之行为主要发生于执行职务之时间及地点;(3)受雇人系为雇用人提供服务而从事一定行为;(4)在受雇人以故意分割行为加害他人时,该加害行为需雇用人可预期之行为。即使规定得如此“明确”,司法实务上仍然歧见迭出。如在警察追捕犯罪嫌疑人过程中对其实施强奸的案件中,法院认为,雇用人应否承担侵权责任,若取决于将受雇人之加害行为所生之损害视为雇用人之商业成本,则显得突兀而不合理。因为第一,警察代表国家,行为为民主国家对人民最大与最危险之强制权力,此项权力具有滥用的可能性;第二,社会整体因警察权力之使用而受到实质利益,因而此项权力滥用所生之成本,应由社会全体负担。然而,在超声波师对病患为性侵害的案件中,法院认为,引起性侵害之情绪反应,需确实可归咎于与工作有关的事件或条件时,雇用人始需对受雇人之性侵害负责。[10]对上述两种特例,笔者认为,仍然应当从区分侵权行为是否发生在交易领域出发进行分析。上述两例均系发生在交易领域,宜径采行为处观说进行判断。
注释:
① 有学者则认为该理论作为一般性的理论是不成立的,“因雇佣他人导致将风险提高到一个足以成立侵权责任的程度也无法成为论证雇员侵权责任的其他正当性基础。因此主张雇佣他人引发危险的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委托一个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执行事务甚至可以降低风险。某人基于雇主的利益而行为,尚不足以在缺乏其他前提要件时,将其在执行雇主利益时出现的违法行为归责于雇主。此种归责思想的重要性,与就自己过错行为承担侵权责任的归责基础相比,看起来显然弱的多”。参见[奥]库奇奥:《损害赔偿法的重新构建:欧洲经验与欧洲趋势》,朱岩译,载《法学家》2009年第3期。
② 《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8条规定了法人侵权责任(广义,含法人的使用人责任),第9条又规定了雇主(含法人)责任,该二规定在适用范围上有重合。
③ 对此,立法部门的释义也未明确,但从其郑重考虑使用人对行为人的追偿权来看,似系认为使用人对被侵权人所承担的责任系单独责任,使用人在向被侵权人承担责任后,方始发生对行为人的追偿问题。参见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解释与立法背景》,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136-137页。
④ 对此,可参见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第2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页;刘士国:《使用人责任疑难问题探讨》,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陈现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精义与案例解析,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版,第115页。
⑤ 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侵权行为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149页;张新宝:《侵权责任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0页。但是,张教授后来又认为:“雇主在承担替代责任后,对有过错的雇员具有追偿的权利,此为公论。但是,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雇员是否应当与雇主一同承担连带责任,则缺乏共识。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持这种态度,但是其依据和合理性尚待进一步研究和证明。”参见氏著:《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页。
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1992]22号)第45条规定:“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合伙组织雇佣的人员在进行雇佣合同规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造成他人损害的,其雇主是当事人。”
⑦ 参见张民安:《现代法国侵权责任制度研究》(第2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05-206页。法国学者发展出的危险理论,主要包括危险活动理论、危险利益理论、危险物理论以及危险权力理论等。参见该书第120-123页。
⑧ 对于雇用人的该项追偿权,学者通说认为雇用人与受雇人之间无分担责任之问题,应由受雇人负全部赔偿责任。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4页。但另有学者对此提出反思,认为该项追偿权之行使,“应顾及雇用人与受雇人之实际情况(如企业之危险性如何,收入之利益如何,工资是否低廉,劳务是否过度,以及企业设施是否不完备等)而受限制,否则应认为求偿权之滥用”。参见郑玉波著,陈荣隆修订:《民法债编总论》(修订2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0页。对于该项限制,有学者提出应适用过失相抵之原则。参见王泽鉴:《连带侵权债务人内部求偿关系与过失相抵原则之适用》,载氏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1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4-87页。
⑨ 该项公平责任,在比较法上属于特有;司法实务上似乎尚无雇用人通过举证免责的案例,因而“雇用人实际上系负无过错责任”。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2页。
⑩ 最近,有学者提出所谓“支配或重大影响说”,参见尹飞:《为他人行为侵权责任之归责基础》,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5期。不过笔者认为,其基点仍未脱出使用人的经济地位这一传统理论的角度。
⑪ 参见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09年12月22日),载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解释与立法背景》,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352页。
⑫ 学者于此采取行为人意思说,认为雇用人应否承担侵权责任,应视受雇人之行为是否与其职务有内在关联,抑或纯为个人利益而定。参见王泽鉴:《雇用人无过失侵权责任的建立》,载氏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1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据此,王教授认为在上述情形下,雇用人不必承担侵权责任。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40页。
[1]邵建东.论雇主责任[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7年,春季卷.
[2]吴永新.从《劳动合同法》谈劳动关系[EB/OL].北大法律信息网,2010-05-20.
[3]史尚宽.债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4]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侵权行为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5]王泽鉴.侵权行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朱岩.论企业组织责任——企业责任的一个核心类型[J].法学家,2008,3.
[7]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
[8][德]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M](上卷).张新宝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9]刘士国.使用人责任疑难问题探讨[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
[10]陈聪富.受雇人执行职务之行为——1997年台上字第1497号判决评析.侵权归责原则与损害赔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