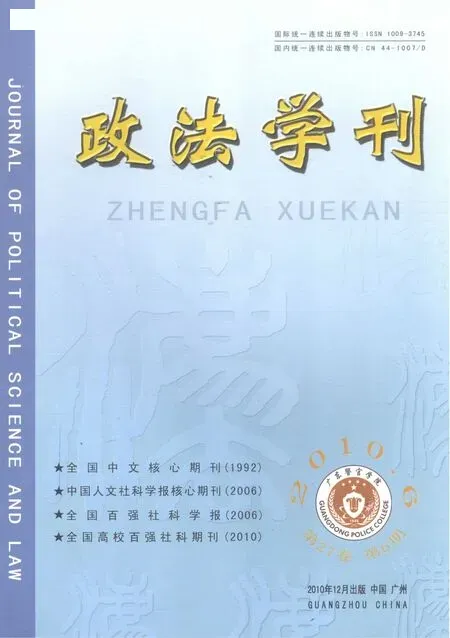李庄案与刑事辩护——考察德国刑事辩护人与被告人的关系
李 倩
(柏林自由大学 法学院,德国 柏林)
2009年底发生的李庄案入选中国“2009年十大影响性诉讼”,引起中国司法界的激烈讨论。该案件就笔者而看,无非就是程序价值和实体价值孰轻孰重,这个法学永恒论题的持续讨论。今天,我们以李庄案为背景,考察德国刑事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与被告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关系问题。
一、辩护关系的范围
刑事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与被告人之间的辩护关系基本上要延长到所有针对犯罪嫌疑人所提起的诉讼上。如果在委托书中没有明确指明辩护关系仅仅存在于某一特别诉讼过程 (比如:上诉审中)或者辩护人仅仅可以实施某一特定行为(比如:阅卷),那么该辩护关系要存在于整个诉讼过程中,直到法院作出有效的判决为止。[1]而整个诉讼过程则包括刑事判决发布之后的刑罚执行,刑事执行程序,以及再审程序。
二、辩护人与被告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关系
(一)辩护人和被告人的关系
在刑事诉讼中,虽然辩护人要依据被告人的利益来进行辩护,但是在整个诉讼过程中,辩护人仍然具有一种独立的地位。只要辩护人认为正确,他可以不根据被告人的指示辩护。因此,辩护人要独自承担其辩护工作的责任。
同样,被告人相对于辩护人而言,其行为也是独立的。被告人可以在尚未和辩护人协商的情况下,自己向法院提出证据申请。被告人可以独立的针对庭审中和庭审前的侦查行为提出自己的意见。被告人可以独立的参与诉讼行为,比如:提起上诉或放弃上诉。甚至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二百九十七条,辩护人不能违背被告人的意愿,提出上诉的要求,即如果被告人表示要放弃上诉,那么辩护人不能向法庭提出上诉的申请。
发现事实真相的义务是律师工作的重要基础之一。辩护人因此没有权利说谎或者建议被告人说谎。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允许辩护人合理的“告知”被告人:如果被告人自己说谎,被告人自身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①LR/Luederssen/Jahn,Vor§137 Rn 133g讨论被告人说谎的自由;他们认为,提供帮助的辩护人在此情况下无论如何不能被判定有罪。,这也是法律所规定的“不得自证其罪”原则的体现。但是我们要注意,这里辩护人的工作仅仅是“告知”被告人,而不是去“建议”被告人在诉讼程序中说谎,辩护人的“建议”行为是不允许的。同样,辩护人不能影响证人,为了委托人的利益而作虚假证词或者故意将证人的证词违背事实真相的与被告人的供述相协调。为了避免辩护人出现违法或犯罪行为,辩护人违背“发现事实真相的义务”的行为要受到两方面的监控。第一,辩护人可能违背德国刑法典第258条,实施“消除刑法的犯罪”。[2]第二,律师法庭可能用严厉的手段惩罚其违背“发现事实真相的义务”,因为辩护人的违背事实真相的行为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如果辩护人对于委托人所告知的事实的“确切性”有所疑虑,但是又不能百分之百的确定,辩护人的上述行为不可受罚。[3]因为法律并没有要求辩护人只能表述其内心十分“确信”的“被告人所告知的案件事实”。通常,允许辩护人信赖委托人所供述的案件事实的真实性。[4]“发现事实真相的义务”并不要求辩护人向刑事追诉机关汇报:刑事追诉机关还未得知的“加重”被告人罪行的有关事实。并且尽管被告人已有“自白”,辩护人仍然可自申请做无罪辩护。
其次,辩护人还要承担“沉默义务”,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律师的“保密义务”。这种保密义务涵盖辩护人由于职务行为而被“信赖”从而获悉或者在职务活动中凭借经验获悉的事项。[5]这种保密义务不仅仅存在于诉讼过程中,而且在诉讼结束之后,辩护人仍然需要承担保密义务。但是辩护人所承担的“保密义务”不是没有限制的。如果辩护人违背德国刑法典第138条“不报告已知的犯罪行为”也可能构成犯罪。对于其所获悉的谋杀和故意杀人行为,辩护人有绝对的报告义务。[5]在其他情况下,根据德国刑法典第139条第3款,如果辩护人已经尽力劝阻被告人不要实施犯罪或者避免犯罪结果的出现,那么辩护人不受刑事处罚。[5]而辩护人是否要告知其所了解的“秘密事实”,辩护人可以对其进行利益衡量。因此,如果辩护人通过被告人可信的“自白”了解到,被告人就是一位谋杀犯,并且另外一位没有责任的人因为该谋杀案已经被宣判,那么辩护人有权利“告知”司法机构该事实。
这里有一个争议,如果辩护人表达的是对于委托人来说是可以“受益的”情况,比如:委托人是限制行为能力或无刑事责任能力,因为患有某种疾病而无行为能力,那么委托人仍然可以为此反对,因为辩护人这种表述仍然有可能使委托人遭受某种不利后果。
(二)辩护人和同案件其他辩护人的关系
如果一个案件存在多名犯罪嫌疑人,他们各自拥有一个辩护人,那么这些辩护人可能有一个共同的“辩护目的”或者仅仅赞同“辩护目的”的某一部分,那么德国法不仅仅允许辩护人之间进行合作,而且,他们可以基于他们各自犯罪嫌疑人的利益来进行协调,以确保实施一个有效的辩护,[6]这在德国也称为“块状辩护Blockverteidigung或者基础辩护Sockelverteidigung”。特别是在共同诉讼中,检控方通常会调派更多的侦查人员来参与案件,因此块状辩护可以很好的平衡辩护方和检控方的关系。[7]从辩护时间和辩护费用上来讲,块状辩护将整体的辩护工作分割成若干部分,益处多多。但是单个的辩护人也要注意,在利益冲突的状况下要以自己委托人的利益为优先。为了确保被告人的个人利益优先得到考量,辩护人如果要实行“块状辩护”必须首先得到委托人的许可,并且在此情况下,每位辩护人都要承担律师执业所要求的“沉默义务”。不同辩护人之间进行基本的信息交流是允许的,并且也允许辩护人之间就其查阅案卷之后了解的案情予以交流探讨。
与教育方面密切相关,19世纪初以来,首先大量出版西学书籍的是教会组织。但从1887年起,由西方人创立的正式出版机构出版了大量政治、科技、史地、宗教、法律等方面的书籍。后者成为维新派思想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在洋务运动中成立的江南制造局等机构出版的科技译著,以及19世纪末成立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促进了新式教育的产生和发展。
(三)辩护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关系
辩护人相比于法院,检察院来说是一个独立的,合法的司法“机构”。[7]应然法下,法院和检察院应当具有中立性,他们不倾向于任何一方当事人,而辩护人并没有这种特征。在辩护过程中,他不必用客观的方法去广泛的调查事实真相,因为他仅仅是要对减轻犯罪嫌疑人罪责的情形施加影响而已。因此我们说,辩护人并不特别受到法院的监管,因此德国法院组织法第177和第178条规定的惩罚措施也不允许针对辩护人施加。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一样,辩护人根据法院组织法第176条的规定要听从法院警察的安排。如果审判长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假定其在没有“独裁”的情况下,认为辩护人的行为存在危害法庭安全与秩序的危险,那么根据法院组织法第176条的规定,审判长可以做出命令,搜查辩护人,但是搜查的方式和方法必须由法官作出命令而予以认可,否则是禁止的。另外,法庭有权利,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38a和138b规定,排除辩护人参与案件,比如:在有重大嫌疑的情况下或者有足够的理由怀疑辩护人参与了刑事诉讼法第138a规定的某一犯罪行为。
三、辩护人的合法行为
联邦律师规则 (BRAO)第43条以下规定了辩护人的职业权。因此辩护人只允许使用符合诉讼程序规定及职业守则的方法来进行辩护工作。根据联邦律师规则 (BRAO)第1条,辩护人作为独立于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的司法机构之一,并没有义务参与“成功实现”以国家名义提起的刑事诉讼。[8]但是法律要求辩护人去发现事实真相和主持正义,并且律师这个职业需要承担对被告人的“保密义务”和“忠诚义务”。因此,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并不需要去证明案件的实质真实(承担证明案件实质真实义务的机关是刑事追诉机关),也就是说被告人在案件中是否有刑事可罚性,对于辩护人来说无关重要。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为了一个“没有责任”的犯罪嫌疑人所作的事情,同样允许辩护人为了一个“真正有责任”的犯罪嫌疑人来实施。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允许辩护人向其委托人多方面解释关于案件的法律情况;他还可以告知其委托人,他从案卷中了解的情况,通常来说,允许辩护人向其委托人出示案卷摘录或者案卷复印件,只要上述行为不会危害侦讯机关的调查行为或者侦讯机关不会担忧诉讼程序遭到滥用;辩护人可以自行调查案件;辩护人可以向委托人指明,其有说谎的权利,但是辩护人不能建议委托人“说谎”。另外,辩护人可以表述对于委托人的怀疑。对于一些减轻被告人罪责的事实,即便辩护人内心尚有疑问但尚未确定,他们仍然可以在法庭上予以表述并展示;并且在法庭上辩护人不需要表达他自己对于这些证据与事实的内心疑问;[9]因为一般来说,除非辩护人有更清楚的认识,辩护人要信赖被告人所告知的那些信息的真实性,[10]这点和中国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有些类似①《刑法》第306条第2款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再次,辩护人可以建议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不要做任何陈述,甚至通过改变“外表” (比如:改变头发的长度)[11]来驳倒检控机关对被告人的刑事指控或者在诉讼程序中采纳合理的手段,督促证人,来督促使其行使拒绝作证权,都是允许的。[12]
四、李庄案审判结果的正当性
(一)中国律师的地位与任务
我国刑诉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因此,对于律师这个概念,现在我国的通说,占主流的观点是:律师不是“辩护人”,而是受犯罪嫌疑人委托“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这点与国际主流学说相悖。在我国,不同于德国的观点,律师可能是基于委托成为辩护人,也可能是基于法院的指定成为辩护人,但该辩护人的权利并不象民事法律上的代理一样,单纯来源于委托人,刑事辩护律师根据律师法、刑事诉讼法享有自己的职业特权。
(二)李庄案问题
抛开李庄所代理的龚刚模涉黑案件不谈,针对李庄自身案件的审判程序,笔者认为仅仅存在证人及侦讯人员未能出庭作证的问题及一些程序瑕疵。李庄在庭审中曾要求《公诉书》列明的8名证人出庭,笔者认为该申请应该给予准许。公诉人给出的“证人不愿出庭,无法勉强”的答复,在法律条文与相关司法解释中找不到任何法律依据。另外,李庄要求对其委托人,即另案被告龚刚模和李庄的助理马晓军进行审讯,也是合情合理的。退一万步的讲,即便另案被告龚刚模不能出庭作证,作为侦办龚刚模案件的公安机关也应派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来确保被告人质询权的实现。
另外,对于媒体报道的有关警方人士提出的“李庄几个方面的违法违规证据”,如果仅仅如官方媒体所报道而言,并且查证属实的话,笔者的观点如下:
1.“向龚刚模宣读同案犯笔录”①案情介绍:据警方调查,李庄在11月24日会见龚刚模时,“将两至三份犯罪嫌疑人的笔录念给龚听”。11月26日会见中,李庄告诉龚刚模,其被指控的一些罪行,“其他嫌疑人在交代材料中并未提到你”。龚刚模在回答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说:“我和李庄第一次见面,他问我,你被刑讯逼供了没有?如果被刑讯逼供的话,上法庭时,你要大声说出来,演示出来,我就要求休庭,这样法庭就开不下去。他说他在辽宁有过案例,那个案子拖了一年半。他说,他有经验。另外,李庄还念了一些同案被告人的笔录,意思是给我讲,我的同案没有咬我。他还告诉我有一个同案犯在逃。”-----辩护人的合法行为,按照德国判例不构成犯罪。
2.“教唆龚刚模翻供,庭审上说不知道”②案情介绍:据警方调查,12月4日,李庄会见龚刚模时教他在一些事情上说不知道,就三个字完了,别的不要多说。-----辩护人的合法行为,按照德国判例不构成犯罪。
3.“唆使龚刚模谎称被刑讯逼供”③案情介绍:李庄三次会见龚刚模,马晓军 (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都作为助手在场。据马晓军的证言,李庄与龚刚模第二次会见时,“李庄说龚刚模你必须说自己被刑讯逼供了,说被吊了8天8夜,吊得大小便失禁,说得越夸张越好,并且还要假装演示刑讯逼供的过程”。但是龚刚模在回答记者“是否曾被刑讯逼供”的问题时,龚刚模说:“没有。”------检察院提供有利证明,龚刚模事后证明自己未被刑讯逼供。虽然在此龚刚模未能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是个程序上的遗憾,但是如果我们“假定”龚刚模的证词是确凿的,并且有另一犯罪嫌疑人龚云飞的证词④案情介绍:龚云飞说:“李庄说,龚刚模的案情很严重,死定了,除非在法庭上翻供,说警察刑讯逼供,‘我已经教了龚刚模翻供’。”“之后,李庄对我和重庆律师吴家友说,龚刚模说警察刑讯逼供需要证据。吴家友干过警察,他去买通几个警察,找几个当事人,说警察刑讯逼供。加以佐证,形成证据链,那么按照德国判例,李庄构成犯罪。
4.“教唆龚刚模配合其扰乱庭审,拖延诉讼”⑤案情介绍:据警方调查发现,在两次会见中,李庄对龚刚模说,他会在开庭时提出休庭,鉴定龚刚模的伤情,“如果法庭不予采纳,我就当庭离开,让法院开不成庭。按规定来说法庭会要求你3天以内另行委托律师,如果不委托法庭就为你指定律师。你要记得一点,坚持只要我给你辩护,法院就开不了庭”。-----按照德国判例,李庄构成犯罪。
根据德国法规定,如果辩护人先前申请过延期审理而被法庭拒绝,并且该案件在被告人缺席的状态下不能被审判,之后如果辩护人建议被告人“不要出席庭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辩护人符合德国刑法典第258条“消除刑法的犯罪”规定的客观行为构成。这里,辩护人的行为从客观角度讲,“违背事实真相”的行为给刑事追诉机关检控犯罪造成了负担。[13]但是德国刑法典第258条还要求辩护人主观上有犯罪的故意 (帮助另一人逃脱刑事起诉的故意)。因此法院在判定德国刑法典第258条的犯罪行为构成要件的时候,并不要求辩护人实现了他原本的犯罪动机,对于辩护人来说,他原本的打算或意图成功实现或者达到了另外一个“更有利于辩护人”的目的即可。Koblenz州高等法院[14]1992年在它的判决中指出,如果辩护人在阅卷之后为了更好的准备刑事诉讼而不愿意接受已经商定好的庭审时间,想阻碍该庭审的进行,那么法院则认为辩护人基本上存在“主观故意的”、“消除刑法的犯罪”行为。借鉴该案件,我们考察李庄案,可以得出结论,李庄构成犯罪。
5.警方透露,调查中了解到,在11月24日“李庄明确告诉龚刚模,把故意杀人案的起因和动机推给樊奇杭”。-----按照德国判例,李庄构成犯罪。该行为,属于辩护人明显的建议被告人作虚假证词的行为,尽管按照德国法,辩护人可以向委托人指明,其有说谎的权利,但是辩护人这种建议被告人说谎的行为是明令禁止的。因此李庄可以定罪。
6.据警方调查,李庄会见龚刚模时要求龚刚模与其妻串证。①案情介绍:李庄在12月4日会见龚刚模时曾说:“我想让你老婆出庭给你作个证,证明你不是黑社会。你要配合她说。”事后,龚刚模案件的另一犯罪嫌疑人龚云飞也说:“李庄对其说过,要龚刚模的妻子作伪证,说他们是长期被黑社会欺压的人。”-----按照德国判例,李庄不构成犯罪。分析如下:
联邦最高法院曾判决,辩护人不能要求证人作伪证。[15]德国司法实践中,不允许辩护人“故意”加强证人作伪证的意图;不允许辩护人建议其委托人即被告人找一些证人作伪证。问题是,司法实践中很难恰当区分无罪的“犯罪预备”和可罚的“犯罪未遂”。德国法院曾作出过以下的判决:
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15],辩护人转交其委托人的“书面要求”给证人要求其作虚假供述,这种行为尚处于辩护人无罪的“犯罪预备”阶段。
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表明:如果辩护人想办法促使证人为了委托人即被告人的利益而宣誓作虚假证词并且因此造成检察院立即展开对证人的询问,那么此时要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38a条排除辩护人参与辩护。[16]
不莱梅州高等法院曾作出判决,辩护人“操纵”一名证人作伪证,作证即属于德国刑法典第258 条消除刑法的犯罪。[17]
如果辩护人让一个做了充分准备打算作伪证的证人“出庭”作证即属于德国刑法典第258条消除刑法的犯罪,具有可罚性。[18]
辩护人向其委托人转告那些由于危害刑事调查目的而应当保密的信息,属于辩护人触犯德国刑法典第258条消除刑法的犯罪,具有可罚性。[19]
杜瑟尔多夫州高等法院判决认为,辩护人和证人协商,证人仅仅是“允诺”作伪证尚未实施,辩护人不属于德国刑法典第258条消除刑法的犯罪的,不可罚。[20]
如果辩护人尚没有“成功的”影响一名证人,让其为了被告人的利益而作伪证,那么辩护人不属于德国刑法典第258条规定的消除刑法的犯罪。[21]
据此,李庄案中,即便有证据明示李庄的确有此“明确示意”,要求龚刚模与其妻串证,但是龚刚模案件尚未审理,龚刚模的妻子尚未“成功”的在龚刚模案件中出庭作证,那么按照德国判例,李庄不构成犯罪。
另外,如果辩护人要求证人:为了不再其后的诉讼中给被告人作损害其利益的证词,向侦讯机关主张一个并没有存在的证人与被告人之间的订婚关系,那么辩护人有罪,具有可罚性。[21]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有利的意见和材料,维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所以说,中国律师的责任不仅仅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律师更要依法办事。因此,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批捕李庄,证据完全充分,刑事立案完全合法恰当。李庄教唆被告人翻供,将罪行推给同案其他被告人,这是典型的伪造证据。对李庄进行刑事立案,有被告人的供述和揭发,还有其他证人所说的情况相以印证。
(三)李庄案审判结果的正当性
排除政治因素不谈,笔者实在觉得当下学者没有必要抓住李庄案诉讼程序上面的瑕疵不放,因为这些诉讼程序上的瑕疵,李庄,作为一个刑事辩护的律师,了然于胸。诚然,如李庄所言,如果法庭在审理该案件时可以按照刑事诉讼既定的“司法程序”规则处理,案件结果可能不同,但是我们要知道,该案件毕竟发生在中国,不是欧美。中国既有的司法审判规则诚然要运用到李庄这个案子上。我们实在不需要大动干戈去讨论它。不是说,现在因为重庆打黑,我们为了避开风口浪尖,避开媒体的疯狂讨论,那么既有的审判规则就不能运用到审判实践中。当然我们也要意识到,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刑诉案件中的被告人定罪,都是证人一律不出庭作证,按照口供定案。甚至那些据称是“刑讯逼供”的案件,侦讯人员也不会出庭来证明自己的无辜。法庭这样审判,违背了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直接原则,并且庭审中被告人的质询权不能得到保障,可那又如何呢?我们必经打击了犯罪行为,达到了实体的真实。笔者不相信,如果今天中国法庭判定李庄无罪释放,社会各界会作何反响?难道是老百姓欢心鼓舞,和专家学者同庆程序价值的胜利;各个媒体在争相报道之际,专家学者又出来讨论,讨论法院程序和实体孰轻孰重。笔者认为,如果真的到了那个时候,专家们又会说,在法治建设不完备的中国,一味追求程序价值是不必要的,我们还是要考量实体价值,不能放松对于犯罪的打击。总之,笔者认为,李庄案件本身就是一个“法治化进程中”中国的缩影,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做出判决,都不会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因为在该案件中,中国刑事诉讼司法审判中的“程序”问题以及法治文化的脆弱,恒久存在;而法院对“法律价值”的衡量,也是一个永恒话题。
[1]Pfeifer,Vor § §137-149 Rn 2;Meyer-Grossner,Vor§137 Rn 5.
[2]Dahs,Rn 43.
[3]BGH NStZ 1993,79,80;Mueller,NStZ 1997,221,222.
[4]BGH NJW 1985,1154.
[5]Peters,Strafprozess,4.Aufl.,Heidelberg 1985,S.241.
[6]Richter,NJW 1993,2152;Eckhart,Mueller,StV 2001,649.
[7]BVerfGE 38,105,119.
[8]BGH 53,257;NJW 09,2690.
[9]BGH NStZ 1993,79,80;Müller,NStZ 1997,221,222.
[10]BGH NJW 1985,1154.
[11]OLG Karlsruhr StV 1991,519.
[12]BGHSt 10,393;Leipold,StraFo 1998,79.
[13]BGHSt 2,377.
[14]OLG Koblenz NStZ 1992,146,147.
[15]BGHSt 31,10.
[16]BGH NStZ 1983,503.
[17]OLG Bremen,NJW 1982,2711.
[18]KG JR 1984,250.
[19]KG NStZ 1983,556.
[20]OLG Düsseldorf NJW 1998,84.
[21]OLG Ko¨ln StV 2003,15 ff.
——读岳南的《那时的先生1940-1946 中国文化的根在李庄》
——李庄古镇代表性应用图案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