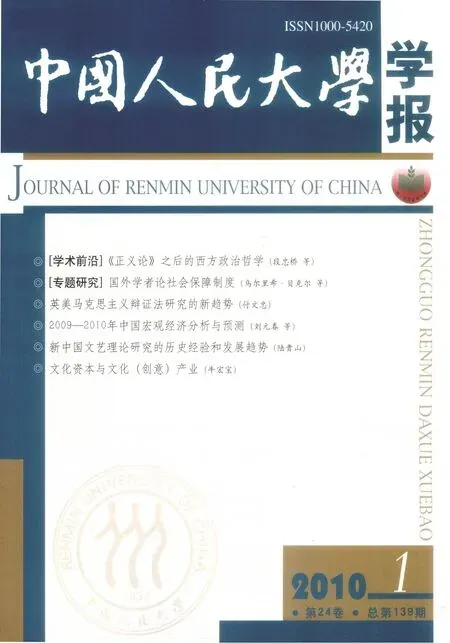科学哲学视野中的福柯研究
刘永谋
福柯深受法国科学史传统的影响,在知识、科学的哲学反思方面硕果累累,并且对后世科学哲学尤其是另类科学哲学的研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说福柯是一位科学哲学家并不为过。但是,在正统科学哲学背景下,福柯并没有引起科学哲学界的重视。大体上说,福柯思想“侵入”科学哲学领域是在20世纪80年代,是另类科学哲学兴起的标志之一。科学哲学界发现福柯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不能忽视对福柯科学哲学的研究。
一、法国科学史传统中的福柯
福柯是从科学史尤其是精神病学史、医学史开始其哲学思考的,他最早的著作《精神病和人格》(1954)和博士学位论文(1961),以及重要著作《词与物》、《临床医学的诞生》等,均属于科学史方面的研究。福柯承认法国科学史传统对自己的影响。福柯哲学彰显了法国科学史研究的特色。
(一)福柯对康吉兰、巴什拉思想的继承
福柯直接承接了法国科学史传统,这集中表现在他对康吉兰、巴什拉思想的继承上。
康吉兰曾是福柯的“研究导师”,对福柯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福柯阅读过康吉兰所有的作品,还给其《正常和病理》一书写过长篇序言。福柯在给康吉兰的一封信中写道:“假若我那时没有看过您的著作,我肯定不会完成以后的研究。(我的研究)内容打上您的思想的印记。”[1](P20)康吉兰的“概念史”理论以及对规范在科学及其历史中的地位的强调,对福柯著作产生了直接和强大的影响。康吉兰认为,科学史并不是对科学发现的简单描述,而是内在联系的理论模式和概念工具的转变历程。他特别关注意识形态与合理性之间的关系,对科学发现的过程、谬误在认知过程中的作用以及“真理”概念等感兴趣。这些都影响了福柯,集中体现在《精神病与人格》、《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词与物》当中。
巴什拉在索邦大学的教席是由康吉兰接替的,巴什拉对福柯的影响与康吉兰有关。康吉兰一生都是沿着巴什拉开辟的道路去思考科学实践问题的,只是他更注重生命科学,而不是巴什拉感兴趣的物理学。巴什拉的科学哲学观尤其是科学发展观是福柯的思想渊源之一。福柯曾说,当学生的时候,所有在世的当代哲学家的著作中他读得最多的是巴什拉的著作。[2](P60)巴什拉特别强调想象在科学中的作用,对诗人有关水、火、土、气的想象进行了详细分析。他认为,想象和理性二者相互补充,是一种辩证的和谐关系。巴什拉认为,合理性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并以不连续方式不断发生变化。他反对总体合理性,坚持认为只有“局部的哲学”才能分析现代科学的复杂性。巴什拉反对“虚假的连续性”,主张科学是不断探索、犹豫和惊异的过程,不断克服精神本身的障碍、无知与错误。这些思想都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福柯的考古学中,比如《疯癫与文明》中“愚人船”的意象显然受到巴什拉《水与梦》的影响。可以说,福柯的科学观在许多重要的方面都“神似”巴什拉。
(二)被忽视的法国科学史传统
沿着巴什拉再往前追溯,可以看到,实际上法国科学哲学一直延续着独特的传统和脉络,区别于英美主流科学哲学的分析传统。人们一般把科学哲学追溯到孔德的实证主义,孔德之后实证主义的中心很快就转移到法国之外,比如第二代实证主义的领军人物马赫主要是在奥地利尤其是维也纳大学活动,他直接影响了以卡尔纳普为代表的“维也纳学派”的形成。20世纪20、30年代,维也纳无疑是正统科学哲学的中心。再晚一些的波普也是奥地利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波普、拉卡托斯去了英国,赖欣巴哈、卡尔纳普、费耶阿本德去了美国,库恩、奎因是美国人,主流科学哲学的中心因此转移到英美。但是,孔德之后法国的科学哲学并没有中断,而经迪昂、彭加勒、巴什拉、柯瓦雷、康吉兰到福柯、德勒兹、利奥塔,沿着自己的理路在前进。不过,由于英美传统和大陆传统的隔膜,法国科学哲学一直没有受到主流科学哲学界的重视,这种状况只是到了20世纪末期才逐渐改变。福柯认为,在当代法国哲学中,以巴什拉、柯瓦雷和康吉兰为代表的“知识的、理性的、观念的哲学”形成了与“经验的、感觉的、主体的哲学”分庭抗礼的局面,后者的代表是萨特、梅洛-庞蒂。[3](P449)可见,科学哲学在法国是很重要的,而福柯自认为属于科学史传统。
(三)福柯思想的法国科学史烙印
从总体上看,法国科学哲学传统与英美科学哲学传统有着显著的区别,福柯的科学哲学打上了深深的法国传统的烙印。
首先,法国科学哲学直接表现为科学史传统,注重从科学的实际发展历程中回答科学、真理、理性、意义等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英美科学哲学则有着明显的分析传统,注重用逻辑分析来解决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德的实证主义是某种社会通史理论。他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要经过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段,实证主义是科学阶段的意识形态——这是一种“大历史”观。孔德之后,法国的科学哲学家们一直都非常重视科学史的研究,从历史中引发哲学沉思。所以,在法国科学哲学传统中,不存在一个类似主流传统中历史主义转型的问题,逻辑分析在法国科学哲学中一直没有占据主导位置。福柯的著作相当一部分属于精神病学、医学、生物学、经济学和语言学等学科的科学史研究。
其次,与英美科学哲学相比,法国科学哲学具有更浓厚的反认识论科学主义的、非理性的气质。法国人对科学的推崇更多的是出于科学改造世界的实践力量,而不是把科学视为逻辑严密、绝对无误的真理。这一点在孔德那里体现得很明显,表现为承自圣西门的技治主义倾向。彭加勒以约定主义而著称,把科学理论视为科学家们的自由约定,坚持“科学知识可错论”。迪昂断言科学理论源自哲学家的想象力,认为任何科学定律都不是绝对的,否认判决性实验的存在,并提出了整体主义来说明科学的进步。柯瓦雷认为,科学思想的演化“非常紧密地与超科学的(transscientique)思想,哲学的、形而上学的、宗教的思想相联系”[4],而不是封闭的演进过程。福柯哲学更是主张真理多元论,不同的学科之间并不存在以客观性、科学性划分的等级,实质已经成为某种“反科学”。
再次,科学发展的不连续性一直受到法国科学史家的关注,逻辑实证主义则把科学发展视为向真理连续前进、连续积累的过程。彭加勒的“约定主义”与连续性观念是格格不入的,每一次新的约定实际就是一次科学发展的断裂。巴什拉提出了“认识论的断裂”(Rup ture-épistémologique)理论,反对基于真理观念的科学连续性,强调不连续性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康吉兰继承了不连续性观念,主张科学革命的思想,将其运用于生命科学史的研究中,并在《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中具体研究了科学革命。福柯的“知识型”理论详细描述了文艺复兴以来思想史的两次断裂,把剖析科学不连续性作为知识考古学研究的指导原则。
最后,法国科学哲学研究不局限于作为经典样板的物理学、数学,而是扩展到更广泛的自然科学领域甚至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不局限于自然科学本身,而是穿透科学指向更为一般的哲学问题。孔德的实证哲学对科学的讨论就包括了社会学的反思,莫诺、康吉兰重视生物学、生命科学的反思,德勒兹研究“游牧科学”,巴塔耶的《色情史》分析有关色情的知识史、思想史,福柯、利奥塔反思的对象扩展到全部知识而不限于自然科学。法国科学哲学家之所以不局限于经典的自然科学学科,部分是因为他们的研究目标不完全是为了厘清科学问题比如科学方法,而是有着指向终极关怀的深沉目标。正如福柯所指出的:“在法国,成为关于启蒙的哲学问题之支柱的正是科学史。”[5](P450)孔德就是如此,他把实证主义看做是解放人类的精神力量,而不仅仅是某种完美认知方法。巴什拉的哲学理想是把科学与诗结合来,把科学的进化程度与人类精神的完善程度结合起来考察。福柯的知识研究与他对现代人生存的真实境遇的理解紧密相连,最终要回答“当下的我们(人)是什么”以及“当下的我们(人)是如何成为其所是的”等问题。
总之,福柯哲学可以看做是在法国科学哲学传统演进中的一环,离不开法兰西科学史的肥沃土壤。实际上,无论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应该说几乎所有法国当代哲学家都受到这一科学史传统的影响。
二、福柯对当代科学哲学的影响
福柯逝世后,其思想迅速传播开来,对哲学、社会学、法学和政治学等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福柯思想全面“侵入”科学哲学领域,许多在当代非常活跃的科学哲学流派均从福柯思想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一)科学哲学界“发现”福柯
长期以来,科学哲学史被局限于英美分析哲学传统之内,主线集中于逻辑实证主义兴起及其后对它的各种回应、发展或批判。因此,以法德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哲学对科学的反思长期被排斥于科学哲学研究之外,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舍勒、曼海姆等的知识社会学,法兰克福学派对科技的社会批判理论,法国的科学史以及福柯、利奥塔等的后现代科学哲学一直没有进入主流科学哲学的视野。从更大的背景看,这种状况只是英美哲学与大陆哲学隔膜的一个侧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柯瓦雷到美国讲学,带来了法国科学史研究的某些理念,对库恩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欧陆科学哲学总体上被主流忽视的局面并没有改变,真正的改变到了20世纪70、80年代才开始,90年代欧陆科学哲学的渗入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科学哲学的面貌,使科学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从对科学的辩护转向批判的立场,因而引起了科学家、正统科学哲学家的不满,在世纪末引发了旷日持久的“科学大战”。在中国,情况也是如此,可以说直至今日科学哲学界仍然没有完全接纳欧陆的科学哲学资源。
科学哲学界全面发现福柯,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这种影响可以从SSK(科学知识社会学)、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后殖民主义者、生态主义者以及劳斯对福柯的借鉴和发展中看出。正因如此,福柯才被“科学大战”中的科学卫士们点名批评,与SSK、后SSK、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后殖民主义者、生态主义者以及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利奥塔、德勒兹、拉康、库恩、费耶阿本德和罗蒂等一起被视为“科学的敌人”。
(二)对SSK、后SSK的影响
以SSK和后SSK为代表的科学的社会建构主义都是试图用社会建构论取代认识论来研究正统科学哲学要解决的科学认识论问题,提出了科学知识实际上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问题,并把其作为理解科学的基点。这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而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福柯把知识生产看成话语形成规则支配下的话语流变和权力斗争的产物,SSK和后SSK把知识生产看成社会建构的结果。实际上,SSK与后SSK的许多研究者都努力从福柯哲学中获取养分,尤其是其知识—权力理论和规训理论。比如,在《实验室生活》中,拉图尔和伍尔伽将福柯的微观权力分析、拉康的精神分析、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与建构主义结合起来,提出“事实的微观社会学”,以分析“事实的社会建构的微观过程”[6](P133),并且评析了巴恩斯对福柯哲学的回应[7](P222)。在《实践的冲撞》中,皮克林尝试用规训理论解读气泡室的建造,并指出“对科学的文化研究”一个重要的方向“实际上是追随了福柯(1979)的思想”,“这一研究方向关注特定的规训和时间对科学文化的特化和构成作用”[8](P262)。皮克林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可以说是福柯谱系学在实验室研究中的发展,与后者相比较,前者更为强调非人类力量的作用,而在福柯那里,人是知识—权力穿透的非本真的人,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非人的”。
(三)对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生态主义科学哲学的影响
在福柯看来,谱系学是对“被压迫的知识”的研究。“被压迫的知识”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长期被人们忽视的、边缘化的历史知识,比如关于疯人、监狱、性、屠杀等的历史知识;还有一类是“一系列被剥夺资格的知识,被认为是不充分或精确的知识:素朴的知识,处在等级体系的下层,在被认可的知识和科学的层面之下”[9](P218),也就是一般被称为“低级知识”、“日常知识”、“地方性知识”、“特殊性知识”的那些知识。福柯呼吁“被压迫的知识的造反运动”,以反对18世纪以来按照客观性进行分级的“知识纪律化”过程,并为“妇女、犯人、新兵、病人和同性恋者”[10](P212)争取解放的运动、“工人自治、环境保护和女权运动”[11](P467)辩护。显然,女性知识、殖民地知识和生态知识都属于“被压迫的知识”,因而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后殖民主义者和生态主义者从福柯哲学尤其是谱系学中吸收营养就很正常了。比如,女性主义者“社会性别”的概念以及对身体的研究,借鉴了福柯的性别社会建构的观点以及身体谱系的观点,并比福柯更为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人们认为男性具有客观、抽象、理性的特征而女性则相反,这不过是代表男性利益的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所谓科学的客观普遍性、价值中立性不过是男性中心主义的一种设想。后殖民主义者赛义德就坦言“东方学”深受福柯的影响,并且认为只有按照福柯的“话语”概念才能把握其“东方学”。[12](P23)
(四)对劳斯的影响
当代美国科学哲学家劳斯主张一种“政治性的科学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1987年出版代表作《知识与权力》集中阐述了他的理论。从书名就可以看出,福柯哲学尤其是谱系学的知识—权力理论对劳斯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劳斯理论可以说是福柯谱系学扩展到自然科学实验室研究的结果。对此,劳斯认为:“实验室微观世界的建构和运用,与前一节讨论的福柯式的权力策略是一一对应的。”[13](P235)
从整个哲学发展形势来看,科学哲学界发现福柯与发现欧陆哲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70、80年代,英美哲学阵营与欧洲大陆哲学阵营正由分立逐渐走向对话、交融。从科学哲学发展史的背景来看,科学哲学界发现福柯与另类科学哲学兴起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把福柯视为另类科学哲学的标志性人物之一。①关于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标志及其基本特征,参见刘大椿、刘永谋:《另类科学哲学的思考》,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3)。20世纪60、7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以1968年“五月风暴”为标志的学生造反运动、反对越南战争的和平运动以及环境保护运动、女权运动、性解放运动、同性恋解放运动等政治运动风起云涌,对西方社会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它们催生出的各种新思想,包括社会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环境保护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对科学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显著的特征就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另类科学哲学的迅速崛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科学哲学界发现了福柯,将其划归另类、非主流、反传统、反科学和后现代的一派。
三、福柯哲学对科学哲学的价值
知识问题尤其是科学问题与权力、伦理问题,是福柯哲学思考的三大基本主题之一。他认为,启蒙实践或现代实践整体隶属于三个大的领域:“对物的控制关系领域,对他人的行为关系领域,对自身关系的领域”[14](P541),这三个领域就对应着知识、权力和伦理三条轴线,“必须对它们的特性和相互关系作分析”[15](P541)。关于知识和科学,福柯提出大量深刻的、独到的见解,形成了一种反主体的后现代知识理论,主要包括知识的话语分析理论、“知识型”理论、知识—权力理论、规训(技术)理论等,彻底颠覆了传统认识论。对此,学界多有阐述,这里不再赘述。我们要讨论的是,福柯哲学在20世纪80年代被科学哲学界发现,从科学哲学史看其价值何在?
(一)“知识型”理论的意义
被谈论最多的是福柯“知识型”理论与库恩“范式”理论的相似之处。没有证据表明两人曾经相互影响,却异曲同工,这是当代哲学史上一桩轶闻。①或许,索绪尔等人开创的结构主义启发两人产生了相似的思想。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序言中,坦言结构主义尤其是皮亚杰的结构主义心理学对自己的影响。而福柯在当时被认为是结构主义在法国的主要践行者之一,尽管他不承认这一点。又或许,柯瓦雷带到美国的法国科学史传统同时启发了两人,而柯瓦雷对库恩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相比较而言,“知识型”理论比“范式”理论的计划更宏大,它要描述的是整个现代西方思想史的转型,而后者的主要目标是分析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革命。但是,“知识型”理论的论证远不如“范式”理论全面和严密,“知识型”理论没有考察数学、物理学等典型自然科学的演变就作出了结论。更重要的是,“知识型”在科学哲学界的影响远比不上“范式”,因此“知识型”理论引入科学哲学最多也不过是强有力地支持了科学革命、科学结构等历史主义的基本信念。这勉强算是福柯科学哲学的价值之一。实际上,科学哲学界发现福柯之时,库恩早已如日中天,历史主义也已发展到新历史主义,因此福柯对科学进行历史研究已经不是新思想了。也就是说,主流科学哲学转向历史主义的过程中,福柯并没有发挥作用。
(二)福柯对科学哲学的创新
福柯对科学哲学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福柯扩展了科学哲学的研究领域。福柯在科技史方面主要研究的是被认为不那么“严格”的自然科学如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性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如犯罪学、经济学、语言学等。在他看来,所有的知识都是平等的,必须要注重研究边缘化的学科。按照他的思路,科学哲学应该是广义的知识论即对知识的哲学探讨,而不仅仅是对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数学的探讨,而应该扩展到整个知识领域。并且,他和巴什拉一样,反对将知识总体合理化的理想,主张微观的、局部的合理化努力——“我们要做的是分析具体的理性,而不是总是引出一般的合理化过程。”[16](P274)也就是说,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知识不能用同一种模式来合理化,而是应该制定不同的标准。这就指出了哲学反思边缘性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乃至非科学知识的基本认识论原则,即多元化、具体化、局部化。总之,福柯提出的边缘化研究方向及其研究原则,值得科学哲学界认真借鉴。
第二,福柯丰富了科学哲学的问题域。逻辑实证主义主要讨论有关现代物理学、数学和逻辑学的认识论问题,典型的比如科学划界问题、意义问题、发现与辩护的问题、判决性实验问题、理论与经验的关系问题,等等。历史主义扩大了科学哲学的问题域,把目光从自然科学内部引向外部,提出科学的动态发展模式、观察的理论负荷、科学共同体等问题。福柯科学哲学引出了许多新问题,比如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知识对人尤其是身体的规训问题、“被压迫的知识”与知识纪律化问题、人文社会科学哲学问题、反主体的知识论问题、反主体的科学编史学问题、真理与理性的历史问题,等等,它们与主流问题大相径庭,丰富了科学哲学的“问题库”。
第三,福柯给科学哲学增添了新的研究方法。相比于科学认识论,考古学是从实践的角度看待知识、科学的,即把它们看做是一种实际展开的历史活动。相比于科学史研究,考古学是从话语角度来看待知识、科学的,即把它们看成按照一定形成规则组成的话语群中的一类。因此,考古学方法不同于传统的科学认识论和科学史研究,值得科学哲学尤其是科学史研究借鉴。谱系学是对考古学的修正。谱系学与考古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后者引入了权力分析方法,破除了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认识论观点。并且,谱系学还包含了完整知识—权力的分析方法,是分析科学与实践关系的有力武器。这两种方法中蕴含着的“解构”精神,提醒我们要与科学保持某种适当的距离,而不是一味地赞美。
第四,福柯实际上提出了科学哲学研究的新目标。传统科学哲学的目标是理解或规范自然科学,而福柯对科学的哲学反思并不仅仅停留在科学之中,而是经由科学指向人类的终极问题。这是前述法国科学哲学的一大特点:不仅仅是“philosophy of science”,同时是“philosophy from science”,即一种由科学研究引发的关于人类最根本问题(比如人是什么)的哲学沉思。这启发科学哲学开掘新的研究范式,即经由科学问题回归一般哲学研究。这种思路必将极大地扩展科学哲学的视野,引发全新的思考,比如科学与当代生活,科学与自由、民主和平等,科学与伦理,科学与个体心理、群体心理,科学与经济危机,科学与社会风险,科学与非西方文化,这些问题都应进入科学哲学的研究范围。
相对于库恩所处的时代,科学哲学研究处于相对衰落的时期,甚至可以说出现了危机或枯竭的迹象。在这种状况下,以福柯为代表的另类思想兴起,新对象、新方法、新问题和新目标的引入,将给科学哲学注入新鲜的理论,创造新的增长点。但是,对于中国科学哲学而言,福柯的“反科学”气质太过激进。当前中国仍然需要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提倡科学方法,培育科学传统。要承认福柯对于科学哲学的重要性,也要对其某些激进结论持保留态度。对待科学,既不能一味辩护,也不能一味批判,而是要理性地、历史地审度。
[1]引自王治河:《福柯》,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2]James E.M iller.The Passion of M ichel Foucault.New Yo rk:Ancho r Books,1993.
[3][5][10][11][14][15]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
[4]柯瓦雷:《科学思想史研究方向与规划》,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1(12)。
[6][7]布鲁尔·拉图尔、史蒂夫·伍尔伽:《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8]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9]福柯:《两个讲座》,载包亚明主编:《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2]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3]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6]L.德赖弗斯、保罗·拉比诺:《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附“福柯的附语:主体与权力”,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
——博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