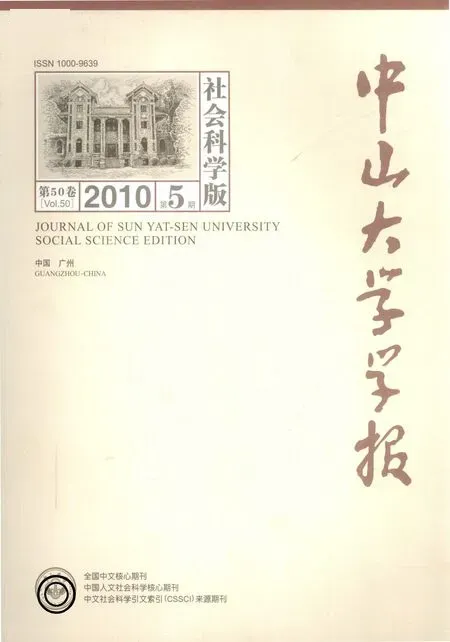王阳明思想世界中的佛教*
李承贵
王阳明思想世界中的佛教*
李承贵
王阳明心学向来被认为具有鲜明的佛禅特色。不过,从“道体”的判断、“著相”的理解、“出家”的评论、“心性”的分析、“儒佛”的定位以及“排佛”策略的提出等角度考察,可见王阳明对佛教诸多教义的理解是失之片面的,王阳明对儒、佛关系的安排是“儒体佛用”的,王阳明应对佛教的策略是抑制、排斥的,而完成这些观念活动的根本依据是儒家的基本观念、基本价值。这一判断将有助于我们对王阳明心学中的佛教与儒学关系进行更完整的理解。
王阳明;佛教;儒学;儒体佛用
“道体”:一抑或二?
在《近思录》中,朱熹断以己意,把周敦颐、张载、二程等涉及“道体”的语录加以编辑,形成了自己关于“道体”的认识。被列入其中的“无极而太极、诚、中、和、心、性、仁、理”等,当属“道体”范畴,而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对于“道体”的描述。比如,讲到“中”,是“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间,亭亭当当、直上直下之正理”①朱熹、吕祖谦撰,严佐之导读:《朱子近思录》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2,34,35,32,33页。;讲到“仁”,是“天体物不遗,犹仁体事而无不在也。‘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无一物而非仁也”②朱熹、吕祖谦撰,严佐之导读:《朱子近思录》卷1,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32,34,35,32,33 页。;讲到“性”,是“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③朱熹、吕祖谦撰,严佐之导读:《朱子近思录》卷1,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32,34,35,32,33 页。。总起来看,则是“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为两段事。洒扫应对是其然,必有所以然”④朱熹、吕祖谦撰,严佐之导读:《朱子近思录》卷1,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32,34,35,32,33 页。,则是“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已具,未应不是先,已应不是后。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叶,皆是一贯”⑤朱熹、吕祖谦撰,严佐之导读:《朱子近思录》卷1,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32,34,35,32,33 页。。朱熹心中的“道体”本末一体、上下贯通、内外兼备,这其实也是所有儒家学者对“道体”性质的理解。由于儒家学者对“道体”结构特性有了基本的定位,因而面对佛教时,很自然地会将佛教放在儒学这面显微镜下加以观察。对此王阳明有没有例外呢?
王阳明的学生王嘉秀曾经说,佛教以出离生死诱人入道,道教以长生久视诱人入道,他们的初衷也不是要人作恶,如果真要刨根问底的话,佛、道二家也见得圣人之学的上一截,所以在极点处,佛、道二家与儒学可以说是略有相同,那与圣人之学相似的上一截,还是不可否定的。对此,王阳明的回答是:
所论大略亦是。但谓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见偏了如此。若论圣人大中至正之道,彻上彻下,只是一贯,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一阴一阳之谓道”,但仁者见之便谓之仁,知者见之便谓之智,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仁智岂可不谓之道?但见得偏了,便有弊病。⑥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8页。
王阳明基本上赞同学生的说法,但同时认为,所谓“上一截”、“下一截”,也是人们主观上的偏见所致而已,因为圣人之学是彻上彻下、一以贯之的,无所谓“上一截”、“下一截”。比如,阴阳交替变化即是“道”,可是,仁者见这个道就叫“仁”,智者见这个道就叫“智”,而老百姓天天实践这个道却不认识它,可见“道”无所谓上下,只是人们认识上的偏颇所致。值得注意的是,王阳明所讲完整而无上下之分的“道”,是圣人之“道”,是儒家大中至正之“道”,而非佛教之“道”。这就意味着,王阳明理论上强调“道”的完整性并不是肯定佛教的“道”是完整的。如下文献即是具体的证据:
——“佛氏着在无善无恶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圣人无善无恶,只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不动于气。然遵王之道,会其有极,便自一循天理,便有个裁成辅相。”①《王阳明全集》,第29,98,146,179,245页。佛教、儒学虽然都主张本体之“无善无恶”,但佛教只就本体上言,本体之外的事情概无兴趣,所以不能治理天下;儒学不仅主张本体之“无善无恶”,其本体之“无善无恶”还要表现为遵循王道,掌握大自然的规律,顺应大自然的实际情形,以开物成务,治理天下百姓。这是说佛教在道体上“本末不一”。
——“吾儒养心,未尝离却事物,只顺其天则自然,就是功夫。释氏却要尽绝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渐入虚寂去了。与世间若无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②《王阳明全集》,第29,98,146,179,245页。佛、儒两家虽然都注重“养心”,但差别甚大。儒家“养心”,不是养空心,而是“著物而养”,也就是顺天道而为,它与现实生活密切关联着,因而儒家的修行是生活中的修行,是有内容的修行。佛教“养心”是离事物而养,是空寂的,它与人间物事毫无关系,所以佛教不可以治天下。这是说佛教在道体上“上下不一”。
——“昨论儒释之异,明道所谓‘敬以直内’则有之,‘义以方外’则未。毕竟连‘敬以直内’亦不是者,已说到八九分矣。”③《王阳明全集》,第29,98,146,179,245 页。对于程颢说佛教有“敬以直内”无“义以方外”,王阳明的回应是“已说到八九分”,为什么只说到“八九分”呢?因为实际上佛教“连‘敬以直内’亦不是”。如此说来,王阳明不仅认为佛教在道体上是“内外不一”,而且连佛教引以自豪的“敬以直内”也“不是”。可是,作这种判断的根据是什么呢?“彼释氏之外人伦,遗物理,而堕于空寂者,固不得谓之明其心矣。”④《王阳明全集》,第29,98,146,179,245 页。在儒学语境中,“心”即理,“心”即人伦物理,所以“尽心”就是穷尽事物之理,“养心”就是即物即事以纯洁心灵;但佛教不是这样,佛教是离却事物而“养心”,是遗弃人伦物理而“尽心”。这是说佛教在道体上“内外不一”。
佛教之所以在“道体”上表现为“本末不一、上下不一、内外不一”,就是因为“遗物事、弃伦理”:“佛、老之空虚,遗弃其人伦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谓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遗也。至宋周、程二家,始复追录孔、颜之宗,而有‘无极而太极’,‘定之以仁义,中正而主静’之说;动亦定,静亦定,无内外,无将迎之论,庶几精一之旨矣。”⑤《王阳明全集》,第29,98,146,179,245 页。在周敦颐、二程那里,“道”并无动静、内外、本末、上下之分,正是因为没有“遗物事、弃伦理”,所以说他们恢复了孔颜精一之学。
可见,王阳明的确认为佛教之道是支离的、断裂的,而他作如此判断的原因是佛教“外人伦,遗物理”;也就是说,他是将儒学的“道即一”(心性之学必须表现为经世致用)观念作为判定佛教道体的根据。可是,本体上的“无善无恶”并非只有落实在末用上才体现出价值,道德上的“养心”并非离开了事物就毫无价值,“内心正直”并非表现在“无意外王”上才有意义,这是其一。其二,就佛教“道体”而言,虽然不像儒学“道体”上下、内外、本末统一,但它有自己的统一,佛教的“道”事实上也是完满自足的,不能因为缺了“人伦物理”,就判定它是断裂的、支离的。因此,王阳明的判断不仅错误地估计了佛教“道”的特质,也显示了其儒学实用主义情结的膨胀。
不著相,还是著了相?
佛教认为,世间所有“相”都是虚妄,但是,凡夫俗子心念执著,意想住相,因而只有做到破执、扫相、无念,才能自心清净,才能见得诸相非相,才能见得如来。所以,“不著相”是建基于佛教“万法皆空”本体观念之上的不住声、色、欲的修为方法和心理状态。王阳明对佛教“不著相”是怎样理解的呢?
先生尝言:“佛氏不著相,其实著了相。吾儒著相,其实不著相。”请问。曰:“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为个君臣、父子、夫妇著了相,便须逃避。如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妇的相?”①《王阳明全集》,第99,70页。
在阳明看来,佛教说它“不著相”,实际上著了相,不仅著了相,而且“著相很深”。为什么?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不仅处于父子、君臣、夫妇等人伦关系之中,而且要为美好的生活打拼、奋斗,如果佛教“不著相”,就应该积极面对并解决这些问题,但恰恰相反,佛教要人们出家离世,逃离父子、君臣、夫妇之伦,逃避生产、生活之苦,放弃对社会的责任。如果不是“著相”,怎么会有这么激烈的反应呢?怎么会有这样消极的行为呢?与佛教比较,儒家反而做到了“不著相”。为什么?因为儒家对君臣、父子、夫妇分别还他以“仁”、还他以“义”、还他以“别”,而且,儒家主张经世致用、利用厚生,积极为美好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而努力奋斗。概言之,儒学并不以生活为累为苦,而是积极勇敢地面对,这就是“不著相”。
如此看来,阳明说佛教“著相”,就是说佛教“身已离心未去”,就是说佛教“心”仍然有住于现世、有住于名利、有住于声色,就是说佛教逃避现世生活,以之为累为苦。阳明说佛教怕苦怕累,真正的深山老林修行究竟是甜还是苦、是轻松还是劳累呢?阳明说佛教不顾世事,放弃责任,远离功名利禄,是“著相”,那么执著于尘世的功名利禄、泡在声色利欲之中是什么呢?佛教所谓“不著相”明明是要求“破执扫相”、“离相无念”,它要破的正是人们对生死的执著,正是人们对功名利禄的执著,怎么在阳明这里变成了“有念”、“住相”呢?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去探求一下阳明判断佛教“著相”的究竟。阳明判佛教为“著相”的根据是佛教害怕尘世之苦之累,从而出家离世,从而放弃了作为一个伦理人的责任;而不以尘世为苦,该工作就工作,该休息就休息,遭遇痛苦不回避,碰上幸福不拒绝,在家尽孝养之责,遵守伦理,正是儒学的处事原则,正是儒学的价值要求。因此,佛教究竟“著相”、“不著相”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佛教的教义、教规、行为是否符合儒家的价值,符合即是“不著相”,不符合便是“著相”。
王阳明对佛教“不著相”的判断,还可以根据他对《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理解来考察:
圣人致知之功至诚无息,其良知之体皦如明镜,略无纤翳。妍媸之来,随物见形,而明镜曾无留染。所谓情顺万事而无情也。无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为非也。明镜之应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处。妍者妍,媸者媸,一过而不留,即是无所住处。②《王阳明全集》,第99,70页。
“良知”好比一面明亮的镜子,晶莹剔透,无论是人还是物,只要来到“良知”面前,美丑自然呈现,但“良知”不曾留下任何痕迹。佛教“无所住而生其心”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明镜照物,美者自美,丑者自丑,没有任何虚假,这就是“生其心处”;明镜照物,美也好,丑也罢,各物自有,不会在镜子上留下任何痕迹,这就是“无所住处”。由此看来,王阳明所理解的“无所住处”,就是像镜子照物那样不留任何痕迹;而“生其心处”,就是像镜子照物那样“物如其故”。
这样,我们可以如是分析:第一,阳明肯定“无所住而生其心”,是在证明“良知”特质情况下发生的,所以不能因此认为阳明支持佛教,而应认为佛教是阳明用于诠释、论证儒家思想的工具。第二,阳明说“无所处”是“一物不留”,注意到佛教不住物、“不著相”之内容,但不是说“无所住”就像镜子照物那样没有任何主体的投入就“一物不留”,因为要做到“无所住”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而是需要主体的努力,比如出家、修行、守戒等。所以,阳明对佛教“无所住”的理解省去了许多“工夫”。第三,在阳明这里,“良知”是本体,“一物不留”与“一照皆真”只是“良知”的功用,这就等于说,“无所住”与“生其心”也被视为“良知”的功用,二者是并行的“用用”关系;而在佛教,“无所住”是体,“生其心”是用,用不离体,体不离用,体用并显,没有“无所住”就没有“生其心”,有什么样的“无所住”就有什么样的“生其心”。第四,阳明说“生其心”就是“一照皆真”。“良知”如同一面镜子,人物美丑,一照自现,这就是“一照皆真”,其所内含的是“良知”的功能和使命;也就是说,“良知”是事功的、“著相”的,如果将“生其心”等同于“良知”的发用,就是暗地里将“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看成是“著相”的。
由此看来,王阳明对佛教“不著相”的判断,虽然为许多人津津乐道,甚至成为某些人贬低佛教思维方式的依据,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它显然是存在误读之处的。之所以如此,在于阳明完全是拿儒家的基本思想、基本价值作为审视佛教的坐标。
出家:修行还是自私?
“出家”是佛教基本教规之一,通俗地讲就是离开家庭到庙宇里去做僧尼;而且,“出家”不是出两片大门之家,而是出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之家,不仅自己出三界之家,还须与众生同出三界之家。可见,“出家”并不是件轻松简单的事,不是“剃发染衣”就“出家”了,它含有牺牲、责任和理想。
王阳明认为,佛教“出家”即是去人伦、遗物理,就是放弃责任。“夫禅之说,弃人伦,遗物理,而要其归极,不可以为天下国家。”①《王阳明全集》,第245,1226,26,809,272页。可是,人伦物理怎么能去得?社会责任怎么能抛弃?所以,王阳明对于“出家”是非常反对的。比如,王阳明曾成功地劝说一位僧人离寺回家:
往来南屏、虎跑诸刹,有禅僧坐关三年,不语不视,先生喝之曰:“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甚么!终日眼睁看甚么!”僧惊起,即开视对语。先生问其家。对曰:“有母在。”问:“起念否?”对曰:“不能不起。”先生即指爱亲本性谕之,僧涕泣谢。明日问之,僧已去矣。②《王阳明全集》,第245,1226,26,809,272页。
对一位修行三年的和尚大声喝斥,责问对方想念不想念自己的母亲,并成功地说服僧人归尘还俗,尽人间责任。不难想像,王阳明对“出家”行为是极不尊重的,而他成功说服僧人的武器是“爱亲本性”,即儒家血亲伦理。王阳明为什么如此痛恨“出家”呢?
第一,佛教“出家”表现的是“自私”品性。“又问:‘释氏于世间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着,似无私心。但外弃人伦,却似未当理。’曰:‘亦只是一统事,都只是成就他一个私己的心。’”③《王阳明全集》,第245,1226,26,809,272 页。王阳明认为,佛教所谓不染世间一切情欲,正是其远离尘世、放弃责任的结果,因而还是“自私”之表现,“外伦理”就是超出伦理之外,不受规范和约束,“遗物事”就是对人间之事毫无兴趣,置之不理;可是,伦理规范是使社会秩序稳定和谐的保障,“物事”是社会中所有人必须面对、处理的任务,因此,“遵守伦理”就是积极面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勤于物事”就是积极地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佛教不愿遵守伦理、不愿勤于物事,而是“出家”以远离俗世,成一己之好,当然是“私己”。王阳明既然认为佛教“出家”是“自私”的行为,其肯定陆九渊以“义利”辨儒、佛的主张自在情理之中。他说:“而象山辩义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后学笃实为己之道,其功亦宁可得而尽诬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实,而概目之以禅学,则诚可冤也已!”④《王阳明全集》,第245,1226,26,809,272 页。佛禅才是“自私”,竟然有人将陆九渊心学等同于“自私”的禅学,当然是对陆九渊心学的最大冤枉;之所以出现这种偏见,可能与某些人分不清儒家“为己”之学与佛教“出家”的差别有关系。王阳明说:
君子之学,为己之学也。为己故必克己,克己则无己。无己者,无我也。世之学者执其自私自利之心,而自任以为为己;漭焉入于隳堕断灭之中,而自任以为无我者,吾见亦多矣。呜呼!自以为有志圣人之学,乃堕于末世佛、老邪僻之见而弗觉,亦可哀也夫!⑤《王阳明全集》,第245,1226,26,809,272 页。
儒家“为己”之学实际上是为公之学,因为它是无己的,这与佛教醉心于修身自好完全不同;而佛教是私己的,也是“无人”的,与君子“为己”之学、无我之学是完全相悖的。第二,佛教“出家”表现为对人性的残害。王阳明说:
人之生,入而父子、夫妇、兄弟,出而君臣、长幼、朋友,岂非顺其性以全其天而已耶?圣人立之以纪纲,行之以礼乐,使天下之过弗及焉者,皆于是乎取中,曰“此天之所以与我,我之所以为性”云耳。不如是,不是以为人,是谓丧其性而失其天。而况于绝父子,屏夫妇,逸而去之耶?吾儒之所谓性与天者,如是而已矣。①《王阳明全集》,第1046—1047页。
人生在世,在家有父子、夫妇、兄弟等亲情伦理,出外则有君臣、长幼、朋友等社群伦理,而且,人生而求美食华服,这都是人之天性。儒家圣人立教,就是使人顺其天性而已,如果不能顺人之性而全人之天,那就是丧失人之天性。可是,佛教要求俗人远离世俗生活,绝父子,弃夫妇,自是背离人之常情;佛教要求僧人衣衲服、吃粗食、喝生水,自是戕杀人的天性。
王阳明对佛教“出家”的定性是“自私”和“害性”。判“出家”为“自私”,因为阳明认为“出家”带来的后果是遗人伦物理、弃人间物事,人伦物理、人间物事这些都是“天下大公”,而“出家”意味着这些全被抛诸脑后;判“出家”为“害性”,因为阳明认为“出家”带来的后果是弃绝君臣、父子、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是去除人追求声、色、欲、味之天性。所谓“人伦物理”就是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为中心的儒家礼制系统;所谓“人间物事”,就是儒家崇尚的立功、立德、立言之“三不朽”,就是开物成务。可以说,判“出家”为“自私”、为“害性”的根据,是儒家的基本观念和基本价值。因此,王阳明对“出家”所持的态度是批评、否定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王阳明对佛教“出家”的理解和判断是正确的。
佛教“出家”的根本原因是基于佛教对世界人生的看法。佛教认为,世间所有的物事都是空幻的,是没有规定的,所谓“缘起性空”,所谓“万法皆幻”,众生因为不能觉悟到这种智慧,才陷于苦痛之中,而要超脱这种苦痛,就必须修行,修行最直接的办法之一就是“出家”。因此,佛教“出家”教规完全出于它的世界观、出于它的人生哲学。这是王阳明所没有涉及到的,如此便可进一步分析王阳明判“出家”为“自私”、为“害性”的不合理性。
就“自私”言,约可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利益上的自私自利,属于伦理学范畴;一是心智上的自私自利,属于心理学范畴。佛教“出家”,不存在利益方面的争夺,因而阳明讲的“自私”只能是后者。就“害性”言,也不能说佛教“出家”完全是为了自己,洁身自好,因为佛教“出家”还有“渡人”的任务,还有“出得三界”的使命,这显然是不能以“自私”来定义的,而佛教“出家”的使命和责任,在今天已由人间佛教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所以,无论在哪个层面上,王阳明判“出家”为“自私”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那么,“出家”能否判为“害性”?如上所言,王阳明讲佛教“出家”残害人性,无非是说,“出家”就弃置了君臣、父子、夫妇等人伦关系,就穿得破旧、吃得粗劣、住得简陋、行得辛苦等。然而,“出家”是一种修行方式,这个行为本身的确是悬置君臣、父子、夫妇等人伦关系的,的确是穿得破旧、吃得粗劣、住得简陋、行得辛苦的。可是,第一,“出家”主要出于个体自愿,它并不会成为君臣、父子、夫妇人伦关系实际上的否弃者,而且,佛教还规劝那些没有“出家”的人们遵守人伦关系。第二,“出家”对人性的完善与提升具有积极作用,人性的完善不能仅仅体现在物质生活、感官欲望上,还应体现在精神生活上,因而不能说“出家”就是残害人性的。第三,从事实上看,佛教“出家”只是对物质生活的淡漠,而不是完全绝去;只是对人伦关系的悬置,并不表示彻底颠覆;而真正的出家人,身体上并无损害,精神上丰富而高尚。所以,王阳明判佛教“出家”是残害人性,也是失之片面的。
心性:“自得”还是空疏?
佛教所言“心”,是菩提心、如来藏心、清静心,也是三界的根源、万法的本体;佛教所言“性”,是本体、本根之“性”,是诸法诸相之“性”,是灵明之“性”,是成佛的根据。佛教认为,自心清净,心即真如,“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反对于“心”外去寻讨、于“心”外去摸索,而应“即心见性”。所以,佛教心、性为一体,它们既是本体又是方法,强调在“自心”中体证、在“自心”中觉悟。王阳明没有专门讨论过佛教心性论,但文字中常有对佛教“心”和“性”的理解和评论。
首先,王阳明认为佛教可算是“自得”之学:
今世学者,皆知宗孔、孟,贱杨、墨,摈释、老,圣人之道,若大明于世。然吾纵而求之,圣人不得而见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爱者乎?其能有若杨氏之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净自守、释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杨、墨、老、释之思哉?彼于圣人之道异,然犹有自得也。①《王阳明全集》,第230,231,257,294,41页。
王阳明告诉我们,他之所以对杨、墨、老、释有所吸取,乃是因为它们有自己独到的东西。墨氏之兼爱、杨氏之为我、老氏之清净自守、释氏之究心性命等,都是这些学派专有的东西。这些学派虽然都是“异端”,但又都是“自得”之学。正因为都是“自得”之学,有其特殊性,所以值得尊敬。阳明说:“居今之时而有学仁义,求性命,外记诵辞章而不为者,虽其陷于杨、墨、老、释之偏,吾犹且以为贤,彼其心犹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后可与之言学圣人之道。某幼不问学,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于老、释。赖天之灵,因有所觉,始乃沿周、程之说求之,而若有得焉。”②《王阳明全集》,第230,231,257,294,41页。一个人如果抛弃了记诵辞章之学,那么即便陷于释、老,它还算“自得”之学;领悟了“自得”之学,就可以继续学习圣人之道;而佛教“自得”之学即是“究心性命”之学。可见,王阳明对佛教心性论是有所了解、有所肯定的。
不过,王阳明并不认为佛教心性理论及其工夫是可以接受的:
夫禅之学与圣人之学,皆求尽其心也,亦相去毫厘耳。圣人之求尽其心也,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吾之父子亲矣,而天下有未亲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君臣义矣,而天下有未义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夫妇别矣,长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别、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一家饱暖逸乐矣,而天下有未饱暖逸乐者焉,其能以亲乎?义乎?别、序、信乎?吾心未尽也;故于是有纪纲政事之设焉,有礼乐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辅相、成己成物,而求尽吾心焉耳。心尽而家以齐,国以治,天下以平。故圣人之学不出乎尽心。禅之学非不以心为说,然其意以为是达道者也,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于其中则亦已矣,而亦岂必屑屑于其外;其外有未当也,则亦岂必屑屑于其中。斯亦其所谓尽心者矣,而不知已陷于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伦,遗物事,以之独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国天下。③《王阳明全集》,第230,231,257,294,41 页。
在阳明看来,佛教与圣人之学都以“求尽显其心”为事,但是,二者是有差别的。圣人之学“尽其心”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就是亲父母还亲他人,否则就是心未尽;为了使“心尽”,圣人之学就有纪纲政事之设、礼乐教化之施,加以裁成辅相、成己成物。佛教尽心与儒学尽心是完全不同的:佛教虽然也以“心”为说,但佛教所谓“尽心”,只停留于“心”而已;佛教认为,不昧于吾心就不错了,怎么还能劳困于“心”外的事情,而“心”外之事又未必相当,难道就一定要劳困于“心”吗?这就是佛教所谓“尽心”,实际上已陷入自私自利之偏。因此,像佛教这样外人伦、遗物事之学,独善其身或许还可以,但要它治家齐国平天下是不可能的。
比如,佛教号称可以使人清心绝欲、求全性命,那为什么它对于当今民众之困苦毫无办法呢?王阳明说:“以为其道能使人清心绝欲,求全性命,以出离生死;又能慈悲普爱,济度群生,去其苦恼而跻之快乐。今灾害日兴,盗贼日炽,财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极。使诚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岂徒息精养气,保全性命?岂徒一身之乐?将天下万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苏息!”④《王阳明全集》,第230,231,257,294,41 页。再如,佛教自称明心见性,但既不见其实地用功,也不见其实际成效。王阳明说:“区区‘格致诚正’之说,是就学者本心日用事为闻,体究践履,实地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积累在,正与空虚顿悟之说相反。”⑤《王阳明全集》,第230,231,257,294,41 页。与儒家“格致诚正”之说比较,佛家“明心见性”就是空疏之学。
概言之,王阳明肯定佛教心性之学是“自得”之学,是独善其身之学,而且,这种“自得”之学对于他进入圣人之学产生过积极作用。但是,他仍然认为,佛教心性之学是空疏而不究实用的,对于齐家治国平天下毫无积极意义。不过,这种理解和判断还是存在很大问题。问题就在于,阳明将佛教心性之学放在现实层面拷问,见的是什么“心”?明的是什么“性”?其中有无“理”?是不是遵守伦理?是不是履行责任?是不是能解决现实中的难题?很遗憾,王阳明没有找到想要的答案。这样,佛教心性之学在阳明的心里就从“自得”之学转变成了“空疏”之学、无用之学。然而,佛教就是佛教,它不能做、也无法做不属于它做的事情,就是说,王阳明从儒家经世致用之学去认识、进而否定佛教心性之学的价值,是以马之用要求牛之体,不符合佛教本身的特质。
毫厘之差,还是天壤之别?
佛教、儒学关系是宋明儒家学者必须面对且必须回答的课题。王阳明自然不能例外:“大抵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①《王阳明全集》,第36,98,98,808,106,257页。“毫厘”之间,也就是一个小小的差别,这个小的差别在哪里呢?请看王阳明的回答。
就“动静”言,佛、儒各有其“动静”,二者的差别在何处呢?这正是王阳明一位学生的疑问:“儒者到三更时分,扫荡胸中思虑,空空静静,与释氏之静只一般,两下皆不用,此时何所分别?”②《王阳明全集》,第36,98,98,808,106,257页。儒者静坐到三更时分,心中便空无一切,与佛教没有了差别。王阳明不同意这个说法:“动静只有一个。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只是存天理,即是如今应事接物的心。如今应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天理,便是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心。故动静只是一个,分别不得。知得动静合一,释氏毫厘差处亦自莫矣。”③《王阳明全集》,第36,98,98,808,106,257 页。王阳明认为,在儒学这里,动也是静,静也是动,动静一体,为什么?因为儒者在静的时候还是应物接事,还是存天理,所以儒学的“动静”是一。换言之,儒学不存在不应事接物的静,不存在空洞的静,而佛教静时没有“天理”,所以是不应事接物,所以是空洞无物,所以它的动静是分离的。这就是儒佛差之毫厘处。
就“觉悟”言,佛、儒各有其“觉悟”,二者有无差别呢?王阳明作了肯定回答:“‘觉悟’之说虽有同于释氏,然释氏之说亦自有同于吾儒,而不害其为异者,惟在于几微毫忽之间而已。”④《王阳明全集》,第36,98,98,808,106,257 页。“觉悟”对于儒学、佛教言,虽有相同,但这并不能掩饰它们的差别。曾有人认为象山的“觉悟”与佛教的“觉悟”没有差别,从而指责象山心学为禅。王阳明回应说,象山之“觉悟”虽然在形式上类似禅宗之“觉悟”,但在内容上仍然是孔孟之学,仍然有“理”,所以不是空虚。从王阳明自己的“觉悟”看,他悟的是“格物致知”之旨,悟的是“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也就是说,王阳明“觉悟”的对象是“理”。因此,在王阳明这里,儒佛在“觉悟”上的差别,就是儒者悟的是“理”,佛教悟的是“空”。
就“养心”而言,佛、儒各有其“养心”,但二者还是不同的。“吾儒养心,未尝离却事物,只顺其天则自然,就是功夫。释氏却要尽绝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渐入虚寂去了。与世间若无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⑤《王阳明全集》,第36,98,98,808,106,257 页。差别就在儒学“养心”,是不离事物而养,是顺天则自然而为,是以治天下为目的;佛教“养心”是离事物而养,把“心”看成幻相,所以陷于空寂。“盖圣人之学无人己,无内外,一天地万物以为心;而禅之学起于自私自利,而未免于内外之分;斯其所以为异也。今之为心性之学者,而果外人伦,遗事物,则诚所谓禅矣;使其未尝外人伦,遗事物,而专以存心养性为事,则固圣门精一之学也,而可谓之禅乎哉!”⑥《王阳明全集》,第36,98,98,808,106,257 页。佛教心性之学“外人伦、遗物事”,儒家心性之学“守人伦、尽物事”,二者的差别还是“理”之有无。
由上可以看出,在动静、觉悟、养心等方面,佛教与儒学存在相似的地方,但差别也是显著的,那就是佛教遗弃物事,没有“理”,不可以治天下。所以,儒学、佛教主要的不是异同问题,而是是非问题:
(郑德夫)问于阳明子曰:“释与儒孰异乎?”阳明子曰:“子无求其异同于儒、释,求其是者而学焉可矣。”曰:“是与非孰辨乎?”曰:“子无求其是非于讲说,求诸心而安焉者是矣。”曰:“心又何以能定是非乎?”曰:“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口之于甘苦也,与易牙同;目之于妍媸也,与离娄同;心之于是非也,与圣人同。其有昧焉者,其心之于道,不能如口之于味、目之于色之诚切也,然后私得而蔽之。子务立其诚而已。子惟虑夫心之于道,不能如口之于味、目之于色之诚切也,而何虑夫甘苦妍媸之无辨也乎?”曰:“然则《五经》之所载、《四书》之所传,其皆无所用乎?”曰:“孰为而无所用乎?是甘苦妍媸之所在也。使无诚心以求之,是谈味论色而已也,又孰纵而得甘苦妍媸之真乎?”①《王阳明全集》,第238—239,1179—1180,106页。
佛儒不在同异,而在是非,但是非由“心”而定,“心”诚而与圣人同。经书只是甘苦妍媸,诚心求之方得其正。在这里,王阳明强调“心”诚是一个人能够真切地识得“道”的根本,“心”诚,甘苦美丑自然呈现于眼前。“心”诚是本体,“心”诚才能辨是非,但“心”有昧的话,就不如口、目来得真切,就是求之经书,也只是谈味论色而已。因此,佛儒之间有同者并不能说明佛教怎么好,有异者也不能说明佛教怎么坏;重要的是观其“是”,察其“非”。这样,“几微毫忽”之间,虽差之毫厘,可能谬以千里。
儒佛之间,不仅有同异,更有是非。在异同、是非之间,究竟怎么安置它们的关系?王阳明提出了“三间共为一厅”的比喻:
说兼取便不是。圣人尽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但后世儒者不见圣学之全,故与二氏成二见耳。譬之厅堂,三间共为一厅,儒者不知皆我所用,见佛氏则割左边一间与之,见老氏则割右边一间与之,而己则自处中间,皆举一而废百也。圣人与天地万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②《王阳明全集》,第238—239,1179—1180,106页。
在阳明看来,圣人之学完备不缺,所以不能说“兼取”佛教、仙家中有益的东西,因为佛教、仙家中有益者,完全可从圣学中推演出来,如在尽性至命中完善此身,即为仙,在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界,即为佛,也就是说,佛教所有的,完全可从儒学中获得,因而无需“兼取”。因此,那种把儒、佛、仙分成一房三厅的观念是错误的,因为这样做就会导致“举一废百”之后果。事实上,只有儒、佛、仙都为儒者所用时,这叫做“大道”。不难看出,在王阳明的观念中,佛教的功能及其效果,完全可以在儒学的展开中实现,因而佛教并没有独立的主体地位。
王阳明甚至认为,仙家之“虚”、佛教之“无”,不能加进儒学的“实”和“有”,如果勉强加入,就会丧失它们的本色。他说:
仙家说到虚,圣人岂能虚上加得一毫实?佛氏说到无,圣人岂能无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说虚,从养生上来;佛氏说无,从出离生死苦海上来:却于本体上加却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虚无的本色了,便于本体有障碍。圣人只是还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在。良知之虚,便是天之太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日月风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虚无形中发用流行,未尝作得天的障碍。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③《王阳明全集》,第238—239,1179—1180,106 页。
“太虚无形”是张载用于批判佛教的概念。在张载看来,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佛教所讲的绝对的“空虚”,即便被人们看成是“空虚”的东西,其实还是“有”(物),这个“有”(物)就是细微的“气”。我们可以说,王阳明以“太虚无形”形容良知,而拒绝等同于佛教的虚无,无非是说,“良知”之为本体,虽有虚无之象,但它仍然是“造化的精灵”,世间所有“貌象形色”之物无不在良知的发用流行中,而且各得其所,然其所然。可见,“良知”之为本体与佛教是有着根本性差别的,而佛教在阳明思想世界中的位置也就一目了然。
修己明道以应对
对于王阳明而言,佛教是不理物事之学,是遗弃伦理之学,是偏执之学,是空疏之学。然而,就是这种违背常理的“异端邪说”,竟然吸引了无数人的心。这不能不让王阳明忧虑。不过,化解这种忧虑还是需要拿出具体的办法来。王阳明非等闲之辈,在应对佛教的挑战上,既继承了前辈儒者的智慧,也有自己的创造发明。
其一,占据阵地。佛教的发展和传播,需要寺庙;儒学的发展和传播,需要学堂。可是,自佛教进入中国之后,传播儒学的学堂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传播佛教的寺庙一个接一个地兴起。真所谓“此消彼长”。这委实让王阳明气愤和担忧。事实上,北宋初年的欧阳修就大力将寺庙改为学堂,随后,李觏、张载、胡宏、张栻都提出过类似主张①李承贵:《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1—3章。。王阳明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极力主张恢复学堂、书院:
夫龟山没,使有若先生者相继讲明其间,龟山之学,邑之人将必有传,岂遂沦入于老佛词章而莫之知!求当时从龟山游不无人矣,使有如华氏者相继修葺之,纵其学未即明,其间必有因迹以求道者,则亦何至沦没于四百年之久!又使其时有司有若高君者,以风励士习为己任,书院将无因而圮,又何至化为浮屠之居而荡为草莽之野!②《王阳明全集》,第898,862,861—862页。
东林书院如果继承了杨时的讲学传统,这里的人们怎么可能陷于佛老词章呢?如果有人像高氏那样以教化百姓为己任,东林书院怎么会成为佛教僧人住宿、传教的场所呢?不难看出,王阳明对儒家书院变成佛教寺庙非常郁闷,因为书院变成了寺庙,不仅意味着儒家学者没有传道的场所,也意味着普通百姓没有学习礼仪制度的场所,更意味着僧人可以随心所欲地传播佛法,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百姓将皈依佛门。这种景象是阳明所不能容忍的,“占据阵地”是其应对佛教的策略之一。
其二,自修其身。怎么样占据阵地?王阳明认为,主体素质的提升是关键:
孟子曰:“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今不皇皇焉自攻其弊,以求明吾夫子之道,而徒以攻二氏为心,亦见其不知本也夫!生复言之,执事以攻二氏为问,而生切切于自攻者,夫岂不喻执事之旨哉?《春秋》之道,责己严而待人恕;吾夫子之训,先自治而后治人也。③《王阳明全集》,第898,862,861—862页。
所谓“经正则庶民兴”,就是把老百姓兴旺的前提归于“经正”,“经正”实际上是要求人正,要求领导者正;所谓“自攻其弊”,就是检讨自己,通过检讨自己,克服自身缺点,发展自身优点;所谓“先自治后治人”,就是强调先把自己的素质提高、完善,才谈得上战胜他人。相反,如果主体素质不高,不仅会陷入异端而不自知,而且还会使好的学说导致坏的结果。王阳明指出:
今夫二氏之说,其始亦非欲以乱天下也;而卒以乱天下,则是为之徒者之罪也。夫子之道,其始固欲以治天下也,而未免于二氏之惑,则亦为之徒者之罪也……今夫夫子之道,过者可以俯而就,不肖者可以企而及,是诚行之万世而无弊矣;然而子夏之后有田子方,子方之后为庄周,子弓之后有荀况,荀况之后为李斯,盖亦不能以无弊,则亦岂吾夫子之道使然哉?故夫善学之,则虽老氏之说无益于天下,而亦可以无害于天下;不善学之,则虽吾夫子之道,而亦不能以无弊也。④《王阳明全集》,第898,862,861—862页。
为什么有人会陷于佛老?就在于人们不能认识佛老的问题出在“专于为己而无意于天下国家”,自己做到仁义就可以了,天下人做得到做不到仁义就不管了,是“置其心于都无较计之地”,致使稀里糊涂地陷于佛老而不自知。就儒学言,由子夏到田子方,由田子方到庄周,由子弓到荀子,由荀子到李斯,儒学名声逐渐变坏,其原因就在于主体素质不高。可见,一种学说有益无益于天下,完全取决于主体善不善于学习,完全取决于主体善不善于应用,完全取决于主体素质之状况。
其三,明了圣道。朱熹曾经说,要战胜佛教,首先要把自家的东西搞明白,如果能把圣人之学搞明白,使其内化于心,佛教是侵袭不进来的。王阳明继承了这一观念:
然则天下之攻异端者,亦先明夫子之道而已耳。夫子之道明,彼将不攻而自破,不然,我以彼为异端,而彼亦将以我为异端,譬之穴中之门鼠,是非孰从而辨之?今夫吾夫子之道,始之于存养慎独之微,而终之以化育参赞之大;行之于日用常行之间,而达之于国家天下之远,人不得焉,不可以为人,而物不得焉,不可以为物,犹之水火菽帛而不可一日缺焉者也。然而异端者,乃至与之抗立而为三,则亦道之不明者之罪矣。道苟不明,苟不过焉,即不及焉。过与不及,皆不得夫中道者也,则亦
异端而已矣。而何以攻彼为哉?①《王阳明全集》,第861,295—296页。
既然异端之产生在于人的识见上的问题,那么一种学说本身价值的消极与积极不在自身,而在主体;而主体对圣人之道的“无明”,才是无法与佛教对抗的根本原因。因此,攻击异端,应该掌握圣人之学,使圣人之学了然于心,使自己的思想得到充实强大,如是,佛教不仅无法侵袭进来,而且将不攻自破。
其四,儒佛优劣。有明一代,信奉佛教者比比皆是,其中也包括高高在上的皇帝,原因在于他们认为佛教有许多优点,有许多让他们着迷的地方。王阳明为了让人们远离佛教,回归圣人之学,不得不对佛教的“缺陷”予以揭露:
夫西方之佛,以释迦为最;中国之圣人,以尧、舜为最。臣请以释迦与尧、舜比而论之。夫世之最所崇慕释迦者,慕尚于脱离生死,超然独存于世。今佛氏之书具载始末,谓释迦住世说法四十余年,寿八十二岁而没,则其寿亦诚可谓高矣;然舜年百有十岁,尧年一百二十岁,其寿比之释迦则又高也。佛能慈悲施舍,不惜头目脑髓以救人之急难,则其仁爱及物,亦诚可谓至矣;然必苦行于雪山,奔走于道路,而后能有所济。若尧、舜则端拱无为,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明峻德,以亲九族”,则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则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则黎民于变时雍;极而至于上下草木鸟兽,无不咸若。其仁爱及物,比之释迦则又至也。佛能方便说法,开悟群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杀,去人之贪,绝人之嗔,其神通妙用,亦诚可谓大矣,然必耳提面诲而后能。若在尧、舜,则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至诚所运,自然不言而信,不动而变,无为而成。盖“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无方而妙用无体,比之释迦则又大也。②《王阳明全集》,第861,295—296页。
佛教虽然也有它的长处,但与圣人之学比较,还是全面落于下风:第一,佛不如尧、舜寿命长,不值得羡慕;第二,在慈爱施舍的方法和内容上,儒学比佛教更高一筹;第三,在觉悟群生、规范众生行为、教化方法和效果等方面,儒学也优胜于佛教。既然佛的寿命不如尧舜,既然佛教施舍方法与内容不如圣人之学,既然在教化民众、觉悟群生方面,佛教并不比圣人之学高明,那么,上至皇帝,下至百姓,还有什么必要皈依佛门呢?
王阳明判佛教“道体”为支离,判佛教“无念”为著相,判佛教“出家”为自私,判佛教“心性”为空疏,并提出了“占据阵地”、“自修其身”、“明了圣道”、“儒长佛短”等一系列抑制、排斥佛教的策略,其佛教之态度已是昭然若揭;在分辨、处理儒学与佛教关系上,王阳明一句“佛儒不在异同,而在是非”,即将佛教降为异端邪说,即便其尚有“自得”之处,还是连占据“一厅”的资格都没有。这些“判定”和“分辨”,呈现了王阳明对佛教义理理解的肤浅和片面。尽管在王阳明心学体系中,似乎处处都可以找到佛教禅宗的印记,以致人们千篇一律而又毫无迟疑地认为,心学是佛教禅宗的藏身之地,阳明心学与佛教禅宗不过半斤八两,然而本文的初步探讨及所显示的问题,或许提醒我们需要有检讨进而纠正俗见的勇气,以求得对阳明心学与佛教关系之完整认识。
【责任编辑:杨海文;责任校对:杨海文,许玉兰】
B248.2
A
1000-9639(2010)05-0130-10
2010—03—04
李承贵(1963—),男,江西万年人,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21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