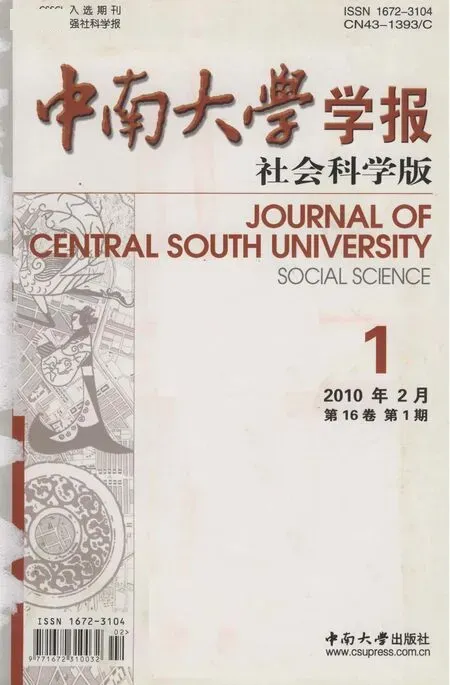“实践存在论美学”的理论实质与思想渊源—对一种反批评意见的初步回答
董学文,陈诚
(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100871;南开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天津,300071)
“实践存在论美学”的理论实质与思想渊源—对一种反批评意见的初步回答
董学文,陈诚
(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100871;南开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天津,300071)
“实践存在论”是近年出现在美学、文艺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本体观。这种本体观曲解和泛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并将其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相等同,由此组合成“实践存在论”。“实践存在论美学”建立在“实践本体论”或“主体性实践哲学”基础上,与西方“实践派”理论和国内“实践美学”有着内在关联,其本质在于以西方存在主义存在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及其历史观。以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具体成果和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突破,是行不通的。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存在论; 实践存在论; 中国化
《中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发表张瑜、刘泽民同志《对美学、文艺学领域实践思想的一系列范畴的再思考》一文。这是近年系列针对笔者的关于“实践存在论美学”讨论和商榷文章①中的一篇。由于该文提出的一些问题,仍是在朱立元同志于《上海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上发表的《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与董学文、陈诚先生商榷之一》一文的范围内,所以,本文主要还是力求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集中对朱立元同志的文章在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理解上的曲解和泛化作进一步辨析,同时,对“实践存在论美学”的理论失误及其思想渊源作初步的探讨。
一、如何科学、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
在《“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本体观辨析——以“实践”与“存在论”关系为中心》一文中,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初步考察和分析,其基本的观点是:马克思所讲的“实践”,是指人的物质劳动和变革世界的实践,既包括最初的本源意义上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的含义,也包括在现实基础上社会活动和革命实践的含义。这里的“实践”,不能也不应理解为包容一切的活动和行为,不能也不应理解为是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道德实践”。[1]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从本源的意义上来说,是指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这构成人类社会起源、存在、发展的基础。从现实的意义上来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是指物质劳动和社会实践,即马克思所说的“客观的”“对象性的”(马克思使用的是同一个词:gegenständliche)的活动。[2](54−55)后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较少使用“实践”一词,比如在《资本论》中,就代之以“生产”“劳动”等概念。
“实践存在论美学”论者则主张,“应当在西方思想史背景下考察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完整内涵”②。这本来没有什么不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确是在整个西方思想史的背景下发展而来的。但问题的关键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西方整个思想史中的“实践”概念有何异同?如果不加区分地全盘接受整个西方思想史的“实践”观念,那么,“实践”概念固然可以获得其所谓“完整内涵”,但是,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就拉开距离了。按照有些“实践存在论美学”论者的思路和设想,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基本上囊括了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经康德到黑格尔、费尔巴哈的所有内涵,而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经典作家对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扬弃与批判置之不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究其原因,无非是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道德伦理”、康德的“实践理性”以及黑格尔的“精神实践”、费尔巴哈的“感性活动”统统纳入“实践”的范畴,并进一步将“实践”与“存在”问题勾连一起,从而为“实践存在论”寻求理论上的支撑和依据。道理很明显,如果单单依靠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是不可能也无法达到“存在论”的层次的。
在“实践存在论美学”论者看来,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区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狭义的“实践”(praxis)主要指的是追求伦理德性与政治公正的行为,而广义的“实践”则还应包括工艺制作(制造)和理论活动在内。并且认为,“在西方思想史上前一种狭义的实践概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更为深远。但是,近代以后,广义的实践概念得到更为广泛的虽然不是十分明显的认同”。这事实上就是承认了“实践”主要应该指狭义的实践概念,而对于广义的实践概念,显然也是接受的。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是与善分不开的,它更是一个伦理学范畴而非现实的物质实践,道德上的至善在他看来是一切行为的准则和目的。亚里士多德说:“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③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实践,一种是他所说的“有界限的实践”,也就是技术活动,他称之为运动;一种是目的性的实践即现实活动。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那种与目的同一的实践才是真正的实践。“那些有界限的实践没有一个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例如减肥,在减肥的时候,那些东西自身就在这样运动中。而不是一些运动所要达到的现存的东西,像这样的活动不是实践或者不是完满的实践,只有那种目的寓于其中的活动才是实践。……这两者之中,一个叫做运动,一个叫做现实活动。一切运动都是不完满的。”[3](209−210)所以,“如果在我们活动的目的中有的是因其自身之故而被当作目的的,我们以别的事物为目的都是为了它,……那么显然就存在着善或最高善”[4](5)。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不是物质劳动和生产实践,根本上是一种道德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表达了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道”即逻各斯,也表达了所谓人的整体性品格。
在对康德“实践”概念的理解上,“实践存在论美学”论者表现出了在康德“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即“道德地实践”)和“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即“技术地实践”)这两者选择上的矛盾。按照康德的规定,这两种实践存在根本的差异,不能混淆,而真正属于本体意义的实践,作为理性存在者的基本方式的实践,乃是“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即“道德地实践”。但是,在“实践存在论美学”论者看来,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工业革命的推动,把实践主要理解为物质性的技术生产的这一“流俗”见解已经相当普遍,以至于需要康德来纠正。[5](109−110)这就令人难以理解,既然现代科技和工业生产意义上的“实践”已经成为“流俗”的见解,需要康德来纠正,那么,论者所说的“实践”只能是康德的“道德地实践”,这样一来,马克思意义上的物质生产劳动,即作为“技术地实践”则只能弃而不顾。因为按照康德的理解,这两种“实践”存在根本差异,是不能混淆的。如果将这两种“实践”不加区分地囫囵吞枣、合为一处而接受,即有些论者所谓的“广义的实践”,那么,其内在的矛盾该如何解决呢?
对于黑格尔的“实践”观念,“实践存在论美学”论者以很大的篇幅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黑格尔更重视被康德所忽视的、视为“流俗”见解的那种人利用工具改造自然的生产劳动实践。并且认为,黑格尔的伟大之处在于并不贬低那种“自然需要”或“感性需要”,即“饥,渴,倦,吃,喝,饱,睡眠”等比较低级的“实践”。由此得出结论,认为“马克思对实践概念的理解,就范围而言,在黑格尔那里已经基本具备了;马克思没有、也不需要另起炉灶,赋予实践概念以全新的、与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再到黑格尔全然不同的、毫无联系的语义”。暂且抛开黑格尔“实践”概念的确切内涵不论,就上述的论述,也再一次暴露出“实践存在论美学”对“实践”理解上的矛盾性。显然,在这种理论看来,对于马克思来说,对实践概念的理解,就范围而言,在黑格尔那里就足够了。这个“范围”就是综合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道德伦理”,康德的“道德地实践”和“技术地实践”,以及黑格尔对康德的“流俗”的“实践”(即“技术地实践”)的认同,外加上黑格尔那种“自然需要”或“感性需要”等比较低级的“实践”。这个“范围”可谓足够大,差不多把西方哲学、美学、文艺理论中所有关于实践的概念都顾及到了。按照一般的常识,一个概念的外延越广,其内涵就越狭窄,当“实践”概念包罗万有、无所不及的时候,其实它也就等于“无”。以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恐怕是不确切、不科学的。
既然“实践存在论”者说马克思对实践概念的理解就其范围而言,在黑格尔那里已经基本具备了,那么,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看一看黑格尔对“实践”概念的理解。
在黑格尔体系中,“有”“无”“存在”“理念”“逻辑”“绝对精神”这样的概念反复出现,含义相似,都意味着本体和存在。绝对精神就是“无”,黑格尔也承认自己的方法是“从无,经过无,到无”。对于一些黑格尔主义者来说,就像马克思引述一位波恩的教授所说的那样,“懂得一点‘无’,却能写‘一切’”[6](40)。这就是黑格尔思辨的精神本体论的实质,本质上是一种唯心论的实践观。这种唯心论的实践观,也正是他的文学、美学本体论思想的实质。黑格尔的文学本体观,立足于精神哲学和纯粹逻辑,在精神的维度上完成自我演绎和自为存在,即恩格斯所说的,“实践的最终目的主要还是穿着哲学的外衣出场”[7](221)。这里的“哲学”,指的就是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所以,“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8](163)。这无疑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实践观。
马克思的文学和美学理论是建立在物质生产和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并伴随着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一道发展。在此过程中,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艺术生产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辩证的解决。而在黑格尔那里,精神本体论也就是他的逻辑方法论,逻辑方法是绝对的、唯一的、最高的,具有无限的力量。如果按照黑格尔的逻辑,“任何一个运动、任何一种生产行为都归结为方法,那么由此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产品和生产、事物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2](140)。这就是黑格尔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从这种形而上学的政治经济学中生发出的艺术生产和艺术实践,就不可能是唯物的艺术生产论和艺术实践观了。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艺术通过摹仿理念和本体得以生成;在黑格尔那里,艺术则是理念本体自身的实现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理念的显现和精神的实践来完成的。黑格尔的文学本体观一刻也没有离开过理念本体的基地,是为他的理念本体服务的。理念构成文学发生发展的本体,也是他的作为科学的美学研究的初始之点。黑格尔使用的是一种哲学本体带动文学本体、文学本体来实践哲学本体这样一种求证方式。虽然黑格尔在一些时候强调外部世界及其运动和实践对文学的意义,但他认为外在世界由心灵产生,而且文学必须抛弃外在世界的制约而退回到理念本身,才能完成真正的存在和本体论建构。所以,他的文学本体论不是建立在现实的物质实践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思辨的形而上学基础上。在黑格尔那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思想和逻辑中完成的,包括外在一切客观现实存在和思维的纯粹形式,当然也包括文学和艺术。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实现的,也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实践的。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出现都是在精神之中,对于实践来说,亦是如此。总而言之,黑格尔所说的一切活动、行为、实践,都只存在于精神领域,精神具有能动的实践功能。
与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不同,也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具有永恒结构的静态的理念本体和实体本体不同,黑格尔的确发展了思维的能动方面。但这种发展却是抽象的唯心主义的发展的,因为显而易见,黑格尔是不知道也不探讨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他所谓的“感性”显现,也只是停留于理念自身的内部,“这种理论不仅和哲学中的唯心论者相吻合,并且像后者一样,最终化为幽灵般的唯物论”[9](4)。黑格尔的这种唯心论,不但应用于文学和艺术,而且德国的“意识形态家”们所说的改造和变革世界的行动,也是通过理念来进行的,亦即“一切都是在纯粹的思想领域发生的”[2](62)。
当哲学家们在纯粹意识中进行对世界的改造和变革的时候,他们就发展了精神的能动的方面,思维的能动作用就落实成为一种“实践”。“马克思仍然认识到黑格尔主体的能动性走得太远,它已经成为物质现实的思辨结构,同时其后果就是丧失了所有外在于主体的客体性。意识与现实之间的统一性发生于思维的内部。存在已经被等同于思维。费尔巴哈第一个认识到主体与思维之间的差异,肯定了涉及主体的客体的外在性。所以马克思利用费尔巴哈的思想去批判黑格尔。”[10](37−38)马克思的唯物论和实践观,刚好形成了对黑格尔的唯心论和唯心实践观的倒转和置换。
但是,与黑格尔相比,“实践存在论美学”论者认为费尔巴哈的实践观“反而有所倒退”,原因在于费尔巴哈的实践观“只是指人的实际的、现实的、自然的生活”。这就奇怪了。上面刚刚肯定黑格尔的“伟大之处”在于并不贬低那种“自然需要”或“感性需要”,即“饥,渴,倦,吃,喝,饱,睡眠”等比较低级的“实践”,这里又否定费尔巴哈关于人的实际的、现实的、自然的生活的实践观。马克思确实对费尔巴哈这种直观的唯物主义进行了批判,认为他对于实践“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2](58),但是比起黑格尔那种抽象地发展了能动性的唯心主义“实践观”、那种将物质现实归结为精神思辨结构的“实践观”,费尔巴哈仍然是有所进步的。所以,马克思才会利用费尔巴哈的思想去扬弃黑格尔。将费尔巴哈的实践观说成是一种“倒退”,去肯定唯心论的实践观,这无疑不能说是一种进步。
二、“实践存在论”文学、美学本体观的理论实质
对于“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本体观来说,关键的理论前提落在对“实践”概念的重新界定上,因为只有将“实践”重新划界,并在某种意义上与“存在”相等同,才能消除“实践存在论”内部的理论矛盾和冲突。于是,“实践存在论美学”论者在对“西方思想史背景”下的“实践”作了一番考察之后,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马克思继承了从亚里士多德到德国古典哲学将“实践”与“理论”作为对应、对立概念的传统,在这一框架中,实践被视作与理论(认识)相对的人的“做”(制作)、行为、行动、生活、活动等,即认识(理论)的应用和实现,以及对现实世界的改变。第二,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对实践作广义的理解和应用,他把物质生产劳动看成实践概念最基本、最基础的含义,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他从来没有将实践的含义仅仅局限于单纯的物质生产劳动。”
这一结论构成“实践存在论”对“实践”范畴理解的基础。关于马克思的实践观,笔者在《“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本体观辨析——以“实践”与“存在论”关系为中心》一文中已经做了一些分析,从前面针对“实践”概念的辨析中也可以看得出来,马克思的实践观,无论如何是不能与“西方思想史背景”下的“实践”概念等同视之的。
“实践存在论美学”论者为何对“实践”概念作毫无顾忌的无限制放大和泛化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不仅将马克思主义物质生产劳动意义上的“实践”(practice),而且将伦理道德、政治公正乃至人的感性存在意义上的“实践”(praxis)全部纳入“实践”的范畴,从而肯定了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的多种意义上的“实践”一词,即所谓“实践”“在最广义上,是人存在表现的全部形式的总称”。这样一来,就在事实上将这种“实践”(praxis)概念人为地植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以生产为核心的社会客观物质活动的实践观的改造和更换。而对于praxis概念,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其与practice之间的异同也存有争议。一般的看法是,praxis更倾向于伦理道德和个人感性存在方面的所谓“实践”,而practice确切说指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意义上的“实践”。
在冯契主编的《哲学大辞典》中,对这两个概念有过初步的比较,指出:“中国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虽曾在早年手稿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著作中,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感性的人的活动即 Praxis(实践),Praxis也确实包括了人类整个生活活动,但马克思在使用Praxis一词的同时,强调劳动、物质生产、经济生活在整个人类社会中的基础地位和决定性的意义,认定物质生产是整个社会生活即社会存在的根本,因而主张把practice(而不是Praxis)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提出‘以使用和制造工具来界定实践的基本含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多使用praxis一词以包罗人们的一切活动,认为‘实践即批判活动,即辩证法,他们离开社会发展规律,用文化、心理的批判,取代物质批判和政治批判,强调注意人的精神改造而不是社会物质生活的进步,抽象地主观地去要求人的个体自由和解放,从而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对。’”[11](1333)
应该说,这种看法是比较符合事实的。那种将practice和praxis混淆一团从而组合成一个最为广义上的超级“实践”概念,不仅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也与整个西方哲学史上的“实践”观念相冲突,是既不科学也不可取的。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强调了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的重要性和基础作用,这构成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真正内涵: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念、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由过去那样做得相反。[12](776)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等同于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的精神实践,正是一种头足倒置的做法。
更值得深思的是,“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实践”观,与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哲学观点有着内在的相似性,或者说,在理论解释的原则上有着内在的同质性。在南斯拉夫“实践派”看来,哲学的出发点应该是praxis而非practice,而人正是“实践”(praxis)的存在物。他们认为,“实践”(practice)“仅指主体变革客体的任何活动,这种活动是可以被异化的。而‘实践’(praxis)则是一个规范概念,它指的是一种人类特有的理想活动,这种活动就是目的本身,并有其基本的价值过程,同时又是其他一切活动形式的批判标准。……也不应把‘实践’(praxis)同劳动和物质生产等同起来。后者属于必需的领域,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必然包括不同的作用、固定的操作、从属关系和等级制度。只有当劳动成为自由的选择,并为个人的自我表现和自我完善提供一种机会时,劳动才成为实践(praxis)”[13](23−24)。
不难看出,南斯拉夫“实践派”关于“实践”(praxis)的观点,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practice)观点是有着根本差异的。南斯拉夫“实践派”明确表示不能将“实践”(praxis)同劳动和物质生产等同起来,事实上也就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生产劳动剔除出了“实践”的范畴。对于“实践存在论美学”来说,虽然它没有那么直白地将物质生产劳动排除出“实践”范围,但就其本质而言,已经毫不费力地将“实践派”的“实践”(praxis)纳入其应有的内涵之中了。
就“实践派”对“实践”内涵的基本解析来看,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物质生产劳动采取的是贬抑的态度,认为那是不自由的,不成为真正的“实践”,而“只有当劳动成为自由的选择,并为个人的自我表现和自我完善提供一种机会时,劳动才成为实践(praxis)”,这事实上是颠倒了唯物史观物质生产劳动和他们所谓的“实践”之间的关系。因为,诚如恩格斯所说的,没有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作为基础,就不可能有国家设施、法的观念、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当然也就不可能有“自由的劳动”并为“个人的自我表现和自我完善提供一种机会”。究其实质,“实践派”是把“实践”范畴与“物质”范畴对立起来,否定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和物质本体论,代之以对所谓“全面的实践活动”的信奉,结果就走向了“实践本体论”。这种做法,也必然得出“正统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即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一般被认为是抽象的、与历史无关的二元论的观点而受到摈弃”[13](4)的结论。“实践存在论”不过是“实践本体论”的换一种说法;“实践本体论”正是“实践存在论”的思想渊源。
对于“实践本体论”和“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本体观来说,反对物质本体论和“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成为其理论发展的动势。“实践存在论美学”论者在引述马克思早期作品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极力求证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不是狭义的、单纯指称物质生产劳动,而是继承了上自亚里士多德、下至德国古典哲学的对实践概念广义使用的传统”的同时,却对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和客观存在性只字不提,只是一味寻求所谓“实践”的“存在论”(本体论)意义。事实上,即便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是首先承认物质世界存在的优先性和客观性的,指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8](92)此外,马克思更明确了“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8](96)的对象性生产活动,而不是像“实践存在论美学”论者所说的那样,对实践概念继续保持了广义的使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还说:“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2](77)这也是比较明确地表述了外部自然界的客观存在性,可视为对“实践本体论”的直接否定。
“实践存在论”的美学、文艺学本体观,事实上是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念无限泛化之后,又在反对主客二元对立的借口下,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存在论转向”。
这里,第一个问题就是“实践”与“存在论”的关系问题。“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具体做法是,先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进行扭曲化、狭隘化,然后将“实践”观念加以泛化,接着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加以比对、结合,最后,生造出所谓的“实践存在论”体系来。对于这种论述,“实践存在论美学”论者认为存在逻辑上的矛盾,事实上是论者本身没能充分和正确的理解。对于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来讲,是无法像“实践存在论美学”论者所说的那样,“从来是广义的”。如果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基础的物质生产劳动意义上的实践概念是“狭隘”的,那其当务之急注定是将它泛化。于是,广义的经过人为泛化的“实践”概念,就“包含了政治、伦理、宗教等人的现实活动,还包括了艺术、审美和科学研究等精神生产劳动”,并进而将“实践”与“存在”“人生在世”等同起来,认为人的存在表现的全部形式、人的整个生活都是实践。并且认为这种“实践存在论美学”并非是将马克思主义美学海德格尔化,而是“海德格尔的上述观点(指关于‘人生在世’的现象学存在论思想——引者注)其实早已在马克思那里以另外一种方式,即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的方式得到了表述”[14](41−42)。将海德格尔关于“人生在世”的存在论观念,人为地植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样一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就自然而然地容纳了存在主义的存在论。这种经过对概念的曲解和泛化之后所生成的理论范畴,不但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歪曲,同时也造成了对海德格尔存在论的误解。
这就牵涉到本文要说的第二个问题,即关于主客二元对立和二元论思维模式问题。对于“实践存在论美学”论者来说,“当代中国美学要实现重大的突破和发展,一个最重要的途径就是要首先突破主客二元对立的单纯认识论思维方式和框架”[15]。这里,隐含着两个问题,一是它认为马克思的实践观在超越二元论思维模式上起码是不够力度的,或者本身就存在二元分立问题,故难以实现“重大的突破和发展”;二是它认为只要实现了“实践”概念的存在论化,超越和冲破二元论思维和二元对立就可以完成了。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实践存在论美学”竭力将“实践”说成是“存在”,并借助于“存在论”来完成对主客二元对立的克服。但是,稍作观察就会发现,既然“实践存在论”中所谓的“实践”已经本然地涵盖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根据“奥卡姆剃刀”定律,即“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的原则,倘若“存在论”维度果真是“实践”概念所固有的,那么“实践存在论”也就仍然是“实践论”。[16]所以,在“实践存在论”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海德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存在论化”之后,势必也就同时完成了对自身的消解。
就“实践存在论”的理论解释来看,其所称的“突破”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是依靠将“实践”进行“存在论化”来完成的。在“实践存在论”看来,“实践与存在揭示着人存在于世的本体论含义,是对近代以来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重要超越。‘人在世界中存在’这个命题是海德格尔针对近代认识论主客二分思维方式无根的缺陷所提出的一个基本本体论(存在论)命题。……人在世界中存在,就意味着在世界中实践;实践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实践与存在都是对人生在世的本体论(存在论)陈述”[15]。至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始终没有达到马克思的实践论的高度”云云,不过是论者所使用的障眼法,其存在论的根基则是一目了然的。退一步来说,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在超越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问题上,仍然有着相当的局限性,当海德格尔确立“此在”在生存论上的优先性,“此在”成为世界的筹划者,也就确立了“此在”的绝对主体性,从而走向了“此在”的形而上学。关于海德格尔“存在论”超越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局限性,我们已经在另外一篇文章[17]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这里也就不再赘述了。
三、怎样以科学的态度和学风来讨论学术问题
在“实践存在论美学”论者的商榷文章中,我们注意到,其开始并没有就事论事地讨论问题,而是一上来就声称“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学风来讨论问题”,将一顶帽子先扣过来,似乎对“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本体观的讨论和质疑,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学风了。我们本着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态度,对“实践存在论”观念的理论实质及其内在逻辑矛盾进行了初步分析,这在该论者看来“称作‘尖锐’已嫌其轻,简直是在‘棒杀’了”。真正的学术问题需要探讨和争鸣,良好的理论氛围应当允许不同的声音,如果稍作讨论就嫌“尖锐”,就称“棒杀”,那么还能有真正的问题讨论吗?况且,真理是无法“棒杀”,也“棒杀”不了的。如果理论缺乏科学性,恐无需“棒杀”,也是在人们的质疑面前立足不稳的。
综观“实践存在论美学”论者的反驳文章,它在对“实践”“实践本体论”“实践唯物主义”等一系列概念范畴的理解与阐释上,都是存在问题的,甚或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的。正是由于论者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采取一种随心所欲的诠释态度,不加证明地将所谓“实践唯物主义”等同于唯物史观,将“实践”概念“存在论化”,这才构成了对经典作家论著的断章取义行为。“实践存在论美学”打着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旗号,完成的却是“去中国化”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消解与置换,此等做法,虽有国际国内的某些环境和语境,但这毕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学风”。
“实践存在论美学”论者对“实践唯物主义”作了极为轻率的理解。事实上,论者并没有对“实践唯物主义”作任何文本上和理论上的辨析,就武断地认为对这一提法语义上的批评“早已被哲学界经过反复、充分的论证所否定”。考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著,其表述是:“[……]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75)这里的“实践的”,是“唯物主义者”的定语和形容词,不是“唯物主义”的定语和形容词,因此,根本就没有是某一种“唯物主义”类型的意思,更没有以“实践”为本体的意思,而是专门用来指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的特征的。那种以“实践”为本体,并走向“实践”的“存在论”之途的理论,倘称之为“实践的唯心主义”或“唯实践主义”,或许更为确切。
将“实践唯物主义”等同于唯物史观,为什么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呢?这是因为,首先“实践唯物主义”的提法,根本是一个生造出来的概念,其本意是取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定,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曲解和误读。这个概念本身在学界引起了很大争议,直到今天,围绕“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的争论仍在继续。这种争论,最终归结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作唯物主义解释还是作唯心主义解释的问题。可见,这个概念并不是得到了“反复、充分的论证”的。假如“实践”真的如同“实践存在论美学”论者说的那样,是包容了诸种精神、心理、审美等在内的广义的“实践”,当这种“实践”走向了观念性的本体论,走向了“实践的唯心主义”,那么,把它再与唯物史观等量齐观,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成立的。用此种标准来批评别人,也是没有多少道理的。
在阐述外在世界不依赖于我们的主观感觉而客观存在时,列宁曾说:“如果颜色仅仅在依存于视网膜时才是感觉,那么,这就是说,光线落到视网膜上才引起颜色的感觉;这就是说,在我们之外,不依赖于我们和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着物质的运动。……这也就是唯物主义:物质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引起感觉。感觉依赖于大脑、神经、视网膜等等,也就是说,依赖于按一定方式组织成的物质。物质的存在不依赖于感觉。物质是第一性的。感觉、思想、意识是按特殊方式组成的物质的高级产物。这就是一般唯物主义的观点,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18](50−51)经典作家总是首先承认物质世界的第一性,在此基础上,才建立起以物质生产实践为核心的社会存在结构。
但是,对于“实践存在论美学”来说,却不是这样。它首先承认的是人的感觉的优先性,不是从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而是从人的个人生存—即所谓的“人生在世”—来解释“存在”问题。这里所说的“人”,不是作为关系性存在的社会的人,而是抽象的、孤立的、个体的人。我们知道,文学创作当然不能仅仅停留于这种的“人”上面,而需要在更为广阔的层面上来把握人,即历史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人。事实上,人不可能是一种孤立的存在物。对个体的人的思考,人的孤独感的发生,恰恰是在社会发达的时代。“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的时代。”[6]存在主义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追求人的飘泊无依的孤独感,它恰是发达的社会关系的一种体现。可见,“实践存在论”对人的个体性“存在”的追求,根本无法脱离人的社会性本质。它将个人性质的“存在”,确定为“实践”“本体”,这不仅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实践观,而且也违背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
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进行人为的泛化,将整个西方有关“实践”概念的所有内涵归于一统,并将它说成被马克思全部“继承”,将“实践”和“存在”概念做轻率的偷换,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论”并举和混合,这就很难说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了。如果这种奇异的结合也看作是“发展”,看作是“中国化”,那就未免太强词夺理,太不负责任了。
马克思主义美学如何中国化,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决非一两篇文章所能说透彻。这里,我们只想提及,“实践存在论美学”承袭的是上世纪50、60年代美学大讨论以后所形成的“实践美学”的遗续。在“实践本体论”和“主体性实践哲学”的理论支撑下,于上世纪80年代形成了“文学主体性”等美学、文艺学思潮,进入到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之后,在“存在论转向”“语言学转向”等西方理论的鼓动和诱惑下,产生了“实践存在论”这样的理论样态。在西方,“存在论转向”“语言学转向”是具有很大诱惑力的哲学和美学命题,构成一种“转向”思维,且具有相当的号召力。但是,从根本上说,它们不同程度的都是在向旧的本体论回归,回到传统的形而上学,甚至回到古希腊以前更为古老的“存在论”。这不是向哲学和美学的明天翘望,而是一种向昨天的昨天之退守。“实践存在论”的美学、文艺学本体观,把西方存在主义方法论引入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和文艺学研究,虽说改换了名头,但理论实质并没有变,它只是“实践本体论”在新的历史条件的一个变种,与早期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美学”是一脉相承的。
早期的“实践美学”或“实践本体论”,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人为地区分为“工具本体”和“心理本体”,并将“心理本体”意义上的“实践”,强调为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性,这就是所谓的“主体性实践哲学”或“人类学本体论美学”。而对于“心理本体”来说,关涉“实践存在论美学”所说的“个人存在”和“人生在世”,即一种“存在”的心理结构或形而上学。此外,本体论具有一元论的特征,双本体或多本体现象的存在,事实上是取消了本体论自身的意义。无论是“工具本体”“心理本体”,还是“历史本体”“人类学本体”,其不加辨析地任意使用“本体”概念,也形成了对“本体论”的威胁和解构。对于“实践存在论美学”来说,当指称“实践与存在都是对人生在世的本体论(存在论)陈述”的时候,那么除非“实践”与“存在”完全同一,否则也同样是取消了本体论的意义。
“实践存在论”的美学、文艺学本体观,事实上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纳入了整个西方的形而上学思辨体系,并与更加古老的“存在论”结构一体,从而便容易走向一种泛逻辑神秘主义,形成对辩证的物质本体论和实践观的抵触与消解。其实,“马克思主义美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绝不是一种抽象的、建立在先验范式基础上的唯心体系。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其出发点还是应当回到历史和现实的维度中来,回到物质本体论的维度中来,回到人的社会存在及关系中来。”[19]“实践存在论美学”恰恰在这里迷失了方向,将原本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范畴的许多“实践”概念,强加给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将原本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物质本体论范畴的存在主义的“存在论”维度,硬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固有内涵。在完成了相关概念范畴的曲解、泛化、通约和置换之后,也就大体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存在论化”,完成了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础的海德格尔化。以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实在是有点说不通的。
注释:
① 对董学文、陈诚《“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本体观辨析——以“实践”与“存在论”关系为中心》一文(载《上海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朱立元同志于该刊第5期回应以《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与董学文、陈诚先生商榷之一》一文。接着,又于《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10期发表了他与刘旭光合写的文章:《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存在论维度——与董学文、陈诚先生商榷之二》。此外,张瑜、刘泽民发表于《中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的《对美学、文艺学领域实践思想的一系列范畴的再思考》一文,也是针对笔者的讨论文章。本文主要回答朱立元同志的第一篇商榷文章。
② 朱立元. 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与董学文、陈诚先生商榷之一. 上海大学学报, 2009, (5). 本文引用该文的出处,不再一一注明。
③ 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 廖申白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在古希腊语里为πράξίς,“是对于可因我们(作为人)的努力而改变的事物的、基于某种善的目的所进行的活动。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著作中,实践区别于制作,是道德的或政治的。道德的实践与行为表达着逻各斯(理性),表达着人作为一种整体的性质(品格)。”——译者注。
[1] 董学文、陈诚. “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本体观辨析——以“实践”与“存在论”关系为中心[J]. 上海大学学报, 2009, (3): 42.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3]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 7卷)[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4]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M]. 廖申白译注.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5] 朱立元. 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8.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9] 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M]. 陆建德, 等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7.
[10] Jorge Larrain.The Concept of Ideology[M]. London: Hutchinson & Co. Ltd, 1979.
[11] 冯契. 哲学大辞典(修订版)[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1.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3] 马尔科维奇, 彼德洛维奇. 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M]. 郑一明, 曲跃厚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4.
[14] 朱立元. 略谈马克思实践观的存在论维度及其美学意义[C]//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11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15] 朱立元. 简论实践存在论美学[J]. 人文杂志, 2006, (3): 76−78.
[16] 汤拥华. 主客二分与实践存在论美学[J]. 人文杂志, 2007, (2): 121.
[17] 董学文, 陈诚. 超越“二元对立”与“存在论”思维模式——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文学、美学本体论[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2009, (3): 1−6.
[18] 列宁选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9] 董学文. “实践存在论美学”的缺陷在哪里?[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2009, (4): 8.
The theoretical essence and ideological source of“practical ontology aesthetics”: Our initial answer to a kind of opposing criticism
DONG Xuewen, CHEN Che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The “practical ontology” is a kind of ontological concept in the research of literature and aesthetics in recent years. This kind of ontological concept misinterprets and extends Marxist practice concept, and then combines the practice category of Marxism with the ontology of Heidegger to construct a new concept. “Practical ontology aesthetics” is based on the “practical ontology” or “subjective practical philosophy”, which is also related to the western“praxis school” and domestic “practical aesthetics”. It’s essence is to use western existential ontology to replace Marxist materialist dialectic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 won’t work neither as a kind of particular sinicization achievement nor as a breakthrough of Marxist aesthetics.
Marxism; practical concept; ontology; “practical ontology”; sinicization
book=16,ebook=85
I0-02
A
1672-3104(2010)01−0005−08
[编辑:苏慧]
2009-12-23
董学文(1945−),男,吉林省吉林市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文学理论和美学.
——围绕《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若干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