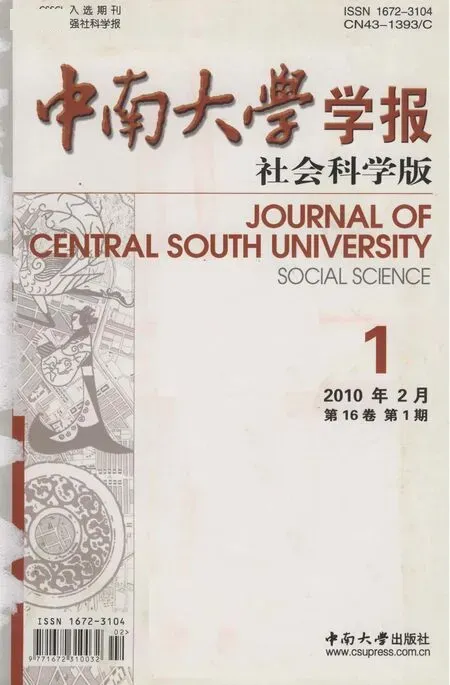中国的大学需要什么样的目的?
——基于克拉克教授《高等教育系统》的思考
钟华明,陈卓
(浙江警察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浙江杭州,310053)
中国的大学需要什么样的目的?
——基于克拉克教授《高等教育系统》的思考
钟华明,陈卓
(浙江警察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浙江杭州,310053)
伯顿·克拉克教授的《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其关于大学目的的思想对于今天中国的大学改革仍具有批判价值与借鉴意义。结合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经验,从大学目的的“自然模糊性”与“追求真理”的关系、大学目的与大学组织的关系、大学目的与大学现实的关系解读大学目的,对今天中国的大学改革不无裨益。
大学目的;“自然模糊性”;大学组织;大学现实
伯顿·克拉克教授的《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以下简称《高等教育系统》)是高等教育学界的经典著作,该书从组织的观点把高等教育系统看作由生产知识的群体构成的学术组织,从高等教育内部揭示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以工作、信念和权力三者为高等教育的基本要素并据以反思高等教育运行的规律,其严谨学风和真知灼见一直为研究者所敬佩和重视,并不断给予今天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以启发。其中关于大学目的的观点,更值得批判借鉴。本文结合近代中国大学的经验,针对当今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梳理从大学目的的“自然模糊性”与“追求真理”的关系、大学目的与大学组织的关系、大学目的与大学现实的关系,就大学目的与克拉克教授作一初步商讨。
本文所说的“大学”是从狭义上说的,不包括独立学院、高等专科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
一、大学目的的“自然模糊性”与“追求真理”的关系
大学目的的“自然模糊性”实际上涉及大学目标系统自身的内部关系问题。
克拉克教授在《高等教育系统》的第一章中就讨论了“知识”,他认为“只要高等教育仍然是正规的组织,它就是控制高深知识和方法的社会机构。它的基本材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各民族中比较深奥的那部分文化的高深思想和有关技能”[1](11)。可见知识对于大学的重要意义。同时,他指出:“由于高等教育的任务既是知识密集型又是知识广博型的,因此很难陈述综合大学和学院的目的,更不必说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的目的了。”[1](18)在克拉克教授看来,一方面,知识很重要,它是“处于行动核心的无形材料”[1](26);另一方面,知识很复杂,所以大学目的似乎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
克拉克教授认为:虽然对于大学而言知识很重要,但类似于“消除无知”之类的目的却是“自然模糊”的,但“这种表述并没有说清楚高等教育为什么(why)、是谁(who)和怎么样(how):学术和教育是为了自身的理由还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学校应该培养统治人才还是训练普通百姓?是应该满足学生的需要还是人力规划的需求,或两者都不是?应不应该传授社会学、工艺学和理发术?对这些课程重点应放在哪里?”[1](18)这段话有待进一步分析。作为一个系统,知识是复杂的,但并不意味着杂乱无章、不可通约,所以维特根斯坦提出了“家族类似”的概念。与其说大学的目的是一个具有“自然模糊性”的东西,倒还不如说它是种“家族类似”,这样更能比较清楚地把握知识系统的内在层次,将差异性(也就是“自然模糊性”)和统一性结合起来。
克拉克教授在书中对大学目的的“自然模糊性”有很精当的论证,很能说明问题。但他只是把不同层次的问题混在了一起,虽然精辟,但不够清晰。他的分析存在一个值得商榷的地方:忽略了复杂知识系统内部的层次性。这种失误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他在界定大学目的时,把目的和原因(why)、措施(how)、职能等混为一谈。这些东西在克拉克教授看来,都是“目的”。其实,如果要用目的一词来统称它们也并无不可,因为根据亚里士多德对目的与手段的相对性的分析,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不是绝对的,在不同的关系层次中,它们可以转换。问题就在于这些要区分出这些不同的层次,而不是把它们混为一谈。克拉克教授恰恰忽视了这一点。
根据克拉克教授所提到的几种关系,可以对“大学目的”这个家族类似进行三个层次的划分。最高层次上的“目的”其实就是大学的“精神”,它的核心就是“追求真理”(也就是克拉克教授所批评的“消除无知”)。对真理的追求是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的共性。学术和教育无论是为了自身的理由,还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学校无论是培养统治人才,还是训练普通百姓;无论是应该满足学生的需要,还是人力规划的需求(或两者都不是);无论是主张还是反对传授社会学、工艺学和理发术:都是在“消除无知”(也就是“追求真理”)这个总目的的统摄下进行的,与这个总目的相比,其他方面都是手段。比这要低一级的层次则是大学的“职能”,它包括“是突出教学,还是强调研究,抑或看重社会服务”这些被克拉克教授作为“目的”讨论的内容。这些职能虽然从不同角度对大学的职能进行了解释,但同时都是以“追求真理”这样一个总的目的为底色的。再低一级的层次则是更为具体的“措施”。“应不应该传授社会学、工艺学和理发术?对这些课程重点应放在哪里?”这样的问题,是对应于不同的职能(教学、研究、服务)而采用的不同的措施。“精神”-“职能”“措施”三者构成三个不同的层次,他们交叠着产生着因果关联。具体地说,对“精神”与“职能”而言,“精神”是目的,“职能”是手段;对“职能”与“措施”而言,“职能”是目的,“措施”是手段。这种层次间的联系与差别是需要弄清的,而克拉克教授则用他所谓的“自然模糊性”进行了笼统的概括。这种概括从局部看无疑是有道理的,但由于他未能对不同层次和类别进行区分,也就难免片面。
虽然知识系统本身很复杂,但在大学领域中,它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呈现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上的“家族类似”。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大学在“职能”和“措施”上各有不同,但它们都是以“追求真理”作为最高也是最终的目的,在这一点上殊途同归。所以说“一个礼仪的、有秩序的社会依赖于人们对真理和公正的概念性理解,而这些理念正是高等教育关注的目标”[2]。时至今日,即使是科尔所概括的复杂多样的“多元巨型大学”也没有偏离这一目标,“虽然受到变革的折磨,但它保持着稳定的自由。虽然它连一个可被认为是自身的灵魂都没有,但它的成员却为真理而献身”[3]。也正是靠着这一点,西方现代大学才得以走过数百年的风雨历程,我们才得以把大学与其他社会组织结构区别开来。
克拉克教授其实看到了知识这个核心的无形材料的重要性,他认为“知识材料,尤其是高深的知识材料,处于任何高等教育系统的目的和实质的核心。不仅历史上如此,不同的社会也同样如此”。[1](12−13)他甚至谈到了“承认这一点是最基本的:各组成单位都有它们自己的目标,这些目标反过来以累积的形式成为规模更大的系统的操作目标”[1](23),但他没能更进一步,或者说没能更上一步,他忽视了“意义是属于感官所接触的世界的,而知识则属于超越感觉的永恒的世界的”[4],所以他没能指出大学目的的统一性,没能说明大学“追求真理”的最终目的,否则他就不会对“消除无知”这一大学最根本的目的进行批评。其实这一目的不仅妥当,而且天经地义。这样的目的固然含糊,但对大学而言,却十分重要。由于有了“消除无知”的目的,大学才不会成为工具,才不至于沦丧到“为政治服务”、“为经济服务”的地步,这一点在确立了“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亚里士多德的归亚里士多德”的观念和秩序的美国也许并不成其为问题,所以克拉克教授没有把它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但在今天的中国,却是头等重要的问题,因而也才是我样应该关注的真问题。例如即使同样是“教育市场化”,在价值判断、目的、制度环境、权力分配等方面,东西方也是有着天壤之别的[5]。
片面强调大学目的的“自然模糊性”而忽视了它的统一性,只能导致大学改革的南辕北辙。今天中国的大学改革运动轰轰烈烈同时又举步维艰,包括北大这样的最高学府也身处改革的旋涡之中,这一方面体现了传统惯性之强大,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大学目的不明确而造成的失误。现在人们公认20世纪初中国大学的起点很高,因为她从一开始就走的是一条正路,她一开始就弄明白了大学的目的究竟为何。这种目的,就体现于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所说的“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6],体现于竺可桢在《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中所说的“大学的最大目标是在蕲求真理,要蕲求真理,必得锻炼思想,使人人能辨别真伪是非”[7]。说白了,一点也不模糊,就是那四个字:“追求真理。”
二、大学目的与大学组织的关系
克拉克教授十分重视组织研究,《高等教育系统》通篇贯穿的都是组织研究的方法,这正是他的一大特色。但是,组织研究并不意味着可以抛开目的、意义、理念、精神等等抽象的东西而不顾,更不意味着可以否定后者在大学中的作用以及对后者进行研究的价值。但是,很遗憾,克拉克教授在这本书中在这一点上做得不是很到位,他表现出了明显的厚此薄彼的倾向,他认为:“那些用全面综合的形式阐述目的或概括高等教育特点的人,是典型地、重复地从错误的端点出发的人。他们从系统的顶端开始,而高等教育更佳的端点是基层。”[1](25)
既然如此,讨论大学目就丧失了意义。克拉克教授认为关于大学目的的各种陈述,“除了它们用现在粗糙的形式帮助指明高等教育的责任主要不在于生产物质产品、保卫国土、提供福利服务、拯救灵魂或维持法律秩序外(尽管仔细考虑的话,高等教育与上述各方面都不无关系),并不能有效地指导我们开展工作。”[1](20)他还引用了迈克尔·科恩与詹姆士·马奇的话作为论据:“几乎任何一位有识之士都可以做一次题为《大学的目标》的讲座。也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自愿去听这种讲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类讲座及其有关论文虽然出发点是善意的,也不乏精美言论,但却几乎没有可供操作性的内容。制订规范的大学目标陈述的努力往往不是提出毫无意义的目标,就是提出的目标十分令人怀疑。”[1](19)
不知道两位学者所说的“有识之士”当如何理解。因为正如克拉克教授所分析的,这里所谓的“识”其实也是一个具有自然模糊性的概念,在物理学上“有识”的人,在社会学、教育学方面,就不一定“有识”,最近几年不是有物理学界的名人说中国的大学教育办得很成功么?即使是在同一领域,专家的“识”与普通人的“识”也有不同,不是有经济学家公然宣称“中国根本不存在两级分化”、“说中国两极分化是胡说八道”么?如果是这样的“有识之士”讲《大学的目标》,估计会“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自愿去听这种讲座”。
但是,还有一类“有识之士”,他们包括克拉克教授提到的弗莱克斯纳、牛曼、洪堡,也包括克拉克教授所没有提到的中国的蔡元培(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竺可桢(将“求是”做为浙大校训)、张伯苓(提出办南开只有两个目的:“其消极目的,在矫正上述民族五病;其积极目的,为培养救国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等等。即使是今天的中国,象刘道玉、朱九思、张楚廷、朱清时这些老校长,他们关于大学(包括大学的目标)的讲座,非但不是“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自愿去听”,反而是门庭若市、应者云集。这些校长们今天已经不再“身居高位”,来听讲座的,大概没有几个是领导指派的吧?更多的是出于对问题本身的兴趣和关注。这一道道景观,继承的正是西方“为知识而知识、为真理而真理”的传统,这也正是如今“天下滔滔”中的中国大学改革的方向和希望所在。
“善意的”“精美言论”本身并不足以构成对大学目标的质疑,用“几乎没有可供操作性的内容”来批评对于大学目的的讨论,则更是有点吹毛求疵之嫌。就好象批评一条裤子不漂亮,因为它不是一条裙子一样。组织强调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而目的则是贯穿、体现于各自项具体操作之中的,两者的作用内涵和方式均不一样,大学目的本来就是一个“务虚”的命题,但批评者往往要用“务实”的标准来要求它,这真有点要公鸡下蛋、母鸡打鸣的味道。克拉克教授认为大学目的“并不能有效地指导我们开展工作”,“正规的目标可以帮助内部人和局外人了解高等教育系统的一般性质。作为整合性的神话,正规性目标有助于提高士气和抚慰外部群体。但它们丝毫不能告诉你具体做些什么。”[1](25)这种批判逻辑本身就是不合逻辑的。逻辑与目标一样,也是一个虚的东西,而且也具有“自然模糊性”,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得讲逻辑,正如讲大学目的一样。布鲁贝克看到了这一点,他在区分了学者和决策人在大学的分工的差别的基础上,建议“学者不能因为这种差别而走向极端去批评行动者的粗心大意的分析,同样,行动者也不能走向极端指责学者生活在象牙塔里”[8]。
问题不止于此,克拉克教授进一步指出:“在考察时,我们有必要对知识和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这样我们就更有可能说知识是一个行动者,是它决定了任务和群体。其实它不是:个人和群体都为知识行动,教育群体组成和受控的方式决定了知识组合的方式。随着一般性教育机构的演进,他们发展了各类知识,并且决定了哪些种类的知识可以存在并具有权威性。”[1](26)简言之,这里涉及的是知与行的关系问题。为了论证组织的有用与目的的无用,克拉克教授主张行前知后,行难知易。这种主张对于今天的中国大学改革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因为我们的许多大学主事者,缺乏的不仅仅是理论,更多的是改革的诚意和行动的勇气。熊丙奇在对当今中国高校体制问题进行剖析时,曾约请过六位国内著名大学的校长,但是他们都以公务实在太忙,安排不出时间为由给推辞了。对此,陈丹青说:“我不同情熊先生,而宁愿同情校长们:他们又忙又累,哪里顾得上谈教育?要知道,不是他们在办教育,而是教育在‘办’他们;他们虽则是执行体制的人,其实每走一步无非被体制所‘执行’。”[9](序1)可见,大学校长的日子也不好过,但校长毕竟不是愚钝之人,徐友渔指出:他所见识的学校领导,都对教育界的种种弊端了如指掌,私下批评起来,“鞭辟入里”[9](28)。但实际的格局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机械僵硬、牢不可破,厦门大学不是破格聘请只有大专学历的著名学者谢泳为中文系教授了么?
在另一方面,无论是“随着一般性教育机构的演进”,组织的改变如何“发展了”“决定了”什么样的知识,大学“追求真理”的目的却是恒定不变的,任何真正的大学改革,都是要围绕这个目的而进行的。克拉克教授自己的论述也体现了这一点,他说:“如果许多在操作层次上相互分离的群体富有意义地连接起来,形成更大的团体,那么在操作上他们就能实现更大的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目的,甚至形成自由或普通教育。”[1](23)只是他没有意识到这种把“许多在操作层次上相互分离的群体富有意义地连接起来”的东西正是他所轻视的大学目的,具体点说,是最高层次的目的,也就是大学理念和精神。诚如刘道玉所指出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仅应当拥有大师级的著名学者、先进的教学与科研设备、丰富的馆藏图书、充足的经费等最好的硬件,而且还必须拥有自己先进的、专有的软件——大学精神。二者相得益彰,都是必不可少的。精神力量是巨大的,创造性的大学精神更犹如“文化原子弹”一样,对于办好世界一流大学的作用是无形的、长期的和无可估量的[10]。
三、大学目的与大学现实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克拉克教授在这里提出了“正规的目标”一词并把它作为批判的靶子。克拉克教授说:“为学术界确立统一标准的任何尝试都会导致强求活动和产品的一致性,而这与特定领域的特定学科内容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1](45)撇开《高等教育系统》一书在概念之间跳跃的频繁与活跃,单就“正规的目标”提出批评,这种批评则是值得肯定的。正如迈克尔·科恩与詹姆士·马奇所说,“制订规范的大学目标陈述的努力往往不是提出毫无意义的目标,就是提出的目标十分令人怀疑。”实际上,杜威在对他著名的“教育无目的”的论点进行阐释的时候,就明确指出,教育目的必须根据受教育者的特定个人的固有活动和需要(包括原始的本能和获得的习惯),教育目的必须能转化为与受教育者的活动进行合作的方法,教育者必须警惕所谓一般的和终极的目的。所以说“一个真正的目的和从外面强加给活动过程的目的,没有一点不是相反的”[11]。这对当今中国的大学改革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在这里,“正规的目标”应理解为政治势力要求所有的大学遵循共同的、具体的标准。这种要求显然是与“追求真理”的目的背道而驰的,同时也违背了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原则。就其内容而言,知识是多元的,高深的学问更是如此。用“正规的目标”(不管它戴着多么光彩夺目的帽子)来实现“统一”,只会扼杀知识和思想。雅斯贝尔斯说得好:“就像教会的情况一样,大学依靠国家的税收。但也像教会一样,大学的任务是超国家的。”[12]这种观念在西方社会已经基本上成为一种常识,西方大学校长都赞同大学应该是超政治、超国家的,即使是“服务社会”,也强调大学对社会的引领而非简单的跟从,更不用说盲从了。
在大学目的的现实超越性上是没有国别之分的,近代中国的大学就懂得它的重要性。1939年3月,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后,为了加强对大学的控制,通过行政手段,对大学教育的诸多方面强行统一管理,其中有些规定是合理的,比如统一招生,但也有一些部令是不合理的,如颁布大学课程科目表,统一课程教材,大专以上学校毕业考试实行总考制等等,严重窒息校园的自由空气,限制师生的思想自由,因而引起联大师生的反感和抵制。1940年6月10日,联大教务会议对教育部的统一大学课程教材和学生成绩考核办法等,据理抗驳,要求教育当局给予党校更多的教学自由,不必“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明确表示“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13]。然而今天的中国大学却在走相反的路,长远的如“统一思想”“政治建校”,近期的如高校政治课教材统一编写、研究生入学专业课统一考试。可见目的与现实的距离。
“制订规范的大学目标”没有必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目的本身是没有必要的。轻视宏观层面上目标的共性,片面强调中观层面上的组织研究,这样的做法却造成了大学目的与大学现实的割裂。正如前面所说,目的这个“家族类似”区分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子家族”,具体到大学目的与大学现实的关系上,可以从两个层面展开分析。
从最高的层次上说,知识领域是一个特殊领域。在社会的其他领域,目的与现实的对立统一是应该的,也是必需的。但知识领域却似乎是个例外,它是一个只有下限而无上限的无限敞开的领域,中国的古人就知道“人贵知足,唯学不然”。也正是因为如此,中世纪的大学才就“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这样的与现实毫无关联的“伪命题”争上数百年。正是在这样一个“超脱”的领域,大学保持住了它的生机与活力。现在的“走出象牙塔”还是“守护象牙塔”的争论,本身就是大学这一生机与活力的体现。大学正是在保守与开放之间稳步发展起来的,保持两者的张力十分重要。否则只要“有关部门”一纸文件宣布“不争论”,就万事大吉,岂不痛快?
赫钦斯当年提出的命题“大学应服务社会,抑批评社会?大学应仰赖于人,抑能独立自主?大学是一面镜子还是一座灯塔?应谋解决国家当前的实际需要,抑其主要职责在传递及推广高等文化?”[14]也许真是永恒的。对于大学目的的争论,反映的正是大学的理念和精神,那就是“追求真理”。这种理念和精神是最抽象的东西,它虽然不能直接指导实践,但却是大学的灵魂,没有它,大学就不成其为大学了。反观今天中国的大学改革,虽然“气势恢弘、波澜壮阔”[15],但却主要是在通常所说的人、才、物上做文章,意识到要更新意识、变革观念的却少有见到,能体现出“追求真理”的则更是凤毛麟角。所以丁学良说“中国大学最缺的是理念”[16]。落到现实层面来,我们可以说目的体现的是一种期望,合理的目的扎根现实又高于现实。我们不能批评大学目高于现实,因为与现实平行就不成其为目的,批评的关键在于它是否扎根现实。如果脱离现实,那就是盲动,是大跃进,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是有教训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克拉克教授批评了“主张目的清晰论的典型”赫钦斯对大学目的的观点,并切中要害地评价道:“他在纯梦幻中所指摘的现实,却是美国现代大学的现实,也是其他国家现代大学的现实。”[1](20)正如克拉克教授所批评的,赫钦斯的教育思想中的确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单一、纯洁的目的观,在赫钦斯看来,大学的目的必须是明确的、唯一的,“就是在强调、发展及保护人类的理性力量”[17]。在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期间,为了实现他的教育目的,赫钦斯实行了芝加哥大学本科教育计划和“4E合同”改革,但最后,他私下认为并公开暗示自己是一名失败的教育家。结合这段历史,可以说,克拉克教授的批评是很有分量的。
赫钦斯的纯美的大学目标注定了只是一个乌托邦,但“取法乎上得乎中”,它对于今天的中国教育改革是有着借鉴意义的。2000年哈佛大学遴选新校长时,有人提名总统职务即将卸任的克林顿和副总统戈尔,但哈佛大学聘任委员会很快就把这两个人排除在外。哈佛大学解释说,像克林顿、戈尔这样的人可以领导一个大国,但不一定能领导好一个大学。领导大国和领导大学是两回事,领导大学必须有丰富的学术背景,而克林顿和戈尔不具备[18]。从克林顿和戈尔最终未能染指哈佛的结局可以看出,赫钦斯所说的那种“强调、发展及保护人类的理性力量”的大学目的在美国是存在的,她不仅有存在的现实根基,而且还根基雄厚,生机勃勃。无论是从理论上的完备性看,还是从实践上的可操作性看,大学目的及其研究都有存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所以说,研究大学的目的不是没意义、不重要,而是很有意义、很重要;我们现在谈论大学的目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关键在于是真谈还是假谈,是在把握了大学的精神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谈,还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事论事、隔靴搔痒地谈。
[1] 伯顿·克拉克. 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王承绪. 杭州: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4.
[2] Jr. Edward LeRoy Long. Higher education as a moral enterprise [M].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92: 220.
[3] 克拉克·科尔. 大学的功用[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3: 29.
[4] 罗素. 西方哲学史(上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164.
[5] 马健生. 公平与效率的抉择: 美国教育市场化改革研究(序)[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8: 2−3.
[6] 聂振斌. 文明的呼唤: 蔡元培文选[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71.
[7] 樊洪业, 段异兵. 竺可桢文录[C].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9: 68.
[8] 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M]. 王承绪.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26.
[9] 熊丙奇. 体制迷墙: 大学问题高端访问[M].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05.
[10] 刘道玉. 论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从创造性与大学精神谈起[J]. 高教探索, 2004, (2): 4.
[11] 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M]. 王承绪.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122.
[12] 雅斯贝尔斯. 雅斯贝尔斯哲学自传[M]. 王立权.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58.
[13] 王文俊. 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9: 260.
[14] 赫钦斯. 教育现势与前瞻[M]. 香港: 今日世界出版社, 1976: 122.
[15] 周济. 谋划改革的新突破实现发展的新跨越—关于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几点思考[J]. 中国高等教育, 2004, (17): 3.
[16] 丁学良. 我们的大学最需要什么[J]. 中国改革, 2001, (11): 51.
[17] R.M.Hutchins. Higher Education of American[M].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6: 33.
[18] 沈颢. 燕园变法—谁能站上北大讲坛[M].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3: 91.
Rethinking of the Goals of Universities—In view of Burton Clark’s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ZHONG Huaming, CHEN Zhuo
(College of Education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3, China)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Academic organization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is valued because of its special perspectives and methodology. His thoughts on the goals of universities can still be instructive for China’s universities reforms today. The implication is that we interpret the goals of universities in view of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iginally vague” and “truth-pursu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oals of universit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als and organizations of universit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als and reality of universities.
the goals of universities; originally vagueness; university organizations; university reality
book=16,ebook=79
G640
A
1672-3104(2010)01−0112−06
[编辑:汪晓]
2009−09−12
钟华明(1961−),男,浙江诸暨人,浙江警察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管理学,治安学;陈卓(1981−),男,湖南怀化人,教育学博士,浙江警察学院社会科学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德育原理,高等教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