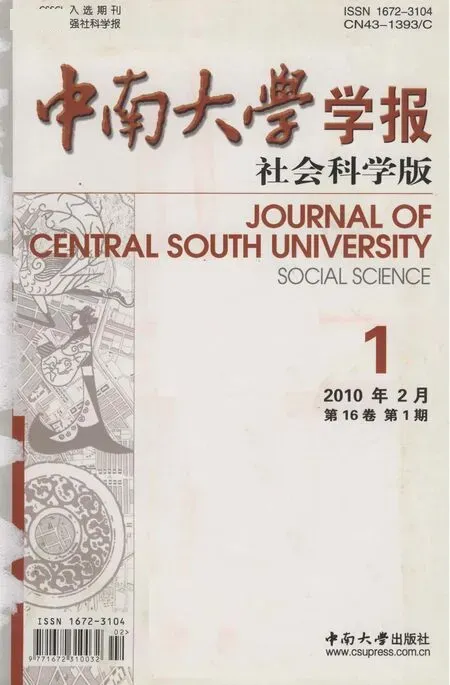小说叙述距离的审美本质及艺术生成
白春香
(晋中学院文学院,山西 晋中,030600)
“距离”是美学和文艺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同时也是被人们广泛运用的文艺学基本范畴之一。艾布拉姆斯曾给“距离”下过定义,他说“距离”“不仅常用于说明文学创作和作品欣赏等经验的性质,同时还用来分析作家控制读者对作品中人物的喜怒哀乐的心理距离或超然程度的众多手法”。[1]实际上,艾氏这儿所指的“距离”有两种:一种是审美心理距离,一种是小说叙述距离。审美心理距离是英国美学家爱德华·布洛于1907年在《作为艺术要素和审美原则的“心理距离”》中提出来的,它强调的是,在审美活动中审美主体只有以超现实的态度观照审美对象,与审美对象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才能保证审美活动的顺利完成。而小说叙述距离是美国学者布斯在 1961年《小说修辞学》中最早阐述的,它强调的是,在小说创作中,小说家为了控制读者的接受,总要在文本中运用各种叙述技巧精心创造叙述主体(隐含作者、叙述者和人物)之间的距离,从而实现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理想交流。但由于布斯对“叙述距离”论述时,在字面上沿用的是布洛的“距离”,而且也没有直接对他的“距离”和布洛的“距离”的不同内涵做出阐述,学术界也很少有文章从理论上深入研究小说的叙述距离。本文试图弥补这方面的不足,着重对小说叙述距离的内涵、审美本质和艺术生成做出理性探讨和阐释。
一、小说叙述距离的审美内涵及本质
在《小说修辞学》中,布斯是在论及读者的审美接受时谈到叙述距离的。他首先肯定了布洛关于欣赏者必须以超现实的态度观照审美对象的“心理距离”说,但他又对那种一概“排除接受者对艺术作品的感情,以便使他在理智上思考艺术作品”的布莱希特式的“间离效果”持批判态度。因为他认为,读者的审美兴趣并不仅仅是理智的,而是包括智力的、审美的和情感的三个方面在内的混合和冲突,那种仅仅强调读者对作品保持远距离的理性态度是对审美距离的一种简单化认识。那么,如何才能使读者的审美兴趣处于理智的、审美的和情感的交织状态呢?布斯认为这个问题应该由作家来解决,他认为小说文本本质上就是作者对读者进行距离控制的系统:“任何的文学作品—不论作家创作作品时是否想到了读者—事实上都是根据各种不同的兴趣层次,对读者介入或超脱进行控制的精心设计的系统。”[2](129)他认为只有在这样的系统中,读者才能与小说文本保持审美距离,从而实现道德的、智力的、情感的等多方面混合在一起的理想的审美阅读。
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曾有这样一段阐述:“在阅读过程中,总存在着作家、叙述者、其他人物以及读者之间的隐含对话。四者中的任何一者,与其他任何一者的关系,从认同到完全的反对都可能出现,而且可能在道德的、智力的、关系的甚至肉体的层面上发生。”[2](163)在这段话中,布斯描述了审美阅读中时时存在的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和读者相互之间在道德的、智力的和情感的等层面的隐含对话。稍加分析,我们就不难看出,布斯在这儿实际上谈到了两类隐含对话:一类是文本中各个叙述主体(隐含作者、叙述者和人物)相互之间存在的隐含对话;另一类是接受主体(读者)和文本中各个叙述主体之间的隐含对话。显然,前一类隐含对话是小说家在创作中“精心设计的系统”,它是小说家对文本进行距离控制的结果;而后一类隐含对话实质上表现为读者和小说之间的审美距离,它是一切充满叙述距离的小说文本必然带给读者的阅读体验。可见,叙述距离创造在先,而审美距离发生在后,叙述距离是审美距离产生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如果作家不在小说文本中精心创造隐含作者、叙述者和人物之间的叙述距离,读者就不可能与它们产生对话与交流,读者和小说文本之间的审美距离也不可能形成。从这些分析中,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布斯认为,作家在小说文本中创造的隐含作者、叙述者和人物之间的叙述距离是读者进行审美阅读的必要条件。
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不仅提出了小说叙述距离对读者审美阅读的必要性,还充分论述了小说叙述距离控制的具体方法。他说:“写小说本身就意味着找到表达技巧,使作品最大限度地为读者接受。”[2](112)他认为小说家的距离控制必须通过各种叙事技巧的精心设计才能实现。布斯的《小说修辞学 》实际上着重回答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小说家们是如何运用叙事技巧进行距离控制的,他通过对西方传统小说和现代小说的分析得出了许多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如透视人物内心能缩短读者和人物之间的距离,获得读者对人物的同情;作家的声音能“控制读者对故事情感介入的深浅或情感距离的远近”[2](211);“赋予主人公以反映他自己故事的权利便能够保证获得读者的同情”[2](293);“赋予或收回中心观察者的特权能够控制感情距离,同样,它也能有效地控制读者的智力方向”[2](295);作者退出小说所进行的非个人化叙述很容易造成“距离的混乱”[2](328);不可靠叙述不仅拉开了隐含作者和叙述者之间的距离,而且还直接影响了读者和故事之间的距离,等等。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布斯的《小说修辞学》表达了这样的小说创作逻辑:能带给读者审美兴趣的小说文本是通过小说家的距离控制来实现的,而一个富有距离控制的文本又是通过各种叙事技巧完成的。显然,布斯是把叙述距离控制当作小说创作根本的修辞目的来看待的,而叙述声音、叙述视点、叙述者叙述的可靠性与不可靠性以及反讽等诸多叙事技巧都是作为工具直接为距离控制服务的。傅修延先生说得好:“《小说修辞学》中具有统摄性的概念是‘距离’,通过这个概念可以把握住布斯理论的精髓。”[3](108)但遗憾的是,由于他们的论著中并没有直接阐明叙述距离和叙事技巧之间的这种关系,致使许多学者对叙述距离的本质内涵产生误解。比如李建军在《小说修辞研究》中就把视点、声音、时空、人称、节奏和距离一起,并列为宏观修辞技巧[4](105)。
实际上,小说家在文本中对叙述主体之间距离的精心设置,在叙事本质上是要使现实世界通过小说叙事实现创造性的变形,使之以不同于读者熟悉的常态方式出现,打破读者的接受定势,从而创造出读者对小说文本的审美距离。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论述艺术陌生化本质的,他说:“作家和艺术家全部工作的意义,就在于……使所描写的事物以迥异于通常我们接受它们时的形态出现于作品中,借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延长和增强感受的时值。”[6]
小说叙述主体之间距离的存在,不仅给读者展示了一个陌生化的艺术世界,而且也引发了读者与小说叙述主体(隐含作者、叙述者和人物)之间距离的产生。因为“作者与叙述者看法相左时,读者可能对叙述者产生反感而同意躲在幕后的作者,但也可能站在叙述者或某位人物一边”[3](109),这样,读者的阅读活动实质上就成为读者和小说各个叙述主体之间的距离不断变化的过程。但不可忽视的是,小说家对读者和叙述主体之间的距离设置需要有效控制,既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应该处于一种不即不离的胶着状态。朱光潜先生曾经说:“凡是艺术都要有几分近情理,却也都要有几分不近情理。它要有几分近情理,距离才不至于过远,才能使人了解欣赏;要有几分不近情理,‘距离’才不至于过近,才不至使人由美感世界回到实用世界中去。”[7]小说家在隐含作者、叙述者和人物之间所创造的“从认同到完全的反对都可能出现”[2](163)的距离控制,实质上正是为了给读者创造一个既有“几分近情理”又有“几分不近情理”的艺术文本。所以,小说家只有在各个叙述主体之间进行有效的距离控制,才能保证读者与小说之间审美距离的形成。
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也论述了这一问题。他说,小说最理想的距离控制模式应该是“叙述者开头远离而结尾接近读者这一距离变化”,即在小说开头隐含作者的思想情感要远离读者,而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这种距离要逐渐缩小,最后在结尾时读者和隐含作者取得很大程度的认同,彼此趋于同一。显然,布斯深深懂得陌生化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接受原则。小说文本与读者之间由大而小的距离控制,不仅给读者提供了一个陌生化的审美对象,而且使读者在经历了与隐含作者、叙述者和人物之间理智的、审美的和情感的较量以及随之而来的审美体验之后,最终还是找到了那个“众里寻他千百度”的隐含作者,从而与作者产生共鸣,得到艺术美的享受,最终实现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理想交流。
总之,陌生化是小说叙述距离的修辞本质。作者在小说文本中对叙述距离的有效控制,不仅创造了一个陌生化的审美艺术世界,而且也创造了读者对小说文本理想的审美接受。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小说叙述距离控制的优劣,直接决定着小说艺术创作和艺术接受的成败。
二、小说叙述距离的艺术生成
既然小说叙述距离是作家有意识地采用各种叙事技巧精心创造出来的,那么,小说家是如何运用叙事技巧实现距离控制的呢?距离控制表现出来的一般规律有哪些?笔者将分别从各个叙述主体之间的距离控制入手来探讨这些问题。
(一)控制隐含作者和叙述者之间的距离
隐含作者是真实作者在文本中的自我形象,是文本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的最终主宰,但他并不在文本中直接露面,而是通过文本的整体叙述表现出来。叙述者作为隐含作者为了艺术地表达其思想情感在文本中创造的一个讲故事的人,他有时与隐含作者靠近,有时则相距较远,有时甚至完全相反。实际上,不管叙述者如何叙述,都是隐含作者允许的,因为他在本质上是受隐含作者支配的。
布斯在论及隐含作者和叙述者之间的距离关系时,曾把与隐含作者基本靠近或可以完全吻合的叙述者称为可靠的叙述者,而把与隐含作者距离较远或完全不同的叙述者称为不可靠的叙述者。一般地说,在全知全能的叙述中,叙述者往往是可靠的,因为他那上帝般的讲述者身份,决定了他的思想认识和价值判断是代表隐含作者的,这时候,他与隐含作者的距离最小。申丹曾经总结:“就几种不同的视角模式而言,全知叙述中隐含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距离一般来说相对较小。”[8](232)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者就是最典型的可靠叙述者。可靠叙述不仅使隐含作者和叙述者保持近距离,而且也能够拉近读者和隐含作者、叙述者之间的距离。这是因为叙述者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叙述声音,总是迫使读者只能无条件地接受他的认识和判断,并从他的观点出发来衡量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同时,读者在叙述者的干预下也不可能近距离地感知人物的思想意识和内在心理,只能对人物保持远距离的观照。
但在一些限知叙述的小说文本中,叙述者是故事外的旁观者或故事内的人物,这些叙述者由于其自身知识视野的限制或思想价值体系存在的问题,往往在叙述故事和评价人物时,带有个人的主观偏见,从而导致其价值判断和隐含作者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因而形成不可靠叙述。比如,马克·吐温的小说《哈克贝利·芬》就是如此。在这篇小说中,叙述者哈克是一个有很多劣习的流浪儿,他经常冷嘲热讽,着意欺骗,并公然蔑视法律帮助黑人逃跑,还声称自己要变成世界上最邪恶的人。显然,叙述者对哈克的思想和行为是完全否定的,但正是这些被叙述者否定的东西却得到隐含作者的默默肯定,隐含作者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哈克勇于反抗黑暗精神的赞美。叙述者要否定的东西,成为隐含作者肯定的东西,隐含作者和叙述者之间存在很大距离。而正是两者之间这种距离的张力使读者在开始阅读小说时无所适从,总是和隐含作者、叙述者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时候,读者只能尽可能地走进人物的思想世界和内心世界,并依靠自己的判断对人物的思想行为做出理智的和道德的裁决。渐渐地,他开始怀疑叙述者的价值判断,并逐渐远离叙述者而最终走向隐含作者。在这一阅读过程中,读者始终都在近距离地接触人物,始终都在叙述者和隐含作者之间的距离张力场中调动自己思想和情感的每一根神经,并在审美理解和玩味中完成与隐含作者之间的审美交流。
(二)控制叙述者和故事中人物之间的距离
叙述者和人物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叙述主体和叙述对象之间的关系。叙述者采用不同的叙述视角、叙述声音、叙述话语和叙述时态,都会直接影响到它和被叙述的人物之间的距离。
1.通过叙述视角控制叙述者和人物之间的距离
叙述学上关于叙述视角的分类较为繁杂,许多叙事理论家所使用的概念也不统一,概而言之,人们往往把叙述视角分为零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三种。零聚焦采用全知叙述者的眼光进行叙述;内聚焦采用故事中人物的眼光进行叙述;而外聚焦则采用外部观察者的眼光进行叙述。一般地说,内聚焦叙述能够拉近叙述者和人物之间的距离;外聚焦叙述则疏远了叙述者和人物之间的距离;而零聚焦叙述者由于具有绝对权威,因而使叙述者和人物之间总保持很大的距离。下面主要阐述一下内聚焦和外聚焦叙述是如何控制叙述者和人物之间的距离的。
在内聚焦叙述中,由于叙述者为故事中的人物,他直接参与了故事的整个事件,所以,从他的眼光出发对故事进行叙述往往显得真实可靠。而尤为突出的是,内聚焦叙述能够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逼真地展示人物细致入微的内在心理,这样,自然拉近了叙述者和人物之间的距离。这种叙述效果在主人公充当叙述者的小说中尤其明显。比如在鲁迅的小说《伤逝》中,涓生以内聚焦的叙述方式,不仅声泪俱下地述说了他和子君之间的爱情悲剧,而且通过内心独白逼真地展示了他内心深处对子君之死的深深忏悔和无奈,从而赢得了读者对他的理解和同情。面对叙述者“我”的内心剖白,读者必然要走入“我”的内心世界,必然会情不自禁地与“我”的思想情感产生共鸣。所以,在内聚焦叙述中,叙述者与人物之间距离的拉近,也必然同时拉近读者和人物之间的距离。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一个人内心的了解越多,你就会越同情他;他越跟你交心,你越会理解他,因此,叙述者对人物的内心活动展示得越多,读者和人物的距离就会越近。难怪布斯说:“如果一位作家想使某些人物具有强烈的令人同情的效果,而这些人物并不具备令人十分同情的美德,那么持续而深入的内心透视所造成心理的生动性就能帮他的忙。”[2](389)
而在外聚焦叙述中,叙述者充当了故事事件的旁观者和见证人。在叙述过程中,他总是不动声色地进行客观叙述,对故事不做任何评价和判断。这样的叙述者就像一台摄像机,他只是把他所看到的、听到的如实记录下来,他和人物之间没有任何情感的沟通和交流,因此存在很大距离。白先勇小说的叙述者就常常采用这种“见证人”视角。比如《一把青》,作者让一个毫不相干的旁观者秦婆婆来充当叙述者,讲述了女主人公朱青由一个淳朴善良的少女演变为一个放荡冷漠的女人的故事。由于叙述者是一个不动声色的讲述者,他只是把他看到的一幕幕场景客观再现出来,这样,读者由于看不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也无法领略到导致主人公精神裂变的内在心理原因,因此,读者和人物之间必然始终存在很大距离。申丹在谈到这种摄像式外视点产生的叙述效果时曾经说:“尽管读者身临其境之感是……最强的,仿佛一切都正在眼前发生,但读者与人物之间的情感距离却是最大的。这主要是因为人物对读者来说始终是个谜,后者作为猜谜的旁观者无法与前者认同。”[8](216)阅读《一把青》,读者在远距离地对朱青的不幸遭遇扼腕痛惜的同时,只能对主人公及其悲剧命运进行深层的审视、寻味和追思,这一点也许正是白先勇小说希望获得的理性韵味。
2.通过叙述声音控制叙述者和人物之间的距离
叙述声音是叙述者在叙述过程中对人物和事件发出来的带有主观性的声音,叙述声音的强弱和叙述者对人物的介入程度是成正比的。叙述声音越强,叙述者的主体意识也越强,人物受叙述者的理性控制就越多,叙述者与人物的距离就越远;反之,叙述声音越弱,叙述者的主体意识也越弱,人物受叙述者的理性控制就越少,叙述者与人物的距离就越近。
传统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个全知全能的讲述者,它的叙述声音很强,经常直接或隐蔽地对人物评头论足,人物往往直接被叙述者左右,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距离。阅读这样的小说文本,由于人物被深深地打上了叙述者意识的烙印,所以,读者对人物的认识和把握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叙述者思想意识的制约。实际上,读者在这类文本中最终接受的只能是一个被叙述者理性化的人物,因为“在普通的全知叙述中,读者一般通过叙述者的眼光来观察故事世界,包括人物内心的想法”[8](216)。可见,叙述者对人物的叙述干预,不仅拉开了叙述者和人物的距离,而且也拉开了读者和人物的距离。而现代小说为了更直观逼真地展示故事和人物,叙述声音被逐渐弱化,叙述者和人物的距离被拉近。因此,在现代小说中,像传统小说那样时时站出来发表议论、高居于人物之上的叙述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和人物平起平坐的纯客观叙述者。一般来说,这种纯客观叙述者对人物的叙述往往采用两种方式:“一是倾向于采用越来越有形的戏剧性描述,直截了当地依靠列举物件和行为的名称,报导人物所说的话;另一个方面,是倾向于对不受阻遏的意识之流作表面完整的、连贯的复制。”[9]前者是在逼真地展示人物的语言和行为,后者则是在逼真地展示人物的内在意识。在这类小说文本中,叙述者似乎退到了幕后,他让故事进行自我演绎,让人物进行自我表现。同时,叙述者这种对故事和人物生动形象的近距离展示,必然也拉近了读者和人物之间的距离。阅读这样的小说文本,读者似乎在亲眼目睹故事的整个发展,亲身感受人物的内心矛盾和情感变化,因而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
3.通过人物话语的不同表达方式控制叙述者和人物之间的距离
申丹曾经说:“叙述学家之所以对表达人物话语的不同形式感兴趣,是因为这些形式是调节叙述距离的重要工具。”[8](306)一般来说,小说家转述人物话语的方法依据叙述者介入程度的不同可分为:言语行为的叙述体、间接引语、自由间接引语、直接引语和自由直接引语五种。①在这五种方式中,叙述者的介入程度在依次递减。叙述者介入程度越高,叙述者对人物的理性控制就越强,叙述者和人物的距离就越远;反之,叙述者介入程度越低,叙述者的主体意识就得以弱化而滑入人物的主体意识,叙述者和人物之间的情感距离就越近。因此,在这五种表达方式中,叙述者和人物之间的距离也在依次减小。同时,叙述者和人物之间距离的变化,也必然导致读者和人物之间距离的变化。因为随着叙述者主体意识的逐渐淡化和人物主体意识的逐渐增强,读者就越能近距离地感知人物的思想意识和内在情感,从而使读者和人物之间的距离也越近。比如,申丹在谈到自由直接引语时就曾说:“这是 叙述干预最轻、叙述距离最近的一种形式。由于没有叙述语境的压力,它使作者能自由地表现人物话语的内涵、风格和语气。……自由直接引语使读者能在无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直接接触人物的‘原话’。”[8](320)所以,一般来说,小说家为了拉近读者和人物之间的距离,往往采用叙述干预较小的自由直接引语和直接引语;而为了疏远读者和人物之间的距离,也往往采用叙述干预较大的言语行为叙述体和间接引语的方式。
4.通过叙述时态控制叙述者和人物之间的距离
叙述学上,一般根据叙述行为与故事的时间位置可把叙述分为四种类型,即“事后叙述(常见于过去时叙述);事前叙述(预言性叙事,一般用将来时,但也可用现在时);同时叙述(与情节同时的现在时叙事)和插入叙述(插入到情节的各个时刻之间)”[10](150)。显然,这四种叙述类型包含着三种叙述时态:现在时叙述、过去时叙述和将来时叙述。现在时叙述由于呈现为“故事与叙述完全重合在一起,排除了各式各样的相互影响和时间上玩的花样”,因此,“现在时的使用缩短了主体间的距离”[10](151),也就是说,缩短了叙述者和故事中人物之间的距离。阅读这样的小说文本,读者感受到的要么是纯客观的故事展现,要么是人物的内心独白,这样,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仿佛一幅幅在眼前发生的真实景观,因此,读者与故事中人物的距离也最近。而在过去时叙述和将来时叙述中,由于叙述者是在讲述过去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事件,叙述者必然和故事中的人物保持一定的距离。
一般来说,绝大部分作品都是事后叙述,因为事件只有在发生以后才能被叙述出来。一般叙事作品并不特意标明叙述者与故事之间的时间距离,它们之间的距离往往显得朦胧而模糊。但有些叙事文本为了特意拉开叙述者和故事之间的距离,总要特别强调过去时的叙述行为。张爱玲的小说就是典型。张爱玲小说的叙述者都是现代人,但她讲述的却是三四十年前旧上海正在走向衰败的封建大家庭中发生的古老故事。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叙述者和故事之间的这一时间距离总是被凸显出来,比如《金锁记》的开头就说:“30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张爱玲曾在《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中对这一叙述行为做出这样的阐释,她说:“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如果这画面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10]显然,张爱玲是有意在她的小说文本中创造一个以窥视者身份出现的现代人叙述者,从而使叙述者和故事拉开很大的距离,而这种距离的存在,必然会在读者与故事之间笼罩上一层无法跨越的历史距离感。阅读张爱玲的小说文本,读者似乎跟随叙述者的视角,隔着几十年的时光隧道,去品味在古老的服饰、过时的礼节和旧式的家具映衬下所发生的各种离奇的事件,同时去感受从黯淡的历史深处走出来的那些陌生人物的可怜、可悲和可笑,进而对社会人生做出深沉的理性审视。这是一种由距离而引发的对历史文化的深层审视,也是事后叙述必然产生的一种叙述效果,正如米勒曾说的:“在叙述中采用常规的过去时是表达叙述者与他所描绘的文化相分离的一种方式。……这种保持距离的做法削弱了小说中人物分享的那些设想和价值观念。”[11]
(三)控制隐含作者和人物之间的距离
我们知道,在小说文本中,隐含作者的思想意识并不直接表现,而是通过文本的整体叙述间接地流露出来。一般地说,隐含作者与故事中人物之间的距离,与叙述者对人物的叙述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人物被叙述者用第一人称叙述时,隐含作者与人物的距离近;而当人物被用第三人称叙述时,隐含作者与人物的距离远。我们以李锐的《无风之树》为例来说明这一距离控制规律。
在《无风之树》中,故事中的13个人物分别被采用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进行叙述,其中,12个国家意识形态淡薄的民间人物都以第一人称“我”出场,而只有那个根正苗红、语录连篇的烈士后代苦根儿被赋予“他”的称谓。隐含作者如此来设置叙述行为,实质上是为了调控它与故事中人物之间的距离。12个民间人物通过第一人称“我”的述说,从人的生命需求和生命存在出发,表达了自己的情感态度和生命追求,张扬了一种原生态的富有生命活力的人生哲学。隐含作者通过赋予这些人物“我”的叙述权力,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他们生存状态的深刻理解和同情,同时也表达了重视个体生命体验的民间意识。而苦根儿在《无风之树》中作为唯一的一个“他”者,张口就是“阶级斗争”,闭口就是“毛主席语录”;他不想娶媳妇,认为“女人是妖精”;他也不懂什么是死亡,认为“死亡就是生命结束了,除此以外什么也不是”;他的情感世界是空白的,不懂人情世故,也没有喜怒哀乐;他只想清理阶级斗争队伍,只想把矮人坪改天换地。显然,他是一个不懂人生情感和生命价值的政治可怜虫。隐含作者通过赋予苦根儿第三人称“他”,远距离地审视着这个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并在12个充满生命活力的“我”对“他”的不理解和不认同中,深深地流露出对这个人物的反感和拒斥。
实际上,隐含作者与“我”和”他”之间的不同距离来源于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不同的叙述效果。布斯曾经对这两种叙述的不同本质进行了论述,他说:“从叙事学的角度看,第一人称叙事与第三人称叙事的区别就在于二者与作品塑造的那个虚构的艺术世界的距离不同。第一人称叙述者就生活在这个艺术世界中,和这个世界的其他人物一样,他也是这个世界里的一个人物,一个真切的、活生生的人物。而第三人称叙述者尽管也可以自称‘我’,但却是置身于这个虚构的艺术世界之外的。”[12]虚构的艺术世界所表达的价值取向往往代表着隐含作者的思想意识,第一人称叙述者生活在虚构的艺术世界中,与虚构的艺术世界的距离近,自然与隐含作者的距离也近;而第三人称叙述者生活在虚构的艺术世界之外,与虚构的艺术世界的距离远,自然与隐含作者的距离也远。同时,隐含作者与叙述者“我”和“他”之间的不同距离还会影响到读者与叙述者“我”和“他”之间的距离。一般来说,第一人称“我”的叙述在拉近隐含作者和人物之间距离的同时,也拉近了读者和人物之间的距离。读者阅读《无风之树》,情不自禁地总会被“我”们的述说所感染,并对“我”们的情感世界和生命存在寄予深深的理解和同情。而第三人称“他”的叙述却不仅疏远了隐含作者与人物的距离,而且也疏远了读者和人物的距离。因为“他”的叙述往往展现的是人物的外在行为,内在心理读者是看不到的,《无风之树》中的苦根儿自然也只能成为读者远距离审视的对象。在这种审视中,读者不仅会深刻地感受到这样一个没有个体情感的政治躯壳的可悲和可怜,而且还会进一步反思政治化时代对个体生命的严重戕害。这种深层的理性思索也许正是作者试图通过不同人称叙述进行距离控制所期望达到的艺术效果。
注释:
① 采用利奇和肖特对人物话语表达形式的分类。
[1]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79.
[2]布斯.小说修辞学[M].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
[3]傅修延.文本学—文本主义文论系统研究[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麦·莱德尔.现代美学文论选[C]// 孙越生、陆梅林、程代熙,等译.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423.
[6]佛克马·易布恩.二十世纪文艺理论[M].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1988: 19.
[7]朱光潜.文艺心理学[M].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31.
[8]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32.
[9]李文俊.福克纳评论集[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96.
[10]热耐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11]张爱玲.有几句话同读者说[C]//张爱玲文集(卷四).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259.
[12]程锡麟,王晓路.当代美国小说理论[M].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127.
[13]布斯.小说修辞学[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