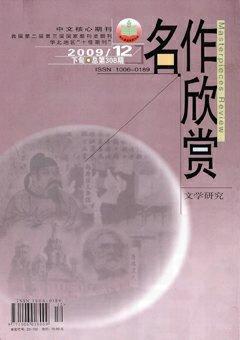铁凝乡土小说的精神意义
景 莹
关键词:铁凝 归依乡土 精神指向
摘 要:穿越铁凝30年的创作,我们看到在她书写乡村的小说中总是表达着对农民的好感,总能体会到一种或喜悦或高亢的情感。而且在她后来的创作中将这种好感上升为一种歌颂,即乡村醇厚的人情、人性美,作家也在其中找到了精神的归属感。
铁凝的创作题材可以分为城市和乡村两部分,不过,她书写城市的文字绝对多于书写乡村的文字。但穿越她30年的创作,我们看到她的写作由乡村出发,也由乡村而终。而且稍微留意一下铁凝的创作,就会发现铁凝写乡村的情感与写城市的笔墨是截然不同的:乡村质朴醇厚,城市诡秘龌龊。
铁凝自小出生在城市,农村和农民不是她最熟悉的题材,可一旦写乡村时,哪怕是说话不着调、谎话连篇如瞎话那样的人,也是民族危难中抗战英雄,她仿佛被乡村俘虏了,生活在城市的铁凝这般钟情于乡村实在值得玩味。
回到生活
赋予时代和生活太多的意义,哪怕再微不足道的螺丝钉、一株小草都能承担宏大意义主题,是截止到1980年代普遍的社会主题,以小见大也是文学创作的写作方式。动辄以革命的名义或向毛主席保证以示自己行为的纯洁性和高尚性。太多的意义承载所导致的是逃离意义本身。铁凝早期平易朴素地叙写乡村生活的小说,也许就是对那意义的逃离,或许也包含了文人的持久的回乡冲动:对于俗人、俗事的价值情感取向。当然也反映出作家的一种创作心态。这或许也暗合了赵园先生所说:“兵团有利于保存这一代人的价值观中至关重要的‘集体主义。而插队则恰恰相反,功能在消解形成于群体中的观念与习惯,有助于插队者走出红卫兵状态,重建‘个人,以个体形式面对世界,鼓励更为个人化的认知要求。……乡村作为经验对象也改造着知青们的经验形式,外在世界缘曲折的路径进入内在自我。”{1}在寻找自我创作的途径中,铁凝发现的是古旧乡村生活中稳定性的纯净。在农民身上找到的也不是那个大写的人,而是他们憨厚性格中的沉稳、内敛,尤其是农民灵魂深处的韧性生存精神让她投以持久的敬畏。
大芝娘平静地接受丈夫无理的离婚要求,而后她一生都抱着一个大枕头睡,在大芝死后她把全部的爱给予了沈小凤、杨青、花儿、五星等她身边每一个需要爱的呵护的人,她永不疲倦地爱着,她就像铁凝小说中雕塑一样的人物点滴地遍布于每篇作品中。
如果说大芝娘的隐忍源于乡村的稳定性的话,那么铁凝较早反映知青生活的小说《村路带我回家》就把乡村生活观念的稳定性和乔叶叶内心的稳定性有机结合的表现了出来。面对城市的诱惑和无需扎根农村的政策,乔叶叶莫名其妙地选择了留在东高庄,但这留应该说与金召无关,她对宋侃和金召之间的态度都不是特别明确,她选择留下来的原因是:她愿意闻她已经熟悉地柴草灰味儿,她喜欢初秋时节庄稼地里散发出的清甜味道。她是否做好了充分准备,永远做一名普通的、长年辛劳在土地上的农民,这是没有主见的乔叶叶自己也不能回答的问题。在大街小巷写满政治口号的时代,规避外在大世界的招呼,寻找趋稳定性现存生活,这是乔叶叶留在乡村最自然不过的理由了。从没有主见到任性地留在东高庄,农民的那种执扭的韧性已经慢慢地流进她的血液中。
“许多年了,他似乎总是一个模样,仿佛他不曾年轻过,也不能变得更老”(何士光《种包谷的老人》)在这含义丰富的文字中,将农民恒久的韧性生存也表现了出来。在旧中国这种韧性尤其包括了无法实现的压抑和无奈。
灶火(《灶火的故事》)在解放后平静地接受了回乡务农,而且生活非常简单甚至是寒酸,他住的房子古老到有着“中世纪建筑风格,不用说是黄昏进来,就是大白天进来,也是伸手不见五指。”{2}他的生活状况近于原始程度,然而他无意改变这种现状,这也恰是中国农民的韧性生存。可在其他农民都偷偷摸摸地卖柿子到外地多赚钱的时候,只有灶火留下来给麦田浇水,提醒村支书不能因自己的事耽误生产队的劳动,还以一个老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把柿子卖给供销社,以至招来村口男男女女的笑话。
有时无奈也能激发出巨大的生命爆发力,《砸骨头》中由于贫困造成的无法完成乡里税收,于是上演了村长和会计之间砸骨头的恶斗。它不是个人恩怨和私利激发下的拼杀,而是共同承受痛苦,共有的承担、压力和贫困,不得已的排解,使两个共同命运的男人在刹那间成为你死我活的仇敌,在对打中,“直砸得天昏地暗,直砸得眼花缭乱,直砸得赤身裸体,直砸得两个血人突然想搂抱在一起”{3}。当他们互相搀扶着爬上河岸,在微笑中取得谅解时,也在骨头缝里砸出了村民们对他们的体谅,村民们自发凑齐了上交乡里的税款。铁凝以砸骨头的形象化文学手段既表现了农民无奈中的智慧之光。
贫困的生活时代赋予中国农民坚韧的性格,而新时代的到来也让新一代农民开始建立并捍卫自尊,开始了迈向自我实现的第一步。
《寂寞嫦娥》中的嫦娥,她从山村来到城市,内心无比寂寞。但她不甘于寂寞,她以一个山区农民的质朴和特有的坚韧,由一个保姆到升格为教授妻子,但周围教授太太们一直用“培根”“土司”等洋话驱赶她。在离开老教授后,改嫁给了锅炉工,并找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职业——种花卖花,而且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她靠自己的劳动换取了生活的尊严,确立了自己在这个城市中的价值,使整个城市从此对她刮目相看,赢得了城市对她的尊重。寂寞嫦娥终于走出了寂寞。
生命不是为意义而生,它指向个体生命的内心世界,拥有怎样的人生也许我们无从把握,但是树立一个并不遥远的生活目标也许更为切实,并为实现它做出最大的努力。生命不为招摇过市而来,那就留一份踏实给自己,平平淡淡才是人生真相。这是铁凝在朴素平实的乡村小说中提示给我们的。
醇厚的人情
回到最贴近生命本真的乡村,铁凝像发现宝藏一样被乡村所吸引。或许是城市的异己感,或许是传统文化的浸润太久,隔着时间的记忆,作家也把审美的目光瞥向乡村,从而表达一种中国文人不能拒绝的文化乡愁感。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一个普通的村落,仅有场圃、桑麻的日常村野之景,然而最日常的背景后隐藏着农人最诚挚的热情,单纯的村民要把丰收的喜悦传递给每一个路人。这是一份诗意表达。
众所周知,《哦,香雪》是铁凝用诗一样的情感首次表达了她对农民的体认。铁凝在20世纪80年代还专门创作了一组以“爷爷”为主反映农民醇厚情感的小说。
《三丑爷》中,三丑爷不因自己做过瑞典牧师的厨师而得意,他不媚俗,不崇洋媚外,更不轻看自己的农民身份,面对出国还是回村当农民的选择他毫不犹豫地留了下来,淡然地对待他曾经历过的辉煌。回了村,每有红白喜事,他从不拒绝去帮忙。他欣赏乡村厚重的人情,满足于膝下儿孙满堂的幸福。
《东山下的风景》房东大爷在儿媳收了“我”的住宿费后又跑到车站还给我9.6元钱,撕碎了儿媳给我的收据,用一句最朴实的话表达了他对金钱的蔑视,对人情的看重,“这是你的,我嫌数目少。我要的数目你又拿不出来。”{4}
《老丑爷》中老丑爷听到房外年轻后生们偷摘“大荷包”的声音,仅仅一句“谁啊”喊走年轻人便罢了,不再进一步追究。在“我”回老家时,老丑爷总也不忘塞一兜“大荷包”给“我”,而且还为“我”这样一个孙女辈的孩子再次重操旧业,说起20多年都没再说过的评书。让“我”感慨于老丑爷的爱心和真情。三年困难时期,在漆黑的冬夜,他不求任何回报,用动听的声音为乡亲们创造了一个神秘、生动的世界,让贫困的乡邻们暂时忘却了寒冷和家中的空锅。爷爷们的正直、厚道、纯净的品性成为扛起乡村醇厚、仁善的背脊。
与爷爷们同代的还有戎马一生的向喜,在他征战的一生中相继纳二丫头顺容和女艺人施玉禅为妾,但他不是那种喜新厌旧的男人,向喜给发妻打了一枚铸有“向梁氏同艾”的金戒指,“这枚分量不轻的金戒指不仅是向喜对发妻的一份情意,也是向喜对发妻身份的再一次郑重确认”{5}。而且无论他走到哪里,总把“四蓬缯”的被子带在身边。“四蓬缯”这块由同艾亲自从纺线、染线、浆线直到上机织布、尔后缝制成的被子,虽非为他俩定情之物却胜似定情之物。男儿的重情重义不仅仅体现在对下属晚辈的关爱上,更体现为对爱人的一往情深。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中国乡村也正是有这样多彩立体的人格支撑才更显示其醇厚的人情美和人性美。
爷爷们是乡村仁厚道德的传承者,奶奶们则是爱的承载者。
大芝娘用她宽厚温暖的胸脯驱走了来到乡下的女知青们的迷茫和恐惧,给失去母亲的孩子五星以母爱的温暖。相似的情景在《笨花》同艾的心中升起,她把丈夫和艺人施玉禅生的女孩取灯视如己出,让这个从大城市武汉来到乡村既无根基又失去母爱的小女孩获得了无尽的爱和快乐。
写村人的醇厚,一方面乡村是古老民风保持最完整最完美之所在,另一方面也源于城市生活竞争中体现出的人性刻薄;对于一个乡村生活经历并不丰富的年轻人一再写乡村之美,还根源于文化心理上的不能忘却,“人类感情的真正深刻处,是难以言说的,说出来的或只不过是其‘粗”{6},这种粗憨在铁凝的小说中也另有表现。当小黄米终于等来了客人老白,陪他喝酒,让他拍各种姿势的裸照,这在小黄米看来一切都只是预演,最重要的事还在后面,她没想到拍完照片就一切都结束了,老白给钱走人了。小黄米和老板娘都因环节的缺失而觉得有些失落感。《笨花》中向桂对来钻窝棚拾花的细胳膊瘦腿的小妮儿表示拒绝,却让她背走了一大袋子棉花。小黄米、向桂都是成天在和泥土打交道的粗人,然而粗中之痴,粗中之细恰恰是在日渐粗鄙人性中闪现的最为耀眼的光亮。
道德的纯洁性在农民虽经历曲折仍然顽强保存下来的纯正本性中体现出来,也造就了乡村如逆旅中的憩园的恬淡安适。指引着“我”一次次回到冀中平原的故乡,发现了乡村依然留存的美。
精神的家园
铁凝的创作可以分为以母亲家族为背景的作品和以父亲家族为背景的作品。
母亲家族系列作品作为她创作的主体,展现反思现实时,作者是以颠覆的立场来写作这类作品的。而为数不多的以父亲家族为背景创作的作品尽管数量不多,但与前者的精神立场则完全相反,她以景仰之心书写父亲家族。同时乡村也是一块巨大的文化沉积岩,乡土中国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支撑地,乡村人的剽悍、粗野、坚韧持重、通达见识与洒脱姿态以及侠义性格也是无根的城市知识分子文化精神上的父亲。铁凝小说中的乡村男性长者表现出作家潜意识中对“农民——父亲”的体认。
那个长期寄居在北京外婆家的女孩在城市看到种种人生的不堪。而长大后无论是乡村插队还是短暂的回故乡,都让年轻的女孩见证了别样的生活和生存空间的巨大不同,她给城市和乡村下了不同的定义——生活在城市的人都在欲望中拼杀,生活在乡村的农民则通透洒脱,活出了人生的智慧,能够淡定从容地面对人生的生生死死。
三丑爷能在没吃没喝的情况下,以说书为精神食粮慰藉自己和乡民,已经足以传达农民的笃定从容,而向氏父子则将这从容进一步生发。总结向喜的一生,我们看到他没有非常明确的政治理想,他的一生有不得已的被历史裹挟着前行的被动选择,尽管事实更移,但他决不贪恋高官厚禄,他识大体、顾大局,本着一个农民最朴素的道德感,靠着中国人最讲良心的朴素感,使他在最关键的时刻,葆有了内心的尊严、气节。传统文化的魅力在向喜身上充分体现出来“他并非乱世之中的英雄,他仅是历史风云中的一颗尘土, 但却是珍贵的尘土,是一个民族的底色”{7}。
向文成是个根植于乡土的知识者的形象,虽然眼睛看不见身外的世界,然而他的内心却是一片光明,他上通天文、下懂地理,并对村里的人事予以人性化的理解和帮助。虽然身处偏远的冀中乡村,但他却胸怀整个世界。是他把小小的笨花村和整个世界联系了起来,使整个笨花村在精神指向上出现了一种通达的感觉。
铁凝通过描述冀中平原的乡村,以及生活在棉花地里的乡民,以表达她对灵魂之乡的依托,尤其是乡村小说中频频出现的智慧通达的男性,是“祖父”、“父亲”的标记,她以此表达对他们的体认,以及对自己身份的认同。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小说历史意识研究”,项目号:07SJB750008
作者简介:景 莹,文学硕士,南通大学文学院讲师。
{1}{6} 赵园.地之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33,57.
{2}{3}{4} 铁凝.铁凝文集.六月的话题[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324,25,415.
{5} 铁凝.笨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325.
{7} 丛琳.植根于当代乡土中国的“笨花”[J]文艺评论2007:(4).
(责任编辑:范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