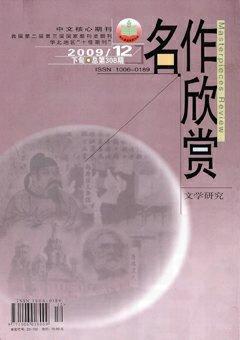试析阎连科小说的疾病意象
关键词:阎连科 疾病意象 性病 喉堵症 热病
摘 要:疾病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经验,也是文学表现的原型母题。阎连科作为一名有着“健康崇拜”情结的作家,善于用密集的疾病意象点缀文学审美空间,其耙耧世界里的性病、喉堵症、热病都蕴涵着丰富的道德修辞和文化隐喻。
疾病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经验,也是文学表现的原型母题。无论是中国古典诗词“多愁多病”的审美趣味,还是现代作家的“疾病情结”{1};无论是西方文学对“肺结核”的浪漫想象,还是艾滋病书写的世纪恐慌,各种各样的疾病意象爬满了文学空间。而文学时空里的疾病不再仅是生理意义的医学症候,而是灌注着社会文化意蕴。
在当代文学的疾病叙事里,阎连科的写作姿态引人注目。也许是对大姐早年穿透墙壁的疼痛哭声的铭心记忆,也许是对父亲染病早逝的内心愧疚的情感投射,也许是自身腰椎病折磨的痛楚经历,疾病既丰富着作家的生命体验,进而也引导着作品的精神漫游。在耙耧系列小说里,《耙耧天歌》里的“痴傻”、《日光流年》里的“性病”与“喉堵症”、《受活》里的“残疾”、《丁庄梦》里的“热病”、《风雅颂》里的“精神病”等疾病意象,成为文本绵延的叙事动力,成为人性度量的重要符码,成为文风氤氲的美学元素。由此,选取阎连科小说的疾病意象进行文本细读,可以品味和开掘耙耧世界独特的文学意蕴。
性病
《日光流年》里温柔美丽的蓝四十因性病而自杀。当司马蓝看到蓝四十的薄裤衩“被她用那把寒寒的剪子从正面用力扎下了五六剪、七八剪,甚或是十几、二十剪。那裤衩的前部已经成了一团红蜂窝,从蜂窝口漫出来的肉和血浆在她的两腿间枯蔫的牡丹一样烂漫着”,他内心充满着疑惑,直到发现她腿间碎烂的血肉中“长满的白粒如同一盘开盛又揉碎的白色花”,始才恍然明白蓝四十这次为了他的手术而做“卖肉营生”,得了不治的妇女病。然而,小说叙事似乎刻意回避着蓝四十的性病。如果仔细考量文本,只有六处“红淡淡的中药气息一丝一股地从院落起伏荡荡涌出来”的类似描写,且只是“漫不经心”的简单的一句话,药味背后谁在生病、何种病症、怎样治疗等油然而生的一系列疑问,均没有下文和解释。无论是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还是马舍雷的“沉默论”,都提示我们“遗漏”、“空白”、“沟壑”等没有说出的潜文本可能蕴涵着比显在文字更为重要的意义。由此,作家躲躲闪闪的性病“盲视”,有着丰富的话语蕴藉和强烈的意识形态。
蓝四十的性病有着鲜明的道德指向和文化修辞。无论是性欲的介入导致人类伊甸园的放逐,{2}还是中国“万恶淫为首”的警句,性一直被视为肮脏的、有罪的和需要规训与惩戒的,性病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披上道德审判的帘幕并刺烙耻辱的印记。虽然蓝四十以黄花闺女“侍奉”公社卢主任是为了三姓村能“吃上新土打的粮”,虽然她带领妇女去九都卖淫是为了凑资修渠,虽然她最后一次做“人肉生意”(此次患上性病)是为了村长司马蓝的手术,既实现与所爱的“合铺”宿愿,更可以早日完成引水工程,她把最私密的个人化的性爱,变成了献身集体利益的公共事件,但是,无论如何身体的不贞本身就意味着永远涤荡不尽的罪恶。由此,司马蓝尽管曾有“我要不娶你做我媳妇我天打五雷轰”的赌咒发誓,最终还是背叛了爱情,而“杜柏宁要三九不娶我”的行为,也使蓝四十悲伤地自知“我一辈子嫁不出去了”。何况还有杜竹翠几番“呼天叫地骂她是人世间的最烂的破鞋,是世上的人肉王”,还有亲妹妹说她“你还是猪,还是破鞋是婊子是肉王,你蓝四十至死都不配做我蓝三九的姐”。这一系列风刀霜剑无不使蓝四十遭遇民间价值的原罪屏障,经历“自我骤减”的心理惨痛,陷入无处诉说的精神暗夜。这样一位“集中国传统之大美、大善、大德”{3}的女性人物,在患上性病后无奈地整日大门紧闭过着不相往来的幽居生活,最后又用剪刀选择异常独特的自虐自戕方式。然而,那“红蜂窝状的肉和血浆”,是以死亡为代价的身体言说,既呈现和记录着她的耻辱与悲惨,也回旋着生命的呐喊与哀歌。
在“身体社会”,性已被视为原罪,因性而病更是声名狼藉,它不可宽恕且须惩戒。性病,不仅未能因为蓝四十的美丽善良和牺牲奉献而剥落历史叠加的道德污名,而且还成为她短暂生命旅程的凶猛杀手。她痴情地为爱活着,注视着当年的定情物而离开人世,无怨无悔地将爱情进行到底,甚至既为司马蓝也为三姓村几度肉身沉沦,但是,那本该应有的身体与灵魂的冲撞,情感与伦理的徘徊,以及道德折磨、生命留恋、自杀决绝的文学场景都付之阙如,小说文本没有留出足够文字进行描绘和倾听,没有提供探索人物内心隐秘世界的机会,即便是她的生命凋谢,也只是通过处于精神恍惚状态的司马蓝的视角给予客观展示。这样,蓝四十的身体似乎只是铭写事件的场所,她被定位于一个不会“发言”的、内囿的、从属的他者。在此遥望耙耧女性天空,不难从性病个案“透视性理解”穿越千年的悲剧处境,她们的历史就是单向“身受”的历史,她们囚禁于男权社会的栅栏苍凉无语地静默着。
喉 堵 症
喉堵症是《日光流年》里导致三姓村死亡遍布的生命杀手。三姓村位于三县交界耙耧山脉的深皱之间,它在明末清初可谓是水土两旺、人畜两盛的世外桃源。如果说“早些时候,村人多都害黑牙病、关节病,有的弯腰驼背、骨质疏松、肢体变形,甚至瘫痪在床”,只是拉开了疾病苦难的不祥序幕,那么,自从百余年前司马天仁最早发现喉堵症,这一死亡病魔便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成为村民一旦出生便注定活不过四十岁的生存处境。
喉堵症的病状,小说文本没有详述,只有“喉咙里开始肿胀得如喉管里塞了一段红萝卜”、“忍不住喉痛上吊了”、“开始吐血了”等简单概括性的寥寥数语。相比较而言,作家的兴致似乎集中于疾病的治疗。如果说司马蓝的曾祖爷动员村人迁徙出耙耧山脉,拐子杜桑号召村民多生育使生殖超过死亡,杜柏翻看《黄帝内经》熬喝“益寿汤”,一些村民到医院做“通喉”手术,尚不失为现实的理性的治疗处方,那么,司马南山的吃“青岛的盐和海带”与司马笑笑的“吃三年五年油菜,换一遍肠胃”,蓝百岁的深翻土地以“吃上新土长出的粮食”,司马蓝的修渠喝上灵隐水,则既是原始思维的现代翻版,同时又充满着寓言化色彩。意味深长的是,小说文本以主要篇幅浓墨重彩热情洋溢地叙述了护种油菜、翻地换土、修渠引水的曲折历程与壮观场景,而其余的治病方案仅仅是三言两语或轻描淡写地顺笔带过,这种具体病状的几近缺席与集体治疗的隆重出场,使喉堵症早已越出村民个人化的病历界限,上升成为耙耧世界社会痼疾的象征层面。
喉堵症既埋藏着又流露着作家的现代性反思与生存忧患。百余年前开始发病,愈演愈烈,这一精心预设正暗合着中国社会如火如荼的现代性进程。耙耧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可由古老的灵隐河作证。它曾经两岸山势俊美、林茂叶秀,河水清澈见底,受其滋养沿岸百姓多有百岁老人。于是,“那白色的水流声清脆悦耳”,多少年都流淌在司马蓝的脑海,特别是在翻地换土的那一刻,“脑子里水津津地生出了把这流水引到村落的绿色念头”。然而,现代化既带来经济繁荣的幸福畅想,同时也付出了生态摧残的重大代价。还是这一条灵隐河,在县城改市后两岸的林地早已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工厂和住宅区向上游的飞速蔓延,“使那水里没有了鸟,也没有了鱼,只有河面上面汤般的黏丝、发霉的草木,漆黑了的女人的红裤头,还有死猫、死猪、死雀”。由此,当小说有意让“乡城变成京城”时,文本设置的人物情感间离促使读者保持一份清醒与警惕,县城如“京城”般的繁华可能无须更多地欢乐礼赞,反而激起内心沉重的忧虑,因为正是这“乡城”到“京城”的语言变称,关联指涉着灵隐水的命运变迁和三姓村民的人生悲剧。灵隐水,被三姓村视为根治喉堵症的最后良方,为此他们不惜男人们卖皮、女人们卖淫凑资引水,不惜倾家荡产流血碎骨,但最终引来的却是“如夏天各家院落门前酵白的粪池味”的腥臭黑水。当寄寓多年殷殷期盼并付出惨重代价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突然蒸发,不难理解杜流跳水自杀的绝望心情。三姓村梦想以喝上灵隐水迈入长寿天堂,不料血肉献祭跨入的却是无底的死亡深渊。
其实,灵隐水根本承载不起治疗喉堵症之舟。小说里“洋伙”调查表明,在耙耧山脉,环绕三姓村数十里,除了有无法精确计算的超高水氟含量外,空气、土壤、植物中还有一种混合毒素,这种毒素中可能有126种元素外的新元素。小说在故事时间结束时的盖棺论定,把喉堵症隐喻地、永恒地定格,让三姓村坠入永世不能超度的无边黑暗。
热病
“热病”,是《丁庄梦》里村民对艾滋病的民间称谓。如果对其进行词源的知识考古,它于20世纪80年代出现在大陆报刊时,最初音译是半带幽默、半含讽刺的“爱滋病”。由“爱(性放纵)滋生的病”,在传统文化语境里自然增生了道德堕落的情感评判。因此,丁庄人曾认为,“热病都是外国人的病,城里人的病,心行不正的人才肯有的病”。于是,他们十天半月间的发烧,三朝二日地吐血,却都说是有了胃病,有了肝病,有了肺病,并以“热病”这一常见的感冒发烧症状自我宽慰。直到越来越多的村民如树叶飘落一样死掉了,如灯灭一样不在世上了,才突然灵醒那遥远的罪恶的艾滋病早已潜藏体内,那十年前卖血的人今天必得热病,得了热病必得要死。这当代版的“古典瘟疫”把丁庄人抛入恐怖的无助的死亡深谷。
热病病因在于沩县倡导的“血浆经济”。当年县教育局局长以每人每天补助十块钱、顺便看看二·七纪念塔的诱惑,动员村民到“致富模范县”参观。在上杨庄,大街上一律铺成的水泥地,家家居住的小洋楼,一应俱全的室内电器,去村委会自由领菜的日常生活,无不让丁庄人切身感受到浓烈花香里的温暖与和谐。卖血致富的“榜样”,既激发了他们对未来的乌托邦想象,同时也悄然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由此,丁庄轰的一声卖血卖疯了。卖血虽然直接催生了丁庄二层楼的新街,一年四季飘荡着新砖新瓦的硫磺味,但是缺乏医疗卫生条件的抽血方式,也导致了热病的大规模感染与传播,从而彻底粉碎了喧闹一时的“血浆经济”的致富神话。“致富”,曾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地畅行不衰声势浩大的现代性运动,其不断放大的光晕,既焕发了国民的激情也滋生着人性的疯狂。阎连科以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进行审美现代性反思,如果说在《日光流年》里是以喉堵症书写了当代生态忧患,那么在《丁庄梦》里则以热病表达了强烈而又沉痛的社会批判。
热病病状在《丁庄梦》里有着细致入微的描写。小说通过丁亮等人物叙事,较为完整地勾勒出其不同阶段的病理特征,如脸上、腰里、腿间到处都是疮痘并奇痒难耐,吃东西呕吐,最后肝疼、骨头疼等。这里如果把热病与喉堵症做一比较,会发现同样是苦熬苦等的绝症,作家处理却显现不同的叙事策略。《日光流年》里喉堵症的病状叙述语焉不详,小说重在以疾病象征突出三姓村的群体性灾难,以宏大叙事传达现代性的风险图景,承载时代社会的病象审判。《丁庄梦》里的热病整体上也属于现代性语境里的宏大叙事,也有鲜明的社会意识形态,但与此同时它对个人身体疼痛的聆听,对其慢性发展的耐心关注,对生命破碎的悲悯沉思,在桑塔格所谓疾病还原、“反对阐释”之中又开辟了“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的通道。“个体叙事只是个体生命的叹息和想象,是某一个获得过生命印痕或经历的人生变故。”{4}小说文本里,无论是赵德全把红绸袄递给媳妇心愿已了的离世,还是丁亮与玲玲梁祝式的现代演绎,“向死而生”的他们弹奏了个体生命的悲情与尊严。
热病的叙事功能是以日益迫近的死亡映照人性的镜像。热病的无药救治使患者无疑宣判了死刑,而它对生命的逐渐消耗,又留下了一定加速的时间进行人生谢幕的表演。热病们在村小学过着集体生活,共同吃饭、熬药、娱乐,“人自由得像是草地上的蒲公英”,但谁料想竟然会发生丢粮食丢钱丢公章的偷盗行为,有人会在收缴的米面袋里掺塞砖石瓦块。他们骗婚,明知道热病传染,还编造谎言以迎娶外庄姑娘;他们贪财,哄抢瓜分学校的东西,连夜砍光村庄的树木;他们爱权,不择手段地攫取村委会的官位,临死还不忘把公章埋到坟里陪葬;他们疯狂,丁嘴嘴只是讲了一个老掉牙的笑话,就因“你凭啥活得这样高兴”被人活活砍死。濒临没有未来的死亡,他们拼命扭动欲望之舞,彻底毁灭了世代生存的家园。
热病的死亡恐惧既敞开了人性的幽暗,也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因为“疾病不仅是受难的史诗,而且也是某种形式自我超越的契机”{5}。的确,如果不是热病,丁亮是宋婷婷的男人,玲玲是丁小明的媳妇,他们可能一辈子都难以走到一起。即便走到一起,道德的压力与习俗的禁锢也会让他们望而生畏和却步。也许“在死的时刻,生之大门才敞开它的全部现实性。亦即死是有限生命的自我意识,是对感性存在的有限性领悟,它迫使人们去关切自身生存的价值和意义”{6}。正是由于死亡的胁迫唤醒了海德格尔所谓的生命“沉沦”,丁亮和玲玲“明目张胆”地、“夫妻样”地、“胆大妄为”地住到一块,他们甘愿放弃家产,相爱得大胆热烈,感天动地,一个不顾危险地用凉水浇身以相拥降温,一个用菜刀自杀以下世追随,以爱情与死亡的恋曲获得生命的升华和存在的深度。
疾病不仅属于生理世界,同时还属于意义世界,它以人本质上的肉身存在汇聚漂浮着社会、文化、伦理的各种话语。阎连科作为一名身患疾病和有着“健康崇拜”{7}情结的作家,善于用密集的疾病意象点缀文学的审美空间,既塑造形成了语言、文风的病幻风格,也为我们提供了别样的历史症候、文化视域和人生终极关怀。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08FWX0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保亮,洛阳理工学院中文系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车红梅.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疾病情结”[J].文艺争鸣,2005(1).
② 凯特·米利特.性政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③ 阎连科、侯丽艳.关于《日光流年》的对话[J].小说评论,1999(4).
④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⑤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⑥ 靳凤林.死,而后生——死亡现象学视阈中的生存伦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⑦ 阎连科、晓苏.文学·生活·想象——阎连科访谈录[J].语文教学与研究,2001(18).
(责任编辑:吕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