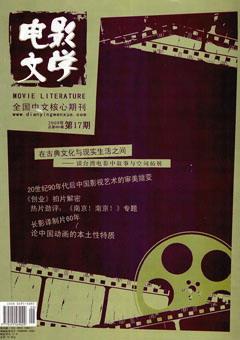东影译制片:母亲成就理想的地方
李东东
母亲李景超在生命最后的一两年里,记忆力已经严重减退,严重到有时连家人的名字都叫不上来。可每当问起长影译制片来,她仍能说出译制片许多同事的名字。长影留给母亲的印象太深刻了!
从1949年8月来到长春,到1983年离休,她在长影整整工作了34年。到她去世的2008年,她在长春整整生活了59年。作为一个电影译制演员和导演,她对配音生涯的记忆,当然在头脑里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她和许多译制片的同伴们一样,把这个事业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
晚年的母亲,病魔缠身,但每当她回忆起译制片的历程,就会忘掉病痛。她常讲,早年的电影观众像今天的歌迷、粉丝一样狂热。译制片在中国观众心目中,同样占据着重要位置。有一年东影的译制片演员出席某片的首映式与观众见面,他们站在舞台上面向观众说话时,观众在台下齐刷刷地把他们的名字喊出来:这是李景超、这是向隽殊、这是车轩、这是白景晟……我能想象出当年的盛况,那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场面啊!做一个译制片的演员或导演,该是多么的荣耀和辉煌!
新中国电影译制工作起步之初,母亲和她的同事们,从四面八方走到一起,也许最初是偶然,但这辉煌决不是一个偶然就可以创造出来的,那是许多电影人的勤奋、智慧和生活磨难赋予他们的才干所创造的。
母亲生于北京,抗战时流亡中原、西北,经历了无数坎坷。她从幼年起就热爱艺术,正是这种对艺术的执著与追求伴随她走过艰难。
1949年的1月,北平的飞机场由西苑搬到了南苑,又搬进了天坛,进而飞机已在东单练兵场起落了。当时母亲、父亲就住在西四颁赏胡同,每天晚上都能听到枪声和炮弹穿透夜空的呼啸声,全城处在迷茫之中。北京的和平解放,开始了这座古城的新生命。
3月,北京各报纸上刊登了华北大学招生的消息,动员有文化的青年人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母亲当时刚刚有了第一个孩子(我的大姐),看到消息,就去投考华北大学第三部。华北大学的校长是吴玉章,一部为政治部,二部为教育部,三部是文艺学院,也就是今天中央戏剧学院的前身,院部主任为光未然。考试时母亲讲述了自己的生活和演过话剧的经历,还唱了一支歌,就考上了。
经过半年学习之后,1949年8月里,袁乃晨同志风尘仆仆地从东北来到华北大学,为新中国电影译制工作选取配音演员。母亲从未到过东北,只听人说过东北奇冷,冬天会冻掉下巴,可是电影的魅力远远超过了寒冷对人的威胁,母亲也报了名。
母亲自幼喜爱表演,嗓音清晰亮丽,、兑一U标准的北京话,又有过话剧表演的基础,经过了一番声音素质和声音表现力的考试、筛选,一下子被选中。母亲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的袁乃晨穿一身军装,非常年轻,干练果断,人又十分和蔼可亲,给她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这一次一共录取了八个人:李景超、白景晟、车轩、向隽殊、尉骞、薛挽澜(彭勃)、张珉和赵双城。当时母亲咬着牙果断地决定:把不到一岁的大女儿留在天津的老人家里,几天之后就和其他同伴一起登上了去长春的列车,那一年,母亲24岁。
母亲说,刚刚进入东影时,厂区是一片荒芜,战争的痕迹到处可见,除主楼外四周都是残垣断壁。那天她们一进厂,就看见在第一录音棚外躺着一具马骨,白森森的骨架很吓人。当时厂里实行供给制,职工们都穿着统一发的军装,俗称“二尺半”,而母亲和向隽殊阿姨都穿着自己织的毛衣外套,别人看着很新鲜,称她们是“北京来的大学生”。但很快,“北京来的大学生”融进了东影的干部和职工中间。大家在一起学习、交流、创作、劳动,真有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觉。每天清晨,泽制片的年轻人都在厂外喊嗓练功,形成了刻苦练本领的风气。刚刚经历过战争的城市,到处都是战火的痕迹,当时的六宿舍是一片废墟,演员们就脚踩废墟迎着阳光在那里练习发声、朗诵,他们知道将来这里会建起新的厂房、宿舍,知道这里充满希望……
1949年9月,母亲他们一进厂,就参加了新中国第二部译制片《俄国问题》的配音工作,到年底,影片已经在全国放映了。据陈占河导演回忆:他和华大的其他同学在当年10月分配到新成立的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那年北影还没有生产,他们整天在大食堂里学习,没有工作可做。有一天,厂里放映苏联影片《俄国问题》,他们惊喜地看到字幕上有白景晟、李景超、向隽殊等人的名字,大家高兴地叫起来,这不是咱们同学吗?随即嫂论起来:看人家,都译制出影片了,可咱们还在这里无所事事。大家一商量,就向电影局打了报告,申清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工作。局里很快批复同意,因为东影太需要人了。这年年底,又一批华大毕业生陈占河、赵琪、徐世彦、高步、凌萃等来到东影,投入了译制片的工作。
在刚刚进入东影译制片的1949年9月到12月,母亲就参加并完成了《俄国问题》和《蔚蓝色的道路》两部苏联影片的译制,在片中她都是担任女主角。最初搞配音没有经验,对口形成了工作的最难点。背台词,大家都能背得滚瓜烂熟,可一对口形就难了,母亲和伙伴们在实践中反复摸索,他们数字数,找节奏,也就是说,先数准俄语的音节,再对应汉语的字数,来调整速度。用的虽然是笨办法,可的确让演员们找到了配音的规律。当时的学俄语热,也是为了了解原片语言的节奏和语感,从中找出译配的规律来。母亲说,要做得好,其实没有窍门和捷径,就是要下工夫反复练习,要细心。当时在厂内工作的苏联专家格列布涅夫夫妇发明了一种“循环盘”,用它挂上胶片可以不用停机反复放映,这样就给演员们反复练习提供了许多方便。一直到了上世纪90年代,母亲还常常提起这件事,说这是格列布涅夫夫妇对长影译制片的贡献,她怀念这对夫妇,一直盼望能再次见到他们。
母亲在1954年以后做了译制片导演,工作更忙了,记忆里,几天见不到母亲是很平常的事。1986年肖南导演写了一本《一个配音演员的日记》,当时送给母亲一本。我看到他在扉页上写道:“景超同志:我永远记忆着我们那一天连续录音30多个小时的情景,人们都睡在地毯上——好像我们这里是另一个‘斯莫尔尼。”这段画再现了母亲他们那一代人在录音棚里忘我工作的情景,让我感动了很久。那时配音任务多、任务重,需要常常加班,彻夜工作已经习以为常。他们当年译制的多是苏联的革命英雄主义影片,他们在电影里塑造的是革命英雄,在影片外,他们也用革命英雄做榜样,用英雄的精神来工作。泽制片演职员们为了更好地理解苏联影片、更好地塑造人物,还兴起了一股学习俄语的热潮。后来在好多年里,母亲下班一回到家,就用俄语喊我们:我的可爱的、漂亮的女儿们,我回来了……逗得我们哈哈大笑也跟着学。母亲一直到60多岁时,还记得她曾经泽配的《政府委员》中女主角的一段重要台词,还能用俄浯朗读出来。在家中的书架上,母亲最常读的书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那本书已经翻得飞了边、卷了角;还有《我的艺术生活》《电影演员的角色创作》等,以及托尔斯泰、契河夫等作家的小说和剧作;也有《列宁选集》《联共(布)
党史》等政治书籍。母亲说把苏联的历史和现实弄懂了,我们才能理解苏联的电影。
母亲和同事们逐渐找到了配音创作的规律,把电影配音艺术做到臻于完美、精益求精,并形成了长影泽制片独特的风格特色。从1950年以后,长影的译制片工作大幅度发展,生产任务最多的上世纪50年代,几乎每个月有三四部外国电影被译制出来,发往全国的城乡影院。当时东影的故事片生产还不够成熟,译制片就挑起了全厂生产的大梁,每个人都把为电影厂创造经济效益挂在嘴边,记在心里。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国家经济还很困难,当时电影都是光学录音,为了节约胶片,袁乃晨同志曾提出了“五千米OK运动”。意思是争取五千米不翻面,一次录成。大家搞起了劳动竞赛,汀出节约指标,缩短周期,成本核算的经营观念就是从这时候深入人心的。最多的一年1956年译制片出品了56部影片(当年全国各厂摄制的故事片、戏曲片总数才63部),给长影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那时每次完成一部翻译片在厂里放映的时候,全厂像过节一样,大家不光是爱看苏联电影,许多人把它当成学习电影艺术的宝贵资料。
20世纪60年代前后,译制片组织的舞台剧演出给许多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记得小时候家里经常高朋满座,除了译制片的叔叔阿姨常常来家交流、切磋艺术,还有不少父母的艺术界朋友们,王晓棠阿姨曾和母亲在家里清唱过京剧,云南的歌唱家也在家里演唱过。1962年,中国评剧院来长拍摄《花为媒》,其中一些演员与长影京剧票友在工人文化宫、长影剧场合演过京剧《龙风呈祥》,母亲与父亲李荣滏分别饰演剧中角色孙尚香、刘备。我还看过母亲和同事们演出的京剧《打渔杀家》《三不愿意》,也看过译制片剧组演出的、由母亲执导的《日出》《全家福》《钗头凤》《南方来信》《李双双》等画剧,其中《日出》有上海的艺术家高博、李景波参加,演出之后轰动了整个东北。《钗头凤》这个剧目,从东北三省演到关内,在许多城市里盛况空前。这些演出丰富了艺术实践,也为厂里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还记得后来《钗头凤》准备南下,黄世光同志去上海联系演出,那时已出现“文革”前兆,未能成行……
如今,母亲和我熟悉的许多叔叔、阿姨都已作古,离我们而去,可他们人虽去声犹在,他们留下的作品至今仍是观众喜爱的,那是对他们人生最好的告慰。今天我走在长影花园似的厂区里,看到母亲和她的同事们栽下的树早已长得高大茂密,仿佛他们的音容笑貌犹在树丛间;静谧的老录音棚让人感到那样安详、亲切,那些年年会盛开出五颜六色鲜花的花圃,永远闪动着电影人特有的风采和活力。
拉拉杂杂写下了这些怀念的文字,一则为纪念我刚刚逝去的母亲李景超,也为向我所尊敬的长影译制片前辈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