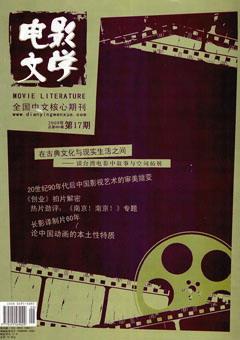东影
向隽殊
时光荏苒,转眼间,60年过去。60年的风雨历程,60年的艺术人生,桩桩件件刻骨铭心,许多珍贵的镜头虽年深日久也未曾淡忘,它已化作记忆中的永恒,伴随我终生。
难忘的摇篮
建国前夕,新中国第一部译制片《一个普通的战士》在东北电影制片厂诞生了,上映后好评如潮。厂领导极其重视这一现象,认识到新中国需要开拓一种新型艺术——电影译制事业。当时,我国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日渐频繁,国外著名影片大量引进,特别是译配前苏联的影片是东影的重要生产任务之一。为了使译制片更上一层楼,从根本上解决演员的声音素质及标准语言问题,遂派人专程赴京从华北大学戏剧专业中挑选了白景晟、车轩、李景超、尉骞、张珉、薛挽澜、赵双城和我一行8人充实东影厂译制片组。
电影,在年轻人的眼里该是一项多么诱人的事业呀!一切都是那样新鲜、那么神秘。译制片组的负责人袁乃晨既是久经战火考验的革命前辈,又是一位具有使命感的艺术家。他带我们或去录音棚试音,或到放映大厅观看国外原版故事片。他满怀激情地向我们描绘着未来的美好前景,决心带领译制片组成员在设备陈旧简陋的情况下不断创造条件,去完成一部部生动的可与原片媲美的译制片。我想起在华大学习时,曾看过一部由久居国外的华侨配音制成的所谓华语对白片。不但声音和口型不相吻合,语言又是北调南腔,悲哀的感情引人发笑,本是扣人心弦的情节,观众却不知所云,无动于衷。因此,作为一名称职的译制片演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不能仅凭自身的条件去照本宣科,要不断充实自己多方面的素养,要在艺术创作上有追求、有信念、有实力……我生平第一次把精益求精与心中的艺术结合起来,于是,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油然而生。
就这样,我和志同道合的同事们切磋琢磨,全身心地投入各类影片之中,了解它们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熟悉一个个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地位、年龄、性格的角色,依据原片进行二度创作,使自己身临其境,把全部的爱和感情融会其中。几十年来,我感同身受般经历了那么多角色的人生,既体味出世间曲折艰辛的苦辣甜酸,也领略了真情大爱的五彩缤纷。于是,我走进一个个人物的内心世界:《流浪者》里对恋人一往情深的丽达,《忠诚》里历尽忠贞考验的妻子艾明娜,《复活》中备受摧残而良知未泯的玛丝洛娃,《静静的顿河》中整个心儿都为葛利高里燃烧的阿克西妮亚,《人证》里为维持上流社会地位竟酿成人间悲剧的八杉恭子,《永恒的爱情》里向亲人声声泣血地倾诉诀别之隋的罗西……
感谢东影,给了我艺术生命,使我从一名文艺爱好者成为新中国第一代译制片演员;感谢东影,催我奋发进取,使我将全部情感倾注在一个个为我所爱的角色之中。
难忘东影啊——我的艺术摇篮!
珍贵的镜头
多少年来,我们在艺术海洋中畅游奔波,多少珍贵的镜头深深镌刻在心灵深处,尽管时光不断流逝,然而,那些底片永远不曾褪色,永远不会消失。
记得初到电影厂,我和我的合作伙伴们互帮互学,先是纠正一些同志的地方音,继而克服做作的翻译腔调,使译配的角色语言生活化;大家精读原著,一起研讨剧本,努力使声音感情与原片人物吻合得天衣无缝。我忽然觉得我们是在担负着友谊使者的重任。看哪,自己的声音插上了翅膀,同角色的人生同步飞翔。观众在影院欣赏着一部部世界名片,同时也获得了视觉与听觉的完美统一。这种对观众、对演员同样强烈的感染力与冲击力,绝对是一种艺术享受。我庆幸自己从事的是一项多么令人喜爱的事业啊!
生活像一朵朵欢乐的浪花,我的心中充满了喜悦。我爱我们这个和谐温馨的集体,大家相亲相爱像一个家庭。发生在身边的感人故事数也数不清,让我只撷取其中两例:记得一次配音任务很重,我要连夜背词,第二天就要实录了,可孩子病了,发着高烧。李景超导演听说后,连夜赶到医院,她坚持留下来陪护,催我快些回家。当时她斩钉截铁地说:隽殊,昕我的话!好好休息,爱护嗓子!如今,她的话音犹在耳,人却永远地去了,我再也听不到她对我的叮嘱了——但她那关爱的表情亲切的话语,留存在我心中永远不会忘记。记得有一天,我们上演话剧《年青一代》,我母亲猝然去世。而当天的门票已被订购一空,剧团既不能停演,换角色也来不及。在这非同寻常的时刻,我想到的是广大观众。我亲爱的同事们想到的是为我分忧,一些人特地赶到家里帮我料理后事。当我含着泪水走进后台时,静悄悄的化妆间里没有人说话,而人们关切的目光中却流露着无尽的言说。化妆师默默拭干我脸颊上不断流淌的泪水,一遍遍地为我补妆;同台的演员静静地帮我拿服装、递道具、把上场门轻轻地推开……许多年过去了,这一场景——朋友们给予我的无声慰藉,仿佛就在H艮前。
多年来,在配音道路上,我有幸在烟波浩渺的历史长河里,接触了各个国家、各个时代、各种身份的女性:曾配饰过纯真无邪的少女,也表现过萍踪浪迹的烟花女子;配饰过正气凛然的革命者,也表现过被侮辱被损害的灵魂;配饰过权倾一时的贵夫人,也表现过质地美好的贫家女;配饰过正面人物,也塑造过反面形象。在年龄跨度以及音域幅度上,接触过老中青各种年龄段、各种性格的女性,却惟独没有配饰过小女孩。记得当我接受《战争与和平》女主角配音任务时,感到此片既有深度又有难度。影片开始时,娜塔莎只是个未谙世事的小姑娘,导演为难了,怎么解决她的童年配音呢?如果找来一个同龄女孩,如此深刻的主题,复杂的剧情,恐怕难以配出戏来,何况音色音质也会同我有差异。我望着大家期盼的眼神,忽然产生了勇气。是的,一个真正的演员不该定型化。应具有挑战自我的能力,遂提出由自己试试看。感谢导演和同志们对我的信任和鼓励,有了这第一次,便有了新的感悟,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难题,都会想方设法努力去开拓、扩展自己的语言表现力。
演员的主体表演与观众的客体观赏,二者密不可分。我们常常在完成译制片之余,也排演舞台剧,代表作如20世纪50年代塑造《雷雨》中的繁漪,20世纪60年代扮演《钗头风》中的唐婉等。舞台剧中大起大落的感情变化,以及故事情节的起伏跌宕,对演员掌握语言节奏,表现人物感情大有裨益。舞台剧要一气呵成,不但在短短的两个小时之内,演绎出人间百味,而且很快又能获得观众的反馈。一次,演罢《钗头风》,当我们离开剧场时,夜已经很深了。只见许多观众还等在雨地里,一位年轻的妈妈抱着幼儿挤到我身边,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而她,只想对我说声谢谢,顿时我热泪盈眶,觉得向观众、向这位女士道谢的应该是我。还记得1978年,我在《姜花开了的时候》塑造了一位年轻的打入敌营的共产党员,演出结束后,话剧界的几位同行特地到后台祝贺,她们说一定要为演员的“青春”干杯!
是的,不只是同行,观众对我的情谊和厚爱也难以忘怀。多年来,我收到许多封热情洋溢的信。有位大学生说,《流浪者》一口气看了十四遍,声称还会看第十五遍!他说因为影片的歌美、舞美、演员漂亮,剧情感人,
尤其是女主角丽达的表演和您那字字句句都动以真情的配音,真真切切地感动了我。有位解放军同志说:只要是您配的音,我每片必看,甚至觉得由您配音的那个角色就是您本人。因为声音能和角色如此吻合,一定是您对所塑造的人物倾注了深情,不只是追求形似,而是真正做到了神似。请不要笑我,我总是同您所配音的人物如花妮、春香、罗西、艾明娜……一起流下热泪。有位青年学子写信说:每次看您配音的影片,我都激动不已。比如《萨特阔》中伊尔明公主放萨特阔乘海马逃去时,您发出了“快走!不然我要变心了!”的呼喊,这一句话,道出了人物内心复杂的情感,我听到四座发出一片“啧啧”的感佩之声。还记得我看《教师》的第二天,历史课老师也像《教师》中的教师那样,提问我俄国农民革命的性质,我当即把您在影片中的回答流利地背诵了,老师(也是您的影迷)惊诧地脱口而出:难道你也看过《教师》?这次我被提问的成绩获得了满分,我真开心!
“文革”之后,一位老观众在信中写道:我看《舞台生涯》,片头没有泽制演职员表,但一听那年轻的芭蕾舞演员黛丽的配音,便感觉像是您的嗓音,当我真的从片尾看到您的名字时,我激动极了,为经历十年浩劫之后,我们国家仍保留了您这位艺术家而庆幸。一位年轻观众来信说:今年春节,当我和朋友们看了由您译配的新片《奇普里昂-波隆贝斯库》时,我们一起议论过,给人如此诗情感受的嗓音,一定是位非常非常年轻的姑娘;后来,我们又看了您许多年前《百万英镑》的配音,大家惊奇不已,纷纷推选我立刻写信向您祝贺,祝贺发生在您身上“青春永驻”的奇迹。
我的心底还留存着一组珍贵的镜头:
记得那是1962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邓大姐到长影厂视察。在录音棚里,我亲耳聆听了总理的教海与勉励,还荣幸地同总理对话。总理问:“你是哪里人?”我答:“北京人。”总理笑着对邓大姐说:“她的语音很纯正啊!”接着又转向我:“你是什么时候到长影的?”我答:“建国前夕。”总理微笑地望着在场的译制片演员们,高兴地说:“你们老演员很多,年轻人也不少,年轻演员应向老同志学习。”那一天,总理的兴致很高,他对大家说道:
“你们都是幕后英雄嘛,今后片头上也可以有你们的形象!”
记得2005年中国电影百年庆典上,我被列为50名有突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之一。那天,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地接见了我们,当胡锦涛主席同我握手时,留下了一帧十分珍贵的照片。
多年来,我在译制片工作中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却获得了党和国家的表彰,获得了政府和人民给予我的多种奖励。我忘不了那年在首都体育馆内,当主持人宣布由本届金鸡奖、百花奖的获奖演员为首都观众作精彩表演时,我看到万人大厅里一片沸腾……对于这些崇高的荣誉,我充满感激之情:感激党多年来的培养教育;感激老一辈艺术家的言传身教;感激同我8工作的导演、翻泽、录音师和演员们的帮助;感激广大观众的热情鼓励;最后特别要感激东影~长影,您是我的艺术摇篮,是培育我成长的地方。荣誉不只属于我个人,那是群体的智慧,群体的创造啊!
我相信译制事业是永恒的事业,相信我国的译制艺术会发扬光大,祝愿一代代承上启下的有志者,期望他(她)们用心、用爱、用我们民族优美的文化语言,架起一座座和平友谊的桥梁。
——译制片配音艺术浅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