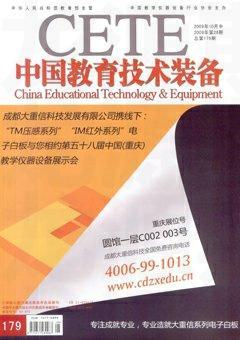教育学的语义转向与教师的角色重建
马艳萍
摘 要教育学中,本质主义的终结、强势话语的消解以及文本意义的僭越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了更为充裕的空间与自由度。教师不再是理论与实践之间被动的导体,而是二者之间积极活动的对话者。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现实背景下,教师的反思实践者角色、理论的调和者角色以及理论诠释者角色的凸显与建构具有鲜活的时代意义。
关键词教育学;语义转向;教师角色
在教育界,教育学正在或将要发生这样的语义转向:理论不再是学究式的规律证明,而趋向多样的意义阐释;实践不再是理论的机械应用,而是理论发展的力量;教师不再是理论之于实践的被动传输者,而是二者之间积极活动的对话者。对本质的解构、对统一的拒绝、对规范的超越、对教育生活本身的关注,是这一转向的主要显在特征。
教育学意义中的单向度、确定性与强制性元素逐渐消逝,取而代之的是多元化、互动性与民主参与的显现与强化。这一转变“不仅引起人与人、人与事之间的关系结构重建,而且引起个体文化心理的意义结构调整和实践智慧的生成”[1]。教师作为课程改革中的关键性存在,也应转变传统的“路径依赖”“机械控制”“单向传递”的惯力与定势,而具有更高的实践智慧与专业素养。
一、本质主义的终结与教师的反思实践者角色
传统教育学承继了其哲学母体对事物本原追寻的一切基因,对本质、规律表现出极大的爱好与迷恋。
启蒙运动以后,受科学实证主义的“启发”,教育学引入了“目标”“测量”“标准”等颇具科学色彩的话语,企图通过移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对教育客观规律的研究与求证而走上科学化的道路。不料,却更加远离了教育的内在逻辑、远离了教育最本真的生命指归,传统教育学中的本质主义、化约主义等严重影响了教育及教育学的发展。
一般认为,本质是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4]。事物的本质是内隐的、深藏不露的,不能直接简单直观地被认识,只能通过对外在的、可观察与测量的现象来研究,即“透过现象看本质”。相对于本质,现象总是后来的、派生的,所以现象总是本质在时间上的拖延,时间不可逆转,本质也就无法追寻,因为有现象就代表着本质已经逝去,没有现象则无法“透过现象看本质”。故本质无法认识,一切事物的本质都是在一个巨大的非本质的现象网络中得以暂时的栖息,所谓的本质事实上只是一种拖延于此的现象的承诺,并不存在所谓恒定不变的本质,只存在不断外显与拖延着的现象在不同场景中的流动着的意义。教育本质的坍塌宣告了传统教育学价值的祛魅,传统教育学中的本质、规律、结构将被悬置[5]。
杜威讲,“教育即生活”。“生活”可理解为“生”出“活”来,“活”有鲜活、活动的意思,说明教育要面对的、要研究的是学生鲜活的人的内在世界,丰富的活动。教育学的视野应该转向对教育的本真生活的关注,对学生内心世界的关注,对充满生命活力的课堂的关注。对于此,教师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教师不再是技工、操作手,而转向对教育问题的关注,过真实的教育生活,成为一名“反思性实践者”。
在实际水平上,教师的教育叙事研究是一种很好的方式,通过写日志、写教育札记、写教育博客、讲故事、经验交流等方式,“从亲身经历中梳理、寻找教育故事、在独特的叙述、言说、反思中,通过真实、有意义的经历描写与写作,回味自己的体验,探索其中的意义,引起共鸣、唤起同思、获得心灵的颤动和精神的震撼”[6]。通过反思,教师可以将凭借经验所感知的模糊的、纷乱的和不确定的情境转化为一个清晰的、连贯的和确定的新的情境。教师的意义与价值在此得以体现与升华,从而拥有真正的教育教育生活,成为一名真正的教育者。
二、霸权话语的消解与教师的理论调和者角色
哲学史上长期的二元对立斗争,在潜意识里形成了人们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总是试图从一个确定性的理想出发,择其一元而拒拆另一元。这在教育学中得到进一步的演绎和病理化,即“对方反对的就是我们赞成的,对方赞成的就是我们反对的”。在教育发展史上表现出一种明显的 “跷跷板现象”,即人们对某一教育问题的认识常常在两个(或多个)极端化的观点之间无穷的较量,忽上忽下、时冷时热。如个人与社会、知识与经验,教材逻辑与学生心理、个性与习惯、教师与学生等。实践证明,自身存在着的致命性弱点恰恰是对先前观点抨击最为严厉的、最鲜明的地方。“唯一正确的方法”往往是对事物真相的歪曲。某些权威者一时心血来潮似的极端的个人主观构想造成了事情真相的“遮蔽”,教育该何去何从难以把握。
在看问题时,应从既定的思维模式、既定的研究视角中跳出来,换一种思维方式,换一个视角看问题。对现实世界的解释不能是一元的、单向度的,而应是多元的、多视角的。正如当只有一个力作用在物体上时,它是不可能处于平衡状态的,这个力反而应该叫做使该物体发生偏向的“偏力”,但如果两个或多个这样的“偏力”作用在物体上就有可能处于平衡状态。对于同一教育问题,不同的理解者在不同的境域、不同时期可能有不同的解释。故教育理论者无论怎样标榜自己的理论论证多么的充分、逻辑多么的严密、用词多么的绝对,至多也是教育理论者主观的、暂时的、基于某一视角的解释罢了。
一个不断地推动、提醒我们转过来探究反思种种情况和条件的人,才是真正的对话者,所以,我们不是要排除偏见,而是要正确地认识并超越它。目前,正值我国的实行课程改革,更应避免这种缺乏理性思考的“追风”弊病。对于相互对立的观点,不能简单地做正确与错误的划分,最终选择一种“正确的”观点,抛弃另一观点,而应该在各种观点之间加以调和,这种调和并不是以辩证法的方式将这种对立扬弃,而是将这种对立看成是思维中永远产生作用的两种对立立场的反映。将所有观点投放到各种教学情景中,让事物“如其所是”的那样显现出来,达到一种“无蔽”状态。通过分析各种理论观点的交叉点与分歧点,构建起的更多的联系性,深化对事物意义的理解。
新课程改革提倡体验并非不要知识,培养情感并非忽略认知,提倡探究并非拒绝讲授,重视学生并非要取消教师。教育是一种复杂的活动,学生的身心发展需要各个方面的积极配合。强调任意一方而忽略另一方都是不明智的,调和者的作用在于,通过了解各种观点的意义以及学生的内在需求,找到最佳的结合点,为有意义的教学服务。在此,观点得以融合,学生得以发展,教师得以提高,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
三、文本意义的僭越与教师的理论诠释者角色
理论与实践是相互联系的、一体化的活动,而不是单向的、序列化的步骤化的活动。课程改革中企图把专家、学者的先进意识移植到教师的思维中的做法是不能奏效的。课程改革不是一种思想的印制行为,而是一种对话与转变的过程,没有对话就没有转变。理论的意义是教师内在的适应并积极寻求的,而非强加的。传统教育学中那种“超然智力姿态”的存在,因将理论凌驾于教育实践者的思维之上,也把自己孤立于教育实践场景之外。在这种先验主义、非历史主义的教育学话语体系下,教育理论没有创造、没有生成,也没有情景。
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面临这样的困境:满腹思想张口欲说却难以言表,提笔欲书却不知从何处下笔,符号或文本的表现形式对于丰富思绪的舒展显得无力与苍白。同时,语言、文本所要表达的意义也不可能在它原来的意义上毫无歧义地被解读、指称,总被曲解或异化。理论的提出者与解读者之间存在着各种差距,这些由时间间距、历史情景、个人素质、文化程度等所引起的差异是不可能消除的。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所有想精确重建过去意义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文本的意义也不是已然存在的,它要由读者和作者一起来加以创造,甚至可以说文本的意义完全要由读者来加以创造,而与作者不相干,因为文本的意义只能在解释者的解释中才能得到确定。对于任何一个文本,我们只能创造出我们所能理解的意义,文本之所以存在,就因为意义的创造所需,文本的多意性也正是意义的栖息之地。文本意义的僭越宣告了传统教育学中文本意义的绝对确定性的消逝。理论的文本不管语言多么的时髦、风格多么的现代、形式多么的自由,既不能圆满表达作者的意图,也不能被读者圆满的解读,更不能企图让读者理解作者的原意。
当我们面对一个强制立即执行的文件时,常表现出拒斥或敷衍了事,当面临一个开放性的、具有启发性的文本(如故事)时,则会表现出一种积极的、与之融合的态度,这是一种生物体内部的自组织力量。因此,当课程理论、教学计划不是采用固定的、规划好的结构而是宽松的、多少带有一定不确定行动方式表述时,教师就会将理论与实际的教学情景、学科知识的结构、学生的发展特点、自己的教学经验积极地融合,并对理论赋予实际的、具有实践意义的解释。这样教师不再是理论之于实践的被动传输者,而是在自身与文本之间积极调和的活动者,教师通过与理论文本的互动而成为理论的诠释者、理论意义的激发者,每一次实践活动都是对理论的一种补充、增加、发展。随着课程的进行,理论的意义愈加明确,并在不断合作中获得。在这样一种动态的系统中,教师与理论文本相互作用,使理论趋向一种无限多样、无穷增殖的永恒运动之中。教师与学生的相互作用,彼此臻于成熟,从而创造出教师与学生自己的课程。■
参考文献
[1]杨小微.转型时代教育者的生存智 慧[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7(1):1.
[2][德]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教育学 讲授纲要[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 社,1989.10.
[3]郝德永.课程与文化:一个后现代的检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334.
[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61.
[5]王治河.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增补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6,
[6]苗洪霞,徐瑞.教育叙事研究的 理想追求与现实困境[J].教育发 展研究.2007.
[7]岳龙.教育叙事:感悟教师的真实生活[N].教育时报.2004-02-05 (3).
(作者单位:河南省汤阴县第一中学)
——《教育学原理研究》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