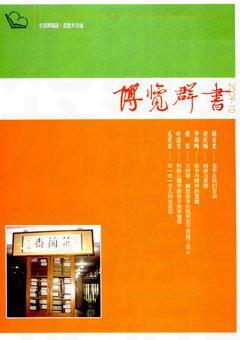读书与精神的重建
李剑鸣
我认为,新中国6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10种书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马克思、恩格斯著,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毛泽东选集》(第1—4卷),毛泽东著,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鲁迅全集》,鲁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后陆续出版。
《红楼梦》,曹雪芹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
《唐诗三百首》,蘅塘退士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著,三联书店,1987年版。
《顾准文集》,顾准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钱锺书集》,钱锺书著,三联书店,2001年版。
《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著,中华书局,1982年版。
今天,即使不到书店或图书馆,只是站在自己家里的书柜跟前,我都有一种强烈的感受:书太多,想读的书怎么也读不完。现在,我们的阅读已是高度的多样化,在种类繁多、难以计数的书籍中,要找出哪几种书最具影响力,显然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然则在我开始识字和读书的年代,情况恰好相反:书太少,允许读、而且能读到的书更少。因此,要从当年读过的书中选几种印象最深的,真可谓易如反掌。
虽说每个人的“阅读史”都是独特的,但或多或少总会带有时代的烙印。就读书而言,我们这一代人是格外不幸的。我们在“文革”的高潮中发蒙读书,待到“文革”结束时,我们已经高中毕业了。“文革”与其说是一场政治和社会的“动乱”,不如说是一种罕见的思想文化“暴政”。它对我们国民的精神和创造力的伤害,其烈度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在那个时代,多数有阅读能力的人都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读书生活。当时盛行某种“反智主义”风气,往往把读书人和“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联系起来,不鼓励读书,或者不允许读某些书。再者,我那时所能见到的“书”,除了课本,主要是《毛选》和鲁迅著作。自由而快乐地读书,在那个年代,在我所生活的偏僻闭塞的乡间,似乎只是一种新奇的想法。
早年的读书经历,给我留下了两种至今都未消除的“后遗症”。一是在最能读书的年纪,却没有读到多少该读的书;二是养成了一种迷信书的心态,习惯于被动地接受知识。相对说来,后者让我付出了更痛苦的代价。古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西哲也称“权威性阅读”容易导致思想的“奴化”。我早年接触的书,都是当时认为“正确”而“健康”的读物;对于书中的知识和观点,甚至每一个字,都是自觉地加以接受和相信。“读书须有疑”这种“异端邪说”,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由此造成了这样一种状况:知识单一而贫乏,眼界狭隘而僵化,缺乏提问、思考和判断的能力。
1978年,借着高考恢复的“东风”,我毫无思想准备地进了大学。当时,思想控制有些松动,文化气氛开始活跃起来,加上可以出入平生从未见过的“巨型”图书馆,可读的书陡然增多起来,一时颇有无所适从的感觉。同时,对“文革”的反思、批判和否定也已经开始。这个转变对于比我年长的一代,不外乎是重新肯定他们以前所接受和熟悉的东西;对于比我年纪小的一辈,不啻是遇到了一种新的思想文化气候;但对于我这种在“文革”期间形成基本价值取向和社会政治观念的人来说,却无异于一场“精神毁灭”。我一直相信的观点动摇了,长期积累的知识作废了,一时有点不知自己是谁,看不到将来的前途是什么。再加上那个年龄段还有一些特殊的不安和苦闷,不用说,当时的心境是何等的灰暗和压抑。
于是,我开始读郁达夫的《沉沦》,读鲁迅的《伤逝》、《明天》和《在酒楼上》,读《红楼梦》,读唐宋诗文中那些吟风赏月、惜春悲秋的篇目。对于这类文字所表露的惶惑、忧伤、愤世或无奈之类的“消极”情绪,不仅颇为欣赏,而且深有共鸣。有一个时期,我的思想完全退回到闭锁的私人领地,有意识地回避“公共问题”。“诚知不得吴钩用,何故无端论古今”这样的句子,正是我当时的精神写照。对于社会上正在悄然出现的各种变化,我似乎感觉迟钝,或者干脆懒得去关心。凡是涉及公共性的话题,一般只是被动地援用流行的意识形态话语。那时读书很杂,有时难免囫囵吞枣,但所读的东西大多带有“精神疗伤”的作用。
我个人所经历的“思想解放”,大致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完成的。那个时期是我迄今少有的“自由阅读”的阶段:既不必为功课而读书,也无需为“炮制”论文而读书;读书,读什么书,完全出于一种知识和思想的饥渴,纯粹是为了追求精神的愉悦。在此期间,国内相继发生了几个意义重大的思想文化事件,给我带来了在个人精神的废墟上进行重建的契机。
首先是“青年马克思”的发现和“异化”理论热的兴起。多年以来,在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反复塑造下,马克思形成了一种严肃而凝固的面目;而“青年马克思”的发现,让人看到了马克思的另一种形象,了解到他那些鲜活而富于启发性的思想。特别是他提到的“异化”理论,对于我们理解当时面临的许多社会和人生问题,真有一种“及时雨”的作用。人性的“异化”,政治权力的“异化”,社会理想的“异化”,这些不正是当时让许多人困惑不已的问题吗?在“青年马克思”的指引下,这些难题似乎有了过去想都不敢想的答案。
其次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翻译和出版。这本书当年有几个版本,今天看来其编译都不无瑕疵,但并没有妨碍它发挥巨大的影响力。这本篇幅不大的书,呈现出一种很不一样的思维方式,一种很不一样的研究路径,一种很不一样的理论境界。过去大家所相信的很多理论和观点,在韦伯洞彻而活泼的思想面前,忽然显得那么刻板和苍白。韦伯告诉我们,一种制度,一种行为方式,可能与特定的价值取向和做事习惯相关;要解答一个问题,不是只有一种途径,而是有多种方式。他向我们展示了自由思考的美妙,揭示了“真理”的多样性,以及接近“真理”的多种可能性。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只能用一种方式思考、用一种话语表达的人,韦伯带来的刺激和震撼,是可想而知的。一本小书搅动了一个大国的思想池水,久久未能复归平静。
最后是顾准遗著的整理和发表。在今天看来,顾准的著作存在明显的局限,某些知识有失准确,观点也不乏可商之处;但它的意义主要不在于知识和思想的贡献,而是成了一个独立思考、敢讲真话的象征。在那个思想禁钢、万马齐喑的时代,还有一个大脑在按照自己的方式思考,这种勇气和魄力,不仅值得敬佩,更是反照出许多人当年在思想上、精神上的“奴性”和“媚骨”。读了顾准的书,我的心绪长久难平,由衷感到自由思考和独立判断的可贵。由此联想到,90年代初期学术界争相传阅《陈寅恪的最后20年》,其中似乎也带有反思“文化专制主义”,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意蕴。
在这种思想文化氛围中,我通过读书而寻求自我精神的重建。我逐渐明白,在知识和思想的领域,原来是“条条道路通罗马”;只有思想多样化和“真理”多元化,才能构建一个色彩缤纷、美妙无比的精神世界。在这以后,我的阅读经常陷于另一种“不自由”的困扰中,大部分有效的时间为备课、查资料和写文章所占去。而且,随着专业工作的细化,阅读的目的性越来越强,那种随意读书、忽有所得的痛快,那种偶读好书而“醍醐灌顶”的酣畅,似乎是越来越少了。不过,我始终觉得,在人类向往的各种“自由”当中,自由地追求知识和思想,可能是一件关乎文化命运的大事。一切认真的阅读,任何严肃的提问,所有用心的思考,都有可能成为知识和思想创新的先导。这是我从有限的读书生活中悟到的一个朴实的道理。